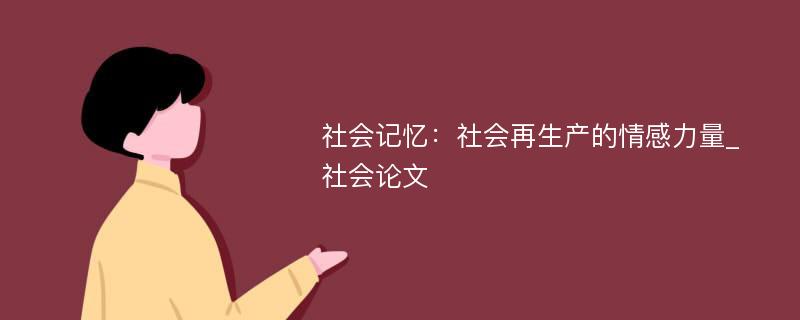
社会记忆———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力量论文,记忆论文,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记忆”往往沦为社会学思想中的细节,不那么引人注目,甚至有时被“遗忘”,尽管这个细节很有社会学的缘分。涂尔干认为各种宗教仪式就是联结集体情感的社会记忆行动;滕尼斯觉得“记忆发挥着感激和忠诚的作用”,因而是联结共同体的纽带;西美尔把感激看做是人类的道德记忆,因而它“本质上更富有实践性和感情冲动性”;布迪厄讨论了身体记忆的问题,父母的文化举止可以为子女所模仿而成为一种惯习,这是社会记忆的传递过程,其结果是形成了身体化文化资本;被舒茨称为“库存知识”的是行动者在过去的生活历史中所形成的主观体验的沉淀物,对这种生活历史的记忆就构成了人的“生平情境”;吉尔兹开创了“深度描写”的显微研究法及求索与经验相近的“地方性知识”,于是普通人的社会记忆才进入社会研究的视野。
上述思想家对社会记忆的图谋由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变为正式的理论话语。保罗·康纳顿在其著作《社会如何记忆》中指出,记忆不仅属于人的个体官能,而且还存在叫做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现象。社会记忆的提出是对传统记忆观的挑战,它认为记忆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而不仅仅是机械地对所获信息进行编码、储存和提取,它更强调记忆过程中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发挥,强调个人记忆的社会制约性。这就突破了传统上把记忆看做是生物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局限性,把记忆视为社会文化活动而非个人自然活动,从而超越个体记忆走向社会记忆。
对社会记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把社会记忆区分为两大类型:认知记忆和情感记忆。记忆既是一种认识活动,更是一种情感行为。一般地把社会记忆看做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在情感社会学的理论中,社会记忆是缺席的。实际上,社会历史不仅是认识研究的对象,也是情感体验的对象。情感社会学关注社会记忆的情感价值,认为社会记忆是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
社会是一代一代变更的,社会记忆使社会历史代代相传。在这一过程中,情感让记忆变得鲜活起来,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不是简单地复制,而是通过波澜起伏的变化方式获得社会的连续性。我们把情感生活当做记忆实践的核心特征。过去回忆的往事不一定是真实的,但一定是人们情感上所怀念的。人的记忆力的秘密何在?就在主要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有情感力量的心灵记事,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不能认为历史档案与社会记忆是同一的,历史档案是死的,是不可更改的认识的积累,社会记忆则是活生生的,它从情感的视角体验过去。
人们的社会情感具有多向度,它不仅重视现实,期待未来,也缅怀过去。过去的生活都存于我们的心中,我们会带着这些往事活下去,无论这些往事是愉快的,还是痛苦的。被时光带来又带走的一切都是造物主写给人间的情书,人们必须像阅读情书一样认真阅读历史,珍惜往事。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群体,都可视为记忆性的载体,都拥有各自共同的文化、道德、宗教、信仰、风俗等历史传统。社会被看成是一个“记忆的共同体”,它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成员不会遗忘其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体现其集体价值观的往事。社会记忆可以整合历史资源,梳理社会文脉;它是保存社会文化的载体,也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纽带。记忆的过程就像酿酒一样,时间越久就越香醇,传统文化由此源远流长。当今,文化怀旧已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潮流。
社会记忆受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状况的制约,是其发展状况的因变量。一个社会记忆什么,遗忘什么,反映了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所怀念的情感寄托对象。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记忆可以分为愉快记忆(memories of cheer)与创伤记忆(memories of trauma)。社会记忆具有一种暧昧的意味。在记忆中,人们能反刍最美好的东西,也可能再现丑恶的东西。一个社会的情感记忆是愉快的还是伤痛的,反映了该社会历史发展的顺利或受挫折的程度。如十年动乱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给我国人民的心灵蒙上了沉重的阴影;人们对“文革”的社会记忆是沉痛的,不堪回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就是一场旨在使中国从十年动乱的毁灭性影响中恢复过来的社会运动。它不仅是人们痛苦记忆的释放过程,而且也是化伤痛记忆为积极建设力量的过程。对于给社会、给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人们不希望再发生;而对于失去或逝去的美好事物,人们则希望恢复或重建。文艺复兴运动就是通过对古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复兴,张扬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禁欲主义,回归自然,回归人性,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同时,也可以被视为是14至16世纪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社会记忆运动。
社会如何保存和重现记忆?社会记忆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学家们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可称作断裂性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记忆并不是现在与过去的连接,而是现在对过去的重构,过去是按照现在的需要,通过社会建构来形塑的,因而也是断裂的。社会记忆与其说是基于过去,不如说是现在生产出来的,过去成为表述人们当下情感的有用的资源,社会记忆就是一种表意主义(presentism)。
另一种观点可称为连续性的,认为过去形塑了我们对现在的理解,而不是相反。正如前后的社会结构之间有着继承性一样,现在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联系。人们不能选择过去,就像每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国家、选择自己的出身一样。如果对过去任意篡改或缺乏坚定的信仰,社会的团结和发展就会受到损害。这种观点更多强调的是记忆的惯性(inertia)。社会历史就如同有着巨大惯性的火车,按照自己的既定轨迹前进,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社会记忆的惯性只不过是对这种社会历史发展惯性的反映。上述两种视角要避免其狭窄和偏执性,相互交叉和融合是很有必要的。社会记忆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是对历史的机械复制,它具有传递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作用。
既然社会记忆有传递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作用,那么对它的激活和保存就显得非常重要。如前所述,社会记忆主要是社会成员对历史的一种情感体验过程,激活社会记忆就是唤起人们的社会情感。这种唤起主要有两类基本途径,一类途径由客观对象(物质文化遗产)唤起,如城市古老的建筑物、文物古迹、人物雕塑、英雄纪念碑和乡村古朴的庄园、古塔寺庙等,它们作为特殊的社会存在物,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留了可能的真实的历史因素。过去的场景或历史的标识,都将引发人们的怀旧体验和“思古幽情”,从中经历非常深刻的情感感受和历史洗礼。
另一种保留和唤起社会记忆的是人们加工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静态的物质文化到流动的非物质文化,需要创造一个历史与现实、时间和空间、心灵与身体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文化氛围,营造这样的氛围,是为了满足人们情感体验的需要。在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这些与四周现代面貌有着巨大反差的历史文化,能使我们游荡的灵魂找到精神的家园。
在历史时间不能倒流的情况下,对于历史文化的情感体验,为人们在动荡不安中寻求永恒和稳定开启了一条情感归属的道路。现代社会理性与技术的发展,将人分裂成了碎片,失去了完满性,人生的发展链条断裂在有限的特定时空,没有了过去,也看不到未来。根源于各种文化遗产的社会记忆能消解在现代性生存境遇中的人的生命和本质被割裂的倾向,激活世俗化的僵硬世界中人的感情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从而超越有限的、被异化了的世界,去把握超时间的无限延展的属人本质。
社会成员对社会历史的情感体验,还可以通过主观头脑保留社会记忆、叙述记忆,以实现情感延续和寄托。在社会研究中,口述史、地方性知识、阐释学等方法就是主观的社会记忆方法。一件件往事就像积淀在人们脑海中的一个个熠熠生辉的亮点,不时地激起人们的回忆,引起人们的思考。主观性的社会记忆强调一种心灵感知性的深层描述及阐释,它是人的心灵与社会历史互动对话的结果,其目的与其说是对往事的客观回忆,不如说是期望达到人们之间的情感理解。社会记忆不是对过去的一种刻板的重现,或对过去的一种惟妙惟肖的描述,它更多地体现出人们的情感价值态度。社会记忆的过程是一个人的情感不断选择的过程,记忆总是嵌入在情感体验的框架中。人的情感意向参与了三重选择: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人们首先注意的是自己情感认同的事物,而把自己不喜欢的人或事排除在视野之外。其次是对这些事物加以理解,理解中既有理性的因素起作用,又掺杂很多情感的因素。经过理解,人们对事物形成一定的价值评价,评价高或评价低的事物往往对人的情感形成很大的震动和冲击,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会形成选择性记忆。社会发生的事千千万万,只有那些深刻影响人们思想、情感的事物才能在其脑海中留下浓墨重彩的画面,才能为人们所记忆,所保留,所珍藏。社会记忆正因它的选择性而闻名。这是因为,社会成员对往事有着不同的解释和情感期待,人们往往根据自身的利益、价值观念和情感偏好来给历史拍照。社会记忆如同相册,只是整合了在许多不同时刻和角度拍摄的即兴之景。人们通过社会记忆对往事进行诠释、再现、重塑和想象,决定了不同时期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和观念,也决定了对于未来的态度和观念。
社会记忆选择的结果使得一些往事对一些人是不可遗忘的,对另一些人又是不可能延续和面对的,这会形成社会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冲突。最明显的一个事例是代际之间的冲突,例如,上辈的忆苦思甜对下辈而言很难引起他们的共鸣,有时甚至使他们产生反感。还有就是恋人们分手后的冲突,提出分手的一方力图忘记过去,而不愿分手的另一方则留恋过去,这导致了前者的记忆倾向于贬低过去,而后者则会竭力美化过去,这两种记忆之间冲突的结果将导致双方情感的最终断裂。从宏观的角度看,新旧社会之间、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之间,全球化过程中各种文明之间都会存在不同的社会记忆的龃龉。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记忆冲突的存在是社会冲突产生的根源之一。例如,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极右势力无耻抵赖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言论甚嚣尘上,对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过的中国人民的感情是极大的伤害,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当然每个国家的人都希望以自己国家的历史为荣,希望自己国家的历史辉煌灿烂。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明智的人会选择从自己国家的负面历史中吸取教训。记忆不是为了播种仇恨。不种植仇恨,却应该记取和吸取历史教训。
社会记忆的冲突说明,社会记忆具有非中立性,社会在热烈追忆某些往事的同时必然冷漠某些往事。社会记忆的过程同时是一个社会忘却的过程,它要记住某些事则是以忘记某些事为前提的。尽管主观的社会记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社会现实,但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任何记忆都有着社会的框架,文化的背景。社会或者有意识地抑制和禁止某种记忆,或者有意识地提倡和张扬某种记忆,“记忆”既可以被有意删除,又可故意保留,比如某种仪式,某种节庆,都可能是一场有组织的使现存秩序合法化的记忆活动。社会记忆并非铁板一块,不可能形成统一的社会记忆,任何社会记忆的形成都是千差万别的记忆相互磨合的结果。
对于社会记忆,我们需要搞清楚“这是谁的记忆”,“记忆什么”以及“记忆如何被制造和利用”等基本问题。任何社会都存在着“记忆”和“反记忆”的斗争。“反记忆(Counter-Memory)”是福柯提出的概念,指那些挑战于主流记忆的记忆。因此争夺记忆反映了一种权力关系,对记忆的解释和支配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处于下层社会各种集体记忆很难存活下去,它会受到来自统治阶层的压制。然而,非主流的另类记忆具有一定的批判价值,是底层社会人们争夺话语霸权的表现。它的存在,为社会记忆增光添彩,使社会记忆变得更为真实,更贴近本色。也许,我们可以把社会记忆比喻为一条绵延奔腾的河,它存在于不同的记忆流动中。非主流记忆就像记忆河床下面的深流,不时搅动着浮在河床上的记忆主流,如此,社会记忆之河才得以鲜活。通过建立一种关于社会历史的记忆方式,可以让历史成为如同河水一样的活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入现今的社会发展中去,让历史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复活。同时,人们的现实生活也创造社会记忆,社会记忆中记载着普通人的甜酸苦辣,正因为如此,非主流的记忆才显得纯粹和生动。
虽然世事多变,时过境迁,但以往的故事都已经深深地融入人们的记忆深处,通过种种文化符号传递和保留下来。社会记忆的传递过程是社会化的过程,社会记忆是一种社会化的方式。不同层次的群体,如家庭、地区、阶级、民族乃至人类整体,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保留着他们关于过去生活的社会记忆,这实际上就保留着他们认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这是维系共同体情感的深厚凝聚力。一个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同一个只有怀旧的民族一样是没有进步和希望的。在真实历史因素缺席的地方,则通过社会记忆的暗示或公示,提示历史的可能性。例如,很多国家都拥有自己的“烈士纪念日”。通过这些纪念,感知并铭记那些于危难中撑起民族脊梁的先辈,进而担当起自己对国家的道义和责任。
无论社会如何日新月异,将来如何发展,人们仍然需要社会记忆,这是因为人们需要不断与过去产生跨越时空的对话,以加强和巩固人们在情感上与这个社会的联系。这种不断进行的对话和互动,使每个社会呈现出自己独特的情感轨迹和心理轨迹,成为社会文化的积淀。社会的生活质量不仅是物质生活的质量,同时还包括社会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归属。
一个有深度的社会是一个有着自己社会记忆的社会。社会记忆给社会打下的深深烙印,在文化上影响着这个社会,影响着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居民,它还将影响这个社会的未来走向。哲学大师培根对于学科做过这样的分类:“从这三种源泉——记忆、想象、理性——产生了三个产品:历史、诗和哲学。”我们可对培根的学科分类做个实践性补充,这个补充就是,社会记忆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生产力,不仅生产社会历史,而且生产社会的现实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