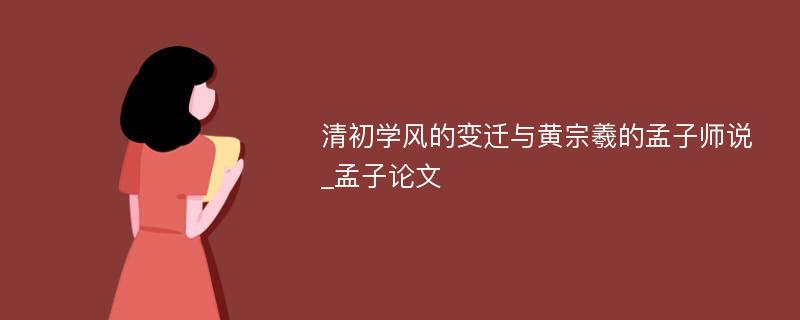
清初学风流变与黄宗羲的《孟子师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清初论文,学风论文,师说论文,黄宗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1-0084-04
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识的意义从属于道德修养或政治需要。清初以降,这种知识和道德的关系出现了变化,清初孟学研究的种种特点便是明证。
清初思想界针对晚明心学一派奢谈心性、空疏悬思,无济民生而起,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宋明理学展开反思和批判,尤其对以陆王为代表的谈心说性的形上思辨学风大加鞭挞,清初学术风气暗中转变。清初学人普遍认为理学家对经典的解释受佛道二氏的浸染而违背了孔孟学说的本质,力图通过文字、训诂、考据的汉学方法来重新阐释经学原典,学界重实学、重考据、重践履的实学之风由此兴起,清初孟学研究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黄宗羲的《孟子师说》即其中之典型。梨洲在《孟子师说》的题词中明确提出其著述要旨[1],以“师说”的形式从分析孟子的思想入手直斥当时学风,在继承蕺山的同时又与时代思潮密切联系,意在别开生面倡导清新的治学风气[2],梨洲的学术思想表现出继承与创新是清初学风流变的产物,而其中更蕴涵着传统知识与道德关系的深刻变化,成为乾隆年间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阐发重知思想之先导。
一、以习之“实”补理学性论之“虚”
人性善恶是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之精粹,晚明王学便重在阐发孟子性善之旨。清初,黄宗羲作为宋明理学之殿军[3],借重新诠释孟子性善论表达自己独特的性论观[4],而这其中隐含着传统知识与道德关系变化之先机。
清初学人对孟子性善论的诠释各具特色,然总体上是在反思理学性论观,并从多角度对理学二元性论提出批判,如颜元认为“人之性命、气质虽各有等差,而俱是此善”,用彻底的性善论否定理学性论观[5]。梨洲亦不满宋明儒“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性论观,试图直承孔孟性论,秉持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论说,明确指出“气质之性”便是“习”。梨洲认为先儒对“习”字的理解过于狭义,其实“习”不仅包括“先天之习”,即人“在胎之时,已有习矣”,也包含“坠地已后之习”[1](138),即后天之习。梨洲把习区分为先天、后天之论,同朱熹分性为天命、气质的论说可谓异曲同工。如果说朱熹的二元性论旨在消解人性善恶之间的矛盾,那么梨洲的二元习论则重在强调后天之习对于人性善的重要性。
梨洲之师蕺山尝云:“古人言性,皆主后天,毕竟离气质无所谓性者……予谓水,心也,而清者,其性也,有时而浊,未离乎清也,相近者也。其终锢于浊,则习之罪也。”[1](77-78)蕺山显然注意到习对人性的重要性。这就大不同于陆王一派在人性论问题上忽视外在的影响因素,一味求本心之善的论调。蕺山认为人性存在着善与恶之间的转化,这正是对理学性论的修正。然须知人性善、恶之间的转化,正是荀子性恶论中“化性起伪”之旨意所在。钱穆认为,乾隆年间戴震、焦循等移用荀子之言而论孟子,是因为当时学人本致力于荀子而“不觉其言思之染涉者深也”[6]。从清初学风流变而言,钱穆所述乾隆年间戴震、焦循的此种情形正是肇始于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这一“阳孟阴荀”之思想伏流,而此亦成为传统知识游离于道德之外的隐性表现。荀子重客观、重知识的积累,孟子重心性、重道德的内修,这在学界是不言自明的共识。
梨洲发展了蕺山重“习”的性论观,并以之为诠解孟子性论的关键。梨洲曰:“‘湍水’……言其无善无不善也,东流西流,只是为习所使。晦翁谓其善恶混,亦非东流西流;告子兼善恶以言习,搏之激之。孟子单以不善言习,其善者即从习来,亦是导其性之固有耳。”[1](133)梨州所本《孟子·告子章句上》①。
孟子强调的是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以驳斥告子所谓无善无不善,孟子并没有提及“习”字,只是说“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而已,并解释说这并不是水之性,而是“其势则然也”。也就是说,外在环境使得“水”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向下”之“性”。梨洲却用一个“习”字来替代孟子所言“搏”、“激”,强调后天践履对道德进修的重要性。这种思想透露出梨洲性论中强调“习”的特识,契合清初实学之风,然我们从《孟子》原文中丝毫读不出孟子以“习”说教的意味,是故梨洲此识不能不视为是对孟子思想的一种“曲解”。
清初思想界对孟子道德人性论作出了符合时代需求的新诠释,改变了从先验角度对性善论的认识,主张在人性的形成过程中分析人之善性,从“实”处着眼,重视外在知识积累及实践,把重实学、倡实践之实学精神贯穿于具有思辨特点的人性论讨论。从方法论的层面看,这种转变从形下具体的经验层面消解了理学形上思辨的超越意义,开启了清代重视认识论、知识论的思想先河。
二、将“学”与“良知良能”并重
理学所见孟子精义唯在性善论与“良知良能”,陆王一派认为“良知良能”是人心自足的基础。然人心能否自足,人之道德是否具有自修的能力,这在明清鼎革的时代成为学界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在清初实学之风的影响下,对道德善恶的探究更多地考量外在因素的作用,梨洲将“学”与“良知良能”并重是为例证。
梨洲从“良知良能”与“学”之间的关系着眼,重新阐释“良知良能”,旨在把陆王的“空言”拉回到具体、切实、可以为人把握和操持的层面,以切合清初实学之风。他说,“其人力可学而能者,较天成分数,万不及一,故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假使人性本无此道,虽学亦不能矣”,“由学而能者,万不敌天生之一;由不学而坏者,一丧其天生之万。故学为要也”[1](78)。梨洲认为,人通过后天学习掌握的能力与其先天具有的能力相比是“万不及一”,这当然是陆王哲学的基本认识和判断。然“学”字所指,是对外在于人的知识的获取途径,是一个“由外而内”的知识获得过程,是相较于“良知良能”所指示的“由内而外”过程的逆反。此论中尤可注意的是梨洲对后天学习的重视,他认为由“不学”而丧失的是“天生之万”。梨洲在“学而后知”、“学而后能”的基础上,强调“良知良能”是德性的基础,并从“不学而坏”的角度发出警示,强调后天知识学习的重要性。而众所周知,重视“学”、“习”,重视通过学习、积累知识进而增进德性的观点是程朱在治学认识论上与陆王的重要分歧所在。
明末清初,阳明后学的空疏学风为世人批判和摒弃,陆王偏重心性之论的形上思辨学风,因其对外在知识学习的忽略受到当时实学思潮的挑战,梨洲深感重实学、倡实行的时代之潮对王学治学方法论的压力,但又不愿放弃陆王建立在孟子“良知良能”基础上的“大本”之说,于是借孟子发论,采朱学之“实”而补陆王之“虚”,用强调“学”而为“良知良能”的玄虚之言增添进“实学”与“重知”的色彩,把朱熹和阳明原本几乎对立的概念硬是拼到一处,这自然带有挽救明末心学走向只重“本体”而忽略“工夫”的空疏学风之意。在清初理学清算大潮中,梨洲强调人先天具有的德性,同时突出客观之“学”对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以使其遵奉的阳明心学适应时代思潮之发展,虽仍将知识之积累与道德之增进捆绑在一起,但知识“独立”之势已现其胎芽。
但显而易见,此种诠释存在着对孟子思想的曲解。正如梨洲自己认识到的那样,“四子之义平易近人,非难知难尽也”。孟子“良知良能”本指“不学而能者”、“不虑而知者”,“良知良能”与“学”在孟子思想中本无关涉,梨洲则为“良知良能”注入“学”的因子,把孟子打扮成一个“道问学”的君子,凸显其尊重知识的形象。梨洲对孟子思想的阐释颇显其对心学修正和补充的良苦用心,而又见时代学风已不得不转而走向趋“实”之途。
钱穆认为,梨洲与阳明心学者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多讲本体,而梨洲更注重工夫[6](29)。孟子的性善论和“良知良能”说以“养气”论为补充,梨洲从“习”、“学”的角度阐释孟子性善论与“良知良能”说,那么对于孟子的工夫论——“养气”说,梨洲又是怎样理解的呢?
人之善根,即“良知良能”须通过“养”来扩充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善养浩然之气”是孟子思想中的重要一环。毋庸置疑,陆王把孟子“养气”说提升为“养心”说,更清晰地道出了孟子“养气”说的核心和关键。然时至清初,梨洲不满陆王“养心”之说,重提孟子的“养气”说,他认为,“养气即是养心,然言养心犹觉难把捉,言养气则动作威仪,旦昼呼吸,实可持循也”[1](60)。
在清初学界的大反思中,学人对阳明后学空谈心性的学风大加批判,他们通过检讨宋明儒治学的得失,试图返回儒学原典,从源头话语入手对儒学经典重新阐释,“弃虚蹈实”成为当时社会的学术呼唤。梨洲正是在蹈实之风的影响下,把陆王的“养心说”还原为孟子的“养气说”。梨洲认为,“养气”之于“养心”更接近物质的层面,所谓“养气则动作威仪,旦昼呼吸,实可持循”,也更易把握。梨洲对孟子工夫论的阐释暗合着清初社会重实践、重实行、倡实学之时代思潮。
三、对“人心道心”之论的检讨
如果说,梨洲对朱熹之学注重“习”、“学”的采纳是其所处时代“弃虚蹈实”学风的必然表现,那么,梨洲对于朱熹一派的批判则是理学清算之时代精神的鲜明写照,其批判直指“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原则。
在程朱理学中,“道心”即指天理,“人心”则是人欲。梨洲继承蕺山思想,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一心,他说孟子但言“求放心”,而不言“求理义之心”,言“失其本心”,而不言“失其理义之心”,“孟子之言明白如此,奈何后之儒者,误解人心、道心歧而二之?……道心即人心之本心,唯其微也故危”,“盖此心当恻隐时自能恻隐,当羞恶时自能羞恶,浑然不著于人为”[1](141)。梨洲强调“道心即人心之本心”,否定人心之外别有道心。
梨洲曾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作《序》,亦涉及人心、道心之论,其文颇可玩味。《序》中写道,“忆吾友朱康流谓余曰:‘从来讲学者未有不渊源于危微精一之旨,若无《大禹谟》则理学绝矣,可伪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节目。‘允执厥中’,本之《论语》。‘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论语》曰:‘舜亦以命禹’,则舜之所言者即尧之所言也。若于尧之言有所增加,《论语》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恶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恶;惟微者,此理散殊无有形象,必择之至精而后始与我一,故矫饰之论生焉。后之儒者于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觉,理则在于天地万物,穷天地万物之理合于我心之知觉而后谓之道。皆为人心道心之说所误也。夫人只有人心,当恻隐自能恻隐,当羞恶自能羞恶,辞让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无有移换,便是允执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则此十六字其为理学之蠹甚矣!康流不以为然。呜呼!得吾说而存之其于百诗之证,未必无当也。”[7]
这里,梨洲拈出了一个“人心”,认为“虞廷心传”在“人心”旁边又设一“道心”,殊为多事。梨洲用“当恻隐自能恻隐,当羞恶自能羞恶”来批判后儒“惟精惟一”的“矫饰之论”,这是用“践履”之“行”来批驳“务虚”之“知”;用形下之“器”来排斥形上之“道”。此正是清初“弃虚蹈实”学风的应有之义。梨洲与朱康流辩,主观愿望是为了捍卫理学,然而,殊不知理学之论人心,恰恰是借助于论“道心”之“微”,也就是将形下践履安顿于形上之思的基础之上,这才得以使理学的理论体系“上”“下”兼顾,圆融无碍。如若抽去了“道心”,抽去了道心之“微”,从方法论上说,实乃抽去了理学之所以为理学的精神内核,不啻是对理学的釜底抽薪的破坏与打击。值此求“器”不求“道”、重“行”不重“知”、取“形下”而弃“形上”的学风转轨的时代,理学既遭清算,学人遂不免将理学分为两橛,取其“致用”(形下践履之用)而弃其“无用”(形上哲学之思),是故有梨洲这种既想捍卫理学,却又不自觉地破坏了理学的矛盾之举。于梨洲此举中最可体味出学风将变而未变之消息,而在学风转变之际,对客观的肯定和重视中又透露出知识与道德的关系已逸出传统思想的樊篱。
梨洲“人心道心”之论以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为批判对象,从理论上否认程朱一派天理的存在,而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从反理学、破除“天理”的统治局面、肯定人之情欲的合理性角度而言,梨洲的《孟子师说》实是乾嘉年间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的“先导”。钱穆就认为梨洲是从重视“情”的角度论及性善,而“其后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即力阐此义。二说虽造语有异,而论旨则一”[6](26)。
晚明王学在清初理学清算运动中备受批判,学界大有“由王返朱”之态势。梨洲的学术根底在王学,《孟子师说》的主旨仍是阐发阳明“良知”之论。因此,梨洲置身反理学的浪潮中却并没有一味地否定王学,也没有盲目地倡言朱学,而是针对王学末流“束书不观”、“空言心性”的特点,对理学学风表现出强烈不满并试图予以纠正,在涉及具体问题的阐释方面对阳明学术路径多有修正。
梨洲的《孟子师说》注重挖掘孟子的实学思想,突出孟子思想中的践履成分,在德性修养和治学中重视外在知识的学习,试图以朱学之“实”来弥补王学末流的玄虚之弊。钱穆曾说:“梨洲论学,两面逼入。其重实践,重工夫,重行,既不蹈悬空探索本体、坠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倡狂一路,专任自然,即认一点虚灵知觉之气,从横放任以为道也。”[6](28)因此,《孟子师说》体现了黄宗羲学术思想的时代特征,即顺应清初实学思潮,议论多切诸实际而不为空谈,着意开创一种面向社会实践、强调践履、重视实学的新学风,从而把明末清初的实学之风逐步推向高潮。
清初学人已经深刻认识到:不结合社会实践的道德理想只能流于空谈,而缺乏道德理想指引的社会实践则可能动力不足且具有盲目性。如是,清初学人对孟子思想的种种“曲解”正是极富时代特征的烙印,因为在他们看来,外在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某种程度上就是内在道德之善的积淀。清儒将道德与知识、理想与现实相结合恰恰表明清初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转轨路径,清学之义理也在传统与时代的纠结和矛盾中发生裂变,最终脱胎而出,成为传统学术向“前近代”学术转型的关键一环,而传统思想中知识也逐渐脱离道德权威的钳制而具有了独立的、前近代的意义。
注释:
①《孟子》原文:“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标签:孟子论文; 黄宗羲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国学论文; 人性论文; 哲学家论文; 理学论文; 经世致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