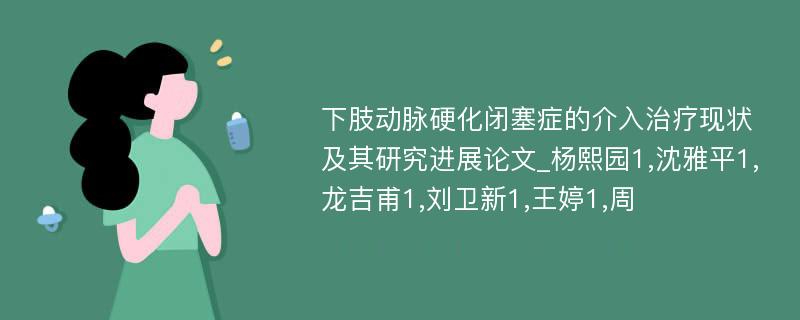
杨熙园1 沈雅平1 龙吉甫1 刘卫新1 王婷1 周石2(通讯作者)
【摘 要】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由于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引起下肢动脉狭窄、闭塞,进而导致肢体慢性缺血。随着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的老龄化及饮食结构改变,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病率逐年提高。近年来随着介入新器材的不断面世和基因药物临床研究的出现,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接受动脉腔内介入治疗的比例逐渐增加,患者的保肢率明显提高[1]。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主要累及髂、股、胭动脉,目前随着TASC II共识文件的出现,有助于选择治疗方案,越来越多的患者接受腔内介入治疗[2]。介入治疗具有微创、可重复、高效等优点,可显著降低其对患者机体的刺激,减少对机体创伤,安全性高。随着对介入治疗方面的深入研究,其运用价值能得到了明显提升。
【关键词】 下肢动脉闭塞症; 介入腔内治疗; 疗效; 保肢率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atherosclerosis obliterans,ASO),是指由下肢动脉发生粥样硬化性改变导致动脉管腔狭窄或闭塞引起肢体缺血临床表现的慢性疾病,常为全身动脉硬化性病变在局部肢体的表现[3]。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属于退行性病变,主要发生于大、中型动脉中,临床表现为纤维基质、细胞、脂质以及组织碎片异常沉积[4] ,动脉内膜或中层中出现增生过程的病理变化,而周围血管疾病中,绝大多数动脉的狭窄、闭塞或者动脉瘤是由动脉硬化造成的[5]。主要病因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吸烟等,随着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病率逐年提高,对于此类患者治疗的重点是改善肢体血供以改善缺血症状、提高保肢率及降低截止率。近年来介入治疗因其微创、高效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6-7]。在过去几年里,国内外学者对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机制及治疗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尤以血管腔内介入治疗的研究最为突出,本文就国内外对该方面的研究综述如下: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分级及分类
2007 年环大西洋协作组织(trans-Atlantic inter-society consensus,TASC)出台新的周围动脉疾病治疗指南(TASCⅡ)[8]。 根据TASC分级标准将股腘动脉病变分为A、B、C、D 4级:A级单一狭窄性病变≤10cm;单一闭塞性病变≤ 5cm;B级复合病变(狭窄或闭塞),每处≤ 5cm,单一狭窄或闭塞病变≤15cm,未累及膝下腘动脉,单个或复合病变,没有连续的胫动脉提供远端灌注,严重的钙化性闭塞病变≤5cm;单一的腘动脉狭窄;C级多处狭窄或闭塞,无论有无严重钙化,总长度>15cm,两次腔内治疗后,需进一步处理的狭窄或闭塞病变;D级慢性全程股总动脉或股浅动脉闭塞,包括腘动脉,病变>20cm,慢性全程腘动脉和胫腓干三分叉近端;对临床治疗及预后具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诊断标准
目前国内对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主要诊断标准为:(1) 年龄大于40岁; (2) 有吸烟、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等高危因素;(3) 符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临床表现; (4)缺血肢体远端动脉搏动减弱或消失;(5) 踝/肱指数(Ankle Brachial Index,ABI)≤0.9;(6)影像学检查证据:血管彩超、CT血管造影、MR血管造影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等影像学检查显示相应动脉的狭窄或闭塞等;符合上述诊断标准前四条可以做出下肢ASO的临床诊断。ABI和彩色超声可以判断下肢的缺血程度,对于是否将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DSA)作为诊断金标准讨论较多,2015版中国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诊治指南认为目前明确ASO患者动脉病变的金标准仍是DSA[9]。
发病相关危险因素分析下肢ASO的主要病因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男性发病率略高于女性。
1.吸烟
吸烟和下肢ASO的发生明显相关。吸烟可以减少运动试验时的间歇性跛行距离,增加外周动脉缺血、心肌梗死、卒中和死亡的危险,增加CLI和截肢的危险。疾病的严重程度和吸烟量呈正相关。
2.糖尿病
糖尿病使本病发生率增加2?4倍,女性糖尿病患者发生本病的风险是男性患者的2?3倍。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每增加1%,相应ASO风险增加26%。糖尿病患者发生严重下肢动脉缺血的危险高于非糖尿病患者,截肢率较之高7?15倍。
3.高血压
高血压是下肢ASO的主要危险因子之一,收缩期血压相关性更高,危险性相对弱于吸烟和糖尿病。
4.高脂血症
高脂血症使下肢ASO的患病率增高,出现间歇性跛行的危险增加。
5.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相对于普通人群,ASO患者中高同型半胱氨酸的合并概率明显增高。同型半胱氨酸是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约30%的ASO患者存在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6.慢性肾功能不全
有研究表明慢性肾功能不全与AS0相关,对于绝经后女性,慢性肾功能不全是AS0的独立危险预测因素。
7.炎性指标
动脉粥样硬化是涉及多种炎性细胞和因子的慢性炎性反应。与同龄无症状人群相比,炎性指标(如C反应蛋白)增高的人群5年后发展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概率明显增高。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介入治疗的发展历史
1964 年美国医生Dotter及Jukins采用同轴导管血管成形技术性血管扩张,完成首例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PTA) 标志着腔内技术治疗血管疾病的开始;1974 年 Andreas Gruntzig 发明了由聚氯乙烯材料制成的双腔球囊扩张导管行动脉扩张成形术,取得成功,因其具有微创性和可重复操作性,获得了迅速发展,开创了动脉闭塞性疾病腔内治疗的先河。1985年Palmaz报道了一种球囊扩张式钢丝网状编织血管内支架并进行了动物实验,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1983至1989 年 Dotter、Palmaz、Gianturco等相继研制多种支架,使 PTA 技术逐渐走向成熟;1987 年英国的 Leicester、Bolia 等在治疗一月国动脉长段闭塞的患者时,意外造成了一条内膜下的新腔,从而形成了后来的内膜下血管成形术(subintimalangioplasty, SIA);吴泽涛等[10]采用SIA进行经皮腔内血管球囊扩张(PTA)+内支架置入,结果显示全组治疗成功率83.3%(10/12),8例行SIA支架置入后,随访(3-36)个月,血流均保持通畅; SIA在髂、股动脉慢性长段硬化性闭塞的PTA+内支架置入治疗中,可显著提高成功率,减少并发症、是安全有效的方法。随着介入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器材的不断改进,尤其是下肢专用长球囊和支架的应用,PTA 正快速地替代外科手术治疗;李炜淼[11]进行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显示应用长球囊治疗组的患者肢术后3月、6月、12月及24月的累积初次通畅率分别为:91.35%、80.60%、73.11%和73.11%。术后1年及2年的肢体保全率均为100%;江娜等[12]对32例共35条下肢膝下动脉硬化闭塞性病变患者采用长球囊成形术治疗,结果成功治疗了29条下肢,技术成功率达82.9%。除1例于术后10天行踝上截肢术外,其余病例临床症状均有明显改善,足部溃疡或坏疽经换药等处理逐渐结痂或将坏疽足趾截除而愈合。术后25例随访了3~34个月,先后有12例复发,9例行二次介入手术重新获得好转,仅1例转外科行截足术,无死亡病例,使用长球囊行PTA治疗膝下动脉硬化闭塞性疾病是安全、有效的。近年来兴起了通过自体干细胞移植的治疗方法,是一种通过治疗性血管生成方法恢复患肢血供的安全有效的治疗新手段,不仅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也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的希望[13]。
治 疗
动脉硬化性闭塞症是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在肢体局部表现,是全身性动脉内膜及其中层呈退行性、增生性改变,使血管壁变硬缩小、失去弹性,从而继发血栓形成致使远端血流量进行性减少或中断。综合治疗方式包括消除危险因素的常规治疗、运动、药物治疗、血管腔内治疗、手术治疗以及试用基因治疗等多种方式。在决定治疗方案时应结合病人的TASC分级级别、临床症状、全身情况等多方面因素抉择。症状较轻的病人可选药物治疗,症状较重的间歇性跛行、静息痛、溃疡或坏疽等重症缺血患者应以血管腔内治疗或手术治疗为主。内科的药物治疗,外科的血管旁旁移植,超声消融等,治疗效果欠佳,最终导致截肢及甚至危及生命;目前认为血管重建是治疗重症下肢缺血的最佳方案[14]。
随着介入技术的飞速发展,介入设备、器械及操作不断改进,减小了对血管内皮的损伤,提高了手术成功率,降低患者创伤,减少了术后再狭窄的发生,通过再建患肢血液循环,使保肢率明显提高,截肢平面明显降低。国外相关数据统计指出下肢动脉闭塞的腔内治疗具有较好的疗效,其中球囊扩张对于狭窄性病变的3年通畅率为61%,闭塞性病交48%,重症狭窄病变43%和重症闭塞性病变30%;而支架植入的3年通畅率为63%~66%[15]。国内也相关报道显示PTA和PTAS术后6、12、36、60个月的通畅率分别为:髂动脉为:98.53%、92.65%、91.18%、89.71%;股浅动脉中、上2/3段阻塞为:91.67%、86.67%、81.67%、73.33%;股浅动脉下1/3段阻塞为:85.37%、78.05%、68.29%、56.09%[16]。
1.介入治疗的临床指征
1.1 临床表现
早期可无明显症状,或仅有轻微不适,如发凉、麻木等,之后逐渐出现间歇性跛行症状,这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特征性症状。表现为行走一段距离后,出现患肢乏力、疲劳、酸痛,经过休息一段时间,休息后症状可完全缓解,再次行走后症状复现,每次行走的距离、休息的时间一般较为固定;另外,酸痛的部位与血管病变的位置存在相关性。随病情进一步发展出现静息痛,即在患者休息时就存在肢端疼痛,平卧及夜间休息时容易发生。如缺血进一步加重引起肢体溃烂、坏疽甚至危及生命。严重下肢缺血是下肢动脉疾病最严重的临床表现,特点为由动脉闭塞引起的缺血性静息痛、溃疡或坏疽。
1.2 DSA动脉造影
DSA进行下肢动脉造影能够清晰显示下肢静脉病变,对于诊断下肢动脉病变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与应用价值。清楚地显示动脉血管的主干、分支、走行、分布及异常分流,病变的大小、形态、解剖部位、供血动脉的起源数目,具有直观、可靠等优点,对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治疗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1.3适应症选择
除患有原发性出血性疾病或近期内(一般 6 个月内)有并发出血性的疾病外,各级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均为介入适应症。
1.4 禁忌症
①对造影剂过敏者;②严重高血压,舒张压大于110mmHg(14.66kPa)者;③严重肝、肾功能损害者;④近期有心肌梗塞和严重心肌疾患、心力衰竭及心律不齐者;⑤甲状腺机能亢进及糖尿病未控制者。
1.5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血管特点及术前评估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全身性疾患,好发于大中型动脉,亦可累及股、腘动脉等处。血管特点:病变血管内膜增生、粥样斑块形成,动脉中层强力纤维往往发生退行性改变,而动脉外膜可保持完整;病变常呈节段性或弥漫分布,多好发于动脉分叉起始部的后壁及动脉主干弯曲或受压的部位;动脉狭窄常成缓慢进行性发展,导致远端肢体组织成慢性缺血,而当粥样斑块破溃或脱落,基底粗糙造成血小板及纤维蛋白物质的停滞粘附,继发血栓使动脉管腔闭塞,甚至血栓可向动脉远、进端蔓延,使肢体缺血加重造成缺血坏死。
通过介入治疗(PTA)重建肢体远端血管,使得下肢血管病变的治疗从根本上得以改善,但是其远期疗效仍待进一步观察,在介入治疗手术前,正确地判定动脉闭塞的部位、程度、范围及远端侧支循环情况,从而选择适宜的手术适应证,对于保障术中、术后动脉血管再通率、远期疗效及预后至关重要。
术前对于动脉血管病变程度的判定,目前公认的有效方法是ABI、双下肢动脉血管超声、螺旋CT血管成像(CTA)、核磁共振血流成像(MRA)或 DSA,根据下肢ABI、动脉血管超声、CTA 、MRA或DSA血管造影的情况,并结合患者TASC分级级别、有无间歇性跛行或静息痛,选择介入治疗的方法。
血管腔内治疗进展
近年来,血管腔内技术得到迅猛发展,并逐渐成为治疗下肢动脉闭塞性疾病的主流治疗手段[17]。新的腔内技术和器械的临床应用,使手术适应证也进一步扩大,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征的血管腔内治疗的范围几乎涵盖自主髂动脉至小腿的整个下肢动脉系统。
1.血管腔内成形术(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PTA)
传统血管外科手术主要通过人工血管或自体血管旁路移植,常因病变广泛或狭窄程度重而疗效不佳,经皮血管腔内介入治疗兼有微创及并发症少的优点,其保肢率甚至优于外科血管移植手术[18]。血管腔内成形术具有创伤小、不损伤血管周围组织、术中仅需局麻、可重复操作等优势,有望成为下肢动脉缺血的首选治疗方法。经皮球囊扩张成形术治疗下肢动脉流出道闭塞性硬化症的入选标准[19]:下肢动脉MRI 检查示治疗股总动脉、侧髂动脉、股浅动脉等狭窄度<50%;患者间歇性跛行距离<100 m;胫前动脉、胫后动脉单节段性闭塞长度<4cm 或单一流出道动脉多节段性闭塞总长度不足动脉长度一半。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下肢动脉血管流出道病变具有多节段、多条血管狭窄或闭塞的特点,同时由于球囊规格等器材的限制,常规PTA治疗疗效不佳或难以从技术上实现。目前高顺应性长球囊使用价值的不断在临床推广,受到愈来愈多的介入医生的亲睐,目前临床最常用的Amphirion 球囊(Invatec 公司) 和Savvy Long 球囊(Cordis 公司),因其囊壁薄、轴长、压力低、亲水性及渐细的设计成为膝下动脉专用球囊的代表,完全可满足目前长球囊低压、长段、顺应性好等膝下动脉的治疗要求。由于长段血管同时扩张,血管壁受力均匀,扩张后管腔相对规则,不易出现斑块脱落或动脉夹层等并发症,因此可降低术中或术后急性闭塞等并发症 。蒋天鹏等[20]采用SAVVY球囊行下肢动脉流出道血管PTA的15例共22条患肢,其结果显示:手术技术成功率90.9%(20/22)。术中未出现与球囊结构相关的并发症。术后7d ABI在l4条血管中升高超过0.5,3条超过0.3,3条超过0.1。随访时间平均7.2个月,有5例复发不同程度静息痛。术后7d ABI平均为0.74,1个月平均为0.66,使用SAVVY长球囊行PTA治疗膝下动脉缺血性病变安全、有效,短期疗效肯定。Romiti 等[21]的相关研究分析显示,球囊扩张血管成形术1、6 个月及1、2、3 年的一期通畅率分别为77.4%、65.0%、58.1%、51.3%、48.6%, 二期通畅率分别为83.3%、73.8%、68.2%、63.5%、62.9%,均低于外科旁路手术组,但保肢率与外科旁路手术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TA 后的再狭窄是导致膝下动脉闭塞腔内治疗远期通畅率低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目前在植入支架等方面有许多新的尝试,其效果尚存在争议,需要大宗样本的长期随访证实。但是再狭窄不能成为PTA 在膝下动脉病变中应用受限的理由,PTA 术后远端组织可迅速恢复供血,防止组织坏死; 另外,PTA 后的再狭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再狭窄的逐渐形成,肢体的侧支循环也随之逐渐代偿建立,因此经过PTA 治疗后保肢率远大于血管通畅率;同时,PTA 的可重复操作性,有助于提高远期血管通畅率。
在PTA过程中可能导致血管夹层撕裂和弹性回缩,可通过血管内支架成形术( PTAS)植入血管支架挤压斑块和压迫管壁,克服了PTA 的主要缺陷,是一种新的腔内治疗手段。支架主要应用于以下情况[22]:①PTA不易成功者;②PTA技术成功后易发生再狭窄的部位和病变;③PTA后出现并发症者,乳内膜剥离、严重血管痉蛮导致血管闭塞等;④PTA再狭窄的再次治疗;⑤动脉粥样硬化有溃疡形成或钙化;⑥长段狭窄或闭塞;诸锡奇等[23] 探讨经PTA联合支架植入术( PTAS)治疗老年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ASO) 的临床疗效显示:行PTAS 手术后,髂动脉的成功率为100%,股腘动脉的成功率为95.24%;术后1 个月,患者的踝肱指数由术前的(0.35±0.11) 增加至术后的(0.95±0.09) ,间歇性跛行距离由术前的( 117.3±29.9) m 增加至术后的(518.4±122.7) m,手术前、后比较差异显著(P<0.05) ;术后2 年髂动脉的血管通畅率为91.67%,股腘动脉的血管通畅率为80.95%。Schillinger等[24]观察股浅动脉单纯PTA和自膨支架置入两组的疗效, 随访1a 发现单纯PTA 组术后再狭窄率明显高于自膨支架置入组(P<0.01),认为支架置入的效果明显优于单纯PTA。但亦有不同观点,最近Dorrucci 的荟萃分析表明:PTA后1、2、3、4 年的原发通畅率分别为58%、51%、47%、40%,而球囊扩张支架置人后1、2、3、4 年的原发通畅率为65%、55%、58%、52%,与PTA相比并无优势[25]。且因支架置入仍然存在术后再狭窄的问题,故对于膝下小动脉病变的支架置入应持慎重态度,支架内再狭窄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个体差异、支架选择、血管直径、术后原发疾病的控制等均是影响因素,对此尚缺乏量化研究。综上所述,目前尚缺乏足够支持膝下动脉放置支架的资料,仅认为支架成形是PTA失败后的补救措施[26]。
2.内膜下血管成形术
1989 年[27] 首次报道应用内膜下血管成形术(subintimal angioplasty,SIA)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至今其在临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特别是治疗髂动脉及股浅动脉的效果较理想。即在长段动脉闭塞或动脉严重钙化无法从动脉真腔完成腔内手术时,使用带导丝的导管,于动脉闭塞部位近端动脉腔处进入内膜下,制造动脉夹层,并逐渐推进至动脉闭塞远端,再进入动脉真腔,将动脉夹层形成新的“动脉管腔”,经导丝导入球囊导管行PTA 治疗,以扩大这一新的血流通道,依扩张后动脉造影情况决定是否置入血管支架。据相关文献报道,李大林等[28]采用内膜下成形术治疗长段髂动脉、股浅动脉闭塞患者, 对手术成功率、并发症发生率、初始通畅率、后期随访通畅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43 例SIA 成功41 例, 技术成功率95.3% , 术后6、12、24、36 个月的初始通畅率分别为97.6%、84.2%、68.8% 和53.8%。41 例中无截肢患者, 保肢率100%。SIA 失败的最常见原因是越过闭塞段后,在远端无法重新进入血管真腔。Cordis 公司推出Outback LTD导管及FrontRunner XP 导管,张宏鹏等[29]在股浅动脉慢性完全闭塞性病变中应用Outback LTD导管内膜下成形术治疗技术的近中期结果显示平均病变长度为(210±15)mm,操作技术成功率为97.1%(34/35),无操作相关的并发症发生。平均随访时间(7.2 4-0.3)个月。随访3、6、12个月支架一期通畅率分别为90.9%、84.8%和50.6%。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在常规方法无法进入真腔时,FrontRunner XP 导管可顺利通过闭塞动脉内膜下,其顶端的爪形结构开启最大直径2.3mm, 关闭时仅1mm,无明显阻力进入约15mm,较多用于股浅动脉和腘下动脉病变,特别是股浅动脉,相对于其他导管,FrontRunner XP 导管可行钝性分离,将导管有效控制在真腔内,减少内膜穿孔和夹层的发生,对于高度钙化的病灶效果更佳。但其存在一定的风险, 有可能穿破血管可能,且其尺寸较大在腘动脉应用存在较大争议,在国内研究较少,据相关研究显示[30],FrontRunner XP 导管在治疗下肢慢性动脉完全闭塞病变的成功率达89%。Pioneer快速交换式球囊扩张导管有着卓越的通过性及跟踪性能,可为复杂血管病变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其先进的激光焊接技术实现头端和管体的无缝连接,使球囊导管在弯曲而狭窄的病变血管中顺利推进,锥形头端科减少推进阻力,对血管的损伤降至最小,操作过程更方便。
3.ASO治疗的新技术
近年来,我国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的发病率迅速上升,由此引发的全身性血管病变的局部表现如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病率亦呈明显上升趋势,所致严重肢体缺血带来高致残及致死率严重威胁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随着腔内治疗的病例数呈不断增加,使得技术研究也有了优越进步,特别是对一些如主髂分叉部与股浅、股深分叉部的特殊部位的特殊病变,钙化与非钙化病变,血栓性闭塞,完全硬化性闭塞,短段与弥漫性病变,PTA及支架术后再狭窄,支架变形与扭曲等,为选用合适的方法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针对各类型病变特点,相继推出了许多新的腔内手术器具。
3.1 下肢血管超声消融
下肢血管超声消融是使用低频率超声消融血栓,再通狭窄或已经闭塞的血管[31]。下肢血管超声消融主要是借助机械破碎和间接的助溶生物学效应来达到消融血栓和裂解硬化斑块的目的,从而恢复促进血液循环,其优势在于重构血流通道,从而改善肢体血供,恢复肢体远端的血液循环。
3.2 冷冻血管成形术
球囊扩张导管(PolarCath cryoplasty balloon)上配置有冷冻能源,在球囊扩张时对动脉壁施以冷冻作用。主要应用于再狭窄病变部位,且这些部位不适合放置血管支架,如腘动脉和股总动脉。Das等[32]的一项针对膝下动脉病变的研究中,使用冷冻球囊成形术后3 个月和1 年的保肢率分别是93.4%和85.5%。该治疗疗效较为显著,且PolarCath 系统已被美国FDA 批准用于周围动脉闭塞性疾病的治疗,有望在国内临床工作中进一步开展。
3.3 激光导管辅助血管成形术
在手术过程中使用准分子激光导管在极短的脉冲发送高能、可控的紫外光至病变部位以融化斑块,减少局部热损伤和远端栓塞并发症的发生,激光辅助血管成形术可以开通一些血管腔内介入治疗无法开通的局部或长段动脉闭塞性疾病。激光导管通过导丝的引导,逐步开通闭塞动脉,动脉开通后再行PTA即可。
3.4 切割球囊
切割球囊(cutting balloon,CB)是有美国的Barath peter在1991年开发研制的一种外表面轴向装有小型刀片的球囊。用于球囊扩张的同时可对血管病变部位的斑块进行切割。适合长段散在的钙化病变;与PTA 的钝性、无序扩张相比,CBA能以较低压力获得充分扩张,切割球囊PTA 术可降低局部炎症反应、内皮损伤、细胞增殖反应,并使管腔达到最大化。王爱林等[33]报道中分析研究33例常规球囊扩张与切割球囊相结合的“复合球囊扩张”在股浅动脉长段闭塞治疗中的扩张效果和中期疗效显示: 33例患者中3例在切割球囊扩张后出现轻度夹层,但不影响动脉血流,未做特殊处理。术后24例患者随访1年,下肢CTA示,再通率为66% ,与前期完成的24例单纯球囊扩张患者比较,通畅率明显好于单纯常规球囊扩张(37%),在常规球囊扩张基础上应用切割球囊扩张可以增加扩张效果,增加中期通畅率。
3.5 斑块切割球囊
目前斑块切割包块单向动脉斑块切除、高速动脉斑块旋切、改良动脉斑块旋切等,单向动脉斑块切除尤其适合于多节段分散病变、近分叉及关节处病变等不太适合常规球囊扩张和支架植入术治疗的病变;高速动脉斑块旋切主要用于高度钙化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治疗,它利用高速旋切,辅助球囊导管通过病灶进行ASO的治疗;改良动脉斑块旋切系统可旋切产生微粒甚至可以通过人体内皮细胞,并在切除斑块的同时,可将切割下来的斑块回收,避免远端血管栓塞的发生。
3.6 药物涂层球囊
目前PTA可有效改善ASO患者下肢供血情况,但术后血管再狭窄情况成为PTA的治疗世界性难题。为降低血管再狭窄的发生率,随着科技的发展,药物涂层球囊技术产生。国外最新研究表明[34-34a]:使用紫杉醇药物涂层球囊经皮腔间血管成形术治疗外周动脉疾病受限于血管弹性回缩和再狭窄的发生。药物涂层球囊动脉血管成形术使抗内皮细胞增值的药物直接作用于血管狭窄处, 可明显改善血管情况,减少再狭窄的发生。
问题与展望
ASO作为常见的慢性疾病,其发病率逐年提高,目前国内相关资料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病率约为10%[35],70岁以上人群的发病率在15%?20%。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国外相关调查显示该病在美国的发病率约为15.6%[36]。其病情的发展以及预后不佳,下肢动脉闭塞不及时治疗将导致肢体坏死和感染,乃至截肢,甚至危及患者生命,严重危害着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已引起临床医师广泛关注。下肢AS0的诊断需要针对每位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首先是危险因素的评估,如高龄、吸烟、高血脂、糖尿病以及全身动脉粥样硬化情况,并着重对进行心脑血管系统情况评估,通过病史询问和体格检查,综合临床症状和体征,并判断肢体缺血的严重程度。
目前血管重建仍然是治疗重症下肢缺血的最佳方案,在制定治疗方案时应结合患者的TASC分级级别、临床症状、全身情况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分析。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2015版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治疗指南[9]指出:主-髂动脉TASCA?C级病变推荐首选腔内治疗,保肢是腘动脉以下病变腔内治疗的最主要目的;股-腘动脉TASCA?C级病变应将腔内治疗作为首选治疗方式,当TASC-D级病变合并严重的内科疾病或存在其他手术禁忌时也可以选择腔内治疗,但应在有经验的中心完成,覆膜支架可以作为复杂股浅动脉病变治疗的一个选择;保肢是腘动脉以下病变腔内治疗的最主要目的,当需要重建腘动脉以下血运时,腔内治疗应作为首选治疗方案,球囊扩张是首选治疗方法。不推荐常规支架植入治疗,支架植入可以作为球囊扩张成形术效果不满意或失败后的补救治疗方法。对于 TASC- A、B 级和部分 C 级病变,通常首选 PTA,重建缺血下肢的动脉血流,以迅速恢复远端肢体供血, 缓解因缺血引起的症状,促进溃疡愈合,从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达到保肢目的,并使截肢率得到有效降低[37];尤其基本情况不佳、年纪较大或不能耐受传统手术的患者,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对TASC-C、D 型股浅动脉长段闭塞的治疗,很多学者认为 PTA 治疗的难度相对较大,血管旁路移植远期通畅率较满意,但随着 PTA 技术发展和介入材料的不断更新,TASC- C 级和 D 级病变的介入治疗也逐渐开展并取得了较满意的疗效[38-40]。但对于经造影证实的下肢动脉无远端血管显影的病变,因考虑无法有效重建肢体远端血液循环,一直被认为是下肢动脉开放手术和 PTA 治疗的禁忌证,甚至在血管腔内治疗后复查造影仍未开放的远端血管,这部分患者不得不面对截肢的结局,当肢体无法挽救时,需在患者全身情况恶化之前截肢。因此,提高这部分患者的保肢率,保证其基本生活质量。针对重症病人, 血管腔内重建术和开放手术对下肢动脉闭塞症的近期和远期结果相当时, 应首选血管腔内治疗。另外下肢血管超声消融、冷冻血管成形术、激光导管辅助血管成形术、斑块切除技术等也可作为ASO腔内治疗的辅助治疗手段,有待进一步研究及远期临床疗效的观察。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专家会议( 广东东莞,2008年) 认为以上TASC分级标准和治疗依据仅供临床医生参考, 不作为临床绝对和惟一的治疗标准。在疾病治疗过程中, 需要逐渐积累国人自己的经验。建议在符合基本治疗原则基础上根据病人具体情况和术者经验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对于如何预防和治疗术后血管再狭窄也是目前的一大热点,如应用下肢专用超长球囊、药物洗脱支架、血管内照射等方法。
介入治疗属于微创性手术治疗,伴随医疗技术的发展和介入治疗技术的逐渐成熟,可显著降低其对患者机体的刺激,防止发生心脑血管性疾病的风险性,对患者的机体创伤小,可反复操作,安全性高,对老年及基本情况欠佳患者身上也可进行,能有效降低截肢率、病死率,提高临床患者的治愈率,提高其生活质量,减轻心理及经济负担。相信随着对介入术后再狭窄预防和治疗的不断进步,介入治疗在ASO治疗中的应用将有更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马天宇,谷涌泉,郭连瑞,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外科治疗方法的比较及预后:单中心十年经验[J].中华外科杂志,2015,53(4):305-309.
[2]顾建平,楼文胜,徐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介入治疗的现状和进展[J]苏州国际介入医学论坛,苏州,2011.
[3]王玉琦.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外科治疗问题[J].中华普通外科学杂志,2003,18(4): 197-198.
[4]Ugalde H,Espinosa P,Pizarro G. Clin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is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ong patients aged 80 year or older[J].Rev Med Chil,2008, 136(6):694-700.
[5]范利,崔华,胡亦新,等.不同年龄老年急性心肌梗死住院患者近期预后的临床分析[J].中华老年医学杂志,2009,3(28):190-2.
[6]Silva GV,Femandes MR.Cryoplasty for peripheral artery disease in an unselected patient population in a tertiary center[J].Tex Heart Inst J,2011,38(2):122-126.
[7]李京雨,刘涛,路军良,等.介入治疗复杂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技术与疗效分析[J].中华放射学杂志,2011,45(10):960-963.
[8]Norgren L,Hiatt WR,Dormandy JA,etal.Inter-society consensu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TASC Ⅱ)[J].Vasc Surg,2007,45 Suppls:65-67.
[9]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指南[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15,95(24):1883-1896.
[10]吴泽涛,李焕祥,马彦寿,等.内膜下血管成形术治疗慢性下肢长段动脉硬化闭塞症的疗效分析[J].青海医药杂志,2015,1(1): 56-58.
[11]李炜淼.长球囊扩张成形术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J].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08.
[12]江娜,杨维竹,黄兢姚,等.长球囊成形术治疗膝下动脉闭塞性病变的疗效评价[J].当代医学,2009,23(15):388-390.
[13]秦汉林,高斌.自体干细胞移植治疗糖尿病足的研究进展[J].介入放射学杂志,2010,19(9):753-754.
[14]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指南[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8,28(II):923—924.
[15]Scott EC,BiuckiansA,LightRE,et a1.Subintimal angioplasty:Ourexperi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506 infrainguinal arterial occlusions[J].J Vasc Surg,2008,48(4):878—879.
[16]张希全,凌宝存,朱伟.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疾病血管腔内治疗[J].当代医学,2009,15(17):284—286.
[17]田硕,黄新天.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血管腔内治疗的研究进展[J].中国现代普通外科进展,2011,14(4):302-305.
[18]Adam DJ,Beard JD,Cleveland T,etal.Bypass versus angioplasty in severe ischaemia of the leg (BASIL):multicentr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Lancet,2005, 366:1925-1934.
[19]吴石白.超声血栓消融及小球囊介入方法治疗糖尿病下肢动脉闭塞硬化症及足坏疽[J].第二军医大学学报,2008,29(10):1208-1212.
[20]蒋天鹏,周石,李兴等.SAVVY球囊行PTA治疗下肢动脉流出道硬化闭塞症[J].影像诊断与介入放射学,2010,19(5):290-292.
[21]Romiti M,Albers M,Brochado-Neto FC,etal.Meta analysis of infrapopliteal angioplasty for chronic critical limb ischemia[J]. J Vasc Surg, 2008,47(5):975-981.
[22]李麟荪,贺熊树,邹英华.介入放射学基础与方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23]诸锡奇,赵伟.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联合血管内支架治疗老年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的疗效[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5(35):6180-6181.
[24]Schillinger M,Sabeti S,Loewe C,et a1.Balloon angio-plasty versus implantationof nitinol stents in the superfi -cial femoralartery [J].NEnglJMed,2006,354(18):1879.
[25]Dorrucci V.Treatment of superficial femoral artery occlu -sive disease[J].J Cardiovasc Surg,2004,45(3):193.
[26]李天晓,谢敬霞.经皮月国下动脉腔内血管成形术初步经验分析[J].中国医学影像技术,2007,23(3):432.
[27]Bolia A, Brennan J, Bell PR. Recanalisation of femoropop liteal occlusions:imp roving success rate by subintimal recanalisation[J].Clin Radiol,1989,40(3):325.
[28]李大林,陈允惠,张鲲,等.内膜下血管成形术治疗下肢动脉闭塞症的临床疗效观察[J].临床普外科电子杂志,2013,1(3):28-34.
[29]张宏鹏,郭伟,刘小平,等.股浅动脉闭塞性病变中Outback LTD导管的应用分析[J].中华外科学杂志,2012,50(3):226-229.
[30]Peter A.New Strategies for Crossing Iliac CTOs. Two case studies demonstrate the utility of controlled blunt microdissec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iliac CTOs in many patients[J].Supplement to Endovascular Today,2009,12(4):3-10.
[31]吴石白.超声血栓消融及小球囊介入方法治疗糖尿病下肢动脉闭塞硬化症及足坏疽[J].第二军医大学学报,2008,29(10):1208-1212.
[32]Das TS,McNamara T,Gray B,etal. Primary cvoprestv therapy provides durable support for limb ischemia salvage in critical limb patients with infrapopliteal lesions:12 -month follow -up results from the BTK Chill trial[J].J Endovasc Ther, 2009,16(Suppl 11):1119-1130.
[33]王爱林,徐恒,刘军.切割球囊扩张在股浅动脉长段闭塞治疗中的作用[J].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2012,20(3):156-158.
[34]Kenneth Rosenfield,Michael R,Christopher J,et al.Trial of a Paclitaxel-Coated Balloon for Femoropopliteal Artery isease[J].N Engl J Med,2015,373:145-153.
[34a]Gunnar Tepe,Thomas Zeller,Thomas Albrecht,et al. Local Delivery of Paclitaxel to Inhibit Restenosis during Angioplasty of the Leg[J].N Engl J Med,2008,358:689-699.
[35]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指南[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8,28(11):923—924.
[36]Fowler B,JamrozikK,NormanP,A1 lenY.Prevalence of peripheral arterialdisease:persi stence of excess ri sk in former smokers [J].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02,26(3):219—224.
[37]李大林,张鲲,颜京强,等.股浅动脉闭塞84例治疗体会[J].临床普外科电子杂志,2013,4(1):21-24.
[38]丁明超,李芳,王斌,等.无流出道显影的下肢动脉闭塞症腔内血管成形治疗的预探索[J].介入放射学杂志,2015,24(15):383-387.
[39]温志国,杜丽苹,李文明,等.TASC C D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腔内治疗[J].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14,29(1):29-31.
[40]李艳奎,吴义生,张小明.TASC-D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腔内治疗现状[J].介入放射学杂志,2015,24(6):383-387.
论文作者:杨熙园1,沈雅平1,龙吉甫1,刘卫新1,王婷1,周
论文发表刊物:《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6年4月第7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6/7/18
标签:动脉论文; 闭塞论文; 下肢论文; 血管论文; 动脉硬化论文; 狭窄论文; 支架论文;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6年4月第7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