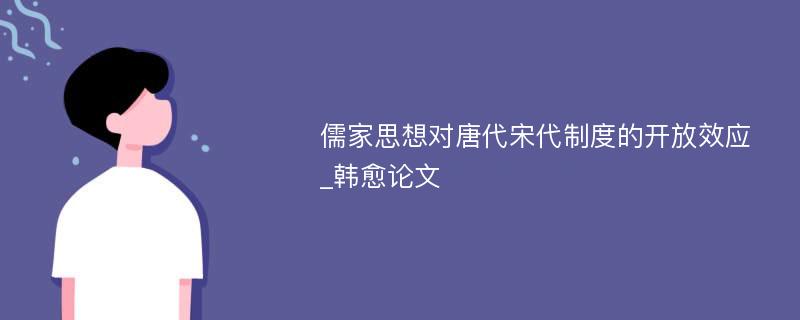
唐代儒学对宋学系统的开启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唐代论文,作用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安史之乱”后,韩愈大力提倡儒家关于君君、臣臣的政治伦理思想,尊王攘夷,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中央政权的统一,以儒家的道统和仁义道德学说,来取代佛老之道。而陆淳等人的新春秋学对经义的任意发挥,以“忠道原情”的形式,对历史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从而使经学与现实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直接服务于唐代中央集权政治,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
关键词 儒学 宋学 韩愈 陆淳 新春秋经学 经世致用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从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1〕就儒学与经学而论, 唐代前期是汉学系统的终结,《五经正义》的完成标志着章句之学至此已告一段落。安史之乱后,与韩愈等倡导的古文运动“文以载道”的新文风相适应,经学也从笺注之学中走了出来;啖助、赵匡、陆淳等首创新春秋经学,兼采三传,独抒己意,从而开启了宋学系统的新局面。
一 韩愈、李翱的新经说
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前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的确,在中国儒学由低落向复兴的历史转变中,起到了承先秦两汉儒学之“先”,启宋学系统之“后”的历史作用。
章句之学虽然在近千年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尊崇下,适应了中国古代缓慢渐变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古老的经文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却无疑地日益加大。在政治平和的时代,儒家经学或许还能发挥些化民善俗的教化功能,但一旦政局动荡,古老的章句之学就显得无能为力且不合时宜了。儒学在社会政治中实际地位的下降,必然引起关心社会政治教化的儒生们的不满,他们力图弘先王之道,济时艰,拯民困,恢复儒学在现实社会中实际上的领导地位。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异教盛行,寺院经济迅速发展,中央财政拮据等状况,都使阶级矛盾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深化。因此,重整纲纪,重建封建统治秩序,进而加强中央集权政治,实现安定统一,就成为当时最为迫切的政治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适应大一统政治的儒家学说,经过与佛、道的对比,显示了它在中国的不可替代性,又一次地被推上了强化的地位,从而掀起了唐代历史上复兴儒学的高潮,涌现出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等一批以振兴儒学为己任的思想家,尤其以韩愈为代表。
针对安史之乱后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以儒者自居的韩愈,站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立场上,“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2〕, 大力提倡儒家关于君君、臣臣的政治伦理思想,尊王攘夷,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中央政权的统一。同时,韩愈还提倡和实践辞严义伟、制述如经的古体散文,并以之作为与佛教斗争的武器,从而使复兴儒学、排斥佛教的斗争做到了从形式到内容的统一。
由于当时“自佛行中国以来,国人为缁衣之学,几与儒等。……今世儒道少衰,不复与之等矣”,〔3〕以及寺院经济对世俗地主经济的严重破坏,韩愈积极主张辟佛。他在《谏迎佛骨表》中大胆指出:“佛者不过夷狄之一法,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并以历代“信佛求绝福,乃更得祸”的史实,揭示了佛教乱政害民的本质,请求“投诸水火,永绝根本,以断天下之疑,以绝万代之惑”。〔4〕
应该说,韩愈的辟佛与尊儒是一致的。其辟佛正是为了维护儒家道统而否定佛老之道。《原道》是韩愈辟佛最有力的一篇檄文,同时也是他宣传道统最具代表性的文章。韩愈指出:“夫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5〕韩愈所谓的“教”,是针对佛、道之教提出的, 并显示了“先王之教”与佛、道之教的绝然不同;而其所谓的“道”,更是完全针对流行的佛老之道提出的,也即所谓的儒家一脉相承的圣人之道统。韩愈要以儒家的道统和仁义道德学说来取代佛老之道,佛老之教。
韩愈辟佛的理论没有什么新发明,仍然基本上是从经济、政治伦理入手,而没有能够从哲学的高度上对佛、道做出更为有力的批判。但韩愈提倡儒学的理论却表现出了一定的特色。
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政治伦理学说,同时包含有许多伦理道德和人格修养的理论,具有突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如果脱离了现实的政治生活,丧失了对现实政治的批评、指导功能,儒学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因此,儒学要在佛学盛行于天下的形势下,重新找回自己的立足之地和存在价值,就必须首先恢复其内在的社会现实性和道德实践性,从空洞琐碎的经义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社会和人生问题;对社会政治提出自己的意见,对佛教思想的渗透做出积极的反映,创造性地挖掘和发展儒家的心性理论以抵抗佛教心性学说的继续渗透。韩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复兴儒学所提出的理论便带有了这种时代特征。此外,魏晋以来儒、释、道相互排斥又互有融合的特色在韩愈的理论中也有明显的反映。
韩愈在《原道》中特别推崇孟子,认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道统。韩愈选择孟子为儒家道统的正宗传人,而否定董仲舒,可以说是出于佛教情势的逼迫。当时人们普遍信奉佛教,佛教中关于心性、修持等理论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孟子的学说中却不乏谈心谈性的内容,如“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6〕等,就具有神秘主义倾向, 而其“寡欲”、“养心”之类的修身养性之法,又多少与吸引时人的佛学有相近之处。所以,以孟子为儒家道统的正宗传人,是想以孟子,进而以儒学取代佛教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出于同样的原因和目的,韩愈《原道》中特别引用了上述《礼记·大学》篇中关于修齐治平及正心诚意的说法,并指出“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说明儒、佛虽然都有“治心”之道,但一个为入世,一个为出世,其目的不同,结果自然也不同。
韩愈探求“道统”,是为了推出儒家仁义之道,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人性的问题。为了使自己的理论前后贯通,韩愈在其发挥性情说的《原性》篇中认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焉而巳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巳矣”。情之品也有三,上焉者于七情“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
韩愈的性情说,一方面承认人的道德本性,认为是“与生俱生”的;另一方面又承认人在具体的生活中,实现人性的禀赋能力有所差别,因而所能达到的道德境界不同。于此,韩愈既指出了按照儒家道德标准来完善人性的可能性,又为按照儒家道德原则对人民实行教化提供了内在依据。另外,韩愈以仁、义、礼、智、信为人性的本质,主张通过“动而处其中”来体现人的道德性,并以此与佛教出世的佛性论相区别。
然而,佛教思想体系中关于心性等哲学问题的讨论是更为丰富和缜密的,韩愈的性情说在对儒家心性理论的体会和阐发上,距离鞭辟近里的境界尚远。若想更有力地辟斥佛老,复兴儒学,就必须首先对佛教的心性理论有较深刻的理解,并从儒家的角度对心性等问题做出不同于佛教的解答。韩愈的道统说和性情说,被他的弟子李翱在《复性书》中做了更进一步的发挥。
李翱首先论述了性与情,以及人与圣人的关系。他认为:“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欲恶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溺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情不作,性斯充矣。……情之动弗息,则弗能复其性。”〔7〕所以,能做到“情不作”, 也就达到了所谓“性斯充矣”的“复性”目的,从而得以达圣人境界。而“情不作”却并非无情,而是圣人的一种“寂然不动,照乎天地”的心理状态,也即“诚”。
李翱论述了儒家关于修养成性,也即“复性”于“诚”的方法。他说:“圣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于圣也。故制礼以节之,作乐以和之。……所以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也就是说,人们只要循之不已,最终就能复性成圣人。在这里,儒家使人之欲望、情感皆发而有节得其中的礼乐,被解释为圣人用以“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带有类似宗教的特点;而儒家讲求的不断修养以达于道德人格完全的圣人之道,也被用来解释人们达于“诚”的方法。
至于儒家早已具备的圣人关于达于“诚”、“归于性命之道”的修养方法为何不见流传,也即儒家道统的废缺,李翱在《复性书》中解释说:“昔者圣人以之传于颜子,……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轲曰:‘我四十不动心。’轲之门人达者,公孙丑、万章之徒,盖传之矣。遭秦灭火,《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于是,此道废缺。……呜呼,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所以,是由于秦焚书坑儒,儒家性命之书才不传,儒家的性命之道才有如此废缺,而世人不明乎此,以为只有老释才有性命之说,竟纷纷转而崇信佛老了。
从韩愈、李翱提倡道统说的内容和方法上,不难看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暗示人们想要在佛道中寻求的答案,其实本来早可以在儒学中找到相应的解答。其动机是显然的,正如李翱在《复性书》中所说,是为“开诚明之源”续“缺绝废弃不扬之道”,以使人们重新回到儒学的立场,以儒家的方法成就儒家的圣。他们的主观意图虽然企图抵制佛教,但在许多具体的论点上,又表现出一定的佛学色彩,尤其是李翱的复性说,以性为真,以情为妄,灭情以复性的理论,与佛教的基本精神不无相通之处。而复性说的价值,又恰恰在于它的援佛入儒,以儒统佛,借用佛学方法,来补充和完善儒学在心性理论方面的不足,从而重建和复兴了儒家的心性理论。
中唐晚期的复兴儒学运动,形成了韩愈、李翱等人的道统论、性情说,开展了激烈的反佛道斗争,从而使贞元、元和时期成为唐代历史上又一次复兴儒学时期。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这场运动并没有获得成功。然而,韩愈和李翱在反佛旗帜下,以孔孟儒学传人自居,以儒家一脉相承的圣人之道否定佛老之道,在吸收佛教内容基础上,提出“道统说”和“复性说”以复兴儒学反对佛学。他们的理论虽然不够成熟,但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8〕的尝试, 以及援佛入儒的反佛形式,却为宋明理学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韩愈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从唐末到宋初,随着地主阶级要求的发展,也越来越高,五代刘煦所编《旧唐书》对韩愈只道:“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9〕到宋代欧阳修、宋祁所编《新唐书》, 对韩愈则作了极高的评价:“自晋讫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义,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距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乱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10〕
二 怀疑学派与春秋学的崛起
唐初统一经学以来经学界所形成的“无异文”、“无异说”的局面,使唐代儒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以章句之学的形式出现。经义烦琐,远离人世。对现实政治生活的脱离,使其丧失了作为社会政治学说应具有的现实性和实践性,从而也就丧失了对现实政治的批评指导功能。儒学的发展受到了遏制,而流入僵化烦琐的理论体系。发展到中唐,儒学已在佛教的强大功势下处于劣势,社会上出现了“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始终”的疑经思潮。刘知几所著《史通》中甚至出现了《惹经篇》,对《春秋》大胆地提出了批评。然而,中唐晚期出现的疑经思潮,还并不是反对五经,而是对历来的五经的传、注、疏加以怀疑和批判,又尤以批判《春秋》三传为主。怀疑派著名人物除史载的冯伉、韦表微、卢仝、刘轲等人外,还有中唐晚期创立“新春秋经学”的啖助、赵匡和陆淳等。
安史之乱及其所造成的政治混乱,风俗浇薄的状况,也对一些儒生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们认为“今试学者以贴字为通,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而“忠信之凌颓,耻尚之失所,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此四者尤为“取士之失也”。〔11〕因此,为了重振儒学,重整纲记,他们反对“唯择浮艳”的文风,反对“不穷旨义”、唯墨守于章句记诵的经学方法,提倡施之于实事的儒学精神。
陆淳(后避宪宗讳改为质)的3本著作《春秋啖赵集传纂例》、 《春秋微旨》及《春秋集传辨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唐德宗贞元年间问世的。而啖助可谓首开其端。《新唐书·啖助传》曰:“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断,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可知啖助、赵匡、陆淳3人同属一派,而啖助有首倡之功。所以,陆淳的3本著作,也就不仅是陆淳本人思想的体现,还应视作其3人思想的集中体现。
《春秋》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242年间的历史, 然而在古人眼里,《春秋》从来就不仅只是一本史书。庄子在《天下篇》中历数六经,而以为“《春秋》以道名分”;〔12〕孟子则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13〕司马迁则称:“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14〕可见,《春秋》经历来被视作一部政治学的经典,包含着“道名分”、“寓王法”等一系列事关封建统治的理论。《春秋》因此受到历代政治家的重视。
然而,《春秋》作为经,只有16000余字,其记事过简, 语意晦涩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如果离开传、注、疏之类的解释,学者们往往会于《春秋》经义莫明所以。这样,在后人的重视、研究和利用下,就形成了一门专门以解释《春秋》经为内容的学问——春秋学。所以,《春秋》代有纠纷,也就不是《春秋》本身的问题,而在于《春秋学》的演变。
《春秋》作为认识的客体,具有既是经,又是史的双重性质。如果从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就必然要求采用考证的方法来探求名物训诂,进而反映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而如果从经的角度解释,又必须探求其微言大义,并予以阐发。所以,从两种不同角度入手加以解释,必然会形成重史实和重义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风格。《春秋左氏传》属于重史实的一类,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则属于重义理的一类。啖助、赵匡和陆淳的新春秋学,就属于后者,偏重义理。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中认为:“习左氏者,皆遗经存传,……不复知有春秋微旨。”〔15〕所以,尽管他们对3传都有批评,但尤以责《左氏传》为甚。
陆淳等人所以于5经中选择《春秋》作为怀疑、批判的对象, 并以《春秋》为突破口来完成其新经学的建立,除因《春秋》作为封建政治学经典与中唐突出的现实问题相关联外,还因为《春秋》史经一体,有记事简略故往往需要因事以明义等特点。《春秋》既为经,其中的微言大义就一定要在注释中加以阐发,然而《春秋》所含的微言大义,往往不是以逻辑的语言形式出现,而是通过记事中的“春秋笔法”来传达的。陆淳等人正是抓住了《春秋》经因事明义的特点,利用其特殊的释读原则,重新解释《春秋》的。他们在提出《春秋》“不全守周典礼”的同时,强调其“仁政”、“民本”的“王道”,并以“忠道原情”说重新评价历史人物,达到了直接为唐王朝服务的政治目的,并由此实现了将章句之学导向义理之学的尝试。
唐代经学能实现由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的转变,是因为具备了中唐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这样一种社会现状,对于儒家的思想家们来说,则更为集中地反映为如何用经学这个武器达到维护统一,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
唐德宗贞元四年,兵部侍郎李纾请求改变太尚父庙的祭礼。当时身为刑部员外郎的陆淳表示赞同,认为“武成王,殷臣也,纣暴不谏,而佐周倾之。夫学道者师其人,使天下之人,入是庙,登是堂,稽其人,思其道,则立节死义之士,安所奋乎?圣人宗尧舜,贤夷齐,不悦桓文,不赞伊尹,殆谓此也。”〔16〕流露出极鲜明的欲重整人伦,重正纲纪的想法。其新春秋经学正是为此目的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经学。
而其主旨,就在于推明《春秋》“不全守周典礼”。这在《新唐书·啖助传》中有较完整的概括。其传曰:“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球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敝且末,设教于末,将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以用之,周公殁,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于二代。孔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敝。故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矣。盖言唐虞之化,难行于季世,而夏之忠,当变而致焉。故《春秋》以权辅用,以诚断礼,而以忠道原情。……古语曰: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而公羊子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拟后圣。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而陆淳在《春秋啖赵集传纂例》中也指出:“《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礼必然矣。”〔17〕可见陆淳春秋学的主要内容,就在于认为《春秋》并非全守周典礼;并倡导所谓“忠道原情”,从道德出发,对历史人物进行再评价。
传统的《春秋》三传,较多周礼中关于分封制下诸侯等级世袭等内容,对诸侯中尊王攘夷的霸主,也持赞美态度。而这些观念,对于处在藩镇割据等危机中的唐代中央王权是极为不利的,必须予以纠正。所以,“《春秋》不全守周典礼”的核心,也就是借此以否定周礼分封,以维护现行的中央集权制。此外,陆淳还评击了《春秋》中所讲述的诸侯盟会,指出“若王纲举则诸侯莫敢相害,盟何为焉?贤君王则信著而义达,盟可息焉”。〔18〕在这里,陆淳只提“王纲”、“君主”,而贬抑诸侯盟会,实现了理论上的尊王贱霸的意图,同时也反映出希望唐王朝能恢复中兴,使“诸侯莫敢相害”的愿望。
陆淳还指出《春秋》要旨“唯立忠为教,原情为本”。〔19〕这里的“忠”就是孔子所说的忠恕。也就是说陆淳认为《春秋》经旨在以忠恕进行教化,而这种忠道本原于人的本心。提倡“忠道原情”的目的,在于冲淡《春秋》中那些不合时宜的礼法等内容,而继以道德、心理等无从查考的主观因素,并以此改造陈旧的义理。如《春秋》“隐公四年”记有“卫人立晋”。当时真实的情况是卫国大夫石碏杀了杀兄纂位的州吁,立公子晋为国君。对此,《左氏传》无褒贬;《公羊传》批评石碏“其立非也”;《谷梁传》则认为晋虽是贤人,但“春秋之义,与正不与贤”,所以,也认为石违反了礼法。而陆淳在《春秋微旨》中则认为当时次当立者不贤,石碏出于国家安危的考虑,不得已才立贤能的晋为国君,并赞美石碏所为既忠且义。这样,不但可以不考虑什么“诸侯与正不与贤”的诸侯等级世袭制,而且借称赞石碏忠且义将这一条在唐代社会中不应再有存在余地的周礼置之一旁。由此可见,“忠道原情”的目的,主要就是利用经义的简略含混,结合唐代郡县制下等级名分的特点,以君臣关系为新的伦理观念的核心,抑制并清除周礼分封制下的诸侯名分观念,从而使经学内容伦理化。
陆淳春秋学在对《春秋》三传批评的基础上,利用《春秋》史经一体、因事明义等特点,在释读中灵活地发挥新义,针对唐中后期的社会现实,大胆地提出《春秋》“不全守周典礼”;并以“忠道原情”的形式对历史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从而使经学与现实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直接服务于唐代的中央集权政治,达到所谓经世致用的目的。尽管陆淳等人的新春秋学对经义的任意发挥,使其与不变的历史事实之间的不协调性更加突出,但作为一代思想家,他们毕竟成功地改造了春秋经学传统,更新了其中的思想观念,为本时代、本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解决藩镇割据等重大政治问题的理论,从而维护了郡县制的国家政体和大一统的国家实体。经学经历这次蜕变的尝试,又在一定历史时期恢复了面对现实的能力。就此而言,陆淳等人的新春秋学是进步的,成功的。
陆淳新春秋学在唐代经学史上,以及在整个中国经学史上的意义,更重要地还在于它完成了经学的蜕变,从而起到了它在由以训诂为特色的章句之学向以陈析义理为特色的宋代新儒学转变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陆淳新春秋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在创立初期就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受到当时包括中唐八司马的柳宗元、凌淮等人的支持,而且由于它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在后代也受到重视和称道。宋代程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朱熹则明白道:赵、啖、陆皆说得好。吴澄则评论说:唐啖助、赵匡、陆淳3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20〕在陆淳春秋学的影响下,到了宋代,五经都被重新以现实的眼光做出了新的解释,而经学也就随之完成了由汉学系统到宋学系统的转变。
三 对宋代新儒学(理学)的影响
汉学系统与宋学系统相比较,有着明显的差异。以内容上看,汉学侧重于名物制度,宋学则偏重于性命义理;从方法上看,汉学重视章句训诂,宋学则讲究缘词生义;从指导思想来看,汉学者笃守法家,宋学者则荡弃家法,直抒胸臆。而宋学种种特色的形成,中唐后期的新经学可谓巳肇其端。
清代皮锡瑞认为:啖、赵、陆“杂采三传,以意取舍,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21〕中唐后期的新春秋经学对宋儒有极大的影响。啖、赵、陆的的新春秋学,不受《春秋》三传的束缚,弃传谈经,专凭己意说经,并敢于对三传提出批评意见。这种治经方法,对宋儒以义理解经,注释中不拘泥于文字训诂,而着力于对经典宗旨的通体把握,直接探求和发挥其义理,并以义理为标准对后儒传注以至于经典本身广泛质疑特色的形成,无疑有着相当直接的影响。以宋儒治《春秋》为例,孙复撰《春秋尊王发微》,废弃传注,专谈书法;刘敞作《春秋权衡》,以主观评论三传得失;此外,叶梦得《春秋传》、高闶《春秋集注》及胡安国《春秋传》等,不是排斥三传,就是杂揉三传,基本上都是沿着中唐后期新经学的道路并有所发展。至于宋儒遍注五经,疑序继而疑经文本身,更是对中唐后期以来疑经思潮和新经学的继承和发扬。
在新经学影响宋儒治经方法的同时,韩愈、李翱则在致思趋向和治学途径等方面开宋学之先河。韩愈提出的以《大学》为纲领的理论体系,将治心与修齐治平联系在一起,使久而未彰的《大学》重放异彩,对此宋儒十分推崇。而其他为韩愈他们所重视的,如《孟子》、《中庸》等,也以其倡导的儒家一脉相承的道统观及达于诚明修养至圣之道而为宋儒所欣赏和重视。
此外,韩愈的性情说,虽然难免流于粗糙,但他关于仁、义、礼、智、信的性之本质和性三品的理论,却对宋代新儒学中最基本的命题“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学说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李翱的“复性说”更以其以儒统佛,援佛入儒,以补充和完善儒家心性理论的治学方法,给宋儒以重要启发。不但宋儒心性学说的主要思想的大体结构得利于李翱的“复性说”,而且其大胆地引佛入儒,以儒统佛的致思趋向和方法,也都得利于李翱。而韩愈、李翱对《大学》、《孟子》、《中庸》及《论语》的重视,扭转了汉唐以来以五经为主进行注疏训诂的学风,这对宋儒推崇“四书”,以“四书”为儒学中心的观点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注释:
〔1〕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
〔2〕〔9〕《旧唐书·韩愈传》。
〔3〕范文澜《唐代佛教》,《沈下贤文集》卷6《移佛记》。
〔4〕《韩昌黎集》卷39《谏迎佛骨表》。
〔5〕《韩昌黎集》卷11《原道》。
〔6〕《孟子·尽心上》。
〔7〕《李文公集》卷3《复性书》。
〔8〕《东坡文集》卷55《韩文公庙碑》。
〔10〕《新唐书·韩愈传》。
〔11〕《旧唐书·杨绾传》。
〔12〕《庄子·天下篇》。
〔13〕《孟子·滕文公下》。
〔14〕《史记·儒林传序》。
〔15〕〔17〕〔19〕《春秋啖赵传集纂例·春秋宗指义》。
〔16〕《新唐书·礼乐志五》。
〔18〕《春秋啖赵集传纂例·盟会例》。
〔20〕〔21〕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
标签:韩愈论文; 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孔子论文; 春秋论文; 大学论文; 原道论文; 孟子论文; 佛教论文; 中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