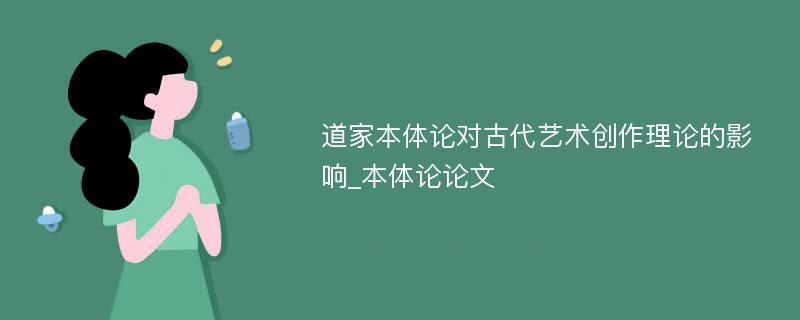
道家本体论对古代艺术创作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道家论文,艺术创作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0X(2003)03-000410
一般认为,道作为道家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兼有本体论和本原论双重含义。就是说,在道家看来,道既是天地万物派生的根源,又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正是这种双重特性构成了道之为道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道范畴在整个道家思想中的特殊地位。所以,讨论道家思想对后代的影响,无论是哲学领域还是其他领域,都不能不追溯到道的这一基本规定,不能不由此出发,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执一统众,纲举目张,真正从理论架构中,从内在层面上探讨其影响发生的根源和作用的方式。
道家思想对后代文艺理论的影响当然也不例外。早先那种仅仅着眼于若干命题、范畴的理解其实并非探本之论,在诸如“大音希声”、“虚静”、“言不尽意”等观念之后,还掩藏着更为深层的决定性因素。较之这些命题、范畴,道家的本体论思想、本原论思想乃至方法论的影响要更为深刻、久远得多,因为这些命题、范畴都植根于道家的思想体系,都是由道这一基本范畴衍生出来,而有其自身的逻辑构成。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从道家本体论思想入手来考察其对后来文艺理论的影响,以期能够更好地认识道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建构中的作用和意义。限于篇幅,本文的考察主要是文艺创作论,至于影响的其他方面则留待另文。
一
先秦思想家中,尤以老子对道的论述最多,事实上,道是老子哲学的中心范畴,老子的整个哲学都是围绕道范畴而展开的。老子第一个真正赋予道以本原论、本体论的意义,道家既由此而得名,后世论道者也不能不追溯到老子。
老子笔下的道具有双重性质,即本原论与本体论的统一。我们看老子对道的描述: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二十五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复之。(五十一章)
老子首先将道看作是派生万物的始源,“万物之宗”,天下之母。它不仅先天地而生,而且创生了天地万物。不过,道并不是一个有意志的上帝,不是一个造物主。在老子看来,万物的创生完全是自发自动的,而这种自发自动就是道之为道。换言之,道是老子对推动宇宙万物自然生成、自然变化、自然发展的必然性的抽象表述。道的作用和意义,并不止于创生天地万物,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道仍继续发挥其作用(“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复之”)。它隐在现象之后,作为万物存在的依据。这样,老子之道又带有本体论的意味。
老子一再强调,道是一种超验的存在,它无形无声,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摸之不觉,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我们非但不能凭借感官去直接把握它,甚至不能像对别的事物那样给它一个名字,称之为“道”,只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然而,这又不等于说道是虚无,是零。道是初始,是浑一,是永恒,是绝对,它君临万事万物之上而又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应该说,老子是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从对自然界、人事社会的发展变化的静观默想、比附推演中,得出他对宇宙终极观念的理解的。道是老子的一个假定,一种预设,而这个假定、预设的种种内涵则来自他的观察和体验。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论并有所发展,并以老子之后的道家学派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见知于世。在将道视为天地万物的本原这一点上,庄子与老子并无不同。《庄子·大宗师》道: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 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这就是说,道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尽管无为无形,但它却在冥冥之间发挥着作用。道是自本自根,无所依傍的,鬼帝以之神,天地以之生,同时它还纵横古今,超越时空。这里,本原论的意味是相当明显的。
比较而言,庄子道论更多本体论的成分,所以庄子之道突出了以下特征:
第一,道是永恒的,绝对的。从上述引文中也可看出,道是越时空的存在,它无始无终而又无所依傍,它的存在不依赖于任何条件,相反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最终依据。
第二,道是形而上的,它具有超越性,同时又存在于、体现于万事万物之中,无所不在。一方面,它超越于各种具体有形的事物之上,人们不能凭感官去把握道、认知道,也不能借名言来描述道、传达道。所谓“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另一方面,道又依存、内附于万物,甚至在蝼蚁、在屎溺。道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广,日月得之以行,万物得之以昌。道既超越于万物之上,又贯穿于万物之中。
第三,道是整一的,无差别的。道既然超越于有形的事物之上,那它也就超出了万事万物之间的种种差异。万物是杂、是多,道则为纯、为一。万事万物在形态上虽然千差万别,但体现在其中的道却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万事万物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它们都统一于道。以道的眼光来看,万物原无形态的差异、美丑的差异、善恶的差异,所以庄子主张“道通为一”、“万物皆一”。
第四,道是无目的的,无为而无不为。《大宗师》道:“吾师乎!圣师乎!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雕刻众形而不为巧。”道所成就的一切,都不是有意为之的结果,所以既不能说义,也不得以仁、老、巧等名之。
应该说,庄子之所以强调道的绝对性、超越性、整一性、无目的性,就是为了突出道的本体性特征。尽管与老子相比,庄子之道更多人生体验的意味,更倾向于将体道看作一种人生的极境,但无论老子还是庄子,道作为其哲学体系的终极范畴,都不能不被赋予形而上的特性,并以此来统摄各自的思想体系。而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之所以有别于儒家、墨家、法家等,其根本差异也就在于这种对终极意义的叩问。
如果说在先秦道家思想体系中,道始终兼有本体论与本原论双重意义的话,那么魏晋玄学的出现,又进一步强化了老庄之道的本体论意义。《晋书·王衍传》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所谓“以无为本”,也可以说就是以道为本。本来老子提出有、无范畴,意在说明道是有与无二者的统一,因此无论有还是无,都只是道的一个侧面而不可以名道。何晏、王弼则不作如是观。在他们看来,有与无并不具有同样的意义,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是现象和本体的关系,无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它既是万物之所从出,又是万物之所以成,它能够使阴阳变化,万物成形,贤者立德,不肖者远祸。它的作用是无形的,但又是无限的,包揽万有的。因此,魏晋玄学家在贵无贱有的同时,便将有从老子之道中剥离出去,而等无于道。张湛《列子·天瑞篇》注引何晏《道论》:
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响而出气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规以之员。员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
何晏论道,本体论的色彩相当明显。虽然他也说“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但已较少生成论的意味,他更多的是强调“事而为事,由无以成”。这即是说,道之为道,首先在于它作为万有存在的依据。
王弼则明确等无于道。“道者,无之称也。”(《论语释疑》)王弼发展了老子“道常无名”的思想,认为道既然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不可诘以形名,因此便只能以“无”名之。“无名,则是其名也”。(《老子二十一章注》)他将无看作事物的本体,它无形,无名,但又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其《老子指略》道: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平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故其为物也则混成,为象也则无形,为音也则希声,为味也则无呈。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
王弼反复申述的,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即作为事物之本体的无,它是无定性的,是混一而不可分的。惟其无形无名,所以才为万物之宗,而要想把握无,就必须超越于一切具体的形、名之上。
简而言之,经过魏晋玄学家的改造、发挥,老子有无统一之道被分解为体与用、道与器、本体与现象两个方面,而道家之本体论思想也由此得以光大。
二
老子很少直接谈论美,也不曾有意识地将道和审美问题联系起来。不过,《老子·第一章》中谈到的“妙”,却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范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老子认为,“常道”(根本之道,终极之道)是“常无”和“常有”的统一。“常无”是无定性的,所以老子将“妙”规定为“常无”的特性。“妙不可言”,这是今天人们仍常说的话,但它的确很好地说出了“常无”的特性。作为一个抽象的存在,一个超感官的精神本体,“常无”就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那样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常有”,是天地万物方生未生之际。较之“常无”,“常有”是可以感觉到的,它较为实在,所以老子将“徼”规定为“常有”的特性。“徼”是边界的意思,引申为端倪、形迹,但这种端倪形迹又毕竟只是初现,它尚不十分明朗、清晰,故老子仍将它和“妙”同归之为“玄”。按照苏辙的解释:“凡远而无所至极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极也。”(《老子解》)玄者,深青色也,老子用它来形象地说明道的神妙不测的特征。而玄之又玄,则为众妙之门,亦即众妙之所出。老子此言,既隐含了道作为美的本原的意味,同时也表明妙是一种形上之美,与道、无存在着某种同一性。
所以,魏晋以后,随着玄学的盛行,妙开始进入审美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正如朱自清先生概述的:
魏晋以来,老庄之学大盛,特别是庄学,士大夫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欣赏与批评也在长足的发展。清谈家也就是雅人,要求的正是那“妙”。后来又加上佛教哲学,更强调了那“虚无”的风气,于是乎众妙层出不穷。在艺术方面,有所谓“妙篇”、“妙诗”、“妙句”、“妙楷”、“妙音”、“妙舞”、“妙味”,以及“笔妙”、“刀妙”等,又有“庄严妙土”,指佛寺所在;到于孙绰《游天台山赋》里说到“运自然之妙有”,将万有总归一“妙”,在人体方面,也有所谓“妙容”、“妙相”、“妙耳”、“妙趾”等;至于“妙舌”指的会说话,“妙手空空儿”(唐裴铏《聂隐娘传》)和“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宋陆游诗)的“妙手”,都指的手艺,虽然一个是武的,一个是文的。还有“妙年”、“妙士”、“妙客”、“妙入”、“妙选”,都指人。“妙兴”、“妙绪’、“妙语解颐”,也指人。“妙理”、“妙义”、妙旨”、“妙用”,指哲学,“妙境”指哲学,又指自然与艺术。哲学得有“妙解”、“妙觉”、“妙悟”,自然与艺术得有“妙赏”,这种种又靠着“妙心”。[1](P131)
宋元以后有所谓“神、妙、能”三品论画,妙品居神品之下,能品之上。这虽与老子对妙的理解不尽相符,但究其根源,仍是由老子之妙而来。
当然更直接的,还是老子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希声”,即无声,或者说是听不见的声音。《老子·十四章》道:“听之不闻曰希。”老子的本意,是借“音”(音响、音乐)作比喻来说明“道”的特性。在老子看来,“道”是一种超感官的终极存在,是人的视、听等知觉所不能直接把握的本体性对象。恰如老子经常用“无”、“朴”、“素”、“淡”等概念描述“道”一样,听之不闻的“大音”正意味着“道”的浑一性、形上性。因此,在老子哲学中,“大音”即是“道”,是那个隐藏在现象之后的本体;而与“大音”概念相对的具体的、可以感知的音响、音乐,则相当于本体赖以显现的事物和现象。王弼正是这样理解的:“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同时王弼也指出,“大音”、“大象”的显现离不开具体的音声、形象:“然则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老子指略》)从对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论的影响来说,“大音希声”这一命题在于指出或者说隐含了这样的思想,即最高层次的美是超言绝像的,是浑一不可分解的。一方面,美的显现固然离不开具体的表现媒质;另一方面,对美的把握、领悟又必须有所超越,而不能止于具体对象。
庄子的“天籁说”与此相类。
在《齐物论》中,庄子将所有音响分为三类:人籁、地籁、天籁。“人籁则比竹是已”,所谓人籁,就是人吹奏各种笙簧箫管之类的乐器发出的音响。“地籁则众窍是已”,地籁是风吹自然界各种大小洞窍发出的音响。至于天籁,那是自然界众窍自鸣发出的音响:“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依庄子之意,天籁与人籁、地籁的差别,除了发出音响的物体有所不同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这些物体发出音响。人籁须依仗人力的作用,地籁离不开风的作用,而天籁则完全是自发自动,不假任何外力的。因此,天籁即是自然之道的显现,它代表了最高的美。在《庄子》一书中,与天籁相类似的还有“天乐”,这是一种“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的音乐,它无声无形却又无处不在,令人“无言而心悦”(《天运》)。
天籁说集中体现了庄子法天贵真、崇尚自然的思想。一方面,与老子“大音希声”理论相似,庄子天籁说对后世文艺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自然之美、天真之美、浑朴之美的追求,反对人为的雕饰;另一方面,庄子并没有将人籁、地籁与天籁的差异绝对化,而承认三者仍可以沟通。正如释德清《庄子内篇注》所说:“果能忘机,无心之言,如风吹窍号,又何是非之有哉!”就人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庄子实际上是赞成自然而不废人为,人为而不失自然的。就是说,如果人为能够遵循自然的原则,能够“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话,那么这种人为并没有违背自然之道,而仿佛是自然假手于人来完成一样。清人刘熙载《艺概》论书法道:“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天复人也。”所谓“立天定人”,是说创作应从自然出发,而所谓“由天复人”,则是说创作应功夺造化,回复自然。这实际上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最后达到“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矣”的境界。
阮籍《清思赋》云:“余以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是以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可以覩窈窕而淑清。”自魏晋以下,人们开始认识到艺术之美并不仅仅在于表现形式,艺术创作也不仅仅是表现技巧问题。玄学所关注的有无之辩在弘扬道家本体论的同时,也启发了艺术家对艺术之美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既然有不过是无赖以显现的手段,而真正的美乃在于无本身,那么,对于艺术创作来说,较之表现形式、技巧,作品的表现对象无疑更值得关注。艺术之美实际上在虚而不在实,在神而不在形,逐渐形成时人的共识。诸如画论中的以形写神,乐论中的声无哀乐,人物品评中风神韵致,都应该看作是此种价值取向的表现。文论亦然。六朝文论尽管不乏关注形式技巧者,但作品之内美也开始进入理论家的视野。如刘勰论文,既讲情采之美,同时又提出了风骨、隐秀等重要的美学范畴;钟嵘论诗,以“文已尽而意有余”释兴,于丹采之外,复倡滋味。所有这些,一方面固然可以归因为随着文艺自身的发展,人们对文艺本质理解的有所深化,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道家本体论思想影响所起的作用。
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重神贵虚的传统。从中唐刘禹锡提出“境生于象外”,晚唐司空图主张“辩于味而后可以言诗”,到宋人苏轼认为“味在咸酸之外”,范温以“声外之音”喻韵,严羽谓唐诗妙处“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乃至明清画论中所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笪重光《画筌》),“画有有笔墨处,画之妙在无笔墨处”(戴熙《习苦斋画絮》)等等,尽管表述各异,但中心指向却是一致的。同样,中国古代那些重要的美学范畴如气、神、韵、味、意境等,也都在虚而不在实,在无而不在有。这当然不是偶然,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先秦道家的本体论思想。
三
道家本体论思想对后代艺术创作论影响的又一重要方面,是主体创作心态或审美对象的把握方式。
最有代表性的当是虚静说。所谓虚,指排除主观的成见、欲念,保持一种空明的心境;而静则是指内心的平和、宁静。虚静说最早源自先秦老子关于体道心态的描述,《老子》第十章中说“涤除玄览”,第十六章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意思都是说对道的体悟,必须消除内心的欲念、成见,以一种空澈澄明的心境来观照道,这才能把握道周而复始的变化,领悟道的精微要妙。
老子有关虚静的思想与其对道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道既然是隐藏在现象之后的本体,是决定事物存在意义以及发展变化的终极依据,那么道本身就必然是一种超越于任何具体事物之上的存在,也就是说,道具有形而上的特征。老子认为,道是无,是浑一,是绝对,因此道不可诉诸语言文字,不能凭借概念、推理等思维形式去把握。对道的领悟不同于对具体事物的认知,它要求主体必须具备特殊的条件。这就是去除主体的知识成见,摆脱主体的欲望杂念,消解主体的心智活动,使主体处在一种无己无欲,无识无虑,无是非得失,无巧拙毁誉的心境之中,这才可能把握道,领悟道。老子之所以反复申述“绝圣弃智”、“绝学无忧”,赞赏赤子、婴儿,主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即是基于此种认识。
与老子主张“道可道,非常道”相似,庄子也认为道不可言说,不可形名。《庄子,知北游》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既然不可闻,不可见,不可言,那么道究竟能不能把握,如何把握?《庄子·天地》讲述了一个故事:
黄帝游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得之乎?”
故事中的“玄珠”比喻道。“知”即智,谓巧智、理性;“离珠”是传说中视力最好的人,此处泛指感官;“喫诟”指巧妙的语言,而“象罔”则是空无所有。“知”、“离朱”、“喫诟”都不能找回“玄珠”,“象罔”却能得之,这正表明对道的领悟必须超越语言、感官和知性,必须以一种空澈澄明的心境来观照。在《人间世》中,庄子将此意思表述得更加清楚:“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认为,人的感官只能感知外在的现象,理智(心)的作用固然可以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但仍不免将对象进行分解,因此都不能真正把握道,只有像气那样一种空虚澄明的心态,才有可能领悟到道的底蕴。道只呈现于空明的心境,这空明的心境就是心斋。换句话说,只有空无所有,才能包揽万有。此外,庄子还以水作比喻说明“静”的重要:“水静则明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也,万物之镜也。”(《天道》)平静的水面能够映照出岸边的景物,可以作为工匠衡量平直的工具,人的精神世界也与水相似,惟其平静,才能洞悉事物精微的变化。圣人之所以能够洞察天地万物,领悟道的精神,就是因为他的心境极度平和宁静,如同不染纤尘的镜面。
《庄子》中不少寓言故事都谈及虚静问题,如“梓庆削木”、“轮扁斫轮”、“庖丁解牛”、“宋元君将画图”等。概括起来,虚静心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去欲、去知、去己。所谓“去欲”,指消除种种功利欲望和是非得失的计较,如“梓庆削木”寓言所记那位制作钟架的木匠,没有庆赏爵禄、非誉巧拙之想;或如《田子方》中提到的那位“解衣槃礴”(脱去衣服,盘腿而坐),旁若无人的画师,如此方能说是“去欲”。“去知”,指消解心智活动,庄子借“庖丁解牛”故事说明,语言文字传达的不过是糟粕,真正的大道并不能由概念来传达,要想进入体道境界,必须排斥理性的认知而代之以感性的直觉。“去己”,主要是泯灭物我的区别,消除主客的对立,真正与物融为一体,我即是物,物即是我,如“庄周梦蝶”所说:“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一旦做到去欲、去知、去己,也就意味着进入到虚静状态。
应该说,老子与庄子的上述言论并非专就审美而言,他们的本意乃在描述体道的心境,但虚静说却与审美、与艺术创作所需要的心态不无相通,特别是在审美的非功利性和非理智性这一点上,与老庄对体道心境的认识无疑是非常相似的。只有排除对对象的占有欲、利用欲,将对象真正作为审美对象去感受、体验,我们才可能获得美感。而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在感情激烈的时候纵情挥洒,产生佳作的情况固然也有,但更为常见的则是在冷静的回味、精心的构思之后形诸文字。严格说来,创作并不是将心中所感直接倾倒出来,而是需要一种自我审视和自我观照,需要内、外双方面的静观默察。也正因为如此,虚静说对后来的文艺创作及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论艺术构思便指出:“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将虚静视为进行艺术构思的重要前提。唐代诗人刘禹锡认为:“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秋日过鸿举法师便送归江陵引》)只有清除杂念,才能使内心保持空虚以容纳万物,从而创作出好的作品。宋代苏轼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在《送参寥师》一诗中写道:“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空与静是使诗歌创作臻于高妙之境的重要条件,惟其平静,才能洞察天地万物的变化;惟其空虚,才能将大千世界收入自己的视野。这既是苏轼本人诗歌创作的经验之谈,也道出了虚静说之于艺术创作的价值和意义。
还应该提到庄子所说之“心斋”、“坐忘”。作为虚静说的另一种表述,“心斋”、“坐忘”与“虚静说”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心态理论的基本内核。上文曾引《庄子·人间世》语:“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斋的本义,谓古代祭祀前洁净身心以示虔诚,故庄子所说“心斋”即是清心寡欲,排除思虑杂念,保持内心的空明纯净。庄子的“心斋说”与老子体道思想有着直接的关联。《知北游》假托孔子向老子请教如何认识道,老子答曰:“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话虽未必真出自老子,但其净化心灵、去除智识的要求与老子思想无疑是一致的。在《庄子》一书中,与“心斋”类似的说法还有“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弃知,同于大通,是谓坐忘。”(《大宗师》)忘却形体,放弃智虑,与道为一,这就是“坐忘”。可见,“心斋”也罢,“坐忘”也罢,都是体道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状态。
“心斋说”之于审美和艺术创作的要义,在于突出了主体心境的特殊作用。审美的实现,除了审美主体和客体两个要素之外,还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主体的审美心境,这才能在审美主客体之间建立起关联。而所谓主体的审美心境,也就是去除功利意识、认知意识和取消物我之别。“心斋说”所以为后来谈艺者称引,对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产生重要影响,原因就在于此。
“神遇说”其实也应该置于这一理论构架。《养生主》篇中庖丁的经验之谈:“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枝经肯綮之未尝微碍,而况大軱乎?”从文艺创作的角度说,庖丁解牛的境界,也就是艺术创作的一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此外,“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作为一种感受,一种经验,与现代艺术创作中的艺术直觉和非理性现象等问题也是相通的,在宋元以后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它往往被看作是天才之作的标志,或者说是产生“逸品”、“神品”、“妙品”的必要条件。
四
道家本体论思想对后代文艺创作论的影响还表现在言意关系上。
老子对道的理解决定了他在言意关系问题上的态度。《老子》开篇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已包含了言不尽意的意思。在老子看来,道是“无”,是处于混沌状态的不可分解不可名言的整体,而包括语言在内的任何具体事物,都属于“有”的范畴。“有”只是道的部分显现,整体之道是“有”无从表现的。同样,语言能够描述的也只是道的片断、局部,而难以描述恒常之道、完整之道。道作为一种终极性存在,它既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又超越于万事万物之上,从而不可究诘,不可名言。所以老子又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五十六章)由老子奠定的这一思想,对后来的中国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有必要指出的是,老子虽然说“道可道,非常道”,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语言的意义。诚然,大音希声,妙不可言,然而道不离器,有无不二仍是老子思想。上文曾引王弼语:“然则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道既然因器而显,则因言传道并非绝对不可能。正是在这一点上,庄子在继承老子思想的同时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天道篇》中,庄子明确提出了言不尽意的问题:
世之所贵道(称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有所指向),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庄子认为,书籍是用文字写作的,文字本身并不珍贵,值得珍贵的是文字所传达的意义。但意义本身也还不是价值所在,因为“意有所随”,即意义是指向道的,道才是决定书籍价值的最终因素。而道却是语言所不能传达的,因此世人看重的书籍对庄子来说并不值得珍贵。接下来庄子讲述了轮扁斫轮的故事,表明书籍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真正的精微要妙之处是无法口传言授的。应该说,庄子并没有否认语言能够传达意义,但意义并不就是道,因此肯定言能尽意和指出道不可言二者并不构成矛盾。在《秋水篇》中,庄子再次谈到言不尽意:“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的意思是说,语言只能描述对象的外在形貌,意识(思维)可以把握对象内在的精微之处,然而,在精、粗这两个认识对象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存在,一个无所谓精,也无所谓粗的存在。对这个“不期精粗”的存在,无论语言还是思维都无法把握。庄子实际上是从语言文字的局限、人的思维的局限,以及客观世界的无限性等诸方面指出了言不尽意的绝对性。
在肯定言不尽意这一前提之下,庄子提出了“得意忘言”作为解决言、意矛盾的方法。《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在庄子看来,言和意的关系恰如筌(一种捕鱼的工具)和鱼、蹄(捕兔的网)和兔的关系一样,是一种工具、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既然言只是传达意的工具而非意,因此就不能执著于言,必须忘言,忘言才能得意。当然,庄子所说忘言,并不是排斥或放弃语言,而是说接受者在理解时不能过分拘泥于语言,以致影响了对“意之所随”的领会。
除道家外,先秦时期儒家经典之一的《周易》也持“言不尽意”说。《系辞传》假托孔子语:“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这里一方面肯定言不能尽意,另一方面又指出象能尽意。与道家言意观相比,《周易》在言、意之间增加了一个环节,即象。为什么言不能尽意而象却能尽意呢?因为象具有象征、隐喻等功能,从而较之语言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为宽泛的内涵。
正是在整合儒道两家言意观的基础上,魏晋时期著名玄学家王弼对言意问题作了全新的论述。
王弼分析了言、象、意三者的关系。他既肯定了言能尽象,象能尽意,因此可以由言以观象,由象以观意;同时又指出,言只是象之蹄,象只是意之筌,要想真正得意,就必须超越言、象,由个别进入一般。王弼对于言意问题的发展主要有二:一是他将象作为连接言、意的中介,二是他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就前者言,王弼指出了语言是象的构成与存在方式,而意通过象得以呈示;就后者言,王弼强调,尽管言能尽象,象能尽意,但言并不就是象,象并不就是意,所以,忘言才能得象,忘象才能得意。此前《庄子》、《周易》旧说固然是王弼论述言意象问题的出发点,但《庄子》、《周易》旧说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周易》“立象以尽意”的说法容易使人误以为把握住象也就把握了意,《庄子》筌蹄之喻也会让人理解为得意之后再弃筌蹄(言、象),这其实是不对的。言者所以存象而非象,象者所以存意而非意,因此存言者非得象者,存象者非得意者。这就如同筌蹄虽然捕获到了猎物,但这猎物此时尚未到猎(渔)人手中,以存象为得意者正是那个执有筌中之鱼、蹄中之兔的猎人。这不能真正算是得意。只有舍弃筌才能得鱼,舍弃蹄才能得兔,同样,只有舍弃(超越)言、象,才能真正得意。应该说,到了王弼,才真正从理论上理顺了言、意、象三者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言、意、象三者的矛盾。
从哲学角度看,言意象问题既属于认识论的领域,同时也是阐释学关注的对象,而其实质可以说是有限与无限的关系问题。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言不尽意说与文艺创作、审美鉴赏存在着共同之处,从而对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魏晋以后,一方面是汉代泥于字句、寻求所谓微言大义的繁琐经学渐趋衰微,而以删繁就简、注重义理为特征的玄学大为流行,这从理论上扩大了言不尽意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文学自身的发展渐趋自觉,其抒情性特征日益明显,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见解开始得到诗人和文学理论家的认同,并在这一时期的文论著作中表现出来。如陆机便将“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作为《文赋》探讨的中心问题,而特别论述了创作过程中物、意、言三者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也一再论及言和意的不一致性,认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语言很难完全传达出作家的心意。“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那更是“言所不追,笔固知止”。刘勰用“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来形容表现“思表纤旨,文外曲致”之难,认为它们与饮食至味和斫轮绝技一样,都是微妙不可言喻的。再如唐代刘禹锡《视刀环歌》说:“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宋代苏轼论辞达之不易,谓:“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一不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苏轼此论,看似别出心裁,其实不过是将庄子言意观用于文章写作之道,与陆机所说“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并无二致。
由言不尽意、得意忘言出发,中国古代文艺家便将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弦外之响作为创作的审美追求,如司空图讲诗之美在“咸酸之外”,严羽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为诗之上品。尤其是中晚唐以后,禅宗思想的影响日渐扩大,而禅宗之言意观恰与老庄之言意观殊途同归,故而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及理论大多取言不尽意说。反映在创作和理论上,便是以诗证禅、以禅喻诗。而且,在理论的表述方式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言简语短,点到为止,不作长篇大论的分析论说,多用形象的比喻等。如传为司空图所作《二十四诗品》,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既然“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诗),那么干脆不辨,留待读者自己去体悟。显然,这种理论表述和创作的一致性,正植根于先秦的言不尽意说。
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在其《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将受道家思想影响而形成的文学理论称之为“形上理论”,并认为,“对于最后可能的世界文学理论,中国人的特殊贡献最有可能来自这些理论”。[2](P27)虽然刘若愚更多的是着眼于道家本原论思想对后来文论的影响,但他这一看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文论并非如先前个别论者所说缺乏体系,而确有其独特的哲学渊源,有其内在的逻辑构成。即使是那些零散的只言片语、印象式的批评,实际上也都有共同的中心指向,都源自一个共同的文艺观念。以此为切入点,使中国古代文论潜体系得以凸现,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之特征与价值,同时也可为中西比较诗学的深化、为当代文论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收稿日期:2003-0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