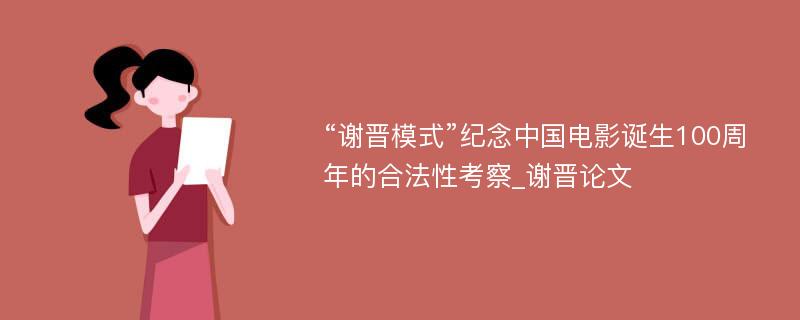
重审“谢晋模式”的合法性——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影论文,合法性论文,周年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6年6月,在上海“城市文学、电影讨论会”上,当时任教于上海财经学院的朱大可先生,以他惯有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发言风格,炮轰谢晋,称“经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的反复经营,某种我称之为谢晋模式的东西便进入了中国电影史,成为最令人关注的文化现象之一”,而这种所谓“谢晋模式”“是中国文化变革进程中的一个严重不协和音,一次从‘五四’精神的轰轰烈烈的大步后撤”[1]。尽管朱大可先生的观点随即遭到激烈批评(赞成者也不乏其人),但从此,“谢晋模式”作为一个命题进入了中国电影批评史,并成为80年代末期中国电影批评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短短几年,发表的相关文章近百篇。
从某种意义上,笔者认为,关于“谢晋模式”的讨论是中国电影批评走向学术化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后殖民主义者对第五代导演的批评,由此命题而产生的部分论文(近十篇),摆脱了以往中国电影评论主题分析+人物分析的批评模式和印象式观后感的浅显姿态,通过对结构主义叙事学、原型批评理论等学术话语的运用初步显现出一定的学术深度。而回头看20年的谢晋研究,对“谢晋模式”的讨论不能说唯一有学术价值,至少也可以说是最有学术价值的命题。这一命题在很长时间内规定了谢晋研究的讨论方向,思维习惯,有点类似于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李约瑟命题。然而正如中外科学史告诉我们的,越是那些看上去不证自明的命题,越是需要进行考古学式的合法性质疑和有效性界定,作为中国电影批评经典命题的“谢晋模式”自然也不例外。
一、“谢晋模式”的合法性质疑
1.外延考察:“谢晋模式”的有效边界在哪里?
在朱大可提出所谓“谢晋模式”并予以激烈批评不久,电影界重量级的研究者邵牧君即作文“为谢晋电影一辩”。邵先生辩护的焦点在于“‘谢晋模式’是否真有那些令人生厌的缺陷”——这固然无可厚非,然而他认为“谢晋电影是否已形成了某种模式,这不必争论”[2],则未免轻巧,事实上,首先应当追问的恰恰是:是否存在或者在多大范围内存在一种所谓的“谢晋模式”。
关于“模式”,《现代汉语大词典》解释为“标准的形式或样式”,《辞源》解释为“pattern”亦译“范型”,“一般指可以作为范本、模本、变本的式样”。作为“范本”,其最大的特点是“可重复性”。我们的问题是:“谢晋模式”在什么范围内被重复?作为一个命题,“谢晋模式”的外延在哪里?
朱大可是以中国电影史为背景谈论“谢晋模式”的,然而纵观百年中国电影史,无情的阶级斗争和薄情的游戏娱乐消耗了中国电影片库里的绝大多数胶片,他所总结的“以情感扩张蛊惑观众”、“以道德神话消解矛盾”的所谓“谢晋模式”的重复率并不高。或者我们可以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电影史中寻找所谓的“谢晋模式”,中国电影每年上百部的产量,我们固然无法对几千部电影一一统计,但是考察从第三代到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作品,究竟有多少在重复所谓的“谢晋模式”呢?即便在谢晋自己的作品范围内考察,作为从影近半个世纪,有近30部电影问世的大导演,谢晋自觉地拒绝重复,谋求超越,所谓“谢晋模式”也只涵盖了谢晋作品中的极少数。事实上,尽管对“谢晋模式”的内涵言人人殊,但是被论者反复提到的所谓“谢晋模式”的电影,不过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3部当代史题材的作品,至多再加上《高山下的花环》。也就是说,所谓“谢晋模式”,其有效场域,只局限于20世纪80年代谢晋本人不多的几部作品。这样狭窄的范围,如此低的重复率,称之为“模式”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2.内涵考察:“谢晋模式”是谁的模式?文学的抑或电影的?
1989年,余纪先生在其总结性的论文《解放的思想与思想的解放》中认为:“朱大可等著者有一共同的偏差,那就是对‘模式’这一概念自始至终未曾给予科学的说明和界定,因而至今仍不清楚,所谓‘谢晋模式’,究竟是一个技巧风格层面的问题,还是一个思维逻辑,即心理学层面的问题”,而按作者的意见,“讨论谢晋模式,必须在心理学层面进行”。何谓心理学层面呢?余纪的回答是,所谓心理学层面,即“谢晋创作中固有的思维逻辑,思维习惯”,“具体说来,就是研究其作品常见的叙事安排”。事实上,无论是朱大可本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大都把“谢晋模式”的内涵界定为某种叙事上的特征,如此一来,我们不禁要问,所谓“谢晋模式”,究竟是文学的模式还是电影的模式?该由文学家负责还是导演负责?
1986年的朱大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原型批评理论的了解或许也不过一鳞半爪,但想来是他对影像语言的更为陌生,使他一开始就对“谢晋模式”作出了叙事学的界定:“正如一切俗文化的既定模式那样,谢晋的道德情感密码又总是按规定程序编排,从中可以分离出‘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善必胜恶’四项道德母体,无论《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高山下的花环》,总有一些好人(罗群、许灵均、靳开来)不幸误入冤界,人的尊严被肆意剥夺,接着便有天使般温存善良的女子翩然降临(冯晴兰、秀芝),抚慰其痛楚孤寂的灵魂,这一切便感化了自私自利者(赵蒙生母子)、意志软弱者(宋薇)和出卖朋友者,既而又感化了观众。上述冥冥道德力量有力保证了一个善必胜恶结局的出现。”[1]
邵牧君先生曾暗讥朱大可的批评是“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因为他缺少“实事求是的分析和颠扑不破的论据”。的确,朱文中似是而非之处太多,许多观点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毋宁说是跟着感觉走的放言。然而,有意思的是,随着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原型批评理论的引进,一些论者借着这些现代批评方法恰恰坐实了朱大可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马军骧发表于1988年的论文《谢晋电影的叙事结构和文化构型》,就是一篇地道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分析,它杂揉了索绪尔语言学、普洛普结构分析与荣格的原型理论,通过对谢晋四部电影《牧马人》、《天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的纵向比较阅读,从男主人公被恶势力所迫害中读出了中国传统的“忠臣原型”,从女主人公身上读出了作为拯救者的“生殖女神原型”,而拯救则是通过“家庭关系”重构实现的,这种拯救同时也是对崩坏的伦理秩序、人际关系的修复[4]。应雄发表于1990年的论文《古典写作的璀璨黄昏》同样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谢晋电影中的“家道主义”进行了分析论证,从而呼应了朱大可提出的“恋家主义”模式[5]。
毫无疑问,电影也是一门叙事艺术,对电影进行叙事学分析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然而同样毫无疑问,叙事作为电影与其他艺术尤其是文学的共性,是最缺少电影独特性的,因此才会有理论家把电影的叙事性称为电影的文学性。从叙事学角度归纳出来的所谓“谢晋模式”,是个早在前影像的文字状态就存在的模式,或者更直白地说,是个文学意义上的模式。而论者提到的几部模式化的谢晋电影,恰恰都改编自文学作品,而且,对照小说原作和电影,谢晋无论在故事情节、叙事结构还是角色定位上都十分忠实于原作。如此,把上述结构上的特点命之为“谢晋模式”,并归罪于谢晋,岂非张冠李戴?
其实,评论界并非没有注意到上述问题,早在1986年钟惦棐先生就指出:“如今被称为‘谢晋模式’的,其中确有不少是文学方面的缺陷”,然而或许囿于“谢晋模式”这一命名,钟先生紧接着话锋一转,强调起“拍成电影,自然也就包括导演自身的认同”了[6]。
3.追光灯效应:谢晋在“谢晋模式”中的作用
偌大的舞台,全场黯淡,追光灯突然亮了,光柱下明星引吭高歌,于是在台下观众的眼里,舞台上只有明星一个人在表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舞台的某个地方,在追光灯之外,有乐队在为之伴奏,有合唱队在为之伴唱,有舞者在为其伴舞,追光灯对舞台来说,既是一种澄明也是一种遮蔽,遮蔽与澄明同时进行。谢晋在“谢晋模式”产生过程中起到的正是类似于追光灯的效应。
虽然“谢晋模式”在中国电影史乃至谢晋电影中有效性极为狭窄,然而一旦放之于文学史,却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源远流长而又重复率极高的模式。不是早有论者找到了它与古代诸如忠臣蒙冤、公子落难、女神拯救等原型间的传承么?也早有论者指出由于历史生活本身的规定性,所谓“谢晋模式”不过是80年代反思文学的普遍形态。但是,谢晋借助电影这一“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传媒,把上述几部作品突出出来,就象追光灯把明星从舞台上哼唱着同一曲调的合唱队中间突出出来,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这些具有一定模式性的作品是由于谢晋才出现的。
如果把舞台想象成中国电影乃至谢晋电影的表演舞台,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所谓“谢晋模式”只是舞台上很不起眼的一个小角色,舞台上除此角色(歌者)外,还有操练各式乐器的乐手,有形态各异的舞者,这时追光灯的效应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遮蔽,让人忽视了谢晋本人以及当代中国电影中丰富多彩的其他作品。当然这枚追光灯的操控权似乎更掌握在批评家手里。
二、“谢晋模式”的合法性再论证
从上述质疑中,我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热闹一时的“谢晋模式”讨论,不过是个伪命题,至少是个有效边界极为狭窄的命题。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一命题在80年代后五年,被电影批评界乃至中国文化界反复言说,热烈争论。仅仅解释为当时学人的不够严谨显然是无法服人的。
反思是学术研究者的起码品格。这意味着,当我们理直气壮质疑“谢晋模式”的有效性时,我们必须时时眷顾质疑本身的有效性。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命题的有效性往往并不取决于命题自身,而是它所放置的场域。“谢晋模式”在电影领域里的合法性可能是微弱的,但当我们把它放置在80年代的文化大时空下,背景扩展了,奇怪的是,它的合法性反倒加强了。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而其原因,则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早已指出的,盖因80年代中国的一切文化话题都可以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寓言。
而一旦我们把“谢晋模式”讨论看成8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事件,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电影圈外的学人(如朱大可、李劼、戴锦华、汪晖等)都热烈参与了讨论甚至成为主力,为什么讨论集中于叙事学,集中于电影的表意层面,而不是影像分析。而这一话题在1986—1990年间的延续,呼应了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进程,是这一进程的载体,也是其组成部分。关于这五年的“谢晋模式”的讨论,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6年朱大可等对这一命题的提出,第二阶段是1986—1989年学界对这一命题的结构主义论证,第三阶段是“后1989”汪晖等对这一命题的意识形态自觉。考察这一讨论的不同阶段,我们看到的是80年代后期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分分合合的镜像。
1.谢晋模式”的提出与两种话语的错位
从发展电影工业的角度,电影创作中的模式存在并非坏事,好莱坞成熟的类型片正是好莱坞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上强势地位的保证;从电影艺术发展的角度,我们当然要鼓励创新,反对模仿。但是1986年朱大可及其同伴们对所谓“谢晋模式”的批判,并非出于鼓励艺术创新的目的,而是因为它“以情惑人”的美学对“主体独立意识、现代反思性人格和科学理性主义”进行了“含蓄否定”,因为它的“道德神话”化解了社会冲突,因为“谢晋所一味迎合的道德趣味,与所谓现代意识毫无干系,而仅仅是某种被人们称之为‘国民性’的传统文化心态”,即所谓“电影儒学”,其标志是“老式女人的标准图像”和一种“恋家主义”。
朱大可上述批评话语的核心概念是“传统与现代”,是站在以“五四精神”命名的所谓现代的立场上对谢晋电影中“传统因素”进行批判。这正是80年代激进精英的普遍立场。谢晋电影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自觉的体现者,而主流意识形态不可能一味否定,必须有所守成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其中民族文化的某些传统内核就是他们守护的要件之一。主流文化对民族传统的上述立场,也是对文革极左意识形态彻底否定传统文化道德的一次有意反拨(例如谢晋电影对家庭的重视一直颇遭诟病,然而,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批判只能通过人物命运来实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具体的人一定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中,如果说谢晋电影突出了家庭关系被人诟病,那么除此以外故事还能放在哪里呢?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怕只剩下一个同志关系、单位关系、革命关系了。难道我们此前的电影,尤其是文革样板戏,不正是一味集中于此,极端忽视否定家庭关系吗?谢晋事实上正是出于对上述极左习惯的反拨,而突出人性的、人情的家庭)。然而80年代激烈否定文革的精英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反倒与文革极左观念站在了一起,这不能不让人深思。余英时先生认为在态度和形式上,80年代的知识分子精英延续继承了“五四”以来包括文革在内的激进性[7],是为明言。其实不仅在形式上,就“全面谴责中国文化传统”这一点来说,两者在内容上也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朱大可对所谓“谢晋模式”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其目的仍不过是要进行“扬弃性超越”。又打又拉,出现裂痕但试图弥补,这正是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精英与主流意识形态间的暧昧关系。毕竟文革后的较长时间内,两种话语在反对文革、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上曾经相互支持、亲密合作过。
2.“谢晋模式”的论证与激进话语的文化反思
朱大可对谢晋电影中传统要素的批判,明显受到当时方兴未艾的知识精英文化反思思潮的影响。而随后马军骧、应雄等人运用结构主义与原型批评方法对这一模式的论证,则成为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反思洪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革以后中国思想界进入了一个“反思时代”,为了解释文革产生的原因,在摒弃了文革自身的“意识形态对立”解释系统后,反思主要针对中国的政体、民主制度,然而一方面由于这一向度的反思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牵制,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步步推进的反思逻辑,更重要的是,反思者自觉不自觉地模仿“五四”包括它的文化决定论,加上其他一些偶然因素,于是在80年代中期,反思掘进到了民族文化层面,知识精英们试图一劳永逸的在民族文化中发现制约中国发展的原型结构,解释文革产生之谜。这一思路带来的影响最大的成果当属金观涛、刘青峰的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理论。
与上述反思进程的要求相适应,适合深度思维模式的“结构主义”方法论和“原型批评”理论被广泛使用。一时间,无论文学评论、历史研究还是泛文化批评,“结构、模式、原型、母题”满天飞,人们孜孜不倦试图找到中国文化的终极秘密。电影界对所谓“谢晋模式”的研究既是受这一思潮影响而产生的结果,也是这一思潮的表现。
然而正如“寻根文学”中既寻到了韩少功的批判对象“丙崽”(《爸爸爸》),也寻到了阿成的理想人物“王一生”(《棋王》),当人们把目光转向传统文化时,既有人发现了负面的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也有人发现了正面的传统文化中温情可贵的一面(也有人发现了所谓儒家文化现代转化的可能)。前者是当时激进的知识精英们凝视的对象,后者则是保守的主流意识形态瞩目所在,于是在文化反思潮流中两种话语出现了分歧。当然在80年代后期,前者在知识界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因此体现后者思路的谢晋电影受到批判也就不足为奇了。
3.“谢晋模式”成为他者与两种话语的决裂
1990年第2期《电影艺术》上,同时刊登了多篇对谢晋电影的评论,其中戴锦华和汪晖的两篇值得注意,虽然他们并没直接使用“谢晋模式”这样的字眼,但是他们对谢晋电影“历史与叙事”、“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的揭示,仍然是在总结一种“谢晋模式”。而且由于写作时间的特殊性,他们眼里的“谢晋模式”,以及他们在阐释“谢晋模式”时的姿态就颇有意味了。
戴锦华在其《历史与叙事》中这样解读谢晋电影的历史叙事,“他总是在用历史——刚刚逝去的世界与时代来阐述并界定着现实与今天”,同时“他要依据现实政治的主旋律来定义历史,不是历史的背负,而是历史的消解”,“死者必须死有所值,死者必须在精神上复生,今天必须与历史对接,生者才能得到抚慰,时代政治主题才能获得合法化成立”。戴锦华明确揭示了谢晋历史叙事的现实功能,即对现实政治合法性的维护和论证。然而性别视角限制了戴锦华的意识形态分析,她关注的是写进电影中的女性叙事,是从《红色娘子军》到《天云山传奇》再到《芙蓉镇》女性身份和功能的变迁[8]。
汪晖认为谢晋具有某种“以政治为天职的人”的素质,因为他的电影“不断地寻找和创造一种信仰体系,一种对于现实统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信仰,一种用以支配人们在中国社会的特定的‘命令—服从’关系中行动的基本原则”。汪晖认为,文革结束以后,“当对一切政治意识形态的幻灭本身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谢晋试图在历史的废墟上迎接现代虚无主义的挑战,创造一种肯定性的意识形态”,然而,“既要揭示历史悲剧的残酷性,又要表明这个历史悲剧不足以动摇那个造成悲剧的‘权力关系’的合法性,这个历史的窘境迫使谢晋采取了一系列的策略来重新表述它的政治信念,而重新表述的过程当然也包含了对于他们政治信念的修正和补充”,这“一系列的策略”,就是汪晖试图揭示的谢晋电影的“秘密”。
这个所谓秘密,这个总策略,就是对政治进行道德化的重写,把政治事件置换成道德事件。通过这种置换,谢晋成功地“把信念体系与以这个信念体系作为自身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人及其‘命令—服从’关系区别开来”(例如在《天云山传奇》中把吴遥和党组织区分开来),这样“对特定权力关系的否定才能无损于信念本身”;把“作为‘命令—服从’关系中的权威人物”与“整个权威系统”加以区别(例如把毛泽东和党中央区别开来),这样,“个别权威人物以至相当普遍的权力者的过失才能不导致对现实统治秩序的怀疑”;同时适应现实政治秩序自身的改革,也对原有的信念体系进行了更新,使之能为现实的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和道德合理性的基础(例如《天云山传奇》中把敢于纠正错误、勇于创造未来作为党重新确立合法性的基础;例如《牧马人》中把民粹意识、对土地的热爱等民族主义理念吸收进主流意识形态);那些“人们据以抗争和生存的素朴的信念和感情”由此也被“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并与原有的信念体系结合起来”,作为“新的合法性证明而上升为一种主旋律”(例如《天云山传奇》中罗群对党的“忠诚”、冯晴兰对罗群的“同情”;《芙蓉镇》中人性的坚韧和原始生命力的正当等)[9]。
然而,当我们阅读上述分析时,我们读到的难道仅仅是谢晋电影的秘密?难道这些不都是后文革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重建的策略?在戴锦华和汪晖的眼里,谢晋的身份不再暧昧,而是清晰地定格在“以政治为天职的人”(汪晖),他的电影则被明确视为“一系列意识形态铭文与实践,意味着一种真正的主旋律式的艺术”(戴锦华)。谢晋身份在这一时段终于被确认,笔者认为,其功倒不在谢晋研究的深入,而是因为在1989年知识精英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间发生了彻底的分裂,知识精英开始把谢晋电影及其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他者”看待。而且由于1989年主流意识形态再次遭遇合法性危机,后1989的知识精英们——正如戴锦华和汪晖文章所表现的,关注的不再是这个“他者”对传统文化道德的回归和维护,而是直接涉及它的合法性问题。
谢晋电影可以在最原始的意义上被视为共和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镜像”,从50、60年代的《女篮5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到70年代的《海港》、《春苗》,再到80年代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直到90年代的《鸦片战争》,谢晋不断调整自己的叙事策略,在维护民族精神昂扬向上的同时也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提供论证。因此,考察知识界对谢晋电影批评的变迁,就是考察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变迁,也就是考察他们在国家系统中身份的变迁。中国知识界关于“谢晋模式”的讨论,由此也就可以被看作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立场嬗变的一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