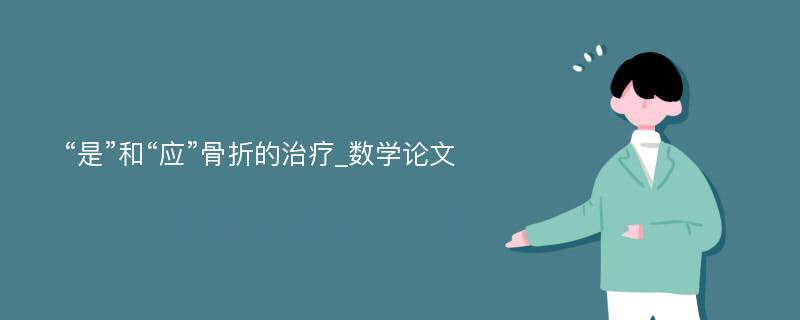
治疗“是”与“应该”的断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致力于一项消解工作,指向那个著名的哲学难题:“是”与“应该”的断裂。不是回 答它,而是分析其断裂性的自明性,取消其效力。途径是追问“事实作为事实”如何可能。
断裂的结构
所谓“是”与“应该”或“事实”与“价值”的对立,指的是从“事实”不能够合乎逻辑 地推导出“应该”如何的结论。这种见解以休谟的表述最为经典:
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 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做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 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 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 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 明 ;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 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不过作者们通常既然不是这样谨慎从事,所以我倒想 向读者建议要留神提防;而且我相信,这样一点点的注意就会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学体系。 (注: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09~510页。)
休谟的质问足够机敏,他自信由此“就会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学体系”。其实所谓“推翻 ”,乃是要转移道德基础,转移到情感主义基础上。在休谟看来,能够生发特定行为的动力 ,只是情感冲动而不是理性。情感与理性遵循不同的规范,相互没有作用。休谟视理性为冲 动的参谋,他甚至认为:“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 再不 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注: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53页。)理性向情感冲动提供事实判断以资参考,此外的事——价值选 择的事——就与理性无关了。休谟曾以一些极端的例子来凸显这一点:
人如果宁愿毁灭全世界而不肯伤害自己一个指头,那并不是违反理性。如果为了防止一个 印第安人或与我完全陌生的人的些小不快,我宁愿毁灭自己,那也不是违反理性。我如果选 择我所认为较小的福利而舍去较大的福利,并且对于前者比对于后者有一种更为热烈的爱好 ,那也同样不是违反理性。(注: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54页。)
休谟的见解中有两点是关键的:
第一,事实是中性的,与人——尤其是人的价值取向——无关。事实是惰性的、僵死的, 针对事实的理性和逻辑也是惰性的、僵死的。
第二,价值或“应该”只是一种逻辑上无法决断的、情感冲动的选择,其根据不在于事实 ,因为事实本身没有价值负荷。归根结底,价值主体只是一堆抽象的诸种情感意志的聚合体 。
这两点共有的症结是对历史过程中人的生成发展境遇之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忽视和背离。休 谟 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了不适当的抽象,一个方向是把“事实”从它与主体的关系中抽象出来 ,损失掉了事实与人的关联,随后他自然发现事实就是事实,不包含与人的价值有关的任何 成份 。结果当然无法重建事实与价值的逻辑关联,因为这种关联已经先行抽掉了。众所周知,演 绎推理的结论就其内容而言必定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内容贫乏的前提不可能推出内容丰富 的结 论。这就是休谟的逻辑噱头:先让事实变成“木乃伊”,然后就无论如何不能从中弄出活人 了。
另一个方向是把人从历史生活中抽象出来,人成为各种能力的机械组合,其中损失掉了各 种能力在现实生活上的有机关联。待到要重建诸能力的关联时,自然无法成功,这也是因为 关联已经先行抽掉了。这类损失是古典经验论所进行的抽象分析的代价。怀特海曾指出:“ 18和19世纪的认识论的弱点在于它自身纯粹以对感官知觉的狭隘表述为基础。……结果,就 把构成我们经验的所有真实的基本因素给排除掉了。”(注:引自陈奎德《怀特海哲学演化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页。
)休谟将“是”与“应该”做断裂 的理解,也是这种抽象分析的产物。
如果要克服这种断裂,首先就要找回一些意义重大但却先行被抽象掉的因素,填平断裂的 鸿沟。在这些工作之后,道德哲学也许会获得一个较为全面和坚实的基础。本文的主要工作 是努力填平鸿沟,而且偏重于对事实与人的非关联性的消解。
解析事实
“事实”多种多样,我们把精力集中于最坚硬的事实——科学事实。
“事实”当然与“对事实的判断或陈述”相区分。自然科学日益昌明以来,人们已惯于用 “事实”来鉴定“对事实的判断或陈述”,以核实真理。准确地说,鉴定就是诉诸事实观察 。要“科学地”认识事物,就要排除成见,进行观察性的实验或实验性的观察,从最客观的 事实出发,达到“科学的”认识。
但是,作为“事实”的“事实”是如何观察到的?是自然“呈现”的吗?是作为观察者的人 张开眼睛就看到的吗?
科学过程和科学史的研究都揭示出了否定的回答。“观察”不是本能的生理知觉行为,而 是基于社会教化的行为。
著名物理化学家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描绘了一个医学事实之呈现的例子:
想想一个医科学生在学习用X射线诊治肺病病人的情形。他在暗房中观察停放在病人胸前的 荧光屏上的阴影,听着射线分析师用技术语言对其助手作的关于这些阴影的有意义特征的 评论。起初,这位学生完全迷惑不解,因为他只能在那幅胸部X射线图上看到心脏和肋骨的 影子 以及肋骨间几个蜘蛛状斑点。专家们似乎是在凭空虚构了。他看不到他们所说的任何东西。 后来,随着他继续听课听了几个星期,细心观察了不同病例的新的图片,他开始有了点一知 半解。他开始忘记了那些肋骨,看到了肺。最后,如果他能用心坚持下去,一幅具有重要细 节的全景图就会呈现在他眼前:生理变化、病理变化、痂痕、慢性感染、急性症状等等。他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依然只看到了专家们所看到的一小部分,但现在这些图像对他肯 定有了意义,专家们对这些图像的大多数评论也肯定为他所理解了。他就要掌握他受过教育 的东西了;他取得了成功。就这样,这位学生在学会了肺部射线学语言的同时也学会了理解 肺部射线图。这两种知识只能同时产生。(注: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152页
著名物理学家迪昂(Pierre Duhem)描绘了另一种情境:
请走进这个实验室吧;接近这张堆满如此之多器械的桌子:电池组、用丝包裹的铜导钱、 充满水银的容器、线圈,带有镜子的小铁杆。观察者把带有用橡胶制作的棒的金属柄插入小 洞,铁杆摆动,并借助与它连在一起的镜子把一束光发送到赛璐珞标尺,观察者追踪光束在 它上面的运动。无疑地,在这里你有一个实验;借助这个光斑的振动,这位物理学家精细地 观察铁杆的摆动。现在问他,他正在干什么。他将回答“我正在研究带有这面镜子的铁杆的 振 动”吗?不,他将告诉你,他正在测量线圈的电阻。如果你感到惊讶并问他,这些话具有什 么意义,它们与他知觉的和你同时知觉的现象有什么关系,他将答复说,你的问题也许需要 十分冗长的说明,他将建议你修一门电的课程。(注:迪昂:《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
第一个例子中,“看”片子的人如果不是学医的学生,而是普通的外行人,甚至是一个刚 刚涉足文明世界的土著,那么他很可能连心脏和肋骨也得不到。第二个例子中,从表面上“ 看”,物理学家的举动与小孩子做游戏无甚差别,但他并不是做游戏,而是在测量电阻。那 些想得到同样物理“事实”的人则需要学习电学,接受教化。
在较为极端的情境中,维特根斯坦展示过“鸭—兔图”(注: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5页。),它既可以是鸭子的头,也可以 是兔子的头。当它被插在一本养鸭的科普书中时,无疑当即会被认作鸭子;而当它被插在一 本养兔的科普书中时,它也就会被一眼认出是只兔子。当这种刻意而为的“怪图”除去 一切参照情境包括观察者知觉经验的储备时,它是什么就变得不确定了,甚至它到底是一件 作品还是墨迹的偶然泼洒,或者是纸张本身的瑕疵,也无法辨识了。汉森(N.R.Hanson)提供 了更多类似的简明图画(注:汉森:《发现的模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8页。)。它们的启示是:如果没有适当语境,主体没有得到一定教化, 所谓“事实”是根本无法作为事实出现的。
上述“事实”也许在最严肃的意义上与重大科学真理没有直接关系,那么让我们来考虑一 些意义重大的“事实”及其观察。
近代科学史上,伽利略以实验精神和数学方法更新了自然知识,打破了亚里士多德体系和 托勒密体系的统治。从比萨斜塔上抛下轻重两个铁球的判决性实验一向归于伽利略。两个球 被“发现”是“同时”落地的,这个“事实”决定性地摧毁了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原理。这个 实验究竟有没有作过,是否确为伽利略所作,尚存争议,有些科学史学者甚至认为这不过是 伽利略的新科学确立后为方便教育而臆造的传奇。退一步说,即使“轻重两球同时落地”是 “事实”,它也不是“自然”事实。因为,所谓“同时性”,若非有适当的理论框架支持以 及由此产生的特定想象,天然的眼、耳和手要确定两个球同时落地几乎不可能。两球初始高 度的误差,抛掷是否严格同时,空气密度涨落的扰动,地面与两球初始位置连线的平行性, 以及地面自身的平整程度,等等,此类因素只有都考虑和控制之后,“同时落地”才可能是 出于自由落体本性的“事实”。但是,当时的实验水平远不能弄清这些因素,遑论控制。就 是在现代精密的实验条件下,这些因素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地控制。而且,即使这些条件都得 到了控制,也不构成“看”出“同时”落地的充分条件。在爱因斯坦之后,人们知道,“同 时性”是不可能观察到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
但是,按照伽利略的落体定律,这是一个完全普通的物理实验,其结论也肯定是两球同时 落地。而落体定律是一个经过创造性想象、有意或无意地——多半是有意地——忽略或强调 某些因素才得到的理论产物。因此,对“事实”的“发现”,并不是自然的,而是用心造成 的。
当然,对“事实”的“发现”,在常识的理解中,甚至在很多学者的理解中,却也还是“ 看到了”而已,并正因此被视为自然的(非人为的)、无意的(非主观的)、无辜的(事实自己 在说话),从而是人人都不能怀疑和违背的。科学真理就建基于其上。唯其如此,这样的真 理才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涉及伽利略的惯性定律时,丹皮尔(William Cec il Dampier)写道:“伽利略还发现:如果摩擦力小到可以忽略时,球滚下一个斜面之后, 可以滚上另一个斜面直到和出发点一样高的地方,而与斜面的倾斜度无关。如果第二斜面是 水平的,这个球以后将以恒速在这个平面上不断地向前跑去。”(注: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98页。)这仅仅是“发现”吗?忽 略充分小的摩擦力,这是主动的选择,而且摩擦力要小到什么程度才忽略,这又是重要的识 度问题。况且,就算存在无摩擦平面,球能不断向前滚动的前提是平面无限长,而平面无限 长的前提则是宇宙粒子数无限多,可是这一点既不是事实,也不是共识。考虑到这些因素, 我们必须承认,所谓“发现”,除非借助于特定类型的想象,否则就是不可能的。这种想象 ,在伽利略是“创造”,在学习“新科学”的人们就是“教育”。
其实,伽利略自己从不惮于让事实位于理论想象和创造之下,也不加隐讳。1610年前后, 他把望远镜指向天空,并发现了许多惊人的天文事实。其中之一就是对月亮的崭新观察。他 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惊喜若狂,无限感谢上帝,他喜欢和允许我发现这么多前所未知的伟 大奇迹。月球是一个类似地球的天体,这一点我以前就已深信不疑。”(注:A·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6页 。)
“我以前就已深信不疑”的构想,现在找到了有利的观测事实。
由此,就需要把“发现”考虑得复杂些才行。更有意味的是,伽利略通过望远镜看到月亮 也有和地球上一样的“山谷”,他认为这正好表明月亮和地球是同类。与此相映成趣但能更 鲜明地衬托出理论想象之塑造事实的,则是旧派天文学者。他们坚信月亮之类的天体是完美 球 体,始而拒绝用望远镜看天空,认为那只能带来魔术般的幻像(当时望远镜质量低劣,这样 认定并非蛮不讲理),继则给出符合旧说的特设性解释,认为月亮的“低洼”之处填满了透 明的晶体。(注:参见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页脚注。
)这样,月亮就还能保持为圆满无缺的天体。如此辩护在逻辑上并不导致矛 盾。反过来伽利略自己也并未真正遵从事实和理性。从一幅伽利略绘制的月面图(注:这幅月面图由法伊尔阿本德(Paul Feyerabend)重印在《反对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
992年版)一书中,并与一幅现代的月面图对照,见该书第112~113页之间的图版。
)来看, 那上面的确显示出有山和坑,可轮廓却是完美无“缺”的圆。这可能是一个无意的迁就数学 优美性的想象,但要害就在这里。他对此不作解释:月面上既然遍布山和坑,何以边缘还能 是可 见的“整”圆?这无论如何与实验精神和理性精神的严谨性相冲突。但丹皮尔却习惯性地渲 染着伽利略的实验精神:“哥白尼的天文学是根据数学简单性这一‘先验’原则建立起来的 ,伽利略却用望远镜去加以实际的检验。……靠了望远镜的帮助,伽利略用人人可以复按的 事实证明了天文学的新学说,而在那时以前天文学的学说是仅仅建立在先验的数学简单性 的根据上的。”(注: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95~196页。)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检验若要是“实际”的,那也必须是实际地运用 了 想象。要得到“人人可以复按的事实”,则必须人人都先接受伽利略创造性想象的教化。— —毫不奇怪,深深濡染于伽利略教化的现代人已经很难反思这一点了,“居芝兰之室,久而 不闻其香”。
科学诉诸事实以寻求真理,实质上首先需要对主体进行甚至深及基本知觉方式的改造。事 实当中必须已经含有人的选择和定向,事实才能作为事实出现。人的改造往往是获得事实和 真理的前提。质言之,事实是教化和选择的所得。马克思说得好:“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 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在这个意义上,感官所及的事实,以及由此所得的真理,就并 非与人的特定历史生活方式,与理论的创造、传播、选择无关,因而也就并非与人的价值追 求无关。“与人无干的事实”只是一个乌托邦。
重置客观性
然而,这样一来,真理的“客观性”岂不要丧失?
通常,客观性是对某种不依赖于人的感受和谈论却能够制约、评判感受和谈论的东西的诉 求,其中在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是对事实的诉求。事实,唯因其不受人的干扰,才有资格评判 由人的诸多因素运作而成的东西,例如标志知识的一系列判断。
这颇类似于法庭审判中的“回避制度”——只有与目前当事人及其事务没有亲属或利害关 系的人才能公正地判断原委曲直。区别在于后者尚未这样要求:既然要审理的是人事,就应 该由“非人”来操作。但是,哲学却作出这样的要求:既然在确定真理时必须处理和评判的 是人的认识,那么就必须诉诸某种“非人”的东西。这便是哲学上“客观事实”的含义。
即使如此,下述问题还是不能回避:存在谁都没有感受到也没有谈论到但却能够行使事实 职能的那种事实吗?迄今为止被称为事实的东西——虽然大部分在出现时都不再与其提及者 和提及方式相伴随——显然都有它们最初的提及者和提及方式。这也就是说,事实总是被某 (些)人以某种方式意识到了的事实。一般而言,某个事实肯定并没有被所有的人知道,某些 事实肯定只是有的人——可能是一小部分人——知道,但决没有那样一种事实:它是事实, 可任何人都不知道。
不过,这样的问题也经常困扰着思想:直角三角形的三边有精确稳定的关系,这当然是在 毕达哥拉斯之后才广为人知并深信不疑的。但似乎即使在毕达哥拉斯之前,这个关系也肯定 是客观事实。它似乎与历史上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特别提及此事没有关系。确实,在数学上 进行证明时,既不必用“毕达哥拉斯如何如何”的话语,也不必用“我此时作如此这般构想 ”的话语,可见,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内容作为事实,是不依赖于人之是否意识到它的。几乎 所有的数学定理都有这种与人无关的特征。
但这种理解是不透彻的。
人们往往忘记或忽略了一个教化的前提: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教会了人们想象抽象的三角 形。他们的三角形(以及其它几何图形)在经验世界根本不存在。经验世界中确实存在三角的 东西(一块楔形的草地)四边的东西(一个方形的井圈),但却没有一个是毕达哥拉斯意义上的 几何图形,也没有一个能够合乎几何定理所精确确定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承认,在 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创造性的抽象构想之前,不存在几何学意义上的“三角形”之类的东西 ,相应的特定关系也不存在。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贡献与其说是提供了较早的一批定理, 不如说是创造性地教会了人们进行一种前所未有的抽象想象的方式。常有人说古埃及、中国 的“数学”是希腊数学不精确的雏型,但也完全有理由说后者是前者的一种创造性的变态形 式。只有当我们忽略了改造过程中的“创造性”层面,我们才会以为,无论如何存在着与人 无关的、毕达哥拉斯定理所涉及的“事实”。
熟知常常延宕了真知。而哲学的使命之一就是找出那些被延宕的东西。
然而不可以走极端,夸大“事实”中人为创造因素,以至完全取消基于“事实”的真理的 “客观性”,陷入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那就又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真理仍然是客观的,只是它不再完全与人及其历史性的生存方式无关。相反,客观性离不 开人,它不是在人之外来衡量人的,而是人生存内部的一个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客观性并 不因为与人相关就失去了强制性。
一旦学习了毕达哥拉斯的体会方式,直角三角形三条边的关系就是客观真理。学习了伽利 略的观察方式,月球与地球一样高低不平就是客观真理。人可以——而且实际上也在不断地 ——更新这些方式,并从中求得自身发展,这也就是人的历史。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质疑, 但是人决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方式的情况下还能得到事实,更不用说真理。
不仅如此,与以往那种冷漠的客观性不同,重新定位的客观性,其强制性和非随意性竟达 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在特定历史性生存方式中人的现实生活,都与其中相匹配的客观真理水 乳交融。因为感知(识别与趋避)和想象(评价与预期)既是认知事务,也是生存事务。以至于 纯粹知识的改造和创新,也会激起物质利益的纷争乃至居间的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信仰、伦 理、道德的纷争。真理问题的现实性和敏感性也根源于此。
但在社会细致分工尤其是知识分子职业化的情况下,真理的现实性和敏感性往往很难辨识 ,但我们必须努力辨识。
数学和自然科学理论分歧背后的生活方式取向纷争最为隐晦,但决不是不存在。这里的价 值 取向纷争不能直接与个人生活利益和道德风格相等同,而是转变为类型的分歧。
爱因斯坦与玻尔(N.Bohr)的著名争论就表明了这一点。爱因斯坦认为不确定性不是“事实 ”,只是假象,因为“上帝不掷骰子”。他相信斯宾诺莎的上帝,即自然神论的上帝,那是 非人格化的和谐的保证。谁都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意味着某种道德,自然神论乃至无神论却也 决不是指向非道德,而只是指向另一种道德。其实,作为无神论典型的唯物论,首先激起的 反应就来自道德方面而不是学理方面。伊壁鸠鲁在历史上长期作为“缺德”的形象流传着。 至今在西方语言里,和唯物论相关的词语还有功利、贪婪、肉欲等贬义。那么居间的自然神 论也必然具有某种折衷的道德旨趣。莱辛(G.E.Lessing)临终时才敢对雅可比(F.H.Jacobi)
说他信仰斯宾诺莎的上帝。但这还是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抨击说信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根 本不信上帝,是无神论,“无神论者是危险的人、不道德的人,他既不能成为家庭中的一名 象样的父亲,也不能成为国家中的一名当之无愧的公民。”(注:参见A·古雷加《德国古典哲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7页。)
数学争论也难免与道德问题沆瀣一气。据说,毕达哥拉斯学派中发现并确证不可公度性的 人希帕萨斯被同仁们“公审”后投入了大海,因为他败坏了和谐完美的宇宙理想(这既是科 学理想也是生活理想)。(注:威廉·邓纳姆:《天才引导的历程——数学经典定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 年版,第10~12页。
)另外,当康托尔(G.Cantor)引入“实无穷”,得出集合论的怪 异结论时,克罗尼克(L.Kronecker)既在学理上攻击,也大举声讨康托尔的品格,指责他是 疯子、骗子、耍魔术的。因为在克罗尼克看来,自然数是唯一由上帝所赐的正当的数学对象 ,别的都属虚构,是不诚实的把戏。数学史家克莱因(M.Kline)写道:“涉及集合的许多问 题的争论,是无休止的,并且卷入了形而上学的甚至神学的辩论。”(注:M·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4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
)违背上帝意旨的举 动自然是不可饶恕的,结果在巨大压力下康托尔进了精神病院。因数学争执而精神失常,似 乎滑稽,但恰恰透露出知识事务所涵摄的价值旨趣。的确,康托尔的某些结论(例如部分等 于全体),动摇了向来天经地义的教条,它们既是理论通则,也是生活共识和规范。这个数 学惯例的颠覆者,同时就是生活惯例的颠覆者。康托尔集合论“象征着十九世纪有先见之明 的预言家们认为是从物理科学到民主政府的一切事物中,极其合理的原则的总崩溃”(注:E·T·贝尔:《数学精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43页。)。
至此,本文的思路是不断增加“事实”的价值负荷,不断填塞“是”与“应该”之间的鸿 沟,使那个著名的断裂变得越来越困难乃至不可能。而且,着眼点一直是具有最可靠“客观 事实”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注: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就有关问题的其它方面做了类似的消解工作,参阅《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6页。
)借此顺理成章地调整了真理的客观性,在不牺牲其强制性的 前提下,显示了其中人的因素。也只有这样的客观性,才真正对理论和生活有意义。道德真 理的客观性,一端与人的欲望相连,另一端与实在世界的事实相连。当事实——人性化的事 实——有力地参与到道德真理之中的时候,休谟的情感主义道德哲学也就消除了令人烦恼的 任意性和无根据性。存在与理想、是与应该、事实与价值都不再泾渭分明。当然,情感主义 可能也就不必再是道德哲学的一种了。
B·罗素抱怨过很多哲学家思想不真诚,其中就有休谟。确实,休谟并不讳言这一点:在哲 学上他是怀疑的,但在生活上,他是一位不错的英国绅士,并不为怀疑所困扰。他在理论上 所带来的一系列断裂,在“习惯”面前统统不算数了。为了生活而离弃理论,是休谟的策略 。本文的工作则是在不放弃理论的情况下,避免休谟的难题,保住生活的合理性。其关键之 处是不再像休谟那样抽象地设想“事实”,这不是靠离弃理论而是靠推进理论来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