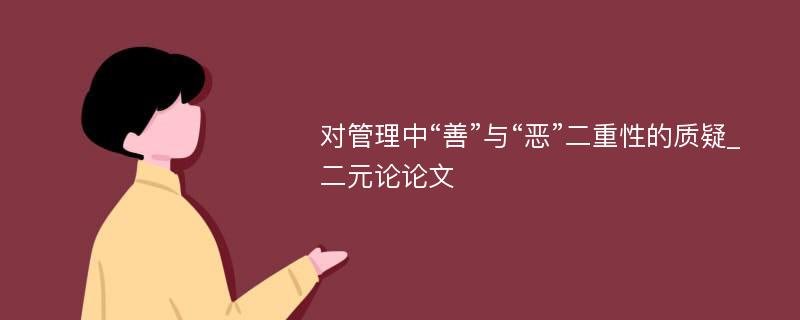
管理中的“善”“恶”二元论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性特质具有善恶两个方面的立论,对企业管理的影响最为突出。因为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处理人的问题,而困扰企业的人的问题之所以发生,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恶的人性特质。所以,为了减少人事问题的发生,作为管理人员必须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注意随时表彰发扬善的人性特质,提高全体员工的情操。发扬善的特质就是遏制恶的特质,恶的特质的遏制也就是善的特质的发扬,它们之间被认为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当然,这一观点把这种对人性特质的发扬与遏制作为一种教育过程是可取的。因为教育与纪律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而要求严格的纪律,必然会促使管理者过分的行使职权,这是导致各种人事问题的祸源之一。不仅如此,我们还期望在组织中通过对员工不断地教导来建立一种崭新的道德秩序,这种道德的理想状态实际上也是以善恶二元论为基础,只不过其中善的好的行为处于绝对优势,恶的坏的行为处于绝对的劣势。
上述有关人性特质的描述以及相应的管理措施似乎很完善,但我们又常常发现在管理实践中即使做得很好,有关的人事问题仍会层出不穷,甚至某些问题有恶化趋势,令管理人员感到极为困惑。当我们以现代企业的分工日趋复杂、员工价值观多元化、乃至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等诸多因素做出解释时,似乎是在做一种以一个令人费解的理论去解释一个令人费解的现实的把戏,理论家似乎可以安心,但实践者仍要硬着头皮面对实际问题。当然我不是说,这些因素对企业的人事问题没有影响,因为“事物都是相关或间接相关的”观点,对含糊的解释与不费力气的说法似乎最有帮助。到此为止,我们还是回过头去找一找原因,如同一道数学难题一样,当做了几十步,越做越乱、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回到第一步,或重新再做,或转变思路。
我们可以重新考察将人性特质的善恶问题以二元论的方式来概括,是否在出发点就存在问题?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在向我们表明,人性特质由两种相等而独立的力量所组成:一为善,一为恶。而人的头脑及这个由人组成的世界就是它们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它们永无止息地互相争斗,人类的发展史以及人们的经验似乎也为二元论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因此,有关人性特质的二元论似乎最符合人的思维习惯,也是最有力和明智的解释。
但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不难发现二元论有其明显的漏洞与逻辑错误。假定二元论是对的,那么恶势力必然是一种为了自身的原因而追求“恶”的存在。但在人们的实践中,并不存在“因为它是恶,所以追求恶”的经验。例如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坑蒙顾客,利用贿赂等手段获取权力,以残暴的手段攫取快乐与安全等等,这些恶的行为都是企图从中得到某种东西——金钱、权力、安全、快乐等。但金钱、权力、安全和快乐都是善的东西。恶的行为之所以产生乃是以错误的手段去谋求它们。当我们研究各种罪恶时,它们都是以错误或邪恶的方式去追求善的东西。所谓“金钱”是万恶之源,“权力”是万恶之源,不是在说,金钱和权力是“万恶”的核心或是首恶,而是在说,人们有可能利用各种恶的方式去追求它们。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只能因为善的目的而使用善的手段,或因为善的目的使用恶的手段,而不会因为恶的目的使用恶的手段。我之所以说在正常情况下,是为了排除不正常的变态。一个有着严重心理变态的人可能“为了杀人而杀人”,正如同老虎为了吃人而吃人一样。我们对老虎的态度是相信老虎吃人这一事实,但不会去指责老虎这样做不对;同样道理,对一个远离正常人性的人,我们除了认为他需要治病以外,还能指责他什么呢?当然,表达此观点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减轻我们对恶的憎恨。而是要表明,将人的特质区别为“善”和“恶”,“好”和“坏”的二元论是站不住脚的。它既有违于“人之初,性本善”这一儒家学说的真义,又是导致我们在管理实际中,在对待人的问题上,经常出现的各种藐视人性尊严的“万恶之源”。之所以说它是“万恶之源”,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以人性特质的二元论为管理的根据,我们会掉进两种错误或两种恶何者比较坏或何者比较好的陷阱,将错误成双的带进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中。它会使我们由对一种恶的憎恨,而逐渐对另一种恶产生好感,使整个管理工作误入歧途。例如,无视组织整体观念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一种恶,它败坏了组织的纪律性及健康的人际关系。但当我们以“善和恶的较量”的理念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据时,就可能采取诸如加强监督,令某些“集体观念强”的人拥有更多的权力,或者干脆实行一种不信任任何员工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殊不知又导致了管理上的集权主义。而且我们不能贸然地说,这种员工对管理与决策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参与权的体制缺乏群众的支持,因为有太多善良的群众憎恨先前那种不良的组织风气,对眼前的集权主义的恶视而不见,或以为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这个时候大谈什么“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能是对集权主义的一种恭维。再比如,企业内部各种形式的浪费和盗窃是一种恶,我们可能以摘去半数灯泡或普遍降低灯泡亮度来节约电力,以及惩罚那些没有随手关灯习惯的人;我们也可能为了公共洗手间的手纸时常被人偷走,而不再设置;为企业产品的丢失,安装监控器;等等。这些措施都可以堂而皇之的冠以“加强管理”的美称。然而,实际是为企业组织内部添加了更多的恶。显然,对一种恶的遏制并不一定就是对善的发扬,而可能是以一种恶取代了另一种恶。前一种恶并未消除,后一种恶却披上了善的外衣。后一种恶之所以可怕,不仅在于不易被人所察觉,更在于它的“理直气壮”,即“理直气壮”地行恶。
第二,二元论将善恶区分为两种相互独立的力量,与其说是让人们行善,不如说是让人们惧怕恶,或催迫人们行恶。因为一些人之所以以恶的手段追求善的目的,而不是以善的手段追求善的目的,必有其理由。这理由就是恶有其极为诱惑人的“方便”和“省力”之处。换句话说,在某些条件下,为达到同一目的,恶的手段比善的手段显得更有效率。它可以不费太多的力气得到财富(通过偷、接受贿赂、抢劫、欺骗等),也可以不费太多的努力得到权力(通过溜须拍马、贿赂、欺骗、伪装等)。当一个组织或一个社会为这种“恶的效率”提供了(往往无意识的)发展的空间,行善的效率就会远远地低于行恶的效率。或者说,恶的势力将会更加强大。很自然地,在人们的心态中形成一种由对恶势力的憎恨转变为一种惧怕,进而转变为对恶的服从与皈依。有很多的例证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常听到的“做好人吃亏”就是一个很好的概括。例如:在许多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坚持守法的人就过不了马路,只好加入“违章大军”;一个组织内如果单纯直率、不善于奉承的人不讨领导的喜欢,得不到晋升,必然溜须拍马成为一种组织风气;一个社会或一个企业如果经常亏待积极肯干贡献大的人,而偷懒耍滑的人可以和前一种人共吃“一个大锅里的饭”,那么这个社会或企业就是在生产“懒惰”。所谓“无产阶级思想松一松,资产阶级思想就攻一攻”,也是这种二元论的一种十分朴实的“创造性再版”。之所以具有其“创造性”,乃是因为此说法更强调了恶的力量的强大,人的特质更具有恶的本质。因为当你反过来说:“资产阶级思想松一松,无产阶级思想就攻一”,其结果,不仅可能会遭受围攻与讥笑,就连你自己也会认为是在违反常识。
第三,如果善恶二元论是对的,那么在对人的教导或教化的过程中,我们只能以人的行为和后果来判断他人。(且不说何为善,何为恶本身就难以定义,更难有一个公义的标准,它们也许只能为我们所感知,而不能为我们所认识。)也就是说,具有较多的好的行为人需要较少的教导,具有较多的坏的行为的人需要较多的教导。假定有两个人甲和乙,甲自幼就生长于一个极差的环境之中,在这里对他人的粗暴、残忍被认为是一种正确的事情,但通过甲自身的努力和选择,他目前可以初步抑制自身粗暴和残忍的习性,作出一点好的行为了;乙则出自一个极好的环境,他可以不通过自身的丝毫努力,甚至于有一些退步,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好的行为上远远地超过甲。甲显然无论在努力的付出上和所表现的勇气上都要比乙强得多。再假定一个人被置于一个很高的地位上,他的愤怒和愚昧可以使千万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另一个人是平民百姓,也有着同样的愤怒和愚昧,但其同样的表现只会招来周围人的嘲笑而已。在道德的天平上,第一个例子中两者差距极大,第二个例子中两者却是相等的。显然,以二元论为基础的教导或教化在道德上是无能为力的,只是徒然增加了更多的不公平而已。
把人的特质区分为善与恶,所谓好人就是其特质中的善多一些,恶人就是其特质中的恶多一些,善人之所以成为恶人,是由于其特质中的恶占了上风,恶人之所以成为善人,是因为其特质中的善占了上风,进而推广为善与恶两种势力的并存与永无休止的争斗,善之所以为善就是其喜欢包括仁爱在内的一切好事,恶之所以为恶就是其喜欢包括残暴在内的一切坏事,善的本性就是善,恶的本性就是恶,双方都坚持己见,都认为自己是对的。那么当我们提及这两种力量时,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好人越容易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或看到自己恶的一面;一个越变越坏的人就越看不到自己的恶。即一个好人知道自己不很好,而一个坏人则认为自己不很坏。好人知道善与恶,坏人则两者都不清楚,这的确是一种常识。人睡觉时不能了解睡眠,只有睡醒时才能了解睡眠,只有当人清醒的时候才能了解醉酒时的情形。
如果我们认为基督耶稣不是神,而只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那么就必须清楚他未曾给人任何新道德的标记。圣经的一个金科玉律是“你愿意人怎样待你,就得这样待人”,这实际是从根本上为人总括了什么是善的或好的一切行为。我记得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真正伟大的道德教师绝不制造一些新道德,只有冒充内行的门外汉或怪人才会这么做。人需要被提醒甚于需要被教导。道德教师的真正工作乃是不断地将我们引回或重温一些古旧与传统然而却被我们忽略的简单规则之中。正如同牵一匹赛马回到它不愿意跳过的栅栏之前,或者将一个小学生带回到他想逃避的功课之中。下棋也是如此,棋手在复盘或研究已下过的棋局时,才能了解怎样行棋更好一些,才能增长自己的棋技,而不是在下每一步棋之前,都需要别人告诉你应该怎样走,更不需要为了改变棋手拙劣的棋技,而去创造什么新的行棋规则。果真如此的话,且不说那些随意制造新规则的人可能就是一些“棋痞”,根本就没有什么“棋风”可言,观其制造新规则的后果也只能是造就一大批更差的棋手、更赖皮的棋手,永远不再会有优秀的棋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