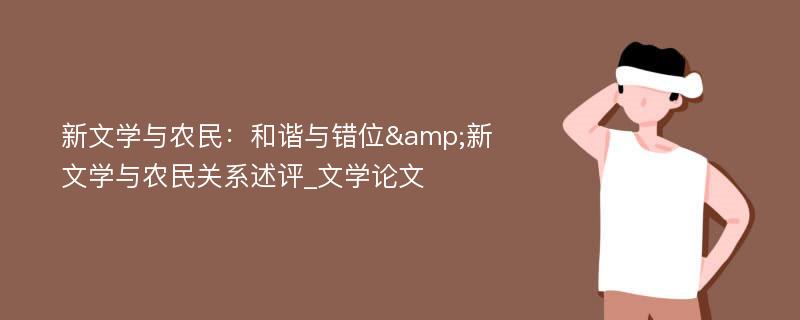
新文学与农民:和谐与错位——对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的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农民论文,和谐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即使是在已经初步进入到工业化阶段的二十一世纪初,它的大多数子民还依然是农民身份。在长期的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地位始终是最低的。虽然有所谓“士农工商”四民等级之说,但实际上,除了个别农民通过农民起义的极端方式获得过非常态的利益外,它基本上是以沉默和分散的姿态承受着社会最大的压力和最多的灾难。由于文字普及和社会等级制的限制,农民自身的文学始终以边缘和低层次的状态生存,在历史上,它只通过有限的几次“民歌采风”得以部分保留,除此之外,它几乎湮没在历史的流变之中,没有得到自足的呈现。
在封建等级制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传统主流文学对农民这一群体基本上是漠视的。正如五四文学先驱们所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学,“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①。它所承担的主要是为封建帝王做“家谱”和为封建文化“载道”的任务,最多还加上文人们的自我抒怀和相互唱和,农民阶层的生活和声音是很少被反映到其中的。显然,以“沉默的大多数”来形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学中的农民,无疑是合适的。
中国新文学诞生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大的改变。这首先是因为新文学面向大众的基本宗旨,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矢志于“平民文学”和“人的文学”,决心革除传统文学与社会大众相疏离的积弊,农民作为社会大众的主体成员,自然会与它相遇。正因为这样,新文学的第一个小说家鲁迅在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不久后,就将笔触伸进了农民生活这一领域,并以不懈的姿态将它作为自己始终的关注对象之一。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学发展,乡村和农民一直是其最重要的文学场景和文学形象,乡土题材成了新文学中最兴盛、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创作。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新文学精神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新文学的基本指导思想,给予了新文学作家与农民之间深在精神渊源充分展示的机会。由于中国社会的构成特点,新文学的作家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乡村,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也多在农村中度过,并普遍有血缘和亲情之根牵系在乡村之中,他们的精神文化也不可避免要受到农民文化的影响。在传统的封建文化背景下,这种情感和文化联系往往处在受压抑的位置,阶级间的巨大差异和“文以载道”的思想重负,使作家们不可能公开表示对农民的精神亲和,最多不过是抒发一些“悯农”的情怀而已。但新文学引进的“民主”、“平等”思想,以及所遵循的“人的文学”主张,却使作家们与农民的情感和文化联系有了充分呈现的可能。事实上,在新文学的大多数历史上,许多作家并不避讳自己与农民的情感和文化关系,如沈从文、师陀、贾平凹等作家更公开以“我是农民”的身份自居,也不乏赵树理、浩然等作家以“为农民写作”作为自己显在或隐在的精神指向。
当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无论是在物质还是在文化方面,农民还并没有取得与其他阶层真正的平等,还有不少的作家对自己的农民出身,甚至为自己创作的“农村题材”而感到精神的压力。即使是像沈从文、贾平凹等公开以自己农民身份为自傲的作家,内心深处其实也未尝没有更复杂的心态②,浩然等作家的姿态和创作实际之间更存在着政治主导的根本性精神反差③。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农民生活迅速进入新文学创作并很快成为主体内容的同时,作家于乡村的关怀,与乡村的文化联系,也必然会进入文学世界,并对他们的创作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使乡村题材创作成为新文学最主流创作的同时,乡村关注也成为萦绕许多作家整个创作生涯的基本精神。所以,尽管就主体精神而言,新文学是以西方现代文化为主导,其文学形式也主要以西方文学为榜样,但农民文化对新文学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复杂的,包括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审美上,农民文学的色彩和传统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在新文学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新文学与农民的密切关系还与二十世纪的社会环境有关。新文学发展的近一个世纪历史,正是中国革命的进行与成功之时,农民在这一革命中承担了主力的角色,尤其是在特殊的战争政治时代中,农民和乡村的意义被深刻地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经验相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它们代表的是本土生活,也被赋予了特别的精神内涵。此外,建国后乡村生活复杂而广泛的政治改革运动,也深刻地影响了新文学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尽管在特殊的政治时代下,这种关系可能是一柄双刃剑,它既促进了新文学对乡村的关注,却也伤害了新文学的自主性,并在深层次上伤害了新文学与农民的内在和谐。但从另一方面讲,在时过境迁之后,它又可能促进新文学对这一关系的深层反思,“文革”后新文学乡村题材创作取得了超越以往的更高成就,正可以看做是这一反思的直接结果。
二
新文学与农民关系和谐最直观的表现,自然是以乡村和农民为叙述对象的文学创作,也就是一般称为“乡土文学”的作品。但是,“乡土文学”概念与乡村和农民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错位,或者说,这一概念中的文化内涵盖过现实内涵,不仅是反映乡村和农民生活,更是反映乡土文化意识的。正因为这样,当叙写乡村的新文学发展到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其现实意味胜过了文化意味,也就不被人们当做“乡土文学”来看待,而普遍被称做“农村题材小说”。也有人因此而放弃了“乡土文学”的概念,转而以“乡村题材文学”来代替。混乱概念背后折射的是新文学与乡村和农民之间的疏离,也内在寓含着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我以为,要谈新文学与农民的关系,也许需要抛开“乡土文学”,改用“农民文学”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还没有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它确实是客观的存在,其基本内涵是:将农民作为文学的服务对象,或者自觉将文学创作作为农民的代言工具。在新文学历史上,“农民文学”经历了几起几落的复杂过程,更蕴涵着复杂的内在变迁:
一、起始阶段
“农民文学”的萌芽阶段是在三十年代初。在这之前,虽然有李大钊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写出《青年与农村》,提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愚黯,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黯;他们的生活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并号召青年们“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痛苦”④,有鲁迅在《故乡》等作品中书写了乡村和农民,但是,新文学最初并没有明确将农民作为自己的主要接受对象。换句话说,新文学作家们虽然也写农民,甚至将农民和乡村作为主要的书写对象,但是,在作家们的意识中,农民只能是启蒙对象,改造对象,同情对象,而不是服务对象,所以,他们提出的“平民文学”内涵很模糊,或者说基本上是将农民排除在外的。这一点正如四十年代有人的批评:“他们所谓‘平民’其实是意指着市民而不是工农大众,所谓平民文学,其实是市民文学,不是‘大众自己的文艺’。”⑤
最早表现出“农民文学”意识的作家是郁达夫,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创办《大众文艺》的刊物,明确表示“我们的新文艺……独于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感情,农民的苦楚,却不见有人出来描写过,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的新文艺的耻辱”⑥,并发表《论农民文学》等文章,在对文学现状的批评之余,表达了对“农民作家”的期待:“可是在现代的中国,从事于文学创作的人,还是以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人居多,真正从田里出来的农民诗人,或从铁工厂里出来的劳动诗人,还不见得有。”⑦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新文学作家开始将笔触深入到乡村世界,关注起农民的生活。这其中,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是最为突出的。从革命的功利角度出发,激进的左翼作家们特别希望能够更大范围地鼓动大众(大众中最主要的成员自然是农民)。这样,在强调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的同时,蒋光慈的《田野的风》、丁玲的《水》、华汉的《地泉》等作品将农民生活纳入视野,部分地描绘了乡村生活世界,再现了乡村灾难,传达了革命的宣传思想。而最有代表性的是真正来自于农民阶层的作家叶紫,他以自己的创作为鲁迅的话作了清晰的佐证:“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倘写下层人物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而且从来也很难言。”⑧ 叶紫的作品渗透了自己亲人的血泪和自己的艰辛,其情感也自然密切联系着底层的农民大众:“只有一类人为叶紫活着,他活着也就是为他们,那被压迫者,那哀哀无告的农夫,那苦苦在人间挣扎的工作者。”⑨ 他的作品中包含着较强的政治内涵,但在那一特殊时代下,这种政治内涵并不割裂于农民生活,相反,它正是时代农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就大部分的所谓“农民文学”理论和创作而言,实质上存在着巨大的自我矛盾。或者说,他们尽管在口头上高喊“农民”和“大众”,表示对包括鲁迅《阿Q正传》在内的“五四”文学精英姿态的否定和批判,但实质上,他们自己也并没有脱离这种姿态。正如有学者对瞿秋白的分析:“在三十年代,瞿秋白很少使用‘民间文学’这个词,他总是讲‘平民文学’,意即‘市民文学’。因为在他看来,民间文学是散漫的社会成分——农民的创作,没有什么重要的价值……瞿秋白的无产阶级新型语言文学,几乎没有给‘农民文学’留下一席位置。他认为农民与无产阶级不同,农民的语言是原始、粗鲁的语言。”⑩ 瞿秋白的思想代表的是这时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显示出“农民文学”在这时期的表面化和简单化。
二、发展阶段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毛泽东于一九三九年所提出的“新鲜活泼的、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 就有了它极强的针对性,它不只是在题材上号召作家们写农民,更明确表示作家们的创作方向应该以“老百姓”的接受为目标。到一九四二年,毛泽东的延安《讲话》更进一步以“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强化和明确了这一思想,对之前的“农民文学”观念有了大幅度的理论提升。
正是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启发和指导,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呈现出了与五四新文学传统有很大不同的面貌和特点。赵树理的“问题小说”是其最突出的体现(12),这一方面缘于他大量而熟练地运用农民文学形式,更重要的是他积极关注农民的现实问题,将文学作为为农民代言的工具,从而使他的文学作品在精神和形式层面都体现了农民文化的特点。也正因此,他取得了独特的成就,获得了农民们的特别欢迎——在新文学历史上,这是其他作家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赵树理之外,许多其他的解放区作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对农民生活和农民文学形式的关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之间兴起的“新秧歌运动”是新文学对农民文艺形式的直接借用,“民歌叙事诗”和“新章回体小说”的流行,都直接受惠于作家们对农民歌谣和民间小说形式的学习,农民文学在新文学中得到了大范围的实践。
与此同时,在围统区,以晏阳初在定县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为代表,“农民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推进。晏阳初将艺术教育分为平民文学、艺术教育和农村戏剧三大部分,一方面对民歌、鼓词等进行采集整理,并在平民读物中将民间文艺、通俗旧文艺和新文学作品穿插起来编辑。另外,他们还办有当时全国唯一一张面向农民的报纸《农民报》,刊登农民稿件,传达农民声音。这其中,农民戏剧创作的影响最大,著名戏剧家熊佛西在定县近两年的时间里,立足于“农民需要”和“农民能接受”的两个理念,创作了《过渡》、《锄头健儿》等多个剧本,在农民中取得很好的演出效果(13)。但相比之下,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国统区“农民戏剧”所取得的成绩有限。
建国后,“农民文学”有所发展,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异。从发展角度说,延安文学的思想在建国前基本上只是地方性的思想,还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实施,“十七年”文学中,“农民文学”的思想才大规模地成为作家们的追求目标。早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所作的主要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明确把《讲话》作为指针,把“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作为最基本的审美要求提出来,要求作家“与群众打成一片”,是解放区文学思想明确的延伸。五十年代初出台了一系列的文学政策,对农民的审美习惯表示重视,对文学也提出了向农民大众倾斜的要求。其中既有出版政策的倾斜,还包括对农民作家的大力扶植。在这种情况下,该类文学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而且,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探索,“十七年”的“农民文学”在艺术上比解放区时期更为成熟,包括语言、形式,都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从变异的角度讲,是这一时期不再像四十年代一样,农民不再占据革命的中心,城市建设取代了之前的农民中心地位,有关政策和思想文化与农民之间的不和谐开始有较明确的体现。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农民文学”最突出的代表赵树理在五十年代多次受到批评,影响力也显著下降。至于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人民公社制度、大跃进运动、三年灾害等,对农民的人身自由和生活质量、生存空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当时的许多作家在政治要求和压力下却不得不违背生活真实去书写各种“乡村奇迹”,则更可以证明政治与农民利益的割裂。于是,作家们在政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中就不可能像四十年代那样和谐和平衡,而是比较明显地偏向于政治,甚至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农民的利益和立场。很多“农民文学”外衣虽然还存在,但真正的实质已经是对农民的剥夺和瞒骗,对农民利益构成了很大损害。
三、自觉阶段
“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化的整体方向是向“五四”现代文化的回归,“农民文学”失去了在文化上的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政治束缚的相对减轻,思想文化较广泛的解放,使部分作家能够超出主流思想文化的范围,表现出自己有个性的思想。所以,尽管这时期的文学主流是启蒙文学,但是,也有作家继承了以往“农民文学”的创作传统,甚至有明显的创新和突破趋向。当然,这一创作的发展过程是缓慢而艰难的。比如,“文革”结束初,高晓声以他多年的农民经验和对农民的朴素感情,表达了农民的部分心声,但是,他很快回到了“五四”启蒙文学的道路上,并因此而陷入创作上的巨大困境(14)。只是到了“寻根文学”的后期,一些作家对新文学传统的启蒙立场有了更深的体认:“我们再不应把‘国民性’、‘劣根性’或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描述当做立意、主旨或目的……”(15) 在这一思想前提下,“农民文学”才有了真正实质性的发展。莫言的《愤怒的蒜薹》、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等作品分别在现实和历史层面表现了农民的愿望和理想,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农民精神。
到了文化更为自由活泼的九十年代后,作家们的思想表达更为直接和大胆,“农民文学”的创作也更加自觉和深刻。莫言在文章中明确表示自己放弃“为农民写作”,转而走向“作为农民写作”(16),他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为农民代言的立场更为自觉,也更为坚定。同样,阎连科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创作:“精神上必须是和底层人、劳苦大众有血肉关系,和土地有天然的、血缘的联系……文学也许不应该成为劳苦人的心声或者传声筒,但应该唤起人们对劳苦人的爱。”(17)至于刘震云的“故乡系列”、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作品,都表达了比较明确的农民文化历史观念。如果说《白鹿原》所表达的还是儒家文化姿态和乡野文化姿态相结合的立场的话,那么,“故乡系列”所表达的就是彻底和完全的农民文化立场,代表的是农民对历史的看法,传达的是农民审视历史的方式。
除此之外,贾平凹、张炜也在文化上代表着农民的立场,或者说,他们在农民文化面临现代化的社会转形的冲击和覆灭之际,表达了农民文化的绝望却是明确的否定之声。他们所表达的对农业文明生活方式的怀念与肯定,通过对现代文明的恐惧和批判,以回归和向后走的文化姿态,传达出了农业文明在消亡前的最后声音。
“农民文学”在新文学历史的几度起落,历程复杂而坎坷,概括而论,大体走的是马鞍型的道路。三十年代之前,新文学与农民基本上处于疏离状态,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则是新文学与农民的“蜜月”期,相互之间存在着借重的关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系,八十年代后,两者的关系从整体上变得有所疏远,但内在中又存在着深入的自觉和深化,尤其是随着九十年代后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生大的改变,两者的关系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总的来说是始终有许多问题在跟随,又面临许多新的变局。
三
“农民文学”代表了新文学与农民的亲近和一致趋向,但是,新文学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远不是平静和单一,而是复杂充满张力的。这种复杂关系构成了新文学深层的文化和精神语境,也导致了在新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中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它们包含着内在的错位,制约着新文学与农民之间的深层发展。
一、现代与传统的错位
农民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而中国农民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是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过渡阶段,因此,在一般观念中,农民文化往往被当做与农业文明相一体的传统来理解,也就面临着被选择现代化方向的中国新文化和作家们所抛弃的命运。正是立足于这样的思想前提,中国新文学的主流是以批判和启蒙的姿态来书写乡村和乡村文化的。与这种批判姿态相对立的另一方面,那些选择与现代化方向相背离,对现实发展持批判态度的作家来说,农民文化也成为了他们的“最后的堡垒”。比如三十年代的沈从文,就始终以文化上的“农民”自居,以对自己农民文化姿态的张扬抗击现实生活中的都市文明。他的这一传统在九十年代后的贾平凹、张炜等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挥,在这些创作中,乡村和农民文化承担的正是传统卫护的角色。
这当中其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读。按照社会学家的说法,文化可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18),中国乡村文化应该是非常典型的小传统,它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有关系但也有大的差别。正如陈思和先生所分析的,农民文化属于“民间文化”(19),其内涵是复杂的,绝对不是简单的封建文化,也不能简单地作为传统文化来看待。在这个角度上来看,无论是新文化运动中对农民文化的批判者,还是对传统文化的卫护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误读和借用了农民文化,却混淆了农民文化的真实身份。
更值得关注的是,许多作家创作中对农民文化的批判态度其实包含着对农民及其文化的歧视和忽略,其背景则依然与传统文化有关。也就是说,许多作家的思想貌似现代,但在他们对农民文化的批判中间包含着更传统的文化因素——或者说是与传统文化某种程度的趋同。这中间实质上涉及到一个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差异问题。现代作家们基本上是接受主流(精英)传统影响成长的,他们所借重的西方文化本质上也是精英文化,它们在精神实质上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是相一致的,这样,作家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就有些错位。在对待主流传统时,他们的姿态是批判和否定的,但在内心却始终保持着对它的尊重,而对待民间小传统,他们虽然表面上支持和认可,但从内心来说是拒绝和排斥它的,他们对它表示同情,但缺乏必要的尊重。
这表现在作家们对待民间宗教的态度上。整个新文学历史上,作家们对主流宗教是始终保持着比较尊敬的态度的,他们也多次呼吁宗教宽容,甚至加入宗教文学的写作,但这仅限于主流宗教,对待民间宗教,他们普遍持排斥和否定的态度。然而,事实上,在主流宗教和民间宗教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它们的“信仰”核心都是一样的(20)。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作家个体思想上的缺陷,而是他们的文化教育使然。他们接受的是精英文化,生活与文化都与大众先天地隔膜,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文化姿态上的矛盾是必然的。
文学形式和文学接受也涉及到现代与传统的困境。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之前),他们能够接受的文学形式主要是民间文学形式,如民歌、章回体小说、评书等等,他们对新文学形式的接受也存在着很大的障碍。民间文学形式自然有其优点,但它又确实积淀了许多旧的程式,与传统文化、传统生产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适合现代文明的要求。这就使新文学面临着非常艰难的二难困境。若要农民接受,就需要对文学形式进行转换,借鉴落后的农民文学,但农民接受了,却又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自己的启蒙初衷。从三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当下,新文学的这一困境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也影响了新文学与农民之间形成真正和谐的关系。
二、现实与文化的错位
在新文学对农民和农民文化的表现中,存在着这么一种现象,即作家们往往将自己的文化立场混淆于农民的现实态度。其实,这中间存在着一定的错位,其核心依然是农民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农民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生存艰难,因此,它的文化比较功利,与现实生存有密切的关联。这与长期作为主流文化的传统文化不一样,相比之下,传统文化的文化色彩更纯粹,保守色彩更强。
从这个角度来看二十世纪的社会变革,应该说,大部分农民对中国农村的现实变革,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的现代化的变革,是持着欢迎态度的,因为它带来了可以看得见的物质上的巨大变化。对于农民来说,最首要的关注是生存,是物质的丰盈。至于改革对乡村文化的触动和改变,对于农民来说其实很难简单地说是优还是劣。但作家们普遍将关注点放在文化上,比他们对现实的关注要多得多,这显然缘于他们自己的觉悟而不是农民的现实状况。比如在三十年代,沈从文就表示过:“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性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现代’二字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21) 但这与其说是农民们的心声,不如说是作家们内心世界的折射。同样,九十年代贾平凹、张炜等作家的创作也存在着类似的文化错位。他们以农民文化卫护者的姿态自居,却并不一定能得到现实中农民的理解和拥护,农民和他们是相隔膜的。
再如九十年代以来的农民工文学,作家们的关注点都在农民出路、城乡冲突这方面。这确实是很现实的问题,但他们也许忽略了一个更本质的乡村观念问题。在作家们看来,农民们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往往是一种对更高文明的追求和向往,其隐含的前提是城市化应该是农村的出路。但其实,这里存在着比较大的思索空间,就是农村的发展方向是否一定要像美国一样,走都市化的道路?乡村世界自身能否自足地发展?像上世纪四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等人进行过“乡村建设运动”,像八十年代的苏南模式,他们设想的是另一种乡村改革和发展模式。他们的“乡村建设”、“离土不离乡”是否完全没有其可行性?农民是否一定要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生活才是现代化的标志?(22) 在这一前提上思考,也许我们许多作家在出发点上就存在着许多可商榷的地方。
当然,我这里不是要求作家们都去当社会学家,去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把脉,我们所提出的是,作为中国关注农民和农村的作家,立足于乡村和农民文化本身来看问题,是最重要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才能走出思想的困惑,突破现有创作的瓶颈。这是考察一个作家思想深度的重要方面,但就目前来看,中国乡土文学领域的作家似乎大都没有实现这一突破。
与之相关联的是在新文学研究中,一般只关注新文学对农民的书写和影响,谈现代文化对农民的启蒙,却很少人谈到农民及其文化对新文学的影响。比如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一般人都谈“启蒙与被启蒙的错位”,似乎是农民文化借助政治压制了知识分子文化,是低等文化侵凌了高等文化。事实其实更为复杂,从根本上说,应该是政治意识形态(它本质上也是一种知识分子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压制,农民文化和启蒙文化都是受压制者。而从文学角度,这时期农民文学对新文学的影响也不单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它包含着新文学自身的选择和要求,是新文学某种自觉的结果(像赵树理,很多人把他看做是政治作家,其实并不是这样。他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农民的。赵树理的出现是新文学的一个异数,也构成了对新文学某种尖锐的警醒)。在这个角度上说,不只是新文学在影响着农民,农民也在深层次上,多方面地影响着新文学,它们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具体说,这其中既有对作家深层精神世界的影响,也有对文学本身(如语言、如叙事方式等)的影响。这一错位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知识分子的传统启蒙立场,源于新文学对农民不变的俯视姿态。
三、政治与文学的错位
二十世纪是一个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时代,任何作家都不可能完全脱出政治的影响,走在所谓的“纯文学”道路上。
农民与新文学的关系也不可能摆脱政治的影响,相反,这一关系的各个时期,都被蒙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如三十年代作家的集体左转,中国农村社会的广泛破产,是“丰收成灾”成为时代乡土书写的重要原因;四十年代解放区作家的通俗化、生活化,也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与解放区的有关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作家对现实农村的书写,更与乡村社会的现实变革运动密切关联。
但是,新文学与农民的关系与政治影响并不呈现直接对应的密切关系,而是有一定的错位。最典型的是四十年代解放区至五十年代初,这是文学与农民关系最和谐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如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运动对农民的解放和乡村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不排除其中存在的多种问题),农民也真诚地欢迎和支持共产党。但这时期的新文学在对乡村的表现上却又存在着一定的错位。原因是这时期的政治运动虽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但在具体运作中却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如土改运动中的过激,如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的盲目和仓促等,都对乡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产生了一定的伤害,而当时的新文学,受政治形势的限制和作家思想的局限,在反映这些政治运动和乡村生活时,几乎无一例外只能以歌颂和肯定的方式来书写。它们强调了其中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却忽略乃至掩盖了其中的阴暗面。这使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文学评价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显然,如何理解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区分政治与文学的不同标准,是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基础。
文学和政治,应该遵循不同的价值标准,也就是说,政治上的正确绝对不能代替文学上的成就,反之亦然。因为一方面,政治环境也许是时代文学所不能抗拒的。以四五十年代农村题材文学而论,即使是作家书写了揭露现实阴暗面的作品,在现实情况下也根本不可能发表,也就是说不可能作为这一时代文学出现。另一方面,政治的复杂性也许不是简单地以文学评价可以解决的。比如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制度问题,很多文学批评的思想前提是一些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即这一制度违背了现实要求,导致了农民丧失勤奋品质,培养了懒惰风气,并进而导致了八十年代前农村社会的萧条。事实上,这一问题远非如此简单。集体制度对于农村社会的利弊得失,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新农村建设”中也存在着争议,更有许多学者和政策在重新肯定集体制时代的“合作医疗制度”、“农业集体建设”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农村也采用了集体制的方式。而当时农村经济凋敝的原因,也远非是因为农民自身,而与当时整个国家的政策有直接关系。这一点有充分的数据可以证明,“建国三十多年来,农民通过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三万六千亿元以上的原始积累,却没有分享到任何工业化带来的文明和进步。贫困、落后和愚昧状况依然如故”(23)。在当时,农民虽然在表面上受尊重,实际上却受到剥夺,处于二等公民的身份地位,受到社会的歧视和忽略。将乡村经济的凋敝完全算在人民公社制度上显然是片面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评价新文学的农村题材创作显然需要祛除过多的政治因素,要回到文学标准上来审视。在这里,我们既需要对这些作品在真实揭露的不完备方面的缺陷有所批评,又应该看到它们所拥有的细节真实性;同样,我们既应该批评它们在艺术上单一的现实主义方向发展,也应该看到它们在文学乡村生态建设方面,在语言的口语化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这时期的文学创作。
(国家社科项目“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的阶段成果)
注释: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
② 贺仲明:《论中国乡土小说的二重叙述困境》,《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
③ 浩然的创作很值得反思,他所宣称的创作姿态和作品实际之间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反差,这一反差甚至是作家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因为作家的主体精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了,也许他有对农民的深厚情感,并在主观上希望代表的是农民,但实际上他代表的主要是时代政治观念。政治已经成为他血脉中最深刻的部分,压制了农民文化在他精神中的生长。
④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⑤ 《新文艺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潘梓年同志的发言》,《新华日报》1940年7月4日。
⑥ 郁达夫:《农民文艺的提倡》,《郁达夫文集》(五),第28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⑦ 郁达夫:《〈鸭绿江上〉读后感》,《郁达夫文集》(五),第25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⑧ 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二心集》。
⑨ 李健吾:《叶紫的小说》,《咀华集·咀华二集》,第12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⑩ 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第292-293页,董晓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11)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12) 虽然赵树理的创作有其充分的自发性,但他的创作发展与时代政治给予的肯定和激励是有直接关联的。
(13) 见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第216-217、220-22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4) 贺仲明:《“农民文化小说”:乡村的自审与张望》,《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15) 李锐:《厚土自语》,《上海文学》1988年第10期。
(16) 莫言:《作为农民写作》,《文学报》2002年10月21日。
(17) 阎连科:《“不是巧克力,而是黄连”》,《南方周末》2006年3月23日。
(18) [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9)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修订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20) 周星:《“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开放时代》2006年第4期。
(21)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第10卷,第294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22) 见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读书》2005年第7期。
(23) 吴象语,转引自同春芬《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不平等待遇透析》,第5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