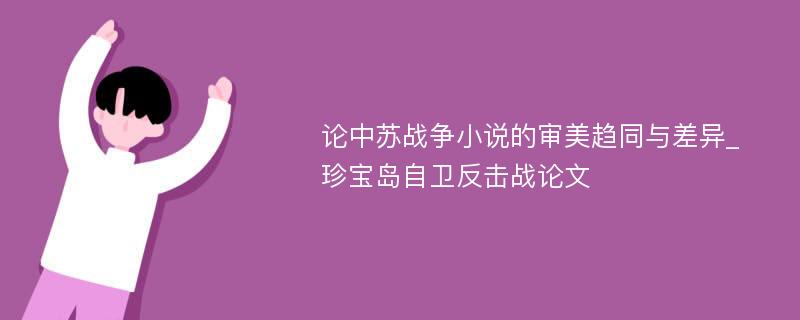
论中苏战争小说审美的趋同性和差异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性论文,中苏论文,战争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战争小说是20世纪中国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其发展过程,它既从传统创作方法中得到启迪,又直接从外国战争文学作品中吸取经验,特别是对俄苏战争小说的借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几乎每个时代都广泛地与俄苏文学发生着联系,如19世纪俄罗斯古典文学对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拉普”文艺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发展的影响;50年代“解冻文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等。俄苏文学从文学观念到作家具体创作都深入地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作家,同时也获得了中国读者的普遍推崇。本文以“战争”作为研究视角,意在客观论述中、苏战争小说在寓意构造、审美形态上的趋同性和差异性,探索中、苏战争小说鼎兴与沉落的动因。
1.中、苏战争小说都呈现出直抒胸怀的表层寓意构造:“政治——功利”的叙述模式
中、苏战争小说在战争爆发初期其题材选择上有着一致的趋同性,其主体特征表现为作者昂奋的创作激情与峻急的时代要求相结合,全民抗战的主流意识与战争文化心态、人的理想模式的紧密联系。中、苏作家都自觉地把战争事件本身的层次和逻辑确定为艺术世界展开的层次和逻辑,时代政治需求成为社会时尚和个体的生存价值,因此战时战争作品特别富有一种敏感的政治自觉,将“题材”与“革命”之间的关系直接对应,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他们表现的共同中心,战争残酷的气氛是他们共同的背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民族精神是他们共同的旋律,革命最终胜利是他们共同的乐观主题,时代的政治价值范畴是他们审美创作价值的旨归。战争既是历史主题有力度的实践形式,又是时代主题的集中凝聚。
战争爆发初期或随着战争深入时,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是比较接近“原汁原味”的战争小说,其战争观念也是原初意义上的观念,没有什么突破与超越。战争的观念是“为祖国而战”、“为民族而战”或“为正义而战”;“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战争的胜利与失败、民族的生存与灭亡要求作家们站在战争的第一线,为自己的祖国而呐喊。因此,战时的作品是一种“粗放型”似的风格。强调政治宣传与鼓动作用是战争初期文学创作的重要任务,是激烈的战争本身对作家提出的要求。这正如阿·托尔斯泰所说:“隆隆战火似乎本应该压倒诗人的声音,本该使文学受制于狭窄的战壕,显得仓促粗陋。但是战斗的人民在你死我活的浴血奋战中从自身找到愈益强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就愈益迫切地要求自己的文学发出铿铿巨响。苏联文学在战争文学中终于成为真正的人民艺术”〔1〕。在远东中国,作为时代主旋律的“抗日救亡”, 使中国现代文学在熊熊的战火中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换,从过去“五四”时的启蒙文学转向了“救亡”文学。民族救亡成为战争时期世界文学关注的重心,大批作家带着炽热欲燃的民族热情参加到反法西斯的革命洪流中去,大批中国作家奔赴抗日前线,在战争中牺牲的也有数十人之多;苏联对德战争是从1941年开始的,持续了4年——1418天, 到前线直接作战的或指挥战争的作家、诗人有一千多,牺牲的有四百多,那些在苏联内战时期就出名的作家如法捷耶夫、涅克拉索夫、富尔曼诺夫、肖洛霍夫、阿·托尔斯泰都奔赴前线进行战斗和体验生活。这一时期中苏战争文学都是在最激烈艰苦环境下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而诞生的。
虽然战争是人的战争,文学作品应该表现战争中的丰富性、复杂性,在审美意义上表现出战争与人的深刻的矛盾,才能把对战争的认识推进到深刻的层次上去。但是在战争年代,人们的文化语境却是由战时环境所决定的。战争时期,人们所面临的是怎样维持“生的状态”和“人的状态”。人与人处于相互对立之中,一部分人成了“攻克”、“占领”、“进军”、“征服”的对象,一个人的信念、信仰、理想、反思、感悟、追求、憧憬等精神内涵都面临着战争的考验。此时,整个社会的文化语境而同样要经历战争考验。战时战争小说在战时所寄托的理想并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冲动”,所有具有正义和良知的作家都要将自己的情感转向于对战争的关怀与思考,要表现民族在战争中顽强的生存意志、战斗意志,要表现为民族解放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在特殊的战争文化语境中,战争小说在现代文学的格局中也有着特殊的价值意义。
“一切能永存的艺术作品,是用时代的本质铸成的。艺术家不是一人独自进行创作,他在创作中反映他的同时代人的心情,整整一代人的痛苦、热爱和梦想”〔2〕。战争时代的战争作品, 正是与时代紧密相贴,才真实地反映了战争的本质、战争带来的残酷、毁灭、痛苦和战争中人们的理想、热爱与梦幻。战时的战争作品由于复杂艰苦的作战条件,虽然写得仓促粗率,但情感炽热,震憾人心。如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作品是对战争真实直接的描绘,揭示出抗战时代的本质与历史的真实,熔铸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作品其寓意主要通过民族战争中的生存意识、反抗意识、英雄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发展过程及这些意识相互交融产生的巨大民族抗战的凝聚力来体现的。
“生存意识”是战争初期众多作品表现的主题。战争使人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由悲伤转而愤怒,由愤怒转而为夺回失去的土地而战斗。
东北是最先沦陷的地区,人们对失去土地、家园的心情最为沉痛,因此大部分东北流亡作家首先表现了对失去的土地的眷恋之情。《八月的乡村》中,“义勇军”最大的目的就是把侵略者赶出东北,将被占领的土地还给人民。小说首先表现了人民为基本生存、为夺回失去的土地而斗争的强烈愿望。虽然当代小说也可用种种手法来表现人的生存困境、精神的痛苦与绝望,但是在日寇血洗东北大地的时候,人们确确实实是在为最简单的生存(活命)而呐喊战斗着。小说中9 个人的小小队伍,“有的从农民里来的,有的从军队里来的,更有的是别的‘柳子’上来的……”他们抗日有着不同的动机:或者是为了能够真正地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或者是为了过上太平日子,做个自由农民;更或者仅仅为了不花钱娶个老婆,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求生存,要求摆脱奴役,要求把日本强盗赶走。从队伍内的司令陈柱、队长铁鹰、朝鲜姑娘发娜、爱吸烟的小红脸,到中途参加队伍的李七嫂,一直到队伍外的老八,他们都强烈地希望早日消灭日本强盗。小说中“小红脸”人生最大的理想就是赶走了鬼子,能清静地在自己的田野里扶犁耕种,这是多么质朴而又原始的愿望啊!然而,这个愿望的实现又需要付出多大的艰苦努力。另一位东北作家端木蕻良《紫鹭湖的忧郁》则是“对土地爱情的自白”,是一首哀婉、沉郁的土地咏叹调。《大地的海》深沉而悲郁地揭示了农民和土地生死悠关的血肉联系,写出了土地的辽阔、荒凉和神奇,把土地当作生命的本源,描绘着它的性格,塑造着它的灵魂。王统照说:“作者以他特有的雄健而又冷艳之笔,给我们画出了伟大沉郁的原野和朴厚坚强的人民”〔3〕。 通过对在日寇铁蹄下东北乡土的抒怀,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生存意志和蕴藏于社会底层的生命潜力。
苏联战争小说与中国战争小说一样在主题意蕴方面都表现出共同的生存意识、抗战意识、英雄意识和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及其相联系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历史主义精神。
苏联战争小说表现了人民的顽强的生存意志。战争打破了和平宁静的美好生活,大片土地沦陷,无数家庭卷入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人们首先面临的是为生存而斗争。《一个人的遭遇》中索科洛夫的愿望也并不大,只要求能满足基本的生活条件,基本的生存愿望:“10年间我白天黑夜地干着活。我的收入很好,我的日子过得不比人家差。孩子们也叫人高兴:三个人的学习成绩都是‘优’,儿子阿纳托利对数学特别有才能,连中央的报纸都提到过他,……我为他骄傲,是的,真为他骄傲!10年中间,我稍积蓄了些钱,在战前盖了一座小房子,有两个房间,还有贮藏室和走廊。伊林娜又买了两只山羊。人生在世,还需要什么呢?孩子们吃的是牛奶糊,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有鞋穿,可以说心满意足了”。〔4 〕这样的基本生存愿望就像前面分析到的中国小说《八月的乡村》中“小红脸”只希望早点把鬼子赶走,然后能够安宁地在田野扶犁耕种。然而,战争爆发了,为了早日过上和平的生活,索科洛夫走上了战场。在卫国战争中,他失去了妻子儿女,自己也在战争中历经了难以想象的磨难。瓦西列夫斯卡亚的《虹》,展现了乌克兰人民在大片国土沦丧的空前艰难的条件下人民团结一致的抗争力量和爱国精神,反映了人民的抗战潜力是多么深厚与强大。小说写一个只有300 多农户的村庄,德寇们在这里残酷地践踏着这块土地,这里的人民。他们将怀有身孕的女游击队员奥莲娜剥光衣服押到冰天雪地的街上示众,而她不屈不挠的形象是整个村子、整个乌克兰的化身,“这不是奥莲娜,这是全村在裸着身子,被士兵的笑声追着,在雪地上走着。这不是奥莲娜,这是全村的脸跌倒在雪地上,被枪托打着,艰难地爬起来。这不是奥莲娜的腿上往冷冻的雪地上流着血,这是全村在德国人的铁拳下,在德国人的铁蹄下,在德国强盗的羁绊下流着血的”。这个村的妇女自由被剥夺,贞洁被凌辱,爱情被践踏,母爱被摧残,甚至儿童、幼婴也被杀戮,沉默的人民最终不能再沉默了,他们终于公开、大胆地抗争了起来。苏联很多战争小说揭示了蕴藏在人民内心深处的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体现了抗击法西斯的坚强意志,预示了战争的胜利必然是属于他们的。《不屈的人们》、《青年近卫军》、《人民是不朽的》、《祖国》、《军人不是天生的》、《日日夜夜》、《英雄之死》、《一寸土》等无数小说,都真实地展现了苏联人民的反抗精神。
战争时期,中、苏战争小说以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渗透在直接寓意层面,以革命功利主义作为最直接的目的,少有对战争本体的思考。然而,中、苏战争小说在文化意蕴又呈现出明显的差别。中国战争小说具有中国独特的色彩,即显示出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战争文学”的独特文化品格,作品中充溢着一种传统道德的表现力与震撼力。如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刘白羽《龙烟村纪事》、谷斯范《新水浒》、骆宾基《边陲线上》、萧红《生死场》、林风《一个农民出生的兵》、周而复《地道》、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这些作品以无比的向往和满腔的热情去展示农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他们高尚的品质和顽强的生命力,其政治价值大于审美价值。苏联战争小说在展示表层直接寓意的政治功利之际,同时对战争中道德与人性、胜利与失败、心理深度与现实矛盾作了不懈的探讨。
战争结束后,中国战争小说仍然遵循着解放区承传下来的内在的文化规律——表现工农兵的历史主动精神,“政治——战争”模式再次确定为新中国军事文学发展的、独尊的一元结构秩序。前十七年的中国战争小说更带有浓厚的政治热情、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当我们无数读者被《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的英雄主义热情所感动、所激励之时,苏联战争小说则走向了新的天地,“尉官小说”、“战壕真实派”小说、“前线一代”小说、“全景”式小说,战争文学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潮,新的审美视角和叙述方式也不断被接受。《暴风雨》、《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一寸土》、《营请火力支援》、《热的血》、《岸》、《战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牧童与牧女》……这些作品既有对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民族精神的赞颂,又有对战争残酷的真实描绘,对战争中人性的全面展示,甚至洋溢着浓郁的战地浪漫气息。
2.中、苏战争小说都呈现出复杂的思情趋势:“文化——哲学”的深层寓意构造模式
战时战争小说主要是强调表层的直接寓意,这是由战时艰难的创作环境所决定。在和平时代,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对战争进行深层的反思,对战争中人的精神行为、心理状态、道德观念及对战争本身进行全方位的思考。如苏联战争小说一直比较注重文化意义上的开掘,而中国则直到新时期以后战争小说才开始了对人性的全面探索和对战争本体的思考。文学与人性的关系历来是被文学家及批评家所十分关注的问题,长期以来就存在着“文学即人学”的美学命题。高尔基认为:“文学的目的,是帮助人了解自己本身,提高他的自信心,激发他们对真理的企求”〔5〕。贝科夫在谈到战争小说时进一步提出:“战争与道德, 战争与个人——这是二十世纪如何艺术地理解人的本质的基本问题”〔6〕; 艾特马托夫说:“任何东西都不能像战争那样最强烈地显现出作为人类的永恒的、始终存在着的美德和同情心”。〔7 〕战争和人道主义关系最为密切,因为战争最能体现人的思想和心灵,最能坦露和揭示人的本质。真、善、美是人道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战时战争文学中,一切有正义感和良心的作家都要为民族的生存而斗争,要以祖国民族利益为重,肩负起文学的神圣使命。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懑,对遭受灾难的人民的满腔同情,对沦陷故土的眷恋,对中国百姓长期压抑的灵魂与在民族苦难抗争中的觉醒。如东北流亡作家群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从广阔的时代、社会、人生背景中以悲凉苍劲的笔调展现了一幅幅壮阔激烈的抗日画面,以浓重的色彩描绘了东北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洋溢着对沦陷的东北旷野、河流、草原、大豆、高粱的乡恋之情,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抗日决心,是人道主义精神最美的体现。与东北作家群雄健悲壮、慷慨悲歌相对应的另一种创作特色的是绵密婉转、忧伤哀怜的叙事方式,展示乡土、民族和个人命运,从普通民众灵魂深处去发掘倔强、善良和正直的人生,如王西彦的《眷恋土地的人》描写了主人公对自己土地根深蒂固的眷恋,并认识到“总得把鬼子打退”才能安身立命,于是,他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战争。《村野恋人》、《微贱的人》则着意写出了乡村男女精神中人性的坚韧。
新时期以来,人道主义的描写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并对人道主义进行了多次探讨。人道主义在战争作品中的表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人道主义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思想体系,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政治因素,对人道主义本质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战争年代,人道主义并不等于不抵抗投降主义、或无原则的和平主义。如反法西斯文学中提倡的人道主义是带有正义性和阶级性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不同于传统的人道主义,也不同于今天所提倡的人类文化相融合的人道主义,它是把敌我分明的爱憎感情升华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英雄主义精神,成为人民为争取最后胜利而战的动力。新时期的战争作品更多是从人的“主体性”方面去思考人道主义,包括人的价值、战争的价值的思考。如《红高粱》虽是写抗日战斗生活,却展示了中国北方农民强悍的生命力和敢做敢为、富于冒险的个性品格,表现了一种令人敬畏的壮美人格和民主的抗争意志,超越了过去所表现的单一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新时期以来的战争小说如《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灵旗》、《黑太阳》、《长城万里图》、《新战争与和平》、《炮群》、《穿越死亡》、《末日之门》等作品都表现出一种深层的哲学意蕴和人类意识。
苏联战争小说对人性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从战时的《不屈的人们》、《虹》、《青年近卫军》到战后的《星》、《白桦》、《一个人的遭遇》、《生者与死者》、《岸》等作品都对战争中的人性、人道主义进行了探讨。在战争时期着重表现关于青春、友谊、爱情、母爱,关于善良的人民和普通的人的辛勤劳动等等的歌颂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的深邃的内容。50年代中期,以《一个人的遭遇》开始,战争小说加强了对个人命运的思索,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命运负责,同时也强调个人对社会、人类负责的主题。从艺术上论证了个人与土地、人民、祖国的血肉联系。这样的作品还有《生者与死者》、《一寸土》和《这样的战争》。六十年代战争小说还深入到人们精神世界的更高领域——人性、人格、人的本质问题去探讨。生与死、善与恶、爱与憎、恩与怨、同情与冷酷、关心与冷寞、诚实与狡诈、公证与不平、崇高与卑鄙……成为人物道德伦理探索的内容和评价人物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准绳,这样的作品有《母亲——土地》、《岸》、《选择》等。苏联战争小说对人性的探讨到了七十年代后,开始从全人类的角度,从更深的哲学角度去表现,并且大量借鉴了西方的战争小说的创作手法。
苏联战争作品对复杂人性的表现十分细腻,如《星》、《一个人的遭遇》、《静静的顿河》等无数作品充分展示了战争中人性的执着、扭曲或变异。《静静的顿河》中对主人公葛利高里这一复杂形象的塑造。作者集中描绘了葛利高里充沛的生命力,男性的力的美和哥萨克的野性美,具体深刻而富有民族特色的展现了葛利高里情爱的复杂性及生命历程和个性经历发展的复杂性。通过葛利高里人性的抒写,典型地反映了哥萨克群众在苏联大转变时的情绪和心理,也反映了该民族的普遍愿望。同时,不少作品讴歌了俄罗斯民族伟大的人性美,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俄罗斯的性格》等。《俄罗斯性格》中的儿子、母亲、女友等形象充分表现了人性的悲壮与美好,作者在小说中议论道:“是的,你们看看这几个人,他们所代表的就是俄罗斯的性格!一个人看样子似乎普普通通,平平凡凡,但是一旦严重的灾难临头,在他身上就会产生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伟大的力量就是人性的美。”
历史主义美学原则则是战争文学的时代要求。中、苏战争小说给历史以广阔的艺术再现,用现实去观照历史,用当代意识去审视战争,用战争的历史经验来反思现实生活。苏联的“战壕真实”与“全景小说”,以历史的真人、真事、真史为前提创造出富有时代特征的典型形象。《生者与死者》、《莫斯科41年》等作品,将历史与现实交融,让读者在文学的审美世界里,感受到现实与历史的关系。中国战争小说同样对中国战争历史作了全息性的审美观照,特别是当代战争作品中的“新历史主义”的创作手法得到了普遍关注。《皖南事变》、《碧血黄昏》、《长城万里图》、《新战争与和平》从更深层的角度展示了历史的复杂性、必然性、深邃性,表达了对人类本质的关怀。
3.中、苏战争小说在创作手法上都呈现出现实主义的直接描绘与对传统战争文学经验的吸收,但在审美构造方面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在创作手法上,中苏战争文学在战争初期多是现实主义的直接描绘,注重从各自国家的文学传统中吸收经验。苏联战争小说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时期就奠定了规模宏大的结构,经十月革命和内战,又产生了大批战争作品,如《苦难的历程》、《毁灭》、《铁流》、《静静的顿河》、《恰巴耶夫》、《暴风雨》,塑造了具有典型性格特征的军人形象恰巴耶夫、莱奋生、郭如鹤等。这些优秀的战争文学传统对反法西斯时期的苏联战争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结构上的恢弘复杂,革命史实与艺术结合,严峻真实的战争画面与细腻的心理分析,内容深邃,气势雄浑等。随着战争的深入,苏联战争小说形成了“全景”与“局部”两种模式,规范了战时和战后的战争作品基本框架。中国战争小说主要是借鉴古典小说传统的创作方法,注重故事情节的传奇性,少有心理分析,塑造具有伦理道德的英雄形象,结构上比较喜欢“章回”体的说书形式。如《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保卫延安》及解放后的《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
苏联战争小说在《一个人的遭遇》之前,多是传统的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从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到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都是在小说中探索英雄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中国战争小说在方法上同样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在解放区以塑造“新英雄形象”为主;在国统区的初期战争作品对现实有着强烈批判性。如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茅山下》,将抒情、叙事、批判相融合,文笔质朴遒劲,产生出一种震憾人心的力量,被郭沫若喻为抗战时的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姚雪垠、荒煤、罗烽、谷斯范、端木蕻良等直接写战争的作家或以战争作为文化背景的作家如茅盾、巴金、老舍等,都力图表现抗战热情和追求现实精神。在解放区,虽然主题是新鲜的,人物是新鲜的,战斗的场面是新鲜的,在文艺表现上也是一种新鲜而丰富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但是,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并且更加与中国传统与民间文化相联系。
中国战时作家也有不少直接从苏联战争文学作品中学习新的手法,如碧野对潘诺娃“美妙、纯洁和严肃、真实而诗意盎然”的学习,萧军对《铁流》中技巧的学习,刘白羽对西蒙诺夫的学习。碧野的作品《北方的原野》、《灯笼哨》、《风沙之恋》等,以一个漂泊者的广阔的时空视野和一种青年人的新鲜的热情,展示了别人难以企及的绚丽多姿的人与山川的画卷。他的作品与苏联卡扎凯维奇《星》、瓦西列夫斯卡亚的《虹》,阿斯塔维耶夫的《牧童与牧女》等抒情浓郁的浪漫主义战争小说十分相似,都充满了战争中雄奇浪漫的色彩。孙犁的作品可以说是达到了解放区短篇战争小说的高峰,他的语言清新、朴素,富有节奏感,特别擅长对战争环境中女性形象的描绘,那些妇女形象聪明、美丽、勇敢、机智,同时使人嗅到冀中平原纯厚的泥土气息。他的作品使我们想到瓦西里耶夫笔下的战争中的丽达、奥夏宁娜、丽扎·勃丽金娜等一群单纯、活泼、聪明、勇敢的女英雄形象;想起《青年近卫军》中的邬丽亚、柳芭。刘白羽的创作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饱满激情,文笔酣畅。他的作品《政治委员》、《火光在前》、《无敌三勇士》描绘了解放战争的风云,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图画。磅礴的气势,扑面而来的战争气氛,单纯明朗的人物,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成为其作品的基调。同时,他的作品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着战时浪漫主义的风格,意气风发,豪迈奔腾。他的作品给解放区军事题材的中长篇小说增添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这些特点与苏联著名战争作家西蒙诺夫展示英雄人物的风姿,弘扬他们无私无畏、所向披靡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作品非常相近。
因为苏联战争小说没完全按照政治模式去图解生活,而是在必须尊重生活的基础上而写,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至今读起来也并不感到陌生。因为战争生活本来就是如此,他们的小说只不过原原本本地把战争中所发生的一切真实地记下来了。苏联战争小说在描写战争场面的同时,特别强调战争环境、战争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增添了作品内容丰富的意蕴。相对来说,中国战争作品政治意识浓厚,而在表现人性方面比较薄弱,这和中国战时特殊复杂的环境的民众文化心理有关,如《八月的乡村》中知识分子萧明与朝鲜族姑娘恋爱却遭到了大家的嫉妒和不理解,被以“谈恋爱不利于革命”而强行拆散;铁鹰队长却对女人存在着蔑视,从来没爱过女人。《关连长》、《百合花》等作品虽然表现了些人性、人情的东西,后来却遭到了批判。直到新时期开始,中国战争小说在表现人性方面才真正得到了开拓并向更深层次发展。
战时中国战争小说虽然表现战斗场面,战斗事件,战斗中的战士及其关系,但多数作品是侧面的勾勒,如《一个连长的遭遇》、《刘粹刚之死》、《月黑夜》、《乌不浪的夜祭》、《戎马恋》等,而苏联战争小说规模宏伟、画面广阔,气势雄浑,具有史诗气魄。中国战争小说却缺少心理深度和细腻描写,多属“新英雄传奇”,将民族化、大众化与时代气息相结合,以农民的思维、语言、心理特征去表现战争生活。苏联战争小说如果是“橄榄”的话,那么中国战争小说的审美韵味则属“甘薯”。
4.中、苏战争小说审美差异的动因在于各自不同的战争文学传统和不同的战时文化背景
苏联在十月革命内战争时期就出现了一批杰作,如《苦难的历程》、《恰巴耶夫》、《暴风雨》、《毁灭》、《铁流》等,它们将革命史实与艺术虚构相结合,宏伟的革命斗争与民族风情相结合,现实描绘和浪漫主义激情相结合,以一系列严峻真实的战争画面与细致的心理分析,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性格特征的军人形象,这些优秀的文学传统为反法西斯战争小说的涌现奠定了基础。欧美战争小说有着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化传统,因此,海明威、雷马克、海勒等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用现代性的批判眼光去审视战争,写出了具有普遍意蕴的战争小说。中国在“五四”时期,虽然出现一些反映战争的作品,如《民国演义》、《战争三部曲》、《一个女兵的日记》、《一个兵丁》、《兵士的妻》等,但主题都是揭示战争带来的民生疾苦,士兵的不幸,否定军阀的混战,表现作家人道主义同情,是“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探索。二战爆发后,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都面临着抗击法西斯的艰巨任务,但中国形势更为错综复杂,分为国统区、解放区、敌占区、孤岛区等不同空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中国这样严峻的形势,因此,在艺术创作上文学与政治已成为自觉的“联姻”。战争小说没有本质的突破,主要表现对解放区的热烈颂歌与对国统区对现实的揭露批判,解放区文学规范一直影响当代中国战争小说的体构与审美模式。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大批著名的“非战”作家,却难以寻出几个可与俄苏相比且有自己独特创造个性的战争作家,也许姚雪垠、杜鹏程、刘白羽、魏巍就是相当出色的战争小说家了。而翻开苏联文学史,不少著名战争作家的名字占据着文学史的空间,出现这种差异,与我们作家缺少战争生活体验有关,正如老舍在评价自己失败之作《火葬》时说:“它的失败不在于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的很少。我的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荡来荡去,始终不能透入到水中去。”〔8 〕苏联在二战时一大批著名的老作家奔赴前线体验生活,而我国“五四”时期就成名天下的作家能奔赴前线的寥然无几,且在抗战中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作家是否应该奔赴前线”的论争。另外,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特征,主要体现在“言志”与“抒情”,注重道德的寓教功能,我们反映战争的文学仍然表现于士大夫的“志”与“情”中,少有对战争本身深层的哲学观照。在审美趋势上注重民间文化心理和文学传统,以《三国演义》、《水浒》、《三侠剑》、《七侠五义》作为塑造现代英雄的“蓝本”,“浪漫传奇”则必然成为现代战争小说的审美架构。
注释:
〔1〕A·托尔斯泰:《苏维埃文学二十五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346页。
〔2〕罗曼·罗兰:《母与子》,转引自《读书》1990年第4月号。
〔3〕王统照:《〈大地之海〉后记》,1937年《文学》月刊。
〔4〕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大系,苏联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
〔5〕《高尔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页。
〔6〕[苏联]《文学报》,1974年6月26日。
〔7〕转引自《当代文学中的伟大的卫国战争》,莫斯科1982 年版,第322页。
〔8〕老舍:《火葬·序》。
标签: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论文; 小说论文; 战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一个人的遭遇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静静的顿河论文; 青年近卫军论文; 生者与死者论文; 暴风雨论文; 铁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