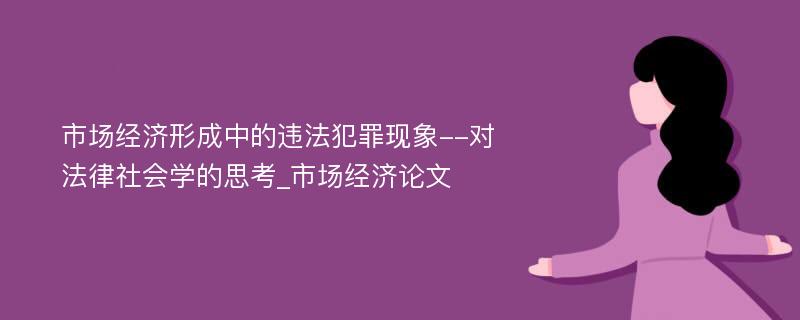
市场经济形成中的犯罪违法现象——法律社会学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市场经济论文,现象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治安和秩序近年来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之一。目前我国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不好是一个几乎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仅与经济联系的明显危害社会和公民的违法犯罪现象大量增加,①其它类刑的违法犯罪现象也明显增加。本文试图利用法律社会学的一些知识,结合历史的和外国的经验,特别是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社会变化探讨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有关违法犯罪的现象问题。首先,我想一般地探讨市场经济与违法犯罪现象的关系。其次,我将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一下为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经济体制转换时期违法犯罪会增加。据此,我就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预防违法犯罪的激增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Ⅰ
违法犯罪现象的增加在中国近年是一种共识。而在这同时,中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直到党的十四大才正式提出,市场经济的成分在过去的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中是不断增长着的。那么违法犯罪的增加与市场经济究竟有没有联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能限制违法犯罪的增加或根除?
从统计数据来看,自七九年以来,全国法院系统处理的犯罪案件逐年增加。考虑到立案标准的变化,社会中实际增加的违法犯罪现象将是统计数据本身未能反映的。不仅案件的量增加了,犯罪情节也有严重化倾向。近年全国各地严厉打击“车匪路霸”,而这种打击本身就反映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这类犯罪行为在早些年是未有所闻的。各种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都常有报导。收受贿赂或变相收受贿赂的犯罪、违法或不轨现象侵袭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呈上升趋势。尽管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对打击犯罪违法,改造罪犯作了大量组织领导和具体的工作,就社会整体来看,违法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犯罪违法、城市犯罪、流窜犯罪、团伙犯罪、目前仍然趋向增多。②
一方面是犯罪违法现象的增加,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并不是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发展中独特的现象。放眼世界,这种现象曾相当普遍地存在并仍存在于各国。犯罪和现代化问题是法律社会学、犯罪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尽管学者们对这两种现象的关系的性质未能或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这两者在许多社会中的共生关联却是无人否认的。例如,在西欧和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的犯罪违法现象大量增加,正是在与各类违法犯罪的较量中,产生现代的犯罪学各流派。③在当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犯罪率也随之激增。④正由于这种紧密的伴随着的关系,以至于西方一些学者激烈批评和反对社会的现代化特别是以西方经济模式为摹本的现代化的道路。⑤
也有经验表明并非所有的市场经济都总是伴随了⑥犯罪的激增。众所周知的日本和新加坡的现代化过程中尽管犯罪也有增加,却没有出现西方国家和当代第三世界的其他一些国家的犯罪激增。特例的存在显示了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有可能避免犯罪违法的激增。但特例本身就证明了市场经济发展与违法犯罪增加有一种普遍性的联系。
Ⅱ
于是,重要的问题在于了解在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中,究竟由于触动了那些社会因素从而可能导致犯罪违法的增加呢?⑦
大量的法律社会学研究表明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违法犯罪现象也会大量增加。社会的急剧变化改变了社会结构,使原有的社会中制约犯罪违法的机制打破了,当没有新的功能上可以替代的机制时,犯罪违法就会大量增加。同时,由于社会的变化也会带来冲突的社会规范,规范的冲突也会使人们无所适从或进而“无法无天”,从而促使人们冒险违法和犯罪。特别是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化的过程中,物质利益具有强大的诱惑力,传统的道德和习惯的力量都难以与之抗衡,为了经济利益而铤而走险的行为到处可以发现。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增加,也使道德规范多元化。人们的共同的道德意识和规范意识淡薄了。⑧
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少到目前的经验表明,总是伴随着城市化,人员的高度流动化。不仅大量农民暂时或永久性地进入城市,而且许多城市居民也处于前所未有的流动中。这种人员的高度的流动性和城市化使犯罪违法有了可乘之机。一般说来,处于陌生环境的个人对他人以及周围的环境都无法产生一种切身的责任感和道义感,这就使他或她更易于从事一些在家乡或熟悉的环境中所不为的行为。⑨这就是俗话中常说的“兔子不吃窝边草”的现象。而另一方面,高度的流动性也使这些违法犯罪有更多可能逃脱社会的制裁,包括舆论的制裁和正式的法律处罚,而这种逃脱反过来又可能刺激更多的和更严重的违法犯罪。⑩美国在十九世纪末,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犯罪违法和各种腐败现象就相当严重。当时社会处于一个从社区向社会(from communityto society)的转变时期,(11)城市化以及大量的移民涌入城市使违法犯罪现象激增。后来的美国犯罪学家称这种现象为社会的无组织化(或译为社会解体social disorganization),(12)或无序( anomie,也有译作失范)。(13)认为这种社会的无组织或无序引起了犯罪违法的增加。
我国目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处于这样一个社会变化时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的冲击下,无论社会结构、组织和个人的观念和心理都经历了并仍在经受着空前的变化。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加,全国流动人口激增。据有关资料,1982年全国的流动人口不过3000万人,1985年上升到4000万人,到1988年则猛增到7000万人。(14)1992年以后则有更大增加。流动人口中不仅是大量农村民工涌进在沿海的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地区,(15)而且包括其它形式的流动人口。这种流动性无疑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的,但不可否认高度的人员流动使违法犯罪有了更大更多的可能。(16)有研究表明在一些城市地区,流动人员、外地民工,以及当地人对外地民工的违法犯罪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7)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原来的社会的防止犯罪的一些无形的或有形的机制的消弱,从而为犯罪违法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例如,人员流动、劳务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造成单位作为社区的凝聚力的消弱。在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几乎完全与他或她的单位相联系,他或她的交往主要是同一单位的人。在工作单位为同事,在居住区是邻居的现象是极为普遍的。一个单位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一个社区,有所谓“单位(学校,工厂)办社会”之说;同一单位的人们相当于一个村子里的人们。(18)人们的关系相当密切(但不必然亲密)。张家长,李家短,大学都了如指掌。张三发现李四的孩子有不轨行为,就会出面干涉,或及时——有意或无意地——告知李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隐私很少,违法不轨是很难的,犯罪更难。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才有可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任何外人进来犯罪违法也很困难,因为任何陌生人出现都会引起人们的警惕。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单位,而且在街道居住区体现出来,只是比较弱一些而已。
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之相伴随的人员的流动,社会分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已经消弱了“单位”的这种以前未被意识和理解的作用。在城市中单位已不像先前那样具有作为组织和构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的作用了。单位的人员流动大了,频率高了,相互不知底细的情况也就增多了。人们会发现他或她所交往的人们越来越多地是暂时的、片刻的、纯事务性的;发现工作时交往的人不同于或不完全同于他生活居住区的人。由于工作忙、节奏加快,人们来往也减少,也许你根本不知道你的邻居是干什么的,家里有几口人,有什么爱好或习惯;甚至你也不想知道。人们在变得日益独立时也变得日益隔膜起来,在获得宁静时也获得了孤寂。塔楼里单门独户自成一统使人们怀念——尽管是浪漫化了的——四合院的嘈杂和亲密。同时,社会分工和服务的增加和便利也使许多“关系”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尽管目前在某些领域里关系对某些人变得更重要了)。人们不必为获得某种商品或服务而结识甚至巴结一个售货员或一个司机。人们有了,也有可能有更多的隐私。在这样的环境中,犯罪违法都可能增多,而同时逃避法律制裁也有了更大可能。
社会的巨大转变还总是带来一种无序和失范现象。在有些社会活动中,旧的社会规范在社会的变革中被打破了,而新的规范还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野性”的一面就会增加。比如说,当我们的社会转向市场经济,金钱和享受在人们心目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原有的各种限制对金钱的享受的规范在打破,而新的规范很难在人们心中形成并扎根,这就很容易出现不择手段的追求金钱和享受的违法犯罪行为。此外在新出现的一些社会活动中,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一种普遍的规范,人们一旦进入这样社会活动中,就往往依赖着他们各自的规则或直觉行事从而发生规则的冲突。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必然感觉到违法犯罪的剧烈,尽管事实上违法犯罪的行为也许增加得并不像感觉得那么大。例如,经济活动中的一些行为,例如吃回扣、拿佣金和某些投机行为,就其行为本身来说很难说就一定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但对习惯于计划经济下社会生活的人们来说,这些现象很容易被认为或感受为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
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给对违法犯罪者的教育改造带来问题。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与市场经济发展伴随的观念多元和人的个体化对教育改造违法犯罪者带来的困难。一般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与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和分化相联系的。(19)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变得更“宽容”了。由于职业、背景和利益的不尽相同,人们对问题的看法、行为方式也必然有不同。社会对行为的评价也会有不同。一些人认为是投机盈利的行为,另一些人可能认为是搞活经济,思想开放。一些人的洁身自好,会被另一些人认为是保守和无能。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多的可能是个体主义发展和集体主义消弱,从而导致他人的行为或观念——只要不直接涉及本人利益——而漠不关心;不强求一致,也不追求一致。
由于社会的“宽容”,许多违法犯罪都不再受到先前那样巨大统一的社会舆论的压力,有些甚至被认为是可以原谅的。我们社会对许多行为的评价不再向以前那样统一,反应也不再那么强烈和持久,甚至因为某些经济利益而作出权衡。(20)这种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改造有过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有好处——社会不再拒绝有过违法犯罪行为的人们重新进入社会;但缺乏一种强大的社会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舆论压力和坚决和持久的排斥,也会使一些人会因为所要支付的代价并不特别大而铤而走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道德观念的多元化,以及人际关系的疏远,社会对违法犯罪就没有以前的那种社会压力,违法犯罪的人更可能基于不同的价值观而认定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从而感受不到自己行为的代价,因此只要有机会,就更有可能再次违法犯罪。因此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如果没有其他社会机制的相应变化,就可能有更多的人会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经济体制的变革,刑满释放的人就业问题已经或即将成为一个问题。前面说到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评价的不一致,社会对有过违法犯罪行为的人的排斥力的减弱;但从一般来看,我们社会对这类人仍然是排斥和抵制的。因此即使社会“宽容”了他们昔日的行为,但相对说来社会对这些人比起对他人会苛更刻一些。他们的就业或再就业,即作为一个正常人重新进入社会,会遇到种种困难。在几乎所有社会里这都是一个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人的就业问题常常通过政府有关部门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加以解决的。在很多时候政府也有义务帮助他们就业和重新进入社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即使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在用人的权力上也不再完全听从甚至完全不听从政府主管部门的了。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由有关部门同用人单位协商解决。更多的时候只能由刑满释放的人自谋职业。由于过去的经历,他们与他人在就业问题上明显处于缺乏竞争力的地位。这种状况对他们重返社会,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是极为不利的。
Ⅲ
在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过程中,在寻求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从理论上讲,我们有可能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有效地预防犯罪违法,限制违法犯罪的发展,成功地改造有过违法犯罪行为的人。这一工作显然是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打击犯罪,制裁违法当然是不可缺少。社会的各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工作也是不可缺乏的。道德理想、科学文化、法制教育是重要的方面。这也是所谓的“综合治理”。这方面的文章已经是相当多,政府和社会都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我在此文就不再过多重复。在这一节我将侧重于简单探讨重建预防违法犯罪的社会机制的问题,这是以前的法律或法律社会学研究较少的。
从上一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之所以市场经济可能引起犯罪违法的增加在于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我们不希望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因为我们的目的在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当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后,与计划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社会组织是不可能恢复的。即使恢复了,也只是形式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功能和效力都将是有限的。举例说来,在人员高度流动的条件下,居民委员会就很难发挥其先前的功能。又比如,现在许多人认为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以此来预防犯罪,因为这曾是有效的方法。我并不否认这曾有效的,并仍将有一定效力。但在一个急剧变化发展的社会中,对大多数人来说,道德是非常无力的。不仅道德难以给具体的个人带来实际的具体的利益和确定感,(21)而且由于观念和价值的冲突,社会影响力的多元和冲突以及相形之下道德教育的无力,人们,即使青少年也难以形成强有力统一的道德观念。(22)还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城市,家庭的功能也相对萎缩,家庭不再是生产的基本单位,甚至也不是对后代教育的基本单位(学校的作用加大了,社会的影响,通过电视、电影和书籍,也加大了),这些因素以及社会的流动性都使家庭更加脆弱。不论我们的期望如何善良,破裂家庭的数量都是趋于增加。这些破裂的家庭都更有可能成为违法犯罪的温床。
因此要重建社会秩序,预防犯罪违法,我们并不排斥先前的有效的作法和经验,然而更关键的是要在社会中形成新的功能替代的机制。所谓功能替代,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与市场经济能相容的,同时能起到先前的社会机制的预防违法犯罪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具体说来,在我国目前,在放松和逐步取消人员流动限制的同时,应注意建立减少和缓解人员流动的社会机制和条件。其中首要的是应当注意加强各地的经济的相对平衡发展,从而使人员的流动得以缓解(不是不流动);因为目前来看,促使人员流动的主要是经济因素。因此,发展乡镇工业和农村经济,不仅是具有经济意义的战略,从社会学和犯罪学角度来看,是有效保证社会安定,稳定转变社会结构,预防违法犯罪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措施。现在许多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工作者以及国家各级政府都在探讨各种离土不离乡,发展乡镇工业,特别是内地经济,(23)这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战略意义,从法律社会学上看,对预防违法犯罪也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在城市地区,应注意建立新型的比较稳定的居住生活社区,特别是普通百姓的居住区的建设。由于市场经济对专业化和社会高度分工的要求,单位办社会的现象将日益减少,因此如何建立一种比较亲密的社区关系,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这种关系,不仅是有效预防违法犯罪和青少年犯罪所必须思考的,而且对改善现代都市社会人们的生活质量都有重要意义。另外,在城市地区还有必要加强对流动人员的管理。
从司法机构来看,我国必须加强公安警察的建设。在西方国家治安警察的出现就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出现相联系的。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警察的数量增加,素质提高。据1990年的一个报导,我国目前的警察和人口的比例只有万分之七,而在美国,该比例是万分之五十,在前苏联,该比例是万分之四十,在香港,该比例则高达万分之六十七。(24)即使考虑到城市化程度,我国的警察的数量也是太少——因为我国仅城市人口的总量已远远超过美国的全国人口,而警察总数量才相当于美国的2/3。没有一个相当数量、一定质量和装备精良的治安警察队伍,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治安打击和预防犯罪违法是难以完成的。
要注意保持一定高度的社会道德和舆论的压力,而这只是保持社会相对稳定和渐进发展的后果。如前面所分析的,这种社会的压力是迫使人们不敢违法犯罪和有效改造犯罪和违法者的重要条件之一。当前,我个人认为尤其要注意对犯了罪或有违法行为的“能人”“名人”的处理,不仅在法律上绝对不应从轻,舆论上也不能宽容。(25)这不仅涉及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更重要的是最有效地防止他们对社会道德观念的肆意破坏以及所造成的影响。这也并非是对他们格外苛刻,而是一种竞争机制和淘汰的表现——既然你选择了“出人头地”,影响广泛,社会就要求你格外严格,有得必有失。那种超法律的保护“能人”,舆论上的保护“能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一方面反映了先前的计划经济的影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变相的等级特权观念,而这些恰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逐步改革的。同样,“能人”是在竞争中才能出来的,而不是在特殊保护和超越法律中造就的。
也许最重要的要渐进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变革。渐进并不必然等于缓慢,而是指要注意保护社会中已形成的某些秩序。由于社会生活是极为复杂的,有许多因素是我们不了解的,看不见却影响着社会的运转,由于我们长期生活在其中,我们很有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或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因素的重要。因此,我们无论从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无法依据我们现有的理性或知识对社会的运作有完全的彻底的了解,也无法据此对未来进行理性的设计和按排。一旦社会的急剧变化破坏了这种环境,破坏了诸多因素的协调,我们的理性设计和按排就可能变得无效。因此必须让社会在相对的稳定状态中逐步发展,让原有的社会机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蜕变(不含贬意)、转化和发展。许多国家的历史发展经验表明,急剧的激烈的社会变革,即使在非常细致的理性的计划和善良的意愿指导下,也总是陷入一种社会混乱,需要较长时间来重建社会的秩序,因为计划不可能设计一切。全社会的理性,良好的道德风气,安定的社会秩序都只有在社会相对稳定中才能得以形成和发展。而渐进的变革不仅不必然是不彻底的变革,相反渐进的变革有时会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使原有的、需要变革甚至革除的机制也会蜕变出新的功能,适应新的社会条件的需要。(26)
以上的看法,并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全部措施,有些可能与某些发展建立市场经济的直接措施有冲突。但由于市场经济决不仅仅是经济活动,而是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市场经济就必须同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相协调才有可能实现。(27)一味强调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服从暂时的市场经济利益,(28)不但会使人们“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而且市场经济也无法真正扎根和健康顺利发展。
注释:
*本文的研究写作得到国家教委回国留学人员研究基金的资助,在此致谢。
①在此我特别强调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是为了同某些并不一定危害社会和公民或至少是有争议的违法犯罪区分开来。这后一类违法犯罪可能是由于法律的禁止而造成的,而在法律,特别是社会变革时期法律,有时所禁止的普遍的行为(非特定行为)并不一定,至少在新的形势和社会环境中不一定具有社会危害性,罪与不道德或社会公认的危害性并不等同。
②据最近的报导,我国的青少年犯罪具有低龄化,女性犯罪率上升,流窜犯增多等特点。青少年犯罪比率比五、六十年代增加了十倍,比八十年代增长了1.26倍。见《加强道德建设预防青少年犯罪》,《光明日报》,1993年7月7日,1版;又见《市场经济并不导致犯罪行为必然发生》,《中华第三产业报》,1993年7月15日,第2版。
③如德克海姆于1897年提出社会的无序(Anomie)来解释犯罪和其他违法现象,见,Suicide,1951年英文版);美国的社会学家罗斯(E.A.Ross)于1896年提出社会控制的概念,见,E.A.Ross,“SocialContro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896年,卷1,第515-535页;而美国最早的一个犯罪学学派——芝加哥学派——形成于本世纪开端,并围绕着对芝加哥都市的犯罪研究;见H.Barlow,Introduction to Criminology,1990英文第5版,第46页。
④见M.Clinard和D.Abbot,Crim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1973年英文版,又见,W.Clifford,Development and Crime,1973年英文版。
⑤例如,S.Cohen,“Western Crime Control Models in the Thrid World:Benign or Malignant?”,Research in Law,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1982年:第4期,第85-119页;又见,M.Huggins,“Approaches to Crime and Societal Development,”Compartive Social Research1985年:第8期,第17-36页。
⑥伴随不必然意味着有因果关系。
⑦应当申明,这里的分析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析,基于的是法律社会学和犯罪学的理论,而理论总是灰色的,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因此这里的分析不必然等于现实,基于理论的解释和预测对我们有启发作用,中能有预测作用和能为对策提供根据,但我们对这种作用的信赖和依赖必须是有限的。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地域广阔以及与之相伴的各地的特殊性,以及时间上的变化,这里的理论上的分析决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甚至完全没有实在的有效性。这并不意味着本文作者将不成熟的、自己也缺乏自信的思考匆匆提出,而是试图指出社会现实与理论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差距,不存在一种普遍有效的理论。
⑧见德克海姆: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1984年英文版。
⑨参见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
⑩因此贝卡利亚认为严厉性并不是刑罚制止犯罪的最主要特点,他认为及时性(promptness)更重要。见,Becaria,On Crimes and Punishment,1963年英译本,第19章。
(11)E.A.Ross,Social Control,1901年英文版。
(12)如,R.E.Park,“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Disorganization,”Theories of Deviance,1985年英文版,47-50页;又见他的“社区组织和未成年人犯罪,”《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
(13)如,R.K.Merton,“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同上,第107-138页。
(14)转引自张庆五,“我国流动人口发展的历程与对对策,”《人口与经济》,1991年,第6期,第13页。
(15)据有关部门的调查和研究报告,城市流动人口的60%来自农村(引自,杨金星,“中国城乡人口交流与人口控制,”《人口研究》,1992年第5期,33页),有些城市(沈阳)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甚至高达90%(《沈阳市流动人口问题及管理对策研究》课题组,“沈阳市暂住人口状况分析,”《人口研究》,1992年第6期,24页)。又有报导,仅珠江三角洲就吸纳了3400万民工,北京吸纳了100多万(见游宏炳,“民工潮的呼唤”《了望周刊》,1993年2月22日,第8期,第3页)。
(16)见张庆五,同前,第18页;又见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1994年中译本。
(17)关于外来流动人员的违法犯罪,据报导。北京市繁华地区发生的各类案件中,70%是外地进京人口所为;天津市公安部门统计,流动人口的犯罪率是9.33%,而常住人口的犯罪率为0.36%;广州市1986年清查出来的卖淫妇女中,外来人口占90%以上(见何济川:《人口流动之忧》,《人口剪报》,1991年9月30日,第8页)。而在厦门1986-1989年间外来流窜犯罪率分别占刑事案件数的21%,28%,35%和42%(庄求辉等:《略论厦门市外来暂住人口的管理问题》,《人口研究》,1992年第5期,第44-45页)。关于对外地民工的犯罪作者未见统计资料研究,但这方面的个案报导常见,可参见《沈阳市流动人口问题及管理对策研究》课题组,同上,第26-27页;又见《天津洪江大都会强迫外来妹‘三倍’》,《东方时空——焦点时刻》,1994年7月3日中央电视台。必须指出,这些统计数据不能认为是十分可靠的,因为一般说来,这些“外来人”可能更容易引起法律上的注意和反应。此外,由于这些人之间缺乏其他有效的方式解决冲突,也更可能诉诸法律。因此在法律记录上,这些人的犯罪可能显得更多一些。但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流动人口犯罪率高也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18)西方的一些社会学学者称这种社会结构为“城市村落”(urbanvillege)。如M.K.Whyte和W.L.Parish,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1984年英文版。
(19)见德克海姆,同前。
(20)不久前就有报导,一位曾因腐化滥用权利而被判过徒刑的前某省省长被某大公司总经理。至于“犯过错误的和有错误的能人”在全国各地都不难发现。而全国各地都存在的“三陪”现象的出现,无疑反映了社会对这种现象的道德谴责力度不如先前,以至于有人以改善投资条件为名而为这种现象辩护。这些辩护人的理由实际上是承认这些现象是不好的,但主张为了所谓的经济利益而接受。
(21)可能有人会对此命题提出异议,认为义(道德)利是各自独立的。我接受这样一种关于道德的理论,即道德从根本上看其发生是与人的社会利益或长远利益相联系的。道德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无联系的实在性。道德的发生是与人类生活,生活状况相联系的。参见尼采:“A Nietzsche Reader”,1977年企鹅丛书,英文版,第71页。
(22)而且道德观念、法制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是很值得怀疑的。其实绝大多数违法犯罪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事先都有一定的道德或法律评价的。很少有人公开犯罪违法,而总是隐蔽自己或为自己辩解。国外有实证研究调查表明被监禁的刑事罪犯与社会上普通人对许多行为的道德和法律评价基本一致(其差别在统计学上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报告,因此难作出论断。但从理论上看,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顺便说一句,这就对目前一直进行的全国性普法教育的前提假设、合理性以及经济性提出了怀疑。这值得认真研究。立此存照。
(23)这方面的资料很多,见夏海勇:《现代人口转变的苏南模式及其运行机制》,《人口研究》,1992年第5期,第13-18页;吴立志;《江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回顾》,1992年第1期,第38-39页;王海忠:《改革中的农村社区发展与人口控制》,《人口研究》,1992年第4期,第34-39页;黄立佳:《关于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的几点思考》,《人口与经济》,1991年第2期,第18,第16页。
(24)见梅洁:《橄榄色的世界》,《人民文学》,1991年第5期,第21页。
(25)例如对顾城之死的评价,一些文人大谈其死之文化意义,惋惜其才华,而完全不加或很少加以道德谴责,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精英”)特权观念。
(26)例如在日本,儒家的家族观念和集体观念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使工人们在就业问题上基本上是“从一而终。”这种风气使日本社会的流动人口相对小,人们容易形成对周围的人们的责任感。虽然对这种“从一而终”的利弊有一些争议,但它对社会的稳定安定从而预防控制违法犯罪肯定是有正面作用的。新加坡有效地利用儒家学说来加强对违法犯罪的控制是另一个实例。当代西方社会中许多职业社团显然带有中世纪的基尔特色彩,这些社团,特别是律师和医生协会有相当严格明确细致和系统的并可实行制裁的职业道德规范,有效控制这些职业工作者的违法犯罪。
(27)参见苏力:《实于市场经济和法律文化的一点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28)例如,《三陪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