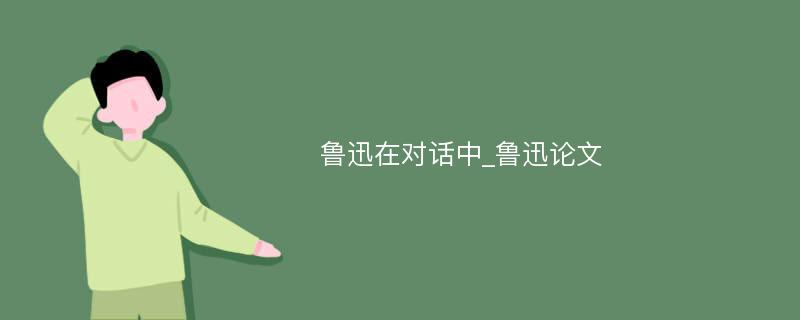
对话中的鲁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10-0128-06 鲁迅研究的困难之处是他与周围环境的复杂关系。在这种复杂性里,表现出其思维的非常规性。他的思想一直在不停息的行走之中,选择中的质疑与质疑中的选择,使他在判断问题时呈现出反日常逻辑的一面。但我们的研究,喜欢以本质主义的、静止方式瞭望其思想与作品。这和鲁迅文本产生了错位。将其固定在一个环节加以讨论,可能会遗漏些什么。 熟悉鲁迅文本的人会发现,他一生都是寂寞的。同代人和他能够交流者不多,他和许多人都产生过误会与冲突。这种冲突对他而言既有伤身之处,也有快意的地方。那快意的缘由是,他与对手的激战驱走了自己的寂寞,让对手置于尴尬之地。有三件事舒缓了他的寂寞,一是与左翼青年的接触,使他多了朗然的东西,鬼气飘散了大半。二是编刊、编书与杂文写作,由此感到生活的充实。据我的观察,在陌生的上海,他已经没有北京教育部时灵通的信息,除了读报,几乎失去职业对话的途径。他是害怕与世隔绝的人,杂文的渐多,乃对隔绝的抗拒,即通过媒体与世界对话。这些在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文章里都有折射。第三则是他找到了另一类对话,是属于内心的,即与陌生的思想者对话。这些对话不是与国人,也非与古人的互动,他的对象是域外的思想者。他通过阅读日文、德文,悄悄修改自己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窃来火种,煮自己的肉。① 鲁迅阅读的俄国作品多来自日译本,他与世界的互动,就在那些日文阅读与翻译实践之中。查鲁迅日记,可以发现他阅读的线索:每年都在购置日文著作,有的通过邮购,有的是从内山书店所得,还有的是朋友所寄。鲁迅搜购的日文著作不限于文学,还有诸多科学与社会学、哲学的著作。他通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了解了世界的形势,以及俄国的变化。所以,说起他的俄国观的时候,日本的因素是有复杂的中介作用的。 阅读他的藏书,其知识的部分来源得到了印证。鲁迅一些思想就是在阅读与翻译里相互碰撞产生的。比如一些概念的使用,一些意象的移植,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来的传统不无关系。而那些域外译本及翻译家的思路也影响了鲁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复杂的人文语境里,鲁迅思想以奇异的方式表露出来。 日译本里的俄国文学作品,对鲁迅来说是直接进入俄国世界的通道。他在文章里不止一次强调日译本对自己的帮助。而那些书籍的风格及译者的观点,也被鲁迅部分所接受。他的藏书数量虽然有限,可是利用率很高。部分喜爱的内容被其翻译成了中文,且在现代文坛有相当的影响。这在他的翻译生涯里有特别的意味,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斯拉夫文明的血色与禁欲里的悲楚的因素,在鲁迅眼里恰是中国文人笔下缺失的存在。他从日本人的译介里隐隐感到汉民族所没有的超验的存在,以及自我否定的因素。日本的作家夏目漱石、有岛武郎就借鉴了相关的因素。东洋小说的进化与作家摄取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营养颇有关系,此其一。作为思想者,鲁迅关于革命、大众化、人民性的思考,也多取自日本译本的概念。他了解俄国革命的进程,无法绕过日本人与德国人的已经过滤过的思维,或者说,他解释革命文化的时候,纯粹的斯拉夫的逻辑是被改造过的。那些概念在这些外来的非俄国的文字里,多少有些减损或增添。而这些不仅妨碍了他对俄国变化的理解,也给国内左翼文人间的对话,带来某些错位与差异。而他以愿望代替认识的偏执性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可是其思想的活跃性也随之产生。较之于那些在专业知识领域呆板地自说自话的文人,鲁迅的精神竟因此而得以生长,此其二。 中国的知识阶层,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学之后,多依傍在其思想里,而后去解释现象,并指点江山。鲁迅的藏书与译书却呈现了如下的态势,那就是通过阅读日文与德文,开始与俄罗斯文学精神与革命精神对话的工作。这些外来的存在在他那里不是一开始就作为凝固的元素静止在那里的。他是通过一点点质疑、自审、清理精神的杂物,并试图于异质的话语体系里,找到自我迈步的方式。 因为依靠的主要是日译本,他对俄国的阅读,就不可避免带有隔膜的地方。他竭力抵御这种隔膜。他发现旧俄的作品,是深入到日本作家的骨髓的。细看大正与昭和年间日本作家的文本,托尔斯泰的因素也渗透其间,许多经典都有了译本,而那译本催出了另类的文学。芥川龙之介吸收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的智慧,②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一度就有托尔斯泰的影子,他借助这个俄国人,找到了许多解释心灵问题的话题。③国木田独步在一篇随笔里,惊讶于屠格涅夫关于风景的描绘,④而永井荷风在厌恶美国社会的时候,就曾以法国与俄国的对比,看出创造性的可爱。⑤芥川龙之介在一篇文章里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了一段会心之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充满各种各样的讽刺画。而且这种讽刺画有一大半肯定使魔鬼也不能不为之发愁。”⑥那些俄国作品,不论是写实的还是浪漫的,都是东方文学稀少的存在。东洋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难说没有参照类似的文本。 拥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的俄国文学,在后来的发展过程里,没有停留在原色调上,新俄(苏联)的文学很快就出现了。这大概与政治的变化有关。新俄的文学问世后不久,日本译界就捕捉到了,鲁迅于此嗅出了新的存在的气息,那里散出的陌生而有趣的意象与思想,无论对日本还是中国,都有深的刺激。鲁迅购置如此多的新俄文学作品,他自己的解释不多,但这些是伴随着思想的转变的。他收集和阅读这些文字,有一种互动的冲动。在不同特色的作品里,吸收别样的营养,通过与陌生者的对话,在默默地解决自己灵魂的问题。 从现存的资料看,日本作家与学者,不同时期对俄国文学的介绍有不同的侧面。明治与大政时期是19世纪的作品集中译介的时期,而昭和之后,革命文学渐渐占了一定的份额。鲁迅对俄国认识的前后不同,其实乃知识结构的变化与现实变化所导致。来自日本知识界的态度也加大了这种变化。我们从鲁迅晚年所引用的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等概念上,都看出日本的影子。 鲁迅所藏日文著作,多是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所购。意味深长的是,在大量收集日译本的俄国文学的时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在许多文章里谈到对日本政府侵略的厌恶。而像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被害,也强化了鲁迅对日本权力阶层的反感。⑦在鲁迅看来,存在着两个日本:一个是法西斯的日本,一个是温和的大众的日本,后者与中国的大众一样,均为被压迫者。而那时候的一些知识人的专心译介俄国文艺,也有对日本文化不满的意味。所以,从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与理论著作中,可以看出其与日本知识人的互动。这一点,日本学者早有认识。吉田旷二在《上海时代的鲁迅:鲁迅的国际政治论——鲁迅的抗日外交观与苏维埃·俄国观》里,写到鲁迅在俄国、日本两国政治间的选择。⑧鲁迅对日本出版物中的非日本化的俄罗斯情节有所认同,晚年许多日本左派与他的交往,都有俄国的话题在。或者说,那些东洋人是欣赏俄国艺术与精神的。他对日本的亲俄派的好感,不言自明。在内心,他或许觉得,彼此都有相近的心。 在北京时期,鲁迅就介绍了片山孤村的理论文章,看得出其鲜明的批判意识。片山孤村批评了人们的思索的惰性,认为文学是国民精神的反映。他以德国文学为例,言及自然主义、表现主义,背后显然有文学进化论的痕迹。到了厨川白村那里,东洋人自觉的批判意识就出现了。鲁迅看到了他对日本的无情的剖析,那理论无疑来自西洋的现代理论。在《东西之自然诗观》里,就谈及东洋的厌生诗人与西洋罗曼主义的文人的差异,非东方主义的精神是浓烈的。⑨这种倾向于浪漫主义的诗学风格,在岛崎藤村的文章里亦有体现。他从卢梭的文章里就感受到自我意识的问题,“向着人的一生,起了革命”。⑩ 岛崎藤村的作品在中国有许多的回应,周作人就在文章里介绍过他。这个极为敏感而有个性特点的作家身上的浪漫的情调,给周氏兄弟很深的印象。许多年后,当梁实秋批评卢梭的时候,鲁迅出来为那位法国思想家辩护,也让人联想起岛崎藤村的精神。 在日本知识界,俄国的思想被广为传播,也有白桦派的作用。这个流派后来被周氏兄弟所注意,与其间的俄国味道也不无关系。有岛武郎、武者小路笃实等人的作品,都被鲁迅所收藏,有的被译介过来。鲁迅在这些日本人的气质里感受到了自我批评和自我凝视的力量。这些对于中国的文人而言,都自有新鲜之处。 精神的进化,离不开的主要是否定意识。有岛武郎在易卜生的作品里,就看到了人类的诸多难题,而解决这难题,就必须有高于易卜生的人出现。那其实就是由思考到行动的转变。而那转变,就必须由革命者来完成了。有岛武郎在《宣言一篇》里,强调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差别,并承认自己不属于那新生的阶级。可是那个阶级对未来的破坏,大概也是不能怀疑的吧。(11) 日本学者关于俄国作家的评述并非都被鲁迅所认同。他对俄国文学的一些判断,有的受到日本人的影响,有些则道路相迥。《壁下译丛》就有多篇涉及文学的进化的问题,特别谈及阶级性的问题。丸山升在《鲁迅和〈宣言一篇〉》里看到了日本激进作家与鲁迅的区别,也就是说,鲁迅在面对俄国文学时,其出发点与日本人存在很大的差异。丸山升发现,鲁迅对革命文学的理解是从日本的视角穿过之后的另类的存在,不仅和一些日本知识分子思想相反,而且在本质是相异的。(12) 许多日本人对俄国文学里表现出来的思想颇为感动。片上伸的许多文章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在《“否定”的文学》里,片上伸写道: 俄国是从最初以来,就有着当死的运命的;有着自行破坏的运命的。仗着自行破坏,自行处死,而这才至于自行苏生,自行建造的事,是俄国的运命。俄国的生活的全历程,是不得不以自己的破坏,自己的否定为出发点了的。到了能够否定自己之后,俄国才入于活出自己的路。(13) 在《北欧文学的原理》里,片上伸讨论过托尔斯泰、勃洛克的作品与思想,并从宗教的层面看到俄罗斯文明的逻辑过程。这篇被鲁迅译介过来的文章,不乏深切的学理。鲁迅在这里嗅出了日本学界钟情于俄国文学的根本的思想。最重要的就是发现俄国的革命精神走在欧洲的前面,似乎在挽救欧洲的堕落。俄国的文学充满了失败感,但那精神也引起了社会的行动。社会的改变,大概就是由此开始的。片上伸于是提出向俄国学习的话题,他说: 我们的学欧洲文学,学俄国文学,并非为了知道这些,增加些智识,必要的是来思索,看欧洲北方的人,例如伊孛生和托尔斯泰等,对于真理是怎样地着想,我们是应该怎样地进行。(14) 俄国文学的发达,说到底,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知识阶级的原因。俄国诗人爱罗先珂谈及这个话题。而日本的青野季吉还有过专门的论述。鲁迅在广东的时候,专门言及俄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在他看来,真的知识阶级是超利害的,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无不如此。这个思想的形成,与日本学者的提示也有关系。他从大量的日译本里,看到了这个问题。青野季吉批判过日本文坛的十大缺陷,那也是对照俄国与欧美文学现状的一种感叹。鲁迅在看过了那文章后,应该是心有戚戚焉。他后来批评中国文坛的浅薄,也就运用了类似的思路。 俄国文学作品对鲁迅而言,范本的价值是无疑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参照。对照它们而发现自己的所缺。欧美的经验毕竟与我们的历史相隔,倒是俄国,似乎更与我们相关。因此可以说鲁迅对俄国问题的敏感,是饥渴于精神粮食的民族的一种选择。 日本译界对俄国革命文学的热情,也感染了鲁迅。他对俄国文艺思潮的印象、观点也受到了日译本的启示。鲁迅一方面去阅读那些新生的作品,一方面从理论著作中寻找线索。那些陌生的话语给他带来的有兴奋,也有困惑。这些都是一看即明的。 日本学者对文坛最大的不满是庸俗与虚无。鲁迅在翻译青野季吉的《现代文学的十大缺陷》时注意到这样一段话: 现在的作家,大大小小,都受着自然主义运动的洗礼的。因这缘故,便大抵带些无理想底的心境,即虚无底的心境。加以现在的作家,即使是无产阶级的作家罢,而有一部分,是小资产阶级,或颇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心境的。这也是使他们怀着虚无底的心境的原因。(15) 这样的陈述,有一种自我否定的力量,对照中国文坛的一切,也不是没有参照价值。中国的文人在译介西洋理论的时候,虽然也批评过中国的文坛,但似乎成了真理在手的上帝,别人均成了恶魔。日本知识界是在真诚地翻译域外的理论,在思考一些问题,但中国知识界的耐心不够,对外来思想的理解的皮毛性也是值得反省的。如此说来,我们还在老的路上,名词新了,精神还在旧路上,并无新鲜的所在。在翻译片上伸《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时,鲁迅于“小引”里有这样一段话: 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了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什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仿佛都已经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现在藉这一篇,看看理论和事实,知道势所必至,平平常常,空嚷“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如此而已。(16) 日文对俄国世界的描述,由于语言的隔膜,在韵律上是有别的。鲁迅在日译本里找到了较为满意的,就进行了转译。其间主要是对文学作品的转译。因为害怕其间翻译失当,也从德译本进行了校刊。 比如关于托尔斯泰,鲁迅曾十分想得到关于他的传记的文字,寻了许多外国书店而不得,只好从日本井田孝平的译本《新露西亚文学研究》转译。1928年,日本国际文化研究所编译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就引起鲁迅的注意,而藏原惟人《访革命后的托尔斯泰故乡记》,也是鲁迅指导许广平译的。有趣的是,鲁迅还据日本经田常三郎的译本转译过卢那察尔斯基的《托尔斯泰和马克思》。联系他自己收集的托尔斯泰的译本,则很能够感受到他对这位俄国作家的印象了。 鲁迅对日译本的关注,和他晚年的文学实践活动不无关系。他认为域外思想固然丰富多彩,而真有价值的也许只有俄国的文艺。这个思路给他带来了自我更新的刺激,也带来了相关的问题。因为过于集中在俄国的资源上,对俄国文化相异的存在缺少对比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残酷的环境里,他无法进入文化的多元的世界,历史给他的时间太少了。 从其保存的日译本俄国作品看,许多的翻译是认真的。那些小说、诗歌,都与纯粹的本土文学不同,有另类的意味。而理论文章的译介,亦多佳作。鲁迅晚年对俄国理论的热情,超出一般作家。他由托洛茨基到卢那察尔斯基,看到了批评的另一种美。他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批评文章的转译,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期待。 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分别从尾濑敬止、中杉本良吉、金田常三郎、茂森唯士、藏原惟人的译本转译而成。在谈到藏原惟人的译文时,鲁迅说: 原译者按语中有云“这是作者现实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基准的重要论文。我们将苏联和日本的社会底发展阶段之不同,放在念头上之后,能够从这里学得非常之多的物事。我希望关心于文艺运动的同人,从这论文中摄取得进向正当的解决的许多的启发”。这也是可以移赠中国的读者的。还有,我们也曾有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自命的批评家了,但在所写的判决书中,同时也一并告发了自己。这一篇提要,即可以批评近来中国之所谓同种的“批评”。必须有更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17) 鲁迅看日本思想者的文章,感受到一种研究的深度,他们一方面译介作品,一方面从世界视野里瞭望文学的发展过程,在态度的认真和研究的刻苦上,都值得中国人的学习。从鲁迅的翻译与收藏看,藏原惟人对鲁迅的文学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俄国革命文学的理解,鲁迅是从他的文章里感受到其间的主旨的。 藏原惟人对俄国文学从托尔斯泰到法捷耶夫的历史的描述,看到了俄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也点到了其间的要害之处。就是革命的政党意志进入了文学。在托尔斯泰的时代,文学是个人与世界的对话,乃自我意识的扩张,有自我焦虑的突围。而到了法捷耶夫那里,个体精神的问题只能够在团体的世界里得到解决。鲁迅看到了俄国解决知识分子困境的办法,这对他是有吸引力的。日本左派文人译介俄国文学的目的明显,就是要直面自己的问题。那些问题的提出,是在与新俄文学的对话里完成的。 1930年,鲁迅翻译法捷耶夫的《毁灭》,就引用了藏原惟人的文章,对革命文学与小资产阶级文学进行了区分。(18)藏原惟人在这里礼赞了无产阶级的文学的特点是有组织性。对此鲁迅一定感到新鲜。但如何组织,谁来组织,组织的形态如何,鲁迅都不知道。他后来所唯一知道的是,中国“左联”的组织活动,是有问题的。苏联的组织形态对于鲁迅不过一个美好的符号。在纸面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里,有很多不能通约的存在。 在面对新俄文学的时候,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话题依然保持着兴趣。法捷耶夫给他的启示不都是革命的对错问题,而是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自己的有限性。而他在列宁主义已经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依然欣赏被逐出共产党的同路人的作品,对《城与人》《竖琴》别有心解。由此他还从法国的纪德和德国的乔治·格罗斯那里,对照审视知识群落的自我调整。他从日本译本的不同观点的文本里,寻找着解决困顿的办法,那些尖锐的批评文字和与现实周旋的文字,与其说是坚信了自己的道路,不如说是在修改自己的道路。他从俄国文学里增加了现实批判的勇气。 在驱赶他之所谓“鬼气”的时候,他的困惑也一直挥之不去。强化了解放自己的思路过程,连带也产生了诸多的疑问,比如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差异,勃洛克和高尔基的不同,普列汉诺夫何以被列宁主义取代,等等。所熟悉的那些同路人的作品,那些作家的感伤的、灰暗的体验,对鲁迅都有相同之处。但这些却是行将消失的存在。他由此而体悟到,自己也是一个即将被扬弃的旧的知识人;从俄国的大变动里,看到自己的未来不能不面对的命运。那些痛苦的、快乐的、忧伤而期待的文字,仿佛无数灵魂的跳动,也与其有着默默的攀谈。鲁迅由此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谈及此类话题时,坦然讲到个人主义的问题,讲到自己的局限性。而那些改造社会的革命者,多是没有旧文人气的。鲁迅在与那些陌生的存在的对话里,渐渐告别了自己身上的旧的遗物和灰暗之气。 这个对话的过程,是他的自我怀疑的过程,也是构建批评思维的一种精神律动。鲁迅不是为了解决信仰的问题而进行对话的,而是如何像日本知识界摄取俄国文明那样形成自己的批评的话语。他从俄国文学那里既看到了革命的话题,也意识到如何自我突围的重要,即克服自己的旧时代的痼疾,在火中获得新生的可能。鲁迅既没有停留在普列汉诺夫那里,也没有歇息于列宁的世界中。他对俄国文学的选择更多是自我审视的需要。这是一个审美的期待,也是自我意识的拷问。他借此而对中国问题进行重新处理,多了怀疑主义的成分,“终于信仰”与否还是一个问题。 研究鲁迅的晚年思想,翻译实践所折射的话题,可以瞭望到他内心最为本然的存在,但他的疑惑、徘徊的阅读状态也可见到一二。不过,他的许多文章没有提及于此,深层的存在还值得我们细细打量。我们由此可以见到以往的论述里片面的存在,它们把不确切性的深层因素遗漏掉了。对照那些译本,有时候会发现鲁迅对一些观点的借用和转用,有时候则能够体会到他“左”转的心境。鲁迅收藏域外图书、翻译俄国作品的过程,是与异质文化对话的过程,在对话里,自己的缺欠才能够清晰,而自我与他人的联系则更为深切了。假如没有这样的对话,晚年鲁迅则无法摆脱更大的寂寞。 我以为抓住鲁迅的这个状态,或许能够使学界对他的描述,从列宁主义的本质主义中移开,进入更初始的状态。鲁迅与同时代的左翼作家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把自己打扮成天使,而他者皆为恶魔。他是带着对自己的怀疑的态度,与那些陌生的存在进行交流,以疗救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研究如果忽略他始终是一个怀疑论者,那就可能把鲁迅置于封闭的描述系统,也就无法证实这样的事实:这个思想者何以在喜欢托洛茨基之后又远离了托洛斯基,欣赏列宁的思想而在本质上是非列宁主义者。研究的任务之一是去掉幻象,看到我们觉得“所以然”的事实而不是“非所以然”的存在。鲁迅不是一个独断论者,他永远在寻找着什么,他一方面直面着现象界,一方面与多样的精神群落对话。他的智慧诞生在多维的交流里,也诞生于默默攀谈的静思中。我们的研究是否应从这个的视角瞭望他的存在,以矫正以往研究思维里的问题?鲁迅的表达体现出思维的无限种可能性,自然,研究也相应存在着无限种可能。那些文本给我们的非结论性的、带着鲜活生命气息的空间,实在值得我们重新去面对、重新去阐释。而研究鲁迅,本身不就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和审视自我的过程吗? 注释: ①《鲁迅全集》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9页。 ②④⑥叶渭渠编选《日本随笔精典》,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40、202、146页。 ③《鲁迅译文全集》4,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6页。 ⑤[日]永井荷风:《法兰西物语》,陆菁、向轩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8页。 ⑦《鲁迅全集》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75页。 ⑧《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3上海)内部印刷稿。 ⑨⑩(11)(13)《鲁迅译文全集》4,第37、41、50、127页。 (12)[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14)(15)(16)《鲁迅译文全集》4,第110、144、161页。 (17)(18)《鲁迅译文全集》4,第388、247页。标签:鲁迅论文; 文学论文; 托尔斯泰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读书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