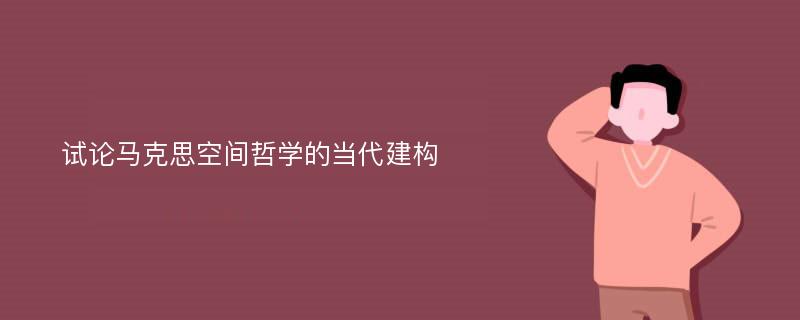
[提要]马克思对空间哲学具有原创性、奠基性和革命性贡献。“马克思空间哲学”的当代建构是在“空间转向”语境下争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需要。“马克思空间哲学”包括社会空间的实践本体论、“社会—历史”的辩证唯物论和“社会—历史”空间的本质规律论。“马克思空间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实践唯物主义空间本质论、空间的社会逻辑、空间生产理论、世界交往的空间叙事、资本空间化及其批判、社会空间的断裂及其解放、社会空间正义思想等。“马克思空间哲学”的研究有助于回应西方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挑战、彰显唯物史观“社会—空间”思维方式和建构马克思空间哲学思想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空间哲学;空间转向;实践唯物主义;现代性
一、何谓“马克思空间哲学”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中,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空间转向”。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空间转向”并没有引起我国学界的高度重视。1998年,李三虎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了《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科学地理学》,这是我国最早关注“空间转向”问题的理论成果;2005年,吴瑞财在《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全球化:现代性研究的空间转向》;2006年,何雪松在《社会》上发表了《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之后,“空间转向”问题逐步受到文艺理论、城市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关注。西方社会科学“空间转向”中的主要领军人物,大都以马克思空间思想为参照,他们的思想体系中都毫无例外地渗透着马克思空间思想的元素。因此,我们明确提出并系统建构“马克思空间哲学”,是因为马克思对空间哲学有着原创性、奠基性和革命性贡献。
(一)社会空间的实践本体论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时空观是在辩证唯物主义部分,作为“物质运动的时间与空间”仅仅在物质本体论的狭隘视域得以阐释,从而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时间与空间的属人性、社会性,或者说忽视了对于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研究。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围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哲学笔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展开,重点阐述时间空间的客观性、有限性与无限性,时间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从实践本体论出发,把对时间、空间的阐发从物质运动领域扩展到社会历史领域。人类文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时间的累积而且表现为空间的累积。人类是时间存在和空间存在的统一。通过实践的空间化可以弥补人类个体生命时间有限性的不足。正因如此,人类“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1](P.5)。
时间与空间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尺度,是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基本维度。一般认为,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实践的时间之维和空间之维并非平均用力,而是存在着一种重时间轻空间的倾向。列斐伏尔看到,长期以来,“空间”只是作为传统的地理学、建筑学、城市学等的研究对象,游离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之外。福柯更是看到,从康德以来,哲学家们思考的是时间,黑格尔、柏格森、海德格尔,莫不如此。与此相应,空间遭到贬值,因为它站在阐释、分析、概念、死亡、固定还有惰性的一边。时间是易逝的、多变的,空间是疆化的、固定的等,因而以往的哲学家们存在着“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这种偏好在马克思那里仍然存在。[2](P.84)这一观点,我们不敢苟同。我们认为,马克思对空间的重视一点不亚于时间。马克思学说的旨趣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他说:“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3](P.152)“旧世界”与“新世界”代表着不同的空间形态,代表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不同的空间组合。马克思、恩格斯“改变世界”的哲学诉求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的空间革命。马克思“自由王国”的空间理想是奠立在实践的革命性基础上的。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不仅是揭开“时间—历史”之谜的钥匙,而且是揭开“空间—社会”之谜的钥匙。马克思“社会—历史”的时空辩证法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空间革命的本质,而且指明了无产阶级空间革命的方向。
(二)“社会—历史”的辩证唯物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包括人类史和自然史。自然史暂且不谈,人类历史主要是社会发展史。在对“社会”的历史考察中,一些人认为马克思出现了“时间偏好”,实际上,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社会”不仅有历史性的时间维度而且更有共时性的空间维度。马克思运用实践唯物论去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阐发了历史唯物论、历史辩证法,实际上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唯物论”和“社会辩证法”。[4](P.33)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关系)是决定社会结构的关键因素。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5](P.187)同时,他把理想的“社会”理解为“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5](P.724)。社会形态的演变归根到底不过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空间结合方式变化。因而,当把“空间”理解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及其变化时,我们便不仅抓住了空间的“社会”内容而且抓住了空间的“历史”演变。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不仅是“历史的唯物论”,而且是“社会的唯物论”。当我们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社会—历史”的辩证唯物论时,才能更好地彰显“社会”的空间之维和“历史”的时间之维。当然,“社会”不仅有空间之维而且有时间之维,“历史”不仅有时间之维而且有空间之维。马克思在实践唯物论基础上深入探讨了“社会—历史”的时空辩证法。但是这种探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并没有开辟专门的章节,相关内容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阐释之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为切入点,向我们全面展示了资产阶级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画卷。马克思对人类存在的空间性尤其是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的阐释、对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历史的揭示、对资本空间的终结与劳动空间的解放的探讨、对“自由王国”理想空间和人的空间发展、空间解放的论述等等,构成了马克思空间哲学的主要内容。简言之,马克思空间哲学是“社会—历史”的时空辩证法。
通过访谈和实验,一致认为目前来说字幕确实是帮助听觉障碍者实现无障碍网络课程的最好途径之一。而像中央电视台一样配备专门的手语老师能够提高课程的效果,但同时也增加了课程的成本。
“马克思空间哲学”的研究坚持从“马克思空间哲学是什么”出发,以空间的实践本体论为基础,从社会空间、空间生产、世界交往空间、资本空间化、空间解放与空间正义等角度进行文本解释和学术梳理,建构“马克思空间哲学”思想体系,确证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空间哲学的原创性、奠基性和革命性贡献。“马克思空间哲学”理论框架的当代建构,有两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一是提出“马克思空间哲学”命题,其中内在地包含着恩格斯的空间哲学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同心同向、共同创作的理论成果,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立场、基本观点和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的。任何企图割裂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比较而言,马克思更侧重空间的实践本质、社会意蕴的探讨,以及从宏观视域研究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恩格斯更侧重空间的自然本质、物质运动的探讨,以及从微观视域研究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二是提出“马克思空间哲学”命题,主要意图是从多个角度系统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历史”空间研究的重大贡献。目前,多数关于马克思空间思想研究的成果,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空间哲学思想所占比重大多不足,往往花费更多篇幅分析阐述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的思想。这些研究能够拓展空间问题研究的理论视野,但也令人感到马克思、恩格斯空间哲学思想挖掘、阐释严重不足,似乎马克思、恩格斯空间哲学思想单薄且贫乏。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空间哲学的重大贡献极不相称。正因如此,需要我们努力建构“马克思空间哲学”思想体系,全面整体地呈现“马克思空间哲学”的理论内容。
当然,不可否认,马恩尤其是恩格斯从物质本体论的层面阐述了时间、空间与物质存在的关系,论证了时间的一维性、空间的三维性,论证了时间与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不可分割。但是,马克思空间哲学的独特贡献却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空间观,以及“社会—历史”的时空辩证法。
(三)“社会—历史”空间的本质规律论
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空间本质论研究主要阐明空间的实践本质,以及基于实践空间的三种空间形态和三个诠释维度。实践唯物主义奠定了正确把握空间本质的理论基础。空间存在于实践活动之中并且作为实践活动的结果而呈现。科学实践观的确立实现了空间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由此,使人类对于空间的理解由“天国”回到了“人间”。马克思关注现实空间,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构成了空间的两大实体性要素。空间是现实的属人的实践空间,马克思所主张的是一种“人类实践活动立论”的空间观。马克思把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理解为基于人类自由自觉活动而将理想空间转化为现实空间的过程。这种空间的社会化形塑本质上是实践活动的对象化,由此形成了三种空间形态,即“人化自然空间”“社会关系空间”和“历史活动空间”。它们统一于实践空间。实践空间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总和。实践空间以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为基点,从“物理—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心理”三个维度全面展开。
马克思的空间断裂及解放途程研究主要剖析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造成的物质变换“裂缝”。资产阶级通过空间发展战略,把物质变换“裂缝”转嫁给落后国家,造成了全球空间断裂。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导致个体发展与“类”发展的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现实的个人二重化为相互敌对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认为,人类解放就是现实的个人从他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是从“人化自然空间”和“社会关系空间”获得解放。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空间革命的巨大贡献,但是,资产阶级空间革命只是解放了自身,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资本空间变成了新的牢笼。资本生产从地域性扩展到全球性,丰富了人类的物质交往关系,彰显了资本的神奇力量,开启了现代性的途程。但是,资本逻辑却形塑了两极对立的空间形态。对于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的空间革命就在于消解空间断裂、弥合空间“裂缝”,用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扬弃和超越资本空间。
二、“马克思空间哲学”的研究内容
1.抓住“人”这一核心元素。凝聚人心,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群众才把社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社区自治最重要的是要发挥“人”的作用,没人管是最大的问题。一是发挥社区党委的核心引领作用。只有党组织始终发挥引领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做好创新社会治理工作。二是发挥党员骨干的带动作用。党员一般守纪律、有追求、讲奉献,群众自然就被影响从而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氛围。三是发挥广大带动热心居民的参与影响作用。创新方式方法,通过热心居民的带动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实现“代民做主”“为民做主”向“让民做主”“请民当家”转变。
21世纪以来的人类实践活动中,高科技与低情感交织、高效率与高风险并存,网络化推动城市化和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空间实践的迅猛发展把人们抛向无边的“空间焦虑”。因此,只有与时代脉搏共振,才能推动空间理论的创新发展。谭长流先生指出:“关于空间的问题,已经到了人类应该研究的时候了。否则,偌大的空间就一定遮蔽人类文明的思想的发展。对空间问题不解决,就会使思考着空间问题的人们感到茫然。”[10](P.4)马克思的时代,空间问题域已经非常明显。马克思的空间思维使其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立足于全球立场。早期,马克思以英国、德国、法国为“样本”,解剖西欧社会空间,形成了西方社会理论;晚期,马克思以中国、俄国、印度为“样本”,解剖东方社会空间,形成了东方社会理论。这种社会形态研究的空间转向,确证了马克思的空间叙事。“空间转向”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实现马克思空间哲学的在场和出场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马克思哲学本身存在着“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的双重维度。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坚持时间空间辩证法是马克思的一贯立场。因此,提出并建构“马克思空间哲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关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空间本质论研究
马克思对时空问题的探讨从物质本体论升华到了实践本体论,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空间的本质和规律。“社会—历史”空间有着人类实践活动的烙印、承载着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是马克思空间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社会—历史”空间的全面展开只有立足实践唯物论才能得到合理解释。“社会—历史”空间根源于人类实践活动,被人类实践活动所建构和改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出发,以劳动异化理论阐释了“人化自然空间”和“社会关系空间”,把“社会”理解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和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系统阐述了“社会—历史”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历史”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复杂的多向度的。在不同社会形态或者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历史”空间呈现不同的视阈和特征。
(二)关于马克思空间的社会逻辑研究
马克思空间的社会逻辑研究主要是全面揭示空间的社会本质,阐明社会运动的空间存在方式。空间是万物的存在形式、实践的布展场域和生命的寄寓处所。人首先在一定的空间持存和展开,并通过生产和交往塑造着社会空间形态。由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由自然空间向社会空间、由物理空间向人文空间的转化,只能当做实践去理解。马克思空间的社会逻辑研究,关注空间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空间化、关注人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空间统一性。在实践基础上,空间的社会化形塑和社会的空间化厝置是同一过程,其本质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相互建构。只有把握了空间的社会性才能揭示它的现实本质。空间作为生产要素是前提,同时,空间本身又是社会生产的结果。马克思对空间社会化重构的解释,是以生产方式为轴心的,尤其是重点解剖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对社会历史空间的形塑,揭示了资本旋风导致的空间异化,并且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空间解放诉求。
(三)关于马克思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
马克思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旨在阐明资本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空间生产方式,它实现了由时间—空间辩证法到空间—时间辩证法的转变,以及“空间规划”扬弃“时间规划”的过程,开辟了空间生产的纪元。马克思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要在阐明空间生产、空间生产力、空间生产关系概念的基础上,论证空间的生产性建构过程、空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效应以及空间的生产方式图式。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表现为时间性积累,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表现为空间性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空间逐步取代时间的地位和作用,成为首先考虑的要素。马克思不仅揭示了商品流通过程的空间—时间辩证法,而且揭示了商品生产过程的空间—时间辩证法。马克思对商品生产空间维度的分析为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的生产”奠定了理论前提。“空间的生产”突出了对人类物质生产过程的空间维度分析。在这种分析中,空间要素成为物质生产过程和结果的优先考虑成分。
(四)关于马克思世界交往的空间叙事研究
马克思世界交往的空间叙事研究主要是以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市场过程中对世界历史的重构为主线,论述了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与以往的历史观不同,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把握不仅坚持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维度,而且立足现实性立场,从时间—空间的辩证统一视角把握。“社会—历史”的本质是人的生产和交往。“社会—历史”作为人的现实的存在方式,不仅是积极的时间性存在而且是对象化的空间性存在。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市场过程中开创了世界历史。世界市场是世界交往的空间展开,世界历史是世界交往的时间展开。因此,资产阶级时代的世界交往表现为空间的时间化。现实的个人和现实的自然是马克思空间叙事的逻辑起点,它们构成“社会—历史”空间的实体性、能动性要素。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轴心,重点解剖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对“社会—历史”空间的形塑,从世界历史的时间之维和世界市场的空间之维全面阐释了资产阶级的世界交往史。
(五)关于马克思的资本空间化及其批判研究
马克思的资本空间化及其批判研究主要探索资本空间的历史生成,资本在征服劳动的过程中实现了从“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转变。资本运动有着自身的时空条件和边界,其结果必然造成世界市场危机。资本空间化的结果是空间资本化。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空间生产是一个“去空间化”和“再空间化”的过程,是一个打破旧的空间壁垒和限制,并且按照新的资本、权力和利益逻辑重新塑造社会空间的过程。其中,最基础最根本的是资本逻辑。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空间生产实现了生产扩张与生活创造的并进。资本逻辑贯通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全过程,创造着空间结构、空间关系和空间产品的全面性、丰富性。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空间生产是一个从资本空间化到空间资本化的过程,推动这一进程的是资本积累的驱动逻辑、资本生产的空间逻辑和资本形态的裂变逻辑。资本本性使得物化的空间生产成为目的,整个社会空间表现为建立在物的依赖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这种异化空间终将被共产主义“自由王国”所取代。
(六)关于马克思的空间断裂及其解放途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对空间哲学的探讨是与其唯物史观的发展同步的。第一阶段,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第一次作了经典表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空间哲学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社会—历史”空间的实践本质,以所有制关系为尺度,阐述了“社会—历史”空间形态的演变规律,论证了生产实践基础上“自在自然空间”向“人化自然空间”的转化,揭示了“社会关系空间”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中介,人类在改造自然的生产中同时进行着“社会关系空间”的生产。第二阶段,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对资本空间进行了典型解剖。马克思提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6](P.29)他说:“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态的结构和生产关系。”[6](P.29)同济大学李春梅认为,马克思对社会空间生产的解剖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宏观的全球空间生产,二是中观的城市空间生产,三是微观的居住空间生产。[7](P.13)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解剖意味着马克思空间哲学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运用与发展。第三阶段,马克思晚年在人类学研究基础上阐述了两种生产理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了系统表达。恩格斯说:“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8](P.16)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从两种生产的视域解释“社会—历史”空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当代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说:“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变化就必定伴随一个新空间的产生。”[9](P.46)他虽然首次提出“空间的生产”概念,但这一思想的源头却存在于马克思著作之中。两种生产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石。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弥补了两种生产理论之空间维度的不足,但是,他用空间叙事逻辑取代生产叙事逻辑的倾向,却是对马克思空间哲学的偏离。
(七)关于马克思的空间正义思想研究
20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科学一个举足轻重的事件就是“空间转向”。这个曾经被忽视的“空间”范畴和领域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学者们开始刮目相看人文生活中的‘空间性’,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给予社会关系和社会的青睐,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11](P.3)为什么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空间转向”呢?按照福柯的解释,大体有三个原因:一是哲学观念的转变。主要是传统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二卷的基本假设是一种无空间的资本主义;第三卷拟开始的空间分析却未曾问世。二是学科从分工到整合。学科分工导致理论的狭隘。社会理论家有意无意地把空间变迁推给地理学,空间被地理学所宰制,地理学只关注空间的自然性,忽视空间的社会性。三是时空体验的转型。空间的缺席或者重申与现实的空间体验直接关联。20世纪是空间的纪元,1970年代后,人类进入空间时代。新的空间体验呼唤人们重新反思空间问题。在“空间转向”中,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到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福柯的权力空间分析到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等,他们突出空间主题和拓展空间分析,打开了现代性批判的广阔视野。回应“空间转向”的挑战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马克思空间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
在脓毒症的免疫抑制阶段,由于胸腺萎缩及外周血中T淋巴细胞减少可导致机体免疫监视功能减弱,对病原体的易感性增强,增加二次感染的可能性[32]。在多细菌诱导的脓毒症动物模型中,炎症早期使用S1P类似物(FTY-720)抑制T淋巴细胞从淋巴器官迁出,对小鼠生存率无显著影响[33]。然而,在柠檬酸杆菌诱导的脓毒症小鼠中,FTY-720长期治疗的小鼠体内病原体清除延迟,且其脾内的细菌含量显著增加[33-34]。
(一)回应西方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挑战
马克思的空间正义思想研究主要是马克思对资本空间非正义性批判基础上,阐明马克思空间正义思想的三个诠释维度即经济空间正义、政治空间正义和文化空间正义。同时,分析研究马克思关于实现空间正义的路径,包括生产和交往的普遍化、共产主义空间革命、实现劳动的解放等。探讨空间正义不可能摆脱马克思的“幽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分析、对城乡空间结构断裂的揭示等,都蕴含着空间正义的价值诉求。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空间化的历程,而且揭露了空间资本化的非正义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空间正义的诠释,虽然沿袭了资本主义的批判指向,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达成空间正义的现实路径。社会正义问题的空间化使空间正义逐渐成为社会批判的理论武器和社会政治行动的价值目标。空间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解资本主义的中轴,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论的梳理和探讨,旨在回应西方社会科学“空间转向”,为中国城市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空间正义问题提供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显然,认定马克思哲学之中空间思想的薄弱或者缺席,是西方空间理论家合乎逻辑地发展社会空间理论的前提。问题在于,马克思哲学中是否存在空间维度?或者说,马克思空间哲学何以可能?如果马克思根本没有空间哲学思想抑或马克思空间哲学思想不过是只言片语,那么,提出“马克思空间哲学”范畴便很难成立。国内研究马克思空间思想的学者大多结合“空间转向”问题,回应和阐释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空间理论的反思。我们提出“马克思空间哲学”的目的就在于积极建构“马克思空间哲学”思想体系,确立马克思空间哲学的基本立场、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结合当今时代的空间实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去挖掘空间哲学思想的宝藏。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理论的任何“空间转向”都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方向。当前,回应西方社会科学“空间转向”,彰显马克思空间哲学的现代性,实现马克思空间哲学的出场和在场,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与空间的关系。社会空间或空间的社会性是西方空间理论家关注的一个重点。马克思空间哲学在揭示空间实践本质的基础上,回答了空间是自然本质与社会本质的统一。二是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时间空间辩证法是把握社会运动的关键。把空间归结为时间的“时间—空间辩证法”和把时间归结为空间的“空间—时间辩证法”都是唯物辩证法的表现方式。空间的实践本质论和时间空间辩证法是建构马克思空间哲学的两大理论基石。
(二)彰显唯物史观的“社会—空间”思维方式
时间与空间是把握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基本维度。马克思主要的哲学贡献是把实践唯物主义引入到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不仅存在“历史—时间”的思维方式而且存在着“社会—空间”的思维方式。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是缺少社会历史视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首先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实现革命性变革的。因此,“历史—时间”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空间”的思维方式都是马克思解剖资本和论证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工具,但是,后者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和遮蔽了。提出“马克思空间哲学”并非是要把“社会—空间”思维方式强行“塞进”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而是力图“显影”马克思空间哲学的历史传承、发展脉络和理论体系,还原马克思基于“社会—历史”的时间空间辩证法。建构马克思空间哲学,必须耐心地爬梳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无论是马克思博士论文中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思想,还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思想;无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交往思想,还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世界历史、世界市场和世界文学思想;无论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中的城市思想,还是《资本论》中的时空辩证法;无论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本“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揭露,还是晚年对东方社会和北美“新大陆”的关注等,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空间哲学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思想的精细研究,是我们建构马克思空间哲学的基础。当然,提出“马克思空间哲学”并不是要在唯物史观之外另起炉灶,而重在彰显唯物史观的“社会—空间”思维方式。
情景教学模式主要引入参观、考察、实习、见习等实践环节,以真实的旅游管理过程为情景,让学生从体验中发现问题、分组调研、解决问题。在情景教学中,学生是主导的,教师是“旁观者”,要给予适当、及时的引导,促进学生自主完成。情景教学对学生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具备一定的问题解决能力,特别是在旅游管理具体事务中,从中来分析、调研、解决相关真实、具体问题,考验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马克思空间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空间。对于社会空间的理解必须置于实践生存论视域。马克思空间思想的遮蔽与社会思想研究的忽视和被误解有着直接关联。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从生动的现实出发,旨在批判旧社会中建构新社会。马克思坚持从社会生产关系视域研究社会有机体,他所理解的社会是一个立足经验又超越经验的哲学概念。马克思的社会概念立足于自由人的联合,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和解确立为社会理想。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具有实践维度、批判维度、理想维度和时空维度。这些维度是研究社会空间问题、建构马克思空间哲学需要重点探讨的内容。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把所有社会事件一概纳入历史维度去理解,于是“社会学”变成了“历史的”。历史变成了理解社会的唯一切入点。他对此非常不满,并试图建立一种“空间—时间—存在的三位一体的辩证法”。苏贾索亚说:“有组织的空间结构,并不是一种独立结构,……表征了各种一般生产关系的一种业已得到辩证解释的成分,这些生产关系也同时是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12](P.119)苏贾索亚从时间、空间的双重维度把握社会的努力值得我们借鉴。
(三)建构马克思空间哲学思想体系
要想重新理解和构造马克思空间哲学,必须揭示长期被掩蔽的马克思对空间理论的重大发现和划时代的创造。改革开放以来,时间与空间问题的研究受到了我国学界的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便发表了一些关于时间、空间本质及其特征等问题的论文。如鲁开荣的“论空间和时间的绝对性和相对性”(1980年)、E.马克特、黄振定的“非间断空间和分立空间运动的辩证法”(1980年)、王廷科的“谈谈历史教学中的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1980年)、刘相安的“户坂润及其空间论”(1982年)、艾萨克·阿西莫夫、冯秋明的“人类空间时代展望——我们在太空的命运”(1982年)、张西平、张保全、张朝宁的“关于空间本质问题的思考”(1983年)、晓原、曾晃农的“消费需要、消费时间、消费空间”(1984年)、江冰的“空间与效益——读《资本论》札记”(1984年)、黄荣滋的“浅论马克思空间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1984年)。尤其是1991年,《哲学研究》第10期上就发表了刘奔的论文《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社会时—空特性初探》,应当说,这是复活马克思时空观的探讨。俞吾金先生认为,此文的主要贡献有三:一是把传统哲学教科书对时空观的探讨从“物质—运动”领域引向了“社会—人类活动”领域,进而阐明了时空理论与人类争取自由活动的必然联系,丰富了时空理论的社会历史内涵;二是把时空理论纳入实践唯物主义体系,阐明了社会时空的基础和源泉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三是揭示了时空观的丰富的辩证法内涵。[13](P.11)近些年来,相继出版了一些涉及马克思空间哲学思想的著作。如2006年,高鉴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他作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书中的第二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市思想”中用了不到3万字的笔墨阐述了马克思的城市空间思想。2012年李春梅的《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用了第一至四章约12万字的笔墨阐述了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孙江的《空间生产——从马克思到当代》,第二章“马克思的空间生产理论”加上第四章“对空间拜物教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部分内容,用了约4万字的笔墨阐述了马克思的空间生产思想。2016年张荣军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用了第三章“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内容与结构”约6万字的笔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马克思空间哲学”研究的旨趣在于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爬梳一部专门阐述空间哲学的著作。西方空间理论家断言马克思存在空间理论“空场”、存在“时间偏好”。我们的研究要证明,马克思是一位真正的空间哲学家,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阐明了社会空间的实践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实现了空间哲学的革命性变革。
精确称取芦丁、野黄芩苷、橙皮苷、柚皮苷对照品,分别配制成 1. 0 mg/mL 的对照品溶液,用0. 45 μm微孔滤膜滤过,4 ℃保存备用。分别取配制的对照品溶液适量混匀,制成混合对照品溶液。
可以看到,同一节假日对不同客源市场旅游需求的影响不同,这可能与各客源市场距离旅游地的远近、自身人口数量的多少、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关。
参考文献:
[1][美]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M].李小科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2]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章仁彪.“人化自然”:和谐社会建构中的三大空间论——从“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时空观谈起[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李春敏.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1991.
[10]谭长流.空间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11]陆扬.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J].外国文学研究,2004(4).
[12][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3]俞吾金.马克思时空观新论[J].哲学研究,1996(3).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6—0065—07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及其现实意义研究”(HB18ZX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维意,河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的空间哲学、实践哲学。河北 保定 071002
收稿日期 2019-03-10
责任编辑 尹邦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