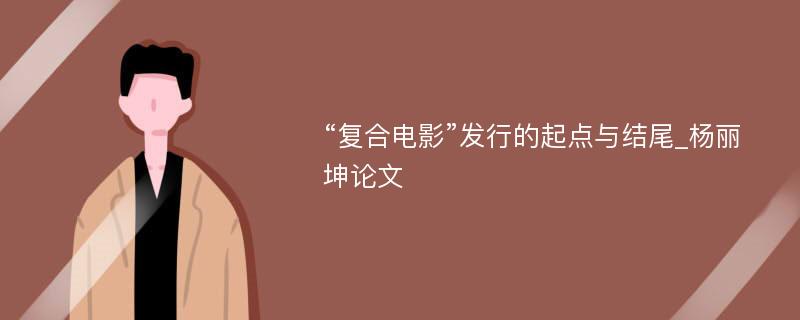
“复映片”公映始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始末论文,复映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0年前,我在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处从事影片与电影剧本审查方面的业务工作。刚粉碎“四人帮”后,根据中央(76)18号文件精神,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广大群众只能看八个样板戏电影和“老三战”故事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三片的统称——编者注),精神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状况,要求文化部成立专门的“电影复审小组”,对被江青、康生一伙扼杀禁锢的“十七年”电影全面进行复审,没有问题的电影尽快予以解放,恢复上映,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在这种特殊形势下,电影局责成艺术处承担起这项艰巨的任务。
一
当时,艺术处人员很少,既要处理日常的故事片、新闻纪录片、美术片、科教片的审查业务,又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新的“复审”任务又很急迫,艺术处的工作相当紧张,当时把拍摄了样板戏电影《沙家浜》的长影导演武兆堤留在电影局,负责“电影复审”工作(后来由丁峤主抓这一工作)。武指定我与李文斌以复审工作为主,兼顾相关业务。从1976年11月起步,一直到1979年上半年基本结束,约两年半时间,过目千余部影片。除600多部十七年摄制的故事片、戏曲片、美术片外,还有十七年公映过的外国片,以及“文革”后期摄制的一批新故事片。工作量相当大,经常一天看三四部影片,若放映室能安排得开,有时早、午、晚连看6部影片,甚至星期天也加班。因为许多影片要分别请对口的有关单位,如总政、军事科学院、外交部、统战部、科技部门的领导人审看,提供意见;有些难以把握的影片,还要请文化部部、局领导审看,帮我们把关。每天看完影片要及时讨论归纳意见,到了一个段落,要梳理总结审看过的五六部或七八部影片的意见和结论,代文化部向国务院写出这一批影片的复审报告,送主管电影的部领导审查、把关、签发后,呈报国务院审批(中宣部恢复后改报中宣部备案)。中央批复下来后,复审组要及时向有关制片厂发文,告知哪些影片已经通过,哪些影片需要修改,并将审查通过的影片,以电影局名义下达通过令给中影公司,安排洗印新拷贝及公映的时间。这个程序贯穿复审工作的始终。向国务院签发复审影片审批报告的文化部领导人先后有:华山、石敬野、黄镇、王阑西、司徒慧敏等。1977年前期,基本上由吴德直接批复。
我亲历了复审十七年电影的全过程,李文斌参加这一工作时间也较长(初期、后期他未参加)。先后还借调过北影演员袁玫,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史宽等人来复审组协助工作,还有些其他人,不过时间较短。
“复审电影”究竟怎样进行?如何把握审查标准?“文革”期间主持工作的领导已停职,新领导又未上任,向谁请示?可以说是特殊年代的一种特殊现象,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既复杂又陌生,复审组初期只能在探索中寻找路径。我们研究了1949年底文化部清理全国电影市场的做法。那是共产党新政权清理国民党旧政权留下来的电影市场。旧社会是美英电影统治中国电影市场,其次是国民党各色形态的电影,是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当时,文化部由电影局草拟了一个清理全国旧片的审查标准和原则,委托各大行政区文教主管机关负责审查清理本行政区的旧片,合格者发给临时执照。其审查原则大致如下:凡是反共、反苏、反人民的,凡是宣传帝国主义的侵略(包括种族歧视)或宣传封建奴役的,凡是宣传淫秽色情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法令相抵触的,视其情节轻重,决定禁演或删剪。凡不违反上述规定者均可上演。1950年2月15日,中宣部发出《对有毒影片审查标准的指示》重申了以上原则政策,并强调审查标准不能过严,禁演必须慎重,要考虑到私营影院营业及群众的需要。当时在两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交替之际,制定的这种清理旧片、整顿电影市场的原则政策,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实事求是而适宜的。一个明显的收效是,清除了美英电影,为新型的工农兵电影开辟了天地。
而我们这次复审影片,是重新复审新中国十七年摄制并曾通过发行的影片,与前述的清理旧片有着质的区别。经过学习,统一认识,明确复审影片的基本原则,仍然是1957年毛泽东提出的辨别文艺作品是香花还是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贯彻“双百方针”的原则,不能以“一风吹”的态度对待复审,而必须严肃认真地对每一部影片逐一进行复查。这个过程也是当时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有力措施,既为被“四人帮”打为“毒草”的影片解禁,也为因影片受到迫害的编导演职创作人员平反,还有部分清理任务,即清查“文革”后期按“四人帮”意旨摄制的一批帮派政治电影。同时也借此时机,甄别一下十七年受各种政治运动影响拍摄的某些图解政策的概念化影片,艺术质量不高,就没有必要继续发行公映,避免浪费。
几十年的电影要重新复审,该从何处着手?复审小组经全面研究,决定按照形势发展需要,区分轻重缓急,采取先近后远、先内后外的方针,安排审片程序。即首先对“文革”后期拍摄的影片进行复审清理,然后复审建国后十七年影片,同时为了调节和丰富公映影片的品种,要兼顾并适时地恢复上映外国影片,还要考虑到传统节庆的需要,及时恢复上映适当的影片。因此,开始复审时,先集中审查“文革”后期摄制的影片。这时摄制的影片大致分三类:一类是样板戏电影,都由江青及于会泳、浩亮、刘庆棠亲自掌控摄制,情况复杂,暂时搁置,待后期下结论。于是,先行复审这个时期摄制的第二类影片——故事片。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编导坚持以往按电影艺术规律进行创作,拍摄了一些思想艺术俱佳的故事片,如《创业》、《海霞》、《闪闪的红星》等片;再如《艳阳天》、《金光大道》、《战洪图》等,虽受到“三突出”的影响,但影片从总体上看还是应予肯定的,因此,这些影片最早复审通过上映。另一种是编导基本上以江青及于、浩、刘一伙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塑造人物,故事内容充斥“阶级斗争”的政治概念化故事片,这种影片复审时未予通过。第三类是反党阴谋电影。这是“四人帮”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组阁”计划遭到失败以后,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便有组织有计划地通过文化部干将于、浩、刘,并组织创作力量,突击摄制的一批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影片,如先后出笼的《春苗》、《决裂》、《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千秋业》等,是一批真正的反党毒草影片,理所当然地判以封禁的结论。为了配合批判“四人帮”罪恶,经请示中央批准,在全国范围组织内部放映反党影片《反击》。
“文革”影片清理告一段落之后,紧接着复审建国后十七年的影片。最先通过复审予以公映的国产影片有《洪湖赤卫队》、《小兵张嘎》、《秘密图纸》、《东方红》等片,以及朝鲜、越南、罗马尼亚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如《卖花姑娘》(朝)、《看不见的战线》(朝)、《劳动家庭》(朝)、《原形毕露》(朝)、《森林之火》(越)、《阿福》(越)、《多瑙河之波》(罗)、《爆炸》(罗)、《宁死不屈》(阿)、《地下游击队》(阿)、《勇敢的人们》(阿)等45部之多。在“文革”年代,人们对这些影片看得多了,编出了顺口溜说:“越南电影真枪真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而经历文化饥渴之后,人们再度看这些影片,却成为满足精神生活的迫切需要。
经过初期的复审实践操作,部局领导把关很严,对我们呈报的每一部影片的摄制背景、思想内容、创作人员的今昔情况都要求了解,我们便向制片厂提出要求,规定了复审程序。要各电影制片厂把本厂在十七年中拍摄的影片初审排队,分成三类:一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可以恢复上映的;第二类是内容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艺术质量不高,并不违背六条政治标准,可以宣布解放,但没有恢复上映意义的;第三类是属于毒草性质或有严重倾向性问题,需要封存的。由各电影制片厂提出处理意见,再经所属省、市委、总政有关部门复审后,分批报文化部复审小组正式审查定夺。我们还要求制片厂呈报有关影片情况时,要附上各影片主要创作人员的今昔政治情况,以及有关背景材料,供复审影片时参考。各电影制片厂得到这一通知后,积极性很高,他们都希望本厂十七年摄制的大量影片上映,既能使创作人员获得解放,也能拿到从未发行影片的收入。此后,全国各制片厂把经过他们初审的影片一批批送来,在电影局的片库里,影片铁筒堆积如山。各制片厂三天两头打来电话,催问复审结果,使复审小组压力极大,简直可以说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三个放映员轮番放映,叫苦连天。打字员打印复审报告,加班加点。
我们复审影片慢慢摸出规律,要配合传统的节庆提供充足的相关题材的影片,才不致被动。如元旦、春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到这些时候,有关部门就要求提供相关的影片作为纪念活动的重要方式。因此,复审组就要预先有准备,集中复审一批相关影片存置在那里,到时候才能满足需求。例如,1977年为庆祝八一建军节50周年而举办电影周,我们便提前复审通过并为此节提供了《万水千山》、《上甘岭》、《风暴》、《海鹰》、《长空比翼》、《永不消逝的电波》、《雷锋》、《女飞行员》等一批内容丰富的军事题材影片。由于经历了“文革”十年电影文化的枯竭期,电影银幕上一下子集中上映了如此多的优秀影片,使军民共同享受到一次丰盛的电影美宴,可谓解渴。
再如,为当年国庆节,复审提供了《林则徐》、《烈火中永生》、《李时珍》、《老兵新传》、《智取华山》、《虎穴追踪》、《女跳水队员》、《白求恩大夫》、《今天我休息》及动画片《大闹天宫》等。
同年11月7日,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60周年,复审组会同外交部、中联部共同集中复审并在全国公映了一批苏联早期的故事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难忘的1918》、《夏伯阳》、《伟大的公民》、《保卫察里津》、《保尔·柯察金》、《乡村女教师》等,又一次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从以上长串的片目中,就可以想象得到,复审组在幕后付出了多少辛苦和时间去一部部地逐一审定所有影片,并研究、草拟审批报告。
1977年底,黄镇担任文化部长,王阑西任副部长主管电影,司徒慧敏任电影局局长,丁峤任副局长。新领导工作作风雷厉风行,进一步要求复审组加快步伐,让更多的影片恢复公映。于是,电影局从电影单位借调人员,加强复审组力量,加快速度复审未审之影片。便出现了1977年底,一次向国务院呈报恢复上映33部影片;1978年初,又向国务院一次报批24部影片;到1978年底,向中宣部一次备案恢复上映50部影片。
到1978年中期,仅外国影片就恢复上映了51部之多,即可看出当时中国的电影市场丰富多彩的面貌。除前述的苏联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外,再扩大范围,恢复上映了欧美诸国的电影。如英国的《雾都孤儿》、《百万英镑》、《查理三世》,法国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塔曼果》,意大利的《偷自行车的人》、《警察与小偷》,德国的《阴谋与爱情》、《古堡幽灵》,捷克的《好兵帅克》、《更高原则》,波兰的《华沙一条街》、《寂静的线索》,匈牙利的《牧鹅少年马季》、《音乐家艾凯尔》,奥地利的《冰上的梦》,阿根廷的《中锋在黎明前死去》,日本的《二十四只眼睛》,美国的《鹿苑长春》,以及《佐罗》、《忠诚》、《叛逆》等片。
此外,还复审上映了香港的《新寡》、《三笑》、《红颜劫》、《可怜天下父母心》等影片。
截至1978年底,经统计,“文革”前摄制的673部影片(其中故事片518部,戏曲片115部,纪录性艺术片40部),经复审批准恢复上映的影片已达554部。影片思想内容与形势不符,或情节内容有较大问题而应停止复映的影片有19部;还有一种情况是电影思想内容没有问题,但影片涉及的主要创作人员的政治情况尚未做出结论,这一类影片暂缓上映,待后处理,也有些影片还未复审。还有一种情况是,在不同时期拍摄的数十部影片,思想内容不违背六条政治标准,但艺术质量较差,虽宣布解放,但已无公映发行的意义,实际上被淘汰。另外,大跃进年代拍摄了一批纪录性艺术片,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面貌,但内容上有浮夸问题,质量上粗制滥造,虽政治上无大错,也无再复映的价值,亦被淘汰之。
1979年春节,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中国影协举行的茶话会上,兴奋地号召电影工作者“奋发图强,创造一个影坛上群星灿烂的年代”。由两年来电影复审所带来的银幕繁荣景象,已预示了这个时代的到来。
二
以上文字均是报喜未报忧,其实复审组在最初一年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是在摸索中探路前行的。不是上报多少影片都能顺利地批复回来。特别在前期,复审一部,即刻上报一部,有时审看数部一起报。有的报告上去一直没有批复下来,我们不明原因,就通过局领导或部领导秘书了解情况,答案往往是:该片“暂缓复映”。文化部领导那里却常打来电话询问报批的某影片的诸多问题,如该片过去受批判的情况,或查询该片主要创作人员,如编导或主演的政治情况等。因为1977年、1978年那个时候,尚未全面拨乱反正,许多冤假错案还未平反、改正,尽管影片本身尚好,主创人员的政治问题还未解决,该片就得暂缓复映。例如,为《阿诗玛》影片的复映就发生过一场风波。该片是上海电影制片厂1964年摄制完成后,尚未发行公映,就被康生、江青以宣传“恋爱至上”和“选美人”资产阶级思想的罪名打为“毒草”。此时,夏衍、陈荒煤在文化部整风中被打为“夏陈路线”而遭受严厉批判,在这种境遇下,陈荒煤对《阿诗玛》影片的表态只能违心地附和江青他们。整风后,陈荒煤被赶出文化部,调到重庆去。1967年,又将陈押回北京作为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进行批斗,之后被关押6年半。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因去昆明参加一个文学教材方面的会议而游览云南石林,引起对电影《阿诗玛》的感触,并呼吁与会代表看了该片,引起很大反响。他又了解到主演阿诗玛的演员杨丽坤,因演此片被打为“黑线人物”遭到残酷迫害,下放思茅地区致使其精神失常。这给陈荒煤很大刺激,回到北京后就写了篇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引起较大反响,广大群众关心杨丽坤现在的情况,纷纷给文化部写信,质问为什么还不解放电影《阿诗玛》?这给文化部很大压力,对陈荒煤的做法很反感,认为当初是你陈荒煤与江青一块儿枪毙了这部电影,现在你却写文章鼓动群众来围攻文化部。为此,胡乔木出面劝说陈荒煤妥善处理此事。
群众强烈要求解放《阿诗玛》,但因杨丽坤当时在云南尚未平反,因此,该片本身虽没有问题,是一部优秀的少数民族神话故事片,但当时仍不能批准上映。这引起了文化部长黄镇的关注,亲自过问杨丽坤的事情,与云南有关方面联系,催促他们尽快解决杨丽坤的冤案问题,并责成上影厂将杨丽坤接到上海医病。经各方大半年时间的努力,杨丽坤的冤案得到平反,病情亦有好转。影片《阿诗玛》在1979年元旦公映,对外友协首先以此片招待外宾。至此,杨丽坤与她主演的《阿诗玛》经历15年的磨难后,方见天日。杨丽坤病愈后还出席了197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不过体形、容貌都发生了极大变化。而《阿诗玛》抒情长诗的整理者,影片《阿诗玛》的文学顾问,著名作家李广田却被迫害致死,未看到《阿诗玛》重见天日的这一天。这一部影片及杨丽坤、李广田的遭遇与劫难正代表了许许多多中国电影人在十年“文革”中的命运,不胜悲夫!
再如影片《清宫秘史》,我们认为这部被“四人帮”作为重型炮弹来打刘少奇的所谓“卖国主义”影片,是强加的罪名,况且这是一部香港影片,又是历史题材,不能说是“毒草”。因此,我们复审研究认为,应对影片《清宫秘史》及其被牵连的人进行平反,并组织有说服力的影评文章从思想、艺术方面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消除戚本禹批判文章的流毒。但这部影片的复审报告呈报上去以后,一直没有回复。我一直关心这部影片,便在1980年,先后给《电影通讯》写了《〈清宫秘史〉不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文章,《解放军报》又约我写了篇《还〈清宫秘史〉的本来面目》的文章,为该片翻案,也引起一些文科大学的呼应,在学刊上讨论这部影片。但终无结果。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由于这部影片是毛主席多次点名批判的,戚本禹那篇文章也是经毛主席审阅修改过的,而且刘少奇是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的,这个案是不能翻的。听说,该片导演朱石麟1967年1月5日,从香港《文汇报》上获悉内地批判《清宫秘史》消息的当天,就发生心肌梗死而去世。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彻底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后,在1979年底,《清宫秘史》才得以平反,可惜朱石麟未看到这一天。
在复审影片中,过去被打为“毒草”的许多影片的解放,都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如说《怒潮》是为彭德怀翻案的“毒草”影片,说影片《燎原》是为刘少奇歌功颂德,说《红河激浪》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影片,还牵涉到习仲勋。影片《大浪淘沙》剧情与陶铸历史无关,因陶铸支持肯定过此片,就被诬为是为陶铸树碑立传。这些影片复审上报后,都被搁置未予批复。一直到1978年以后,彭德怀、陶铸等得到平反,以上影片才得以解放。还有如《革命家庭》、《聂耳》、《烈火中永生》、《兵临城下》等关涉到大的历史背景的影片,报批过程都不顺利,把关的领导极为谨慎。
在偶然的机会,看到在文化部呈送国务院的复审影片报告上,领导人的批示文字。一份是吴德批:“拟同意。请秋里副总理批示”。另一份报告上吴德批:“拟同意,请先念、东兴副主席、耿飚同志批示”。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影片复审报告,不仅由国务院副总理批复,而且还经政治局一些常委审定批复,更感到了这项工作的责任及严肃性,也理解了文化部领导人把关很严的原因。
在相当一段时间,只感到工作上困难重重,总不明原因。后来才知道当时是处在“两个凡是”的时期,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强调“照过去方针办”。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才使我们明白了许多问题,知道我们报批的每一部影片都必须符合“两个凡是”的精神。即凡毛主席批评过的影片,不能动;凡毛主席亲手打倒的人,涉及某部影片背景,这部影片就不能解放。或者江青一伙把一批影片毫无道理地打为毒草,而这批影片写在某一文件中,毛主席看过,或圈阅过该文件,这批影片就不能解放。由此明白了以上列举的《清宫秘史》、《燎原》、《怒潮》等影片报上去迟迟不批复下来的原因。也明白了戏曲电影一直暂缓复审的原因,因为毛主席批评过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而戏曲电影正是这些内容,因此只能搁置一边不碰为好。中国电影史三四十年代有那么多优秀影片,为什么不复审公映呢?因为毛主席亲自审改过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那个文艺座谈会纪要上明确指出,30年代以来是一条又粗又长的文艺黑线。因此,三四十年代的左翼电影亦属“黑线”范畴,复审这批电影则要极其慎重,虽看过一些影片,觉得不错,却不敢上报,一直审视形势的发展变化。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工作,彻底推倒了“两个凡是”,我们的复审工作才得到大步进展。在1978年后期,集中复审通过了一大批戏曲电影,接着又集中复审以前感到比较复杂的被打为“毒草”的电影,皆顺利得到批复通过,使1978年年底一次报批了52部影片(其中一部分是申报淘汰的影片)。
进入1979年,中共中央及中宣部、文化部相继批文对“四人帮”制造的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对部队座谈“纪要”制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被错误批判的人员及文艺作品,统统予以平反。在我们影片复审方面,顺利复审通过了一批优秀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如《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桃李劫》、《风云儿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丽人行》、《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并及时地在1979年“五四”运动纪念日的电影周及上海解放30周年集中公映,更显示了电影银幕的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这是几十年来少有的盛况。
在复审电影工作将要结束的1979年7月份,复审报批了43部录音录像传统剧目折子戏影片。这原是供在病中的毛泽东观看而组织力量秘密摄制的,声腔采用老京剧艺术家的唱腔录音,而表演是当时最好的演员录形象。先以录音录像拍摄,再转换成彩色胶片电影。拍摄得相当精致好看,对保留优秀传统剧目及老艺术家唱腔是很有意义的,又为戏曲电影艺苑增添了新的花朵。这些经典性折子剧目有《借东风》、《空城计》、《武松打店》、《八仙过海》、《红娘》、《火凤凰》等。最后还复审通过了2部著名粤剧戏曲片《关汉卿》、《搜书院》恢复公映。
以上所述,就是在两年半时间里,复审新中国十七年电影所经之历程。深刻感受到处在“两个凡是”时期,复审工作的困惑与艰难。
三
在复审十七年电影的过程中,接触到每一部影片的历史背景,也因影片了解到每部影片的创作人员如编剧、导演、演员的不同命运。往往因影片被以各种名义打为“毒草”,该片主要创作人员就遭到批判和迫害。电影人的命运与电影密切相关,给我强烈刺激的是,中国多少电影人为十七年电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反右特别是在“文革”中,成批的电影被打为“毒草”,就有成批的电影人遭难。粗略统计,如北影厂,以各种罪名被迫害致死的有7人。在上影厂,非正常死亡的达16人。还有长影及其他厂都有电影人含冤去世。最有名的如上官云珠受不了批斗,愤而跳楼殒命。石挥忍受不了被打为右派的批判,跑到宁波跳海自杀。郑君里遭迫害惨死狱中。遭瞿白音“创新独白”牵连的徐韬受不了批判的压力,跳钱塘江自杀。海默受诬陷,在酷刑下含冤惨死。王震之不堪“右派”之辱,迎着飞驶的火车了断生命。《阿诗玛》电影文学顾问李广田遭残酷批斗后,被勒死在污水池中。还有导演王冰、演员冯喆忍受不了迫害,愤而自尽。影片《天仙配》的主演、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含冤反抗,服毒身亡。电影《清宫秘史》导演朱石麟因获悉该片遭批判的消息,受惊而发心肌梗死亡命……不胜枚举。真是“血风腥雨”!这种现象在世界百年电影史上也是少见的。
在复审影片中,有另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十七年数百部电影被打为“毒草”,都与江青有关;毛主席有关文艺界生死存亡的几个批示,也都与江青有直接关系。从《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判,到1964年12月在中宣部会议上一次点名批判10部影片,到1965年“部队文艺座谈会”时,江青一次把60部影片打为毒草。毛主席1963年及1964年两个文艺批示,都与江青搞了名堂有关。江青一直把文艺界看成一塌糊涂,她给毛主席讲了什么话,不得而知。因为这两个批示都是在林默涵经手交给江青的两个文件,江青又交给毛主席后批示的。
十七年电影的复审历程,令人深深感到新中国的电影艺术成绩是辉煌巨大的,是江青、康生一伙的诬蔑所不能埋没的。
十七年电影的复审工作是意义重大的,不仅解放了整个一个时代的电影,而且相应地为大批的电影人平反昭雪。复审影片起始于刚刚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11月,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界拨乱反正的先导,这件事在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