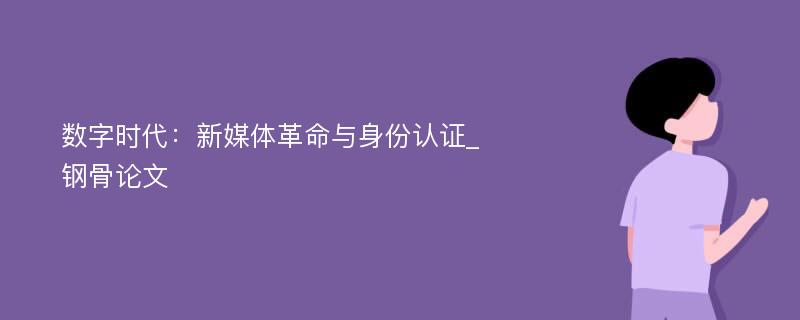
数码时代:新媒体革命与身份认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份认证论文,媒体论文,时代论文,数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09)01-0025-05
20世纪以来,人文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急剧的社会变革、媒体变革和精神变革导致了广泛的身份危机,促使以线性为特征的传统身份向以非线性为特征的新身份转变。传统身份是以清晰化、实在化、固定化为目标的。身份清晰意味着社会交往有明确的情境,身份实在化意味着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有可靠的责任人,身份固定化意味着当事人在社会体系中有基本不变的位置。上述目标不仅为线性媒体所宣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线性媒体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媒体变革与身份危机存在着广泛联系。在以非线性为特征的新媒体方兴未艾之际,阿斯科特1996年提出了“非线性身份”(non-linear identity)的观念,并做了这样的界定:“我连接,因此我多重。”(I connect,therefore I am multiple)[1]非线性身份以模糊化、空洞化、流动化为特征。另一方面,上述变革也带来了身份重组的新契机,其表现之一就是社会分工的藩篱被打破,原先相对固定的各种身份彼此渗透。处在这样的时代,人们迫切需要寻找自身在生态系统中的合理定位,这种需求促成了身份认证的发展。身份认证(authentication)起源于多重需要。在个体心理发展过程中,身份认证是当事人建立自我同一性、避免精神分裂的基本条件;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身份认证是特定人类共同体建立稳定秩序、抵御外来干扰的重要保证;在艺术发展过程中,身份认证是艺术世界建立内在联系的根本要求。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从“交往”、“标识”和“我思”的角度对身份的社会认证、文本认证和心理认证加以考察。
一、交往:身份的社会认证
身份的认证并不是当事人孤立思考所能完成的。它所要解决的不仅是当事人确认自己的心理存在的问题,而且是将个体与群体、社会联系起来的问题。身体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实体,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物质承担者;身份是人在社会上所占有的位置,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模式被称为“角色”,构成具体人的社会存在的各种角色的总和被称为“角色丛”。“角色”与“身份”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互换的,其主要区别在于:角色是与所占有的一定社会位置相适应的行为模式,身份则是这种行为模式和行为主体之关系的体现。身体、身份与角色三者应当保持一致性。人的身体是通过生育而造就、通过抚养而发育、通过教导和实践而社会化的。当它还在母腹中之际,社会已经为它预设了对应的角色体系——这个身体出生之后应当是这一体系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物质承担者。新生儿来到世间之后,身份问题事实上就已经产生。在很多情况下有必要证明特定身体与对应的角色体系的一致性——这个小生命是否与其父母有血缘上的联系。人类的社会制度就是在身体与角色相匹配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所谓“身份的社会认证”的作用就是确保这种匹配。身份的社会认证还有另一种作用,就是确保人格和自我的统一。人格是人所具备的各种特质的总和,自我则是有关人格的意识,它们分别是就“实为何如人”、“自视何如人”而言的。人格的发展、自我的形成都是经过社会化而实现的。正是社会化使当事人意识到“当为何如人”、“愿为何如人”、“能为何如人”、“他人视己为何如人”、“愿人视己为何如人”等问题的存在,并给出不同的答案。在正常情况下,人格和自我都是统一的、连贯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相信有可能和其他人保持稳固的、长久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一切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至于认证的具体方法,有基于体貌、方言、经历、指纹、虹膜等的考察,有提供独一无二的物体(如银行卡)、机密信息(如口令)、确认电子地址的所有权等。
新媒体革命对身份的社会认证构成了巨大挑战。它既破坏了身体、身份与角色的一致性,又破坏了人格和自我的统一性。波斯特认为:“历史可能按符号交换情形中的结构变化被区分为不同时期……在第一阶段,即口头传播阶段,自我(the self)由于被包嵌在面对面关系的总体性之中,因而被构成为语音交流中的一个位置。在第二阶段,即印刷传播阶段,自我被构建为一个行为者(agent),处于理性/想象的自律性的中心。在第三阶段,即电子传播阶段,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2]这一意义上的多重身份和心理治疗中的多重人格紊乱不乏相似之处。笛卡儿(René Descartes)的“我”通过反思自身、描绘自身而获得作为主体的意义(“我思故我在”),并保持自身的本质而不随时而变。相比之下,多重人格紊乱患者在催眠状态下显示出没有自我的“我思”(cogito),其意识被永是当前的暂时所占据,将自身和世界都加以括号。从“我思故我在”到“我变故我在”,多重人格紊乱患者在扮演多种人格身份时,堵塞了通往任何永久自我形成之路。这种“自我缺失”只能在极端“自我膨胀”中表现自身。[3]这样的患者似乎很合后现代主义的品味,因为他们瓦解了源于笛卡儿的cogito的现代主体,为多重身份和流动主体性铺平了道路。不过,很难想象可以将多重人格紊乱患者当成社会的人格楷模,也很难将主体在被催眠之后出现的“前描述状态”当成社会的正常心理,尽管这种状态没有主体、没有意识、身份可以无限多重化。斯托拉布拉斯指出:多重身份的概念与任何关于一个社区主要“基于诚实通信”的假定是根本对立的。[4]台湾大学外文系李家沂(Erik Chia-yi Lee)的《思考赛伯主体性:意识形态与主体》也认为:游戏那种以不同面具呈现的特性不可避免地会妨碍电子空间任何有效的社会化,以及虚拟社区的适当运作。人们一旦被允许在公共通信中不诚实,如何才能达到为(电子)集会所需要的理性背景呢?在政治上授权虚构社区、赞美多重身份与流动主体性的话语,必须面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难题。要不然的话,总有将种种关于身份和主体性游戏总加起来以背弃传统规范(与解放和允诺等值)的危险。如果这样的话,所有这一切修辞不过是与社会化没有可行联系的侈谈而已。[5]我们固然必须正视多重身份实体在互联网这样的非中心化网络的存在,同时也必须正视虚拟世界有序化的下述要求:实体所持有的这些身份彼此之间具备某种有机联系;它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可靠地整合进更大的关系单位。
二、标识:身份的文本认证
自从媒体革命发生以后,身份与文本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仅仅是通过文本才知道其他人的存在,知道他们的身份和身世。文本不仅是他人存在的证明,也是我们存在的证明。如果我们的姓名被从各种身份文件中抹去,那么,即使我们的身体依然存在,社会照样可能不承认有我们这样的人。如果官方档案中有关我们的记载出现错误甚至张冠李戴,由此造成的麻烦是可想而知的。文本认证对于作者来说意义格外重大,因为作者将作品当成自己的生活目的。通常所说的“艺术家”,可能是指某种实体、某种角色或某种身份。作为实体的艺术家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作为角色的艺术家是与社会分工所决定的特殊位置相适应的行为模式(从事创作,向社会提供艺术产品,并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作为身份的艺术家是具体的艺术作品的生产者或责任人。三者在多数情况下是统一的,但也有发生错乱的时候,特定艺术家的作品被错误地系于其他艺术家的名下,某个冒牌人物不正当享有创作者所具备的权益,就是如此。
数码技术促进了数码身份(digital identity)的形成。所谓“数码身份”,是以身份危机和身份重组为背景,在数码媒体支持下发展起来的,通常用数字信息表现,主要对作为一个数字主体的自我呈现起作用。数码主体是呈现或存在于数码领域、被描述或被涉及的实体,可以是人或非人(如计算机或智能程序)。每个数码主体都有一定但数目不限的身份属性。身份的文本认证因此面临着新课题,像网络文本的作者辨别就是如此。创作是由人机协作完成的,究竟是谁对作品拥有作者身份?智能程序已经能够自动回答问题,那么,怎么知道与您聊天的是人还是机器?网络允许匿名登录,究竟是谁将文本发布上网?连线世界活跃着数以亿计的用户,到底是哪位下载了它们?从技术上说,网络采用“通行证”制度保证各子系统既能独立发展、又能共享用户。它将用户认证和用户权限剥离,由通行证服务器负责认证用户的身份,由网站各个功能模块负责用户授权。从组织上说,虚拟社区由多个分权的版主进行管理。数码技术为身份的文本认证提供了新手段。例如,借助于用词习惯统计技术,可以从现有文本的比较中推断出作者身份;运用目录服务技术,可以将网络建立成一个可管理、易调控、有秩序的世界;运用含有用户机器中网卡的硬件地址的文档标识码,可以追踪文档的最初作者;验证计算机处理器系列号,可以为发现用户身份提供参考信息。正如保罗所说:躯体与身份已经在数码领域变成突出的主题,中心是我们如何在虚拟的和联网的物理空间中定义自身。当我们的躯体仍是个人的、物理的“对象”时,它们已经日益变成超越的:准确的监视与辨认看来威胁到个人自治的主张。无处不在的监视摄像头追踪我们的运动;生物测量技术,如电子指纹、面部识别软件与虹膜扫描作为身份辨认手段投入市场。[6]164如同现实生活一样,虚拟世界中同样进行着身份铸造、身份消解、身份伪装、身份识别、身份追踪等活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抑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我思:身份的心理认证
身份以身体为前提而形成。如果说身体是生命的物质承担者的话,那么,它是生物界所特有的。如果说身份是身体的社会定位的话,那么,它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人们通常不认为无机物有身体(除非是在譬喻的意义上),也不认为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有身份(除非是在拟人的意义上,或者是将宠物与其主人联系起来考察等情况)。汉语的“身份”和英语的identity都是多义词,彼此不完全对应。尽管如此,它们的语义域在下述部分是重合的,即说明当事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这种地位既是当事人自行归属的产物,又是他人认定的结果。
汉语中的“身份”有两重意义:一是人的模样或体态,二是在社会上的地位或资历。二者之间可能具备某种逻辑联系:人的身体是由一定的部分构成的,这些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决定人的模样或体态的重要因素。头在上、足在下,腹居中、肢在侧,诸如此类的关系具备恒常性。至于五官是否匀称、身体比例是否恰当,这类因素则可能因人而异。当人们将社会想象成为有机体时,有关人的身体的组成要素的理念就成为社会的譬喻,如领导者好比“头脑”、臣下宛如“左右臂”、参与谋事者像是“心腹”等。在这一意义上,身体通过隐喻朝身份转化,身份又通过当事人的自觉性评估而转化为身份观。就此而言,传统意义上的身份、身份意识都是以躯体为基础而产生的,其前提是当事人的身体与心灵的一一对应关系。
莫尔指出:“身份现象在其历史上解释是五花八门的。该词的语源学根源可以追溯到拉丁文identitas的概念,identitas又源自idem——意为‘同一’。在逻辑学中,该概念被用来表示一种数字的统一。而用于人类之时,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的概念指的是每一个人与他/她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关系。身份的这种逻辑上的原则意味着一个人与他/她自己而不是与其他人认同。在个人身份问题上,人们常常在物体身份与精神身份之间作出区分,因为一个人同时具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体一种独一无二的心灵。”[7]162英语中的identity一词至今还有“恒等式”的意义,这既表明了它与数学的联系,又暗示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意义上的身份与同一性、认同的相通之处。如果我们将某个人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身体当成客我,将这个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心灵当成主我的话,那么,身份也好,认同、同一性也好,指的都是主我与客我之间的关系,即主我与客我相统一的过程。当儿童在心理发展的镜像阶段辨认出自己独特的体貌时,这种统一就有了内在的基础。当然,这种统一是在社会化的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他人的引导或反馈相当重要。正是由于这种引导和反馈使得当事人强化了自我认知,并产生了相应的自我情感。
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和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一样是名言。它的基本含义是:如果一个人正在思考他存在与否的问题,那么,这种思考就是他存在的证明。莫尔指出:从现代性的开端起,身份的概念就经历了转变。“笛卡儿在其1641年出版的《形而上学沉思》中,把‘我’或‘自我’界说为一种思考着的物体——具有(自我)意识的物体。”这种关于人类的理性观有四个重要的特征:首先,笛卡儿的概念意味着人类身份与某种意识,即理性心灵有着特殊的联系;其次,除却人类身份与意识的联系,则意味着人类被设想为一种孤立的主体,囿于自我,站在世界和他人的对立面;第三,笛卡儿把个人身份视为一种永恒的本质(a timeless substance);第四,引人注目的是,笛卡尔在其界说中把人类身份设想成为一种物体(thing)。[7]164-165莫尔同时指出:笛卡儿的上述观点惹来了激烈的批评。对立的理论认为:其一,没有肉体的思考和意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其二,人类主体性本质上不是孤立的,与其他人的联系是我们身体境遇的重要方面。其三,不能忽视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的时间维度和历史维度。其四,主体并不是时间上不变的实体。正如后现代主体观所认为的那样,主体一旦被消解,身份便只是一种幻象。我们可以将莫尔所指出的这四种对立归结为身份之争的基本问题:主我(意识)的活动是否需要客我(身体)的支持,个人身份能否在他人完全缺席的条件下形成,身份是长久不变或因时而迁的,身份的性质是物体还是幻象。
新媒体革命不仅为身体创造了模糊化、空洞化、流动化的新身份,而且为身份创造了多元化的新身体,其中之一就是电子人。艺术作品中的电子人拥有外骨骼、植入性芯片、超强四肢等异乎寻常的器官,可以担当生物人所无法完成的任务。生活实践中的电子人还没有这么高级,但却同样是某种程度上的人机共同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电子人在艺术作品和生活实践中的出现,都是身份危机的表现。这种危机包括性别身份危机、国民身份危机、职业身份危机等。艺术作品中的电子人为生活实践中的电子人导乎先路,生活实践中的电子人则印证了艺术作品的电子人。
电子人理论试图超越现代、后现代身份观所包含的二元对立。首先,它认为肉体与理性心灵不存在本质区别,因为二者说到底都是某种编码系统,只不过肉体所依赖的是DNA编码,理性心灵所依赖的是神经脉冲编码。思考和意识固然不能离开一定的实体,但这种实体并不一定是肉体。这一点最终要由实践来证明。如果计算机也能思考甚至有了意识,那么,理性心灵就有了新的物质基础。其次,它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区分仅仅是相对的,因为人的主体性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出肉体所在的空间,成为彼此融合的场(不管是气功师所说的气场,还是物理学家所说的电磁场)。利用专门仪器接受人的脑电波,已经被证明是可能的。这种电波会随着人的思考而起变化,包含了有意义的信息。只不过它的强度很低,因此无法使人们真正实现心灵融合。如果人体联了网,那么,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单单就这一点而言,电子人也将具备不同于生物人的身份。再者,关于个人身份的永恒性和暂时性的争论,仅仅对于生物人有意义,因为生物人的身份与身体是一对一关系。电子人的身体呈现分布式存在,其身份可能是网络状的集合体,可以通过转录来延续。某个身份的消失并不代表整个身份的结束。这样,电子人的身份从整体上说是永恒的,从局部上说是暂时的。最后,关于身份究竟是物体还是幻象的争论,也只是对于生物人有意义,因为生物人的身份既可能为一定的物质条件(如府第、制服、佩饰、收入等)所昭示,又可能仅仅是一种以认同为特征的心理过程。真正意义上的电子人体现波粒二重性,本身并无所谓物体或幻象之分。正如保罗所指出,虚拟存在与物理存在的关系很难被作为简单的二元来建构。与此相反,它是影响我们对躯体与(虚拟)身份之理解的复杂相互作用。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在什么程度上体验到将我们转变为电子人(技术的增强与扩展的躯体)的人机共生?[6]164这种体验目前还是初步的,因此,电子人身份观有待于深化与验证。
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名言在互联网时代仍具备广泛的影响。以创始IRC戏剧著称的美国导演哈里斯(Stuart Harris)就曾将它写入自己的电子地址——sirrah @cg57.esnet.com(ico_ergo_sum)。人们面临着这样的新问题:如何在网络上证明自己的存在?网民的典型行为不是思考,也不是“潜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笛卡儿名言的各种变体。英语“I think,therefore I am”中的关键词think被网友替换成Chat、Blog等。汉语网页中比较典型的有“我贴故我在”、“我Q故我在”、“我灌故我在”、“我博(客)故我在”、“我聊故我在”之类命题,和比较一般的“我拼故我在”、“我秀故我在”、“我歌故我在”、“我爱故我在”等并存。显然,网民倾向于在线活动取代“思”字。此外,网民还经常以带有另类色彩的形容词取代“思”字,由此而产生“我邪故我在”、“我坏故我在”、“我笨故我在”、“我呆故我在”、“我色故我在”、“我憨故我在”、“我狂故我在”之类提法,和比较正面的“我帅故我在”、“我酷故我在”、“我牛故我在”并存。这种做法的动机也不难理解:“我在”之“在”,不是一般的存在,而是有特色的存在。网民不仅追求获得一般意义上的身份,而且希望获得与众不同的身份。
身份的社会认证、文本认证和心理认证是综合起作用的,归根结底是为人们寻找在人文生态系统中的定位。是新技术条件下身份危机、身份重组的需要推动了身份认证的发展,是身份认证为解决身份危机、推动身份重组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收稿日期:2008-08-26
标签:钢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