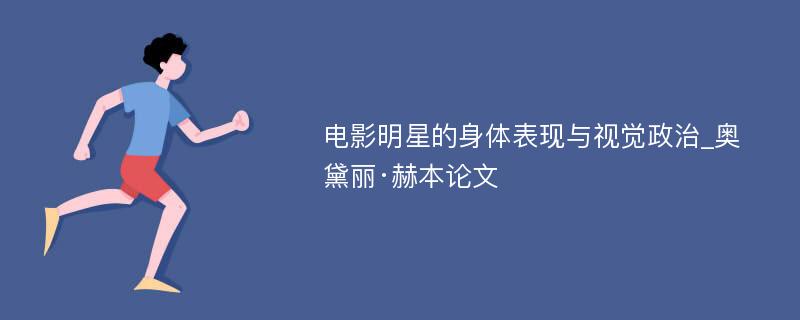
电影明星的身体呈现与视觉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觉论文,身体论文,政治论文,明星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3)03-0027-11
对于电影明星的研究,往往联系着不同的维度,诸如生产、消费、产业、批评等等,而其初始角度,则无不与“身体”联系在一起。电影明星于银幕内外的身体呈现,构成了明星研究的基础维度,并且同时勾连着电影史与电影观念的变迁以及大众趣味的变化,而其与各种权力机制之间的博弈,形构了各种意味深长的社会文化话题。
一、身体:建构明星形象的基础
“不管采取哪种方法,对明星的理论探讨总是围绕着主动性/被动性这对辩证统一体进行的。”一般而言,演员自身并不能决定自己是否能够成为明星,明星与演技也并非呈现为统一的正向关系,反而时常显现为分裂状态。明星是被一种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媒介、产业、受众等各种因素的合力共同制造的。但另一方面,明星又可以借助自身的知名度与商业/文化价值,以自己为中心量身定做来制作影片,或者运用自己的经济权力对影片制作采取主动投资与拍摄的方式,从而体现出主动性姿态。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明星研究通常将明星放置于社会文化场域之中,探讨明星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产物,社会文化如何运用话语和策略来建构出明星的复杂形象。这种将明星作为意识形态产物的探讨,可以追溯到L.罗斯滕的《好莱坞:电影殖民,电影创造者》(1941年)、H.保德梅克的《好莱坞梦工厂》(1950年)。埃德加·莫兰的《电影明星》(1957年)继续延续着相关的明星研究话语,认为“只要他/她反映了被现代社会、现代意识接受的新形式,他/她就是明星”。[1]252-253理查德·戴尔的《明星》一书致力于创立一种明星研究的方法,即认为明星是“被建构的个体”:“这一作为他论述核心的真知灼见——明星在人们的感知中一直只是被媒介化了的现象——导致他提出了‘明星形象’新概念,这一新概念可以供作理解明星形象是由媒体文本——它们可以由营销、宣传、影片、影评和评论等一起组成——建构的复合代表之方法。”[2]2戴尔在讨论葛丽泰·嘉宝的明星形象时,分析其在鲁宾·马莫利安导演的《瑞典女王》(1933年)中的最后一个著名镜头时指出:“嘉宝在这个镜头中的脸部表情之含义,完全来自于该镜头在影片叙事中的位置,取决于该镜头的拍摄方式,她的脸部含有嘉宝形象的投射物。”[2]226在此,嘉宝的明星形象的人格,正是通过瑞典女王这一角色的建构才得以“瞥见”的,“由好莱坞或明星偶尔显示的人格本身是已知的建构,只有通过影片、故事、宣传等才能表达出来”。[2]32
有关明星如何被建构的研究,使得明星认知走出简单浅薄的八卦轶事与花边新闻,进而成为对社会文化、流行时尚乃至权力机制有揭示意义的重要文本。相比之下,对于明星自身的深入讨论却并不多。原因之一是,在通常情况下,由于电影明星在形象建构时主动性的相对缺失,其银幕内外的形象塑造往往在多方面受制于他者,诸如电影表演往往听从于导演的指导与剧本的要求,而文化表演则受制于影片的宣传发行公司以及演员所处的经纪公司等对其形象的规划。①这种要求和规划,与明星本人的形象、气质、特征之间,并非总是呈现为良性的相互塑造与建构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电影演员在建构其明星形象时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凯瑟琳·赫本在建立自己的明星形象时就体现了她的自主性,“不管演哪部电影,赫本都忠实于自己的本性(正直、聪明、独立)。有很多为她量身定做的、顺应社会偏见的脚本,她都拒绝了,因为在她看来,这是对她人格的侮辱”。[1]251凯瑟琳·赫本在选择剧本、购买版权、电影制作等方面确保了主动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她的明星形象独立、聪慧的内在一致性。而其内在前提是,明星在通过电影表演与文化表演建构自身的形象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知名度及权力,并且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前提,他们对于自身有着非常明确而准确的认知与定位,并且能够与当时的大众需求之间形成对话关系。
外在力量与演员自身对身体形象如何建构的博弈,常常聚焦于身体。可以说,明星形象建构是演员本人与制片公司、经纪公司以及各种媒介等外在力量相互争斗和妥协下合力的结果,而明星身体往往成为争执的重要场域。身体作为建构明星的关键,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媒介、产业、受众等宏观因素制造与操控明星形象的重要物质基础,并且由于它与演员之间的亲密性,同样可以轻易地被演员自身使用。演员与其身体之间,形成了一种颇有意味的关系:它们是合一的;但演员又可以运用自己的身体来塑造形象。玛丽莲·梦露生前最后的照片“The Last Sitting”系列摄影体现了各个力量之间的角力。在梦露最后这一系列影像中,她妖娆性感的赤裸身体是被动的,被符号化了的,而照片中鲜明的红色的“X”则暗示梦露对其形象的不满。这一系列照片有一半以上被梦露涂改,该系列照片的摄影师伯特·斯特恩认为,这就像是梦露将自身而不是将照片抹去。[3]作为演员,梦露一直努力使自己不仅仅是性感尤物被世人肯定。至今,这些照片上仍保留着梦露亲手划上的鲜红的笔迹,对色欲身体的展现的否定,破坏了梦露明星形象的统一性;抑或说,展现及对展现的否定,这两者共同构建了梦露最后的明星形象。
如果说梦露通过身体策略使得其明星形象产生了某种分裂性,那么也同样有明星通过该策略完成了银幕内外明星形象的合一,并因此使其明星形象获得了更为深刻的说服力。影片文本中的奥黛丽·赫本常常通过改变其身体造型来建构其形象的主体性。在《罗马假日》(威廉·惠勒导演,1953年)中,奥黛丽·赫本的标志性短发,是人物身份从公主到女孩的转变。《龙凤配》(比利·怀尔德导演,1954年)中的萨宾娜写信给父亲说“如果你认不出你的女儿”,那是因为“我将是格里科夫车站最成熟出众的女子”。镜头展现身穿纪梵希设计的服装出现在车站的萨宾娜,这是一种“并非偷窥的赫本的服装细节展露”,并非色情的,而是“带给观众的一场时尚游行,但这并未让人联想到赫本的身体”。在这场火车站的表演秀中,镜头记录下奥黛丽·赫本的目光,肯定了萨宾娜信中所描述成熟、自信的形象,“她目光的流转足以表现出她的自我意识”。[4]46-48奥黛丽·赫本的自主性并不仅仅存在于影片内部,也表现在影片文本之外。纪梵希“不仅在银幕上为她设计衣物,在生活中也是”。[4]29她曾经给纪梵希写过一首诗,其中提到“这些服装让我感觉如此自信”。[4]61也因此,“戴尔用‘完美的契合’来形容赫本在整个电影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形象”。[4]32在奥黛丽·赫本的银幕形象与纪梵希设计的服装之间,服装不仅仅像一般影片那样用来标明人物身份和塑造人物性格,而是呈现为更加复杂的时尚与文化的建构关系。通过银幕外身体策略,奥黛丽·赫本建构了具有主体性的独立的女性形象,这和银幕内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物之间高度契合。从而,奥黛丽·赫本的明星形象与她本人之间产生了高度的透明性以及渗透性,“赫本的透明度,接近于自我,在这个圈中非常独特;与其制造一种与观众的距离,不如为观众提供这样的机会,帮助她们重构女性气质”。[4]52
明星如何主动建构起他们的形象这一问题具有复杂性和个体性,通过以上寥寥数例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建构是隐蔽的、暧昧的、多元的,而不是匮乏的。身体是明星形象产生的物质基础,也是明星主动建构其明星形象的关键所在。明星的“姓名、服装、社会地位可能有变动,但是他们永远扮演同一的人物,而这个人物就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给人最突出的印象还是他们自己的形象”。[5]303相比明星如何被多种方式所建构的研究,明星自身如何运用其身体策略主动建构起他们的明星形象,以及明星身体如何与社会文化、大众趣味等相互共鸣的研究相对还比较缺乏。在明星研究中,明星的身体问题首当其冲,正如巴拉兹·贝拉所指出的:“这些大明星都是些伟大的抒情诗人,他们不是用词句而是用形体、面部表演和手势来吟诵;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他们在运用他们的艺术时顺手拈来的工具。”[5]303
二、脸:电影明星的微观政治
人类的情绪体验与身体密切相关。手势、姿态、动作等如同情绪的传感器,比如紧张、愤怒伴随着瞳孔的放大,喜悦、激动和血压升高有关。人的脸则是情绪表达的最主要的物质载体。同时,大脑存在着一些特别的区域,如梭状脸区(fusiform face area,FFA)专门用来识别人类脸部的讯息。②中国古代的面相学,就是一种通过分析人脸的面部特征来解释人的命运的学问。③西方曾经风靡一时,后来被证实为伪科学的“颅相学”通过人体的头颅形状来分析人的心理与特质。作为一种心理学假说,尽管颅相学并不具备科学性,但是颅相学中的科学思想,对应用心理学研究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④
人类的面部表情对于表达人的心理和意识是如此重要,“面部表情最足以表达人的主观意识活动,它比言语还要主观,因为词汇和文法多多少少还要受通用的定则和习惯的限制,而面部表情,如上所述,即使它主要是一种模仿,却丝毫也不受种种客观规则的制约”。[5]50特写镜头的发明,使得明星的脸成为演员身上最重要的表意部件与元素。“能够接近人的那张脸才是电影艺术首要的特殊性和独创性。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演员是我们最珍贵的表演工具,镜头除了记录下这个工具的各种反应之外,没有其他用处。”[1]131我们可以看到,“在好莱坞,最频繁出现的镜头(或者说‘半身’镜头)既捕捉到身体的姿势,又抓到面部表情传达的信息;人们永远不会为了某个物件而让镜头上人类的脸模糊;电影拍摄十分钟爱正面镜头,这样就可以尽情表现演员的面部,哪怕在某些背景里这种拍摄风格看似有些矫揉造作;最佳取景将呈T字形,与屏幕水平上端垂直的人体‘成为叙事和图解的中心’。”[1]247
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人们心灵的展现集中在文字上,思维也更偏于抽象与符号,导致人类逐渐遗忘了身体这一直接可见的信号载体,“在文字逐渐发达的年代里,心灵虽然学会了说话,但却变得几乎难以捉摸了”。[6]33然而,摄影机的发明却重新激活了人的感性,以视听语言为主要表征的读图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的关注焦点重新回到感性、具象的形象本身;另外,电影的出现还消弭了戏剧媒介中剧场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特写镜头使观众在银幕上看到放大的身体姿态和面部表情的细部,“人又重新变得可见了”。[5]33卡尔·西奥多·德莱叶的《圣女贞德蒙难记》(1928年)打破了常规电影戏剧性的拍摄方法,用特写镜头支撑起这部影片,它与巴拉兹所说的“我们能在电影的孤立的特写里,通过面部肌肉的细微活动看到即使是目光最敏锐的谈话对方也难以洞察的心灵最深处的东西”[5]54这一观点相互形成注解。审判、杀戮、交战,影片的冲突不存在于任何外部空间之中,而是用演员的面部表情的大特写让观众领略思想和信念的撞击。“他们眉宇之间的交战(眼光的交战而不是刀剑的格斗)却能紧紧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达九十分钟之久。我们可以从交战者脸上看到这场决斗中的每一次进攻和还击;他们面部表情的变化说明了每一个战略和每一次突发的猛攻。”[5]66巴拉兹·贝拉感叹这部影片“我们只是往来在面部表情的精神领域之中”。[5]66也无怪乎德莱叶赞叹:“世界上没有什么能与人类的面孔相媲美。”[1]128
特写镜头对电影演员的面部表现有极高的要求,是对演员演技的最大考验之一。路易·德吕克强调电影演员的脸需要有“上镜头性”,一部电影不论摄影、导演、剧作有何缺陷,“只要演员‘上镜头’,一切就得救了!”[6]60让·爱泼斯坦则认为:“一只在近景镜头中的眼睛,不再是一只普通的眼睛。”[6]86巴拉兹·贝拉描述过阿斯泰·尼尔孙一次精彩的面部表演,尼尔孙扮演一位少女,假戏真做爱上一个阔少,但又因害怕监视他的人看出她动了真情,只好再次戴上假面具。尽管她极力掩饰,镜头却将少女内心隐秘的激情和压抑纤毫毕现地展露出来。
电影史上还有一张被人反复研究的著名的面庞,那就是葛丽泰·嘉宝的脸,而探讨最多的则是《瑞典女王》的最后一个镜头。在影片结尾,当嘉宝为爱情放弃整个王国赶到爱人身边时,她的爱人却已经濒临死亡。影片用一个缓慢的推镜头刻画了这位女王,并停留在她“无表情”的面部。观众通过这张脸读出嘉宝的心情,“她的表情混合失落、孤独、坚定、忠诚、自尊、爱与勇气”。[7]嘉宝那看似毫不动容的脸上,却蕴含着无法用语言文字来传达的丰富内涵。罗兰·巴特则认为,嘉宝的脸“不是描画而成的脸,却是石膏范铸而成的脸,保护这一化妆的,是其表层的色彩,而非线条;这雪白所具的一切性状,是脆弱而又坚固的,只有眼睛,黑得像奇异的果肉,然而毫无表情,是两块微微颤动的伤斑”。[8]路易斯·贾内梯对嘉宝的脸也是赞誉有加:“她的脸显现惊人之美,能容纳矛盾的情感,又同时收放自如,仿佛有涟漪扫过她的五官。”[9]81确实,嘉宝魅力的来源是她的脸呈现出一种高贵的美,这种美有一种“非常明确地表现了她的内心状态的外形美”。[5]304影片中的面部表情是来自于嘉宝的,不论她表演的是女王还是妓女,“在这种种不同的面部表情的背后,永远可看到不变的嘉宝的脸,那个征服世界的固定不变的表情”。[5]304嘉宝脸上有“一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美”,带有“忧伤和孤独的痕迹”,“是一种向今天的世界表示反抗的美”,人们可以从她的脸上看到“对现世界的控诉”,并且赞颂这种控诉。[5]304-305嘉宝的脸不仅仅在于形式上的美丽,它的迷人之处恰恰在于它的非现实性,它的精神性,它的超越性。嘉宝得心应手地利用自己“几乎没有性别的特征”的脸同时扮演了骑士和女王,令人恍惚迷离。相比奥黛丽·赫本的脸,“嘉宝的独特之处在于观念范畴,赫本则在于实体范畴。嘉宝的脸是型相(理念),赫本的脸则是事件(引人瞩目之物)”。[9]82
对于不同的电影明星来说,特写镜头是一把双刃剑。许秦豪的《危险关系》(2012年)用了大量的特写镜头试图表现谢易梵(张东健饰)、莫婕妤(张柏芝饰)和杜芬玉(章子怡饰)之间的暧昧与欲望。然而影片中的特写所呈现的,并非徳吕克所说的让“一切就得救了”的脸。影片通过谢易梵在杜芬玉未完成的火车图画上添上几个从火车烟囱中飞出的烟雾这一细节来说明两人之间爱情的产生,并以影片结尾杜芬玉在黑板上画烟雾的重复动作来呼应式地肯定两人之间的情感。谢易梵角度微仰的特写镜头里,他凝视着自己的爱人杜芬玉嘴角上扬却眉弓紧锁,他并非露齿而笑,而是撇了撇嘴挑动着修剪整齐的胡须,以此来彰显其花花公子的角色身份。同时,杜芬玉闭眼而睡,这种单向度的窥视更加强化特写中谢易梵的面部表演所带来的某种情欲至上的追求享乐的观念。情节的本意是表现两人之间的美好情愫,然而,经特写镜头放大后,演员脸上却写满了生硬做作感和“虚情假意”。影片企图用充满隐秘欲望的脸部特写来展露危险激情,然而经过镜头放大之后的演员的脸却显得呆板无趣,便产生了南辕北辙的叙事效果。
三、裸露:与权力机制的博弈
电影明星在影片中所呈现的身体与布料之间摇曳的关系常常呼应着电影历史、电影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变迁。
在镍币剧场里放映的早期电影,就以歌舞、竞技等撩人视听的内容见长,它们嘲笑“维多利亚式的价值观”,并且其中不乏一些展现身体裸露的片段。20世纪20年代以后,好莱坞银幕里呈现出一种“新女性”,这种女性不再是传统道德下谦和的、温顺的、“邻家的处女”形象,而是对性的问题十分开放的“穿短裙,束胸,涂脂抹粉,跳扭屁股舞和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小野鸭”。[10]40艳星格劳丽娅·史璜孙与导演西席·地密尔合作的多部影片中都有相当程度的裸露镜头。其在《男人和女人》(1919年)一片中尽显身体的诱惑,“当玛丽夫人从床铺走向浴室时,摄影机寸步不离地追随于后,直到高傲的夫人脱得一丝不挂才算获得全胜”。[10]42-4320年代电影中的身体裸露程度可以参照女演员蓓蒂·布丽思所说:“我穿了28件戏服,但即便一起穿上,也保不了暖。”[10]43-44随着20年代末有声片的诞生,更是加剧了银幕上的情欲呈现。声音的出现,使得电影表演不仅仅局限于身体姿态的视觉展示,还可以“浪声浪气地对观众进行挑逗”。[10]60
电影对裸露身体的迷恋必然遭遇电影史上的重大事件——嗣后诞生的电影检查法的杯葛。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英国、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家纷纷出台电影检查法。在中国,“1927年国民党政权出现于历史舞台,对于中国电影检查制度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11]69在国民政府制定的《电影片检查暂行标准》中和身体有关的检查包括:“描写淫秽及不贞操情态者;描写引诱或强暴异性者;描写乱伦者;以不正当方式脱卸妇女衣裳者。”[11]61在美国,威廉·海斯的登场,直接促成了审查美国电影长达30多年的《海斯法典》。《海斯法典》规定,即使在描写纯洁爱情时,“表现方法和方式上决不可细致入微”;服装则“决不能因情节需要而裸露”;在肢体表现上,“暗示或表现性动作的独舞或双人或多人舞、意在挑动观众情欲的舞蹈、摇摆胸部的舞蹈、双腿不动而作过度的躯体动作的舞蹈都是不雅观的和邪恶的”。[10]71值得一提的是,《海斯法典》的诞生除了与银幕上的身体呈现有关,还与银幕外媒体营造的电影明星的身体表演有一定关联。1920年前的好莱坞,尽管在银幕上已经出现了许多荒淫的场面,但明星的私生活却不常见于黄色小报上的丑闻版,直到喜剧电影明星罗斯科·亚勃克尔强奸杀人案被曝光后,好莱坞才开始声名狼藉。电影明星银幕之外的文化表演在建构明星形象上的分量,从此开始与其在影片文本中的表演亦即电影表演自身平分秋色。罗斯科·亚勃克尔的这次文化表演是和身体有关的。亚勃克尔被起诉强奸“女演员”维吉妮亚·拉贝。尽管最后法庭做出了无罪判决,然而,公众舆论仍判定其有罪。对于这件涉嫌身体的明星丑闻,威廉·海斯“于1922年4月19日作出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永远禁映罗斯科·亚勃克尔的影片”。[10]44-48这一由明星身体引发的震惊全美的事件,引发好莱坞工业体制下一系列丑闻的纷纷暴露,这些银幕外与明星身体有关的丑闻和银幕上情欲的身体呈现一起构成了好莱坞道德沦陷的铁证。
电视的兴起,二战战后创伤引起的社会文化变迁,电检法的规则渐渐不再适用于电影发展的实际进程,各大片厂陷入财政问题,经典时期的电影遭遇危机。1966年,好莱坞用分级制取代了《海斯法典》,从而结束了与《海斯法典》的博弈。电影用一次暴露身体的大爆发宣告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逍遥骑士》(丹尼斯·霍珀导演,1969年)将性和摇滚乐、大麻联系在一起,影片描写了男女裸体共浴的场面,在银幕上展现女性的正面全裸。《邦妮和克莱德》(阿瑟·佩恩导演,1967年)的开场就是女性的嘴唇特写,并用一个从这一影像开始的长镜头向观众展现了一具裸露的女性身体。瑞典电影《我好奇之黄》(维尔戈特·斯耶曼导演,1967年)更加彻底地表现了男女的性爱场面。“舍曼没有害怕(其实他很乐意)把一对青年男女躺在草地上,女孩子用鼻子摩擦男子阴茎的画面展示给众人。”[12]电影演员的身体从“犹抱琵琶半遮面”到生殖器官的大特写,演员的裸体频频出现在镜头里,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视为一场革命,一场文化意义上的革命。阿瑟·佩恩认为,《邦妮和克莱德》是好莱坞电影的一道分水岭,从它开始,“那些墙纷纷倒坍。混凝土墙里面的所有东西也都开始消失”。[13]《逍遥骑士》中某些吸大麻的场景并非是虚拟的,杰克·尼科尔森就在一场篝火戏拍摄时猛吸大麻,大麻“是用来表示反抗的道具……它带来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巨大自由感”。[14]110《我好奇之黄》则将性场面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在街头革命还没有开始前,他们早已在床上开始这场革命”。[14]110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之后,西方世界对于裸露问题变得更加开放,碧姬·芭铎让比基尼这样的性感服装成为时尚的代表,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身体裸露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电影新浪潮运动,在如今的电影中也已经司空见惯了。在某些影片中,身体裸露甚至要开始面对一些新的问题与观念。女性主义导演凯瑟琳·布雷亚的《罗曼史》(1999年)结尾用写实主义的手法拍摄了女性生小孩的全部过程,在此,裸露不再与激发情欲相关,于观者而言,它更是震惊性和揭露性的。米歇尔·德维尔的《城市夏夜》(1990年)中两个主人公一直裸体,在此,裸体失去了它的奇观性,而变成了一件“外加的服装”。[1]213另外,身体界线也被“体液”一再突破。昆廷·塔伦蒂诺式的影片中血液横流的场面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沉默的羔羊》(乔纳森·戴米导演,1991年)等影片中有对男性体液的直接展示,“通过电影的方式来呈现体液对社会秩序具有更大的威胁性,因为它们的表现超越了身体的界限。它们超越了肉体、身躯和主体之间的界限,因为它们通过肉体的行为代表了主体性,同时把身躯和主体融合形成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的形象,那是一种不受羁绊和束缚的形象”。[15]
与欧美电影或者日韩电影相比,中国电影中的身体表演则呈现为另一番景象。1979年第5期《大众电影》杂志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的亲吻剧照,这张现在看起来显得十分“干净”的图片,在当年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同年的《不是为了爱情》(向霖导演)中由一个外国女孩和一位中国男孩的嘴唇触碰完成了新中国银幕史上的第一个爱之吻。此后,亲吻镜头以及各种亲密场景虽然频频出现于中国银幕上,裸露镜头却仍然受到严格禁止,除了“第六代”的少数独立电影,国产电影中的正面裸露镜头几乎难寻踪迹,可见的多为背裸或者经过朦胧处理。在《恋爱中的宝贝》(李少红导演,2004年)中,周迅全裸演出,有几处一闪而过的背面的裸露镜头,“影片是以正常程序通过审查,专家们一致认为影片不会给观众造成不健康的影响”。[16]虽然片中裸露镜头一刀未剪,但对于电影中裸露镜头的管理并没有从此放松。相比世界电影的景象,尚没有分级制的中国电影中的身体裸露问题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困扰着电影创作者以及电影受众。
四、衣饰:与大众趣味的共鸣
明星身体还与大众趣味息息相关,身体,以及作为身体修辞的明星衣饰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对社会文化产生蝴蝶效应般的影响。为了让希达·芭拉在电影《埃及艳后》(J.戈登·爱德华导演,1917年)中更好地展现埃及艳后的魅力,其化妆师借用法国戏剧演员舞台妆的创意,用色彩修饰眼部。希达·芭拉的上眼皮的妆容不仅引领了时尚,还促进了当时化妆品市场的繁荣。另一位埃及艳后的扮演者伊丽莎白·泰勒在1963年的《埃及艳后》(约瑟夫·L.曼凯维奇、鲁宾·马莫利安、达里尔·F.扎努克导演)中的眼部妆容,使得世界各地的“眼影、眼线笔以及假睫毛都开始大行其道”。[17]
身体修饰作为明星身体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与大众趣味之间产生共鸣。随着服装工业的发展,富人阶层与底层阶级之间服装样式的时间差距几乎消失,并且有很多现代服装是在工人阶级或者是边缘群体中最先流行开来的。要让一件服装、一种发型跨越阶级、群体的界限被大众所接受,明星往往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明星与大众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时尚的“仿效说”仍然十分有效。1946年,路易斯·雷阿尔设计的由3块布和4根带子组成的比基尼震惊世界,但在女性着装十分保守的时代里,许多国家禁止比基尼的出现。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碧姬·芭铎在电影中穿着比基尼,这一反传统的服装才得以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影片《上帝创造女人》(罗杰·瓦迪姆导演,1956年)里,碧姬·芭铎身穿比基尼的镜头使得这一服装真正开始在美国流行。到了50年代末,生产商开始批量生产比基尼。随后,乌苏拉·安德丝在第一部“007系列”电影中身穿白色比基尼从海滩走向肖恩·康纳利,比基尼开始被大众所赞叹。影片《海滩派对》(1963年)中,各色比基尼登场,引发了60年代海滩片的狂潮,也使比基尼成为流行时尚。[18]比基尼的流行是明星着装影响大众趣味的一个例证。很多时候,“受众并非主动抵制,而是被动地接受媒体发布的形象”。[4]8大众可以通过对明星的服装、发型等外在修饰的模仿来完成建立等级、划分群体以及表达自我等目的。
雷切尔·莫斯利通过对奥黛丽·赫本的明星形象为何在影迷心中经久不衰这一问题的探究,发现了影迷与赫本的身体修饰之间的共鸣关系。在奥黛丽·赫本主演的影片中,服装往往是作为人物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标志性符号出现的。“如果将她的脸遮起来,只留下她的衣服,她的姿势,无论什么,然后你会说这是‘奥黛丽·赫本’。”[4]118在《龙凤配》中,赫本从一个不起眼的家仆的女儿到一位成熟自信的现代女性的转变,是在摄影机对她的带有巴黎时尚元素的服装的细节展现下完成的。《罗马假日》中公主褪去繁冗而沉重的包袱,回归一个女孩的身份,是由她剪掉长发变成随意自在的短发开始的。《甜姐儿》(斯坦利·多南导演,1957年)中赫本的形象从一个简朴的具有智慧的女性到一个时尚的女模特的转变,更是由那一件件富有现代感的服装带来的。影片中第一次出现赫本的形象时,穿着的是立体剪裁的白色连衣裙,上面披着一块粉色的拖地披肩。她的服装中缺少一种传统女性惯常的修饰——腰部修身、纱巾或蕾丝、花朵图案等等,反而呈现一种极简主义的色彩。赫本前后形象的一致性在于它是非传统的,在影片中,“围绕赫本展示了垮掉一代的文化,成为了‘学生们的时尚’”。[4]42这一形象相继出现在奥黛丽·赫本的多部影片中,它着力于通过服装等元素将赫本独立的具有主体性的女性形象建构起来。与梦露、芭铎等具有金发和曲线美的女明星不同,赫本“太高,太瘦,且平胸”。她在影片中穿裤子、男士衬衫、平底鞋、黑色毛衣,相比修饰胸部与臀部的服装,赫本的形象“精确地修剪‘镶褶边’、‘挑剔’和‘过度的’女性化的概念,而是与强调‘现代设计’、‘简单线条’的朴素的现代主义相关联”。[4]102赫本的着装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女性,使得她们从“妈妈的服装”中走出来,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造型。“女性在1950年代穿裤子是不合时宜的。”[4]106然而,赫本的看似并不性感的形象使得她可以穿上裤子并且非常适合。赫本的时尚形象让许多女性找到了自己的风格。雷切尔·莫斯利在《与奥黛丽·赫本一起成长》中记录了影迷罗斯回忆她十几岁时需要出席一个正式的社交场合,她穿了一件黑色的翻领毛衣和一条黑色的滑雪裤,获得了大家的肯定,这一造型即来自于《甜姐儿》。许多赫本的影迷模仿赫本的服装并非想要简单地模仿赫本,或者成为赫本,而是通过赫本发现了自身“可以获得和控制的女性气质”。[4]121赫本短小精悍的头发和她的服装一起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新女性的文化叙事。和她的服装一样,它反对那些“曲线的”、“金发的”传统女性形象,这是她外表现代性的另一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不仅女性的发型有了突破性的改变,男性的发型也是如此。《逍遥骑士》中彼特·方达的BOBO头就与经典电影时代好莱坞男明星的大背头不同,它用额头前的一片长长的刘海模糊了双眼,经典电影中好莱坞男明星自信阳刚的男性气质消失了,代替它的是忧郁的、浪漫主义的、带有女性气质的形象。而影片中丹尼斯·霍珀的长头发更能体现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型的叙事。作为女性气质标志之一的长发与霍珀粗犷的脸形成反差。他的长发不是传统的柔顺造型,而是乱成一团。这样的发型不再是秩序清晰的,而是走向反面的,“对男人来说,长发意味着对男性和女性的自然性的挑战,对性别身份的挑战,最终是对社会惯例的挑战,从哲学上而言,是对分类学和本质主义的挑战”。[19]
在中国电影史上,发型的变迁同样可以作为一种叙事的维度。“文革”电影女明星的文化突围集中体现在发型的改变上。杨春霞在《杜鹃山》(谢铁骊导演,1975年)中的“柯湘头”、李秀明在《春苗》(谢晋、颜碧丽、梁廷铎导演,1975年)中的“春苗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独树一帜;张瑜在《庐山恋》(黄祖模导演,1980年)中以长发飘飘的“新女性”完成了其“外来者”的身份塑造,令刚走出封闭年代的中国观众大开眼界;随后的《小街》(杨延晋导演,1981年)中,“张瑜式”短发也迅速风靡全国。[20]
当奥黛丽·赫本等电影明星的服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国家开始风靡的时候,许多时尚杂志为了帮助大众获得这种崭新的形象,会将明星在电影中所穿的服装价格标出,并告知在哪个百货店可以购买。近年来屡次登上国内外时尚杂志封面的影星范冰冰,在其主演的影片《二次曝光》(李玉导演,2012年)中穿的服装也由该电影的官方网站进行销售。在影片放映不久,淘宝网站上也出现大量出售类似服装的店家。比较而言,这样的服装消费行为与消费赫本等女明星服装的行为有所不同,当然也不同于早期中国电影中带着裁缝看电影的女性观众。从对赫本影片中的服装进行银幕之外的消费,可以看出当时的女性观众对自身女性气质的一种新发现,而中国早期电影明星在影片文本中穿着的洋装、旗袍,则是中国现代新女性发端的重要外在表征。《龙凤配》中的黑色礼服需要在全世界的百货公司竞相摆放销售,《二次曝光》中的衣服则可以通过网络购得,原因不仅在于如今中国服装加工业的发达,使各种稀奇古怪的服装都可以轻易获得,而更在于这些服装的“廉价性”与“复制性”。这种廉价与复制产生于无处不在的当代工业化生产链。赫本的黑色礼服协助赫本建构起她独立的女性意识,强调了赫本形象的现代性。穿黑衣服的背后意义,乃是“风格化、权威的欧洲人,反时尚的风格……源起于二战之后的清教徒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追随者,最后被美国新世代的垮掉的一代所追逐”。[4]42在《二次曝光》中,穿着这些服装的精神病气质的范冰冰与赫本“健康的”、“自信的”明星形象截然相反。比较而言,赫本的服装是观念,范冰冰的服装是道具。观众购买《二次曝光》中的服装不存在上文所提的,通过观察、模仿明星来发现与建构新的自我,从而达成明星与大众的共鸣,而主要是一次简单易行的可被不断重复并不断遗忘的消费行为。
历经一个多世纪发展的世界电影史,电影明星的身体呈现,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折射出电影观念与文化观念的变化,并以此为视角构成了一部独具意味的文化史。它与权力机制之间的博弈,与大众趣味之间的对话,于中国本土电影而言,依然是个意味深长的话题。
注释:
①电影表演,指的是演员在影片文本中的表演;而文化表演,“除了沿用传统‘表演艺术’范畴里,对剧场、仪式乃至电影、电视在内的相关研究,还进一步借用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方法,企图将剧场/电影艺术里的表演技巧,视为一种社会实践与文化价值再现的表演行为”。详见周慧玲《表演中国:女明星,表演文化,视觉政治,1910—1945》,麦田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②参见“维基百科”之“脸”,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89。
③参见“百度百科”之“面相学”,http://baike.baidu.com/view/889521.htm。
④参见“百度百科”之“颅相学”,http://baike.baidu.com/view/16228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