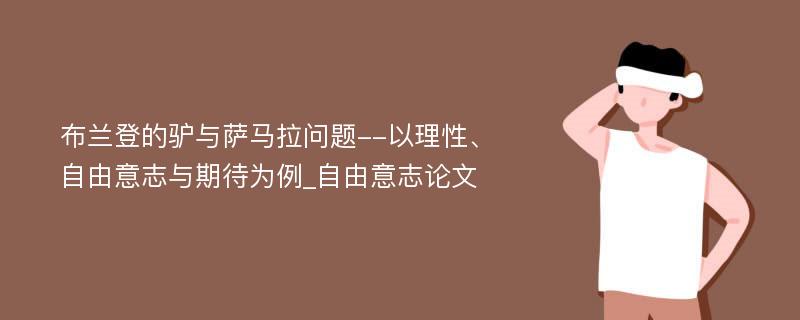
布里丹的驴子和萨马拉问题——以范例讨论关于理性、自由意志和预期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驴子论文,几个问题论文,范例论文,布里论文,意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3)06-0026-06
一、从寓言方法到范例方法
寓言方法是一种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哲学方法和文学方法。
我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就是一位非常善于运用寓言方法的大师。《庄子》一书通行本33篇,虽然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把全书的最后一篇《天下》篇看作全书的“序言”,但也有人——例如王夫之——认为应该把《天下》篇和《寓言》篇共同视为全书的“序言”[1]。在一本书的序言中作者往往是会谈到作者的写作方法和写作意图的。《天下》篇说庄子所使用的写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而在《寓言》篇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说法。我国现代研究庄子的专家杨柳桥认为:两相比较,应该断定《天下》篇关于“三言”的说法是袭取了《寓言》篇的说法,所以,把《寓言》篇的第一章看作是《庄子》全书的“序言”才是更合理的。杨柳桥说:“《庄子》全书,‘寓言’是它文章的基本形式,‘卮言’是它学说的具体内容”[2]。《寓言》篇说:《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寓言占十分之九)”,验之《庄子》的本文,这不但是作者的“夫子自道”而且是对《庄子》一书的“客观”评价。
所谓寓言就是作者所构造的一个小故事,它可以是现实主义的故事,也可以是虚构的以人、鬼神或动物为主人公的故事。寓言与一般的“小故事”的区别在于它的独特的典型性、思想性、哲理性。寓言方法是一个文学家和哲学家都可以运用的方法。虽然可以说文学寓言和哲学寓言之间是没有绝对区分的,但二者之间也还是存在着某些重要区别的。一般地说,文学家不会对自己的寓言作过多地解释,至多“卒章显其志”就行了;而哲学家往往却需要对自己的寓言再作一些进一步的思想发挥、理论分析或哲学解释,特别是在现代学术中,这些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就更是绝不可少的了。文学寓言的灵魂是形象,形象中有哲理;哲学寓言的灵魂是哲理,哲理寄寓于形象。
虽然像庄子、韩非这样一些先秦哲学家是非常重视运用寓言方法的,但其后的中国哲学家就很少有人特别重视使用寓言方法了。在汉代之后,论说方法不但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主导方法,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一统天下”的哲学方法了。如果说中国哲学在其历史发展中,论说法很快就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的话,那么在西方哲学中就更是如此了。可以说,在哲学的发展中,大多数哲学家已经忘却了寓言方法也曾经是并且也可以是一种哲学方法了。
可是,情况似乎逐渐地也在发生变化。可以认为,变化发生在两个方面:方法论的理论方面和方法论的实践方面。在方法论的实践方面,古人的寓言方法在现代学术中正在演变为一种新的范例方法。所谓范例方法就是构造范例、分析范例、解释范例的方法。范例方法也就是案例(英文的case)方法。由于在中文里,案例往往是指“真实案例”,人们往往不把虚构的故事称为案例,所以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地将使用范例这个术语,但也不排除对案例这个术语的使用。
在现代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中,许多人都忽视、轻视和低估了范例方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但在这个“整体背景”下,也出现了几个比较重视运用范例的学科领域,例如现代西方经济学和博弈论就是这样的学科领域,经济学家和博弈论学者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较多地运用了范例方法。“举例”来说,“囚徒困境”就是一个在博弈论和一些相关学科中“应用范例方法”的“范例”。我们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构造出这个“假设”的范例之后,谈论、分析、解释、研究“囚徒困境”问题的人愈来愈多,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几乎无人不知的“现代寓言”和非合作博弈的典型范例了,可以说,所有的博弈论教材都是没有例外地要讲“囚徒困境”这个范例的。其他的范例,例如智猪博奕(boxed pigs)、性别战(battle of the sexes)、斗鸡博奕(chicken game)[3]、纽可姆问题[4]等也都是在博弈论、决策论中运用范例方法的具体例子。翻开博弈论的论著,简直可以说是无范例就“不成书”了。
在方法论的理论研究方面,我们看到库恩就是一位倡导范例方法的“第一旗手”和“孤独旗手”。虽然库恩的范式理论已经成为了“闻名遐迩”的理论,但库恩对范例方法的倡导目前还没有在方法论理论研究领域获得多少重视,可以说是应者寥寥,几乎无人响应。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现在已经成为了一本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后,有不少人批评该书中范式的含义不明确,太多义。1969年,库恩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增写了一个《后记》,对范式这个概念作了一些新的说明和解释。在这个《后记》中,库恩强调了“范例”(exemplar,examples)概念的重要性。库恩更强调说:“范式是共有的范例,这是我现在认为本书中最有新意而最不为人所理解的那些方面的核心内容。”[5]但令人遗憾的是,科学哲学界和方法论学界的大数人在理解范式时并没有注意库恩的这个“自白”,库恩所特意点出的“最有新意”之处许多人仍然不认为有什么新意,库恩所深深感到的“最不为人所理解”的地方仍然继续是一个“最不为人所理解”的地方。
邱仁宗先生说:“Kuhn的特点是思想深刻,但拙于表达。可能由于他本来是学习自然科学的,缺乏哲学、逻辑上的高度训练因此一谈到哲学层次的概念就不能给人以前后一贯、明晰的印象。本来他的思想新颖,足以引起很多歧见,而上述的情况使歧见就愈加增多了。在争论过程中,Kuhn又百般解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我赞同邱仁宗先生的这个评价。我认为,无论是库恩在1962年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范例方法的解释,还是他在1969年版的《后记》中对范例方法的解释,都是非常富有新意但又是有许多缺陷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笨拙”的。与其他“拙于表达”之处导致了“很多歧见”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后果不同,库恩对范例问题的“拙于表达”所造成的后果是使库恩所自鸣得意的这个“本书中最有新意”之点成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在库恩写《科学革命的结构》时,博弈论还只是一个初问世的婴儿,一个刚刚会摇摆走路的丑小鸭;而现在博弈论已经在科学园地中成长为一个众所瞩目的“明星”了。以博弈论中范例方法的广泛应用和显赫地位为“范例”和“支点”,我们再也不能冷落库恩关于范例方法在范式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观点了。
在哲学研究中,我们不但需要重视运用论说方法,而且需要重视运用范例方法——“构造范例、分析范例、讨论范例、解释范例”的方法。范例方法的突出优点是形象生动、易于把理论和现实密切结合起来,有利于结合实际进行具体分析,有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有助于避免空发大而无当、模糊空洞、游谈无垠的议论。在20世纪90年代郭贵春教授曾多次撰文介绍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中所出现的“修辞学转向”,郭贵春教授说:“美国著名哲学家R.罗蒂将‘修辞学转向’称之为本世纪以来,继‘语言学转向’和‘解释学转向’之后,人类哲学理智运用的第三次转向,并认为它构成了社会科学和科学哲学重新建构探索的‘最新运动’。”[7]如果罗蒂的这个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可以说在西方学术界中所出现的重视运用范例方法的现象就是构成修辞学转向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内容和方法论表现。
在本文中我们将对两个范例——“布里丹的驴子”和“萨马拉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和讨论。
二、布里丹的驴子
布里丹(Jean Buridan)是欧洲14世纪的哲学家,巴黎大学教授。据说他曾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头饥饿的驴子,虽然在它前面有两堆完全相同的干草,可是由于它不能决定究竟应该吃那一堆而终于饿死了。数百年来人们都相传这个寓言是出自布里丹的。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也提到了这个寓言[8],在该书中,虽然熊彼特没有并没有直接说明这个寓言出自何处,但其行文却似乎有暗示这个寓言是出自布里丹的《辩证法纲要》和《逻辑纲要》的意思。可是,十月革命后被迫流亡国外的俄罗斯哲学家洛斯基却明确地指出:“在他(指布里丹)的著作中没有找到被认为是他所举的例子。”[9]但是,尽管有洛斯基这样的说法,人们却仍然继续把这个寓言称为“布里丹的驴子”。
有经济学家认为可以利用这个寓言讨论理性、机会成本和无差异曲线分析问题[10];但哲学家却主要是利用这个寓言来讨论自由意志问题的:要是这个驴子只知道根据理性进行选择的话,它是免不了要饿死的;但如果有了自由意志,它就可以想吃那堆干草就吃那堆干草,而不会被饿死了。
在这个范例中,真正的讨论对象无疑地不是驴子而是人,是人的本性和人的生存的根本前提、特性和根据的问题。
人是理性的动物,同时又是有自由意志的动物。在哲学中,认识人性和讨论人生(人的生存)是离不开对理性和自由意志的认识和讨论的。这个寓言的情景和寓意是耐人寻味的。正像熊彼特所说的那样,这个寓言首先已经承认了这头驴子是具有“完全理性”的。在欧洲哲学中,承认人是理性动物的传统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相形之下,对意志的认识和研究就要稍晚一些了。米切姆说:“……意志是一个在哲学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一致意见的概念。在古希腊思想中没有出现意志(will)这个术语;它是通过基督教哲学传统进入西方理智史的。”[11,p.254]
自由意志的直接表现是进行选择;容易看出,没有选择便没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哲学问题,许多重大的哲学问题都是和自由意志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起初哲学家最关心的是自由意志与善恶的关系的问题,而后来,哲学家关心更多的却是自由意志与理性的关系的问题了。
早期基督教哲学家——例如护教者和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问题进行了许多讨论[12]。奥古斯丁是被誉为“第一个现代人”和“早期基督教会最伟大而有创见的思想家”的人,数年前我读了他的《论自由意志》(中译文收入《独语录》[13]),读后使我非常吃惊的事情是奥古斯丁写此文的一个重要目的竟是为了回答关于恶的来源的问题——伦理的恶来源于人的自由意志。
伦理学是研究善恶问题的。人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善行或恶行负责呢?这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因为为善或为恶是出于自己的自由选择,所以人才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反之,如果人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的自由选择,人自然也就不必为自己的善行或恶行负责了。
但在“构造”“布里丹的驴子”所面临的问题时,我们看到: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自由意志和善恶的关系的问题,而是自由意志和理性的关系的问题了。
在“布里丹的驴子”这个范例中,其作者构造了一个理性选择的困境——怎样在两堆没有差别的干草之间进行选择?这个选择困境是一个事关“解决它才有生路,解决不了它便要饿死”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有些哲学家认为,走出“布里丹的驴子”式的理性选择困境的出路——或者说解决理性选择困境的关键问题——是诉诸人的自由意志。因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人也就得以在面临理性选择困境的时候“绝处逢生”了。很显然,坚持这种认识和答案的哲学家在自由意志和理性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方面实际上是主张在人性中自由意志占据了比理性更根本的地位和“高于”理性的地位的。与这种观点相反,也有另外的一派,他们主张理性至上,认为意志应该服从理性,应该由理性指挥意志。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如果说叔本华、尼采是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那么黑格尔就是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了。
在近现代西方哲学史上,自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哲学流派崛起后,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史上,非理性主义思潮有愈演愈烈之势。我认为对于意志主义哲学流派所发挥的引起哲学界空前注意哲学中的意志问题的重大功绩,我们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但对于他们那种把意志和理性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立场我认为又是必须给予批评的。
有人说,哲学问题是没有最终答案的,我赞成这个观点。在此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不但理论形态的哲学问题是如此,而且范例形态的哲学问题也是如此。例如,由于20世纪有了许多科学上的新进展,于是人们也就可以根据新的科学理论和观点对“布里丹的驴子”这个范例作出新的解释和新的解答了。
现代物理学认为,物体不可能处于绝对静止状态,原子也都是处于不停振动状态的,甚至真空也是存在涨落的。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在耗散结构中可以出现“通过涨落的有序”[14]。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思想和有重大意义的科学进展。
根据“通过涨落导致有序”的观点,我们可以推断“布里丹的驴子”也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状态“涨落”的,于是在出现随机涨落的那一瞬间,它同那两堆干草的距离便不再完全相等而是必定有一堆离它更近了,这个“布里丹的驴子”在这一瞬间便可以作出一个理性的决策去吃那距离更近的一堆干草了。于是,“布里丹的驴子”原先所面对的选择困境也就可以摆脱了。
我们也可以给出一个更“形象”的解答和解释:如果这个“布里丹的驴子”有时免不了也要打一个喷嚏的话,那么,在它打喷嚏的那一瞬间,原来存在的它与那两堆干草距离完全相等的绝对平衡的状态就要被打破了,这个“布里丹的驴子”也就可以作出理性的选择和决策了[12]。
很显然,在这个新的解释方式中,选择的意志是从属于理性分析和理性推理的结果的;在这种分析中,理性重新“获得”了对选择和自由意志的“指导”和优先的地位。
那么,在理性和意志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的不同观点的争论是否可以就此而画上一个句号呢?问题当然绝不会这样简单。
以上的分析中,我们没有考虑进行决策所“需要”的时间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任何决策都是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的,那么,这个“布里丹的驴子”便不能确定:在经历了这个进行决策所需要的“一定的时间”之后,在它要行动的那个时刻,究竟原先决策要选择的那堆干草是否仍然还是离它更近的干草。如果在它要行动的那个时刻,随机涨落的结果是使得原先决策要选择的那堆干草反而成为了离它更远的干草,那么,它岂不反而又成为了一个“非理性”的“动物”了吗?如果它有了这更深一层的理性思考,它就又会成为一个“昏头昏脑”无法进行理性选择的动物了——它又要再次地陷入一种新的理性选择的困境了。
米切姆说:“人的行动最终不是由理性决定的。存在着某种更基础、更根本、更现实的东西——即意志。那些不能自制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有些人虽然在理性水平上知道什么是善,但同样仍然别样行事。”([11],p.266)
理性分析和哲学思考的结论似乎在启示我们:意志是一个与理性有密切联系但又不能完全归结为理性的问题。
三、萨马拉问题
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普斯王》是许多人都熟悉的故事:俄狄普斯王生下来便被预言将来他要杀父娶母,于是他就远走他乡以避免应验那个预言,由于他的父母也远走他乡以避免应验那个预言,结果反而是俄狄普斯王最终还是未能逃脱杀父娶母的命运。在古代波斯也有类似的传说。现代文学家毛姆在他的剧本中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索贝尔根据类似的故事构造了一个更便于进行哲学分析的“范例”,并把它称为萨马拉问题(The Samarra Problem)([16],pp.55-56)。问题是这样的:
如果我的敌人和我明天是在同一个城市,他就要杀死我。他已经预测到明天我会在那里并且已经上路了。他已经上路一段时间了。无论我做什么都不会改变他的行程。所有这一切我都是可以肯定的。我的选择是有限的。我处在巴格达和萨马拉之间,明天我可以在这两个城市中的一个城市里,并且必须在二者中的一个城市里。只要明天我能避开敌人,明天我究竟是在哪个城市对我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是:我有最好的理由设想我的敌人已经正确地预测了明天我将在哪个城市。我认为他是一个高度可靠的预言家。作出一个决策应当并不一定等于或接近于等于认识到他的预测和目的地,因为在作出一个决策后我可能很想知道我的决策是否最后的决策。而且,无论我尝试地或三思后决定了要去哪个地方,对于这个决策我都会认为那个地方很可能就是我原来要去的地方,因此那个地方也就是我的敌人已经预测到的我要去的地方。
我要去哪个地方呢?哪个选择是理性的?
可能有两种分析、两种答案。第一种答案说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是理性的;第二种答案说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不是理性的。这两种答案都可以用不止一种方法进行辩护。
对第一种答案可以这样进行论证: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去巴格达,那么我的敌人就会已经预料到我要去那里并且在那里杀死我。假定我要去萨马拉,那也是一样的。所以我究竟是去那里就不是紧要的了。当究竟我做什么无关紧要时,无论我做什么就都是合理的(reasonable)了,或者至少说不是不合理的(not unreasonable)了。选择去巴格达和选择去萨马拉都应该不是违背理性的,因为我所想的是一个低劣的目的地。
对第一种答案也可以这样进行论证:
至少在我进行思索开始时我应该不知道我将作出哪个选择。我应该不知道我将去哪里,我的敌人将去哪里。对于我的敌人的两个目的地我应该有相等的概率。可是,因为所有对我要紧的事只是我要避开我的敌人,所以我的这两个选择的预期效用是相等的。既然一般来说,一个选择是理性的权且仅当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预期效用超过它的预期效用,于是我们得出结论:每个选择都是理性的。
对第二种答案可以进行这样的论证:
要是我决定去巴格达,那么在这个决策吸引我的时候,我会想我的敌人很可能正在去那里。可是,对这个决策的反省会揭示一个不再坚持这个决策的理由。我会发现一个理由改变我的决心,决定去萨马拉而不是去巴格达。尽管决定去巴格达并不必然是非理性的(not necessarily irrational),但它必然不是理性的(necessarily not rational)。如果我选择去巴格达然后再反思这个选择,我反而会想我的敌人正在去那里,因而去萨马拉才是我最好的选择。如果我坚持原先选择的话,那么,坚持原先的选择应该是非理性的。然而,当我改变选择而决定去萨马拉后,我又会发现有理由改变这个新的决定。于是,我无法作出一个稳定的决策。在这个案例中,没有可能有理性的选择。
索贝尔批评了对第一种答案的论证,认为在论证中存在着混淆陈述句和虚拟句的错误;他赞成和支持第二种答案。
索贝尔认为:一个选择是理性的,当且仅当(1)这个选择有最大的预期效用,并且(2)经过思想反省它被证明是稳定的。根据这种理解,尤其是根据对于“稳定性”这个标准的坚持,索贝尔赞成第二种答案,不赞成第一种答案([16],pp.59-62)。
本文不再介绍索贝尔和其他学者对萨马拉问题和其他相关范例所进行的具体分析、论证和具体结论了。在此我只想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一些评论:在国外学者对这些范例进行分析时他们很注意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他们努力具体结合这些具体范例澄清那些原来存在的诸多模糊不清之处,揭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问题上出现了怎样的不同解释和不同理解,努力消除“不经意间”出现的误解——尤其是关键性的误解和错误,特别是注意宣示导致不同解答和不同分析的不同的理论“标准”和理论原则。这些方法论上的优点,我们是应该注意借鉴和学习的。索贝尔认为,在争论中,不同的学者不仅是不同选择的拥护者,更是不同理论的拥护者。例如在对纽科姆问题的争论[4]中,之所以出现两种答案的分歧,重要原因之一是一派学者主张理性行动的标准是证据的预期效用(evidential expected utility)的最大化,而另一派学者主张理性行动的标准是因果的预期效用(causal expected utility)的最大化([16],p.69)。
索贝尔的《意志之谜:宿命论,纽科姆问题和萨马拉问题,决定论和全知全能》[16],一书谈到和分析了萨马拉问题,从书名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本书是通过分析纽科姆问题和萨马拉问题这两个范例来研究自由意志、决定论和预期问题的。
自由意志、决定论和预期问题是“成组”的理论问题,而萨马拉问题和其他问题一起又构成了“成组”的范例。我认为索贝尔这本书的突出特点就是通过对“成组”范例进行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成组”的理论问题。
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意志问题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我国哲学界已有人指出:“当代中国的意志哲学仍呈‘贫困’状态是个不争的事实……社会公众甚至很多学者对意志哲学迄今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误解。”“迄今为止的中国意志哲学研究,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意志理论所达到的研究水平来说,它相对‘退步’了;相对于同期中国其他分支哲学研究所取得的进步和意志哲学应当达到的水平来说,它明显‘落后’了;相对于当代实践对当代合理形态的意志哲学的迫切需要来说,它更是严重‘滞后’了。”[17]目前我国研究哲学原理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对意志问题的研究了,而在我国的科学哲学界仍然很少有人关心研究意志问题,我国科学哲学界的学者也应该迅速地关注对这个问题的科学哲学的研究才对。
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预期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经济学中已经十分注意研究这个问题了,经济学中理性预期学派[18]的出现便是一个突出的“标志”。波普也高度注意了预期问题。他“建议把预测对被预测事件的影响(或者更一般地说,某条信息对该信息所涉及的境况的影响)称为‘俄狄普斯效应’。这种影响或者会引起被预测的事件,或者会防止这种事件的发生。”(按:他对俄狄普斯效应的分析和观点与索贝尔对萨马拉问题的分析颇有不同)他还由此而得出了“精确而详尽的科学的社会预测是不可能的”的结论[19]。与国外学者已经高度关注对预期问题的研究相比,我国哲学界还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哲学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哲学界也应该“急起直追”才对。
上文谈到可以把某些相互关联的范例称为“成组”的范例,例如萨马拉问题、纽科姆问题和“疾病问题(The Disease Problem)”就是一组结构相似的范例。但索贝尔认为这三个“范例”的答案的性质却是很不相同的:萨马拉问题不是一个可以有理性选择的答案的问题,而纽科姆问题却是一个可以有理性选择的答案的问题;在萨马拉问题中有“我”和“敌人”两个行动者(agent),而在疾病问题中,“我”的位置又恰恰是和萨马拉问题中的“敌人”的位置是一样的([16],pp.51-71)。应该注意的是,有些理论问题也是“成组”的,例如意志问题和决定论问题就是密不可分的问题。在我国的哲学界,虽然有很多人都在关注研究理性问题[20],但却很少有人把把理性问题和预期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希望我国今后也能有人像索贝尔那样把理性、意志、决定论和预期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入的哲学研究。
在本文最后我想再重复地强调以下三点:我们应该重视范例的作用和运用;科学哲学界应该重视对意志和预期问题的研究;我们应该尝试以构造和分析“成组”范例的方法来研究“成组”的理论问题。
〔收稿日期〕2002年8月10日
标签:自由意志论文; 寓言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萨马拉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科学革命的结构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庄子论文; 天下论文; 哲学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