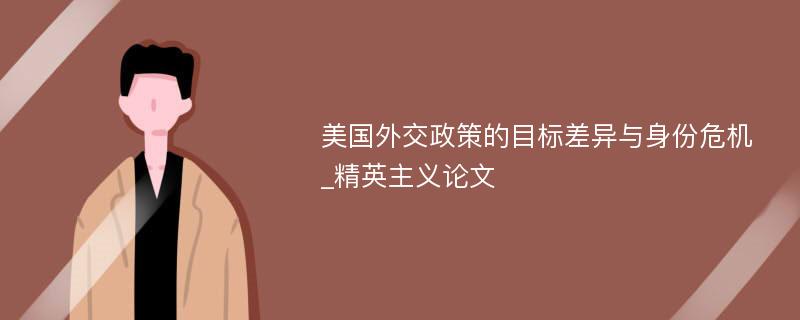
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分歧与认同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美国论文,分歧论文,危机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朝野一直在进行着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这场辩论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在这个新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来自何方。”对此答案,美国政府、舆论精英及普通民众各持一端,即使各阶层、各集团内部也很难找到一致的观点。1993年下半年,美国Times-Mirror中心进行的数次民意调查,集中反映了美国各界对于当前国际事务的不同态度和观点①。这项调查成果的问世,为我们深入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的未来走向提供了重要线索。
Timse-Mirror中心的这项调查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国内进行的一次最为广泛的外交政策民意调查。它是由1993年7月至8日对649外舆论领袖的抽样调查、9月对2000名普通成年人和10月末对1200名成年人的问询所构成,然后将三次调查综合比较得出结论。因此这项调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各种不同观点的比重和来源。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对舆论领袖们的调查。从被调查者的构成中可以知道,他们是美国政府决策的主要影响力量。其中外交界人士主要选自国务院以外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防务与安全界人士选自国防部以外的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所,众所周知,这两个机构实际上是曾经担任过高级职务的外交家的战略家所组成,他们的观点常常间接反映了美国政府外交和战略决策的要求;企业界人士是从《幸福》杂志排名1000家大企业和金融业的行政首脑中选出,所谓政界人士则来自50个州的长和8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市长,这两类人士往往是总统的后台老板或者是未来的总统,但又经常发出与华盛顿不一致的声音;学术界是由各大学校长和各主要思想库领导人的代表构成,科学界则是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科学院的成员,他们代表着美国政府决策的思想来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为总统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取向;传媒界人士是由美国各大报刊、电视和广播的社论撰稿人、驻华盛顿处负责人和专栏作家所组成,由于他们对大众态度的重大影响力,可以称为“真正的舆论领导者”。此外,宗教界代表着美国各大教派,文化娱乐界则是出现在美国名人家上的各类艺术家和文学家,这两部分人往往使政府和大众的选择带上浓厚的感情色彩。所有这些人几乎都是成年白人,2/3以上拥有较高学位,40%具有博士头衔。这些条件决定了他们中大多数人能够从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来作出政策选择,从而也证明了政府分歧的深刻性。这些上层集团的代表人物与下层民众的观点相左,说明美国社会在对外事务中的认同危机正在加深。
以下是按政策的分歧焦点来考察各个集团的取向。
(一)、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是否仍然具有充当“世界秩序领导者”的地位和能力?
这个问题在精英阶层中反映出明显的矛盾心理。在对外事务中最为知情的外交、防务、传媒、企业界人士看来,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也明显低于10年前;但是另有约1/10的精英认为,美国应当在世界新秩序中担任唯一的领导力量。在这两端之间主间的大多数精英(约占总数2/3)认为,美国虽不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领导力量或最有决断权的国家,但却是在处于最高层次的国家中“具有优势的强国”(Prepcnderant power)。在他们看来,只要美国保持唯一的军事超极大国地位,其对世界事务的领导作用就不会消失。然而受各种因素的牵制,他们赞成实行一种“分享的领导权”,使美国在其中最具影响力。可以说,这种“分享领导权”论是美国官方的的主流观点。在对下层民众的测试中,也只有少数人支持美国在世界上进一步发挥领导作用,而2/3的人认为美国不应比别国“更积极地”行使这种领导作用,故赞成“分享领导权”。
由此可知,美国舆论的主流已经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加以定位,即实行某种“形式变化了的领导权”,而如何行使这种领导权,则取决于对世界未来战略格局的判断和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顺序的排列。
(二)、在未来的2000年,最可能影响世界格局的发展进程是什么?
这项预测实际上是美国制定未来战略的依据,所以特别值得注意。由于冷战后多极化格局尚未最后确定,美国对外政策失去战略目标,这是制定新战略的最难之处。因此,美国决策层需要找到对未来世界格局最有影响力的若干因素。
在这次测试中,精英阶层各个集团无一例外地把“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作为第一位的未来发展进程,颇有些出人意料。每个集团都认为这个发展进程是肯定的或可能的,尽管这个选择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将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大多数精英们认为中国不会动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和南沙群岛(斯普拉特利群岛),但对此应有所警惕。只有安全—防务界的预测认为,中国将会在领土争端中动用武力,而且将这种可能性置于未来重大进程的第四位。由于防务界对于战略决策的重要性,这项估计人数虽少,但其作用不可低估。
大多数精英集团把列于第二位的重大进程是“德国在欧洲居主导地位”。对于德国,美国上层人士基本上不担心它会成为一种复仇的力量,相反认为由德国来领导欧洲联合的进程可能比由别国来领导更具有稳定性。
有关第三、四、五位的未来重大进程预测就不如前二位那么一致了,反映出精英阶层思维出现极不一致的逻辑。例如,宗教界、地方政界、传媒界、外交界分别把“美国国内恐怖主义活动上升”列至二、三、四位;表现出宗教界、地方政界更重视美国国内秩序的稳定。而企业界最重视的未来进程是“日本经济力量的削弱”。如果把这个进程与“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和“德国主导欧洲事务”联系起来,则可以看到美国考虑的21世纪世界强国排列的大致轮廓。只有防务—安全界认为“俄罗斯恢复原苏联帝国”是可能的未来的进程,但仅仅把它列在第五位。“俄罗斯因素”尽管在中近期战略中仍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但在美国的远期战略中其地位将有所下降。在区域性的未来事件中,有三个方面被列入预测,其中一个在东亚,即“北朝鲜共产党政权结束”;二个在中东,即“阿以战争再起”和“两伊战争重开”。从排列上看,外交、防务界更重视朝鲜半岛的未来局势发展,而企业界、地方政界和宗教界更关心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
把中国放在21世纪“最可能影响世界格局”的首要因素,可能是这次测试中最有深远意味的结果。尤其是各集团一致的看法将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发生重要影响,尽管这些集团看问题的出发点十分不同。
(三)、世界上对美国战略利益最为重要的地区在哪里,选择战略第一地区的标准是什么?
在美国冷战后的全球战略中最困难的莫过于选择战略第一的地区。在欧洲、亚洲和中东三个地区的重要性比较中,亚洲的战略重要性正在上升,但并不等于安超过了欧洲而成为第一重要的地区。在这次测试中,9个精英集团加上一般公众共10个方面,只有3个方面即防务安全界、科学工程技术界和一般公众把欧洲列于亚洲之前。其中防务界占45%(亚洲仅28%),公众占50%(亚洲为31%),科技界占33%(亚洲为27%)。选择欧洲的理由大多是基于历史原因,因为“欧洲第一论”在美国根深蒂固。
然而,大多数精英集团选择了“亚洲第一”的战略。其中企业金融界占51%、地方政界47%、宗教界50%、思想库及学术界占43%,这些集团中选择欧洲的第一比重远远低于选择亚洲(差距为10~25个百分点)。而传媒界、外交界、文化界虽然选择亚洲者占上风,但其比重仅领先几个百分点。在这七个集团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企业金融界、思想学术界及外交界;而在选择欧洲第一的集团只有防务界具有较大影响力,但很难与其他七个集团的影响力抗衡。
选择亚洲第一的各集团中有3/4的人把经济原因放在第一位,因为亚洲经济作为世界的增长极和美国最大的贸易地区,对美国的未来发展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在美国西部各州,这种观点在一般民众中也得到强有力的支持。选择亚洲的第二位原因是这里可能产生对美国的最大威胁。部分精英认为,如果把俄国包括在内,中国、日本、南北朝鲜及东盟国家构成的东亚地区最具有潜在冲突爆发的危险性。选择亚洲的第三位原因是历史上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这里进行了三场大的战争,其中一场是与日本、两场则与中国有关。选择亚洲的原因还在于这里也存在着核扩散的危险。与欧洲相比,亚洲的上述因素都是在增长的,从而使美国越来越难以控制。
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择战略重要性第一的标准是什么?
“欧洲第一”的主要基点是俄国及东欧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可能对美国带来的安全威胁;市场利益居于第二位。而“亚洲第一”的基本出发点是美国与亚洲的经济相互依存性已对美国构成极端重要的战略利益;纯粹的军事安全在亚洲只能居于次要。实际上,“欧洲第一”还是“亚洲第一”,反映了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中“安全第一”还是“市场第一”的目标选择困难。
(四)、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应如何排列次序,美国全球战略中优先考虑的因素有哪些?
在这次测试中,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下层民众,绝大多数都改变了传统的美国外交战略目标,认为外交政策首先应当为美国的国内议程服务,而不是为了传统的国际战略概念诸如“地缘政治”、“遏制共产主义”等。这种大幅度的改变当然影响着对于具体交政策目标的排列。无论是哪个集团,都肯定地把“加强美国经济竞争力”放在对外战略的最优先考虑的地位。这实际上是把外交政策从属于美国国内政策,与冷战时期大为不同。
在具体的外交政策目标排列方面,各集团之间表现很大的差异。有9个精英集团加上一般公众这10个方面中,“防务核武器扩散”被排列在各精英集团选择的首位。在冷战后的国际环境中,能够对美国安全利益产生直接威胁的可能是那些得到核武器(技术)的第三世界强国和恐怖主义组织。这些“世界秩序的造反派”们能够在使用最原始的核装置上来进行最现代化的“核讹诈”。在精英阶层中,大约40%的人认为,世界并不是更加接近于合作核武器,因为来自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核大战威胁已不复存在。但是,另外40%的人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核武器使用的概率已大大上升了,因为与核武器相关的知识和材料已广泛扩散到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和恐怖主义集团之手。由于扩散的广泛性,使防范的可靠性大大下降。看来后一种观点在各集团内占了上风,从而使美国政府在防止核扩散的政策力度大为增强。
在政策目标的第二位上,9个精英集团中有7个认定是“确保足够的能源供应”,只有科技界和娱乐界确认为“改善全球环境”。实际上这两项目标是互相抵触的,因为美国的巨大能源消耗实际上是全球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确保能源供应”意味着美国将继续向中东地区投放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遏制中东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增长,并在世界上其他具有能源供应的地区保持足够的影响力,为此,美国不得不保持打胜一场海湾战争规模的地区冲突的能力。连同上述“防止核扩散”目标,美国将特别注意防范那些在能源供应重点地区的激进派势力获得核打击能力。这两项目标结合在一起,可以看作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已大体确定,涉及到与这两项目标相抗衡的国家或力量,就有可能被视作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威胁。在“确保能源供应”和“改善全球环境”之间的政策差距方面,无疑将是后者服从前者。这可以看作是新一轮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较量,新现实主义可能是主流派的选择。
如同前述在未来重大进程的选择中的情况,外交政策目标的第三、四、五位就出现较为杂乱的倾向了,但基本上可以理出几个主重集团的选择方向。例如,企业界、地方政界把“减少贸易赤字”列为第三位目标;而外交界、安全—防务界则认为“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居于优先地位;新闻传媒界、思想学术界则在第三位目标上确认是“改善全球环境”;只有宗教界在这一栏上提出了“促进保护人权”,这是9个精英集团中唯一在前5项政策目标中列入人权目标的。就贸易、联合国、环境三个主要目标来看,最有份量的仍然是促进贸易这一目标,因为在其他各集团的第四、五位选择中,至少有6个集团将它列入。而“加强联合国”和“改善全球环境”分别只有3个集团列入。与此相关的,另有5个集团在第四、五位选择了“保护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实际上减少贸易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国内变业机会的增加,这两项选择的重复出现只是说明这些集团越来越使外交政策带有保护主义的色彩。这又是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传统争执在新形势下的另一种表现。
新孤立主义倾向在越是下层的集团中越是明显。在对一般大众的测试中,排列第一位的政策目标就是“保护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而“加强联合国”根本未列入优先考虑的前5项政策目标之内。地方政界、宗教界、传媒界、企业界也是只选择就业机会而不选择联合国;相反,外交界、安全防务界、思想学术界和工程技术界只选择联合国而不选择就业目标。这样就大体上可以看到促使美国外交政策内向化的力量主要来自前面5个集团。
在对待联合国作用的问题上,一般公众与精英阶层的态度更是截然不同。在美军出现索马里悲剧后,支持与联合国进行军事合作的百分比急剧下降。与海湾战争后相比,1991年公众对联合国的支持率高达77%,到1993年10月降至64%,而反对把美军置于联合国指挥之下的更是占压倒多数。在使用美军的目的方面,大部分民众倾向用于防止大规模饥饿发生的人道主义援助,而不愿派往那些政府权威崩溃的国家去执行治安任务。在派往地区方面,民众认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动用美军的条件和理由比前往非洲和亚洲更加充分。与下层民众不同的是,各个精英集团几乎一致同意将美军置于联合国常设部队的指挥之下,只有这种结合才能使联合国的干预行动更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总体上看,美国精英阶层和一般民众都支持采取一种“有选择地卷入干预行动”的政策,只是选择的范围、卷入的程度、干预的规模各有所不同。
如果将各项政策目标综合起来,可以看到美国对外战略的总体调整方向。传统的安全因素仍然是首要因素,但安全目标广泛化了,并且与经济因素的关联性大为提高;经济因素在对外政策中的比重明显增加,甚至达到50%以上而居于重心地位;未来因素和全球化因素(如环境、联合国)也占不可替代的集团,但由于受到国内因素的种种制约,在近期内仍难以成为主导因素。
(五)、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价值观标准是否发生变化,人权因素在其中的地位如何?
在这次调整中,美国的精英阶层对于外交政策中的传统价值观相当冷漠。在所列的11项外交政策目标中,“促进人权”所得支持率仅居第七位,“促进民主化”则位居第九。可见,曾经是美国外交主要的因素之一的民主人权因素在精英阶层中已不被看作是对外战略的灵魂。
对于人权外交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各种观点亦大相径庭。例如美国支持某一国家的民主运动却导致选出一个反美政府,是否应当保持对这种民主运动的支持呢?大约略少于一半的精英认为支持的立场不应改变,而大多数认为这种民主不值得加以支持。另一种情况是当支持人权运动而冒险得罪一些文化传统不同的美国盟友时是否应继续支持人权,只有不到1/3的人持肯定态度。再一种情况是因为支持民族自治运动而引起现存的某些国家分裂以至国际秩序的严重破坏,是否还值得坚持呢?表示支持的甚至不到1/5。由此可知,所谓支持人权、民主和民族自治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其根本出发点仍然是美国的战略利益,如果民主人权等运动与美国的政策目标相背离,大多数社会上层就会要求美国政府放弃对民主人权的支持。因此,人权因素就难以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维持下去。同精英阶层相比,一般民众对于外交政策的人权因素更持反对态度,而且极大多数反对在国外支持民族自治运动。在普通民众看来,美国政府的这种广泛的“支持运动”对于美国人的实际利益并未带来积极的效果。于是,在“人权因素”上,美国各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出现了真正的认同危机。
然而,最高决策层仍然坚持把人权因素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因素之一。就在这项调查展开的同时,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冷战后的美国“扩展战略”(Strategy of Enlargement)以取代“遏制战略”,而这项新战略的核心就是把“民主制度扩展到全球”。按照该战略的设计者Anthony Lake的解释,扩展战略可分为四个部分:即加强现存的民主国家;促进和巩固新兴的民主国家;保护所有这些民主国家免遭独裁国家的侵略;在那些未民主化的国家中支持人权运动。显然,这完全是以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为基础的对外战略,带有浓厚的冷战色彩。它不仅在实践中不会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认同,并且受到美国的实力制约而根本不能在国际政治中奏效。尽管如此,它的出现,表明人权因素还远远没有从美国对外战略中消失。
在人权因素上出现的认同危机,恰恰反映了美国在冷战后时代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虚弱性。作为西方国家的“领袖”,美国不能不打出代表西方价值观的旗帜“人权民主”并为此承担沉重的义务。但是在以国力竞争和市场利益为主体的国际关系新格局中,美国又不得不把经济因素放在最优先考虑的地位。近半个世纪冷战中美国所付出的惨重代价,更是使大多数美国人对于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对外战略感到厌倦。然而,放弃人权因素则意味着放弃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这种状况决定了现阶段美国对外政策具有一种两重性的、过渡的、矛盾的特征,经常地在价值观和现实利益之间摇摆不定。
很快就有一些战略学家提出其他战略设计来取代“扩展战略”,如“一体化战略”即通过世界市场一体化来扩展美国的影响力和利益;“积极的多边主义战略”即通过国际机制和多边力量结构来实现美国对世界事务的领导权。但是,就克林顿政府而言,它所认定的外交政策目标似乎更加实用,更多一些短期行为。国务卿克里斯杜夫在1993年末提出6项最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目标是:一、通过自由贸易来保证经济安全;二、俄国的改革进程;三、北约的新框架结构;四、“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贸易关系;五、中东和平进程;六、防止核武器扩散。“人权因素”和其他意识形态之争根本没有列入其中,与前一段时间的“扩展战略”表现出明显的区别。甚至与精英阶层所作的政策目标选择相比,克里斯托夫也比他们将经济因素置于更优先的位置。克里斯托夫的选择是否受到精英阶层的选择影响,尚不可知。但是整个美国社会对于“扩展战略”的不认同,肯定是促使克林顿政府改变其外交政策目标的重大因素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应当从美国各阶层对于外交政策的行动取向中,找到一些战略性、规律性的线索,进而适时地调整我们的对外战略和对美关系,从而取得保持有利国际环境的主动权。
注释:
①调查结果参见《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对美国舆论领导人和美国公从关于国际事务的态度调查》,1993年华盛顿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