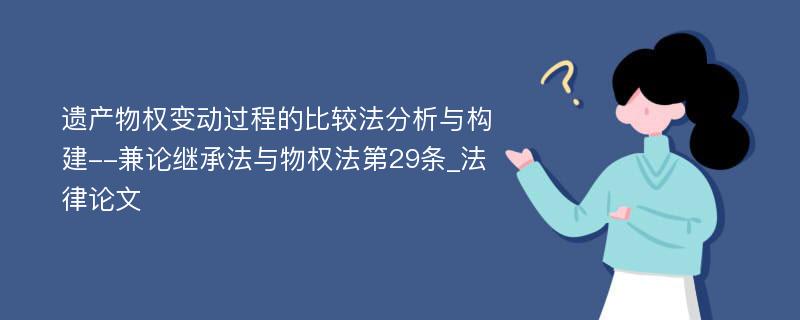
从比较法角度解析和构建遗产的物权变动过程——兼评《继承法》及《物权法》第29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继承法论文,比较法论文,遗产论文,变动论文,物权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008(2015)03-0083-08 一、关于遗产物权变动的理论概述 物权变动是指物权的产生、变更、移转和消灭,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研究物权的发展变化过程,是物权法中基本而又非常重要的制度。在物权法出台之前,我国民法关于物权变动问题缺乏完善的体系规定,理论研究对其也涉及甚少。在物权法起草过程中,该问题得到民法研究者和立法者的极大重视,最终出台的《物权法》以单独一章即“第二章·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对物权变动问题进行了全面规范。该章共分三节内容,“第一节·不动产登记”和“第二节·动产交付”是从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的角度进行规范,“第三节·其他规定”是从非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的角度进行规范。整体来讲,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是物权变动的主要原因,其适用的规则是物权变动的一般规则,非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是特殊原因,其适用的规则是法律的特别规定。 自然人死亡时遗留下来的属于其个人合法所有的财产称为遗产,在自然人死亡后其遗产根据法律规定或遗嘱、遗赠扶养协议等原因要移转给其他自然人或组织,因此,必然要发生相应的物权变动。继承的发生是由于被继承人的死亡而引起,从法律事实的类型来看,被继承人的死亡属于事件,因此物权法将继承引起的物权变动规定在“第三节·其他规定”中,即《物权法》第29条①,该条款是我国法律关于遗产物权变动的唯一明确规定,不但规范了继承还同时规范了受遗赠。该条款将继承和受遗赠并列规定,表明继承和受遗赠的物权变动有所不同,但对于何谓“受遗赠开始时”又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对于遗赠财产的物权变动究竟于何时发生争议颇多。同时,遗产的处理方式除依照继承或者受遗赠外,还存在其他多种方式。如依据遗赠扶养协议取得遗产;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在分配遗产时也可以适当获得部分;另外,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最终将由国家或集体组织取得等。这些遗产的物权变动自何时发生?法律并没有进行明确规定。笔者拟运用民法的基本原理和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则对遗产的物权变动进行全面、严谨的分析和阐释,以期对遗产的物权变动问题提出科学、合理的观点,对现行法律规定之适用以及不同法律之间的关系衔接进行有意义的阐释,也对将来继承法的修订有所裨益。 二、运用比较法方法解析因继承引起的物权变动类型 从世界各国来看,就继承开始后继承人取得遗产的时间和方法而言,大致有以下四种立法主义②: 1、当然继承主义。日尔曼法主要采纳这种立法主义,现行的《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韩国民法典》等从之。《德国民法典》第1922条规定,在某人死亡时,其财产作为总体转移给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继承人。《法国民法典》第711条规定,个人财产所有权可以因继承、生前赠与或遗赠以及债的效力取得与转移。《瑞士民法典》第56条规定,继承人因被继承人死亡而取得全部遗产。《韩国民法典》第997、1005条规定,继承因死亡而开始,继承人自继承开始时起,概括承受与被继承人相关的权利义务。③在当然继承主义下,遗产因继承开始而当然的移转于继承人,无需继承人的意思表示,但是继承的放弃则需有继承人积极的意思表示,并溯及到继承开始之时。 2、承认继承主义。该种立法主义主要为罗马法所采用,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的民法典从之。在承认继承主义下,遗产并不因继承开始而当然地移转于继承人,需要继承人为接受继承的意思表示才发生遗产权利转移的法律效果。如《意大利民法典》第459、470、474条规定,继承财产因承认而取得,继承的效果溯及继承开始的瞬间。继承,得以单纯承认或者限定承认进行承认,得依明示或者默示为之。④《葡萄牙民法典》第2050条规定,对遗产中之财产之拥有权及占有,均通过接受而取得,而不取决于对财产之实际管领。接受遗产之效力追溯至继承开始之时。⑤《俄罗斯民法典》第1110、1152、1164条规定,通过继承,死亡人的财产依照权利概括继受程序,即作为统一的整体、在同一时刻、以不变的形式移转给他人,继承人须接受遗产方能取得遗产。已经接受的遗产被认为自继承开始之日起属于继承人,而不论实际接受的时间;如果继承人对该财产的权利应进行国家登记,则不论进行国家登记的时间,亦自开始继承之日被认为属于继承人。在法定继承时,如果遗产移转给两个或几个继承人,而在遗嘱继承时,如果遗产依遗嘱属于两个或几个继承人,而又未指明每个继承人应继承的具体财产,则遗产自继承开始之日起归继承人按份共有。⑥接受继承是要式行为,其方式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默示。所接受的遗产自继承开始之日起为继承人所有,而不取决于遗产实际接受的时间。由此可见,按照承认继承主义,继承的接受须有继承人积极的意思表示,而继承的放弃则不需要,不接受即视为放弃。 3、法院交付主义。《奥地利普通民法典》采用了此种立法主义。《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436、547、550、797、798、799、818、819条规定,在继承人接受遗产之前,遗产被视为仍由死者占有。一旦继承人接受了遗产,就遗产而言,其就代表被继承人,在涉及第三人时,继承人和被继承人被视为一个人。考虑到数个继承人的共同继承权,他们应被视为一个人。在法院移交遗产之前,这数个继承人对遗产承担连带责任。任何人都不得擅自占有遗产,继承权纠纷必须由法院审理;遗产的移转即合法占有的移转也必须由法院进行。法院的行为都由关于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予以确定。一旦合法继承人作出的接受继承的意思表示被法院所了解,且已完成其义务的履行,遗产就应当被移转给继承人,遗产诉讼程序随之终结。对于不动产所有权的移转,必须遵守法律关于办理地籍登记或文书提存的规定。⑦可见,在法院交付主义下,必须由法院经过特殊诉讼程序后,实际将遗产交付于继承人时才发生遗产权利移转的效力。 4、剩余财产交付主义。这种立法主义为英国法、美国法所采用。如在英国,被继承人死亡后其遗产不是直接转归继承人,而是经过遗产的清点、完税、法院验证、执行遗嘱和承办管理、申请、汇集、分割等一系列法定程序后剩余遗产归属被继承人。⑧因此,遗产先归属于遗产管理人或遗嘱执行人,从继承开始到继承人接受继承,保护遗产是遗产代理人的职责。遗产代理人之于遗产,类似于信托人之于信托财产。英国的《遗产管理法》、《信托法》等法律详细地规定了遗产代理人和继承人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经过清算后如果尚有剩余遗产时,继承人始得请求其交付。在剩余财产交付主义下,继承人对于继承的接受表现为财产交付请求权的行使。遗产代理人有权以其认为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分配被继承人的剩余财产,遗嘱有特别指示的除外。分配一旦完成,该遗产就在财产所在地转移与继承人。美国的遗产继承同样是财产交付主义,其遗产管理和保护制度也非常完备。 在后面的三种立法主义下,继承人并不因继承的开始而当然取得遗产,需要继承人为一定的意思表示或者经过特定程序才能取得。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法律也为遗产的物权变动设计了相应的路径,以实现法律逻辑上的严谨统一。如在承认主义下,罗马法并没有忽视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实际承受遗产之前这个特殊时期的遗产归属。此时之遗产,罗马法上称曰“遗产期待继承”(Heriditas jaceus)。对于此时遗产的性质如何,理论上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一曰法人说,即以遗产具有独立之人格,故可以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但此说终非罗马人之思想。二曰人格说,其要旨是死者的遗产为代表死者人格的继续,在未有合法继承人继承遗产时,此项遗产代表死者人格之继续。三曰继承人所有说,即“期待遗产”为将来继承人所有,不过在此“期待继承”之期间内,未推定何人承受耳。若无人继承时,则国库当然为继承人。在罗马法上颇多以遗产代表死者人格说为是。⑨在法院交付主义下,在继承人表示接受前,遗产仍视为被继承人所有,在继承人表示接受后和法院交付前,将继承人和被继承人视为同一人,数个继承人对遗产承担连带责任。在法院交付财产后,各继承人根据物权变动的规则要求取得遗产的所有权。在剩余财产交付主义下,继承开始后遗产先归属于遗产管理人或遗嘱执行人,通过特定的处理程序后,对于剩余的遗产才交付给继承人。 在当然继承主义下,遗产因被继承人死亡而当然移转于继承人。现行的法国、德国、瑞士、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均采当然继承主义。我国自民国时期即废除旧制,采当然继承主义,以维护继承人利益。⑩根据我国《继承法》第25条规定,继承人要放弃继承需要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可见,依我国法律规定,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无需满足其他特殊要求,继承人即取得继承财产,故我国现行继承法仍然采纳当然继承主义的立法体例。“继承开始”就是“被继承人死亡”之时,此时被继承人的财产就成为“遗产”,其所有权就转移到继承人名下,如果只有一位继承人,“遗产”就归该继承人所有,如果继承人在两人以上,“遗产”就归全体继承人共有。(11)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同时取得现实的继承权和遗产所有权,但继承权是遗产所有权的前提,因此,如果继承人要放弃继承,则放弃的标的应是继承权而非所有权,且需以明示方式作出,放弃继承的效力溯及于继承开始时。 遗嘱继承尽管是通过遗嘱的方式指定了特定的继承人,但其继承本质并没有改变。实际上在被继承人死亡之时,其是否留有有效“遗嘱”可能尚不清楚,是按“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来处理遗产也不明确,所以还不能确定继承人的人数和继承人到底是哪些人,更没有办法进行“分割遗产”或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但是,被继承人已经死亡,权利主体已经消灭,不能让“遗产”处于无主状态,因此《物权法》第29条规定自“继承开始”(即被继承人死亡)之时,由继承人取得“遗产”所有权。(12)此处应当是既包括法定继承也包括遗嘱继承在内的。将继承作为非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的方式,这一规定既符合我国关于继承采用的立法体例,同时也使遗产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有新的所有权主体,不会使遗产处于无主状态下,更好地保护了自然人的合法权益,在逻辑上也较为严谨和周密。 根据《继承法》第33条关于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的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并以其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即继承人在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同时,负有在遗产范围内替被继承人清偿债务的义务。此时,对于继承人来讲,其有权处分遗产以清偿债务,对于债权人来讲,其债权应当优先于继承人的所有权。 三、从对“受遗赠开始”的理解入手解析遗赠引起的物权变动 对于《物权法》第29条关于继承的物权变动规定,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一致,均赞同立法的规定。但对于该条款中关于遗赠的物权变动规定,却有很多不同意见,笔者总结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一)“受遗赠开始”的时间即为遗赠人死亡时间 此观点为当前理论界关于该条款的主流观点,但对于因何遗赠开始的时间与继承开始的时间相同,说法却有很多。有观点认为遗赠虽属法律行为,但依公认的法理,因遗赠发生的物权变动,同样适用继承的规则,即物权不经公示而直接转移。受遗赠人在受遗赠开始时即当然地、直接地取得物权。(13)还有观点认为遗赠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遗赠的遗嘱只要合法,即可发生法律效力,无需受遗赠人同意。遗赠又是一种死因行为,在遗赠人死亡时发生法律效力。所以受遗赠开始的时间通常即为遗赠人死亡的时间。(14)以上两种观点都认为遗赠开始时间和继承开始时间相同,且财产转移原理也相同,只是在表述上有差异。 而梁慧星教授则认为,该条款错误的增加所谓“受遗赠开始”,遗赠的物权变动应与继承同样始于“被继承人死亡时”。《物权法》第29条规定因继承发生的物权变动,从“继承开始”之时发生效力。如果有遗赠,则遗赠财产亦于继承开始之时转归受遗赠人所有。继承法只有“继承开始”而无所谓“受遗赠开始”,条文增加“受遗赠开始”一语属于失误。从被继承人(遗赠人)死亡之时,遗赠财产的所有权就归了受遗赠人,到后来分割遗产时,如果受遗赠人“放弃受遗赠”,则该遗赠财产的所有权就归其他继承人。(15)孙宪忠先生也认为,如果受遗赠人不接受遗赠,遗赠就不能生效,这一分析应该说有一定道理。然而从法理上看,如果受遗赠人做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那么遗赠仍然是在遗嘱人死亡之时生效,而不是在受遗赠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做出时生效。所以,这种情况下的“受遗赠开始”与继承是一样的。(16) (二)所谓“受遗赠开始”应是在受遗赠人明确表示接受遗赠时 根据《继承法》第25条关于受遗赠人接受遗赠应有明确意思表示的规定,王利明教授认为,与遗嘱继承不同的是,遗嘱继承自遗嘱生效时就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但在遗赠中,物权变动则始于受遗赠人受遗赠之时,即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根据遗赠和遗赠协议,受遗赠人愿意接受遗赠,从而使遗赠发生效力,此时就应该发生物权的变动。还有其他学者也持有此类观点。可见,受遗赠开始的时间并非遗赠人死亡之时,而是在遗赠人表示愿意接受遗赠时,此时遗赠才能发生法律效力,物权变动的结果发生。 (三)我国《物权法》第29条将基于继承引起的物权变动与基于遗赠引起的物权变动统一规定,混淆了两者的性质,也与我国采取的物权变动模式相矛盾 该观点认为,在我国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基于继承的物权变动之所以不需要公示,一方面是法律为了避免出现没有权利人,即无主财产的情形;另一方面是法律为了保护物权人。因此,基于继承的物权变动是非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可以无需公示而发生法律效果,而基于遗赠的物权变动属于单方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两者的性质不同,因此不能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我国物权法既然采取了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应该规定遗赠仅具有债权的效力。然而,该观点的不足之处是并没有分析解决在受遗赠人没有取得遗赠财产所有权之前,该遗赠财产的权利归属状况如何。 (四)笔者对于“受遗赠开始”的解析 笔者认为,遗赠是当事人在自己死亡后将遗产留给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真实意愿表现,是典型的法律行为,因此遗赠引起的物权变动应与继承有所不同,并非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就当然发生物权变动的后果,应遵循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的规则,即在法律行为有效基础上再加上相应的公示要件,物权变动的结果始能发生。对此,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各国立法例中分析遗赠并非当然适用继承规则。大陆法系的民事立法关于遗赠发生的效力状况约有两种立法体例:一种是遗赠能够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如日本、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日本民法典》第990条概括受赠人有与继承人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意大利民法典》第649条规定,遗赠不需要承认就可以取得,当遗赠的标的为特定物的所有权或者属于遗嘱人的其他权利时,该权利在遗嘱人死亡的那一刻即从遗嘱人移转于受遗赠人。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002、1003、1006、1010、1011、1014条之规定,遗赠包括全部概括遗赠、部分概括遗赠和特定财产遗赠三种类型,在全部概括遗赠中,如果遗嘱人死亡时没有法律规定为其保留一定遗产份额的继承人,则全部概括遗赠人可以因遗嘱人的死亡而当然占有遗产,无请求移交财产的必要。但在部分概括遗赠和特定财产遗赠中,受遗赠人需要向法律规定为其保留一定份额遗产的继承人要求移交其受遗赠的财产,无此继承人时向全部概括受遗赠人提出请求,无全部概括受遗赠人时,向由“继承”编确定的顺序接受继承人要求移交财产。特定财产的受遗赠人,只有在提出要求移交遗赠物之日或者移交人自愿同意移交之日,始能占有遗赠物以及享有遗赠物的孳息或利息。二为遗赠发生债权效力,如德国、瑞士等国家民法。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174、2176条规定,受遗赠人因遗赠而有向承担遗赠义务的人请求给付遗赠标的物的权利的根据,受遗赠人的债权发生于继承开始时。《瑞士民法典》第562条第1项:“受遗赠人,对执行遗赠义务人,如未特别指定执行遗赠义务人时对法定的或指定的继承人,享有请求权。”对这两种不同的立法态度,史尚宽先生有非常清晰、明确的表述,“遗赠发生物权的效力抑或仅发生债权效力,系于民法之规定及物权变动之基本的立场。采意思主义之法、日民法,物权因意思表示而变动,遗嘱应与生前行为同样,使物权意思表示而生移转之效力,故以采物权效力说为妥。而在采形式主义之德、瑞民法,动产所有权移转,须依交付,不动产所有权之移转须经登记,故除为继承人之指定或视为继承人之指定外,无论包括遗赠或指定遗赠,均仅有债权效力”。(17)因此,学者们所说的遗赠也应与继承规则相同,自受遗赠人死亡时即可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属公认法理,当无确切依据。且从法国民法典的规定也可以看出,即使其采用债权意思主义的变动模式,遗赠也并非在遗赠人死亡时当然全部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 其次,我国采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遗赠作为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理应符合物权变动模式的要求。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遗嘱生效后,是否就能发生遗赠的法律后果要取决于受遗赠人是否接受遗赠。因此,遗赠人死亡之后,受遗赠人并没有取得遗赠物的所有权,而是取得了一种受遗赠权,这种权利表现为:(1)接受或放弃受遗赠的权利;(2)请求给付遗赠利益的权利。前述第2项权利被认为是一种债权请求权,只有当受遗赠人行使该请求权并得到满足之后,受遗赠人才能取得遗赠物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18)笔者认为,即使是在受遗赠人明确表示接受的情况下,其也并非如继承那样溯及既往当然取得遗赠财产的所有权,通过遗赠来获得财产终究是属于通过法律行为进行的,因此应遵循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的规则,即不动产要登记、动产要交付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 再次,从法理上来看,遗赠与赠与合同本质相同,法律亦应当尊重受遗赠人的个人意愿。受遗赠人属于继承人范围以外的人,其本身并不具有获得遗产的法定资格,只是由于被继承人生前立下的遗嘱,使其具有了取得遗产的可能性。遗嘱反映了被继承人处分其财产的个人意愿,属于一种典型的法律行为。这种意思表示虽然在被继承人死亡时能够生效,但是否能产生遗赠的法律效果,还需要受遗赠人的意思表示予以配合,此和赠与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赠与合同需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即赠与人表示赠与,受赠人表示接受才能成立并生效。遗赠虽然是被继承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其成立生效无需受遗赠人的意思表示,但若使遗赠法律效果实际发生却不能忽视受遗赠人的个人意愿,因此《继承法》第29条才明确规定受遗赠人要接受遗赠需要有明确意思表示,如果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这是法律对受遗赠人个人意愿的尊重,并不因遗赠人为死亡之人而厚此薄彼,漠视受遗赠人的意愿而强人所难。 因此,不论遗赠的标的是否为特定物,受遗赠人都不能直接支配遗赠的标的,只能向受遗赠的义务人请求履行遗赠。(19)《物权法》将受遗赠和继承并列规定于同一条款中,并共同作为引起物权变动的特殊情况是一种违背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做法,错误地效仿了采用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国家的规范,与我国关于遗赠的相关规定以及关于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则不相协调。 四、解析遗赠扶养协议等其他方式的遗产取得过程 遗赠扶养协议制度是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总结“五保户”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开辟了自然人依靠个人财力解决养老送终问题的途径,是我国继承立法的一个创造,也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继承法律制度。遗赠扶养协议是典型的双务、有偿法律行为,与其他法律行为相比,其特殊之处在于该协议的履行分为两个阶段,即受扶养人生前受到扶养照顾和受扶养人死后得到安葬并将其财产遗赠给扶养人。依照法律规定,遗赠扶养协议的执行优先于遗嘱和法定继承。关于依据遗赠扶养协议财产何时发生转移的问题,也有不同的观点。很多学者认为,被扶养人死亡时,遗赠发生效力,扶养人当然取得遗赠财产所有权。(20)在过去民法理论关于物权变动缺乏研究和规范的情况下,有此理解也不足为奇。也有学者认为,遗赠扶养协议是代位清偿预约,一旦继承开始,预约需转化为本约,遗赠人的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应当向扶养人交付标的物,那显然意味着所有权并非当然转移。(21)笔者认为,在上文已经分析遗赠财产物权变动情形的前提下,对遗赠扶养协议引起的物权变动亦就无需再赘述,因为遗赠扶养协议是更为典型的法律行为,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该类遗产的物权变动当严格遵循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规则。 除此之外,根据《继承法》规定对遗产的处理还有多种方式,如支付继承费用、给特定继承人的特留份、缴纳税款、清偿债务、分给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非继承人和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非继承人等。这些遗产的物权变动并非在继承开始就当然发生,而是在遗产处理的过程中,通过实际的交付或登记完成的。 其中,较为特殊的当属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财产的物权变动。纵观各国立法,大部分都规定在遗产无人继承时归国家所有。如《法国民法典》第768条规定,无生存的配偶时,遗产归属于国家。《日本民法典》第959条规定,依前条的规定,未被处分的继承财产,归属国库。《瑞士民法典》第555条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无人申请继承,且继承人仍不详时,遗产归属于有继承资格的国家机关。依《德国民法典》第1936条规定,如在继承开始时既无被继承人的直系血亲亲属又无被继承人的配偶存在,被继承人死亡时所属的邦(州)的国库为法定继承人;如被继承人属于数个邦(州)者,这些邦(州)的国库均享受此遗产的相等份额。被继承人是不属于任何邦(州)的德国人者,由帝国国库为法定继承人。但对于国家以何种身份于何时通过何种程序取得遗产所有权各国规定则有所不同,如《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均规定国家是以法定继承人的身份取得遗产。《法国民法典》则规定国家取得遗产必须通过法院及检察官进行以及为此必备的清算程序,否则还有可能产生损害赔偿责任。《日本民法典》则认为继承人不明时,遗产视为财团法人,遗产管理人为法人代表,在继承人搜索公告期间届满,如有剩余财产且无人主张继承权利时,遗产当然归属于国库。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认为遗产经指定遗产管理人经过法定的程序后,仍然无人继承,在清偿债权并交付遗赠物后,归属国库,该程序的运作类似于法人的清算。(22)关于国家取得遗产之性质,又有原始取得说和继受取得说两种观点。我国关于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规定非常简单,并根据被继承人的身份不同将最终遗产归属区分为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在我国将来继承法修改时,需要对此制度进行补充和完善,比较各国规定之特点,我国可效仿德国、瑞士,将国家、集体作为特殊取得遗产的人明确规定下来,在具备无人继承且无人受遗赠这一条件时,遗产就应当归属于国家或集体,属于法律的特别规定,无需公示。作为继承法中的兜底制度,对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财产的处理当属必要且重要,在此过程中,遗产管理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起着保护、管理和依法分配遗产的重要作用,因此,我国未来继承法应当完善遗产处理的规范程序,通过法定程序和规则才能确定遗产符合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这一事实状态,最后才能收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 五、对我国遗产物权变动的整体解析和构建 如前文所述,除继承的物权变动是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发生,通过其他多数方式取得遗产都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完成交付或者登记物权变动才能发生,无人继承且无人受遗赠遗产除外。那么在实际物权变动发生前,这些遗产的权利归属如何?比如在受遗赠人表示接受并实际取得遗赠财产前,该遗赠财产是否处于无主状态下?应当归谁所有?这就需要对我国遗产的物权变动进行一个宏观、严谨的设计,使其既符合物权法和继承法的基本规范,实现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同时又能圆满完成物权变动的过程,使遗产能顺利地、符合逻辑地归属于真正的权利主体。根据该设计理念结合前面的具体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将遗产的物权变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其遗产发生第一次物权变动,由被继承人手中移转到继承人手中,此时的权利主体是一个概括的、笼统的主体——继承人,而这一权利主体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主体,既符合当然继承主义的立法体例,也避免了遗产出现无主状态;第二阶段即对遗产进行实际分配,根据法律确定的各项规则如遗赠扶养协议、偿还债务、继承和遗赠、对某些特殊人予以照顾等,依法对遗产进行具体分配,使其归属给明确的权利人,各权利主体各得其所,从而完成遗产的最终物权变动。另外如果属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在这一事实状态确定后,遗产也发生第二次物权变动,即依法归属于国家或集体。 在被继承人死亡时虽然遗产发生物权变动,已归属继承人所有,若继承人为一人则为单独所有,若继承人为多人则为共同共有。但由于继承的情况非常复杂,甚至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变化,比如继承人可能会放弃继承权,依照法律规定会有丧失继承权的人需要确认,既有遗嘱继承还有法定继承,如果有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时,在执行遗嘱时还需要给他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另外,在分割遗产时,对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但不尽扶养义务的继承人,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诸如此类等等。因此,最终的遗产分配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不是在继承开始时就能够确定的。但如果因为将来的权利主体到底会是哪些人不明确,就认为物权变动不发生显然得不偿失,因此,根据我国采纳的立法体例此时应认为遗产的物权变动已经发生,由继承人作为一个笼统、概括的权利主体取得该权利,至于最终由哪些人具体获得遗产、又能分得多少份额,只有依法对遗产进行实际分割后才能确定。 根据《继承法》规定,在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遗赠扶养协议办理。在对遗产进行具体分配实现第二次物权变动时,还要兼顾对其他人利益的特殊保护,并应注意遵守法律所确定的以下规则: 第一,继承人若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时,不得再参与遗产继承; 第二,继承开始后,由继承人按照法律规定的先后顺序进行继承,继承人如果放弃继承应在法定期限内做出明确意思表示; 第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在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在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如果不尽扶养义务的,在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第四,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适当分配给他们遗产。 第五,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遗嘱人没有为其保留遗产份额的,在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 第六,处理遗产时应当为胎儿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没有保留的应从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中扣回。 第七,继承人中如果有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即使遗产不足以清偿债务,也应为其保留适当遗产,然后再按法律规定清偿债务。 第八,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执行遗赠不得妨碍清偿遗赠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遗产已被分割而未清偿债务时,如有法定继承又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首先由法定继承人用其所得遗产清偿债务;不足清偿时,剩余的债务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用所得遗产偿还;如果只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用所得遗产偿还。 第九,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由此可见,在对遗产进行分配即发生第二次物权变动后,遗产的最终权利归属有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形:第一,支付了继承过程中需要的费用;第二,由遗赠扶养协议中的扶养人取得;第三,缴纳了税款或债务,由国家或债权人取得;第四,分给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第五,由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取得;第六,由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取得;第七,为胎儿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第八,依法由法定继承人分得相应份额;第九,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依法由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组织取得。 因此,遗产的物权变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非在继承人死亡时一次性完成,而是首先通过继承人这一概括、笼统的主体依法先行取得进行过渡,然后再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的意愿对遗产进行具体分配来完成遗产的第二次物权变动,也是最终的物权变动,从而使遗产各得其所,使各权利人利益得以实现。这一体系严谨的制度设计既圆满地解释了遗产最终归属的多种方式,符合我国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则,使继承法和物权法能够协调统一,满足立法的目的和要求,也有效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收稿日期:2015-02-20 注释: ①《物权法》第29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 ②参见戴炎辉、戴东雄:《中国继承法》,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161-162页。 ③参见《韩国民法典》,金玉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参见《意大利民法典》,陈国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⑤参见《葡萄牙民法典》,唐晓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参见《俄罗斯民法典》,黄道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⑦参见《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周友军、杨垠红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⑧参见陈苇主编:《外国继承法比较与中国民法典继承编制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 ⑨参见丘汉平著,朱俊勘校:《罗马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⑩参见郭明瑞、房绍坤、关涛:《继承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11)参见梁慧星:《〈物权法〉基本条文讲解》,载《物权法名家讲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12)参见方金华、陈文颖:《论〈物权法〉中非依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载《法治论丛》2008年第5期。 (13)参见吕波涛:《适用物权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14)参见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15)参见梁慧星:《〈物权法〉基本条文讲解》,载《物权法名家讲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16)参见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17)史尚宽:《继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18)参见曹诗权:《婚姻家庭继承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19)参见郭明瑞、房绍坤、关涛:《继承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20)参见柯瑞清:《遗赠扶养协议的性质和法律效力》,载《河北法学》1986年第2期,第37页;杨振山:《民商法实务研究(继承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 (21)参见张平华、刘耀东:《继承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96页。 (22)参见史尚宽:《继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2页。标签:法律论文; 继承法论文; 法国民法典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所有权保留论文; 遗产分配论文; 民法论文; 比较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