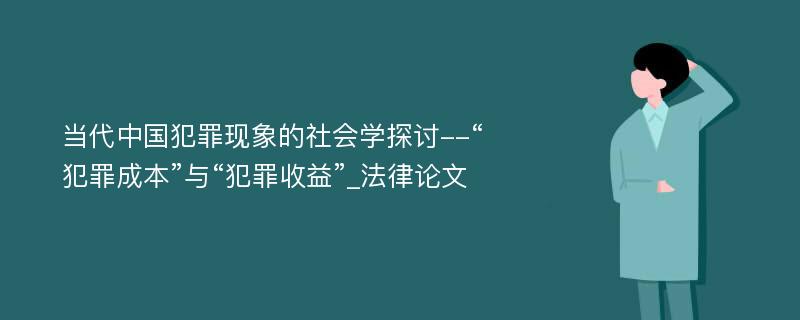
当代中国犯罪现象的一种社会学探讨——“犯罪成本”与“犯罪获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现象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四十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我国犯罪现象先后出现了四个高峰期。〔1〕第一次高峰期出现于建国初期, 第二次高峰期出现在1961年,第三次高峰期出现于1981年,第四次出现于1989年。目前我国正处在第四个高峰期的初始阶段,犯罪现象的严峻程度远未达到峰顶,仍处在大幅度上升的态势之中。前两次高峰期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后两次高峰期的出现,则几乎与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出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持续迅速增长,在此期间,犯罪现象就总的趋势而言呈逐步上升的势头。
1978年至1992年经济发展与刑事犯罪的对比
年份
人均国民收入(元)
刑事立案率(0/000)
1978
3155.6
1979
3466.6
1980
3767.7
1981
3978.9
1982
4227.4
1983
4646.0
1984
5475.0
1985
6745.2
1986
7475.2
1987
8725.4
1988 10817.7
1989 1178
18.1
1990 1267
20.1
1991 1439
20.8
1992 1736
13.5
从上表可以看出, 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从1978 年的315 元上升到1992年的1736元,每万人的刑事立案率也从1978年的5.6上升到1992 年的13.5(其峰值是1991年的20.8)。以这一现象为根据,有学者提出经济增长与犯罪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步效应”,即所谓经济与犯罪现象增长同步论。如,有学者说,“我们认为,经济和经济发展是犯罪原因规律中的决定性因素和动态过程,其作为一个整体与犯罪原因体系之中各种层次、各种因素及其过程的相互作用构成犯罪原因规律中最根本的制约与被制约与被制约关系,是影响犯罪规律的终极原因。”〔2 〕还有学者认为,“‘同步论’功在揭示了经济与犯罪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集中表现为经济对犯罪的制约关系,这种内在的制约关系是经济与犯罪之间复杂的规律性运动的必然结果。”〔3 〕同步论并非中国学者的创造,其首倡者是美国犯罪学家路易斯·谢利。他在《犯罪与现代化》一书中通过对200年间反映犯罪状况及其变化的调查资料的分析指出, 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将会给过去和现在各方面都极不相同的国家带来共同的犯罪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犯罪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代价,因而,经济发展和犯罪增加的对应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上述观点,如果只是简单地考察经济发展程度和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之所以说是“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同步论在解释诸如瑞士、日本及我国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时遇到了困难。而同步论的真正弊端在于把现象当成了本质。经济发展只是犯罪率上升的表面原因,更为深刻的原因是犯罪成本在下降而犯罪获利在上升,引发犯罪率随之攀升,当犯罪成本与犯罪获利稳定之后,犯罪率也会随之稳定。
这里所说的犯罪成本,是指罪犯在触犯了刑律之后将会引起的后果。犯罪成本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因素是将会受到惩处,另一个因素是受到惩处的可能性,不妨称之为定罪概率。一部国家的刑法,实际上就是该国的犯罪价目表,上面详尽地列举了各种犯罪行为的价格(将要受到的法律惩处),杀人、放火、盗窃、强奸、诈骗等犯罪行为将会受到何种惩处,价目表上一目了然。触犯刑法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每一个成年公民都知道的,但“价目表”上列举的法律惩处只是犯罪成本里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犯罪成本由三部分组成,除法律惩处之外,还有社会惩处和良心惩处,可以以下式表示。
C=(L+S)HP
C—犯罪成本
L—法律惩处
S—社会惩处
H—良心惩处
P—定罪概率
一种犯罪行为是否实施,不仅与犯罪成本有关,还与因实施犯罪而给罪犯带来利润的多寡有关,其关系可以以下式表示。
B=I/C
B—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I—犯罪获利
C—犯罪成本
显然,犯罪成本愈高,犯罪获利愈小,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愈小。反之,当犯罪成本下降,犯罪获利增大时,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将会增大,从宏观上看,就是犯罪率上升。下面我们就对影响犯罪成本的四项因子逐一进行分析。
从法律惩处来看,如果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法治社会,法律惩处的强度也是相对稳定的。但我国刚刚进入现代化法治社会,许多法律制度还不十分完备,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也不是很高,法律惩处的弹性较大。同样的违法犯罪行为,有些受到法律惩处的强度高,有些受到法律惩处的强度低。尤其是当犯罪十分猖獗的时候,国家往往会作出“严打”的决定。在“严打”期间,对犯罪的法律惩处要高于一般时期,换句话说,“严打”期间的犯罪成本要高于平时。因此,“严打”期间及稍后的一段时期,由于犯罪成本的提高,犯罪率会下降。例如,1981 年、 1982年的刑事案件立案率分别为万分之8.9和7.4。1983年9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六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接着便在全国开展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到1984年,刑事案件立案率下降为万分之5.0。这之后, 全国刑事案件立案率虽开始逐渐回升,但直到1986年“严打”结束时,刑事案件立案率仅为万分之5.2,与改革开放之前的1976年的刑事案件立案率万分之5.2恰好一样。这说明,通过加大法律惩处的力度来提高犯罪成本,以遏制犯罪率的上升,是有一定效果的。
再来看看社会惩处。所谓社会惩处,是指除受到法律惩处之外的其他一切来自社会的惩处,这些惩处通常包括党纪、政纪、校纪、厂纪的处分,刑满释放之后受到的社会冷遇,如机会的丧失、生活空间的狭小等等。在任何社会里,罪犯受到的惩处都包括社会惩处,而不仅仅是法律惩处。也可以说刑法所标明的犯罪价格还不是完全的价格,而仅仅是部分的价格。例如,有的国家规定有过刑事犯罪记录的人不得担任国家公务员。也就是说,罪犯不仅要被关进监狱剥夺行动自由,释放出来以后还要被剥夺某些机会,如不得担任公务员。但总的说来,在法治社会里,犯罪成本中所包含的法律惩处占的比重较大,社会惩处只占较少的一部分。即使是社会惩处那一部分,也大都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公布于众。中国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虽然也有刑法,有公检法系统,但整体来说并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法律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远不如其他社会规范的约束力有效和有力,也就是说,犯罪成本中社会惩处的成分大大高于法律惩处。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作为这一社会最高司令部的中央政府通过各级组织下达指令,使全社会成员的行动能大体上保持一致。这样的高度组织化如果用于军事行动,无疑比任何类型的社会都要有效。遗憾的是,这套从战争年代沿革下来,并曾十分成功的高度组织化社会,在和平建设年代并未取得同样辉煌的成功。原因固然很多,但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里,组织成员的流动是十分困难的。人员的频繁流动使组织产生不稳定性,对组织化程度有一种分化、瓦解的作用。因而在高度组织化社会里,人员的流动由组织指派和分配,自由的流动受到诸多限制。限制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户籍制,一条是人事档案制。户籍制限制人们作地域流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流动,都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人事档案制限制人们作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流动,即使是同一地域内的流动也是十分困难的。在户籍制与人事档案制的双重作用下,人们的活动空间被压缩在一个十分狭小的领域里,人们之间的交往是相当“透明”的,不仅仅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也知道你过去干过些什么。一个人一旦触犯社会规范(不仅仅是法律),人事档案里将会有完整的记载,单位同事会知道,左邻右舍也会知道。在这种体制下,犯罪成本是极高的。被判刑关进监狱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为严重的是他将受到严厉的社会惩处。试列举一部分如下:
1.被开除公职(如厂籍、干籍等),刑满释放后(以前有一个专有名词,称之为刑满释放犯,仍然是“犯”),他将失去稳定的就业机会,经济收入会下降很多,甚至有可能陷入生活困境。如果原籍在农村,有可能会被取消城市户口,遣送回原籍。
2.他将失去许多人生的机遇。由于他有过“前科”,他被提干、晋级、升职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3.他将承受沉重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家庭也来自他生活圈子中的人,被人议论、遭人白眼,因此对他本人来说,实际上已很难谈得上做人的尊严和健全的人格。
4.他的家人会因此而受到牵连,他的儿女会遭人歧视,他的近亲会因此而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留下不光彩的一笔。
如此高昂的犯罪成本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但法律惩处、社会惩处还不是犯罪成本的全部,犯罪成本还包括良心惩处。在三项惩处中,法律惩处与社会惩处是一种外在惩处,它须借助于政权、社会力量才能得以实施。良心惩处则是一种内在惩处,它借助的是罪犯本人内心的力量,惩处的表现形式是使罪犯产生焦虑、不安、悔恨等情绪体验。良心惩处有两个特点。第一,法律惩处、社会惩处对罪犯并不是现实的惩处,而是一种潜在的惩处,只是被定罪之后,潜在的惩处才会转变成现实的惩处。因此有些人是抱着不会被定罪的侥幸心理去铤而走险的。良心惩处在犯罪行为实施之后(有时甚至在实施之前)是一定会产生的。第二,不同的人有同样犯罪行为,他们受到的法律惩处和社会惩处的强度是相差无几的,但良心惩处则大不相同,很可能不同的人有同样的犯罪行为,而所受的良心惩处的强度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良心惩处的力量来源于本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罪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社会倡导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基本一致,他受到的良心惩处强度最大,这时他的行为与价值观相背离、相冲突。如果罪犯的人生观、价值观与社会倡导的人生观、价值观完全不一致,他几乎不会受到良心的惩处,因为这时他的行为与价值观基本吻合。当罪犯的人生观、价值观与社会倡导的相一致时,此时良心惩处的强度为1。当罪犯的人生观、 价值观与社会倡导的不相一致时,此时他受到的良心惩处为0。因此,良心惩处的强度在0—1 之间。
最后,再来看看影响犯罪成本的第四个因素:定罪概率。定罪概率是指某种犯罪行为实施之后,罪犯被司法机关定罪并受到法律惩处的可能性大小。当所有罪犯都会被定罪时,定罪概率为1。 如所有罪犯都逃之夭夭,司法机关不管不问,定罪概率为0。因此,定罪概率介于0—1 之间。
从犯罪成本模型:C=(L+S)HP来分析,法律惩处、社会惩处、良心惩处的强度越高,犯罪成本越高;另一方面,犯罪成本高有利于遏制犯罪,但并不等于说越高越好。因为过高的犯罪成本有可能造成两种后果,一种严刑峻法施暴政,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代的“文字狱”,这些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有害的。另一种是万马齐喑、死水一潭,如我国六七十年代,当时实际上是以高强度的社会惩处为手段,以牺牲人们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为代价,来换取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在当今世界社会现代化的潮流中,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历史也不可能倒转。
犯罪成本还不是影响犯罪率的唯一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犯罪获利。犯罪获利是指犯罪行为实施之后能给罪犯带来的好处或利益,这种利益有可能是物质性的,如金钱、财产,有可能是社会性的,如权力、地位,也有可能是心理性的,如报复心理的满足。一般来说,犯罪获利主要是物质性的利益。前面已经提到过,犯罪行为实施的可能性可以用公式:B=I/C来表示,一般来说,犯罪获利要大于犯罪成本,犯罪获 利(I)与犯罪成本(C)之比越高,犯罪行为实施的可能性越大。
在经济发展时期、高额的犯罪获利机会大大增加,在客观上刺激了犯罪率的上升。在这一意义上,经济增长与犯罪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步效应”。但并非总是如此。如封建社会所谓的“治世”时期的犯罪率并不高于“乱世”时期,前者是经济增长时期,后者是经济衰退时期。因此,要分析犯罪率上升的原因,仅仅从经济因素出发是远远不够的,所谓“同步论”有着十分严重的缺陷。只有同时考虑犯罪获利与犯罪成本才能全面把握犯罪率上升的原因。笔者认为,我国自1978年以来犯罪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的原因有二,一是犯罪获利在增长,二是犯罪成本在下降。
在计划经济时代,金钱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在那个时候,人们的经济收入十分透明,如果有人以非法手段获取经济收入,过着一种与他合法收入水平不相称的富裕生活,很快就会被单位领导、同事和邻居发觉。即使不被发觉,他也会发现这笔收入既不能用来买肉,也不能用来买布,甚至不能用来买粮食,因为这些东西是凭票供应的。在那个时候,犯罪获利不大,加上非常大的社会惩处和很高的定罪概率,较低的犯罪率是自然而然的。随着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犯罪获利的机会大大增加,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上双轨制的存在,使权钱交易成为可能,于是出现一大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的经济犯罪分子。
2.市场管理体系不健全,打击力度低,产生大批制售伪劣产品、坑蒙拐骗的犯罪分子。
3.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犯罪现象,像计算机犯罪、信用卡恶意透支、信用卡冒用、偷占他人移动电话频率等等。
4.对外交流日益增多是与出入境管理的宽松分不开的,同时也导致走私贩毒的猖獗。
5.我们在大力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的同时,西方国家一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涌入我国,色情、暴力的书刊与音像制品泛滥,卖淫嫖娼屡禁不绝。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会有与之相应的犯罪现象,计划经济是如此,市场经济也不例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犯罪现象的主要特征就是当市场产生某种需要时,就会有人千方百计去满足这种需要,只要满足市场需要这种行为是有利可图的。当某种市场需要超出了社会制定的规则(这种规则常常以法律的形式出现)范围,那么满足这种市场需要的行为便会被定为犯罪行为。当实施犯罪行为会给犯罪分子(或犯罪团伙)带来足够大的利益(犯罪获利)时,就一定会有人不顾惩处而去铤而走险。如贩毒,犯罪获利高达百分之几千,尽管惩处十分严厉,仍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满足吸毒者的需要。由于市场经济具有这一特征,因此,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犯罪获利会大大高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犯罪获利,而且打击越严厉,犯罪获利受市场规律调节亦水涨船高。这样,就使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犯罪率会高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犯罪率。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高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必然会出现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市场经济的犯罪获利比较大,从表面现象看,也就是犯罪率与经济增长“同步”。
正如前已所述,实施犯罪行为不仅与犯罪获利有关,还与犯罪成本有关。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仅犯罪获利在增大,而且犯罪成本也在下降。即,社会惩处趋近于零,良心惩处大大减弱,定罪概率大大下降。从犯罪成本的角度看,我国从“人治”走向“法治”,就是以法律惩处取代社会惩处的地位,推行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惩处趋近于零是社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人员流动的自由度大大增加,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提倡公平竞争,而最重要的竞争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因此,人员流动是市场经济得以实行的必要前提。人员流动的频率与规模的增加,使得社会惩处的基础——单位制悄然解体,档案制、户口制的功能日渐衰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再来看良心惩处。良心实际上是社会所倡导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内化,它成为人们行动的内心准则。良心不是超历史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与历史环境、民族传统相联系的产物。例如,在农业时代,知识和技术与一个人的人生阅历关系极大,年岁越大可能意味着知识越丰富、技术越精湛。因此,在农业时代,“敬老”会成为一种很重要的价值观。但在工业时代,尤其是后工业时代,知识的更新频率极快,技术换代的周期十分短暂,因此年岁与知识、技术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时,“敬老”会成为一个并不重要的价值观。经济体制也是如此,与计划经济相联的有一整套社会倡导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它们被人们接受并内化之后,成为人们的行动准则。人们一旦违反这些准则,即使不被别人发现,也会感到内心不安,这就是所谓良心惩处。与市场经济相连的也有一整套社会倡导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其中有些与计划经济的基本一致,但大多数不会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那一套人生观与价值观逐渐失去行动准则作用,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并未完全建立起来,有些即使已经被建立起来了,也未内化为人们的行动准则,旧的不起作用,新的不具有足够的约束力,人们处在一种所谓的“价值真空”里,这就是良心惩处大大减弱的原因。良心惩处减弱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法律惩处的最终目的是教育人们遵纪守法,树立法律意识。
最后再来看看定罪概率。法治的建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不断惩处罪犯的同时,也告诉了人们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如果定罪概率很低,在客观上助长了人们的犯罪侥幸心理。恰恰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定罪概率太低,究其原因有四。一是犯罪面比较大,司法人员有限,只能择其严重者惩处之。二是“人治”遗风尚存,说情风、关系网使许多罪犯成为漏网之鱼。三是有些司法人员素质太低,与犯罪分子勾结,沆瀣一气。四是惩处力度忽大忽小,严打期间大,平时小,未能保持一贯性。
综上所述,犯罪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并不如“同步论”者所分析的那样简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犯罪率呈逐年上升态势的原因,一是犯罪获利增加,二是犯罪成本下降。遏制犯罪率上升趋势的措施主要是重建社会道德体系,同时提高定罪概率。
最后要说明一点的是,本文的犯罪行为模型是基于“理性人”这一假设,即人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有事先认识,并能对后果中利益与代价有理性的比较。要特别注意的是,人并非都是“理性人”,“理性人”也并非时刻都能保持“理性”,如在突发事件中打人或杀人,即是失去了“理性”。因此该模型有一定的局限性。
注释:
〔1〕参见王智民、黄京平:《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第49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王智民、黄京平:《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第292页。
〔3〕肖剑鸣、皮艺军主编:《犯罪学引论》,第500页,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