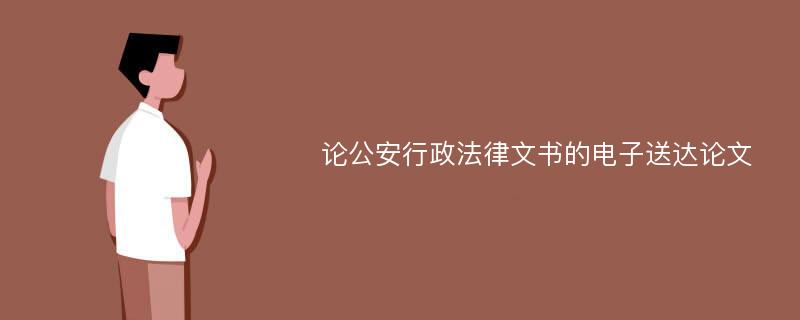
论公安行政法律文书的电子送达
曾文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摘 要】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36 条第3 款新增了公安行政法律文书的电子送达内容,这契合了电子政务迅猛发展的现实需求。因该条款规定内容的笼统性和模糊性,公安机关采取电子送达,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受送达人的同意是电子送达必备的主观要件,在此基础上,电子送达可以成为公安行政法律文书优先的文书送达方式。 但基于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特别保障,并非所有的公安行政法律文书均可电子送达,另外,电话送达作为电子送达的例外方式应当谨慎采取。我国电子送达的成功采用到达主义标准,这要求公安机关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固定送达日期。电子送达的日渐普遍,也对公安信息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关键词】 公安机关;行政法律文书;电子送达;电话送达
文书送达是公安行政执法办案中极其重要的事项,其不仅具有程序意义,而且更具有实体意义,即通过文书送达,行政相对人方能知晓行政行为的内容,许多行政行为的生效只有经送达行政相对人受领方能生效。 相比较授益性行政行为,负担性行政行为如无决定文书的送达,则不能生效;行政处罚是典型的负担性行政行为,行政处罚决定书只有送达给被处罚人后,才能对其发生法律效力。 在我国,无论是行政执法中的文书送达,还是行政诉讼中的文书送达,只要法律没有特别规定,均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文书送达的规定。 ① 如《行政处罚法》第40 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行政诉讼法》第101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关于期间、送达、财产保全、开庭审理、调解、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简易程序、执行等,以及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执行的监督,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0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7 条之规定,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中作出的法律文书原则上应当直接送达,而且应当是“当场交付当事人”。直接送达又分为直接交付受送达人本人和由特定主体代收两种形式。 ② 值得注意的是,《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36 条规定的直接送达中的代收主体为“(受送达人)的成年家属、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员或者其居住地居(村)民委员会”三种,但《民事诉讼法》第85 条规定的代收主体仅限“(受送达人)成年家属”,二者规定不一致,法律没有授权部门规章对送达方式另行作出规定,因此,公安机关在文书直接送达中,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85 条规定,而不宜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36 条规定。 只有在直接送达客观不能时,公安机关方能采取留置送达、代为送达、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等方式送达行政法律文书。随着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电子政务的兴起也要求文书送达方式适应时代的需求,这不仅便民,也更加高效。对此,公安部参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电子送达的有关规定,在2018 年《程序规定》修改中增加电子送达内容,即在原有的代为送达和邮寄送达条款上增加“经受送达人同意,可以采用传真、互联网通讯工具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的表述,形成了现有《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第36 条的第3 款。这一条款的法律宣示意义大于具体操作意义, 公安机关在电子送达中的一些具体事项,仍需适用《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本文就公安行政法律文书的电子送达所须注意的事项进行逐一说明, 希冀能为公安行政执法文书送达工作的规范化建设略尽绵薄之力。
一、 电子送达应当以受送达人同意为前提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36 条第3 款在表述上和《民事诉讼法》第87 条第1 款如出一辄,均为“经受送达人同意,可以采用传真、互联网通讯工具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从条款规定我们能够看出, 电子送达系公安机关裁量决定的送达方式,但这种裁量决定必须以“受送达人同意”为前提。 电子送达的这一主观要件在有些地方的司法实务中已显得无足轻重, 如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其《诉讼平台审理规程》 第32 条将电子送达作为诉讼文书的首选送达方式,且并非以“受送达人同意”为要件, 这种做法不仅不合法, 而且在实际中危害极大,不能为公安行政法律文书的电子送达所取。因为相对于行政相对人, 行政机关在信息化水平上显然更具优势,行政机关如无约束,当然愿意以更为简洁便捷的电子方式送达文书, 从而将信息成本转嫁给行政相对人。电子送达的首要目标是方便当事人,次要目标才是方便行政机关,我们不能本末倒置。 “受送达人是否同意选用电子送达方式, 其实质是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接收电子送达自我评价后得出的选择”[1],行政机关必须尊重受送达人的这种选择,而不能一厢情愿地径直采取电子送达方式, 从而使得电子设备使用能力不足的受送达人“变得更加艰难或者给当事人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很显然,《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36 条第3 款中的“受送达人同意”这一主观要件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能直接影响到电子送达能否采取的因素, 其背后则是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的保障。 为了凸显“受送达人同意”的法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6 条明确规定,“受送达人同意采用电子方式送达的, 应当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予以确认”,因此,受送达人的同意应当是明示的, 这意味着受送达人提供的传真号、 电子信箱、QQ 号、微信号等电子文书接收地址应当是经其明示同意接收公安行政法律文书的, 否则即使是受送达人在之前的办案程序中提供了电子地址但并未明确表示以其接收文书, 公安机关亦不得采取电子送达。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6 条规定,“受送达人同意采用电子方式送达的,应当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予以确认”,因为电子送达地址确认书一般是在诉讼开始之初就已填写,这意味着《民事诉讼法》 司法解释实际上确立起一种明示概括同意的送达地址确认, 即电子送达的地址原则上以填写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为限,诉讼中不得更改,这一理念也值得公安机关送达行政法律文书所借鉴, 即公安机关征得取得行政相对人一次同意即可, 无需每份行政法律文书的电子送达均要征求行政相对人一次意见,从而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 但是,公安机关采取电子送达,是否一定要如法院那般制作《电子送达地址确认书》呢? 笔者认为,司法解释严格意义是统一各地法院的司法活动,并不必然对行政机关适用,只要公安机关通过证据收集和固定,如书面签字、音视频记录等方式证明了“受送达人同意”这一内容,公安行政法律文书就能够电子送达, 公安机关并不需要一定制作《电子送达地址确认书》。
二、电子送达可以是文书送达的优先方式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是将电子送达方式与“委托其他公安机关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一并规定在第36 条第3 款之中,这样第36 条的条文结构上就形成了“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电子送达—公告送达”的公安行政法律文书送达方式的次序, 那是不是电子送达只对委托送达和邮寄送达的替代送达方式呢? 笔者认为,各地公安机关不能囿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第36 条所规定的送达方式次序的理解,必须从电子送达的本质意义出发来看待这一新型的文书送达方式。 毫不客气地讲,《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36 条在立法结构上是与《民事诉讼法》不一致的,根据《立法法》第80 条的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 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民事诉讼法》赋予了电子送达较高的法律地位,这并不是《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所能削弱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关于送达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不一致时,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从《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方式的法律条文(第85 条规定直接送达、第86 条规定留置送达、第87 条规定电子送达、第88 条规定代为送达和邮寄送达以及第92 条规定公告送达等) 来看,电子送达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送达方式, 尽管从其条文顺序来看, 电子送达条款位于直接送达和留置送达之后,但是我们不能由此理解为只有直接送达和留置送达不能时,才可以电子送达。 如果这样理解的话,电子送达将丧失其应有的制度优势,因为在现实中,绝大多数的文书经由直接送达和留置送达均可完成当事人的“受领”。 从性质来看,电子送达应该是与传统送达相并列的新型送达方式,传统送达的次序规则并不能对电子送达发生效力。 从现实操作来看,为顺应信息化的发展潮流,公安机关只要具备电子送达的技术能力,就可以征得受送达人的同意,优先采取电子送达方式。我们完全可以确立起“先电子送达、再传统送达”的公安行政法律文书送达理念,使得电子送达成为公安机关优先适用的送达方式,只有“待电子送达不能时再依此适用传统送达方式”[2]。
三、 并不是所有的公安行政法律文书均可电子送达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36 条是关于公安行政法律文书送达的一般规定, 其新增的电子送达也适用公安行政案件办理各个阶段的文书送达,因此,本规章中涉及文书送达的其他内容均可准用电子送达条款。从上文的分析结论来看,电子送达是与传统六种送达方式并列的, 而且可以作为公安机关优先采取的文书送达方式;但我们能否从“经受送达人同意,可以采用传真、互联网通讯工具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 这一条款表述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的公安行政法律文书只要“经受送达人同意”,公安机关就能采取电子送达呢? 仅从该条款的字面理解,似乎是不存在着任何障碍。一切的公法制度包括文书送达制度的最根本意义都在于保障民众权益,这是从一般意义而言。但从具体制度的设计初衷来看, 电子送达制度实际上是追求了一种行政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 即其一定程序上构成了对当事人程序保障的威胁。 《民事诉讼法》正是基于这种程序正义的理念,防止“单纯的电邮送达可能会剥夺当事人在语言交流中获得的受尊重的感觉”[3],故在第87 条明确规定,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这三类法律文书不得电子送达, 其核心理由就在于这三种法律文书乃是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最重要者,于此,立法者宁要法律的安定和庄严,不要文书送达的便捷和高效。笔者认为,公安行政法律文书和司法文书具有共同的特质, 都是为了法律的实施而制作, 公安行政法律文书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载体,也是考量其行政执法行为合法性的重要证据,行政法律文书是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 不同的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不同,“内容复杂、 后果重大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而且这些行为的书面形式,具有要式性和规范性的统一,即“文书格式统一,书写标准统一,制作和适用符合程序规定”[4],一般需要纸质版打印出来加盖公安机关印章, 方能使得相应的行政行为生效,因此,《民事诉讼法》排除特定文书电子送达的这一立法思想也值得公安机关送达行政法律文书所准用, 一些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较大的行政法律文书不得电子送达。具体而言,绝大多数的公安行政法律文书特别是程序性法律文书,公安机关都可电子送达,但公安行政许可决定书、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收缴追缴清单等,建议不宜电子送达,而应当按照传统送达方式送达。有的部委制定部门规章时,亦有专门规定, 将特定行政法律文书排除于电子送达之外,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 第74 条就有此内容的规定。 ① 该条第(4)项规定,“除行政处罚决定书外,经受送达人同意,可以采用手机短信、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账号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电子方式送达执法文书”。 当然,受送达人身份的不同,也可能会影响到能否采取电子送达, 如即使是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处罚人和被侵害人都是受送达人,对被处罚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不能电子送达,但对被侵害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在其明示同意的前提下未必不能电子送达。 《民事诉讼法》第87 条将调解书亦视为不得电子送达的文书情形,但行政机关制作的调解书和法院制作的调解书法律效力明显不同,前者本质上是一种民事合同,不具有申请法院直接执行的效力, 而后者经由法院的司法确认,本身即具有了像判决书、裁定书那般的司法既判力,具有可直接执行的效力。 对于民事合同来说,电子化已是普遍现象,只要当事人有约定,将其电子送达是完全符合民事交易习惯的, 不能因为行政机关的主持达成民事合同, 就改变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实质。因此,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 条,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案件,进行治安调解,对双方当事人达成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可以基于当事人同意采取电子送达方式。《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78 条规定,公安机关进行现场调解,“当事人基本情况、主要违法事实和协议内容在现场录音录像中明确记录的, 不再制作调解协议书”,这一条款实际上也强化了《治安调解协议书》电子化制作及送达的倾向。
四、公安行政法律文书建议不宜电话送达
在执法办案实践中, 不少民警存在着以电话通知代替文书送达的习惯,这是违法的。对此需要明确的是,电话通知不是电子送达。 在现实中,不仅是行政机关,而且一些司法机关,仍将电话通知视为电子送达的具体样态,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① 如有人认为,“电话送达是指主审法官或书记员针对当事人地址在本地的或者代理人在本地的, 电话通知当事人或律师至法院领取诉讼法律文书。 包括直接用电话通知法律文书内容或通知至法院领取法律文书”。 参见刘生华:《民事诉讼电子送达浅析》,载《江苏经济报》2017 年12 月6 日,B3 版。 公安机关在执法中,电话通知当事人相关事项已是工作常规,但电话通知本身并不是一种文书送达方式, 其往往只是文书送达的前置辅助手段, 即通过电话告知受送达人将要进行文书送达。 电话通知可以是所有文书送达的随附,但不是送达;电话通知的实施,并不丝毫代表文书送达义务的履行。 《民事诉讼法》只明确列举了“采用传真、电子邮件”方式的电子送达,没有电话送达。 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首次规定了电话送达, 将其视为电话送达成为文书送达的一种新的方式。 ② 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推广电子送达的建议的答复》中也指出,“部分法院已拓宽了电子送达的途径,通过微信、电话、短信等方式送达。 下一步,可以考虑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增加微信、QQ、电子邮箱、传真号码等电子送达选择项,更好地引导当事人选择电子送达”,也明确了电话送达这一电子送达类型。 《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14 条规定,“对于移动通信工具能够接通但无法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的,除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外,可以采取电话送达的方式,由送达人员告知当事人诉讼文书内容,并记录拨打、接听电话号码、通话时间、送达诉讼文书内容,通话过程应当录音以存卷备查”,这表明电话送达是在其他电子送达客观不能情形发生采取的新的送达方式, 即送达人员向受送达人电话语音形式宣读法律文书内容。 电话送达只需“移动通信工具能够接通”,但其他的电子送达则必须电子设备“能够确认收悉”,“接通”和“收悉”显然具有不同的内涵,“收悉”不仅要求“接通”,而且要求文书能够以数据化形式整体送达到受送达人处。由此可见, 电话送达这一电子送达形式较之其他电子送达形式,实施的电子技术设备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忽视受送达人的程序权利保障, 故其只有万不得已情形方得采取。例如,传统的老式功能手机无法实现其他电子送达,但却可是完成电话送达。 2018 年公安部修改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将《民事诉讼法》有关电子送达的内容予以吸收,尽管也没有排斥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有关电话送达的内容,但为了法律文书送达的完整性和庄严性起见, 笔者建议,公安机关在公安行政案件办理中,除非情况紧急或者迫不得已, 一般不宜直接采取电话送达行政法律文书。
2.2 溶栓前后NIHSS评分及发病90 dmRS 结果(表3)表明:两组患者在溶栓前、溶栓24 h、溶栓7 d的NIHS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发病90 d mR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五、电子送达的日期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固定
电子送达和其他送达方式相比的最大优势是迅捷及时,几乎是瞬间到达,但是电子送达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是否就是送达日期呢?这其实涉及到两个时间点的抉择问题,即公安机关发出行政法律文书的时间和受送达人阅读行政法律文书的时间,哪一时间为送达成功的标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第36 条第3 款对此语焉不详,“经受送达人同意,可以采用传真、互联网通讯工具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 这一条文表述只说明了公安行政法律文书电子送达的允许性, 但并未讲清电子送达到何种程度意味着公安机关送达义务的履行。 公安机关在部门行政法无特别规定下,只能准用《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民事诉讼法》在立法上采到达主义立场[5],认为只要电子化法律文书到达受送达人的接收系统之中, 就视为电子送达的成功, 至于受送达人是否阅读以及能否阅读在所不问,这一立场鲜明地体现在第87 第2 款的规定中,即“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尽管从技术角度来讲,电子化法律文书发送成功, 往往意味着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接收成功,但电子技术的不完美性③ 这主要体现为电子送达基本上为异步传输方式,即并不要求发送方和接收方的时钟完全一样,字符与字符间的传输是异步的。 总会导致发送和接收的不同步性,这种情形下,我们应当允许受送达人对其予以抗辩, 当其抗辩理由成立时应予采纳,因此最高法2014 年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5条第二款以“但书”的方式肯定了“受送达人证明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与人民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不一致的, 以受送达人证明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为准”。不管是《民事诉讼法》还是其司法解释,都排斥阅读主义的送达成功标准,但为了保障受送达人知悉法律文书业已到达其特定电子接收系统,笔者建议,附随的电话通知必不可少,这也不会太多地增加送达机关的送达负担。 文书送达是公安机关的程序义务, 公安机关应当对文书送达成功承担证明责任,这意味着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固定“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 固定电子送达日期方式是多样的, 如对手机短信可以拍照并记录接收的手机号码, 对电子邮件可以保存送达邮件内容特别是发送成功网页, 对传真可以保存传真原稿图像打印传真发送确认单, 对QQ 和微信截屏保存等,以此固定传真、电子通讯工具等送达时间和结果。另外,电子送达是公安行政办案中的程序性内容,也应在卷宗中表现出来,即公安机关应当将电子送达的状态和结果打印、存卷。
六、电子送达对公安信息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采用传真、 电子通讯工具等方式送达实际上是将公安行政法律文书通过数字信息方式传递, 但电子送达始终面临着“技术的无限性、不稳定性与法律的有限性、稳定性之间的对立”,如“如果有人非法侵入电子信箱对数据进行截收、删减、篡改、伪造法律文书就会使其受到破坏……所以安全性就成为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中的首要问题”[6];同时,随着电子政务的发展, 电子送达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高效便民的文书送达方式, 因此公安机关建立专门系统平台送达法律文书,实有必要。 在现阶段,有条件的公安机关可以建立专门的电子送达平台, 或以执法服务平台为依托进行电子送达, 或者采取与大型门户网站、通信运营商合作的方式,通过专门的电子邮箱、 特定的通信号码、 信息公众号等方式进行送达。 电子送达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制度、一种理念, 这是新时代下公安行政法律文书送达的必然发展, 各地公安机关应当从严格公正文明理性执法的高度,将其融入到“四项建设”特别是基础信息化建设之中,以便更好地尽职履责、服务人民。
从图8中可以看出,在超高加入不平顺之后,各轴向加速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波动,尤其是竖向加速度波动最为明显,而纵横轴向加速度虽然有一定的波动,但是基本上都是在未加不平顺的加速度曲线上下一定范围内波动,其中在曲线路段,不平顺使得各加速度的波动显著增大。所以,实际公路运营期间,当曲线路段出现问题时,要及时进行修整,否则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此外,汽车行驶时还可以对其轮胎的受力与滑动进行监测,对公路线形存在不合理的位置进行修改,减小车辆的损耗,进而提高汽车行驶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参 考 文 献】
[1]吴逸,裴崇毅.我国民事诉讼电子送达的法律问题研究[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11.
[2]宋春龙.电子送达的理论反思及其制度完善[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6):46.
[3]宋朝武.民事电子送达问题研究[J].法学家,2008(6):128.
[4]宋大涵.行政执法教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271.
[5]奚晓明,张卫平.新民事诉讼法条文精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188-194.
[6]李智喻,喻艳艳.论“互联网+”时代我国的电子送达制度[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6):46.
On the Electronic Delivery of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ve Legal Documents
Zeng Wenyuan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The paragraph 3 of the article 36 of the Procedure Spree for the Handling of Administrative Cases by Public Security Organs adds the content of electronic delivery of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ve legal instruments,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realistic needs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government. Because of the generality and ambiguity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provision,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shall apply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when they take electronic delivery. The consent of the person served is the subjective element necessary for electronic service, on the basis of which electronic service can become a priority instrument service mode of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ve legal instrument. However, based on special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s, not all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ve legal instruments can be delivered electronically, in addition, telephone delivery as an exception to electronic delivery should be taken with caution. The success of electronic delivery in China adopts the arrival standard, which requires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to take active measures to fix the delivery date.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electronic delivery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ecurity informationization.
【Keywords】 public security organ; administrative legal document; electronic delivery; telephone delivery
【中图分类号】 DF79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101(2019)04-0053-05
【收稿日期】 2019-06-10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9 年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食品药品“两法”衔接中的证据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9JKF31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曾文远(1981-),男,新疆阿克苏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刑事科学技术学院讲师,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孙雯)
标签:公安机关论文; 行政法律文书论文; 电子送达论文; 电话送达论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