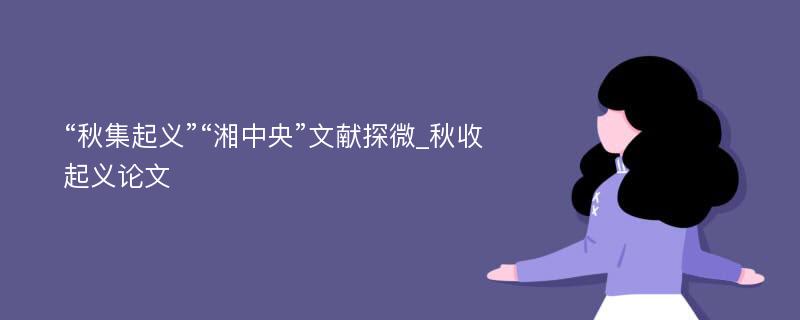
关于秋收起义文献《湖南致中央函》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秋收起义论文,湖南论文,文献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0)01-0016-08
研究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有一份文献是不可以忽略的,就是1927年8月20日的《湖南致中央函》①。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将此信作为附件收入,并注明“从内容看,本文即毛泽东写给中央的信”[1](P354-355)。稍后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1883-1949),在8月20日条下引述此函时也说明,这是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写给中共中央的信。[2](P211-212)然而,几乎同时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军事文集》却没有收入这一重要文稿,且此信亦不见于毛泽东的其它著作专集。② 当然,不论文集和专集,都是作者文稿的精粹选编,并非将所有文稿网罗无遗。但仅就“致中央函”而言,未能收入文集或专集的原因,主要在于对作者的认定存在疑问,即有人认为毛泽东是此信的作者,也有人觉得,仅凭现存文本无法断定信一定是毛泽东所写。③ 那么,“致中央函”是否出自于毛泽东之手?倘若此信果为毛泽东所写,它又有着怎样的理论和历史价值?围绕上述问题,笔者重新对有关资料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一、毛泽东确为“致中央函”的作者
现存“致中央函”为《中央通讯》第3期节录,原题为《湖南致中央函》,无抬头和落款,编者对信件内容作了删节,仅选登了(三)、(四)两个部分,约900余字。加上被省略的(一)、(二)两部分,推测应为千余字的长信。因信的原件不存,对作者的认定只能围绕信件内容及相关因素展开。
(一)毛泽东为“致中央函”作者的可能性分析
1.毛泽东是有可能代表湖南省委给中央写信的人之一
此信既是写给中央的信,写信的必是能够代表湖南省委与中央直接联系的人,有这样资格的人屈指可数。从这一时期湖南省委组成情况的变化中可以找到相关的线索。
1927年5月上旬,湖南区委改称湖南省委,夏曦任省委书记,省委委员有何叔衡、郭亮、易礼容、杨福涛、陈佑魁等11人。5月21日即“马日事变”发生当天,夏曦以到武汉向中央汇报为名出走,省委开会公推郭亮为书记,主持日常工作。“马日事变”后,湖南省委与各地党组织遭严重破坏。6月24日,中央派毛泽东回湘任省委书记,指定了19人组成的新省委,委员包括夏明翰、易礼容、何资深、彭公达、罗章龙等。7月初,中央召毛泽东回武汉,省委书记一职由易礼容暂代。随后,中央复信湖南省委,告湖南省委负责人已经常委会重新审查,决定易礼容为书记。八七会议上,中央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会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两位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彭公达回湖南传达会议精神,并全权负责改组湖南省委,指定彭公达为新的省委书记。8月16日,湖南省委在长沙沈家大屋召开会议,对省委进行改组,新省委由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向钧、谢觉哉、何资深9人组成。18日,省委选举彭公达、毛泽东、何资深3人为常委。30日,省委常委开会决定了秋收暴动的最后计划,并成立起义的领导机构:一是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一是由各县党组织负责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易礼容为书记。
从省委变动情况看,有可能与中央直接联系的不外乎现任省委书记彭公达,前省委书记、现省委常委毛泽东,前省委书记、现省委委员易礼容,现省委常委何资深数人而已。1927年10月8日,彭公达曾就湖南秋暴经过给中央写出长篇报告,述秋收起义筹划过程甚详,但没有提到他本人8月20日写信给中央。易礼容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也从未提出他曾写信给中央。何资深8月19日受湖南省委之派向中央汇报暴动准备情形,[3](P49-50)大概22日或23日抵达武汉,23日中央即根据湖南省委的报告和何资深的口头报告写了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1](P350)据此推断,此时何资深本人正准备赴汉或赴汉途中,也不应是写信人。
毛泽东曾任湖南省委书记,八七会议刚刚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时正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指导湖南省委改组和秋收暴动工作,“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1](P483-484)。有一件事足以证明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中的特殊地位。8月16日改组湖南省委的会议,由彭公达主持,毛泽东因故缺席。事后,“改选的结果报告泽东,征求他的同意之后,再报中央”[3](P96)。毛泽东、彭公达返回湖南后,中央曾在22日来信催促他们报告暴动准备情况:“子任④、公达回湘后,未得兄只字报告,不知暴动工作准备到如何程度?见否可以即时发动,甚以为念。”[3](P52)在这里,毛泽东的名字也是排在彭公达前头的。实际上,湖南省委已在19日以“向彩霞”的代号就暴动办法向中央写了报告,交何资深带往武汉,估计“致中央函”亦是由何资深带去的。据上述情况判断,在数人之中,毛泽东是“致中央函”作者的可能性最大。
2.返湘行程也表明毛泽东可能是信的作者
“致中央函”是8月20日在长沙写就的,这与毛泽东回湖南后的行程也是吻合的。按彭公达给中央的报告中记述,“公达11日回湖南,泽东12日在汉动身,约定13日到长沙,15日召集会议。后因泽东同志13日没有到长沙,会议的时期改为16日。到了16日,到会的人都齐全,惟泽东一人未到”[3](P96)。从报告下文看,毛泽东出席了18日召开的新省委第一次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提出要制定一个土地政纲。而“致中央函”中提到,作者在19日与乡下来的几位农民同志会商,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并在当日的省委会议上讨论了一次。从时间顺序上看,这几个环节是相互衔接的。先不论13日到17日这五六天的时间毛泽东去了哪里,但可以断定,毛泽东至晚到18日已在长沙并参与了新省委的工作。那么,在20日给中央写信是合乎情理的。
(二)毛泽东是“致中央函”作者的直接和间接证据
1.信件内容的印证
“致中央函”中有两处提到作者的行踪。一处是说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对人民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1](P354)。上引文字证明作者是由湖北到湖南的,再从行文口吻看,作者应是长期在中央工作的。就第一点而论,在新省委成员中唯有在武汉出席过八七会议的毛泽东、彭公达两人与这一情况契合。毛泽东除6月24日到7月初在湖南外,其余时间均在武汉中央机关工作。而彭公达“是从下面提拔上来的”[3](P141),6月下旬进入湖南省委工作,7月下旬还在省委农民部长任上且有病在身[3](P36,P41),前往武汉的具体日期不详,估计应是短期到中央参加八七会议尔后于8月11日返回湖南的。显然,毛泽东的情况与第二点更为相符。
另一处是在讲土地问题时写道:“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5人来省)两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1](P355)信中提到的韶山和清泰乡,与毛泽东本人有特殊的关系。湘潭韶山是毛泽东的家乡,长沙清泰乡板仓是杨开慧的家乡,此时杨开慧正带着孩子们住在板仓。按照龙正才、彭长明的考证,毛泽东返回长沙后,就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看望亲人并在杨开慧家中召开了有4位农民、1位篾匠、1位老师参加的调查会,调查了解农民土地问题。此事有参加调查会的钟庆生的回忆为证。另据参加过湖南省委扩大会议的省工会特派员、湘西南特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陈新宪回忆:“在沈家大屋的一次会议讨论土地问题时,毛泽东说,我这次从武汉回来,到了清泰乡,作了两天的土地问题调查,了解到农民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所以要没收大中小地主土地,以满足农民的要求。”毛泽东到清泰乡搞调查的说法也为《年谱》编者采信。[2](P209)
上述两个线索当然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毛泽东是“致中央函”作者的有力证据。
2.毛泽东本人曾提到给中央写过这样一封信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实现下面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除了大地主以外也没收中、小地主的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政权;五、组织苏维埃。”[4](P140)这段话里虽没直接提到写信的问题,但所说的起义纲领的内容与“致中央函”的内容是一致的。延安整风期间,在1943年11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中谈到了1927年11月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插话说:“我在长沙发了一封信向中央提议:国民党旗子不要了,要共产党;不要国民革命军,要工农革命军;不要国民党政府,要工农革命委员会。”[1](P356)从内容上分析,应当就是指的此信。尽管时隔16年之久,毛泽东对信件内容仍记得相当清楚和准确。
3.李维汉、李立三的有关说法
八七会议后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李维汉晚年曾经回忆:“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具体材料我写不出来,但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看见过主席在起义征途中给中央的一封信。大意有:国民党在群众中比狗屎还要臭,国民党左派旗帜也不能再用了,我们要独立领导苏维埃运动,实行土地革命。”⑤ 后来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又写道:“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时也没有用左派国民党的名义,而是旗帜鲜明地以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他并致信党中央提议放弃国民党左派的旗帜。”[5](P177)两处都言之凿凿地提到毛泽东曾致信中央,提议放弃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以李维汉当时在中央的身份,亲眼见到“致中央函”是可信的,而且,他看到的应是包括抬头和落款的原信,而非目前我们所见的《中央通信》上的信件摘录。另外,李立三1930年2月所写的《党史报告》讲到八七会议时也说:“当时毛泽东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为国民党已经死了,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党——就是工农的党,但当时很少注意这个意见。”⑥ 经查八七会议记录和其他资料,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此类意见,提出意见的时间当在到湖南后。下文还将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三)对此信落款的推测
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依据《中央通讯》原样刊印,并沿用了原标题《湖南致中央函》。而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书在收入此信时,将篇名改为《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则缺乏充分的依据。此前一日即8月19日,湖南省委就秋收暴动办法专门给中央一个报告,抬头落款分别用了中央的代号“世荣”和湖南省委的代号“向彩霞”。毫无疑问,这个文件是以湖南省委名义发出的正式报告。而“致中央函”通篇以第一人称写成,内容主要是陈述个人看法,极可能是个人署名,而非湖南省委或省委代号署名。前面引述的毛泽东、李维汉的话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当然,在原件发现之前,这只能是一种推测。
基于前面列举的证据和分析,完全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就是“致中央函”的作者。当我们继续对信件的思想内容进行探讨时,可以从思想发展连贯性的角度,找出更多支持这一结论的线索。
二、“致中央函”的思想和文献价值
“致中央函”写于大革命失败、中共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对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政权问题和土地问题表达了旗帜鲜明的见解。
(一)最先提出抛弃国民党的旗子
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后,中共应当如何看待同国民党的关系?是否还要留在国民党内,继续举国民党的旗帜?蒋、汪的背叛直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此时的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权同盟”,而是蜕变为一个由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军阀势力所控制的政党。共产国际显然对此缺乏认识,它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还是斯大林套用俄国革命经验提出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即中国革命已由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的“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的第一阶段,转入以反对国内封建制度为主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阶段。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6](P116)。至于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现在还没有到来”[6](P213)。
新的临时中央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认为背叛革命的只是国民党上层“少数领袖”,国民党仍然是国民革命的旗帜。“七一五政变”发生后,《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提出,不再拥护武汉国民政府,立即召回在政府中的中共党员,但“仍须留在国民党内工作”[1](P224),“要团结下层左派分子在国民党内组织在野反对派,反对中央的反动政策”[1](P225)。这一决定是根据共产国际“仍要留在国民党内”,“不退出国民党”[7](P535)的指示做出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政策不要依靠到几个国民党的领袖上,而要依靠国民党的群众上面。现在不应退出国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要在国民革命成功社会革命时才能提出。”[8](P54)毛泽东的发言,也只是批评了中共加入国民党后不去做主人只是做客人的消极做法。所以,八七会议虽然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没有提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9](P264)
到湖南后,亲睹国民党地方势力镇压革命、屠杀工农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对国民党的看法发生重大变化。他在“致中央函”中说:“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农工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1](P354)毛泽东还进一步解释了自己思想变化的原因,“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失败。从前我们没有积极的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下”[1](P354-355)。基于对国民党“已成军阀的旗子”的性质判断,他主张彻底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坚决地树起共产党的红旗以号召广大群众。毛泽东的主张得到湖南省委的坚定支持。省委认为,“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利抢地盘的工具”。“国民党死了,并且臭了,不但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3](P99)因此,“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不要国民党了”。“湖南对于此次暴动,是主张用共产党名义来号召。”[3](P98,P99)当时参加湖南省委工作的罗章龙回忆说:“关于秋收起义,省委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不以国民党的名义举行,也不借重邓演达、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会上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以共产党名义领导起义。”[3](P142)
几乎在毛泽东写信的同时,中央常委会于8月21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决议案强调:“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组织暴动,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吸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1](P336)决议案还规定,“凡是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暴动而胜利的地方,工农群众团体,应当用团体加入的方法,加入这种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群众团体联合的党,使反动分子不能假借国民党党部名义,来实际上做阻滞革命的工作”[1](P337)。中央8月23日致信湖南省委,就暴动计划、政权形式及土地问题等项作出答复。信中表示:“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第二阶段。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民的民主政权,但不是照以前那样的工农赞助国民党。到了第三阶段才是国民党消灭,苏维埃实现的时候。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了,这是不对的。”[1](P353)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并未因中央来信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10](P168),正式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而在此时,南昌起义前委也已感到继续沿用国民党的名义不妥,决定从根本上改变政权性质。[11](P125)
直到9月中下旬,中央才完全改变了对国民党的态度,认为“国民党是已经死灭了,已经整个儿被豪绅资产阶级霸占去了。……我党的责任,从此之后,便是举起苏维埃的红旗为中国革命唯一的旗帜,一切革命分子,不论是共产党与否,除非他不革命,否则都是应当团结在苏维埃旗帜之下”[12](P425)。19日通过的政治局会议决议案指出:“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已经很快的把国民党变成政治的尸首,形式上国民党现在正经过分化堕落的过程。由其腐烂的尸体中产生出赤裸裸的军阀专政。所有共产党员的努力,打算创造秘密的革命国民党的组织,或稍为团结左派分子,一直到现在尚无成绩之可言。在别一方面的,以前国民党在群众中的革命威信,已因资产阶级军阀之到处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实行流血屠杀,恐怖与压迫而消灭了。这是毫无疑义的。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可见土地革命的急剧的发展,已经使一切动摇犹豫的上层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战线。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1](P369-370)鉴于复兴国民党左派的设想已无法实现,中央取消了8月21日决议案中关于开展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规定。
尽管毛泽东早在一个月前已得出同样的结论,中央却不承认是受了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影响,坚持认为毛泽东和湖南省委有关秋收起义的全部决策都是错误的,并在1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撤销了毛泽东、彭公达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二)明确主张建立苏维埃政权
“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内部以斯大林、布哈林为一派,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另一派,对是否应该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发生激烈的争论。托、季主张立即建立苏维埃,而斯大林按照他的“三阶段论”坚持目前阶段不应提出建立苏维埃的问题。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在当前形势下,提出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是欠妥当的”,因为这“意味着必然要建立双重政权,必然要实行推翻武汉政府的方针,必然要越过国民党这个群众组织形式和国家政权形式,直接在中国建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苏维埃政权”[13](P331)。到7月底,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建立苏维埃问题上有所松动,同意就建立苏维埃问题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真理报》7月26日发表社论说:“国民党业已出现的危机已将建立苏维埃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共产党员应当毫不迟疑地着手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一旦争取国民党的斗争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能动员号召群众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14](P528)两天后斯大林发表《时事问题简评》一文,提出“如果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是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涨成为事实,那末,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会提到日程上来。现在……应当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极广泛地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⑦。联共[布]中央8月9日的决议更进一步地提出:中共“应当大力宣传苏维埃思想。既然共产党促使国民党革命化的意图得不到成果,既然不能将该党转变为广大工农群众的组织,并使其实现民主化,而另一方面,革命势将走向高涨,那就必须将苏维埃这一宣传口号变为直接斗争口号,并着手组织工农和手工业者苏维埃”⑧。
“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3](P97)湖南省委对政权问题高度重视,8月18日召开的新省委第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一议题。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苏维埃问题的新精神,毛泽东“闻之距跃三百”,力表赞同,并且主张在暴动中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他在“致中央函”中写道:“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1905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之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实行。”[1](P483-484)湖南省委也认为,“现在应扩大的宣传苏维埃政权”,“在我们暴动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应即刻建设苏维埃式的政府”。[3](P99-100)省委19日写给中央的关于秋收暴动办法的报告明确提出,“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3](P49)。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在政权问题上的观点同样不为临时中央所接受。八七会议上,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所作的报告关于政权问题的表述是,“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政府仍用国民党的名义,但我们要占多数,成为工农民权独裁政权,乡村中要农会政权”[12](P4)。接到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报告后,中央坚持认为,眼下不是提出苏维埃口号的时机,更不是马上建立苏维埃的时机。目前所应该做的,只能是向劳动群众宣传苏维埃的意义。“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不[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1](P338)这完全照搬了斯大林的观点。至于暴动后的政权,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在乡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农会政权;在城市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1](P307)。“革命委员会在暴动前是指导暴动的机关,由我党指派同志及少数真正民左分子组织之。暴动成功后即是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1](P307)革命委员会也好,苏维埃也好,都排斥资产阶级与封建军阀的参加,而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除工人、农民和小商人的代表外,还包括了国民党左派的代表,而且要用国民党的旗帜。如南昌起义所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便是以C.P.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1](P411)。
9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国民党的旗帜,也相应地改变了在政权问题上的提法,正式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会议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1](P370)同时又刻板地规定,只能在中心城市组织苏维埃政权,在小县城则不可以。11月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提出把苏维埃作为党在现阶段的主要口号,把“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作为武装暴动的总口号。而此时,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开始了创建红色政权的实践,建立起中国农村根据地中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三)独立制定土地纲领
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也是发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中心环节。中共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要求。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这一议案并未得到实施。八七会议的贡献之一是明确了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并把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毛泽东力主没收所有地主不管是大中地主还是小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根本取消地主制。他在会议发言中指出:党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仅要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而且要解决小地主的土地问题。他特别强调:小地主的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如果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在那些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民协会则要停止工作。[8](P73)然而,中央并不同意立即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规定:“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配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对于小地主则实行“减租”。[1](P295,P296)
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湖南的农民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要求。在省委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阐述了四点意见:“一、没收土地必有没收的对象,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二、没收土地的办法,要由革命委员会(我们的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将全部办法〈提出〉,要农协或革命委员会执行。三、这个没收土地的政纲,如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因此,主张在不能工作或工作能力不足及老弱的地主,应由农协在农业税之内征收若干农产物平均分配给此等分子。四、宣布废除对农民的各种苛税;征收农业税。”[3](P96-97)
“致中央函”把上述思想具体化。“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大要是:(一)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每家实际消费量之多寡)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二)土地分配时由区协命令乡协按户造册,造好交于区协,由区协按册分配土地。(三)土地分配以区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人口多于土地之乡,可以移于人口少于土地之乡。必如此而后分配略得其平,至于甲区移住乙区暂不可能。(四)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安定人心。”[1](P355)这个纲领草案提出要没收一切土地,体现出根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彻底性,但没能切实保护中农的利益,不利于对他们的团结。同时,以区为单位分配土地后来也被证明很难实行。把给予地主家属适当安置作为土地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则是毛泽东最先提出来的。
中央8月23日信重申,不同意马上提出没收小地主和自耕农土地的口号,并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土地问题,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没收小地主土地’的口号不提出,但我们不要害怕没收小地主土地,革命发展到没收小地主时,我们要积极去组织领导,其结果仍是没收一切土地。不马上提出这一口号,只是对小地主的一种策略,在没收地主土地的过程中,对于自耕农的土地不免有打击,我们也不避免这种打击,但我们更不要提出‘没收自耕农土地’的口号。”[1](P353-354)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出现了新的提法,即“一切地主的土地无代价的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一切没收的土地之实际使用权归之于农民。租田制度与押田制度完全废除,耕者有其田。”[1](P501)这种没收一切土地和土地国有制的主张来自于共产国际,[13](P325)是中央“左”倾盲动错误在土地政策上的反映。
显然,无论对于毛泽东还是当时的中央来说,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了一大步,确定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的阶级路线,把没收土地的对象限定为地主阶级。12月,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土地斗争的经验,起草了土地革命时期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这部土地法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农民分配土地的权利,也存在一些原则性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三)禁止土地买卖。”[15](P51)随着根据地建设的开展和土地革命的深入,这些错误在1929年4月的兴国土地法、1930年2月的二七土地法中,相继得到了改正。大约到1930年底1931年初的时候,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开始形成。[16](P350)
从上面引述的材料看,在与国民党的关系、政权和土地政策三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当时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但正是这些观点上的分歧,表明毛泽东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突出体现了“致中央函”特殊的思想和文献价值。
三、余论
“致中央函”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重要文献,信中所言涵盖了起义纲领的主要内容。信件作者的确认,不仅让人们能够对秋收起义的筹划经过有更加准确的认识,而且为全面考察大革命向土地革命转折时期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发展脉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本资料。
大革命失败时,毛泽东也曾有过歧路彷徨的苦闷和无奈,八七会议则令他看到了新的希望。毛泽东后来这样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8月7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10](P12-13)可见,八七会议前后是毛泽东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他是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马日事变”后就提出要“上山”开展武装斗争,八七会议上又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受命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后,他汲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努力把八七会议精神与工农群众的愿望结合起来,形成了秋收暴动的指导纲领。这些新的思想成果,在他写给中央的信中得到集中的反映。“致中央函”与他在八七会议的发言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提出许多新的创见。今天看,这些观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变动错误估计的影响,未必都是完全正确的,有些还带有明显的“左”的痕迹,但相对于当时对共产国际亦步亦趋的中央而言,他的确是在循着一条较为正确的道路探索前行。
“致中央函”也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独立自主、决不盲从的理论品格。如果说在大革命时代,毛泽东还对当时的中央多多少少存有过高的期望,“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15](P47),那么,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则促使毛泽东更加自觉地进行独立思考,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致中央函”中,毛泽东表达了对同国民党的关系、政权、土地等重大问题的看法,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八七会议的参加者,他不是不知道,这些主张与中央的观点是相左的,却仍毫无保留地担承自己的见解。中央8月23日复信几乎全面否定了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意见。9月5日,中央再次批评湖南省委:“关于政权,国民党和没收土地诸问题,中央认为你们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在此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3](P61)即使面临如此压力,毛泽东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秋收起义受挫后,他果断放弃了进攻长沙的原定计划,毅然率领起义部队转进井冈山。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坚持独立探索的精神,尽管为此曾遭受误解、批判甚至是无情打击,也从未发生任何动摇。
总之,“致中央函”真实记录了这一时期毛泽东探索革命道路的思想轨迹,成为在井冈山形成的红色政权理论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发端,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发展完整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日后如果有机会,还是应当把这篇珍贵的历史文献补录到毛泽东的有关文集或专集中去。
收稿日期:2009-09-22
注释:
① 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致中央函”。
② 日本中国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刊印、1976年出版的《毛泽东集》第2卷收入了“致中央函”。该书的例言中说:“虽无毛泽东的署名,但有根据证明确是毛泽东作品的,亦予收录。”但对收录此信的“根据”,未作任何解释。
③ 前者如龙正才、彭长明《关于“八七”会议后至沈家大屋会议前毛泽东的去向》。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216-218页。后者如宋俊生所著《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研究》,此书在引用8月20日信时,便只是说这是“一位负责同志”向中央所作的关于湖南新省委第一次会议情况的汇报。见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3辑,97页。笔者作为编辑组成员,知道《毛泽东军事文集》就是因作者问题难以断定而没有收入“致中央函”。
④ 子任,毛泽东的别名。
⑤ 《秋收起义参考资料》,上海教育学院政治系1977年编印,22页。
⑥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出版,262页。李立三本人没有参加八七会议,有些史实记述并不准确。
⑦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参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203页。作者按:斯大林只是同意在工农群众中宣传苏维埃,而不是像有的研究论著中所说的同意立即建立苏维埃。他在同一篇文章就一再强调“一个新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涨”是建立苏维埃的先决条件,并说:现在“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要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涨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
⑧ 《中国革命的教训》,摘自1927年8月9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345页。
标签:秋收起义论文; 苏维埃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毛泽东论文; 八七会议论文; 易礼容论文; 湖南发展论文; 国民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