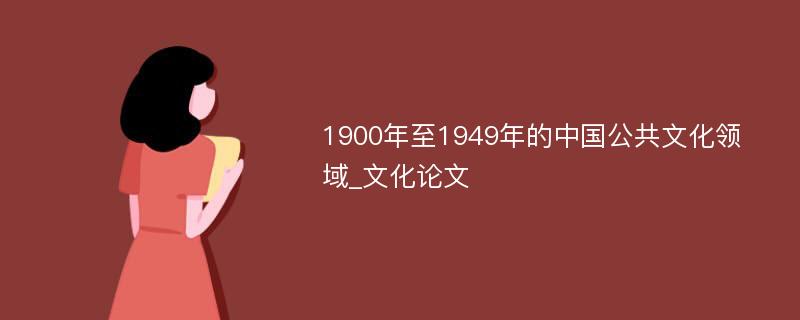
1900-1949年的中国公共文化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领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问题近年成为中外学界的热点话题①。公共领域作为“一个集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和政治功效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②,在我国学界存在广泛争议,人们很难从思想史、社会史或政治史的单一角度对这一概念作一全面的理解。一般认为,近代公共领域是开放的、可渗透的交往结构和人们日常交往行动中所产生的社会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公共领域”可以看作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通过自由沟通以形成理解或通过商谈以达成妥协的机制或制度化渠道,如团体、俱乐部、新闻、通讯、沙龙、报刊、杂志、学校、剧院、博物馆、讲演场所等由私人构成的非官方组织或机构等,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
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公共领域是否存在确实存在疑问,但公共文化领域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中国的文化产品一直就有“高台教化”的功能,本质上就带有与“学校、报纸和学会”以及“集会、通电”功能相似的公共性传统③,具有教化民众、移风易俗、引导社会风气等政治性或公共性使命。需要指出的是,古代中国的公共娱乐场所不具备价值批判功能,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在中国古代宗法农耕社会中,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被赋予了族群、等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识性功能。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文化消费局限于一个狭窄的圈子,以同乡会、行会、宗族、家族等为单位的集团购买和集团消费是其重要特色,市场化和商品化的程度较低,缺乏个人权利和批判精神。因而尽管中国传统文娱空间面向公众开放,却因价值批判功能的缺位而不具备类似于近代西方沙龙、咖啡馆、俱乐部等“公共领域”的典型特征,这一情态在步入近代以后发生了改变。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通过考察1920年代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发现政治精英集团借助于近代公共文化领域实施了极富成效的“唤醒”民众运动。以民族觉醒为导向的文化运动与以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在公共文化领域实现了汇流与协同④。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语境里,近代政治精英集团藉此完成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动员与政治“塑形”。
一、近代中国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与社会动员方式的改变
1840年以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近代都市如上海、汉口等出现了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母体内,近代消费文化形态通过各种新式传媒和传播渠道的建立而不断拓展,文化消费突破了传统的以政治或教化功能为主的生产传播格局,日益大众化和娱乐化,而且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商业价值和政治内涵,近代中国社会的公共文化空间逐步形成。
(一)近代中国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
学者王笛认为“公共空间”即城市中对所有人开放的地方,在公共空间中所进行的人们日常生活即“公共生活”⑤。公共文化空间就应该是开放的供大众进行文化消费和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地方,如剧场、戏院、电影院、舞厅、体育场所、赛马场、公同广场、图书馆、博物馆、通俗教育馆、茶馆、庙会、俱乐部、咖啡馆等场所。本文认为,在这些公共文化空间基础上形成的“生活世界”和“价值批判领域”即是公共文化领域⑥。本文倾向于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公共文化领域”概念进行界定,从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或合作、制衡或补充等关系特征上讨论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态。在这一意义上,近代公共文化领域通常被视为一种由大众话语权主导的民主活动空间,但同时也作为一个社会生活特别是文化生活的领域,兼具社会性、文艺性和价值性的特征。近代公共文化领域在形态上包括:
一是近代学校的出现,形成了公共舆论机制。科举制的废除、各种新式学堂的兴起,以及近代小、中、大学教育体制的建立,大众化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必然会导致文化的普及。教育不仅是文化传播的内容,也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并通过塑造泛化的“文化人”而使得文化广泛传播成为可能。现代学校通过学术研究和社会教育逐步成为新思想和社会舆论的源发地(发源地),成为社会思潮的领导者⑦。
二是新式报刊的大量涌现,形成了公共传播渠道。晚清以来,中国报业大兴。仅上海一地,1901到1911年10年间就出版各类日报和期刊100多种⑧。辛亥革命以后,全国的报纸已达500种,1921年全国共有报刊1134种,其中日报550种,到1927年日报发展到628种。1919年和1922年两年新创办的杂志近百种,1921年全国共有各类期刊584种。报刊一步步地由一种不被理解的新鲜事物逐渐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⑨,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再加上,从晚清开始的大众传媒的“民间化”趋势,民办报刊获得了相对独立性,在政治国家之外逐渐开拓出一个新的自主性社会空间。民办报刊实际成为一种沟通社会民众和政治国家关系的公共文化领域。
三是剧场、戏院、电影院、舞厅、体育场所、赛马场、公园广场、图书馆、博物馆、通俗教育馆等文化娱乐场所在中国的日益普及,以及茶馆、集市庙会等传统娱乐场所的更新变异,形成了都市中公共性文化空间的网络结构。据统计,上海市1931年私立娱乐场所数多达207处⑩。汉口从1899年到1949年共建立了各类茶园、舞台、戏院94所(11),一般底层市民都可涉足其间。在民国建立后,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个创办博物馆的高潮,1921年,全国大约注册了13个博物馆,到1929年增加至34个,到1934年已达到72个。西方学者认为,这些博物馆的建立,具有培育中国公民社会的功能,“在破除旧的伦理秩序并代之以一种历史进步的秩序方面,它们起了主要作用……博物馆预示着种种进步的觉醒。”“被寄予了凝聚全国性公民社会感的希望。”(12)这些新型文化娱乐场所的出现,推动中国普通民众的社交模式以及由此而出现的社会信息网络产生新的变化,从而形成了都市中新的公共文化生活方式。
四是学会、商会和行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出现,形成了近代都市中下层社会的局部整合机制。晚清以后,近代商会的发展和传统行会组织的转型,形成都市中下层的自组织形态。以近代商会为中心,近代一些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大中城市都形成了一种社会化的组织网络,不仅促进了“公”领域的扩张,而且促成了市民阶层的整合,形成了近代公共领域的基础。
(二)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改变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动员方式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成长依赖于世界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和国内文化商品市场的发育,反过来,它的形成又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动员方式。塞缪尔·P·亨廷顿曾引用卡尔·W·多伊奇的观点对“社会动员”作了如下表述:社会动员是“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的过程,“它意味着人们在态度、价值观、期望等方面和传统社会的人们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们看齐。”(13)社会动员的核心是对人们价值观的引导,引导并促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价值观和愿景的变化,从而推动社会转型的过程。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认为,1920年代以来,按照“以党建国”的政治模式,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广泛的“文化动员”过程,他称之为“唤醒理论”(14)。因此,近代社会动员具有价值认同和文化整合的特征,是一种基于共同文化愿景之上的文化价值整合过程。
与传统社会相比,近代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改变了近代的社会结构,使近代社会动员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传统社会中,文化动员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动员方式,完成对私人文化生活方式的改造,同时也完成了国家公权对私权领域的覆盖。对个体而言,因为无法选择,所以这种文化动员方式具有强制性。步入近代后,人们的文化消费日益市场化和商品化,个体逐步获得了文化消费的选择权,个体的诉求和个人的偏好在公共文化领域显得越来越重要,这在客观上迫使国家公权从商业性文化市场领域退缩。国家的文化动员方式必须要建立在个人的“意愿”之上,因此这种文化动员方式必须建立在大众“同意”的基础上。这样就迫使国家由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动员方式向“上下结合”的协商性动员方式的转变。相应地,也迫使社会宣传和文化动员渠道从传统的“国家(政治精英集团)——家族(行会)——个体”向“国家(政治精英集团)——公共文化领域——个体”的转化。报刊、学校、剧院、集会等社会文化组织在社会文化动员体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一,近代公共文化领域的成长推动了社会信仰体系的世俗化过程,形成了新的信仰体系的社会基础。近代中国社会因儒家信仰的衰微而出现了文化和信仰体系的真空状态,形成了对“新的觉悟形式和新的意义架构”的社会需求,近代中国社会从“神性政治”进入到“承认政治”的新阶段(15),这就构成了近代精英集团进行文化与意识形态动员的必然性的社会基础。
第二,近代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超越了传统社会面对面的信息交流形式,形成了公共舆论阵地,构成了近代社会公共表达机制。
晚清以来,伴随着近代报刊传播方式和技术的引入,基于这些近代传媒技术之上的文化形态也对中国的社会生态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早期维新思想家如王韬、郑观应就已经认识到近代报纸、学校作为公共舆论的重要性:“日报与议院,公论如秉炬。”(16)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在政府之外形成了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梁启超指出舆论是天地间最大的“社会制裁之力”(17),认为近代社会中的报纸应当是政府之监督者和人民之向导者。
在1895-1898年间,维新派掀起了一次办报高潮,在《时务报》之外,维新思想家又创立了《国闻报》、《湘报》、《知新报》等20—30家。这些报刊一改千年来民间“不论国事”的传统,大规模讨论国事,建构了近代公共文化领域对于政府的批判功能。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在1912年4月12日总结革命成功的原因时就指出报刊舆论功不可没:“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相成,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15)“辛亥时期‘国体丕变’中的文字‘鼓吹之功’,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全盘反思’、‘打倒孔家店’等,均属公共舆论空间批判精神的一脉相传。”(19)
第三,近代公共文化领域的出现,超越了传统社会中的“血缘地缘”组织方式的局限性,形成了社会自组织机制,为近代精英集团的社会动员提供了社会整合基础。
传统文化中,中国社会中存在宗族共同体,但却缺乏社会动员系统。孙中山曾说:“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有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20)传统的社会动员方式一般要通过家族或宗族实现。但是,维新运动开始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近代都市社会快速扩张,社会流动性增长,近代都市社会组织逐步突破了传统社会“血缘”、“地缘”和“业缘”组织形式。1895年甲午战败以后,中国官绅抱着组织学会以开风气的理念,组织了各种社团。在1895-1900年之间,所组学会至少有73所。“此种学会,并非传统性之结合形式,而系充分模仿西洋,完全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之结合。”(21)民国建立,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思想受到社会各界的颂扬,个人意识得到极大的张扬,不同行业中的市民阶层要求在新的社会生活中表达其团体意志,推动了近代社会文化组织的成长,由此带动了社会公共文化领域的扩张。
例如,1926年,值北伐胜利之机,武汉文化界的艺人成立了湖北剧学总会,并在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备案。湖北剧学总会包括汉剧公会、汉剧学会(业余)、楚剧进化社、京剧公会、新剧公会、影剧宣传社、杂剧(曲艺)公会、剧场业公会等八个团体(22)。1927年3月,为援助上海工人起义及慰劳北伐军伤员,总会动员武汉戏剧界在中央人民俱乐部(今民众乐园)、老圃游戏场(老圃游乐园)、满春、乐园、美成、长乐、天声、楼外楼等戏园义演。1927年6月,联合组织慰劳伤兵演剧大会(23)。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全国文化界在民族国家旗帜于实现了组织整合。作为战时文化首都的武汉,成立了众多全国性文化团体,包括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作者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摄影协会、全国歌咏协会等(24)。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号召一切从事于文学艺术的工作者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笔来发动群众,捍卫祖国,粉碎日寇,争取胜利。”(25)对此,作为亲历者的郭沫若曾评价为:“这是文艺家们的大团结,这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无疑是一个空前的现象。”(26)换言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在抗日救亡旗帜下的整个行业力量整合的最终完成,表征着近代中国公共文化领域出现后社会动员方式的根本改变。
归纳起来,公共文化领域的出现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第一,近代公共文化领域的成长在社会精英集团之外确立了一种丰富的社会性资源,精英集团必须借助于这一社会开放领域才能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声明主张列入公共的议程,政治系统的运行有赖于公共文化领域的合作与参与,公共文化领域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到精英集团社会动员系统的运行情况。第二,近代公共文化领域的自组织功能为精英集团的社会力量整合提供了效率保障,新型社会文化组织的成长过程也是前近代社会结构特别是城市社会结构的解构化过程,精英集团直接面对近代文化组织,以替代直接面对行会或个体,这种机制使得精英集团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价值观以空前规模流播,同时传达到千百万人,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动员的效率。第三,近代公共文化领域的成长建构了精英集团可资利用的文化传播渠道,精英集团通过这一渠道传播政治信息,表达政治意见,提供榜样示范,引导社会舆论为个体提供政治行为指向。
二、近代民族国家理念向公共文化领域的拓展与覆盖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尤其是1895年中国惨败于日本以来,举国上下肝胆俱裂、猛然警悟。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以“救亡图存”为全民族最高任务的特殊社会历史时期,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全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各政治派别为了争取民众的认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与救国、建国方案,必须建立和利用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文化宣传是进行社会动员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因此,每一个政治派别无一例外地都有着把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激情和渴望,总是极力对社会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动员,以实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标。维新派、革命派、国民党和共产党等政治派别尽管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有着很大区别,甚至截然不同,但在社会动员上,都不约而同地借助于近代民族国家理念渗透形成了对公共文化领域的掌控。
近代民族国家理念,包含了政治性的爱国主义和文化性的民族主义两种价值体系,具有政治法律共同体和民族文化共同体双重性质以及由此带来的双重归属感。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共同体的理想模式是从外部移植的,这与西方的从社会结构中自然生长的方式不同。“如果共和的政治内容内在地镶嵌于民族的历史形式之中(比如英国和法国),或者民族国家的文化通过政治的共同体原则重新创造(如美国),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并不一定会表现出紧张关系,反而会相得益彰。然而,对于许多非西方国家来说,当共和模式是外来的,而文化传统又是本土的时候,二种认同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便难以避免。”(27)但是,我们认为,在近代中国,“两种认同”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一直存在,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对公共文化领域的渗透却极大地削减了两种认同之间的紧张程度,民族国家观念对公共文化领域的渗透过程同时也是政治共同体模式对文化共同体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费约翰称之为“唤醒”过程:“‘唤醒’这个词语的无处不在,有助于解释当时两大运动汇合,一个是民族导向的文化运动,另一个是以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为目标的运动。也就是说,民族觉醒观念,帮助我们把各个特殊的文化领域连接起来,并将之与政治行动领域联系在一起。”(28)
(一)国家向公共文化领域的拓展:民族国家理念对公共文化领域的掌握
随着民族灾难的日深,近代中国社会开始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在1840年以后,睁眼看世界的一批先觉者在与世界的交往中逐步形成了近代民族国家观念。1898年6月,康有为给光绪帝上《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揭》,提出了“民族之治”。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自由》中强调:“今日吾中国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指出当前的中国要建立民族国家以“谋公益”、“御他族”,明确提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任务(29)。
在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下,“革命”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紧紧联系在一起。近代意义上的“革命”一词,在晚清之际一经引入,便在公共领域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引发激烈论战,并在社会上迅速播散开来。一些文化名人如黄遵宪、梁启超、章太炎、邹容以及政治领袖孙中山等人均参与了这场思想文化论战。此后,“革命”之语成为国民的普遍意识,“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30),“革命”被赋予了正义性、正当性与现代性,并成为公共领域的主导性舆论。在清末民初,“革命”作为一种文化层面上的舆论主导力量业已形成,并已发展成为一种浩浩荡荡的社会思潮,其流风所及,一直到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当“革命”进入公共文化领域被打造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潜意识之后,作为手段的“革命”与作为目的的“民族国家”之间、公共文化领域与国家之间也就没有了明晰的界线,“革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象征形式”。
20世纪上半叶,维新派、革命派、国民党和共产党等不同政治派别在公共文化领域建构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图景。这一图景是以“革命”话语为中心,由议院、国会、共和、民权、民治、主权、自由、独立、平等、博爱、阶级、资本家、群众、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性新语汇组成的近代民族国家想象空间。这种想象空间既是价值范畴、理想世界,同时又是人们的“生活世界”。在“革命”的话语霸权下,人民大众同意的合法性和领导权决定于各政治派别与市民社会关于革命图景和民族国家想象的耦合程度。近代中国文化动员和政治运动的平行发展,使民族主义得以建立在一套符号、文化概念和理想之上,而这套文化概念和符号系统支持了社会共同的观念和价值,其基础则来自近代社会中逐步成长起来的、由众多文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一起创造的一个统一的知识领域。对于各政治派别而言,建立一种有效的文化动员体系是当务之急;对于大众来说,在民族国家旗帜下进行文化动员具有正当性,是可以接受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难以成长出西方社会公共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批判功能,近代中国公共文化领域在“革命话语”和民族国家旗帜下日益向国家靠拢,这就为近代中国国家公权向公共领域的不受限制的延伸,即公共文化领域的“国家化”准备了思想基础。
此点在晚清公共文化领域开始形成阶段,就有所表露。如发端于清末的戏剧改良运动,就是在服务近代民族国家建构需求下,对传统戏剧的一次合法改造。当时人认为“今日欲救吾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欲无老无幼,无上无下,人人能有国家思想,而受其感化力者,舍戏剧未由”,故而倡议“设剧场,收廉值,以灌输文明思想”(31)。诸如《血泪碑》、《共和万岁》、《波兰亡国恨》等众多宣传革命、反映现实的新剧的排演,使得改良后的戏剧脱离了仅为个体娱乐的局限,充当了“输入国家思想”、“灌输文明思想”的媒介角色。传统戏院由此完成了由单纯的娱乐空间向公共文化空间的转换。
近代中国公共文化领域的其他形态,如公园、图书馆、博物馆、报刊、学会等,在“救亡图存”的整体语境下,也莫不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新型国民的培养存在紧密的关联。在此背景下,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近代文化娱乐场所,被视为了“开民智”、“化民成俗”的“导民善法”(32);报刊成为了“救中国之前途,唤醒世人之迷梦”的利器(33);学会则是“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缓之上策”(34)。可以说,近代中国公共文化领域从一开始就因特殊的时局为政治力量的渗入留下了通道。
现代政治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政党政治。民国建立后,政党成为了民族国家建构的主导力量,党派纷争成为不同利益群体政治博弈的外在表现。不同的政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不同利益群体,为最大程度地争取民众的认同,有意地使用民族主义和革命的话语策略向公共文化领域进行全面渗透。1920年代以后,各政治派别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公共文化领域已日益凸显。到1930年代后期,各政治派别完成对公共领域的分割与控制,公共文化领域基本实现了政治意识形态化(35),公共领域的发展过程被扭曲。特别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旗帜下出现了国家与公共领域的“共谋”,公共文化领域中的舆论成为“背景化的社会现象”(36),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下实现了“舆论同化”(37),近代公共领域基本失去了价值批判的制衡力量,社会文化动员方式基本走上了“国家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轨道。
(二)公共文化领域对国家的响应:文化产品的国家化
“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一方面要体现为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要体现为文化上的现代性和同一性。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建设文化同一性的过程,“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是传统的中华文明帝国瓦解,中国面临着共同体认同的危机。”(38)民族国家建设围绕着建构民族文化同一性和主体性展开:“就中国而言,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自决的过程,而且也是创造文化同一性的过程,创造超越并包容地方性和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同一性。”(39)文化同一性的实现,在内容上体现为民族性,在形式上即体现为国家性。
在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目标制约下,20世纪前50年的文化生产和文化建设均具有“国家化倾向”和“工具化倾向”的双重色彩。1915年7月18日,民国政府教育部拟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向大总统呈文,申办的理由即是建设通俗教育研究会为建设民族国家所需,在与日本与英国、德国的比较中,显示出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文化建设“工具化”的倾向:“国家之演进,胥恃人民智德之健全,而人民智德之健全,端赖教育之普及,而考求教育普及之方法,学校而外,尤藉有社会教育以补其所不逮。……如日本文部省关于通俗教育一项,共设备费用每年达七万五千元以上,其余英德各国更臻发达。……值此国基甫定,民习未纯之时,使非于此项教育积极提倡,不徒人民之德慧不开,社会将日趋于下,而蚩蚩者氓乏适宜之训化,尤惧无以定志气而正趋向,其于国家前途关系甚巨。”为此教育部“拟定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十八条,注意改良小说、戏曲、讲演各项普通人民切近事项。”(40)与此相应,文化生产者也主动使其创作、生产符合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郭沫若早在1923年就提出“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41)。稍后兴起的左翼文化运动更是号召文学、戏剧、音乐等都要为革命服务,从而使得近代公共文化领域愈发具有“国家化”和“工具化”的倾向。
文化建设的现代性要求渗入文化领域,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如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以艺术家组织的近代转型。在文化艺术的内容生产上,中西文化碰撞引发广泛的文化论争并形成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潮(42);在文化艺术界的组织上,则引发了文化艺术界的自组织行为。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文化工作者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各类报纸和文学刊物立刻转向刊登反对侵略、主张抗日的小说、诗歌、剧本;许多学校、团体抓紧排练演出,宣传抗日救亡。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等领域,先后涌现了“救亡文学”、“救亡戏剧”、“救亡电影”、“救亡歌曲”等以抗战为主题的文化热潮。《桃李劫》、《风云儿女》等救亡故事片,《义勇军进行曲》、《黄河之恋》、《热血》、《青年进行曲》等救亡歌曲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全国文化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入伍”、“文化救亡”运动。广大文化工作者一致表示:“上文化战线,唤醒同胞,组织同胞,共同为抗敌救国而奋斗”(43),出现了声势磅礴的全民族的文化社会动员。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后,各地来到武汉的戏剧团体与武汉戏剧艺人联合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劳军公演,名为“全国戏剧界援助华北游击队战士联合公演”。1938年初,国民政府在武汉建立中国电影制片厂,汇集了史东山、袁牧之、陈波儿、袁丛美、高占非、郑君里、王士珍等著名电影人,在半年多时间里先后摄制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等3部故事片和30多部新闻、纪录、动画等短片。这些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影片,不仅在国内发行放映,而且发行到国外(44)。
文化产品的“国家化”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效能。仅以1938的武汉抗战联合公演为例。1938年,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武汉的演剧队、宣传抗战救亡的戏剧团体,决定举行一次空前盛大的联合大公演,为华北义勇军募款,剧名叫《最后的胜利》,由田汉编剧,洪深导演,应龙卫任舞台监督。剧中人物100多人,赵丹、王莹分饰男女主角。据当事人回忆:“这次联合公演,阵容之整齐,规模之庞大是空前的,其盛况与影响之巨大也是空前的!真是轰动全武汉,各界人士都非常重视这次演出!”演出之后,全体指战员高呼口号:“全国军队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45)1942年田汉在《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一文中写到:“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么伟大和显著的作用。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开始以后,戏剧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46)
“救亡图存”的民族任务,极大地推动了公共文化领域向“国家”的靠拢。与西方“公共领域”从社会结构中自然长出来的路径不同,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伴生于1840年以后全民族生存危机之中。“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的压倒性的全民族任务,这就为国家意识向公共文化领域的延伸提供了社会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资源。
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文化的“工具化”成为一种“文化自觉”,正如抗战时期一位艺人所说:“我常听人说,在这样困难严重的情形下还演戏,……我们正是因为在这样严重的局面下,才积极筹备这次演出,理由很简单,我们是把艺术当作抗敌的武器,而不仅是狭义的当作娱乐工具。”(47)“这不是娱乐,这不是消费,是唤醒同胞们在此伟大的抗战局面开展之中。……作一切有力的援助,巩固抗战的阵线。”(48)
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民族自强语境下,以民族自强为核心的文化运动,与以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实现了汇流。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觉醒与拓展,帮助文化精英阶层在各个文化领域实现了有机连接,并为精英集团的政治行动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下,“民族主义政治跨越种种散漫的边界,在科学、哲学和文学中寻找自己的空间,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努力征募知识分子为革命政权服务的同时,政治活动家们很轻巧地就进入了科学、哲学和文学的世界”(49)。在近代中国“以党建国”这一特殊历史道路的局限下,文化产品“国家化”过程与“政治意识形态化”过程成为了同一个主题的两种表现方式。
三、基本结论
近代民族国家理念的确立,提供了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意识、文化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的特殊背景。根据福柯“知识—权力”的相关理论,文化、价值符号与权力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权力和知识相互蕴含,权力通过对知识的征服并在知识上打下权力烙印,但知识也能给人以权力;权力产生知识,知识也产生权力,知识使统治的结构获得某种合法性(50)。依据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近代中国精英集团对公共文化领域中公共议程的控制,本质上就是一种话语权利机制。“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或者是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反叛者们的工具,或者二者兼具”(51)。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对民族国家观念的接受过程即是政治化与国家化过程。“民族国家”理念对社会的掌握使公共领域失去了社会批判功能,同时“民族国家观念”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共享理念,藉此完成了对基层社会的观念同化,成为精英集团在民族国家旗帜下整合社会的思想资源:“人们把社会的主要制度及其被人们所接受的解释,看作是隐含地为公民所共享的理念和原则的资源储备。”(52)由此公共文化领域逐渐沦为政治精英集团的政治表达阵地。正如费约翰所提出的,在近代世界民族竞争中,中华民族先贤由对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这一普遍秩序的觉悟,发展为对单个民族这一理想的觉悟。“从一个民族的理想,转到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的理念,再从一个国家的理念转到一个政党的理想,然后再从一个政党的理想,转到先觉的领导者单一、绝对的声音的出现”(53)。近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借助于这一文化动员的逻辑过程,在公共文化领域构建一幅宏大而合理的民族国家愿景,掌握了有效控制基层社会的关键,获取了社会心理的广泛认同,增强了其政治设计的合法性,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推动实现了民众与“国家”的共谋。
注释:
①近年来,中外学界对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进入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汪行福:《通向话语民主之路——与哈贝马斯对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马敏、朱英、罗威谦、J.G.亚历山大、王笛、邓正来、许纪霖等人从历史学和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讨论中国“公共领域”的生成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意义,成为学界的一大热点。参见Rowe,W.T..Hankou:Commerce and Society,1796-1889.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Rowe,W.T..Hankou: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朱英:《转型时期社会与国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等。
②傅永军、汪迎东:《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三论》,《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③⑦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
④(12)(28)(49)(53)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李里峰、李霞、徐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76页,第7页,第7页,第11页。
⑤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⑥本文所指“公共文化领域”相当于哈贝马斯提出的“文艺领域中的公共领域”,是与“政治领域中的公共领域”相对应的概念。见傅才武:《中国近现代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与公共领域的生成——以汉口为中心的研究》,《文艺研究》2007年第6期。
⑧方平:《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众舆论的表达模式》,《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1期。
⑨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56页。
⑩上海市地方协会编:《上海市统计》,上海:1933年,“教育”第14、16页,“社会”第19页。
(11)《武汉市志·文化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2—194页。
(13)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1页。
(14)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认为,在1920年代,借助于“三民主义”的理论引导和孙中山等革命领袖的权威,特别是建立中央宣传部等创新性措施,沉睡的中国社会逐渐被动员起来(“唤醒”),由此建立了20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重建的社会基础。见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15)按照查尔斯·泰勒对“承认”的解释,政治上的“承认话语”是指:“首先,在私人领域,我们认识到的认同和自我是在与有意义的他者持续的对话和斗争中形成的;其次,在公共领域,平等承认的政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见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董之林、陈燕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00页。
(16)郑观应:《罗浮侍鹤山人诗草》卷1。
(17)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2页。
(18)《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3页。
(19)刘增合:《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0)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4—185页。
(21)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22)邓天澜:《大革命时期的湖北剧学总会》,见武汉市文化局史志办公室编《武汉文化史料》(第二辑)(内部资料),1983年。
(23)《湖北剧学总会中央人民俱乐部为慰劳北伐军伤员发起演剧助捐》,《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1日。
(24)刘志斌:《抗战初期武汉轰轰烈烈的戏剧活动》,见《武汉文史资料》1995年第3辑(总第六十一辑)。
(25)《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发起旨趣》,《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集(辑),1938年4月1日。
(26)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212页。
(27)许纪霖:《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6期。
(29)冯天瑜:《新语探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7页。
(30)梁启超:《释革》,《新民从报》1902年12月14日。
(31)天僇生:《剧场之教育》,《月月小说》1908年第13号。
(32)《考察政治大臣端方、戴鸿慈奏陈各国导民善法请次第举办折》,《大公报》1906年12月8日。
(33)《论报界》,《苏报》1903年6月4日。
(34)谭嗣同:《论全体学》,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37页。
(35)1935年,时人沈志远即曾描述当时的情景:“现在你随便拉住一个稍稍留心中国经济的人,问他中国经济如何,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复你: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段话真实反映了此次论战对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影响,政治派别的意识形态通过论战占领了公共领域的舆论主导权。见沈志远:《现阶段中国经济之基础》,《新中华》第3卷第13期,1935年7月。
(36)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第23页。
(37)李希光、周庆安主编:《软力量与全球传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38)许纪霖:《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39)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见《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4页。
(4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文化)》第三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1页。
(41)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见王训昭、卢正言、邵华等编:《郭沫若研究资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42页。
(42)宫宏宇:《民族国家、文化守成、现代性与近代中国音乐思潮》,《音乐研究》2008年第1期。
(43)《申报》1937年7月29日。
(44)武汉市文化史业办公室:《抗战初期武汉文化活动概况》、《汉市剧业同人劳军公演团举办劳军公演》,见《武汉文化史料》(第二辑),1983年9月,第8—54页。
(45)《创作和排演话剧“最后的胜利”的专记》,见颜一烟:《在救亡演剧二队的日子里》,载湖北文化史志办公室编:《文艺志资料选辑》(三)(内部资料),1984年10月。
(46)章绍嗣等主编:《武汉抗战文艺史稿》,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29页。
(47)刘巍:《这次公演的报告》,见湖北省文化史志办公室《文艺志资料选辑》(三)(内部资料),1984年10月,第302页。
(48)《湖北青年战时服务团公演特刊》,见《文艺志资料选辑》(三)(内部资料),1984年10月,第304页。
(50)参见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0;福柯:《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5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页。
(52)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基本理念》,见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50页。
标签: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公共领域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公共空间论文; 社会舆论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精英集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