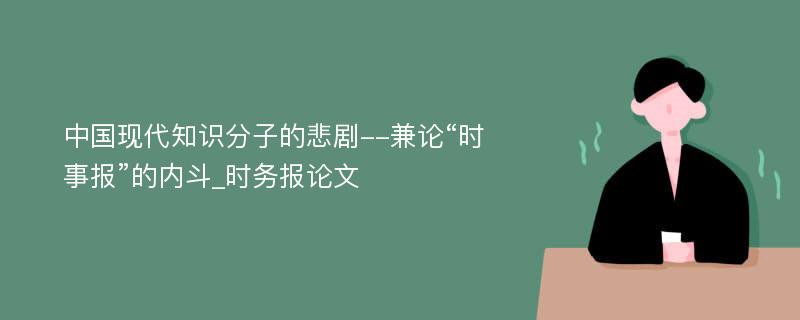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务论文,内讧论文,知识分子论文,试论论文,悲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6)01—0015—10
不论在近代中国新闻史,还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时务报》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之所以如此,应该承认是《时务报》创办伊始拥有一个难得的“最佳组合”:黄遵宪以政界大员的身份掌控大局;汪康年协调内外,负责经营和运作;而“笔头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以如椽之笔提供源源不断的“报章体”文字。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戊戌年间的政治进程,随着《时务报》日趋红火,黄、汪、梁三人的处境开始变化,他们共患难的创业精神开始丢失,他们三人的关系也开始了微妙的变化,并最终导致他们的分手,《时务报》也因此成为历史的陈迹。
《时务报》的悲剧是近代中国政治史的一个缩影,由此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中所蕴含的意味相当深刻,素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不过在对一些留存文献的解读上由于更多地受到“康梁系”强势话语的影响,故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①。本文拟从维新运动进程的宏观背景关照《时务报》的创立、发展及消失的历程,力求揭示这一事件的真相,最大限度地再现历史。
一、黄金组合
《时务报》的创办来源于康有为等人筹办的上海强学会及其所属的《强学报》,而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又得力于张之洞的资助和支持,所以当张之洞觉得无法约束康有为的时候,就决定调汪康年到上海主持强学会的事务,试图在人事布局上掌控强学会。
汪康年是张之洞门下具有维新思想的幕僚,与梁启超、麦孟华也有很深的交情②。1895年初,汪康年有意于联络同仁创办一份“译报”及中国公会,这个想法或许正是汪康年在京师时与梁启超等人商量的结果。在此后的几个月中,译报馆和中国公会的筹备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只是由于汪康年的家事及其他人事原因的耽搁而迟迟未能公开成立,而北京的强学会则已成气候。
当北京的强学会初步成型的时候,康有为南下江宁,欲说服张之洞支持在上海创建强学会,经过20余天的交谈,张之洞不仅同意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强学会,而且建议康有为应将上海强学会与广东的强学会同时举办,并暗示上海方面的事务可以由汪康年主持,而广东方面则由康有为全权负责。张之洞的用意虽然不太清楚,但这一建议对康有为来说则欢迎之至。1895年11月16日,康有为将张之洞的建议向尚在湖北的汪康年作了通报,欢迎汪尽快到上海接收强学会的事务③。所以当张之洞下令由汪康年接管上海强学会的事务时,康有为不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期望汪康年的到来能为上海强学会带来新的希望④。
接到张之洞的命令及康有为的邀请后,汪康年并没有像康有为所期望的那样离开湖北赶往上海。他此时似乎无意于放弃自己一直在积极筹办的译报馆和中国公会,而且由于京沪两处强学会内部纷争的消息不断传来,使他和他的朋友都觉得介入康梁系的矛盾之中并不是一件太合算的事情,不如留在武汉干自己的事情,与京沪两地“不即不离”,这或许是上策⑤。
汪康年最终离开武汉到上海接手强学会的会务,是因为他在武汉筹办译报馆与学会的事也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而他刚到上海的时候,恰恰又遇到张之洞停办强学会与强学报的命令发布的时候,所以他一介入上海强学会的会务,不是为了强学会的发展,而是按照张之洞的意图怎样进行强学会的善后。
在办理强学会善后事宜的时候,汪康年似乎有意于利用强学会的结余款项作为他一直想办而没有办成的译报馆,为此他曾与张之洞进行过协商,但张之洞并不赞成汪康年在上海另办新的报纸,所以张对汪康办理强学会善后事宜的权限似乎也有所限制,仅将强学会的余款75.14元交给了汪康年,热存银730两则直接移交给了经元善。
汪康年准备利用强学会余款创办新报的想法未能顺利实现,不过他对此也没有彻底灰心,而是将强学会原租房屋一年的租金追回了一半,得350元, 又将强学会购置的办公用品、图书等加以变卖,得200余元⑥。有了这笔钱作基础, 汪康年继续进行他创办新报的准备。他计划以这些款项为基础,以京师官书局上海分局的名义出版他构思已久的《译报》,并谋求与康梁进行合作。
《译报》的计划遭到了汪康年的朋友吴樵、汪大燮、沈曾植、叶瀚等人普遍反对,他们既认为京师官书局“诸人大率非我族类,万万不便沾染”⑦,也觉得与康有为等人恐怕并不好合作,“近则见挤于康,退又贻诮于人”⑧,与其将来发生冲突,不如从一开始就谨慎从事。
惟一赞成汪康年计划的朋友是黄遵宪。黄遵宪本为强学会同事之人,此时正以道员奏派办理苏州通商事务,与康有为“朝夕过从,无所不语”⑨,具有浓厚的维新思想,对张之洞下令停办上海强学会本来就不满意,也一直试图设法重新振兴之。而汪康年的办报想法正与黄遵宪合,黄遵宪毫不犹豫地对汪康年给予全力支持。他自愿捐献1000元作为新报开办费,并表示:“我辈办此事,当作为众人之事,不可作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吾所集款,不作为股份,不作为垫款,务期此事之成而已。”⑩
有了黄遵宪的支持,汪康年筹办新报的进展迅速加快。1896年4月, 汪康年连电催促正在京城的梁启超南下,参与筹办具体事务(11)。梁启超对汪康年在上海筹办新报的事情早有所闻(12),他在收到汪的电报后,稍做准备就离开了北京。
梁启超到了上海之后,因汪康年的介绍与黄遵宪相识,在他们三人共同策划下,就办报宗旨、体例、内容等基本上达成共识(13)。按照黄遵宪的设想,新创办的这份杂志的管理体制应该借鉴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的思想,实行议政与行政的分离,选举一个比较超然的董事会负责制定章程和制度。
办报的基本方针定下来之后,《时务报》的名称也随之确定。他们以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吴德潚、邹代钧五人名义印制《公启》两千张分送各处同志,此《公启》有30条,为梁启超初拟草稿,由黄遵宪“大加改定”,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时务报》的创办宗旨,详细介绍了《时务报》招股集资的方法与方式。其中办事条规第九条规定:“本报除住馆办事各人外,另举总董四人,所有办事条规,应由总董议定,交馆中照行。”(14) 显然,《时务报》创办同仁均接受了黄遵宪的制度设计。只是由于创办期的时间仓促,他们并没有就这一动议详加讨论,更没有考虑立即实行,这为后来的纷争留下了种子。
《公启》的发布获得了各地同志的响应,各地认捐的消息不断传来(15),而原本不太支持汪康年在上海办报的张之洞,也同意将原上海强学会人余款转给汪康年作为办报经费。
《时务报》最值得看的、也是当时之所以风靡一时的,还是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从第一册开始直到他离开《时务报》止,几乎每一期都有他那议论新颖、文字通俗、笔头常带感情的文章。在《时务报》第一册上,署名为梁启超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篇为从第二册开始连载的《变法通议》之自序。前一篇相当于《时务报》的发刊宣言,主要列举西方近代国家报纸的发达与政治进步的互动关系,期待通过办报营造中国社会上下不隔的正常秩序;后一篇所序的《变法通议》是梁启超的成名作,这篇文章对于中国当时将要到来的变法维新运动所可能涉及到的问题都有所论述,这些观点对于冲破旧思想的禁锢,对于新思想的传播起到过重要作用。
《时务报》第一册出版发行之后,在国内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北京的朋友如汪大燮、沈曾植、李岳端、王鹏运等对编排及内容都感到满意,但同时也劝告汪康年、梁启超等要谨慎从事,不要有意去触犯朝廷的禁忌,“不必作无谓之讥评”(16),以免出征未捷而身先死,再蹈强学会的覆辙。
从湖南方面传来的消息更是令人振奋,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称看了《时务报》第一期,确实感到梁启超真的是“旷世奇才”,并相信《时务报》如果能够坚持办下去,“必能渐开风气,增光上国”(17)。邹代钧也从湖南致函告诉汪康年,他已经收到的一百份已经散发完毕,现在向他索要《时务报》的人很多,嘱汪康年尽快补寄(18)。至第二年底,邹代钧在湘的销售数已达七百册(19),还不包括不断加寄的一些合订本。
在湖北,黄绍箕致函汪康年称赞《时务报》“至美至美”(20),张之洞的幕僚叶瀚致函汪康年称梁启超“大才抒张”,为不可多得的办报天才(21)。郑孝胥在南京致函汪康年,称“梁君下笔,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慨。”(22) 正在“重庆舟中”的吴樵“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诵万遍,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炽;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我辈亦当互相称庆。”(23) 总之,《时务报》的出版,在全国各地都获得了良好反映,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销行万余份,为中国有报馆以来所未有之盛况。
《时务报》的畅销,无疑是梁启超的文笔与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不应该否认的是,汪康年的经营及其与各方面的疏通交流也起到了极端重要的作用,而黄遵宪多年来积累的人事资源也为《时务报》在南北各地的推广以及劝捐、招聘东西文翻译人才等都起到过重要作用(24)。《时务报》走上正轨后,黄遵宪奉调离沪,馆中日常事务由汪康年打理,然重大决策均向黄请示(25)。
二、裂痕初现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给当时中国一度沉闷的政治格局中注入一股清新的信息,梁启超因此而“暴得大名”,《时务报》也因此而畅销,甚至连最初不太支持汪康年创办《时务报》的张之洞,在读过几期后,也致信梁启超,邀请梁到湖北一游,称有要事相商,并随信捐助银元500元(26)。 张之洞还下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称该报“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27)
张之洞的支持是真诚的,但张之洞的身份毕竟不同于汪康年、梁启超等人,他对《时务报》的支持是因为《时务报》的言论合乎官方政策和他的主张,而一旦《时务报》的言论不再合乎官方政策和他的主张,再指望张之洞继续支持《时务报》显然也不太现实。
在张之洞“公费订阅”《时务报》的通知下发不久,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五册发表他的《变法通议》之《论学校》一节中批评张之洞署两江总督时创建的“自强军”用高薪聘用洋人似乎有媚洋的嫌疑,又称满洲人为“彼族”。这自然引起张之洞的极端不快,他一方面准备不再“公费订阅”《时务报》,另一方面考虑另外创办一报馆,专门批驳《时务报》(28)。
张之洞的不满通过吴樵及时转达给了梁启超,但梁启超对此并不太在意。他在随后出版的第八册之《论科举》中对倭仁之反对西学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在第十册之《论学会》中对当时尚在思想文化界占主导地位的汉学及其首领纪晓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为正是以纪昀为首的汉学家的崛起遏制了中国学术团体的正常发展。这无疑触犯了清廷的忌讳,时任张之洞幕僚的纪昀五世孙纪钜维“大怒”不已,张之洞看了之后也甚为不满,张授意其亲信梁鼎芬著文反驳(29)。
汪康年虽然在《时务报》创办之初与梁启超有某些意见分歧,但当他看到梁因《时务报》而名誉鹊起,也一度跃跃欲试,开始著文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梁启超还要激进。在《时务报》第四册,汪康年发表《中国自强策》,在第九册又发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公开宣传当时还比较忌讳的民权思想(30)。
汪康年的想法或许是要建立自己报人及政论家的形象,不料他这些激进的看法发表之后,立即引来张之洞一系列的批评与反驳,叶瀚、梁鼎芬等纷纷致函汪康年,劝他少发表这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伟论”(31),“万万不可动笔”(32),做好自己的报馆经理就行了。在长沙的邹代钧也致函汪康年,劝其不必撰写文章(33)。
张之洞的不满及各方朋友的劝说,引起了汪康年的重视,为了使《时务报》能够生存下去,汪开始注意调整《时务报》的言论,对一些偏激的言论稍有矫正。另一方面,汪也接受武汉方面的告诫,更加注意对《时务报》人事、经济等实际权力的掌控。
当汪康年对《时务报》进行调整的时候,梁启超请假回广东省亲。在省亲期间,梁启超继续履行主笔职责,不时为《时务报》提供稿件。1896年11月17日,梁启超致信汪康年,称由于《时务报》的影响不断扩大,广东康广仁、何穗田等计划仿照《时务报》的体例在澳门创办一旬刊,准备借用《时务报》的名气,取名为《广时务报》,又告诉康、何等人必欲得梁启超为新刊物的主笔,只是他并没有立即答应(34)。25日,梁启超又致信汪康年,对《广时务报》作了更加详细的报告,强调之所以取名“广时务报”主要是基于两个意思,一是推广之意,一是谓广东之《时务报》。梁启超建议汪康年尽量促成此事,“令彼知我实能办事,则他日用之之处尚多也”(35)。
对于梁启超的建议,汪康年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反对,《时务报》第十五册刊登的《广时务报公启》,基本上是梁启超对汪康年报告的那些内容,注明《广时务报》将由梁启超“遥领”,并称对于近事以言《时务报》所不敢言。
《广时务报公启》的刊登,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吴德潚、邹代钧、吴樵等群起反对,吴德潚认为,《广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似乎可以兼领,但必须坐镇上海(36)。吴樵认为,《广时务报》“断不宜与《时务报》相连。惟其能言《时务报》所不能言,尤不可不如此。”甚至对于“广时务报”之名,吴樵也建议更改报名,不要造成与《时务报》有关系的印象,“与其两败,毋宁慎之于始。”(37) 对于吴樵的态度,谭嗣同致函汪康年解释道:“铁樵深怪贵馆不当与《广时务》馆粘连一片,恐一被弹而两俱废也。”(38) 邹代钧也对梁启超兼领《广时务报》主笔表示不满,认为梁如执意留在澳门担任主笔则是“大有阴谋”(39),他建议汪康年务必说服梁启超放弃这一想法。
反对《广时务报》与《时务报》发生联系,本是出于对《时务报》的爱护,他们的共同担心是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广时务报》放言高论,虽然能够起到与《时务报》遥相呼应的效果,但总有一天会将《时务报》托下水。他们的真实想法,是各地的维新报刊各自另立门面,暗通消息,以成鼎足之势,而不必在表面上连为一体,以免一损俱损(40)。应该说,这一主张是有理有利的。然而或许是由于沟通不够,或许是汪康年的解释对梁启超来说太缺乏说服力,《广时务报》虽在后来改名为《知新报》,梁启超也只兼任一般的撰稿人,但梁对汪的误解却由此而加深(41)。
1897年3月,梁启超从广东回到上海,在《时务报》工作的同门梁启勋、 韩云台向梁抱怨汪康年在这段时间对他们多有不公,而馆中的佣人甚至也对他们另眼相看。对于梁、韩的抱怨,梁启超当然不会高兴,他在随后写给黄遵宪的信中,也多少抱怨汪康年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不尽妥当。黄本来就与汪康年稍有矛盾,在《时务报》筹办之初就不希望汪一人揽权,于是在他收到梁启超的信后致函汪康年,再次提出仿西方近代国家立宪政体,将立法、行政分开,设立报馆董事会,提议汪康年辞去《时务报》馆总理的职务,而改任总董,驻沪照支薪水,任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提议由吴樵或康有为的门人龙泽厚担任总理(42)。
梁启超致信黄遵宪或许仅仅是为了获得黄的同情而已,而黄致汪的信则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梁启超认为,他自己虽然不太满意于汪康年的一些举措,但事情尚未闹到需要汪辞去总理职务的境地,《时务报》馆的总理在当时非汪莫属,于是他抱怨黄的建议实在是“卤莽不通人情”,反而使梁启超自己在报馆中的处境更为尴尬(43)。汪康年在收到黄遵宪的信之后当然很不高兴,他觉得黄遵宪与梁启超联手是在有意识地排挤自己,他复函黄遵宪进行反驳(44),“深衔”黄氏,“日日向同人诋排之,且遍腾书各省同志,攻击无所不至。”黄、汪、梁的矛盾逐步公开化。
其实,黄遵宪提议中不便明说的理由主要是他感到汪康年应酬太繁,不能兼办馆中全部事务,故而希望汪氏让出报馆的实际位置,而利用自己的所长负责馆外联络应酬。而汪康年的办事宗旨也确实为黄遵宪留下了这些把柄,汪氏素来认为“必须吃花酒乃能广通声气,故每日常有半日在应酬中,一面吃酒,一面办事。”这种办事风格显然与具有外国生活经历的黄遵宪格格不入。
黄、汪、梁几近公开的矛盾对于刚有起色的《时务报》极为不利,他们的一些共同朋友如谭嗣同、张元济、夏曾佑、吴德潚、邹代钧等得知此事后也万分焦急,纷纷劝说他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因正常的意见分歧而影响报馆的事务(45)。
在各方友人的劝说下,也正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梁启超主动与汪康年和解,他向汪解释说,这次矛盾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双方性格差异所致,相互之间又缺乏及时的沟通,至于黄遵宪的建议,也不应从消极及权力一层去分析,黄的建议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为了《时务报》的未来发展,有其合理成分在。他与汪康年共约,既然各自的意见都已讲明,此后当“誓灭意见”,为《时务报》的未来贡献各自的心智(46)。
三、乘虚据为己有
或许由于梁启超的大度,使梁、汪之间的冲突得以消解。然而这种消解并没有维持很久,他们之间却又因其他方面的问题再次冲突。梁启超在此后所发表的文章中,一反《时务报》创办之初的承诺,而热衷于宣传康有为的“三世说”、“大同说”以及创立孔教等主张,在时务报馆中的同门甚至以康有为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如此狂妄的说法当然激怒了也在时务报馆主笔政的古文经学干将章太炎的恼怒,章太炎借酒壮胆,大骂康有为为“教匪”,并与康门弟子发生极不雅观的肢体冲突(47)。
章太炎是汪康年的浙江同乡,康门弟子与章太炎大打出手以及章太炎因此愤而辞职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外间纷传《时务报》馆“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48),将报馆内部组成无形中划分出浙、粤两系人马的界限,这势必增加两系人马的首领梁启超与汪康年之间的相互猜疑。
当是时,吴德潚方署钱塘县令,计划在杭州西湖赁一屋,购书数千金,并聘请英、法教员各一人,邀请梁启超前往(49)。吴德潚的邀请对“数月以来,益困人事”的梁启超很有吸引力,他决意离开时务报馆,隐居西湖静心读书(50)。谭嗣同对梁启超西湖读书计划表示赞成,以为有助于缓解《时务报》的内部矛盾(51)。
梁启超隐居西湖读书的计划并未成为现实。1897年8月, 黄遵宪奉调署湖南按察使路过上海的时候,与汪康年等人面谈,再次提出设立《时务报》董事会的建议,梁启超赞成黄的建议,并劝说汪赞成,寻求一致(52)。而汪康年对黄的建议根本不予考虑,寸步不让,他甚至对梁启超说:“公度欲以其官稍大,捐钱稍多,而挠我权利,我故抗之,度彼如我何?”(53)
黄、汪之间的冲突严重影响了《时务报》的前程,引起了各方友人的关注,他们纷纷设法劝说汪康年不要一意孤行。汪大燮致函汪康年称黄的建议值得重视,“办事之人不必议事,奉行而已;议事之人不必办事,运筹而已。此至当不易之论。”(54) 张元济称黄的建议是对事不对人,根据他的了解,黄对汪康年“并无贬词”(55)。在各方友人的劝说下,汪康年终于接受了黄的建议,成立了董事会。
在上海与汪康年交涉的不愉快肯定影响了黄遵宪对《时务报》的立场,因此当他离沪赴湘就任的时候,大概已有放弃《时务报》的想法。所以当他刚到长沙得知湖南创办时务学堂的消息后,迅即向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竭力推荐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56)。黄还致信汪康年,主张梁启超担任学堂总教习的同时遥领《时务报》主笔(57)。谭嗣同、熊希龄、邹代钧等也纷纷向汪康年施压,甚至声言如果汪康年不同意放梁启超赴湘,他们不惜“蛮拉硬作”。
对于湖南的邀请,梁启超很有兴趣,其实早在北京强学会遭到封闭之后,他就有赴湖南开一片新天地的想法。他当时计划如果《时务报》不能顺利创刊,他就转赴湖南(58),以为在“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为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于他省,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59)。对湖南新政寄予无限的希望。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当他收到邀请后,便明白地表示同意。
对于黄遵宪的建议,汪康年处于两难境地,他既希望梁启超顺利离开《时务报》而又不太伤害双方的感情,但对于梁启超在湖南继续遥领《时务报》主笔的建议,似乎并不能接受。所以,汪康年拒绝了黄遵宪,不同意梁启超离开《时务报》前往湖南。
汪康年的拒绝使湖南方面极不高兴,熊希龄致函正在南京的谭嗣同,请他亲到上海向汪康年“哀吁”,如果汪康年执意不肯放行,那么他们将不惜与汪冲突而“豪夺以去”。谭嗣同劝汪不如“自劝”梁启超往湖南任职,“则尚不失自主之权,而湘人亦铭感公之大德矣”(60)。汪康年向谭嗣同解释,他之所以不愿放梁启超去湖南完全是出于对《时务报》未来发展的考虑,绝没有其他任何想法,并将自己心中的苦闷向谭一一道明。谭对汪的解释表示理解,建议汪“毅然决然不允所请。”(61)
汪康年不愿梁启超离开《时务报》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而梁启超出于多种原因急于接受湖南方面的邀请,后经协商达成一致,梁启超如愿以偿,1897年11月中旬赴湖南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
梁启超抵达长沙后,继续兼任《时务报》主笔。但他与汪康年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距离扩大而有所缓和,反而越演越烈,终于导致彻底破裂。
汪、梁关系的破裂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二人似乎都有责任。从梁启超方面说,他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于公于私都不能说有什么错误,但他以遥领主笔身份寄回的三篇文章实在很难让汪康年满意,这三篇文章似乎也不是梁的认真之作,三篇文章的标题为《南学会序》、《俄土战纪序》、《经世文编序》,这三篇应景文章显然与“主笔”的身份不太相符,引起汪康年的不满也就在情理之中。
当然,梁启超刚到长沙也确实很忙(62)。既然忙于时务学堂,又何必一定要遥领《时务报》的主笔呢?而且,由于梁启超已无法安心为《时务报》作文,受到直接影响的还是《时务报》,《时务报》的发行量因没有梁启超而急剧下降,这就迫使汪康年必须寻找能够代替梁的人,以便保持《时务报》的发行不致过分下滑(63)。1898年2月16日,也就是汪康年收到梁启超寄来最后一批稿件之后的整整一个月,汪康年与郑孝胥晤谈,欲请郑为《时务报》总主笔,改梁启超为“正主笔”,在编辑体例上,汪康年也准备将原来以梁启超为主的“论说”栏进行调整,“主选外来文字登之报首”(64)。这种改变实际上是汪康年的无奈,既然得不到梁启超那样的文字,则不如不要。
汪康年将他的计划及时通知了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并告诉他们自己将前往湖南面商《时务报》的困难,以寻求解决之道。只是在这封信中,汪康年在谈及原因时对梁启超不能如约向《时务报》供稿也略有指责,这就引起了梁启超的大怒和彻底翻脸(65)。后经一番交涉,再加上梁启超忙于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时务报》继续由汪康年主持,而且逐渐演变成汪康年的私有产业了。
四、内讧再起
自到湖南任职后,黄遵宪已无力“遥领”《时务报》馆务,而梁启超也无暇继续为《时务报》供稿,更不要说“遥领”主笔了。《时务报》的控制权自然落到了汪康年的手中。梁启超、黄遵宪等人虽然心中有气,但时局的急剧发展特别是康有为受到朝廷的重用直接介入新政,梁启超在受到光绪帝的召见后奉旨筹办管理译书局事务,而黄遵宪则奉命出使,这多少抚平了他们心中的不满。
不过,新政的进展并不顺利。康有为的许多建议都受到朝中重臣的阻挠而无法推行,于是康有为在乃弟康广仁及梁启超的建议下(66),于1898年7月17 日通过御史宋伯鲁上书光绪皇帝,建议将汪康年主持的《时务报》改为官报局,并建议由梁启超主持,以便为将来发生的不测准备一条退路(67)。
光绪皇帝收到这份奏折后并没有当即接受这一建议,而是批给孙家鼐酌情处理。孙家鼐于7月26日向光绪皇帝提交了处理意见:一、 不同意调梁启超主办《时务官报》,理由是梁启超已奉旨办理译书局事务,现在学堂既开,亟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若调梁启超兼办官报,恐其分散精力,不利于译书局的工作。二、建议调康有为督办官报。但对改为官报之后的《时务报》,孙家鼐在这里提出比较严格的管理建议:一是宜令主笔者慎加选择,如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挟嫌妄议、渎乱宸听者,一经查出,主笔者不得辞其咎。二是既为政府主办的报纸,就不能如民间报纸那样自由议论,应该规定该报不得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其主要功能是翻译外国报章杂志上有用的文章,俾阅者略知各国情形。三是经费主要应该由该报自筹及其发行所得,政府不必强行要求各省督抚用公费订阅和摊派,至于开办之初的部分经费,可以考虑由上海道代为设法,但应由康有为自往筹商(68)。
孙家鼐的处理意见虽然蕴含着许多的阴谋,但其通情达理,公事公办,在表面上无可挑剔,于是光绪皇帝当天批准了孙的建议(69)。康有为原本准备为梁启超谋得一个丰厚的实职,却不料被更精明的孙家鼐算计,孙的调虎离山之计实在是期待将康有为赶出京师。
从康有为的本意说,他一直感觉到梁启超自被光绪皇帝召见后仅仅获得一个六品的译书局主管的职务实在有点冤枉,他也曾多次想方设法改善梁启超的地位,无奈他们作为政治新锐受到官场各方面的制约,康、梁等人的所有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懊丧之余,梁启超多次想过离开京城南下继续办报的出路,他似乎通过自己能力的重新评估,觉得自己在舆论宣传方面可能更擅长一些。另一方面,梁启超执意要拿回《时务报》还与他和汪康年之间的矛盾日趋恶化有关。随着梁启超前往湖南尤其是追随康有为来到京师从事政治活动之后,汪康年与梁启超之间的关系基本结束,梁启超对《时务报》的影响力也就无从说起。为了挽回他对《时务报》的影响力,似乎也为了弥补他那个六品卿衔的不足,他借助于政府的压力试图迫使汪康年屈服。梁启超的这些想法曾向康有为表示过,康有为也曾托人致信汪康年,劝说汪将《时务报》总经理一职让给梁启超,并称梁启超“新蒙宠眷”,如果由梁接任总经理,可令《时务报》“声价跃起”,重现辉煌。
当康有为推荐梁启超的建议不被接受反而任命他自己接管《时务报》之后,康有为只好将计就计,赶忙致电汪康年:“奉旨办报,一切依旧,望相助。”期待接手之后再作打算。随后再致函表达自己不得不接受主持官报局的无奈心情,希望汪康年在移交的过渡期能够很好地配合。
无奈汪康年根本不吃康有为这一套,他从纯商业立场回敬康有为,称我汪康年为《时务报》的创办人,梁启超原为我所聘用的主笔,梁今天的名声都是“藉吾报以得荣显,何遽欲反客为主?”(70) 所以,从这种种迹象看, 康有为改《时务报》为官报并请清廷委派梁启超兼职主持的建议,与其说是康有为本人的建议,毋宁说正是梁启超所期待的,或者干脆就是梁启超的建议与想法。
不料,孙家鼐的智慧打破了康、梁的梦想,而孙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反建议,也实在是出于康有为在官场上不太遵守游戏规则、人际关系急剧恶化的考虑。在大学堂的人事布局问题上,康、梁主导的大学堂章程明显地侵犯了作为管学大臣孙家鼐的利益,孙家鼐的反建议说明孙家鼐从内心已对康有为彻底失望,他似乎不愿意再见到康有为。
而且,从当时的情况看,孙家鼐找准机会就打压康有为也不是个人恩怨的孤立事件,事实上孙的做法在中央政府的层面也有许多支持者和叫好者,他们出于对康有为的厌恶,借助于孙家鼐之手去铲除康有为这个政治场上的“另类”,这可能也是孙家鼐反建议的一个重要背景。
康有为在获得光绪皇帝的召见后格外猖狂,他似乎以为在光绪皇帝的主导下一切都会按照他的设计去做。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康有为不知收敛,“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71),树敌太多而又不自知,积怨甚深而又自以为是守旧势力太大,四面出击,大包大揽,以小小工部主事的身份不断与朝中重臣、权臣发生冲突,那么不管你有多大的能力与抱负,政治场的游戏规则都是希望你出局。
孙家鼐调康有为督办官报局的反建议确实促成了康有为陷入“陷人自陷”的困境(72),但孙的建议根本不提官报局的经费问题也委实欺人太甚,为康有为的反击留有足够的余地。7月31日,康有为向清廷呈递《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 表示接受督办官办的委任,但提出比较苛刻的经济资助条件,并提出依旧例用类似于公款订阅的方式加以通融,将皮球又踢到了孙家鼐的一边。
开办费及各项经费问题对孙家鼐来说根本不构成问题,倒是康有为派人与上海汪康年方面的交接并不顺利。事实上,当康、梁挟政府之力欲强行接收《时务报》的时候,尤其是康有为草拟的奏折中提出将各地创办的民间报纸逐步收归官办的消息传出之后,南北舆论界对康、梁的做法基本上都不以为然,都觉得康、梁的做法实在过分。即便相当同情康、梁的维新阵营中的人物如张元济、叶瀚等,对于康、梁的做法也无法苟同,对于《时务报》的未来深表忧虑,对维新阵营“同气之残”深感痛心。被动的汪康年首先在道义上赢得了舆论的同情。
其实,从汪康年方面来说,他不仅对康、梁改《时务报》为官报的活动与用心了如指掌,而且对于《时务报》实际上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正欲放弃而不得机会,康、梁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说正迎合了汪康年的内在心情,不过出于调侃,出于对康、梁的戏弄,汪康年不愿将《时务报》和平地拱手相让,他想尽办法羞辱、收拾康、梁。
光绪皇帝将改《时务报》为官报的奏折批给孙家鼐处理的第二天,汪大燮即从京城致函汪康年报告了这一消息,并称张謇等人对康、梁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建议汪大燮去找孙家鼐申诉商报改官报的条件与委屈,但汪大燮自认为孙“无肩”,没有担当,如果将这一切都向孙家鼐说明,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他建议汪康年要抓紧将《时务报》一切往来账目及档案尽快清理出来,“此事此时即不归官,将来必仍与君为难,断无好下台。兄意即不归官,亦可趁此推出。京城纷纷言近来《时务报》之坏,不堪入目,盖欲打坍局面也,更不如归官为妙。”(73) 由此不难想见汪康年等人面对《时务报》改官报这一契机的微妙心情。
汪康年已对日趋没落的《时务报》不感兴趣,但由于有各方面的道义支持,使他觉得有必要与康、梁斗争一番以回报各方面的支持。他利用自己各方面的管道从容布置,先是建议此时对康、梁已甚为反感的张之洞出面奏请清廷将《时务报》改为《时务杂志》继续出版。张之洞原则上接受了汪康年的这个建议,但对改名为《时务杂志》的名称则不太满意,他授意改“时务”二字为“昌言”,以符合光绪皇帝上谕中“从实昌言”的涵义,并同意委派其幕中重要人物梁鼎芬出任《昌言报》总理,协助汪康年将《时务报》改版,以《昌言报》的名义继续出版,而将《时务报》的空名留待康有为来接收。有了张之洞的支持与授意,汪康年从容不迫地应对康、梁的紧逼,不慌不忙地将《时务报》馆门额及《时务报》的报头均改为“昌言”二字,并在上海《申报》及天津《国闻报》连续刊登《告白》,声明“康年于丙申秋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74),现在尊奉上谕,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继续出版,原《时务报》名则留给钦差督办康有为。
五、无聊的口水战
汪康年的“运动力”本不减于康、梁,他的背后既有张之洞等大员的支持与同情,更得同业之多助,所以从《时务报》到《昌言报》,汪康年不仅仍旧袭用《时务报》的版式,而且利用原来的分发网络,一期也没有停止。这实际上已对康、梁构成了极大的羞辱,而汪康年的声明更将改官报事件公开化,南北各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大伤南海体面。”(75) 康有为得知这些消息后极为震怒,他气急败坏地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西布政使翁曾桂等军政要员,指责汪康年这些做法是在违抗朝廷的旨意,要求他们施加压力迫使汪康年交出《时务报》并停止刊行《昌言报》。
对于康有为的要求,张之洞根本不予理睬,更何况这一套完整的计划正是张之洞一手策划出来的呢?张之洞为此致电管学大臣孙家鼐,称《时务报》原为汪康年募捐集资所创办,从未领取官款,世人皆知《时务报》为一份典型的商办刊物,现在朝廷责成康有为办官报,他自可去办,而汪康年遵照朝廷的旨意另立名目,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似与康有为办官报并不冲突,何得诬为抗旨?对于《昌言报》,岂有行禁止之理?所以,康有为所请禁止发行《昌言报》一事, 碍难照办(76)。孙家鼐原本就对康有为甚为反感,而排挤康有为出京的主意正是他出的,所以他得到张之洞的电报后一点都不吃惊,他甚至颇感高兴地复电张之洞,称“公所言者公理,康所言者私心,弟所见正与公同,并无禁发《昌言》之意,皆康自为之。公能主持公道,极钦佩。”孙家鼐显然有意让康有为难看。
在南京,两江总督刘坤一接到康有为要求封禁《昌言报》及勒令汪康年交出《时务报》的电文后,立即批转上海道蔡钧,蔡钧很快找到汪康年,将康有为原电抄交,而汪康年早已做好布置和准备,他向蔡钧详细介绍了《时务报》的创办原委及其与康、梁之间的冲突始末,蔡钧对汪康年的处境深表同情,遂将汪“所有为难情形”电复刘坤一,而刘坤一据此上奏清廷,称康有为电奉旨改《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私改为《昌言报》,抗旨不交等语。光绪皇帝闻此大怒,遂命黄遵宪道经上海时,查明原委,秉公核议电奏,毋任彼此各执意见,致使创办官报的事情不了了之(77)。
黄遵宪为《时务报》历次纠纷中的当事人,由他出面查明《时务报》纠纷的原委显然是不合适的。事实上,当康有为请求官方协助向汪康年施压的同时,黄遵宪就联络吴德潚、邹代钧、梁启超对汪氏进行反击,他们于7月29日联名在《国闻报》上发表声明,强调《时务报》是他们四人联合汪康年共五人共同创办的,并非如汪康年《告白》中所说的那样,是他汪氏创办而延请梁启超为主笔(78)。紧接着,梁启超更利用自己手中的笔与汪康年在南北各报进行了一场“同气之残”的“告白战”。梁启超抓住汪康年《告白》中的漏洞给予猛烈攻击,他在《创办时务报源委记》中强调他不仅是《时务报》的创办人之一,对《时务报》的辉煌立下过汗马功劳,更强调《时务报》之所以得以创办和顺利出版,正是利用了上海强学会的余款,所以要谈《时务报》的创办,就不能湮没康有为之“旧迹”(79)。至于《时务报》后来的巨大亏空,汪康年难辞其咎。
梁启超的表白为康、梁挽回了不少面子,汪康年在稍后发表的《书创办时务报源委记后》一文也不得不承认,“康年既不欲毛举细故以滋笔舌之繁,尤不敢力争大端以酿朋党之祸,盖恐贻外人之诮并寒来者之心。良以同志无多,要在善相勉而失相宥。外患方棘,必须恶相避而好相授。”汪康年这番表白,虽然有承认梁启超指责为事实的意思,但其宽容的姿态使其在道义上又比梁启超咄咄逼人的文辞更赢得了舆论的同情。
与梁启超与汪康年进行口水战的同时,康有为继续在政治层面对汪康年施加压力,从经济层面争取清廷更多的支持,他实际上似乎准备将官报局作为一桩商业买卖进行运作,似乎也有意以此退出政治场。9月1日,康有为将《时务报》的内幕及筹办时务官报的情形向孙家鼐汇报,但主题却是办报的经费格外困难,希望孙家鼐从经费或公款订阅上予以方便。这实际上是在向孙出难题。康有为称:“《时务报》之设,经费皆有士大夫捐助。今改为官报,则无人捐款。此报前经湖广督臣张之洞等札行州县阅看,每州县每年报费共银四元,未便骤增至十二元。捐款既无,价又难增。既为官报,自应拨以官款。拟照官书局月拨千金,请旨饬下两江督臣在上海洋务局按月拨交官书局一千两,以资经费;另拨六千两,以资开办。官报既发明国是民隐,各省群僚皆应阅看,以开风气。且教案既繁,交涉日多,官欲通外国之故,尤以阅报为要。应请旨饬下直省督抚,令司道府厅州县文武衙门一律阅看。用报若干份,将报费解向上海官报局,按期照数由驿递交各省会分散各衙门,每年仍收四元,仍按湖广督臣张之洞旧例,由善后局先行垫解官报局,以资办公。”如果按照这个办法去执行,这实际上是一桩极具商业价值的生意。康有为的内心深处或许不过是以此难为孙家鼐,不料孙家鼐的政治精明远胜于康有为,他不仅没有回绝康有为的请求,而且如数如实地将康有为所要求的数字与办法上报给了光绪皇帝,“臣以康有为所筹事尚可行,请俯如所请,仅具折呈明。”(80) 孙家鼐的惟一目的,似乎就是将康有为赶出京城,至于经济上的区区数千两银元,在孙家鼐看来似乎并不构成障碍。
孙家鼐的建议很快获得了光绪帝的批准,光绪帝同意参照所请,“以为久远之计,著照官书局之例,由两江总督按月筹拨银一千两,并另拨开办经费六千两,以资布置。各省官民阅报仍照商报例价,著各督抚统核全省文武衙门差局书院学堂应阅报单数目,移送官报局,该局即按期照数分送。其报价著照湖北成案,筹款垫解。”(81) 对于孙家鼐代奏的康有为所提出的条件,光绪皇帝没有丝毫的折扣。按理说,康有为应该离开北京到上海积极筹办了。
不过,康有为依然不愿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当上海方面的接收工作遇到汪康年的抵制的时候,康有为曾建议孙家鼐在京师另行重组官报局,但孙家鼐秉承相当一部分同僚的意思,一定要借此机会将康有为排挤出京师,坚拒康有为的建议,坚持要求康有为离开京师,前往上海。他甚至不惜通过其他手段调动光绪皇帝再次施压,9月17日,光绪皇帝发布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要求康有为迅速离京(82)。 康有为接到这份谕旨后,似乎确曾准备前往上海,可惜政变将发,康有为前往上海不再是接办官报局,而是流亡途中的一站而已。
至于黄遵宪,他于8月22日奉谕旨道经上海查明《时务报》之争的原委并负责向光绪皇帝报告,但他因故直到9月15日方才抵达上海,而当还没有抵达上海的时候,汪康年就于8月30日在《中外日报》上发表《上黄钦使呈稿》,先声夺人, 为其将《时务报》改《昌言报》的行为进行辩解。他强调《时务报》确实为众人集资合办,为典型的商办性质。至于皇帝谕旨命令康有为督办,并划拨开办费六千两,但谕旨中并未提及将《时务报》移交给康有为,故而他作为合办众人中的一员无权也不可能将《时务报》移交给康有为。再者说,皇上的谕旨鼓励民间广开报馆以开风气,《时务报》的报名既改为官办,我汪康年只好代表原《时务报》的创办者用《时务报》余款续办《昌言报》,以此“上副圣天子广开言路之盛心,下答捐款诸人集资委托之重任。”(83) 其实汪康年不必向黄遵宪详细汇报,作为《时务报》的重要创办人之一,黄遵宪对于《时务报》的内幕及康有为、梁启超与汪康年之间的争论与冲突比谁都要清楚,只是没有等到他拿出一个“秉公核议”的处理方案,政变发生了,康、梁逃亡国外,清廷下令停止《时务官报》的创办,于是关于《时务报》争夺战也就不了了之。
注释: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版;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梁启超致汪康年函》第4通,《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0页。
③ 《康有为致汪康年函》第1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664页。
④ 康有为:《致何树龄、徐勤书》,姜义华等主编:《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卷,第205—206页。
⑤ 《吴樵致汪康年函》第3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61页。
⑥⑩ 《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原委》,《知新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⑦ 《汪大燮致汪康年函》第66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29页。
⑧ 《叶瀚致汪康年函》第10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535—2536页。
⑨ 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11) 《吴德潚致汪康年函》第13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94页。
(12) 《梁启超致汪康年函》第5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31页。
(13) 《黄遵宪致汪康年、梁启超函》第10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335页。
(14) 《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原委》,《知新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15) 《邹代钧致汪康年函》第22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654页。
(16) 《汪大燮致汪康年函》第73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47页。
(17) 《陈三立致汪康年函》第13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983页。
(18) 《邹代钧致汪康年函》第35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683页。
(19) 《邹代钧致汪康年函》第63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749页。
(20) 《黄绍箕致汪康年函》第9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306页。
(21) 《叶瀚致汪康年函》第24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560页。
(22) 《郑孝胥致汪康年函》第1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971页。
(23) 《吴樵致汪康年函》第18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500页。
(24) 《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原委》,《知新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25) 《黄遵宪致汪康年函》第25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347页。
(26) 《张之洞致汪康年、梁启超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672页。
(27) 张之洞:《咨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28) 《吴樵致汪康年函》第27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518页。
(29) 《梁鼎芬致汪康年函》第41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900页。
(30) 参见蔡乐苏等:《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第382页。
(31) 《叶瀚致汪康年函》第18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547页。
(32) 《梁鼎芬致汪康年函》第35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97页。
(33) 《邹代钧致汪康年函》第35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683页。
(34) 《梁启超致汪康年函》第19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45页。
(35) 《梁启超致汪康年函》第20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46页。
(36) 《吴德潚致汪康年函》第28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13页。
(37) 《吴樵致汪康年函》第29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523页。
(38) 《谭嗣同致汪康年函》第3通,蔡尚思、方行主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95页。
(39) 《邹代钧致汪康年函》第44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703页。
(40) 《叶瀚致汪康年函》第35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578页。
(41)(43) 《梁启超致康有为函》,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
(42) 《黄遵宪致汪康年函》第25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348页。
(44) 《黄遵宪致汪康年函》第30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356—2357页。
(45) 《张元济致汪康年函》第18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704页。
(46) 《梁启超致汪康年函》第31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57页。
(47)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48) 《梁启超致汪康年函》第31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55页。
(49)(5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67、74页。
(51) 《谭嗣同致汪康年函》第16通,《谭嗣同全集》,第507页。
(52) 《梁启超致汪康年函》第35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58—1859页。
(53) 《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原委》,《知新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54) 《汪大燮致汪康年、汪诒年函》第83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66页。
(55) 《张元济致汪康年函》第10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689页。
(56) 《邹代钧致汪康年函》第61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743页。
(57) 《黄遵宪致汪康年函》第34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360页。
(58) 《梁启超致汪康年函》第5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31—1832页。
(59) 《梁启超致汪康年函》第8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34页。
(60) 《谭嗣同致汪康年函》第21通,《谭嗣同全集》,第511页。
(61) 《谭嗣同致汪康年函》第22通,《谭嗣同全集》,第512页。
(6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8页。
(63) 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第8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64)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册,第643页。
(65) 《梁启超致汪康年函》第29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53—1854页。
(66) 梁启超:《康广仁传》,《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专集之一,第96页。
(67) 康有为:《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2—324页。
(68) 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册,第432—433页。
(69)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册,第4144页。
(70) 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573页。
(71) 康广仁:《致易一书》,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2页。
(72) 参见蔡乐苏等:《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第448页。
(73) 《汪大燮致汪康年函》第96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87—788页。
(74)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75) 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573页。
(76) 张之洞:《致管理大学堂孙中堂电》,《张文襄公全集》卷156,中国书店1990年版。
(77) 《上谕》第147,《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59页。
(78) 《上海时务报馆告白》,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4页。
(79) 《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原委》,《知新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80)(83)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39、112页。
(81) 《上谕》第124,《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51页。
(82)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195页。
标签:时务报论文; 梁启超论文; 康有为论文; 张之洞论文; 黄遵宪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汪康年论文; 变法通议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