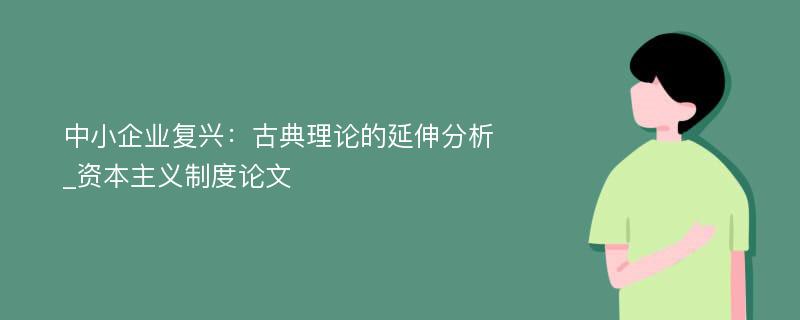
中小企业复兴:经典理论的扩展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小企业论文,理论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457 (2000)05—0034—05
一、问题的提出:中小企业复兴与马克思生产与资本集中理论是否相悖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积累及其趋势时指出,一方面,资本家有“狂热地追求价值增殖”的内在动机,另一方面,“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因此,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单个资本的规模由此而不断增大。在单个资本通过积聚而扩大规模的同时,通过竞争和信用这两个强有力的杠杆,单个资本之间还会发生资本集中。资本集中在推进企业规模扩张的广度和强度方面,远甚于资本积聚。“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注:《资本论》第一卷,688—689页。)生产与资本不断集中的发展趋势,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马克思分析这一问题时,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只是出现了并不稳定、并不显著的垄断萌芽,但此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演进,市场结构的日益垄断化,大企业在经济生活中统治地位的不断加强,中小企业数量减少及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下降,无一不证明了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诊断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就连一些西方经济学权威也不得不臣服马克思的生产与资本主义集中理论。里昂惕夫称赞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制度长期趋势的无比卓越的分析”,“财富的逐渐集中,中小企业的迅速消灭,对竞争的日益增长的限制……,一系列卓越的预见都实现了。”(注:W里昂惕夫,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意义》,《经济学文集》第一卷,78页。)产业组织理论权威谢勒尔也指出,“在众多著名经济学家中只有马克思独立预言,大企业将会发展到统治工业的舞台。”(注:F·M谢勒尔,D罗斯,《产业市场结构与经济绩效》,1990年第3版,78页。)
但是,70年代中期以来,中小企业在世界范围的愈益活跃及其在各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地位与作用的提升,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比重有了明显的上升,中小企业在各国GDP增长、 就业增加以及技术创新等方面都表现出不逊于甚至优于大企业的业绩,而且,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小企业发展呈现出进一步活跃、繁荣之势。正因为此,扶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成为当前许多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小的是美好的”再次成为经济理论界的“亮点”。在美国,1980年非农业企业数1300万个,1989年猛增到2010万个,所有增长几乎都是小企业。(注:高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与竞争》,南开出版社,1996年版,212页。)90年代美国“新经济”成就的取得,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风险型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欧盟,振兴中小企业是进一步增强欧盟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已成为所有成员国的共识,1995年马德里会议专门通过了“欧盟中小企业白皮书”。而在日本和韩国,摒弃长期的“重大轻小”政策,限制大企业垄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则成为摆脱危机、重振经济的重大举措。
自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企业规模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的长期发展趋势,到本世纪70年代确实发生了逆转,世纪之交,这一逆转趋势愈加明显。“产业组织结构正在经历周而复始般的嬗变,从19世纪初原始的小企业竞争到本世纪初大工业时代顶峰时期大企业为主的垄断竞争,然后,再回到知识经济时代小企业的合作竞争。”(注:仇保兴,《小企业集群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231页。)小企业的复兴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广泛的理论热潮,对规模经济理论的再认识就是一个典型代表。那么,中小企业的复兴是否与马克思生产与资本集中理论相悖?中小企业的兴盛是否意味着生产与资本集中的趋势出现停止甚或逆转?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具有两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把握当今世界企业规模的演变趋势,二是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正确处理“抓大”、“放小”、“扶小”之间的关系。
二、经典理论的扩展:集中是动态的、随技术演进而变化的长期发展趋势
1.中小企业的复兴并未改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与资本集中的长期发展趋势。虽然在不同的时期,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支柱产业的更替、经济运行状况及经济政策的变化等原因,生产与资本的集中程度会有所波动,例如美国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按四企业(即C4统计方法)计算的企业加权平均集中率,高于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前期。1963年为38.9%,1972年为39.2%,1977年为38.5%,1982年为37.1%。但是,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主要发达国家生产与资本集中的发展趋势,与马克思的分析结论则是一致的。在美国,100 家最大制造企业占制造业资产总量的比重,1925年为34.5%,1939年为41.9%,1950年为39.7%,1960年为46.4%,1970年为48.5%,1980年为46.7%,1987年为50.0%。在英国,按C3统计的市场集中率,1951年为29.3%,1963年为37.4%,1970年为41.2%,1973年为42.2%。(注:高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与竞争》,南开出版社,1996年版,21—27页。)其它发达国家的生产与资本集中状况在较长期内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被称作“小企业王国”的意大利也不例外。诚然,上述数据主要反映的是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中后期生产与资本集中状况。这一趋势在90年代仍在进一步发展。因为新一轮高新技术在为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机遇的同时,也推动了美、日、欧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支柱产业和经济制高点产业中企业规模的又一轮扩张,促成了90年代全球性的企业并购浪潮。因此,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应该是:一方面,中小企业的数量增加了,地位与作用增强了;另一主面,生产与资本集中的趋势仍在进一步发展。
2.中小企业的复兴表明生产与资本集中、企业规模大小演变是一个动态交替的过程。马克思所论证的生产与资本集中的发展趋势,并不是僵化的、直线型的发展趋势,而是动态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趋势。首先,马克思在得出生产与资本集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结论时,并没有作出单个资本规模只会越来越大、中小资本将不再存在的结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较小的资本挤到那些大工业还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领的生产领域中去。”(注:《资本论》第一卷,687。 )由于大工业不可能支配一切生产部门和一切经济领域,因而,在生产与资本总体上呈现出日益集中的长期趋势下,中小企业始终是存在的。其次,中小企业不仅始终存在,马克思关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大量分析还表明,在某些特定时期,中小企业还会表现出活跃与繁荣的局面。这是因为,当某些行业或整个社会的生产与资本集中达到一定程度时,将会停止、瓦解,而后继起新一轮集中,在这动态交替的期间,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当然会得到提高与加强。“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表现为不断的过程,最后表现为现有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许多人丧失资本。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不断与向心力一起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崩溃。”(注:《资本论》第三卷,275页。 )这里的“崩溃”即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危机的发生必然导致已经集中起来的“旧资本的分裂”和“新的独立的资本嫩芽的形成”。“新资本家手中的△C部分,力图排挤旧资本来取得自己的地位, 而且只要它使一部分旧资本闲置下来,强迫旧资本把旧位置让给它,使旧资本处于部分就业或完全失业的追加资本的位置,这就部分地获得了成功。”(注:《资本论》第三卷,281—282页。)这些分析清楚地表明:一方面,生产与资本集中的进程是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动态演进的过程,另一方面,在这个动态演进过程中,大资本由新资本嫩芽萌发生成,因而必然有中小资本(中小企业)活跃、繁荣的时期。第三,生产与资本的集中不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还是规模不断扩大的动态演进过程,即螺旋式的上升。在分析资本积累时,马克思就已明确指出,资本积累是“由圆形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在对产业革命、大机器应用对资本主义生产所产生影响的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个独立的工业企业为进行有效的生产所必须的资本的最低限额,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注:《资本论》第三卷,292页。)由此不难看出,技术进步、设备的大规模化是生产与资本集中规模递增的重要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的演变、技术演进、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是生产与资本集中动态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当代,由于宏观调节的反周期手段的普遍使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明显变化,但技术演进、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这些引起生产与资本集中动态发展的因素一直存在并发挥作用。众所周知,70年代中期以来,新一轮高新技术在实际生产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它至少在两个方面促成了中小企业的繁荣:一是造就了一大批高科技中小企业,即所谓“新资本的嫩芽”,其中一部分已经实现或正在进行生产与资本的集中,成长为大企业,如微软、英特尔:二是促使已经集中起来的、以传统技术和设备为生产手段的大资本,分解为中小企业,纺织、机械、电器等行业最为典型,这正是所谓的“旧资本的分裂”。
3.中小企业的复兴是当代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与资本集中方式变革的结果。马克思认为,研究经济学必须与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结合。马克思关于生产与资本集中的分析结论,正是以其对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机器与大工业关系的研究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机器与大规模生产即大工业存在着互动关系,“只有在可以大批生产即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机器才能(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得到应用。”而机器的应用,又是生产规模扩大、生产与资本集中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工业革命的起点”。马克思唯物的、联系生产力分析生产关系的方法,为我们分析研究当代生产与资本的集中方式以及中小企业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手段。事实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导致生产与资本集中的具体方式发生变化。第一次科技革命所引起的生产与资本集中的方式,是将动力机构、传动机构、工作机构集中到一个工厂的范围之内,这实际就是马克思所处时代生产与资本集中的特征。第二次科技革命,由于电力的广泛应用和远距离输电技术的成功,动力机构与制造机构分离开来,生产与资本的集中分别围绕生产的各个部门和工序展开,如煤矿的大型化、电厂的大型化、钢铁等基础工业企业以及机械制造企业的大型化,这与马克思所描述的生产与资本集中方式基本相同。而当代高新技术的应用,促使生产与资本集中的方式发生了更大程度的变革。
变革之一,生产与资本的集中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个工厂规模的扩大,生产与资本集中可以在全球范围分散的工厂中,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技术资源、自然资源、人力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分散地进行。这是因为,当代高新技术促成了柔性生产系统的广泛应用。变革之二,生产集中与资本集中发生了适度的分离。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占总数最大比重的中小企业其实不是生产独立产品的企业,而是大企业、核心企业的协作企业。在日本,大量的中小企业是大企业垂直分工体系的组成部分,66%的韩国中小企业是大企业的零部件承包企业。但不管是以雇员数量、资产总额还是销售总额来划分,不管是以定量标准还是定性标准来划分,生产与资本集中在这类企业总是发生了。变革之三,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经济发展的信息化、网络化,企业组织方式将可能出现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全新模式,企业可以在网络上寻找资源或结盟,企业边界的伸缩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集中形成和集中裂解动态交替的频度将会越来越高。
总之,技术演进使生产与资本的集中方式改变了,而这种改变恰恰是近20年来中小企业在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日益活跃、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当比重的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正是新技术条件下生产与资本集中的结果和表现形式。
三、理论分析的现实意义:准确把握“抓大”、“放小”与“扶小”的关系
自中央制定并实施“抓大放小”的战略以来,以我国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和90年代以来全球企业并购浪潮为依据和背景,规模扩张成为众多企业和一些地方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在积极宣传“小的是美好的”,从多个角度论证中小企业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进一步增强了这些学者的信心。究竟是“大”好还是“小”好,如何准确把握、正确处理“抓大”、“放小”、“扶小”的关系,上述理论分析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避免走盲目强调“大”或过分美化“小”的两个极端。前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理论界、实践界和经济决策部门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崇大”的观念与做法,在企业兼并、重组的过程中,甚至出现以进入“世界五百强”为目标,不顾客观条件、强制拼凑大型企业集团的做法。“崇大”风潮源起于多方面的原因,理论上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即深受西方产业组织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的影响,对规模经济学说深信不疑,认为在市场不完全性日益增强的条件下,企业边界自当不断扩大。但正如著名的产业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所指出的,“一个世纪以来,规模经济理论的发展可谓步履蹒跚。其中虽不乏有许多出色的推进,但实际研究的成果很少,且都缺乏科学性。”(注:斯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新制度经济学如今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产业组织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其它一些相关的西方经济理论,当然包含一些科学的成分,有助于我们在技术层面、制度层面、组织层面上对企业“大”与“小”的理解和应用,但马克思的生产与资本集中理论更有助于我们对本质性问题和长期趋势的把握。生产与资本集中是一个动态的进程,企业规模并非越大越好,企业规模的大小更替与技术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企业规模应该做大还是做小,应根据其所处产业,以及产业技术所处生命周期的阶段而定。”人为地强调做大只会导致企业规模的畸形发展,如韩国的“大企业泡沫”。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关于“小”的问题,主要还处在理论探索层面和政策酝酿阶段,学术界引用、借鉴了大量的西方中小企业理论,其中不乏科学的观点和真知灼见,但也必须注意,并非所有的行业,“小的”都是“美好的”。
2.生产与资本集中的长期趋势并未改变,“抓大”是构建、加强国民经济支柱和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战略决策。马克思的生产与资本集中理论虽然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但它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据生产与资本集中演进的规律,应该进行生产集中、资本集中的产业,理所当然地应该做大企业规模。那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对支撑、带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的,前、后向联系广泛的支柱产业,应成为“抓大”产业定位。将“抓大”定位于支柱产业,也符合技术演进与企业规模嬗变的规律,支柱产业的技术通常处于成长—成熟期,应该实行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抓大”不仅是适应生产与资本集中的长期趋势而作出的战略决策,而且还关系到下世纪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规模实力仍将是21世纪国际市场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掀起了巨大的企业并购浪潮,这是生产与资本集中长期趋势并未改变的典型例证,其目的之一就是力图以规模优势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面对全面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因此,着力培养、扶持一定数目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大企业集团,有着深远的意义。
3.“大”与“小”相辅相成、动态交替,“放小”应与“抓大”并重,“扶小”则是“放小”题中应有之意。对生产与资本集中动态进程的分析和对新技术条件下生产与资本集中方式变革的分析,都表明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动态交替的关系。因此,“抓大放小”决不意味着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被轻视,决不是对中小企业弃置不管,这一点如今已成共识。需要强调的是,“抓大”与“放小”是同等重要的历史重任,“扶小”则是“放小”题中应有之意。这是因为,其一,当前世界经济、中国经济都处在技术升级、结构转型时期,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这一时期应有大量“新资本嫩芽”萌发生成。在我国,放开搞活中小企业,尤其是建立健全鼓励、扶持高科技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促进其在今后一个时期成长、壮大或聚合为代表新兴产业的大型企业,是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其二,当前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先进的技术从何而来,富余的人员往何处去,是中小企业不可逾越的障碍。战后美国60%以上的创新技术、德国2/3的专利技术,都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中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具创新优势,这已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所证实。中小企业还是增加就业的重要渠道,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美国为2/3,德国占85%,日本非一次产业占81.4%。可见,能否促成活跃、繁荣的中小企业发展局面,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条件之一。其三,正如马克思分析的,实践已经证明了的,中小企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运用宏观调节手段予以扶持。因此,“‘放小’莫忘‘扶小’,中央和各级政府应该在融资、信息、技术进步、对外合作、市场开发、人员培训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为小企业提供服务。这应该是放开搞活小企业工作的重点。”
收稿日期:2000—08—10
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中小企业融资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集中趋势论文; 经济学论文; 企业规模论文; 融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