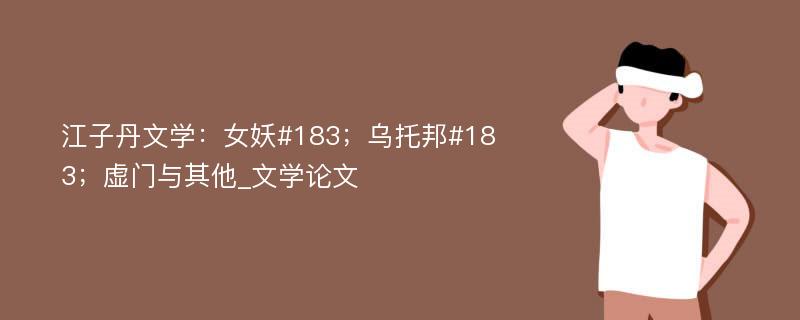
文学中的蒋子丹——女妖#183;乌托邦#183;虚掩的门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女妖论文,及其他论文,文学中论文,蒋子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蒋子丹是一个“女妖”,可能就会象说北冰洋里长着一棵椰子树那样让人感到惊诧乃至愤慨。许多人写印象记中,都说过蒋子丹是一个“居家女人”,一个坐在沙发里织毛衣的“很女人”的女人,一个会裁衣服会绣花会调咖啡会泡茶还会缝制布娃娃的“居家女人”。
然而,读蒋子丹的小说,我却隐约觉得蒋子丹近乎一个“女妖”,或者说她心里藏着一个“女妖”。自19世纪末期以来,无论西方东方,哪一位在文学上崭露头角的女人不同时显露出几分“妖气”呢?无论是伍尔芙、波伏娃、玛格里特·杜拉,还是张洁、残雪,以及近来为蒋子丹津津乐道的林白。况且,早在十年前,当蒋子丹在文坛上尚属一株嫩芽时,就曾经一不留神说出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话。
当然,日常生活中的蒋子丹决看不出半点妖气。她看上去既不古怪更不疯癫,既无模仿深沉的颓废,又无故作豪迈的堕落,一切都正正常常,照从事变态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北京教授吕俊华的理论,蒋子丹简直就与文学创作无缘。然而,这样一个“居家女人”,一旦在她那两眼中间突然洞开了第三只眼睛,第三只眼睛中又穿射出道道黑色的、蓝色的闪电,才真叫人刮目相看。
美国文论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将M·H·艾布位姆斯名著《镜与灯》中的“灯”换作了“妖”,换作一位高擎着文学之灯的“女妖”,撰文《镜与妖》来反思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运动。在他看来“妖氛”首先表露在女性小说家作品中的“雌雄同体”现象中。
那些夸奖蒋子丹是“居家女人”的人们,同时也看出她又是一位“逍遥旅人”,一位坐地日行八万里,不安于家室更不安于女性角色的女人。女散文家斯妤说她是一个“与男人较劲”的女人,女批评家王绯则欣赏于这个女作家摒弃了作品中的“性角色”。在《没颜色》、《绝响》中她似乎是女人,在《圈》与《左手》中她又俨然象是男人。单从小说的文体上看,已难辨作者是雌是雄,这此,可能还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表层上的。更重要的是内心。在创作心理的层面上,蒋子丹不乏这样两种倾向:一是坚决排斥传统女性角色,二是奋力抗拒男人一统天下,两种倾向又不过是一口利剑的两道锋刃。
什么是传统女性?理论上的概念是:成为男权社会私有财产并处于从属地位的妇女。中国人富于诱惑力的幽默则称之为“小鸟依人”。在蒋子丹的作品中,“颜色系列”中的美术学院的女学生不是传统女性;《绝响》中的现代女诗人,现代女记者也不是传统女性;《桑烟为谁升起》中的萧芒则由一个正统的淑女型女性终于演进为一个全方位开放型的现代女性,丈夫死后,她就象一个断了奶的孩子,终于在情感的苦痛中获得了人格的成熟,在失去家庭的依靠后获得了独立自主。《从此以后》中那位规矩传统得心应手的家庭主妇竟被蒋子丹狠心从楼上扔下并置换了大脑,“从此以后”变成了一个年轻任性不太听话的另一种女性。《贞操游戏》中的K女士倒算得上正统加传统,结局是终生困顿,死了以后还要蒙受男人世界的侵略与蹂躏(精神与道义上的)。女人的解放,包括从性专制下的解放,从家庭泥淖中的挣脱在蒋子丹的笔下成了女人躯体内与心灵中潜在的“革命动力”。即使那位很少女人气息、工作事业第一的女厂长,在内心深处也包藏着如此强烈的浪漫情怀,如此热烈地渴望来一次“最后的艳遇”。蒋子丹力图寻找一个无性的立足点,烛照出男女关系历史中的诸多偏执与不义。正如吉尔伯特所说的:“女妖象一个黑影,潜伏在镜子的另一面,表现出反对法律和规定的天启的革命欲望”,女人的行为,“使灵魂成为自己的叛徒”,“成为它自己的引渡人,成为一种活动”,于是,“镜子变成了灯”。①
蒋子丹与那些革命的、乐观的、雄心勃勃的、杀伐果断的西方女权主义者毕竟不同,与那些以“女权”做工具做武器去攻打议会席位的女权主义政治家更为不同,她的这口文学利剑仍旧斩不断她身体中心灵中东方女性的基因,她手执文学这盏灯照来照去照见的仍然只是一团幽晦不明的混沌。女人们即使有了一次刻苦铭心的“艳遇”又如何呢?“繁华过后成一梦”,那个为了爱情奉献出全部身心的清纯少女,也只有在孤寂中“等待黄昏”的到来。当蒋子丹目光如电地审视着现代女性的过去与未来时,她看得越是透彻,也就越是悲观。她在小说中写道:
我们就象这些鱼,成熟产卵然后衰老然后死去。苏密设计了我们作为女人的蓝图之后死去了,甚至来不及等待衰老的降临。也许是她的勇敢,她并不惧怕死亡,也许这是她的怯懦,她惧怕经历衰老的过程。相形之下,我也许比她怯懦,因为我惧怕死亡,也许比她勇敢,因为我迎接了衰老。她省略了衰老直奔死亡的归宿,我忍受着衰老但终归退不出死亡的召唤。
②总归是进退维谷,总归是死路一条。
黛眉死了,苏密死了,K女士死了,蒋子丹说:“我的思绪一不留神就会走入秋天里的死亡图画,在里面如鱼得水地遨游,以致于每一篇小说的构思,主人公都跟死亡相关。”③
作为身陷困顿的女人,淑女萧芒和那个暗恋(也是自恋)着“红蜻蜓”的少女,甚至怀疑起“人类生生相息的延续”到底有什么意义,是否应该为人类的存在点燃起袅袅“桑烟”?
在东方,即使是一位手执文学之灯的“女妖”,面对女人的命运最终也只能陷入一片无奈的茫然。
弗吉尼亚·伍尔芙曾经说过,女权主义学者的理论在根本上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再早一些,还曾有人宣告:一个女性的“乌托邦”将建立在“文学领域”之上。我想这可能更适合那些已经有了几百年罗漫谛克史的西方女性,超载道德负荷的蒋子丹并不这样。在蒋子丹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境况是乌托邦尚未成形就被瓦解,一个“圆脑袋黑头发的男孩子”,一个侯补大男人,将女人精神隐秘处的那只凄艳的“红蜻蜓”“捏成了碎片”。
我对蒋子丹个人的生活世界所知甚少,只是从她的散文集里获悉,她出身于文学的名门望族,父亲是给鲁迅先生扶过灵柩的蒋牧良,父辈人中还有名垂现代文学史册的张天翼、吴组缃、艾燕、沙汀。幼年的她也曾编织过“浮想联翩的童话”,也曾憧憬过“妩媚婀娜的影”与“闪烁跳跃的光”,究竟是什么缘故使她的文字变得如许苦涩滞重?
容易推想到的,有“反右斗争”“文化革命”,家人的悲欢离合,世态的寒暑炎凉。
也许还有她自己人生道路上的起伏跌宕。八年前她曾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潇湘的文士扬帆南征,龙年下海,也曾仰天长啸,也曾壮怀激烈,期待凭自己的年轻与真诚,凭群体的团结与默契,在那遥远而又炎热的海岛上构筑一块理想的王国、一座精神的家园。他们真的把一本色彩斑烂的期刊象升起一面大旗那样悬挂在中国蔚蓝色的天幕上。没有多久,突如其来的风暴吹落了他们的那面旗帜,诺亚方舟上的伙伴们在滚滚而来的经济浪潮中显出不可收拾的离心离德,理想与诗情再次在南海坚硬的礁石上撞得粉碎。用她自己的话说:“世纪末的微型乌托邦终于解体”,生气勃勃的“乌托邦工程”变成了夹在书页中的“乌托邦故事”。
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比如,爱情的蹉跎与消磨。
她只是在小说中处处显示出:她希望过,终于绝望。昨天已经古老。死亡成了一连串探索过后剩下的憧憬,“最庄严的事情,是死之后的清晨打扫干净心房”,让生命回归生命之前的清洁与宁静。刚刚年过四十的蒋子丹就开始遐想死亡、体验死亡、崇拜死亡、恭侯死亡。莫非蒋子丹的文学生涯已经到了地老天荒的地步,难道“死亡”居然成了蒋子丹文学写作的乌托邦?
这可能是蒋子丹目前文学创作达到的极至,也是她文学道路面对的一道悬崖。
为蒋子丹所推崇的加缪其实是抗拒死亡的。他说,荒诞的人拒绝自杀。在文坛上,蒋子丹的小说曾经以“荒诞”引人注目。然而,只具“荒诞形式”与“荒诞色彩”的荒诞,还只能是一种“仿荒诞”,她自己在《荒诞两种》里也曾这样讲过。真正的荒诞是“活着并直面荒诞的人生”。死亡,在清除种种肮脏,在补足种种残缺,在结束种种烦恼同时也就取缔了荒诞。“活着,就是使荒诞活着。”加缪给“活着”赋予的内涵是面对绝望的“挑战”与“激情”,是精神的高傲与优越,是不计成败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在我看来,那就是永远迈向虚悬在地平线上的精神乌托邦。
蒋子丹面对荒诞时选择了死亡,这或许正体现了她那东方女性的软弱。
我说蒋子丹,你不要那样急匆匆地在《无标题自白》中宣告你的放弃与妥协,你不能以“我不具备加缪的境界”为借口,因为你毕竟已踏上文学悬崖的峭壁,已经来到人生地狱幽晦的入口,你如果由此退去,那你就还不如你笔下的那位“关老先生”,他心无旁鹜、一意孤行,倾其心血调教训练出那么强大的一只“左手”,却正是这只“左手”断送了他的老命。尽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关老先生依然含着情不自禁的自我欣赏的微笑驾鹤西去。
你的《左手》,堪称一个精彩的荒诞。
荒诞,也可以是诗。或许,乌托邦精神就是由荒诞谱写的诗。
蒋子丹的小说创作却那样的小心翼翼地回避着诗意和诗化。她凭借着现代小说手法中的反讽与倜侃、幽默与荒诞,把人们关于女人与爱情的传统建构一一消解。在她的笔下,关于女子与爱情的诗歌已衍化为关于女人与爱情的文件甚或相声。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反叛。诗化也许是女性的,不过,正如男人女人在性上的差别是天经地仪一样,文学的“无性”或“中性”状态也只是一个操作中的假设或理论上的假设。在破裂与颠覆都已经实施之后,更要紧的是在碎片之上的整合与重建。乌托邦的前驱诗人菲茨杰拉德在《奥马尔·戈亚姆》中吟颂道:
啊,爱神!
你能否和我同命运女神一道运筹,
去掌握这可悲事物的全部结构,
我们能不能把它粉碎
——然后
将它改造得更接近于所求?④
重建应是男人和女人的共同事业。应当看到当今世界上男人们也在改变。我始终认为,男人变得稍好一点,是世界变好的关键。这倒不是男人更重要,而是因为男人在历史上做恶太多。至于男人如何变?顺应着女权主义者的思路,一些男人已经开始扎起翘楚的小辫子,穿上娇艳的花裙衫,戴上玲珑的金耳环,学着女孩子那样撒娇、撒欢。男人的雌化,正如女人的雄化一样,怕都不是人间正道。“雌雄同体”的诗学只不过表达了女权主义者的一种情绪,诗意再度在小说中升起,有赖于男人和女人携手共建。
重建文学诗意的女人决不会是那些或新或旧的“小鸟”“蝴蝶”“红粉”“红袖”“宁馨儿”“宝贝蛋”,也不再是硝烟战火中的巫女、魔女、妖女、怪女。在蒋子丹近期的一些作品中,读者则不难感悟到葱茏的诗意,感悟到一个女人的心灵在书页中的敞开。这里的女人或许已是一位新人,一位在人类精神世界的攀登中更上一层楼的女人,一位“大写的女人”。
“文如其人”,“文学是经验的再现”,这些过去的文学创作理论,在现代文学运动中一再受到挑战。巴尔特在他的符号学批评中干净利落地蒸馏去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和作家的生活经验,写作成了“语言自身的运动”,作品成了“结构的自足体系”,无论是作家这个人或是作家独具的资质禀赋都不再作为文学阐释的出发点,将被完全彻底地排除在批评家的视野之外。在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指导思想建立起符号学、叙事学、阐释学的批评理论之后,托多洛夫、热奈特、拉康、德里达似乎真的击败了丹纳、勃兰克斯、别林斯基,并且培养出包括中国当代被称作“先锋派”的一批又一批的诗人、小说家。蒋子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她的朋友徐晓鹤、何立伟、残雪之辈的怂容下,用她的笔捅开了小说创作的现代之门。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无意间“踉跄着”“身不由己地”踏进了现代小说创作这扇“虚掩着的门”。
从“昨天已经古老”之后,蒋子丹开始被列入新潮小说家的行列。
她聪明大胆,感悟力强,有着近乎天生的言语操作技巧。她干得很不错:《黑颜色》一炮打响,被批评界鉴定为“荒谬的存在”;《今夕何年》,自我分裂、双重人格、超越意识流内心独白的潜意识自我对话;《绝响》,对同一事件的多重解释,隐藏了作者的意图却构造出文本的意义,“拍——拍”一声绝响,歪打正着地应验了托多洛夫对詹姆斯小说挖空心思的解析判断:“艺术是一种空缺”,“空缺形式序列的含义是秘密、鬼和死亡”。⑤《最后一次艳遇》简直类似一篇“等待戈多”,只是最终到场的“戈多”远非女主人在焦虑中期待的“戈多”,从反面证明了精神的“空白”一旦为物质的“实在”填充,审美的张力随之而萎顿。《等待黄昏》,则是典型的“复调程式小说”,两个女人的悲悲切切寻寻觅觅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犹如梵亚铃与巴松管缠绵悱恻的二重奏,奏出一支女人命运的“悲怆曲”,而那上下翻飞的“红蜻蜒”则是大贝司流出叹息般的和弦。《左手》,则是一个黑色的隐喻,在貌似荒诞不经的“所指”下面,隐匿着一个残酷的与上帝与圣经较劲儿的宿命。
跨过那扇虚掩的门,蒋子丹面对的是一片新鲜而又奇异的密林。她在兴高采烈地走上一段路程之后,才又发现自己在本性里与“现代小说”仍然夹隔了许多生分。她不能象某些“嬉皮”“雅皮”那样肆无忌惮忘乎所以地玩技巧玩文字玩历史玩良心,她太认真以至感到拘紧,反而埋怨起小说写作象一双“夹脚的高跟鞋”,下意识里逃避起写小说来。在她害怕了写小说的时候,她便从现代小说的大林莽中撤退回来,回到散文写作的海边沙滩上。
小说与散文,在蒋子丹的文学创作中竟成了两个世界。散文是经验的现世,小说是超验的彼岸;散文是言语的溪流,小说是语言的工场。散文是情感的倾吐,小说是理性的编织;散文是诗意的境界,小说是文本的建构;散文是澄澈的月夜,小说是昏暗的迷宫;散文是泥土里长出的绿树,小说是钢骨水泥盖起的大楼;散文是那个扎着红绸带跳橡皮筋的小女孩,小说是那个亦真亦幻的X·H·Q·K!尽管如此,蒋子丹还偏要打虎上山,把“写小说”框定为自己文学生涯的“正业”。那么,她下一步的小说将如何写下去?
可以让人宽心的是。虚掩的门不会再度关闭。郑板桥画竹有体会:四十年来画竹枝,画到生时是熟时。蒋子丹的困惑也许是一种高境界呢!
我总也不相信,那些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的理论大师们能将文学言语中的生命主体消解个一干二净。君不见在他们用来消解主体的一部部文本中又凸现出那么生动活泼的叫作“巴尔特”“拉康”“德里达”的生命主体。与其和这些理论体系的制造者、展销者纠缠不清,我宁可向那些个体的文学言语创造者表示亲近。可以比一比,托多洛夫的《〈十日谈〉的语法》较之薄伽丘的《十日谈》显得多么贫瘠苍白。即使是现代小说的写作,并非一定羞于谈论作家的精神人格、作家的人生经验吧。
不是已经有人在提醒蒋子丹吗:“迄今为止你的作品还基本上没有启动你个人经验的贮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也许是你把自己封闭得太深了,要么就是你过于相信当代文坛上那些“形式”“技巧”的神话。其实,你至今写下的那些异彩纷呈的小说,难道仅仅只是因为它们的形式与技巧?不同样因为生命在写作过程中那些涌动着激荡着的“感觉兴奋”?你最近在给自己的一本散文集写的自序中说:“散文之于我,不光是一种文学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想,小说也应当这样。
小说当然不同于散文。但小说正在走向散文。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创作实践可以看作一个成功的范例,他大胆地解散了传统小说行之有效的模式,尽情挥洒恣意汪洋地把随感、杂谈、讽谕、格言,把哲思、抒情、推理、回忆统统容纳进小说中,“小说变成了更富综合性的大型散文体”,一种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文体。⑥“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读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那如湍流四下迸射的言语使我强烈感到:生命再次冲破文本。
对照昆德拉的范例,我突然怀疑起来,那扇关于现代小说创作的“虚掩着的门”是有还是没有?对于精神的自由创造世界来说,对于文学天地中一个活跃精灵来说,会只有一条通道,只有一扇门吗?
1995年3月于海南岛
注释:
①〔美〕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第196、2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版。
②蒋子丹:《等待黄昏》,见青羊主编《情殇》续集B卷,九洲图书出版社。
③蒋子丹:《乡愁》(散文集),第127页,海南出版社,1994版。
④〔美〕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第1页商务印书馆,1990版。
⑤A·杰弗逊等著:《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流派》,第1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版。
⑥参见黄卓越、叶廷芳主编:《二十世纪艺术精神》,第46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