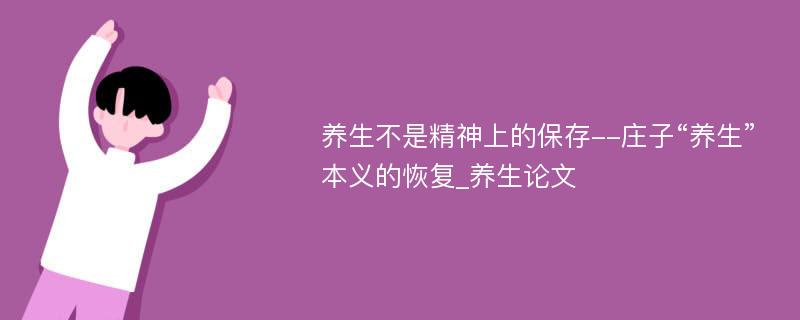
养生并非养神——庄子“养生”本义复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义论文,庄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策纵先生写过《〈庄子·养生主〉篇本义复原》的论文,对《养生主》别有会心。他认为,庄子《养生主》的写作受到所处时代之医学常识的影响,而彼时的医学知识可从《黄帝内经》的基本篇章《素问》和《灵枢》中见到。“庄子似乎企图把医理的‘养生之道’延扩为哲理方面更普遍的‘道’”①,这是很有见地的。但在这篇影响广泛的文章里,周策纵将“养生主”读为“养-生主”,即“养”“生之主”,并指出:“庖丁之言又透露,所养的生之主是‘神(精神)’,即所谓‘臣以神遇’和‘神欲行’……可证庖丁说的‘神’必是指生之主。”②这无异于主张“养生就是养神”。“养生即养神”不只是周策纵一人的看法,而是一个颇为普遍的看法,在哲学界与中医学界均有所见。但笔者认为,这未必是庄子“养生”的“本义”。故作此《养生并非养神——庄子“养生”本义复原》一文,以就正于学界方家。 一、身心二元论 首先要指出,尽管不少学者认为《养生主》的篇名有“养-生主”和“养生-主”两种读法,但我们仅取后一种读法。“养生主”意为养生的宗旨,养生的要义,养生的基本原则。这种读法,证据更为充分。陆德明说:“养生以此为主也。”(《经典释文》)苏辙说:“盖予闻之,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墨竹赋》)其实在《养生主》中,庄子自己就是“养生”二字连读的:“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此外,《达生》篇也说过:“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养生是道家哲学的一个基本方向,也是庄子《养生主》所要谈论的主题。那么,养生是不是养神呢? 在《庄子》一书中,确实出现了“养神”的说法,如“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恬惔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刻意》)。而且在《养生主》中,出现了三个“神”字。最后的“薪火之喻”也往往被视为是对精神不朽的隐喻,如周策纵说:“说是精神不死,也未为不可。”③凡此种种,都使得许多学者认为,庄子的养生就是养神。如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的《养生主》题解:“《养生主》篇,主旨在说护养生之主——精神,提示养神的方法莫过于顺任自然。外篇《达生》篇,通篇发挥养神之理。”④纵然不把养生完全等同于养神,现代学者也大都主张,“养生主要是养神而不是养形”。如封思毅说,《养生主》“末后借薪尽火传,道出形灭而神存之理,意在强调养生当以精神为重,而以形体为轻”⑤。 “养生即养神”说既可在低处立论,亦可在高处立论。我们常说,“打个盹儿,养足精神”,“闭目养神”,小憩片刻,好比给一个运行良好的机器加点油,让它运行得更为顺畅。这当然也算养生,因为闭目养神是休息,而休息乃是养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种“养生”太过常识化也太轻松了。庄子作为哲学家,恰好是要“技进乎道”,把养生提到“道”的层次上来谈论和践履的。庄子要全生、穷年,而在庄子所生活的年代和环境里,全生、穷年恰似哈姆雷特的“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乃“性命攸关”之大事,如“火烧眉毛”般逼迫而至,不是只要优哉游哉地养养神就打发了事的。 因此,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养生即养神”是在高处立论。在高处立论,“养神”就不只是“闭目养神”之类的休息,而是保养真正的生命。较之身体,神,也就是精神,才是真正的生命。既然精神才是真正的生命,那么真正的养生当然是“养神”,而不是“养形”了。保养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即使肉身死亡,精神也能不朽。从而,庄子的“养生”,也就是求得不朽的精神生命。于是我们可以把苏格拉底的话赠与庄子,苏格拉底说:“我们认为真正的哲学家,惟独真正的哲学家,经常是最急切地要解脱灵魂。他们探索的课题,就是把灵魂和肉体分开,让灵魂脱离肉体。”⑥——这句话出自《斐多》,而《斐多》在西方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试图论证“灵魂不朽”。精神的特质,即是不朽性;但当精神还逗留于身体之内时,它有主宰性。按照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人的理路,精神的别名乃是理性。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中,就把理性视为“我们身上的这个天然的主宰者,这个能思想高尚的、神性的事物的部分”⑦。因此,精神就是主宰身体、能够役使身体的东西。我想举手,手便举了起来。“我欲仁,斯仁至矣。”总之,“养生即养神”的说法,认为“神”即精神,而精神区别于身体,是身体的主宰,还可以脱离于身体,是不朽的灵魂。这一说法,建立在身心二元论的思维前提之上。 所谓身心二元论,简言之,就是把人视为肉体和精神的组合,肉体是物质性的,精神是非物质性的,两者截然不同,因而是“二元论”。古代文献中常有“灵魂出窍”的记载,可视为身心二元论的一个经验性例证。一般说来,灵魂出窍观念的产生主要受到梦的影响。梦是一种心理现象或意识现象,做梦时,身体是不动的,而意识活动却极其自由,这种自由往往给人以意识可以脱离身体而独立存在的错觉。这大概是身心二元论在心理上的根源。不过身心二元论从一种心理经验上升到自觉的思想,历时甚久。思想上的身心二元论,在古希腊初露端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已有了身心二元论的思想倾向,他们都把理性看做人的真正自我。但身心二元论作为一种哲学观点,正式产生于笛卡尔。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将“我思”理解为一种完全内在的、与外部世界截然不同的存在,造成了心与身的彻底分裂,导致了把人理解为机器般的身体加上幽灵般的精神的观念。笛卡尔的这种观念,支配了西方哲学数百年。随着19世纪末的“西学东渐”,身心二元论也进入中国。今天的中国学者几乎是本能地将身心二元论的“现时观念”投射到庄子的文本之中。 因此,若要质疑“养生即养神”的命题,我们必须扣紧其思维前提或哲学预设,即身心二元论,推翻用身心二元论来解读庄子养生论的做法。毫无疑问,庄子不可能持有笛卡尔之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身心二元论。如前所述,梦可能是身心二元论的心理源头之一,但庄子是主张“至人无梦”的,他说过“古之真人,其寝无梦”(《大宗师》);纵然在梦中,他也是“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齐物论》),强调物我相通,天人合一。庄子甚至也没有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家的身心二元论,因为他从未将理性独立出来,视之为人的真正自我。但这只是内在于大的文化精神和思想脉络中得出的判断,我们还需进一步结合庄子的文本进行分析和论证。这就要先弄明白,庄子在《养生主》中说的“神”到底是什么?它是灵魂吗?它是主宰身体者吗?它能脱离身体吗?它具有不朽性吗? 二、主宰者与不朽者 在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庖丁两次提到“神”的句子是:“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如前所述,周策纵认为“神”即精神,亦即“生之主”。宋人陈景元把养生之“主”读为“真君”,今人曹础基《庄子浅注》也附议。“真君”即是主宰身体的精神。那么,庖丁所说的“神”是真君吗?是主宰身体的精神吗? 解答这个问题,最好循序渐进。我们要先问,身体之内是否有一个主宰者存在?庄子亦有此问,比如下面的文字: 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齐物论》)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认为“真君”指人身的主宰,即心灵或精神。林语堂《老子的智慧》把“真君”译为“灵魂”。冯友兰和方东美似乎也都持此说。总之,“真君”就是身体的主宰者,即心灵、灵魂或精神。不过,仔细察看原文,不难发现,其实庄子既不明确主张身体内有“真君”,也不否认身体内有“真君”。这种态度比较符合庄子作为一个怀疑论者的身份。 事实上,关于“真君”存在与否,庄子的态度是现象学的态度。现象学的态度有点类似于怀疑主义,它的一个重要术语“悬搁”就来自古代怀疑主义。现象学只关注直接显现于意识的东西,即直接被给予的东西,但凡意识之外的东西即超越的东西,现象学是“存而不论”、“搁置判断”的。上帝是悬搁的对象,灵魂也是悬搁的对象。但现象学并非否认上帝和灵魂的存在,只是暂时不置可否而已。庄子对于身体内是否有个“真君”,也是不置可否的。他指出,“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要说有真宰吧,可是并无迹象可寻。大自然的真宰如此,身体里的真君亦然。于是庄子射出一支疑问之箭:“其有真君存焉?”固然,身体内部是否有个真君,是不能确定的,但庄子不否认它在发生作用,这就像大自然的真宰,虽然不见其形,而造化运行,丝毫不爽。真君也无形,但它显示种种作用。庄子说,“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损益乎其真”,无论求得真君的真实情况如何,对它本身的存在都不会有影响。不过真君的“存在”并非“实存”,而是现象学意义的存在,即“显现”。 可见,在“真君”问题上,一如现象学家,庄子区分了存在与现象,或者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来说,庄子区分了本体与作用。深受庄子影响的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也说: 所谓精神,不是本体,而是从本体发生的作用,是活动。本体是五尺身躯。这五尺身躯的活动,就是精神这种神妙的作用。例如,象炭和焰,薪和火的关系一样。漆园吏庄周已经看穿了这个道理。就那十三种或十五种元素暂时结合的身躯的作用即构成精神来说,就身躯还原即分解也即身体死亡来说,这身体所起的作用即精神,按理也就不得不同时消灭。恰象如果炭成灰,薪烧尽,那末,焰和灰就同时熄灭一样。所谓身躯已经分解,而精神还存在,这是极端违背道理的话…… 所以身躯是本体,精神是身躯的活动,即作用。身躯要是死亡,灵魂就要同时消灭。⑧ 这些话体现了中江兆民对庄子的准确把握。因为在上面所引《齐物论》那段话后面,庄子接着就说:“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可见庄子也赞成“身躯要是死亡,灵魂就要同时消灭”。而中江兆民所言薪和火的关系,本于《养生主》的最后一句话:“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指”就是“脂”,即可燃的脂膏。这话意思是,脂膏为薪火燃烧殆尽,但火却传续下去,没有穷尽。庄子这句话,往往被视为对精神不朽的比喻,如朱桂曜说:“此言脂膏有穷,而或之传延无尽,以喻人之形体有死,而精神不灭,正不必以死为悲。”此说一出,应者云从。可是,此说至少有两个疑点。首先,在很多地方,庄子都不认为精神或心灵会永恒存在,为何这里突然主张“精神不灭”了呢?这不免有违思想的一贯性。其次,如果薪是身体而火是精神,那么若要薪尽火传、精神不灭,岂非就像一支蜡烛点燃另一支蜡烛那样,还需要一个身体?如此,我们就要认定庄子持有转世轮回的思想了。这是匪夷所思的。转世轮回思想与佛教一道传入中国,已是庄子去世数百年之后的事了。庄子确实主张“不必以死为悲”,但他提供的理由既不是什么精神不灭,也不是什么转世轮回,而是认为死乃自然之事。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引用了陈启天的说法,其说颇为与众不同。陈启天说,庄子这句话“犹谓以脂膏为薪火而烧尽,乃一转化,非消灭也。比喻人由生而死,亦不过一种转化,不必悲也。如此解释,始与上文‘安时处顺’之说相应”。我们认为,这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按照陈启天的解释,庄子这句话是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它确实是谈养生的,却并不是谈养神的。 三、身体作用与身体经验 现在我们要问,庖丁所说的“神”是精神吗,是身体的主宰者吗?显然不是。“神”只是身体的作用,不是身体的主宰;它非但不能控制身体、命令身体,而且只能依附于身体、追随着身体。庖丁解牛,动作纯熟无比,技术达到了至高的境界,“官知止而神欲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这并不是说,身体作用停止之后,精神开始游走。实际上,“神”就是身体的作用,而不是身体作用之外独立存在的“精神”。自然,“目视”也是身体的作用。所谓“官知止”,主要是“不以目视”。加之前有“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后有“视为止,行为迟”,可见庖丁强调的是,他不必目视,也能解牛。通俗地说,庖丁闭着眼睛也能宰牛。这似乎不可思议,是天方夜谭。然而未必。目视只是身体的诸多作用之一,关闭了视觉,不等于关闭了一切感觉。庖丁即便是一时不以目视了,还有其他的身体感觉在发挥着作用,况且他杀牛达十九年之久,对牛的生理结构早已了如指掌,就此而言,闭着眼睛杀牛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就像我们在突然停电而漆黑一团的家里,仍然可以顺利地找到某些东西。靠什么?靠的就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 因此,“神”并不是在身体之外对身体发号施令的精神,“神”就是一种身体作用和身体经验。或者也可以说,“神”是身体自身的运作机制,是一种身体意向性,等等。如果说,“精神”的特质是不朽性和主宰性,那么“神”的特质就是自发性和随机性。自发性首先意味着不受意识支配、不为心思左右。事实上,往往在思想意识之前,身体就已经自行运作了。这种身体经验,其实不只是庖丁有,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只是在《庄子》之前,哲学文献中并没有人专门描述和谈论过这种经验,因而可以说,庄子发现了它。庄子对于这种身体经验特别感兴趣,并认为它在技艺中最为常见;在这种经验中,“道”现身而出了,此之谓“技进乎道”。技本身并不是道,但是,当技艺的操作使“神”这种身体作用和身体经验开始呈现时,便进入了道的境界。道为何不可言说?历来学者说得玄而又玄,其实,“道不可言”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使道得以呈现的这种身体作用或身体经验是前思想、前意识的,因而是前语言的。因此,道只能在技艺中去感悟,在身体经验中去“体验”。《天道》篇“轮扁斫轮”的寓言也是这个观点。 斫轮是一种技艺,“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这是典型的身体经验。“得之于手而应于心”,说明这种经验是由身体发出,而后传递到心中的,然而就算传到心中,也只是若有所悟,“口不能言”。斫轮的身体经验是前意识、前语言的,事实上它也是不能理性化和语言化的,因此不能传授于人。精神的表现是思想、是语言,而身体的表现是经验、是感受,这正是无法把“神”等同于“精神”的主要原因。 顺便指出,轮扁斫轮的寓言,以斫轮经验不能传授喻圣人之言不能传授,“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强调圣人既死,则圣人之言也便随之失传,这说明了两点:其一,在庄子看来,道是由圣人之身来体现或显现的;“身教”重于“言传”,“身教”是“言传”的基础。其二,庄子不但未在物理意义上承认精神不朽(灵魂永生),也未必在“立言”的意义上主张精神不朽。 《达生》篇也提到了类似于庖丁的“神”,但更突出了“神”的前意识、前语言性: 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 醉者突然坠车,却能不死,甚至毫发无损,庄子说是由于醉者“神全”。如果“神”是精神,那么“神全”就是精神专注,但这明显说不通。一个酒醉的人,晕晕沉沉,恍恍惚惚,乘车也不知道,坠车也不知道,应当是精神涣散才是,怎么反而精神专注呢?但是,一个人醉了,哪怕醉得“人事不知”,只要并非已死,他的身体就仍是活生生的。由于“人事不知”,反倒使身体从意识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身体的觉知与感应变得更为纯粹、更为完全,此之谓“神全”。当醉者坠车时,身体自发地做出了某种反应和调整,使自己免于受伤。 《达生》篇中还有一个乘蜩丈人的故事,提到了“神”的概念:“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一般认为,承蜩丈人如此技艺惊人,是由于他异乎寻常的专心:“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也就是心无旁骛;“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也就是专心致志。这样解释当然也不错,但它基本上是把“神”等同于“心”。我们则认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是把全部心思都限制于蝉翼之上,从而把身体作用和身体经验解放出来。一任身体作用的自发性和机缘性,不以思想意识去干涉它,那么就能承蜩“犹掇之也”,并让孔子感佩其中“有道”。 如前所述,按照“养生即养神”说,“神”即精神,而精神不同于身体,具有主宰性,甚至可以独立于身体,具有不朽性。但庖丁解牛中的两个“神”字,一不是可以独立于身体的主宰者,二不是可以脱离于身体的不朽者,由此可知,“养生即养神”之说不适用于庖丁解牛。 四、泽雉寓言新解 在《养生主》中,第三个“神”字出现在关于泽雉的简短寓言中:“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这则寓言过于简短,仅得两句,且前一句好懂,后一句却颇为难解。或许在前后两句之间有脱字,但这猜测无从证实,我们只好接受现有的文字。旧说“王”通“旺”,即旺盛,“神”即精神,“不善”即不好,意即纵然精神旺盛,也是不好。何以不好?因为被关在笼中,不得自由。曹础基《庄子浅注》说,这则寓言“着重说明养生主要是使精神上得到自由”。但是,既然被关在笼中,何以不是精神委顿而是精神旺盛?既然精神旺盛,何以不好?因此宋朝禇伯秀主张:“神为形之误,神旺不得谓之不善也。”此说曾为王叔岷所驳斥,但在我们看来,禇伯秀还是有些道理的。在泽雉寓言之前,是仅有单足、即形不全的右师的故事。也许正如“薪尽火传”的比喻与“安时处顺”的故事应合在一起理解,右师的寓言与泽雉的寓言也应并为一个寓言。再将“神”字更改为“形”,相应地,将“神虽王”调整为“形虽全”,新的语境就形成了: 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是以知其天也,非人也。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形虽全,不善也。” 在这个语境下,庄子想要说的是:右师仅有单足,这并非因他不善养生,致使伤身受害,而是生来如此,天生使然,正如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也是天然的存在方式;如果将泽雉关在笼中,为人饲养,哪怕它形体完全,那也是不好的。如此解读,与庄子重天然的思想路向也是合辙的。不过这样一来,“神”字消失了,我们就更没理由说“养生即养神”了。 若是遵循既有原文,不妄自改“神”为“形”,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神”字在泽雉寓言中的用法,与庖丁解牛、轮扁斫轮、醉者坠车、佝偻丈人承蜩等寓言都有所不同,它既不是身体作用,也不是身体经验。既然如此,我们直接把它理解为“精神”,岂非简洁明快?然而事实是,若是把“神虽王”的“神”理解为精神,将庄子的意图定为“说明养生主要是使精神上得到自由”,将会使这段文字更加诘屈聱牙。姑且不追究“神旺何以不善”这个难题,就说精神自由吧。按照身心二元论的倾向,即便身体被关在笼中,精神亦可自由。斯多葛主义者爱比克泰德早已看到:“‘可是暴君将用锁链锁住——’什么?你的腿。‘砍断——’什么?你的脖子。那他既不能锁住也不能砍断的是什么?是你的自由意志。”所以,“人在哪儿违背了他的意志,哪儿就是他的监狱。正如苏格拉底并不在监狱中一样,因为他是自愿呆在那儿的”⑨。锁链之下仍能自由,甚至正是在身陷囹圄的衬托之下,更能见出精神的自由。苏格拉底身在狱中,却无人比他更自由。既然如此,为何非要从樊笼里出来?又何必“不蕲畜乎樊中”?这就是说,如果把“神”解释为“精神”,我们就无法顺利解读泽雉寓言。 关于《养生主》第三个“神”字,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的看法是,它要么应当改为“形”,要么不能理解为“精神”。因此,第三个“神”字也不能证明“养生即养神”。对《养生主》三个“神”字的分析使我们有理由断定,养生并非养神。 五、结论 虽然以上的分析足以表明在《养生主》中,“神”并非“精神”,因而“养生并非养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于一个事实:《庄子》一书中曾使用“精神”这个词,并曾出现“养神”的说法。例如,“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天道》)。“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其名为同帝。”(《刻意》)尤其是《刻意》篇,先是否定了“养形之人”,再明确提出“养神之道”,故而历来被视为“养生即养神”的重要依据。如曹础基《庄子浅注》在《刻意》篇“导读”中就说:“本篇是论述养神之道的。”⑩然而,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庄子》一书的内篇与外杂篇的关系问题。庄学研究者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自著,外篇与杂篇为庄子后学所作。研究解读庄子思想的基本原则是,以内七篇为主,外篇和杂篇为辅;判断庄子的思想,应以内七篇的文本为首要证据,如外杂篇的文字与之有所不同、有所冲突,则选择内七篇。《养生主》属于内篇,《天道》、《刻意》等属于外杂篇,我们不应因外杂篇有“精神”一词、有“养神”之说,就断言庄子主张“养生即养神”。 第二,《庄子》书中的“精神”不等于“神”。“精神”是个复合词,而且只出现在外杂篇。刘笑敢早已指出:“内篇虽然用了道、德、命、精、神等词,但没有使用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由词根和词根合成的词),而在外杂篇中,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都反复出现了。”(11)这是内篇为庄子所著,外杂篇为庄子后学所著的一个证据。在外杂篇中,“神”不仅与“精”相连,还与“明”相连,即“神明”。如此,我们就很难说庄子的“神”就是“精神”。当《刻意》篇提到“养神”时,未必就是指养护与身体相异的精神。 第三,庄子的“神”与“形”相对。但庄子思想中的“形-神”关系,不等于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身-心”关系。如前所述,按照西方哲学的身心二元论,必然会得出在身体之外精神独存或灵魂不灭的观点,而庄子不可能承认灵魂不灭。范缜《神灭论》云:“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较之西方的身心二元论,范缜的“形神相即”论显然更接近于庄子思想。然而,“养生即养神”说所预设的形神关系,却是与范缜《神灭论》正相反对的慧远《神不灭论》中所主张的“形尽神不灭”论。形尽神不灭论接近于西方的身心二元论(12)。慧远在论证神不灭论时使用了一个比喻:“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沙门不敬王者论》)这个比喻在字面上抄袭了庄子的《养生主》,但其内里却注入了佛教的轮回说。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庄子不可能持有轮回说,这表明庄子的养生并非保养那不死的精神或灵魂。 既然“养生并非养神”,那么何谓养生?“养生”之“生”,也就是生命。道家的基本思想是“轻物重生”,如杨朱主张“全生保真”,如老子肯定“善摄生者”,“重生”、“全生”、“摄生”的“生”,都是生命。冯友兰指出:“道家的出发点是保全生命、避免损害生命。”(13)庄子的逍遥论,一个重要维度也是保全生命、避免损害生命。因而在《逍遥游》中论“无用之用”时,那棵“不夭斧斤,物无所害,无所可用”的大树樗,为庄子所肯定,而那只“死于罔罟”的狸牲,却是庄子否定的对象。树不能被砍伐,人不能被杀头。保全生命、全身避害,这跟“养生即养心”或“养生即养神”是不相干的。生命是不可以被等同于“精神”或“心灵”的。 至于“养生”之“养”,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自然层面,侧重于处理生死问题,表现为保全生命;一是社会层面,侧重于处理人我问题,表现为保养生命。《逍遥游》推崇“不夭斧斤,物无所害”的大树,侧重于保全生命。《齐物论》反对“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侧重于强调应保养生命。在《达生》篇中,田开之提到的两个人,大致对应于“养”的两个层次: 田开之曰:“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县薄,无不趋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 单豹和张毅都死于非命,都不是“善养生者”;略有不同的是,单豹不能保全生命,张毅不能保养生命。老子心目中的“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之所以“不遇”,并非他运气特好,而是由于他早已预先避开了,单豹却没能避开。单豹远离人群,从不与人争权夺利,生活在自然之中,但他终究丧生虎口。庄子描写的“醉者”,因为“神全”而“莫之伤”,张毅却为疾病所伤害。张毅生活于人群中,积极建立人际关系,凡是富贵人家,他无不趋附奔走钻营,忧患重重,焦虑不堪,英年早逝。单豹和张毅都是“单面人”,他们的生活是片面的。单豹只是自然人,远离社会;张毅只是社会人,脱离自然。两人都不善养生,且都是庄子批判的对象,这说明在庄子看来,完整的养生理应辐射到自然与社会两个领域。 人生天地间,自然赋予了生命,善待这一天赋生命,免于伤害,“终其天年”,这是养生。但人又不得不生活于社会中,所谓“为人处世”,“为人”也就是“处世”,来自社会的伤害尤甚于自然,因而善于处世,免于伤害,也是养生。合而言之,顺应自然,处理好生死问题是养生(保全生命);适应社会,处理好人我问题也是养生(保养生命)。例如庄子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这句话的前半是顺应自然,后半是适应社会。“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这是处世法,也是养生法。照庄子的倾向,处世是养生的重要维度,善于处世是养生的应有之义,不了解这一点,我们便读不懂“庖丁解牛”的寓言,也读不懂整篇《养生主》。 注释: ①《周策纵自选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16页。 ②《周策纵自选集》,第236页。 ③《周策纵自选集》,第247页。 ④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1页。 ⑤封思毅:《庄子诠言》,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 ⑥柏拉图:《斐多》,杨绛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⑦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5页。 ⑧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吴藻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5页。 ⑨爱比克泰德:《哲学谈话录》,吴欲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⑩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9页。 (11)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27页。 (12)对古希腊哲学有深刻影响的俄耳甫斯教,也有灵魂移植说即轮回说,与佛教相似。 (1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7页。标签:养生论文; 庄子论文; 庄子今注今译论文; 养生主论文; 寓言论文; 读书论文; 天道论文; 二元论论文; 健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