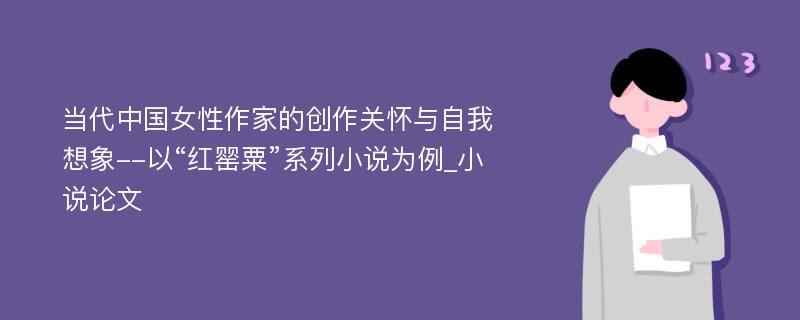
当代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关怀和自我想象——以“红罂粟丛书”中若干小说作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罂粟论文,女作家论文,为例论文,当代中国论文,丛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红罂粟丛书”[1]是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年国内出版的几套女作家作品系列丛书之一。本文拟以该丛书中若干小说作品为例,根据我所侧重的性别角度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阐述论题:一、女性生活史的再现与重构;二、女性经验:妇女与生育;三、女性经验:私人空间;四、性别角度与女性意识。
一、女性生活史的再现与重构
在众多的女性小说中,女人的故事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独立的故事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把女性的故事从一般的生活故事中突显出来,做集中的观照和展示,反映了女作家在性别意识上的自觉,这种自觉的广泛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红罂粟丛书”中有一批这类女性故事长篇,就其题材类型和表现手法的不同,这些女性故事还可以再分为:1.家族故事;2.乡土传奇;3.女性寓言;4.反神话故事。
1.家族故事
胡辛的《我的奶娘》、王晓玉的《正宫娘娘》、张抗抗的《非仇》、范小青的《顾氏传人》这几部中篇都属于家族故事一类。几篇作品均以家族中的女性成员或与叙事者家族有重要关系的一位女性为主角。与男性作家笔下的家族故事不同的是,这些作品均不以家庭兴衰为聚焦点,它关注的是家族中的女人,她们各自的命运、她们承受的苦难或悲剧、她们独特的性格及心理。
《我的奶娘》以一个知识分子女性为叙事者,叙述了“奶娘”这位劳动妇女的大半生。“奶娘”曾是红军的妻子,她的乳汁,喂养大了烈士的遗孤、书香门第的“我”,还喂过伪团长家的少爷。历经四十年代的战乱、五、六十年代的饥荒及“文革”劫难,这位奶娘以她的善良、牺牲和坚韧庇护了她的几个不同阶级、不同血缘的后代。《我的奶娘》把奶娘的乳房、奶汁变成了一个政治化的象征,一个母亲的象征,作品以新的母亲神话参予了“文革”后文学对人性的呼吁。
“奶娘”死于她获得“平反”(“优抚证”弄到,解除其坏分子家属身份)的时刻,广义地说,当人的价值不必依据某权力机构出具的证明——即得到所谓的“社会承认”时,女性作为人的历史才得以诞生。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作品中的女性难免是理念的工具。我的意思是,《我的奶娘》这样的作品,是“样板戏”中男性化的女性形象之终结到新时期文学还原女性以“人”的面目这一过程的一个过渡。今天看来,作品中“奶娘”的神性又表现在,她的正面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男性的成就赋予的,包容一切,承受和奉献一切,是“奶娘”形象呈现出的精神价值,这一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贤良女性应具的美德有内在的统一性。
王晓玉的《正宫娘娘》是九十年代初的又一“妻妾成群”故事。小说似乎以“揭密”的形式,由丈夫向妻子叙述家世家史,实际上却正是正视了其父亲由一个农民之子在城市挣扎、奋斗、发家、破产的过程中与几位女性结为眷属的历史。一个新的视点在于,作者没有把这种一夫多妻现象完全归咎于传统的大家族制度,她把这种事实描写为多种社会因素的综合结果,其中有对家长包办婚姻的不满,有中国社会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造成的必不可免的人口流动,这一流动、还有战乱等社会动荡同时冲击着一切大大小小的家庭,影响着人物的悲欢离合。一夫多妻带来的情感纠葛和利害冲突是男女双方的悲剧。作者这种不囿于性别的深切同情又使作者在作品中实际上消解了充满父权制等级意味的所谓“正宫娘娘”的含义。三位女性都有资格作为“正宫娘娘”,她们都有作为妻子、“正室”受到礼待的理由。却也正是这种各自的合理性中包含了她们作为女性特殊的遭遇、委屈,包括乱伦、被弃置、彼此之间无法调和的名份、妻离子散的境遇。
张抗抗的《非仇》以回忆往事的娓婉风格,叙述了“奶奶”和“外婆”两位女性与家庭后代的恩怨史。人物的独特处在于,两位本属亲家的老人,感情上却格格不入,犹如仇家。她们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形成强烈对比,作者藉此对比探索了人性中善与恶的对立。两位女性的对照还在于,外婆是所谓“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奶奶是广东乡下的劳动妇女,她们的为人处事却仿佛与各自的“阶级本性”相悖。张抗抗以这样两个性格创造,完成了一次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她的切入点却是非中心化的。两位家庭妇女,不在政治活动的中心,她们处在历史舞台幕后的小角落,然而,作为女性,她们对家庭成员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氛围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女性这种既中心又边缘的地位、影响的理解使张抗抗在女性的所谓的家务事、儿女情中找到通向社会、历史、人性深处的途径。
范小青的《顾氏传人》写的是古城苏州世家望族后人的故事。说到这里,不能不补充说明的是,所有在旧时代家声鼎赫的望族进入中国的新时代无一不土崩瓦解。因为家声所代表的财富、功名或知识文化的积累正是一场杀富济贫的变革所要摧毁的对象。作品中主要写了这个家族的后人——三位小姐、一位痴呆儿子的半世生活。这个家族在一个痴呆儿子这里已经失去传人,这或许是一种偶然,暗合了时代冲击下任何世家都气数已尽。但女人们的命运却处在某种游离状态,无论她们嫁给了革命的一方还是不革命的一方(二小姐的丈夫赴台再娶,这一消息令她半世思念成灰),她们总是无法自主的、为世家的末途殉身的人。范小青很少去做静态的心理描写,相反,她写的尽是些寻常里弄里的日常交往,可悲的却也正是在于,日常的交往邻里之间与世家后代的沟通就困难重重。
2.乡土传奇
以旧时代的乡村为背景写女性的故事,故事本身多少具有传奇色彩,这方面我想举迟子建、铁凝的作品为例。
迟子建的《秧歌》、《香坊》、《旧时代的磨房》等作品都在写东北乡村民俗风情中断断续续讲述一个或几个女人的故事。一般来说,在她笔下,生活中的乡民农妇都是粗鄙的,带着原始的、本能的疯狂或丑陋。但超拔于日常生活之上,总有一个、两个凝聚天地之精华、至美至情的女性,似乎为女子痴情、男子仗义这种纯朴民风的最佳境界作证一般。但这也是最后的人证。
在迟子建作品中,女性的生存更多地受到本能和欲望的支配,社会性事件(包括战争)被推到边缘。《旧时代的磨房》中打土豪、分浮财的刀光血影已经迫在眉睫,作者似乎不经意地写到,革命者的动机之一是女人。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女人的被侵犯其意义在于男人的尊严和财产权被侵犯了。四太太不曾拥有她想象中的老爷的痴情,她也不想重新认同那些可能拥有权力,可能使她获得庇护的乡民男性,作者给她的结局似乎只可能是消失得不知所终了。
铁凝的《棉花垛》从乡村男女野合风情的故事说起,然后拉开大幕,把乡村的几位青年男女放在华北抗战的艰难岁月,在政治厮杀的背景下观察他们原本并不复杂的男女之情。有论者指出:“《棉花垛》当是以将人性置放于战争背景中加以考察而建构起小说意义的主体构架的”[2],这种说法的不足之处是忽略了小说中独异的内容: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可欲的对象、政治利益的诱饵、正义复仇的目标这样一个产生多重意义的场所。在小说中,乔、小臭子、国之间的感情关系因战争而复杂化。小臭子爱慕虚荣,与敌伪勾搭成奸,乔与国利用小臭子的奸情获得抗日情报。但小臭子迫于日伪压力又出卖了乔。国代表抗日力量击毙了小臭子,而作为男人,他受到女性肉体的吸引,在举枪之前与其交媾。民族战争的大目标和妇女的自觉自主意识之间无疑还存在广大的断层,因而小臭子面对枪口的哆嗦:“不是刚才还好好的,把你好成那样儿!”这一幕使男性对女性身体支配的权力达到一个悲剧的顶点。它是战争中缺乏自觉自主性的女性的悲剧,并非一般意义上“战争与人性的分裂和统一这一丰富博大的主题”[3],也并非是和男性可以共通的悲剧。抗日的故事有许多讲法,铁凝的这种讲法侧重了女性生存的某种原始状态和现代悲剧形式。
3.女性寓言
林白的《回廊之椅》是寓言方式重塑女性形象的一种尝试。林白也设计了若干历史生活场景:土改时期某富绅的庄园、在庄园主人与共产党的工作队员之间的政治交锋、告密、抄家、枪决等血腥场面。但这些场面所占比例不多,给人更强烈印象的是,她那种叙述的方式和对女性形体美的想象方式。这个作品的寓言性在于,作者几乎不断在提示读者它的某种虚实不定的性质,而其中对女性,具体来说,对朱凉这个阁楼上美丽女性的追寻贯注了叙事者自身经历中许多独特的身体感觉。三太太与七叶之间的同性恋情也围绕着女性的身体魅力,欲望中充满美感。这种超乎寻常的美凌驾于一切有形的历史、政事更迭之上,仿佛是不可战胜的。同样,七叶与三太太那种忠贞不渝与庄园主人兄弟之间的背叛构成另一重尊卑雅俗的对照。这传达出作者某种性别优越感。这是她坦率而深入地表现了女性隐秘的心理经验的一种力量来源。
4.反神话故事
与林白作品中纯净而雅致的叙述相反,徐坤以辛辣的反讽风格,写出她的女性纪事《女娲》。这是女娲造人神话主题的现代变奏,作品以李玉儿为主线写了这家上下五代人的繁衍。公公与媳妇乱伦,生下傻子;傻子长大后强暴母亲,造成怪胎;怪胎的胎衣被饥荒中的兄弟姐妹分而食之……儿子们互相残杀,媳妇斗婆婆,婆婆对孙子灌输仇视父母的情感。阴暗心理、混乱血缘、极糟的生活质量全都没中断这个顽劣的造人过程,作者毫不留情地把有关母亲的美好神话推翻了。她展现出的是一股腐朽丑恶的生殖意志,是母性中的原始性,生物性,更确切地说是兽性。
这样一种文化批判的意味我们在八十年代的男性作家“寻根”一潮作品中已清晰可见,徐坤的特点在于鲜明的女性自审意识,审视女性作为受虐的一方向施虐者的转换,好媳妇与恶婆婆的界限不复存在。还有一个处理也是耐人寻味的,作品中的压迫形式似乎并非性别压迫,至少性别阵线是混乱的。李玉儿受到的身心迫害主要来自婆婆,公公与丈夫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处于劣势。她与公公的乱伦关系里有读书人对弱女子的同情。王晓玉的《正宫娘娘》中也有同样的情形,被弃的儿媳与公公结成盟友,大家庭中婆婆更体现家长的专制性。婆媳关系远比公媳、夫妻关系紧张,压迫也更直接。这或许是中国式的父权制社会造就的又一怪胎:彻底的丧失母亲美德的婆婆形象,父权意志的异性代理。她是一个女性的复仇者,她向自己这一性复仇,在下一代女性身上全面获得报复的快感;报复她作为女性成员在进入男家侍奉公婆、养育儿女过程中受到过的一切伤害。她又是一个父系家族生育意志的强有力推行者,她的意志远比父亲角色本身更执著,因为她自己就洞察一切生育的秘密。《女娲》里描写的媳妇熬成婆的恶性循环是作者对一个不长进的民族、对这个民族愚昧的孕育者们的一声喝问:看看你们生出了些什么东西!
上述几种女性故事类型,反映出当代中国女作家看待女性题材的多重视野。统一的、大写的女性形象为众多性格各异的、被男权文化放逐、被正史遮掩的小女人、恶女人、烈女子或飘泊无依的美女幽灵所取代,女性的历史在文学中显现出一种无中心的离散状态。作家按自己的理解再现、重构女性或作出类似民族寓言的处理,在这种多向的尝试中,中断了几十年的现代女性正视自身的写作传统逐步复活。
二、女性经验:妇女与生育
迟子建的《旧时代的磨坊》、铁凝的《麦秸垛》、陆星儿的《女人的规则》这几篇作品都写到一个共同现象,女性希望以生育来证明自己,证明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生命价值,或者以生育作为不成功的爱情、可望不可即的爱情的补偿。人物的动机不尽相同,但生育对于女性的特殊意义得到关注。
在迟子建的故事中,女性对于生养的渴望使她们最终在精神上区别于男性,而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则暴露出欺骗性、占有性,具有与物欲相同的性质。作品结局揭开短工与二太太“偷情”的真相:“她让我来只想让我和她生一个孩子。”女性被表现为欲望的主体,在这一欲望中,寄寓着女人发自本性的对健全生命的憧憬。这样一种欲望与作品中男性的欲望、男性所重视的价值显出对立。作品中的磨坊因而具有了象征意味,它曾被女性想象为欢爱之地,是爱的极致的证明,但作品中悬念的解决推翻了这一想象。正如磨坊底下藏满了粮食一样,女人不过是另一种欲望的粮食,即使老爷阶级与雇工阶级在一场变革中已是水火不容,但女人的命运有如粮食,不过是双方同样都希望占有的一笔财产。
铁凝的《麦秸垛》写性禁忌的年代下乡知青的故事,描写了那种盲目的情欲冲动和不成功的恋爱关系,但作品中的视野却不限于知青。她让乡村里农妇、村民的婚育、家庭生活场景与之并行发展,这样,两位不同年龄、不同生活背景的女性:农妇大芝娘与知青沈小凤在某一点上的一致性便令人惊愕:面对无望的婚姻或爱情,她们都要求和对方生一个孩子。生育在这里成为一种绝望的挣扎,“来证明女性性经历的成果,来填补作为女性一生只有一次的处女代价的付出。”[4]在这看似无理性的要求里,作者写出了女性主体性的又一种失落形式,她们无法以别的方式,以精神、意志、理性的行为来处理自己的感情,决定自己的婚姻、爱情。如此彻底的出让身体,显示出巨大的性别差异面前女性的无力、被动。把生命价值寄托于感情的代偿——生育,这种传统观念依然束缚着女性。
陆星儿《女人的规则》发展了这样一个情境,女主人公田恬决心生下与一个有妇之夫的孩子,她以为,“这是留住他留住爱情留住生活的最后一个办法。”作品描述了这个单身母亲在怀孕、生产、育婴的全过程独自经历的重重困难。憧憬爱情的浪漫女人穷于应付经济窘迫、时时遭受日常琐事困扰。
把生育的经历处理成夫妻双方精神、感情的全面更新,池莉的小说《太阳出世》因此别开生面。池莉让生育作为积极的生命力量、作为推动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理解和自我完善的力量出现。她以不避俗人俗事、不避粗鄙的态度写了一对浅薄无知的小男女在心理和经验上与为人父母的角色的差距。作品的魅力在于,在怀孕、待产、照顾婴儿等一系列生活琐事带来的麻烦里,意识到作了父母的小夫妇,点点滴滴地改变了自己,新生命的出世重新造就了她(他)们。
在《金手》这篇作品里,池莉也涉及到上述作家所思考的女性处境,作品中有一个情节,女主角在丈夫的压力下,为掩饰男方的性无能,被迫屈从“借种”的风俗。结果提供“种子”的男子对她产生了感情,要求把“借种”的母女变成自己的妻儿。女人是一个出色的妇产科医生,有一双接生的“金手”,然而她在家庭之内,在生育活动中,却不能不扮演一个被动的、被男性权力之手操纵、被争夺的角色。
在女作家笔下,生育通向平凡、世俗,然而,世俗小人物也可能在这最普通的居家过日子的经验中创造奇迹。毕淑敏的《生生不息》就写出人物通过顽强、痛苦的生命孕育,完成对疾病、死亡的超越,这里的生育意志是人物性格的写照。作者极写生育的艰险和女性惊人的毅力,表达了她与《预约死亡》相互补充的主旨,理解生死,珍惜生命。
以上论及的作品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妇女的生育经验中蕴含的社会、心理内容,显示了这一题材对于考察女性生活和身份处境的丰富潜能。
三、女性经验:私人空间
九十年代表现女性作品一个新的动向在这套丛书中也有体现,陈染、林白的作品代表了这种新的取向,即在私人生活、在个人化的情绪体验中书写女性。
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主要描写了作为独身者的两代人、母女两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从其中,读者可以感觉到中国在告别了一个集体主义的年代之后,女人确定自我、把握自我的重重困难。小说结束于逃离,但逃出母亲爱的监视却不意味着自由,旅居异国的经历甚至加深了灵魂的漂泊无依之感。
逃离与无处可逃在《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中都是萦绕全篇的主旋律。逃出成规与把握自我是一个目标,但它难于追逐。出走、归家、重新谋职,女主角一次又一次陷入幻象破灭后的虚妄。面对虚妄和孤独,似乎是守住自我的唯一可能。陈染清醒地分析了人物这种自我放逐于孤独的处境。
在反幻象这一点上林白的作品与陈染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新时期文学对人性的呼唤包括呼唤爱情,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曾风靡一时,而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作品里,这种爱情偶像不复存在,例如,张欣的《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和《城市爱情》等作品。林白、陈染的作品深入地探寻了女性作为独立自我的内心状态,情、爱、欲、性在这个自我的内心里呈现出矛盾的扭结。女性的爱情悲剧在这种意识的观照下,成为自我丧失的悲剧。
在林白的作品中,爱是女性的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重要领域,它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领域。《瓶中之水》写两位女性的恋情,林白把这种同性恋写得充满激情,充满性格的张力,充满自我了解和感情交流的喜悦;相比之下,男女恋情肤浅乏味,远远达不到那种强烈的程度。在断断续续的故事里,她实验着表达自我想象的独特方式、表达那种伴随文字想象应召而来的各种情绪体验、意象画,由此形成她特有的叙述文体,带有强烈主观抒情色彩的自叙性文体。
林白与陈染的文字风格不同,陈染的叙述有女性少有的幽默自嘲,显示一种逆反心态的表述,诸如对“寡妇”、“婊子”、“妓女”的议论等,而她们作品的另一相同之处是对自我的不断召唤和质询,她们都着意描述了作者的某种写作状态,并把这种状态表现为可能把握的唯一真实和自由。
四、性别角度与女性意识
由于本文的论述是在上述几个有限的范围进行,所以,还有不少女作家的作品这里没有涉及,她们作品中的女性及表达方式上的尝试也需要更多篇幅讨论,例如残雪、赵玫、蒋子丹的作品等。
以“红罂粟丛书”为例,总体来看,中国女作家里关注的个体生存及独特的性别经验的仍不是主流,在女性题材作品中,一个比较一致的倾向是,通过女性的故事写这一性作为某一阶层的群体的命运,把女性问题作为一个有较多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来看待。与之相关的另一共同点是,作家对超越性别这一角度的强调。例如,铁凝谈到她自己的女人故事的创作经验时说:“我设想那大约归结于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作‘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景况。……当你落笔女性,只有跳出性别赋予的天然自赏心态,女性的本性和光彩才会更加可信。进而你也才有可能对人性、人的欲望和人的本质开展深层的挖掘。”[5]张抗抗也说过同样的意见,“所以在她看来,也许唯有‘人’的问题,是男人和女人‘性沟’间永远的渡船和桥梁。”[6]
两位女作家强调的超越性别的视角反映了性别意识在中国的复杂处境。正如西方妇女研究学者所注意到的[7],中国极左时期的男女平等理论抹杀性别差异,使女性男性化。新时期批判极左思潮的另一后果是“回到女人去”这一自然性别意识的复苏。但在这一强调女性恢复自然本质的观念里,保留了男女有别一系列男性中心传统观念的内核。它的批判意义在于,反对将男女的自然属性置于任何意识形态的控制下,缺陷则在于,女性仍然被理解为在能力和社会角色上天然低劣于男性的一性。因此,任何关注整个人的问题的女作家都不愿意认同一个简单强调自己的自然性别的女性角度。
但是,另一方面,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中国社会的变革对女性的冲击,出于直接的生活经验和创作上的相互推动,女作家作品中的性别意识有鲜明的表露。如前所述,见之于各种女性题材的探索。有男性批评家认为:“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气候的女权主义运动,也就不可能有西方理论家设想的女权主义文学。”[8]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女作家的作品本身来考察其中的社会性别观念和社会性别关系。在这方面,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出了有益启示,即注重分析女性作家创作的实际状况,分析作品中的形象与作家性别经验的关系,从中发掘女性写作的涵义和女性写作特质。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认为在若干批评家和若干女作家那里,对于女性意识有些误解。来自批评方面的误解是,把女性意识缩减为独特的女性经验,特别是身体经验和性体验,这样,关注社会问题的女性写作就成为超越女性意识狭隘性的表现。例如,方方的作品被评价为:“更关注那些人类性的和社会性的普遍问题,而不限于单纯的女性意识。”[9]但这种批评恰恰错过了方方作品中隐蔽的女性意识。以方方的《行为艺术》、《埋伏》为例,两个中篇写的都是警察破案,类似侦探故事模式。但方方还赋予她的男性主角多愁善感、热爱艺术、自由散漫等具有“女性化”特点而与男性化的警官职业格格不入的性格特征;在《埋伏》的重大行动中,她让某个偶然因素起到出人意料的关键作用,这些手法对男性侦探故事模式中的性格类型以及严格推理是一个玩笑性的挑战。我觉得,方方这些新意与作家性别意识的联系被论者忽略了。
在有的女作家这一方面,由于对女性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意识不分明,这样在表现女性生活时,她的感觉是沉重和困惑,不能有力地写出女人作为经验着的主体那种主动的心理活动,没有力量展开情境中包含的性别冲突,或者说没有意识到这种冲突的焦点所在,例如陆星儿的《小凤子》。在一些描写职业妇女的作品里,女人的内心经历显得贫乏。由此而言,西方女性主义对性别的新观点,她们的文化、文学研究中的性别角度,对于中国的女作家和女性文学的研究者,值得认真借鉴。
注释:
[1]“红罂粟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书目如下:
蒋子丹:《桑烟为谁升起》
黄蓓佳:《玫瑰房间》
王小鹰:《意外死亡》
陆星儿:《女人的规则》
胡辛:《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毕淑敏:《生生不息》
叶文玲:《此间风水》
林白:《子弹穿过苹果》
陈祖芬:《让我糊涂一回》
迟子建:《向着白夜旅行》
方方:《何处是我家园》
赵玫:《太阳峡谷》
陈染:《潜性逸事》
张欣:《真纯依旧》
池莉:《绿水长流》
张抗抗:《永不忏悔》
范小青:《还俗》
徐坤:《女娲》
徐小斌:《如影随形》
铁凝:《对面》
王晓玉:《正宫娘娘》
残雪:《辉煌的日子》
[2]易光:《非女权主义文学与女权主义批评——兼读铁凝》,原载《当代文学》(成都),1995.5.见“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月刊,J3 1995.12,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96年1月30日出版,第206页。
[3]易光:《非女权主义文学与女权主义批评——兼读铁凝》,原载《当代文学》(成都),1995.5.见“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月刊,J3 1995.12,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96年1月30日出版,第206页。
[4]王绯:《铁凝:欲望与勘测》,《当代作家评论》1994.5.转引自易光文章,同上。
[5]铁凝:《跋》、见《对面》,第374页。
[6]张抗抗:《“红罂粟”题解(代跋)》,见《永不忏悔》,第350、351页。
[7]王政:《美国女性主义对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角度》,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5月第1版,第270、271页。
[8]陈晓明:《勉强的解决: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概论》,见陈晓明选编:《中国女性小说精选》,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页。
[9]陈晓明:《勉强的解决: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概论》,见陈晓明选编:《中国女性小说精选》,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9页。
标签: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红罂粟论文; 文化论文; 铁凝论文; 读书论文; 女娲论文; 张抗抗论文; 迟子建论文; 林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