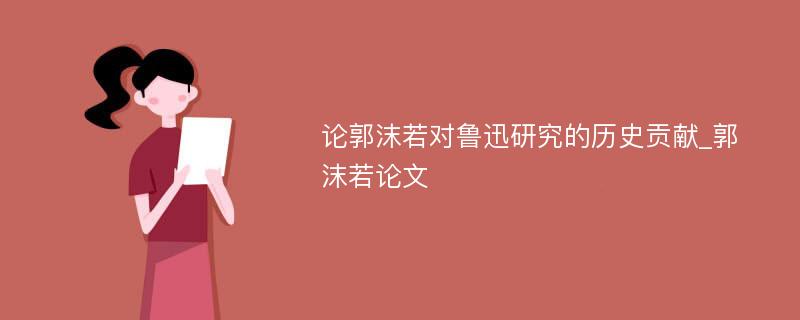
论郭沫若对鲁迅研究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鲁迅论文,贡献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鲁迅逝世后的四十年里,郭沫若研究鲁迅及其作品的文字达数十篇将近十万言。有人曾认为这些文字“巧妙流利”,是“矫情”和“虚伪”。此与相反,我们综观这些文字,有理由说,郭沫若勇敢地捍卫了鲁迅,科学地宣传了鲁迅,独到地阐释了鲁迅的作品,他始终不辍的鲁迅研究的实践,证明他是“鲁迅精神最优秀的继承者”之一①。
一、严厉的自我批判
郭沫若和鲁迅虽然同在新文化战线上战斗了将近二十年,也时常想着最好能见一面,“亲聆教益,洞辟胸襟”;但因“人事的契阔,地域的睽违”,终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鲁迅晚年也有想和郭沫若见面的意愿。郭沫若沉痛地说,鲁迅的逝世,“这愿望是无由实现了。这在我个人,真是一种不能弥补的憾事。”②
众所周知,一九二八年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郭沫若和鲁迅曾有过争论,甚至“用笔墨相讥”,发生过亲者痛而仇者快的事情。然而,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鲁迅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旗手作用愈益显著,以至三十年代初在国民党反动派刀光剑影的“围剿”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郭沫若也随着革命的进程,差不多与鲁迅同时,由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战士,对事物的认识愈见深刻,愈见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因此,他对鲁迅的评价也就产生了一个飞跃。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③鲁迅逝世时,人民沉痛地哀悼,成千上万的人们自觉地汇合成送葬的队伍,棺盖上铺复着“民族魂”的旗帜,表示着亿万人民由衷的赞颂。而当时社会上诸如鲁迅“偏狭”、“偏私”、“刻薄”、“世故”种种恶评也因之蜂起。郭沫若撰文痛斥道:这“都是有意无意地诬蔑”,是“代表社会恶魔来说话。”④他认为,“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鲁迅是拿着剑倒在战场上的勇士”,他的光辉是永不会磨灭的。郭沫若已明确意识到,是否保卫鲁迅,高举鲁迅的旗帜,事实上已经不纯粹是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的小事,而是关系到革命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关系到是否把“五四”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大事。
正是从这样一个大局出发,鲁迅的逝世首先给郭沫若带来的是很大的悲痛。唤起他最初联想的,是四个月前高尔基的逝世。“仅仅相隔四个月,接连失坠了两个宏朗的巨星!”“这损失的重大是不可测算的。”⑤而痛定思痛后,郭沫若在鲁迅逝世后的第四天,就这样诚挚地向世人进行了自我解剖:“作为年青弟弟的我,对于长兄的叱斥,偶尔发过孩子脾气,更曾辩过嘴,倒也是事实。”“这种事,假如我早一些觉悟,或是鲁迅再长生一些时间,我是会负荆请罪的,如今呢,只有深深的自责而已。”⑥六年后的一九四二年,郭沫若在创作历史剧《孔雀胆》时,曾得到昆明的一位青年朋友杨亚宁的帮助。杨在这年十月十八日给郭沫若的信中,说自己曾托友人从重庆购得鲁迅石膏浮雕像一具,“亟须制联以映衬之……敬乞先生于便中法书类似鲁迅像赞之辞句。”郭沫若接信后,立即书写了“返国空余挂墓剑,斫泥难觅运风斤”一副对联寄去。“挂墓剑”典故出自《史记·吴太伯世家》。郭沫若从日本“返国”,鲁迅已不幸病故。他以上联来表达对鲁迅的深切悼念之情。“斫泥”一句典故出自《庄子·徐无鬼》。郭沫若在这里活用了这个典故,说自己鼻端上有污泥,想请鲁迅为自己砍掉,“然则求之而不可得”,已经难以寻找鲁迅那把运风的斤斧了。由此可见,郭沫若是多么恳切地希望鲁迅再来批评自己,帮助自己呵!这对于鲁迅逝世后继续挑拨他与鲁迅的关系,对鲁迅进行攻击的“鞭尸者”也是有力的一击。
正确看待鲁迅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之间的争论,这是郭沫若进行严厉的自我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鲁迅和前期创造社的关系是正常而友好的。他们谁也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相互声援,相互支持的事实。郭沫若多次谈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左右,他失掉了自由回到了上海,与郑伯奇、蒋光慈等同志商议,把《创造周刊》恢复起来,作为启发青年的言论机关,想请求也在上海的鲁迅领导。郑伯奇、蒋光慈和鲁迅商量,鲁迅慨然允诺。因此,《创造周刊》复活的广告便见诸报端,负责人是以鲁迅领头,郭沫若以“麦克昂”的变名居于第二位。但由于“不久仿吾游历日本回来,还有继续回来的所谓‘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他们那时便异常尖锐,都不赞成我的主张,因而便把成议打消了。”⑦
作为创造社的中坚,郭沫若毫不讳言地承认:打消联合的“成议”,“这对于鲁迅的确是对不起的一件事。而更对不住的是《文化批判》出版,竟把鲁迅作为批判的对象”⑧。“把鲁迅作为批判的对象,让蒋光慈被逼和另一批朋友组织起太阳社来了。于是,语丝社、太阳社、创造社,三分鼎立,构成了一个混战的局面。”⑨这就削弱和耗损了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极有害于思想文化阵线上的团结对敌。
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批判”鲁迅,原因来自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前后,正是国内外“左”倾教条主义思潮泛滥之时,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等重大问题认识不清,错误地把鲁迅当作革命的对象加以批判,称鲁迅为资产阶级的“最良的代言人”,“时代的落伍者”,“封建余孽”。鲁迅曾深刻指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⑩鲁迅批评“革命文学家”,说他们不敢正视现实,畏惧黑暗,掩藏黑暗,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郭沫若在回答青年提出的“对创造社应该如何评价?”时,这样沉痛地总结教训:“创造社……后期的同志们犯了一些错误。他们从国外回来,把内部矛盾看成主要的,骂鲁迅,骂蒋光慈。”并坦率地提供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创造社后期,彭康、朱镜我、李初梨、冯乃超等在日本,受了福本和夫的影响,……他们商量以创造社为基础,举起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当时正是白色恐怖的时候,为了更好的工作,我主张隐蔽一些。成仿吾和后期的几位同志都不赞成我的看法,我没有坚持。”(11)
在论战中,鲁迅虽然当时对提倡革命文学的认识不足,但仍肯定提出这一口号“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诚恳地分析了革命文学兴起的原因,“自然是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的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也肯定创造社“在新分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他还很坦白而公平地说过:“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论著,“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12)郭沫若也认为,“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使它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的努力,是有不能抹煞的业绩存在的。”(13)
对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文坛总有人嘁嘁喳喳,搬弄是非。小报偏喜欢记些鲁比郭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他们只有争座位,斗法宝。鲁迅晚年在总结自己战斗历程时明确说过,“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14)郭沫若也说过,创造社的朋友们,“批判鲁迅即使是出于错误的认识,……但他们是对事不对人”,“后来那些朋友,一反而拥戴鲁迅,不就是很明白的吗?”(15)两位文化巨人都认为这场论争是革命文艺界内部争论。正因为如此,才有一九三○年初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终于实现了在共同对付国内外敌人的“同一目标”下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大团结。
郭沫若关于鲁迅与后期创造社所作的自我批判,对于革命文学论争一些带根本性质问题的认识,同鲁迅的意见,“不期巧合”,从而捍卫了鲁迅,捍卫了革命文艺阵营的团结,捍卫了革命的原则性,他与鲁迅的心从根本上说是相通的。
郭沫若在批判周作人堕落,背叛鲁迅的同时,高度赞颂闻一多:“闻一多说过:‘鲁迅是对的,我们从前是错了。’这是把生命拿来做了抵押品的严烈的自我批判。”(16)应该承认,郭沫若和闻一多一样,继承了鲁迅“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的精神,在鲁迅逝世后进行了“严烈的自我批判”。这是郭沫若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也是他能够深入地理解鲁迅及其作品的最新的、最坚实的基石。
二、鲁迅精神永远和我们同在
郭沫若十分钦佩鲁迅的伟大人格,精辟地概括了鲁迅精神中相互联系的两个主要特点,即对于他所痛恨的恶势力的反抗是毫不妥协的,对于他所热望的新生力量的拥护是甘愿粉身碎骨的。把鲁迅的精神归结为:对敌人的“怒”加“忍”等于鲁迅的“冷”;对人民大众的“爱”加“诚”等于鲁迅的“甘”(17)。他认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是很生动地把整个的鲁迅形象化了。”(18)“可以说是毕生战斗与自我批判的生活实验中得来的精粹。”(19)鲁迅逝世后,郭沫若十分强调并科学地宣传鲁迅的革命精神,因为在他看来,足以纪念鲁迅的,是鲁迅自己的文章、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对于仇敌的认识与战斗,“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不朽的”(20)。
郭沫若研究鲁迅的文字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就是他有效地实践着“鲁迅的纪念由书斋走到社会”,“鲁迅的精神深入人民大众生活”(21),让“鲁迅和我们同在”(22)的主张。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火扩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七月底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国投入神圣的抗日战争。他一踏上祖国土地,即发表了步鲁迅七律《无题》原韵诗一首。诗中不仅表明了自己是鲁迅精神的“呼唤”才返回祖国,而且号召四万万中国人以鲁迅为榜样投入反侵略的正义战争。郭沫若甚至说,“我在回国的当时……假如没有鲁迅这座精神上的灯塔,假使鲁迅不曾给过我一些鞭挞,我可能永远在日本陷没下去,说不定我今天是会在南京和周作人作伴的吧?”(23)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使这两位文化伟人在心灵上达到了高度的融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使郭沫若的七律和鲁迅的《无题》一样,思想上得到了高度的升华,“哀世动人,可称绝唱”。之后,在上海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郭沫若慷慨激昂地说道:“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无一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一九四○年六月,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郭沫若在《写在菜油灯下》中说:“鲁迅是奔流,是瀑布,是急湍,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海。鲁迅是霜雪,是冰雹,是恒寒,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春”。这是他对鲁迅的赞美,更是对养育鲁迅的中华民族的赞美,对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事业的赞美,其中所蕴含的对于人民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战士们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鲁迅在《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中,对王国维有过这样精辟的评价:“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既肯定了王国维作为学者的诚实,又指出他对封建王朝“愚忠”的迂腐气。二十年后的一九四六年九月,郭沫若撰写了《鲁迅与王国维》。他在文章中指出,两位的学历,思想及治学方法和态度,乃至他们的性格,差不多有同样“令人惊异的相似”。但是,“却有不能混淆的断然不同的大节所在之处”,这就是鲁迅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进步,并且领导了时代的前进;而王国维却停止在一个阶段上,竟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因此,“王国维的死我们至今感觉着惋惜,而对于鲁迅的死我们却始终感觉着庄严。王国维好像还是一个伟大的未完成品,而鲁迅则是一个伟大的完成。”郭沫若写《鲁迅与王国维》的时候,解放战争业已开始。这是一个风云突变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命运大决战的时刻。知识分子再次面临历史道路的选择。那时,有如郭沫若这样坚定的革命者,有如闻一多这样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以鲜血和生命谱就一曲壮丽颂歌的民主战士;然而也有如朱家骅、张道藩这样反动的知识分子,更有一些苦闷、彷徨,看不清前途的知识分子。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的及时刊布,无疑对于革命者是个激励,对于反动分子是个鞭挞,而尤其对于徘徊歧路的知识分子是个有力的教育。因而,它的意义也就不限于学术研究本身的价值了。
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反复提倡鲁迅“韧”性战斗精神;在伟大的解放战争期间,他反复强调学习鲁迅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横眉冷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而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期间,他都始终坚持宣传和学习鲁迅,同一切恶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以这样的态度努力工作下去,怕才是纪念鲁迅的最好的道路。”(24)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面临着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新形势。郭沫若在继续强调学习鲁迅对敌斗争精神的同时,更着重学习鲁迅的“孺子牛”精神。他说,“今天,建国的大业已经开始,这又是更宏阔而长远的一场斗争——要和一切落后的现实斗,和自然的威力斗,和技术的顽强性斗。要把战争的创伤医好,要把落后的农业中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中国,正须得全中国的人都成为‘孺子’的‘牛’”;“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大家赶快把头埋下去替新生中国做‘牛’吧,而且要做得十分地心甘情愿。”(25)郭沫若这里所强调学习的,实际上就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既是鲁迅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一切革命者无产阶级世界观所必具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取得政权以后,能否有效地保卫和发展革命成果,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到底的关键。为此,在文艺战线上,郭沫若要求文艺工作者,应该进一步学习鲁迅作为伟大作家“化草为奶”的本领,刻苦锻炼,运用文艺武器为革命服务;学习鲁迅的取精用宏,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并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而成为自己的血肉,沿着鲁迅所开拓出的道路继续前进,继续发展,创造出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融洽无间的优秀作品,对祖国、对人民、对世界,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26)。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郭沫若强调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确信“惟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对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怀抱着无穷的信心;指出,正因为这样,鲁迅才能在敌人面前,他的自我无穷大,而在“孺子”面前,在新生力量面前,他的自我又是无穷小。他是把自己融化在新生力量当中了,在对敌斗争时,因而他就成为新生力量的代表(27)。郭沫若这些对鲁迅精神的论述,充满着辩证法的熠熠光辉。
解放以后,郭沫若为在国际上宣传鲁迅和推动鲁迅研究的开展还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因为,在他看来,“鲁迅已不单纯是中国的鲁迅,而是世界的鲁迅了”(28),鲁迅精神是世界革命人民宝贵的财富,鲁迅作品是“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29)。
一九五六年,日本岩波书店准备出版《鲁迅选集》,郭沫若为这个选集写了“题词”。他热情而深刻地指出:学习鲁迅精神、鲁迅作品的“究极的目标是什么?是要战胜一切恶势力,使新生力量顺畅的成长,让创造世界的全体劳动人民能够早一日享受到全面发展的自由、幸福、和平的生活。”郭沫若更进一步把鲁迅的革命战斗精神揭示给日本的广大人民,坚信鲁迅毕生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能在全世界实现。
仙台鲁迅纪念碑修建过程中,郭沫若亲自为纪念碑题了字。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日,仙台鲁迅纪念碑揭幕之时,郭沫若致电祝贺,认为纪念碑的建立,有助于中日友好往来,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标志。同年十月国庆节后不久,毛主席接见了以黑田寿男为首的代表团,把亲笔书写的鲁迅《无题》诗“于无声处听惊雷”赠送给了日本朋友。郭沫若阐释道:主席题赠鲁迅这首诗的深意是“日本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勾结的情形下受着苦难,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全国性的统一行动。即使运动有时在低潮时期,但要求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日本人民是在酝酿着更惊人的霹雳。”(30)遵照主席指示,他把这首诗翻成了日文,同时也翻成了口语,以便于鲁迅诗作的精神在中日两国人民中广为传扬。
一九七一年十月初,法国朋友露阿夫人访华要求见到郭沫若,表白她要研究中国近代文学,要从郭沫若研究起。郭沫若听了后,以谦逊的态度和无私的精神,恳切地劝她去研究鲁迅。这位夫人听从了郭沫若的话,编译出版了鲁迅杂文选、回忆录等书,工作颇有成绩(31)。此时,郭沫若已年近八旬,而且是“文化大革命”非常时期,他虽身心交瘁,仍念念不忘利用一切机会在国际上宣传鲁迅和推动鲁迅研究工作的开展,这怎能不令人感动和钦佩。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更是一个思想家和革命家。郭沫若在鲁迅的研究与宣传中结合中国和世界革命事业的发展需要,强调学习鲁迅及其作品的革命精神,这无疑是准确地把握住了学习鲁迅、继承鲁迅、发扬鲁迅的精髓。
三、独具慧眼的鲁迅研究
郭沫若反对“平时毫不研究,偏偏成为纪念文写作专家”,他认为“死者有知,鲁迅是会蹙额的”(32)。他对鲁迅生平思想及作品有过细致的研究。他的《鲁迅与王国维》、《契诃夫在东方》等,可以说开了鲁迅与中外作家比较研究的先河。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的《契诃夫在东方》,是他在重庆为纪念契诃夫逝世四十周年而写作的论文。郭沫若认为,“鲁迅在早年一定深切地受了契诃夫的影响”,深刻指出鲁迅作品与作风和契诃夫几点相类似之处:其一、假使契诃夫的作品是“人类无声悲哀的音乐”,那么鲁迅作品“至少可以说是中国的无声的悲哀的音乐”,他们都是平庸的灵魂的写实主义。庸人的类似宿命的无聊生活使他们感到悲哀,沉痛,甚至失望。其二、他们都是研究过近代医学的人,医学家的平静镇定了他们的愤怒。解剖刀和显微镜的运用训练了他们对于病态与症结作耐心的无情的剖检。他们的剖检是一样的犀利而仔细,而又蕴含着一种沉默深厚的同情,但他们却同样是只开病历而不处药方的医师。其三、两人都相信着“进步”。这是近代生物学所证实了的,无可否认的铁的事实。故虽失望,而未至绝望。在刻骨的悲悯中未忘却一丝的希望。这希望,给契诃夫和鲁迅的作品以潜在的温暖,就象尽管是严寒的冰天雪地,而不是无生命的月球里的死灭。郭沫若同时指出,后期鲁迅“和契诃夫分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由契诃夫变为了高尔基”。因为鲁迅比契诃夫迟来世界二十年,后离世界三十年以上,鲁迅得以亲眼看见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革命势力的高涨,希望成了现实,明天变成了今天,“进步的信仰”转化为了“革命的信仰”,在“契诃夫不能够高声地公然地向人说出的”,而在后期的鲁迅却能够向人说出了。郭沫若这些将鲁迅与契诃夫进行比较分析的科学见解,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听起来,仍感觉是那么的准确和新鲜。
和许多学者一样,郭沫若肯定鲁迅是从旧写实主义进到新写实主义;但是,他又独具慧眼地指出鲁迅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成分。他是最早提出研究鲁迅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的学者。在《鲁迅与王国维》中,他已提到:“鲁迅也喜欢尼采,尼采根本就是一位浪漫派。鲁迅早年的译著都浓厚地带着浪漫派的风味。这层我们不要忽略。”一九五八年,他指出:“鲁迅的《故事新编》中的那些作品是取材于神话传说的,有的远到了开天辟地以前,全靠丰富的想象力纺织成了绚烂的万花镜图卷。当然,他是借以讽刺现实的,但你能说那里不是饱和着浪漫主义风格吗?”(33)几个月后,他再一次说到:“很多人说鲁迅是现实主义作家,我们不反对,但如果反过来说他是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我看也不是不可以的。比如阿Q这个人物,实际上并不存在,他不是以积极的英雄姿态出现,而是集消极可憎的东西于一身,事实上也是夸大的产物。”(34)认为鲁迅早年的译著带着浓厚的浪漫主义风味,认为鲁迅的《故事新编》饱和着浪漫主义风格,今天几乎已发展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认为阿Q是浪漫主义的产物,甚至认为鲁迅作品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一半对一半”,赞同者怕是寥寥无几。作为学术问题,郭沫若的某些见解自然可以商榷;然而作为研究鲁迅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学术课题的提出,其首倡之功是不应该抹煞的。
一九四○年十二月,郭沫若还撰写了学术长文《庄子与鲁迅》。他从语汇、完整的词句、故事和寓言的题材方面,详细地例举了鲁迅作品中近三十处对庄子的引用和借鉴。郭沫若的细致校勘,对后来鲁迅全集的“精确注解”大有裨益。《庄子与鲁迅》还在指出鲁迅思想和著作都受过庄子影响的同时,深刻地指出鲁迅后期尽力想从古人的影响下摆脱出来,尽力想摆脱庄子的消极影响。此后,郭沫若在别的鲁迅研究的文章中,进一步指出鲁迅从庄子思想中“蜕变”了出来;指出鲁迅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是从庄子的“渊默而雷声”(《在宥篇》)和“听乎无声”(《天地篇》)等语中“蜕变出来的”。但在这里起了“质的变化”,即是由庄子的形而上学观点变成了鲁迅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鲁迅达到了“化腐朽而为神奇”的境界。以上评论都从一个方面鲜明地昭示了鲁迅坚毅的性格和对待祖国文化遗产的科学的批判继承精神。
作为新文学伟大作家的鲁迅,他的主要业绩之一是他精粹的现代题材的小说创作。他的《呐喊》、《彷徨》“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35),以深邃的思想意蕴和圆熟的艺术技巧,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最初实绩”,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性的作品。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也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中外文学史上实属罕见。而人们,包括郭沫若自己在内,对鲁迅小说历史地位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郭沫若曾这样地自我解剖过:早先“委实傲慢”,“多少挟着些意气的作用”,“对于鲁迅作品一向很少阅读”;对于鲁迅小说风格的感觉是,“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后来,他有了新的理解:“中国文学由鲁迅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中国的近代文艺以鲁迅为真实意义的开山”(36);鲁迅小说主要是以人民为题材,“平易近人”;鲁迅小说的风格,“与其说是鲁迅的性格使然,宁是时代的性格使然。”鲁迅生长在民族最苦厄的时代,他吐出了民族在受着极端压抑下的沉痛的呼声;民族的境遇根本不平,反映民族呼声的文字,自然不能求其平畅;民族的处境根本暗淡,反映民族生活的文字,自然不能求其鲜丽,因而“汪洋万顷的感觉,惠风和畅的感觉,在鲁迅文字中罕有。”(37)“迅翁晚上融欧化,一卷阿Q信足多”,认为鲁迅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确是杰作,其妙处能在参用欧美作风而不脱离中国人民大众。郭沫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毅然地纠正了自己傲慢的偏见,科学地分析了鲁迅小说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指出鲁迅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大众化结合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给鲁迅小说以崇高的历史地位。可以说,郭沫若是茅盾、冯雪峰、瞿秋白之后,对包括鲁迅小说在内的鲁迅作品有深刻认识和分析的卓越的评论者。
郭沫若在认识鲁迅,研究鲁迅及其作品上,还提出过其他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他说过:“考虑到历史上的地位,和那简练、有力、极尽最曲折变化之能事的文体,我感觉着鲁迅有点象‘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但鲁迅的革命精神,他对于民族的贡献和今后的影响,似乎是过之而无不及”(38)。又如,他认为鲁迅的杂文是对敌人的投枪,“陵劲淬砺”(39),“实在是社会的散文诗”,“那价值并不亚于《呐喊》、《彷徨》”(40)。而《鲁迅书简》“隆光精气,皎然不滓”,“当常置左右,以生廉立”(41)。对于鲁迅的旧体诗作和书法,郭沫若赞叹道:“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者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虽寥寥十四字,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爱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具足。此真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鲁迅先生也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居风格。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明法度。远愈宋唐,直攀魏晋。”(42)对于鲁迅的学术专著《中国小说史略》,郭沫若更是推崇备至:“这部不朽的著作”(43)“不仅是拓荒的工作,……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44)这些精粹的见解,都大大开拓了鲁迅研究的眼界,丰富了鲁迅研究的内容,直到今天,还作为评论鲁迅的精辟言论被研究者们所常常引用。
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郭沫若认为“这是最有斤两的话”。什么是“鲁迅的方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对于反人民的恶势力死不妥协的方向。”郭沫若并从革命人生观的高度加以剖析:“假使我们实事求是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我们坚忍不拔地死不妥协地向一切反人民的恶势力顽强战斗到底,那便是鲁迅的信徒,我们便可以走向永生。假使我们是反其道而行,那便是鲁迅的敌人,我们便走向万劫不复的死路。”(45)郭沫若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和鲁迅研究的历史贡献,赓续了“鲁迅的方向”,成为鲁迅忠实的“信徒”。作为“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郭沫若是当之无愧的!
一九九五年二月,为郭沫若逝世十七周年而作。
注释:
①(16)(22)(23)(45)郭沫若《天地玄黄·鲁迅和我们同在》。
②⑤(36)《集外·民族的杰作——悼唁鲁迅先生》。
③《新民主主义论》。
④(37)(38)《羽书集·写在菜油灯下》。
⑥(24)《坠落了一个巨星》,见1936年11月16日出版的《现世界》第1卷7期。
⑦⑧⑨(15)《天地玄黄·一封信的问题》。
⑩《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11)《郭沫若同志答青年问》,1958年11月27日,见《文学知识》1959年5期。由戎笙整理。
(12)《三闲集·序言》。
(13)《革命春秋·海涛集·跨着东海》。
(14)《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7)《天地玄黄·冷与甘》。
(18)《鲁迅礼赞》,载《文艺报》1956年4期。
(19)《继续走鲁迅的路》,载1948年10月20日香港《华商报》。
(20)《集外·不灭的光辉》。
(21)《天地玄黄·我建议》。
(25)《继续发扬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载《文艺报》1949年3期。
(26)(27)《继续发扬鲁迅的精神和本领》,载《文艺报》1961年9期。
(28)(43)《雄鸡集·体现自我的牺牲精神》。
(29)(44)《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
(30)《翻译鲁迅的诗》载1961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
(31)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载1979年《新文学史料》第二辑。
(32)《总是不能忘记》,载1941年10月19日重庆《新蜀报·蜀道》513期“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
(33)《雄鸡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34)《就目前创作中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载《人民文学》1959年1月号。
(35)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39)《洪波曲》。
(40)《并没“浪费”》,1941年11月4日香港《华商报》。
(41)致许广平(1937.7.19),见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
(42)《〈鲁迅诗稿〉序》。
标签:郭沫若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契诃夫论文; 无题论文; 创造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