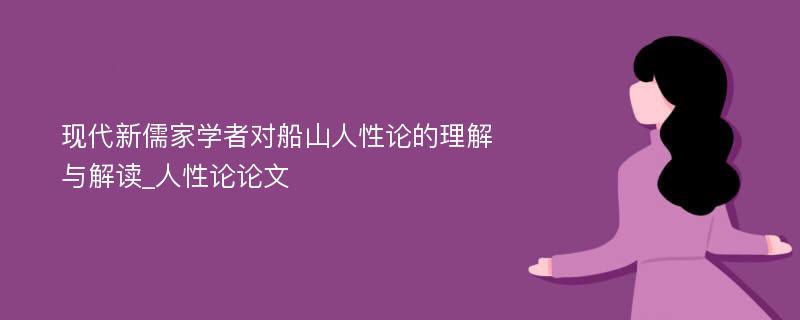
现代新儒家学者对船山人性论的理解与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山人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性论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对人性是善是恶,恶的来源为何,心、性、情、才之关系等等问题的回答,是个体成德与社会教化学说的基础。早在战国时期,人性问题即已成为思想论争的焦点之一。儒家历来重视对人性问题的思考。自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①,孟子在与告子的论辩中提出人性善,荀子则认为“人性恶,其善者伪也”。此后,儒家人性论的内容日渐丰富,除性善论、性恶论,还有性无善无不善、性有善有恶、性三品说等等。宋儒自张载提出人性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以气质之性为恶的来源,朱熹亦沿此二分法而论人性,以性理为形而上;情气为形而下。船山打破宋儒之说,一切从气上说,否定气质之性是人性恶的来源,反对将性理情气分而为二,重视人性在生活世界的日生日成。 现代新儒家群体,普遍重视船山思想。熊十力以“尊生”、“崇实”、“主动”、“率性以一情欲”四大观念,高度肯定船山哲学。对船山人性论的卓绝之处,现代新儒家也有很多精彩的诠释。唐君毅和曾昭旭,是新儒家学者中重视船山整体思想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唐君毅称自己的文化哲学,是直承船山之气论而来;曾昭旭则被林安梧称为以船山思想作为自家思考方式的学者。本文即以唐、曾二人为重点,来探讨现代新儒家对船山人性论的诠释。 一、授、受与理、气 现代新儒家学者,多抓住“气”、“理”、“授”、“受”四个核心词,来阐释船山的性与命,并以此确定船山的人性内涵。 什么是人之性,它与命又有什么关系,船山说: “天之所用为化者,气也;其化成乎道者,理也。天以其理授气于人,谓之命。人以其气受理于天,谓之性”。② “自天之与人者言之,则曰命;自人之受于天者言之,则曰性。命者,命之为性;性者,以所命为性,本一致之词也。”③ 唐君毅认为,船山的性与命,其实是一面之两体。一面是指天与人的关系,这个关系从两个不同的端点出发,则有了性与命。只从“授”与“受”这两个动词的不同即可看出,前者是主动授与,后者为被动接受,当然,人接受后又可以主动创造。就天而言,它通过气把理授与人,这就是命;就人而说,人从天处以气接受理,这就是性。 曾昭旭对船山“性”的含义的理解,则从“气”与“理”的角度来切入。曾昭旭认为,“性”在船山的义理中,涵义很复杂,它与“理”、“气”密不可分。他引用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卷五中的“性只是理,合理与气有性之名……性者,有是气以凝是理者也”④,并据此认为,性在本质上虽为理,但就存在而言,则兼指人的理与气。这里所说的“理”,多指生化根源之至理。既然是生化根源之至理,当然是具有无限的本质的。性是天地的理气在人生命里的凝聚。它是天理、天心内在于人而为人生行为的依据;同时,它又不仅仅是一超越的天理天心,“性不止是人道德行为之依据,亦是人道德行为之对象,抑且是人道德行为之成绩也”。曾兆旭又说:“性是化者,亦同时是待化者;是先在的,亦同时是后成的。”⑤因此,性同时具备“无限性”和“有限性”而不可分。曾昭旭对性的“有限性”的说法,与张君劢所说的“所谓‘人性’只是形而下物质世界合理的产物”⑥所指大致相当,都强调性在社会生活世界中的“待化”与“后成”。 无论是“授”、“受”,还是“气”、“理”,它们其实是褡裢着一块讲的。讲授、受,必说理、气;讲理、气,必说授、受。授,乃授理,理在气中;受,乃受理于气。唐、曾二人从这四个词来诠释,可说是切合船山人性之内涵。船山一方面既属宋明儒学的系统,因为他承接的仍然是宋明儒学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弥补了宋明儒学的不足。而船山之所以能自树新义,关键在于他依循的是张横渠即气说心性的路数。船山言性命,言天授命于人而成性都是本着气言。“而后人乃分宇宙之气,以受理于天。有天道而后有命、有性。人受理,而智能知此理,以启宇宙之化,则为人道”。⑦天之理和道都从气上说,理是气之理,有阴阳两气则必有二气之理;道则在气之化上说。天道之气化,化成人,人有所受命,以成人性人道。正如唐君毅所说,“当明清之际,能上承宋明儒学之问题,反对王学末流,亦不以朱子之论为己足,而上承张横渠之即气言心性之思路,又对心性之广大精微有所见,而能自树新义以补宋明儒之所不足者,则王船山是也”。⑧ 既然人性是在授受之际不断接受和创造的过程,或者说人性同具有“有限性”和“无限性”,那么就不难理解船山之性日生日成的主张了。船山说:“天命之谓性,命日受则性日生矣。目日生视,耳日生听,心日生思,形受以为器,气受以为充,理受以为德。取之多、用之宏而壮;取之纯、用之粹而善;取之驳、用之杂而恶;不知其所自生而生。是以君子自强不息,日乾夕惕,而择之、守之,以养性也。于是有生以后,日生之性益善而无有恶焉。”⑨“形日以养,气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故天日命于人,而人日受命于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⑩人性并非在生命之初即已定型,而是随着生命成长,不断地择善而固执之,自觉修身养性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人不断接受天的赐予的过程。船山人性论对传统人性论的超越即体现在这里。人分有此“气”得此“理”,性是理,理又是气之理。人受于天之理为善,气亦善。于此可理解船山对宋儒将恶之来源归于气质之性的批判。 二、不善源自授受之际 船山合理气而言性,理又是气之理,人性是在后天的习得中不断长养的过程。故而船山对宋儒将人性作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二分法是不赞同的,也否定气质之性是人性之恶的来源。如何理解船山人性中的不善?性之不善的来源是什么?现代新儒家学者,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他们善于将船山“人性之善与不善”的问题跟程朱作对比研究。 程朱认为,人性之不善源于气质之偏。在船山而言,人之不善,原因不在“气质”或“气质之性”,而是流乎情,交乎才者之不正。此与程朱不同。船山以为,“舍气适足以孤性”,固而重视表现于生命之气的情和才。 唐君毅、曾昭旭都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曾昭旭侧重于对船山的气质之性非不善之源进行解读,而唐君毅则从正面诠释船山性之不善的来源问题。针对程朱所说的气质之性,曾昭旭提出,在船山的理解中,“气质之性”并非不善之源,而主要是起到确立人的个体性的作用。他说:“船山之解气质之性,其实义遂在确立人之个体性”(11)。为什么是为确立人的个体性?曾昭旭通过引入“量”这个概念,阐述了性与气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质是气的分化而成,从气凝为质这一点上说,与天的理气相比,有质和量的大小区别。由于量的有限性,人之质因此有善与不善的区别。凝理气于己身的人,其质虽然有个别的差异,但是人的形质是必定要比万物尊贵的。这个“尊贵”即表现在人的形质能使人自觉其所函化之理,并自化其质之不善与偏。这是作为天地万物中最有灵气的人所独有的。在曾昭旭看来,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船山的人性是一个不断地御其气而化其质的活动过程。 那么船山人性中的不善来源为何呢?唐君毅认为,程朱以理言天,以善言理,理就是善,因此天道本身即涵善,而本天道所生的万物之性都是善的,由此得出“不善在于气质之偏”;船山则不同,船山之善“必乃由天之气化流行之依道依理,而有所生有所成,而所成者,复足以继天道,乃有所谓善。天授此理于人物,而人物更受此理以成人物之性,即是天道之继。此继即是善。”(12)由此,船山不像程朱那样,以理言天,就理而言善。船山是即气言天,理依于气,但善不从理气上说,因此天道本身不足以言善,善存在于天命流行于人物以成人成物之际,存在于“授”与“受”的过程之中。既然“善”存在于天与人物“授”与“受”的过程之中,那么不善也必源于这个“授受”之际。不善的产生,具体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人物既生以后不能凝其所自生之善以成其善,其二,虽“成其善”却不能养其善、存其善,尽其善。具体而言,后者是更为主要的。如何能养善、存善、尽善,关键是要调适好情、才、欲与心、性、理的关系。船山对心、性、理、情、才、欲等的关系十分重视,而且谈人性自然也离不开心、理、情、才、欲。唐君毅说:“船山之言心,取横渠心统性情之说,以气载天理,而为心;气所具理,为性;气具理而知之,为思;显此理于外,为情;思此理,行此理,以显此理之能,为才。于此理具之,而能思之、显之、行之者,亦即所谓载理之心也。”(13)由性而有情,情感物,而有喜怒哀乐,为去怒与哀,存喜与乐,而生欲。心之所思、显、行都必循天之理,因而性为心体,心为性用,但体用不可分,因而心性不二。唐君毅认为,船山将人性之不善归溯于气禀与外物相感应之不当。当才不能尽,情不能显理,欲不合理,便有不善。也就是说,气禀、外物、情欲本身不能说不善,不善“唯在外物与气禀与情欲互相感应一往一来之际,所构成之关系之不当之中”。(14)这是船山独特的见解,也再一次印证了船山对不善之性的来源的观点。 船山对人性问题的见解独到,曾昭旭甚至认为,船山本“气”言性,其人性论圆满解决了善恶的问题。道德实践是发于人心之自主,既然为自主,就意味着可以尽心以尽性,也可以不尽心不显性。历来说善恶者大都不离以下两大路数,一为孟子的“即心说性”,可归结为宋明儒之“义理之性”,一为告子的即“自然气质生命说性”,也可相应地归结为宋明儒之“气质之性”。为什么说船山圆满地解决了善恶的问题呢?曾昭旭认为,“形色”在船山而言都是“善”,不能单独说某一事物是不善的。如前所述,“不善”来于阴阳变合之间,几之不相应。而二者之所以不相应,是因为情离性缘物而动,心不尽其才而使人不能主动应几。船山强调,“情”只有奉“性”而动,即有其主,而动皆合理;若离性则为一虚无危殆之几,既然可善可不善,就很可能会滑向不善的一端。所以“心”惟有“思”,一切“情才”与所及之外物乃能为善,若不思,则会失其“几”而致“情才”之不善。所谓“大抵不善之所自来,于情始有而性则无。”(15)性一于善,而情“可以为善,则亦可以为不善也。”(16)因此,一切不善之源,由物之来几与人之往几之不相应,最终归于心之不思诚,心本身不思之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因此,人要尊道、尊善、尊性。人能继天凝善而禽兽不能,圣贤君子能存养其善而庸人与小人不能,这也是船山为什么严守君子小人之辨,华夏夷狄之防的依据。 三、继善成性以立人道 人道是继天道而来,在万物之中,是只有人才有的。它需要人自身不断地“修为”,才能尽人道,合天道。立人道的意义当然很重大,唐君毅说:“是则人道之所以能辅天道,仍本诸天道之大。而天之生人,使之可立人道以自辅,亦即所以完成天道。”(17)唐君毅对天道与人道之关系可说是对船山之说的承继。船山有言:“同一道也,未继以前为天道,既成以后为人道。天道无择,而人道有辨。圣人尽人道,而不如异端之妄同于天。”(18)谈到君子之圣学,又说:“要其不舍修为者,则一而已矣。天道自天也,人道自人也。人有其道,圣者尽之,则践形尽性而至于命矣。圣贤之教,下以别人于物,而上不欲人之等于天。天则自然矣,物则自然矣。蜂蚁之义,相鼠之礼,不假修为矣,任天故也。过持自然之说,欲以合天,恐名天而实物也,危矣哉!”(19)天道自然,而人则当继天道之大,努力尽心、存性,心尽则性成而人道也就此而立。同时,‘与天地参’的辅天目标也借此同时实现。这也是唐君毅所说的“人道辅天道”、“立人道以自辅”之“辅天”与“自辅”的内涵。 现代新儒家学者,对船山人道论的阐述主要围绕道心与人心、心之思、持志等等。曾昭旭从人心的“虚”、“危”与道心的“实”、“微”的相对意义诠释船山道心和人心的关系。人心是什么?人心显发于动静之间。一动一静之几,无自性又无定位,因此才有人心惟危的说法。“故人心者,根本是一物几,无自性而唯待人之实体,宅之以起用者。虽人心若不动,仁义亦无以成能而孤存,然人心之本身,则唯是一虚无之动机,而不足为人之定体者也。”(20)与侧重于一动一静之几的人心相对,道心则是与天道相“继”者。“道心”是“实”,是生此动静之几的气,能定道德方向,是动静之主。因此,真正能成为人的定体的,是道心。人心合于道心,动静之几,则定而不危。但也正由于道心有自主性,道德实践如果不能永保精一,永远自强不息,人心即会偏离道心。 如何以道心统人心,这就落到具体的实践工夫。曾昭旭和唐君毅对船山“思”之特点、“思”之发用以及其与阳明的关系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曾昭旭认为,贯通于一切道德实践的根本动力是“思”之“用”,“思”是“继善、成性、存存三者一条贯通稍底大用”。思是道心的发用,由于“道心”神用之发本身就是一切的保证而没有他物为它作保证,因此它是绝对自主的,而由道心的绝对自主性,可知“道心”的起用,人的一切修养工夫道德实践都只是此心之发用的种种不同面貌,都是自发的。曾昭旭特别强调船山“思”的“自主性”、“无待性”。他说:“其发是自发,其惰是自惰,其欺是自欺,其悔是自悔,其改过迁善亦只是自改过迁善。而总之是心之自主,故易唯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状乾德也。此实为道德实践中至切要之义。”(21)“自发”、“自惰”、“自欺”、“自悔”都是思的自主性的表现,此是人道即道德实践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含义。思的“无待性”是由心之发用的无条件性决定的。而“无待性”,是指贯穿于物中,尽物之性但又不倚于外物的特点,强调心之所显,并不是如耳目有限之定分,而是天德的呈现。由此可知,思又蕴涵着“道德性”。 在这一方面,曾昭旭和唐君毅都注重船山与阳明之间的对比。他们认为,船山在重视思之用,以思贯于一切道德实践的方面,与阳明颇为相近。一般而言,人们只看到船山严斥阳明之处,而未觉察船山与阳明其实有许多暗通之处。当然,船山与阳明还是有明显的差别。曾昭旭指出,船山不同于阳明的地方在于,船山虽然重立本,但不象阳明那样单显心体,而是总说浑然一气之体,而且更重以本贯末。唐君毅则认为,船山没有阳明的即心即理,即本体即工夫论,而且船山认“理”为“所知”,“心”为“能知”,理不能自显,显理之工夫在心之思。 思,是道德实践的极重要工夫,它必定表现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而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亦需在思上用工夫。正心与诚意交修,以使性情通贯;格物与致知相济,以使心物通贯。曾昭旭将船山与程朱、阳明作了详细对比。程朱一派的道德实践工夫,注重即物穷理,以格物致知为正心诚意之本,分知行为二,知先行后,期望通过日积月累的格物,以达到豁然贯通心之全体大用,因此道德实践的标准难免会落于外;阳明则注重根本工夫,以“致良知”便是正心诚意,不分知行,因此阳明的道德实践标准在内。曾昭旭强调,船山补朱王二者的欠缺(一个重末梢工夫,一个重根本工夫),他一方面以思诚为本,以贞定末梢工夫,此同于阳明而补朱子之缺;另一方面,他更重以末梢所得,返以贞定其本,因此,其心之存养,不象阳明只是一虚空的灵明,同时也比朱子的即物穷理更为笃实,从而更有实存实养。 持志在船山的道德践行中更为重要,它能使心之思始终定向于道。唐君毅特别重视船山以持志为正心的工夫。他说:“明善,始乎好学;成善,始乎力行;求无不善,始乎知耻。思诚诚之以无妄之工夫,始于好学力行知耻,而终则归于知仁勇,以尽仁义理智之道。始必终于终,终则始于始。始而即定向于成终之心,则所谓志于道之志也。”(22)船山之“志”之所以能起到主宰和规定心思自始至终向于道的关键,在于能发挥“知耻近乎勇”。志是内在的,并能主宰和规定心思之终,使之定向于道。船山言心重志,因此在人道修为上很重持志。持志必然需要存养的功夫。“存养”之“养”是指养气。理气合一,心气不离,养气才更能知理,行理,更能持其志。在唐君毅看来,船山发挥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将养气与持志并言,能持志则能养气。船山有言:“义惟在吾心之内,气亦在吾身之内,故义与气互相为配。气配义,义即生气”。(23)养气并不依靠静坐,只需要集义,配义与气,气则会盛大流行,至大至刚。 四、诠释特点及意义 唐君毅和曾昭旭对船山人性论的诠释,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看到了船山人性论超越于宋儒的光辉之处,并找到了船山之所以有此人性学说的原因。船山之所以有此性、心、情、才相统一,不断流动,日生日长的人性论,是因船山一切之论皆由气上立说。唐君毅说:“由情才显性,而见气之载理。气之载理为心,理为性,故情才皆原于性,皆统于心,皆出于气也。”(24)从熊十力到唐君毅再到牟宗三,他们在心性论上实是以阳明、朱子为主旨,但是依然肯定船山气论之长在人性论上的突出表现。与此同时,又不满于船山过于重气,主乾坤并建之说。在这一点上,唐、曾二位正好是现代新儒家学者里两种观点的代表。唐君毅代表狭义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家(即熊门弟子),而曾昭旭则代表肯定船山整体思想架构的广义上的更为年轻的现代新儒家学者。 其二,唐、曾二人对船山人性论的诠释,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人文化成之世界,这也是他们以继善成性而论人道之立的内在思路。由此他们也特别发挥船山思想在历史评价、社会生活实践层面的卓越表现。正如唐君毅所说,“船山之学,得力于引申横渠之思想,以论天人性命,而其归宗则在存中华民族之历史文化之统绪。”(25) 其三,在方法论上,善于运用比较法。传统中与宋儒特别是朱子、阳明作比较,在固有传统之外,亦有中西比较,如牟宗三将船山与黑格尔作对比,以凸显船山历史哲学之精湛。船山思想在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中也更显其广大与精微。同时,也体现出他们对船山的深刻理解。如,唐君毅在评析“圣贤之不朽之义”时指出,“程朱言人物之不朽,自理上言;阳明龙溪则自心上言;而船山则自气上言。”(26)即是说,虽然同样是承认宇宙的化育流行不息,但三者的出发点是不同的。朱子是依于“理”,由理之生生不息而宇宙之化育流行不息;阳明则依于“心”或“良知”,他们认为心和良知是天地万物之灵明,此“心”和“良知”是生生不息的。船山则是依于“气”,此气乃天地万物所形成,是生生不息的。由于船山所论依于气,所以其论历史人物,视野广阔,重视心、性、情、才的统一,重视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的统一,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宋儒的道德评价。这一点唐君毅与牟宗三观点一致,牟宗三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以为船山论史乃“综合的尽气精神”的体现。船山是比黑格尔更卓越的历史哲学家。 不过,他们对船山人性论的讨论也有一定的不足。船山不同于一般理学家“贵德而贱才”,“重道义而讳功利”,他以理气并尊,故心身俱贵,理欲同行,德才并重,而重视建功立业、经国济民。这都要回到船山的情、才与性的关系上来。船山反对主静说,反对无情无欲说,情欲虽然可能引起“不善”,但无情无欲也不能显性。唐君毅、曾昭旭虽然也论及要调适好情、才、欲与心、性、理的关系,但是没有深入分析船山之情、才特别是情在人性论中的作用。比如,朱子和船山都批评李翱的灭情说,但是二者又很不同。朱子以四端、七情(喜、怒、哀、惧、恶、爱、欲)皆情,而船山认为四端非情,四端是性,情是七情。这是理解船山为什么严分道心、人心,以性之日生日成对治“宠情”的基础。王立新教授说,朱子虽批评李翱的灭情说,实则与程颐一样,虽不明言灭情复性,然都坚持抑情扬性的主张(27)。朱子和船山之有这样的差异,源于二人论述的前提迥异,朱子的前提是不要把性、理混同于情、气,或者降低于情、气;在此前提下,来重视心性情。性为体,为形而上;情为用,为形而下。而船山一切从气上说,反对将性理情气分而为二。 船山人性论乃至船山整个的思想对现代新儒学有重要意义。面对现代民主与科学的挑战,现代新儒学一直在寻求“返本开新”之路。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于1958年元旦发表的文化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正德与利用厚生之间,少了一个理论科学知识之扩充,以为其媒介;则正德之事,亦不能通过广大的利用厚生之事,或只退却为个人之内在的道德修养。由此退却虽能使人更体悟到此内的道德主体之尊严,此心此性之通天德天理——此即宋明理学之成就——然而亦同时闭塞了此道德主体之向外通的门路,而趋于此主体自身之寂寞与干枯。由是而在明末之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等,遂同感到此道德主体只是向内收缩之毛病,而认识到此主体有向外通之必要。”(28)如何打通儒家道德主体向外通之路,是现代新儒学走出困境,谋求发展的关键。船山人性论上通天道天理,道德主体之尊严得以挺立,下通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不再是局限于向内收缩,而是向外面对整个社会生活世界。船山思想是儒学传统中不可多得的资源,船山主乾坤并建之说,对“气”的注重和提升,贯通到历史文化,表现为对个体独立地位的认可,对社会实践、历史存在和生活世界的关注。船山思想之长正是在正德与利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也是现代新儒家学者,重视船山思想的原因所在。 现代新儒家学者,从熊十力对船山大易原始形上思想的注重,到唐君毅、牟宗三对其历史文化和价值世界的重视,再到林安梧强调回归实存道德主体和生活世界的人性史哲学,并提出后新儒学的发展要走“回到船山”之路,船山思想之于现代新儒学的价值和意义,在他们寻求儒学的现代发展过程之中,得到了逐渐的明晰和凸显。 注释: ①《论语·阳货》。朱熹:《四书集注》,陈戍国标点,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99页。 ②(19)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1139、1144页。 ③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八册,《四书训义》卷三十八,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932页。 ④⑤(20)(21)曾昭旭:《王船山哲学》,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513-514、510、425、435页。 ⑥张君劢:《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张君劢卷》。刘梦溪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61页。 ⑦(17)(22)(24)(25)(26)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540、582-583、596、567、621、617页。 ⑧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485页。 ⑨⑩王夫之:《尚书引义·太甲二》。《船山全书》第二册,第301、300页。 (11)曾昭旭:《王船山哲学》,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517页。 (12)(13)(14)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541、562、575页。 (15)(16)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读四书大全说》,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965、964。 (18)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周易内传》卷五,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529页。 (23)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读四书大全说》卷八,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931页。 (27)见王立新:《从胡文定到王船山理学在湖南地区的奠立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85页。 (28)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时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转引自《现代新儒学研究》刘雪飞主编:《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55页。标签:人性论论文; 人性论文; 儒家论文; 唐君毅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读四书大全说论文; 读书论文; 船山全书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