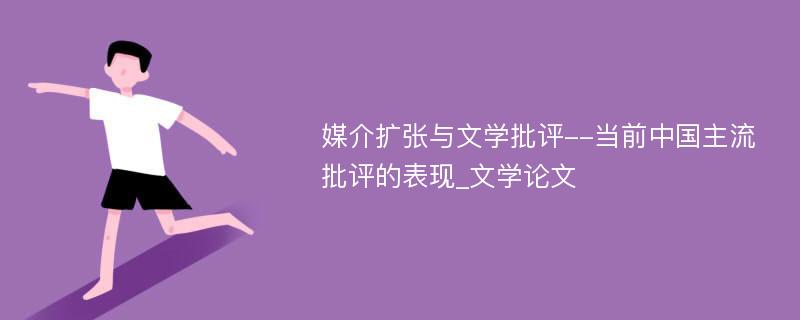
媒介扩张与文学批评——当前中国主流批评症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症候论文,媒介论文,中国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今天,我们身处一个电子媒介构造的生活世界。电影实现了柏拉图关于艺术是自然之镜的古老隐喻——你持一面镜子,就可随心所欲地复制世界。然而,比柏拉图预见更多的是,电影不只是给予我们一个非文字的静态的图像世界,而是让世界的图像自动地在我们的眼前流动展现。电视则比电影更进一步,通过荧光屏,电视超时空地将全球“现实”同步地呈现在我们的身边,正如麦克卢汉所预言的,电视将我们变成了新的“穴居人”,“我们是电视屏幕……我们身披全人类,人类是我们的肌肤”①。继电视之踵而至的网络(国际互联网),正以一种“全球大脑”的模式重组世界信息活动的体系,它不仅构成了“传播——接受”互动的新传播模式,而且通过数字化将信息世界变成了永恒流动的世界,一个被西方信息学家称为“无作者的自然界”②。
电子媒介向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全面扩张,不仅用过剩的影像包围我们,使我们生存在一个形象过剩的、以影像为现实的超级现实中③,而且正在改变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提出了现代传播学的革命性原理“媒介即信息”,并且将电子媒介定义为“人的延伸”。他指出:“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④。这就是说,电子媒介在将世界图像化的同时,也使我们的知觉完成了适应这个图像化世界的转型。据此,我们应当将“媒介即信息”的传播学原理推进到人类学领域,提出一个新的人类学原理:“媒介即知觉”。
“媒介即知觉”,揭示了我们当下生存的现实:我们不仅通过电子媒介去了解世界,而且以电子媒介感知世界,因此,我们的当下生存是以电子媒介为中介的——电子媒介化的。这个人类学事实意味着,我们评估电子媒介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必须从世界景观、信息内容和知觉组织三个层次进行考察。正是通过考察这三个层次的变化,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的人类生活中,电影崇拜、电视迷恋和网络沉迷不仅浸染了全球,而且创造了与这个高科技文明时代反向而行的“再部落”神话。对于一个经受了启蒙教育的19世纪女性,大概难以理解在20世纪的中年知识女性会日复一日、经年持久地把自己的三分之一夜晚(四个小时)交托给那些重复雷同、拖沓乏味的电视剧,难以理解正是观看电视剧变成了她们的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和基本程序。麦克卢汉认为,文字媒介构筑的视觉文化世界,使我们成为一个与对象世界分离的冷静的、理性的观看者;在电子媒介构筑的新的触觉文化世界中,我们重新如原始穴居人一样,沉浸在对这个时空混合的世界图像的非理性的感触中⑤。对于每晚必然要坐在电视机前的当代女性而言,观看电视实际上成为她们感触世界的日常生活方式,对荧屏外的现实她们可能无动于衷,而荧屏中的世界则变成她们最真切的现实经验,甚至可以说是她们生命活动的自然呼吸的一部分。
二
媒介扩张对于文学的直接影响,就是文学被挤出社会生活的中心而边缘化了。在当前,取代文学占据社会生活中心位置的是电视,而电影和网络则与电视毗邻而居。文学的边缘化,不仅意味着我们不再使用文学作为引导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如用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和教育手段),而且意味着我们对世界有了不同的经验方式。本雅明在1936年的《叙事人》一文中就指出,电子媒介向受众传播着非经历的、碎片化的信息,它瓦解了叙事人口口相传的经验(故事)。经验(故事)是在讲述人与接受者的经历中积累起来的具有整体性的、有意义的世界经验;相反,信息是无根基的、碎片化的、无意义的事件,它给予受众的只是瞬息即逝的感受。简言之,电子媒介扩张剥夺了我们对世界(现实)的整体经验能力,将我们置于无意的碎片的信息冲击中⑥。在信息时代,对世界经验的碎片化不仅注定了世界的图像化景观,而且注定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无意义感。电子媒介使用奇观化的书写策略(比如作为基本叙事语言的电视人物特写)遮蔽世界图像的无意义和碎片化,但其实际效果却是不断强化了后者。
文学的边缘化并不意味着文学的终结,而是意味着文学的信息化转型:文学不再成为我们对世界的整体性经验的叙事,它不再传达我们对世界的整体感,不再向我们呈现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图像,相反,文学附着在电子媒介的机体上,以脚注或模拟的方式再现当前世界的破碎而空洞的电子图像。作为文学灵魂的诗意被“堂皇”地粉碎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进入90年代之后,就进行了它的信息化的大转型,纷纷书写和展现类电子媒介的当代中国的奇观化图像。如果我们认同主流批评家对当前时代的中国文学的“一片繁荣”的欢呼,我们就必须同时注释说它是一片无心的风景!那些走红畅销的作品,都散发着电子媒介的诡秘光泽和炫惑气息,惊艳迷人而又枯冷空洞。如贾平凹的《废都》、余秋雨的《霜冷长河》、池莉的《来来往往》、王安忆的《长恨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阿来的《尘埃落定》和莫言的《丰乳肥臀》,附着在这些作品上的奇异“光芒”,已使任何一位书写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史的学者都不能忽略它们的“价值”。然而,当我们认真评析这些作品的时候,剥离掉这些作品的电子信息化的文化属性之后,我们很难寻找到文学的品格和意义。
什么是文学的品格和意义?这个问题可以有另一种提问方式,即:在电子媒介将世界景观全面图像化的时代,文学的叙事是否还是必要的?柏拉图将绘画比喻为一面自然的镜子,这个比喻激励了西方绘画近两千年的写实追求;但是,20世纪出现的电子媒介取代了绘画,真正成为了“自然之镜”,将绘画再现世界的努力化为乌有。这个变化,导致了20世纪绘画的严重危机,如贡布利希在《艺术的故事》结尾中说,对于现代画家,他已经不能“真实地”去描绘一个景物了⑦。文学的信息化转型,实质上是附着于电子媒介转向“自然之镜”。无疑,在直观、逼真和便捷的意义上,文学与电子媒介几乎没有可比性。因此,文学走信息化转型的道路,自然是自我取消——取消文学的品格和意义。我认为,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叙事的必要性正在于文学品格和意义的必要性:文学的叙事是反信息化的叙事,针对信息化向我们呈现破碎而无意义的奇观化的世界图像,文学要重建我们对于世界的整体性经验,重新揭示世界景象的内在意义。
在电子媒介时代,重申文学的品格和意义,实质上是坚持作家作为一个反媒介的叙事人,通过自己的叙事重构人对世界的经验的品格和意义。麦克卢汉将媒介定义为“人的延伸”,这个定义正面肯定了媒介的价值。但是,这个定义也预告了人与世界的现代性冲突,事实上,预告了人借助于媒介扩张将打破他与世界的平衡和统一——凭借媒介强行插入和分割现实,结果是人对世界的整体性经验的瓦解。电子媒介正是世界图像瓦解的“自然之镜”。文学的反媒介意义在于,作家的写作要实现为一个经历,通过这个经历,人对世界的整体性经验被内在地重构,并且展现出这经验对人的意义。因此,文学的叙事,要呈现给读者的,不是当代世界的奇观异景,而是人对世界的内在经验。在电子媒介展现的景观中,我们只能看到电子技术的奇观化制作和人对这些制作的破碎的欲望。与此相应,中国文学90年代以来的流行作品,在满足读者的观影欲望之后,也只能让读者看到作家们模拟电子媒介影像技术的技巧,而看不到人对世界的经验——一位作家的真正有心的世界经验。能否重建人对世界的经验,是当代文学是否具备文学品格和意义的第一标准。非常遗憾的是,上述“当代中国名著”,都没有在这个标准之上。
三
阿多诺认为,艺术作品的内在价值在于它的自我超越(增长),但艺术作品要实现这一价值必须依靠具有哲学意义的艺术批评⑧。在当前电子媒介将一切都快速转化为图像信息的时代,文学批评的必要性变得非常迫切而深刻。概括地讲,新的文学生态向文学批评提出了双重的艰巨任务:第一,对文学的信息化转型进行美学批判,以坚持文学的品格和意义;第二,在对作品的文本细读中发现并阐释作家重建的人对世界的整体性经验和内在意义。然而,当前中国文学批评却并不是以履行其时代使命为努力目标的。正如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主流是信息化转型,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则相应地实现了媒体化转型。批评媒体化转型的特征是:批评丧失了批评家的个性和独立性,转型为作为“媒体的延伸”的集体化批评运动。近年来,在中国文坛实行着一个不成文的“法令”:一部新作品的出版上市,必须通过举行出版商、媒体和主流批评群体三结盟的“神圣仪式”,方可获得市场准入证;这个仪式,名为“作品研讨会”,实为“新书发布会”,其宗旨和手段,与股市上的“新股”上市营销,绝无二致。这就是中国主流批评媒体化的基本形式。因此,过场式地穿梭在这些“作品研讨会”之间,并在媒体的镜头前堂皇而匆忙其事地集体出场,实际上已成为当前中国主流批评家们的常规生存方式,成为令他们兴奋而又倦怠的“岗位责任”。
审视当前文学批评,它呈现出两个矛盾的现象:一是批评的缺失,一是批评的过剩。所谓批评的缺失,就是面对当前难以计数的作品的读者,批评既不能提供可信的阅读选择,也不能提供有价值的阅读启示;所谓批评的过剩,则是主流批评群体聚合在媒体周围,以集体的形式向读者发射被选中的作品的“过剩信息”。经过20世纪中期以后的意识形态禁锢,中国文学批评曾经为了获得批评家的个性自由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然而,出人意料的是,90年代以来,曾经以“自由”、“先锋”姿态著称的批评家,在获得主流身份后,却集体转型为媒体化批评家,步调一致并且异口同声地以“媒体的延伸者”身份发言。媒体化批评家们在媒体的统一体制规定下,集体阅读、集体思考、集体发言。媒体化批评家不再发现,而是沿着媒体预定的文化路线跟进;他们不再思考,而是按照某种既定的主旨发言;他们不再判断,而是对规定的判断添加表现“个人批评风格”的修辞。在2004~2005年之交,中国主流批评群体集体对贾平凹《秦腔》的嘉年华式的“批评”(追捧),是一个中国式媒体化批评的典型案例。在对这部被神化为“终结中国乡土叙事”或“终结中国史诗”的“划时代巨擘”的喧哗而单调的赞美声中,读者根本读不到批评家个人的阅读经验和独立判断。
媒体化批评给予读者的只是关于作品的虚假(过剩)信息的媒体轰炸,它不是让读者进入作品,而是强行将读者卷入关于作品的“信息”的狂躁症的混合滚动,从而达到出版——媒体——批评的利益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媒体化批评不仅伤害读者的利益,而且伤害批评的信誉。2006年春的“韩——白之争”事件,一方面只可作一个当代文化闹剧看,另一方面却又令人痛心地感触到中国文学批评深重的病疾所在。在“韩一白之争”中,一个资深的批评家,何以面对一位青年作家关于其人格、文品的致命责难哑然失声?这是君子长者的宽宏风度,还是被戮及要害痛处的胆怯逃遁?同时,当这位青年作家将矛头指向批评家群体、甚至整个文坛,泼皮詈骂“所有的圈都是花园,所有的坛都是祭坛”,为什么主流批评家们也集体失声?
在这个事件之后,所谓“‘思想界’与‘文学界’之争”就不期而遇。这个事件开始不过是几位社科界的学者“越界”批评了当前中国作家令人忧虑和不满的写作状态,并呼吁作家关注现实、关注底层,然而,却招致了一些当红作家的愤傲回击。在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女作家残雪的回击更是“霸气”十足。残雪不仅轻蔑地将这几位对当前文坛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划入“不懂文学常识”的群氓之列,而且肆意给他们扣上“同权势勾结”的黑帽子。残雪的“霸气”从何而来?用她自己的表白好像是来自她坚定的“文学信念”。然而,她的文学信念是什么呢?按她所言,就是走“个人化的新实验文学”道路,“越个人,便越人类”。正是站在这个“文学信念”的立场上,残雪神经过敏地将“关注现实”与“关注意识形态”划等号,并且梦呓般地宣称:“能不能搞出好作品就看每个作家身上有不有反骨,能不能从深层结构上冲破旧文化对自身的束缚,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个性(我已说过,个人化和个人的独立思考是某些人最害怕的)。”⑨ 一位闻名已久的女作家为何如此敌视关注现实?难道仅仅是“文革”后遗症使然?文学批评当然要尊重作家的个性,但是,“个性”就是拒绝关注社会人生、自我封闭,并且拒绝批评的“豁免权”吗?总观残雪的文学道路,可以概括地说:一开始写出了《黄泥街》的残雪,因为痴迷自我的臆想而坚持对现实的拒绝,将自我三十年如一日永远封闭在她虚构的那座“山上小屋”中,所谓“个人化的新实验文学”不过是这漫长如噩梦的自闭生活中的文学癔症。就此而言,“作家残雪现象”是一个在当前中国文学中具有典型症候意义的重要个案。进一步讲,这场“跨界争论”暴露的诸多重要问题,是批评界应当正视的。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这场“‘思想界’与‘文学界’之争”中,主流批评家却又一次集体人间蒸发式地意外缺席了。相对于2005年集体炒作《秦腔》的主流批评家的嘉年华,2006年的主流批评家却是隐身苦修式地集体噤声了。
审视当前中国批评状态,可以说,主流批评家对《秦腔》的集体炒作、“韩——白之争”和“‘思想界’与‘文学界’之争”,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三大耻辱事件。它们彰显了批评媒体化的严重病症:批评的缺席和批评的过剩。这是媒体化批评不可逃避的结局的一体两面,而文学作品则在这两面之间被扭曲和抽象了——作品不再是批评家用心细读、深切感受和真诚评析的对象,它只是一个可以在媒体化批评的过剩言说中巨大增殖的空洞符号(商品)。我们可以非常善意地说,介入媒体化批评的批评家并非都是自觉自愿为这个符号的增殖服务的,但是,在媒体这个幽灵一样的巨型机器的钳制下,我们很难听到哪位主流批评家真正发出了属于自己的“越轨”的声音。
的确,这个信息时代的特性决定了主流批评必然是媒体化的。因此,我无权也无意要求主流批评家们抵抗媒体化转型。我只能表达这个意见:一个真正能够行使批评的自由和履行批评的使命的批评家,必然是独立于媒体之外的自主的个体;而一个真正独立的批评家,是真正深入作品,并且从作品中发掘深刻而真实的人生经验和意义的批评家。因此,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的声音是天然地具有反媒介的品格和意义的。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意境与现代人生”(项目号:04BZX06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页。
② 保罗·利文:《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熊澄宇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③ J.Baudrillard,Simulacra and Simulation,trans.by S.F.Glase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4,p.6.
④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第46页。
⑤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第412~413页。
⑥ W.Benjamin,Illuminations,edited by H.Arendt,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8,pp.88—89.
⑦ E.H.Gombrich,The Story of Art,London:Prentice- Hall,Inc.,1995,pp.616—617.
⑧ T.W.Adorno,Aesthetic Theory,trans.& ed.by R.Hullot Kentor,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72.
⑨ 残雪:《残雪再回应》,《南方都市报》2006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