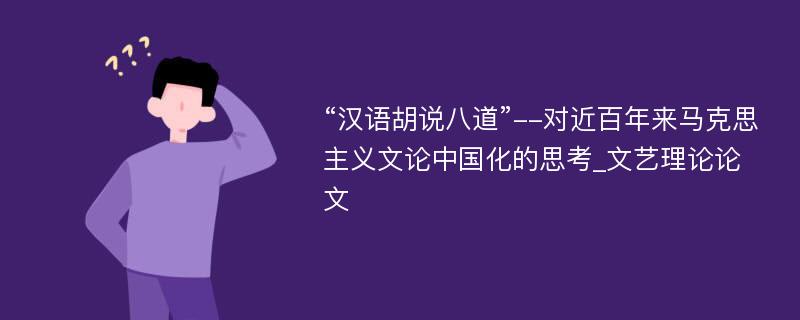
“汉话胡说”——近百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胡说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把李大钊1918年撰写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影响中国现代文论的开篇之作的话(注:此为1965年才发现的一篇佚文,由于某种原因,该文当时未能及时发表,后发表于1979年《人民文学》第5期。也有人认为陈独秀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文学革命论》可以看作是开山之作,因为“虽然看不出哪里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然而确是取同一步调的”。见王振复《中国美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第304-305页。我不同意这一看法。),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以其强烈的实践性品格和鲜明的价值论特色,逐渐成为中国革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在中国文艺理论中的主导地位。但是,近年来不断有人或公开或隐蔽地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它既“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又缺乏“中国原创性”特色,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的异质成分”,直接“导致了中国文论产生失语症”,因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下中国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其中所谓“汉话胡说”现象更成为遭受訾议的中心话题。
一、“汉话胡说”的由来
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存在着话语系统和知识谱系方面“以西释中”、“以西套中”,甚至“以西代中”这种“汉话胡说”的尴尬状况,而在文艺理论领域或许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导地位确立以后,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几乎失去了在学术体制内进行系统言说的可能(注:从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这两本影响很大,可以看作中国文艺理论定型化标志的高校文艺理论教材可以看出,他们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文艺理论框架、概念、范畴和原理,只偶尔引用一下中国文学作例证或更改一下章节设置。前者于1963年和196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1978年根据教育部的要求修订后再版;后者初稿完成于60年代,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在“走俄国人的路”这一启蒙救亡思想导向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开始传播到中国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左翼文学运动的开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曾恳切地指出,“‘五四, 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注: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8页。)。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文化军队”无疑是包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是作为唯一的“合法”理论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设定的体制化框架之内,成为指导中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主导性话语,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实际情形来看,这一话语形态的建构主要是通过三条路径来完成的:
其一,翻译介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首先是通过翻译介绍的途径传播和被接受的。就翻译而言,郑振铎翻译的高尔基《文学与现实的俄罗斯》,瞿秋白翻译的凯因赤夫《共产主义与文化》,鲁迅翻译的《俄苏文艺政策》,冯雪峰翻译的《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等都是较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作。就介绍而言,恽代英的《文艺与革命》、萧楚女的《艺术与生活》、蒋光慈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沈雁冰的《论无产阶级艺术》、周扬的《关于文学大众化》、《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等都是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产生了一定影响的阐释性著述。(注:李衍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324页。)苏俄几乎成为了当时中国获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唯一途径(也有极少数从日文和英文渠道获得的)。由于苏俄理论界是根据自己的社会革命和文化建设需要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因而这种通过“二传手”获得的东西自然会与“真经”有别,而到了我们接受它的时候,“误读”的几率就更大,这是我们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时候必须高度关注的。
其二,总结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现代文论中取得主导地位,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理论权威的总结创新。在这方面,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可以说是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毛泽东的《讲话》系统而深刻地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革命文艺领域的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方法论,系统地阐明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群众、批判与继承、内容与形式、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一系列重要文艺理论问题,“它是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系统、最具有完整体系的重要论著,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民族化和通俗化的典型。”(注: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0-631页。)邓小平的《祝辞》则是一部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纲领性文献。它“总结了建国30年来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对30年来文艺工作作了正确的基本估价”,从根本上推翻了“极左”思想对文艺界“两个估计”的诬陷,提出要正确地评价、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强调指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重要意义,要求“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特别是“把文艺为政治服务改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持和重大发展”(注: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6-799页。)。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总结创新是由政治领袖直接完成的,是从中国政治革命和文化建设角度来论述的,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注: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第579页。)。故其现实针对性很强,这就使它先天地具备了权力话语色彩,意识形态化倾向在所难免,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其三,教材建设。作为大学文学系、艺术系的基础与主干课程(《文学概论》和《马列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通过教科书的编撰与发行,以权威性的特殊言说方式产生了巨大而深入的影响。因为教科书本身具有体系化、学理化的完整理论形式,又是法定的文学理论教材,为各高校普遍采用,于是,它作为一种先在的文艺理论范式在大学课堂上无可争辩地获取了话语建构和播撒的“法定”渠道,这就使之形成了另一条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路径。在这方面,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查良铮译,1953年12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 (根据口译整理,1958年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科尔尊的《文艺学概论》(根据讲稿整理,1959年12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谢皮洛娃的《文艺学概论》(罗念生、叶水夫等译,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等苏联文学理论教材的引入和传播,由于“全国解放以来,我国的大学和中学的文学课堂上,以及广大的爱好文学的读者群中,都感到一个迫切的需要:要掌握新的文学理论,要获得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科学的知识”(注:见季莫菲也夫《文学原理》中译本“序”,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12月版。)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再加上毕达可夫和柯尔尊等人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地为文学系研究生及各地进修教师亲自讲授课程的缘故,所以它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建构和播撒中几乎产生了权威型的影响。此后,尽管中国曾先后出版了霍松林、冉欲达、刘衍文、巴人、蒋孔阳、吴调公等人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科书,但“除了在材料方面增加一些中国文论与中国文学方面的例证,它们和前苏联的几种文艺理论教科书在理论架构、概念范畴、价值标准到语言文体诸方面,都有极为明显的理论渊源关系。并且在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时代氛围中作为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其享有的权威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均远不及上述几种前苏联文艺学教材。”(注:代迅:《前苏联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http://www.Cass.net,en,2000-12-01。)即便是后来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这两本在我国影响很大、体现了我国学者某种独立探索精神的教科书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注:以群将文学鉴赏和文学评论独立出来单独成为一编,为全书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蔡仪将文学的创作过程单独列为一章,都具有某种探索的诉求。)由于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现实发祥地,对各国文学理论建设有一种召唤和示范意义,当时无人敢对这一被“误读”了的体系提出质疑,而它又是通过大学课堂以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知识结构的,因而,作为知识的“前理解结构”它将会长时期地影响中国文艺理论建设。
二、“汉话”“胡说”的张力结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学理论,它是以欧洲人(对我们而言,先是俄国形态的,后来又某种程度回到原始文本)特有的艺术哲学和审美经验为基础的,它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旨趣基本上生成于欧洲人特有的审美实践之中,我们不可能期望让它代替中国人去理解、反思我们的文学境遇,仰仗它具体解决中国现实的文学和艺术哲学问题。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在保持原典精神的基础上,必须从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理论风貌渚方面追求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另起炉灶,要回到中国传统文论话语里去削足适履地挖掘所谓“民族的东西”。就此而言,保持“汉话”和“胡说”之间必要的张力显得非常重要。从这一理路出发,我认为必须处理好以下几组张力结构:
第一,中心话语与边缘话语。
作为欧洲“原版”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边缘姿态建构话语体系的,它的核心品质是“革命”,是以对传统文论的颠覆为己任的,天然就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结构。正如马克思论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文艺观点“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3页。)其他如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及众多有关文艺与美学问题的通信无不表现出浓厚的边缘话语色彩。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却明显存在一个由边缘活语向中心话语转变的过程,如果我们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分界线,则新中国成立前,它无疑是作为边缘话语而存在的,当时它的主要任务是颠覆中国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方文论,批判形形色色的其他现代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喧哗。新中国成立后则由于它所支持的政治实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迅速由边缘话语转化成为中心话语。在这一话语角色转换过程中,它的批判色彩越来越稀薄,建设性的成分却越来越浓厚。由批判到建设这一理论立场的转变,使它原有的张力结构被削弱了,这或许是导致它在建国后非正常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格物”与“格义”。
所谓“格物”指的是那种强调“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著的理论主张;“格义”则指的是那种不追求原汁原味,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精髓来革新中国现代文论的理论主张。如前所述,任何一种外来文艺理论的输入,都取决于本民族审美领域的需要程度,即使输入的是先进的、优越的文艺理论,由于语言和接受心理的差异,往往难以形成真实的“对话”关系,只有那些通过“格义”方式适当改造后变为适合本民族口味和观念的文艺理论,才能被广泛接受和有效传播。综观近百年的理论历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实际上主要是通过“格义”的方式来实现的,而且还是以“二传手”的媒介获得的,而对“原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的把握则相对滞后。这一特殊的文艺理论建构与发展范式,注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因缺乏“格物”与“格义”之间必要的张力结构而在文学本质、形象思维、文学真实、现实主义、悲剧等诸多艺术哲学层面难以有所突破,这也是导致建国后我们的文艺理论话语匮乏、政治意识形态动辄介入的一个学理上的致命弱点。所以,当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等人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概念引入以后,中国文艺理论界仿佛一下子就被激活了。因而,今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必须保持“格物”与“格义”之间适当的张力,一方面要“回到马克思”,深入研究“原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断发掘其中蕴涵的理论资源,掌握第一手的资料;另一方面也不必拘泥于刻板的教条,可以以“格义”的方式把握其精神实质,开拓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就此而言,对当代形形色色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也应采取此种态度。
第三,正题、反题与合题。
假如把中国文论沿着传统道路发展看作是一个正题的话,那么在中国文论发展过程中,西化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导地位的确立无疑是一个反题,因为它通过对异质文论换血式的系统吸收,颠覆了此前中国传统文论的自在、自洽体系,使之成为一堆破碎、零乱,被看作不合时宜的封建文化产物被暂时搁置或轻易否定了。这一正题与反题的切换,实际上是一场“大河改道”式的文论革新过程。因而,当我们从正题的角度进行反思时,“失语”的痛苦在所难免。但是历史逻辑和辩证逻辑告诉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导地位的确立对于中国传统文论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反题,而应该是更高层面的一个合题,因为它通过对传统文论脱胎换骨式的“革命”转化,将中国文论“提高到”一个质的更高的水平。实际上,当我们从“合”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确与我国传统的文论有许多“合”的因素,例如,其中与“文以载道”相结合的“工具理性”精神,与易经“阴阳和合”相结合的艺术辩证法,与“兴观群怨”相结合的“人民性”思想,与“六经注我”相结合的文本批判意识等。作为合题,正如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所写的那样:“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序曲。”当“现在”与“过去”交互作用,形成“将来”时,那些分别属于正题或反题的东西,甚至那些曾经被认为是异端而遭批判、被认为是无足轻重而遭抛弃的合理内核又会被召唤出来发挥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对“汉话胡说”的反思,对“文论失语”的焦虑正是这一合题中应有之义。故而,我们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也必须保持正题与反题之间合适的张力结构,一方面从“反题”入手寻找“异质”理论营养,永葆理论创新活力;另一方面又从“正题”切入获取“同质”资源,闯出一条真正具有本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之路,从而达到更高的“合”的境界。
三、理论困境和话语出路
就当前存在的理论困境而言,我以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1.全球化趋势。“在当今,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思潮一经出现便不胫而走,很快在全世界传播”,“一些批评热点往往成为跨国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一种新的批评理论一出现,很容易在各国找到适宜的土壤,得到不同国度的人们的认可。”(注: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8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年来西方“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思潮对我国产生的巨大影响中深切地感受到。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中去寻找话语资源是不够的,更不用说找到能走出“汉话胡说”体系的资源了。因而,如何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到处弥散,形形色色的文论话语四处飘移的全球化语境下,成功地找到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道路,正成为解决“汉话胡说”面临的第一个理论困境。
2.媒介变革。随着信息传播媒介和电子文化的高速发展,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和传播正在步入一个后工业媒介革命的新时代——视觉张扬、信息便捷的“图文并茂”时代。图像符号的直接性、当下性和电子媒介的快捷性越来越强烈地渗入传统文学艺术领域,既有的文艺媒介和文艺格局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命运。以高科技为背景的网络文学、摄影文学、灾难电影、手机小说等文艺新形式和电子游戏、电子卡通等“次生文艺”形式的纷纷出场,正在对传统的纸质媒介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文学形成强劲的消解力量,弱化人们固有的阅读兴趣。然而,初级电子文艺产品呈现出的思想幼稚、精神低迷以及艺术上的粗糙使它们缺乏起码的人文精神,更不用说高层次的社会内涵了;简单化、类型化、说教化的人物塑造与情节构成又使它们失去了耐人寻味的艺术底蕴,再加上后殖民主义文化预设的种种技术霸权行径(如日本、美国的电子卡通片和游戏都以中国为假想敌),使得恩格斯当年提出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注: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的未来文学理想变得遥不可及。现代高科技带来的媒介变革同失去思想深度的电子文艺产品之间的审美错位,使处于高科技文化弱势处境中的中国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话语常常成为被动的接受场域,没能成为能够相互倾听的“交往对话”的主体。这无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决“汉话胡说”面临的第二个困境。
3.消费主义倾向。在今日中国的文化流行趋势中,消费主义倾向势不可挡,正在对传统文艺理论所言说的认识社会和审美教育的价值取向进行无声消解。中国传统那种“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艺术自信和“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精致从容的艺术心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兴观群怨”、“言志”、“载道”文论理想受到文艺消费者的漠视自有其必然性。虽然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及文艺消费问题,指出“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3-95页。)但是,这一本质主义盛行时代提出的理论预设毕竟太过于理想化,与时下“不求天长地久,只图一时拥有”的消费主义审美现实存在太大距离。故而,消费主义倾向已经现实地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决“汉话胡说”面临的第三个困境。
从当前的理论困境出发,一些学术前辈和新锐学者已经就解决“汉话胡说”问题开列出了形态各异的方案,而在我看来,要刷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思路,切实解决“汉话胡说”问题,方案固然重要,但超越观念形态论争,从现实的文艺问题出发打开“中国人”的理论视野或许更为对症。据此,我认为以下几点值得认真思考:
1.是否具有兼容并包的胸怀。开放意识不应该总是对着“理论文本”,它还应该“挺进”到更加广阔的“现实文本”之中。例如,我们是否允许并鼓励个性化的理论话语存在,哪怕这些话语并不成熟,甚至还有某些地方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略有出入也不求全责备?我们是否允许一些学者迅速介入中国当下文艺现实,发出某些“越界”的声音?我以为这些都应该成为兼容并包应有的内容。
2.是否重视本土关切。如中国的网络文学现状如何?中国当前文学中的“身体写作”现象还会有前景吗?摄影文学是否就体现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中国的生态文学艺术是如何发展的?中国的影视艺术现状如何,它能走向世界吗?中国的卡通与电子游戏等“次生艺术”的文化市场该如何开发和占领?现在的中国存在且需要民间文学吗?中国老百姓现在正在消费的主要艺术是什么,他们最想看到的又是什么样的文学艺术?
3.是否具有发掘话语资源的理论敏感。我们是否可以从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发掘其中的话语资源为我所用?是否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的理论重新进行解读?人文与科学的交融能催生“喷气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吗?美国的灾难电影能给我们哪些理论启迪?是否有手机小说存在的必要?(注:郑永旺、张坤在《俄罗斯文艺》2004年第一期撰文指出,“喷气现实主义”这一在人文和科技基础上形成的新文学,目前正成为俄罗斯文坛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另据有关报道,手机小说《深爱》正在日本流行,成为青年人的最爱。中国的网络作家千夫长也以”短信小说”《城外》获取18万元的版权费。美国以气候灾变为题材的电影大片《后天》,也正因现实气候的异常变化票房价位一路飙升。)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敏感,必将为我们拓宽理论视阈,提供解决“汉话胡说”问题的新路径。
4.是否具有淡化理论体系的意识。我们知道,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由于深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常常会不自觉地追求体系的完整,这对理论本身的完善其实是非常不利的。有鉴于此,是否在编写文学理论教科书时具有淡化体系的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我认为“汉话胡说”作为一种历史形成的话语形态,它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是不会轻易消失的,但也并不意味着将一成不变。现在我们面对的真正问题既不是揪住“中国原创性”的辫子不放,也不是要回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点,更不能以“合法性”为题搞全盘否定,而是如何去选取其中的合理内核,针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加以创造性的综合、发展与重建。如此,则富有时代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将会更具世界眼光,更富现代意识,更有理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