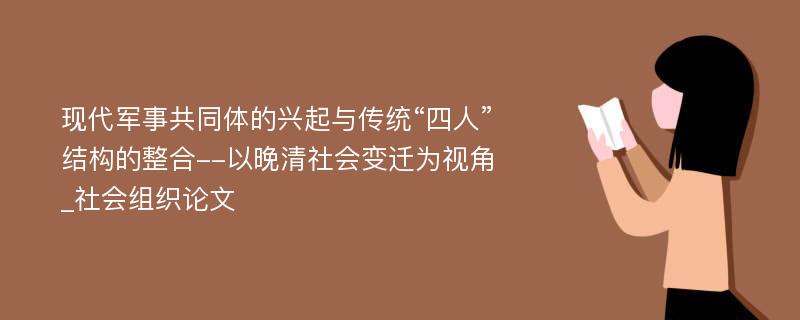
近代军人社群崛起与传统“四民”结构的整合——以晚清社会变迁为视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近代论文,视点论文,军人论文,社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社会自秦汉以下,基本上是士农工商与兵(军人社群)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士为“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兵则连末也够不上,军人社群在正常情况下大都处于传统社会结构的边缘位置。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革,特别是近代军人社群的崛起和传统士人的边缘化,导致“士”与“兵”的角色的错动。近代军人进踞社会主干并扮演社会领导角色,通过兵与士农工商的社会契合,逐步形成了士农工商兵“五位一体”的社会新程序。这种深刻的变化,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笔者就以晚清时期“兵”的角色凸显为视角,探讨其对传统“四民”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影响,以期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军绅权力结构转换有所说明。
一
回溯中国社会历史,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传统的“四民”社会秩序没有“兵”的位置,兵亦不与士农工商相提并论。因此,千百年来,国人视兵在“四民”之外为当然现象。钱穆先生认为中国自秦汉以下便为士农工商兵五位一体的新社会[①a]实际上并不成立。传统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所造成的社会等级与社会职业畛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统社会秩序的排列与组合,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生活的主导因素,这是为多数人所认同的客观事实。
然而,近世社会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变更、转移,使“四民”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儒家伦理本位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危机。在晚清社会转型的大变动中,近代军人、学生、工商业者等新兴社群因社会需求而迅速崛起,传统的社会价值评估体系显然已不适应社会急剧变革的客观形势。以近代新学为取向的社会价值体系,对于士农工商兵的社会地位评估和社会角色规范,较之传统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范式有了重大改变,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把过去受四民社会排斥蔑视的“兵”抬到了重中之重的位置。
当年王闿运在《桂阳兵志叙》中对中国传统社会“兵别于四民之外”所阐发的议论[②a],初步提出了兵与四民进行社会整合的重大课题。其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杨度等人进一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康有为针对中西社会差异而提出“泰西以民为兵,吾则以兵为民”[③a],不仅指出了传统兵制的弊端,对“无兵”的传统社会秩序也是一种间接的批判。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一役,清军屡遭惨败,华夏圣教式微,种族沦亡,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当举国士民无论贵贱,同聚于覆屋漏舟之中时,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兵”愈加显露其社会价值。中国传统的“无兵文化”和无兵的社会组织序列显然已不能适应列国竞争和“军国”时代,情势所迫,近代中国“兵”(军人社群)的凸显及其与四民社会的契合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世纪末、20世纪初推行的近代兵役制度改革,为士农工商与兵的社会整合开辟了途径,其主要特征,是开始了从“以兵为民”向“以民为兵”的转变。在晚清社会的公众议论和官方文献中,“兵”的社会价值评估具有重要地位。近代军人社群及其与“四民”社会的关系,也日益成为引人关注的问题。起初是介绍近代西方“兵学”,继而触及到军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以西方社会的军人角色为蓝本,近世中国的“兵”逐步冲破了历史上与士农工商相互阻隔的格局。最为显著的表现之一,就是当时的社会舆论通常将“兵”与士农工商并列齐称,尽管在“士农工商兵”的排列中,军人居于末位,但兵能从四民之外挤入其间,便是一个寓意深远的社会变化。
事情的发展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国素未与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①b]作为近代西方“新学”的集中体现而得到社会的认同,这是近代中国兵与四民社会实现契合的特点之一,由兵所体现的“中学”与“西学”的特点之一,由兵所体现的“中学”与“西学”的较量,以及学人对西方“新学”的辨识和吸纳,逐渐动摇了维系传统社会秩序的“中学”权威,所谓思想权势的转移由此一发不可收拾。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康、梁鼓吹实行维新变法,国人日渐认识到兵不惟有学,而且还应居于“尤重”的位置。近代兵学在晚清社会的长足发展,构成一大社会变革之源,而“在文明的一般接触中,只要被侵入的一方没有阻止住辐射进来的对手文化中的哪怕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因素在自己的社会体中获得据点,它的唯一的生存出路就是来一个心理革命。”[②b]晚清社会正是循着这样一条途径逐步地调整自己的价值坐标和国民的心理结构,使“兵”在社会文化中获得认同。毫无疑问,近代军人社群较之传统的八股书生更适应近代社会转型的需要。处在新旧社会转型交替之际的“士”,虽不肯自动放弃四民之首的地位,但也不得不承认“兵”应有其恰当位置。例如梁启超就肯定西方社会民分五等(即士、农、工、商、兵)的作法[③b],梁氏虽然是从中国社会的等级观念和职业划分来理解西方社会的组织构成,但将士农工商兵合称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为改变传统的四民社会模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梁启超看来,兵魂既为国魂核心,军人亦当居于国之重心,社会结构无兵,兵魂不为社会所承载,国魂也就难以陶铸。从再造兵魂到兵与士农工商齐称并列,不仅仅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而且也是近代中国从传统宗法社会过渡到国家社会的一种特殊表现。社会组织构成中应有兵的确当地位,是近代军人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由思想权势到社会权势的移易,传统兵民分离格局的解体,以及社会流动方式与导向的改变,从各个方面为士农工商兵的社会整合奠定了基础。在此情况下,兵与四民社会的契合,成为晚清社会的一种共识。梁启超在《南学会叙》中就倡言:一国之内,“有士焉者,有农焉者,有工焉者,有商焉者,有兵焉者。万其目,一其视;万其耳,一其听;万其手、万其足、一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一其事,其位望之差别也万,其执业之差别也万,而其知此事也一,而其志此事也一,而其治此事也一,心相构,力相摩,点相切,线相交,是之谓万其途,一其归,是之谓国,有国于此。”官民之间、士农工商兵之间应当实现高度的组织契合,只有如此方可以言立国。反之,若“士与士不相接,士与农与工与商与兵不相接,”则“不得为有国矣。”[④b]梁氏提出以学会、社团为“中介”,推进士农工商兵的社会整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晚清时期军人参与社团组织的政治性经历以及社会互动的作用影响,大大提高了军人与民间社会的对流契合程度。
军人出身的近代思想启蒙大师严复更干脆将兵、农、工、商作为国家社会(军国社会)的基本组织构成。兵农工商与士农工商同为“四民”结构,但兵与士的置换,却是伤筋动骨的社会秩序变更,他认为,国家有此四者备具,“而其群相生相养之事乃极盛,而大和强立,蕃衍而不可以克灭。”[⑤b]兵与近代国家社会其他社群不可分离,有兵与无兵的社会组织构成,不啻为“古今群制之世殊也”。
近代军人社群的崛起及其与四民社会的契合,同当时兴盛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民主义等社会思潮关系密切。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凝聚力,与推行社会军事化相得益彰,近代军人社群的集团合作精神和集团优势,正好可以弥补传统四民社会“一盘散沙”的不足。当士失其位、四民社会秩序解体之后,人们自然希望进踞社会主干的近代军人在改变传统社会组织软弱涣散的颓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士农工商兵的整合又有着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
二
近代以来,有关中国社会为“一盘散沙”的认识,客观上为军人社群与四民社会的整合提供了理论依据。自从严复提出“进行改造国民心理中的文化劣根性即‘土壤改良’”之后[⑥b],不少有识之士纷纷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近世社会乃为“群与群争”的竞争时代,非力德相备,不可以言自立自强。梁启超提出以兵魂为国魂重建的基石,便有以“兵魂”改造中国社会散漫、不合群、无团体竞争意识之意,“中国人不知群之物为何物,群之义为何义,故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群之我。中国群力之薄弱,因早已暴露著于天下矣。”[①c]无合群观念和缺少“群”之组织的社会,岂能不成散沙一盘?!
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基础和农业宗法社会结构,形式上和谐稳定、秩序井然,实质上不过是众多“马铃薯”的简单堆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缺乏“集团生活”,“士农工商,各事其事,不相闻问,成一秦越之形,则如满盘沙土,涣散离析,国何恃以永立哉?”[②c]孙中山也认为,近代中国之积弱与“一盘散沙”的国民相联系,“中国四万万人实等于一盘散沙”[③c],欲聚此四万万散沙而成为一机体结合之国,非有一强有力的组织体置于其间不可(这与他十分重视会党和军队组织的作用不无关系)。
传统四民社会组织散沙一盘的状况,与担当领导角色的士人阶层有相当直接的联系,如果说中国人散漫,那么第一位的原因就是由于士人的散漫。士人“止于微有联络”而“谈不上有团体”[④c],身为四民之首的士人尚且如此,其他农、工、商民就更不待言。一盘散沙式的社会组织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暴露出组织功能软弱涣散的严重弊端,国力竞争与民族存亡的严峻形势,要求社会组织必须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国民职业虽分而感情相合,固结如胶漆,以成一有机团体。”[⑤c]高度集中,纪律严明,步调一致的近代军人社群在增进社会凝聚程度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通过军事组织和军人群体与民间社会的结合,克服一盘散沙式的无组织弊端,在社会转型的特定条件下更有其客观必然性。以社会军事化来改造传统社会,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社会改良思路。晚清时期士农工商兵的社会整合,颇有些类似“散沙”(士农工商)与“水泥”(兵)的融会调适。通过士农工商兵的对流沟通,实现社会组织构成的优势互补,将一盘散沙改造为“混凝土”式的板块整体结构。兵与四民社会契合并列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近代军人社群为转型社会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秩序中坚和秩序保障。
社会军事化与军队“大学校”似的陶冶教育功能,为新的社会秩序整合提供了有效途径。以近代军人为社会楷模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重要现象,特别是以“尚武”立国的德国和日本迅速崛起,为推行社会军事化树立了样板。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和社会转型震荡日趋强烈的背景下,军队不仅是御侮的工具,而且也是社会稳定的依托和民族振兴的代表。甲午战争以后,“军队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⑥c]国民通过军队这所大学校的培养而增进知识,增强体魄,养成刚毅尚武爱国的军人品格,对于重铸国民新灵魂有着积极的意义。
客观地说,近代军营文化和新式军队严格的军规、军纪、军训,对于改变离析散漫、孱弱保守的传统社会文化惰性不无裨益。辛亥老人胡祖舜在回忆他的军旅生涯时就这样认为:“平情而论,余之学识、品性、精神、体力及公私生活方面,在过去数十年中,虽于国家社会,乃至家庭,无所贡献,而个人之得有今日,使为窭人子、孤寡后者,不为乡愿,不玷祖先,实植基于此二十余月之军中生活,有以坚忍磨练使然也。”[⑦c]许多在新军中服过役的军人对新军“有如新学堂”[⑧c]均有同感。经过军营新学堂的培养,将士农工商锻造为合格的军人,而合格的军人亦必是“军国民”的表率。从严复的“三民”(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学说到梁启超的“新民”理论,对国民性改造与人的近代化提出了极富见地的认识,他们主张的举国皆兵和社会组织军事化,进一步强化了新式军营的社会教育功能,因此,近代军队这所特殊学堂在人的近代化方面扮演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晚清时期,新式军营成了“德、智、力”三者兼备的象征,有不少社会精英出自军营,不说军政显要、达官贵人,只要看看严复与周树人兄弟的成长经历及其个性特征,便不难体察到近代军队在国民改造中的社会效用。问题的答案表明,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先进的军事组织无论对于社会近代化还是对于人的近代化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当以军事近代化为先导的转型社会对军队的依赖日渐加重之际,近代军人社群与社会的整合也就在所难免。近代军人走出“国之干城”的传统禁区而与社会进行广泛的对流互动,把新学凝聚的近代军营文化推向社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或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主导价值和国民心理结构。这种具有浓厚军事化色彩的“心理革命”的推进,为传统社会组织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三
社会军事化和近代军人社群的崛起,导致传统的四民社会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即从四民社会向士农工商兵“五位一体”的社会新秩序转变。严格地说,这种“五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构成在晚清时期只能算是一个雏型,但它却为近代社会“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排列组合奠定了基础。与传统的四民社会相比较,新的社会组织序列中多了一个“兵”,社会结构从无兵到有兵的变化,使兵不仅从四民之外契入其间,而且在五位一体的社会新秩序中一度扮演了与士(绅界、学界)相埒的领导角色。
近代军人虽然来自士农工商,但是职业化、社会化的军人社群和军人集团的独立意识,决定了军人群体与士农工商虽有联系亦有区别,把“兵”提升为与士农工商同位并列的社会角色,不但顾及到传统社会组织的基本构成,而且又肯定了近代军人在社会政治参与和社会新秩序中的特殊地位。晚清社会对兵的认同,对政府的社会政策导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政府刻意整军经武,本身就有意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并把近代化的新军视为支撑社会秩序的一支依靠力量。因此,兵与士农工商的契合采取了赞同支持的立场,近代兵役制度改革与八旗、绿营的改流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刘坤一、张之洞在在“江楚会奏”中,就明确地把“士农工商兵”列为旗籍兵民改流之后的社会出路[①d]。清政府对社会舆论“民分五等”的认可,使兵与四民社会的整合由表及里地获得了进展。及至清末,清政府的民政部门已将兵(军界)与士农工商一样,同列为户政统计的一项基本内容,改变了以往兵民两橛的传统做法。兵与士农工商并列齐称,标志着传统社会对“兵”从排斥到吸纳的转化,这无疑是晚清以来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表象。在新的五位一体社会组织构成中,士农工商兵的顺序排列并不完全反映各色人等的地位尊卑,人们在具体使用“五民”概念时,也不一定严格照此顺序进行排列。例如梁启超在指出“民分五等”的同时,曾具体地将不同社群的地位作了如下安徘:“上而官,中而士,下而农工商兵”[②d],这种见解显然并未真正跳出传统观念的窠臼。士处中间社会,这是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之一,士人沟通官民,且是传统社会文化的承载之体,故其为四民之首理所当然。但在近代新学昌炽,“兵学尤重”的时代变革之下,新式军营向社会开启了更加便捷了当的民官相通之路,从军行伍成为新的社会上向流动生长点。近代军人社群打破了传统社会军人角色边缘化的局面,逐渐进踞社会主干,其结果是军人社会角色核心化。特别是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沿续了一千多年的“士仕相通”故道不复存在,士人阶层独掌中间社会的格局,随之坍塌,各种新兴的社会群体纷纷伺机进入社会中心,出现了一个群龙无首,多头并进的社会重组局面。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是之谓“过渡时代”,而过渡时代的中坚力量孰士孰兵?也曾有过各种不同的见解。如1903年李书城在《学生之竞争》一文中,将由士裂变而来的学生群体视为社会中间主干,“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③d]同年发表的《民族主义之教育》又明确地将学生界定为“中等社会”。但在事实上,士衰蜕后的“绅界”已开始走下坡路,学界虽以“中等社会”自居,却又未必能够替代传统士人的领导角色。在新式教育机构尚不成熟和学界自身弱点的影响下,学生与官与民均有隔膜之虞,所谓“中等社会”之说抑或只是反映了一种承袭传统士人角色的主观愿望。
相反,兵与农工商民虽被学生和绅士目为“下等社会”[④d],但以军事在国家社会中的突出地位和近代军人在社会上的楷模示范效应,军界与学、绅两界相比,也许还稍胜一筹。在晚清政府导向和社会舆论中,无不以为军界“居国家最重之地,而亦为国家最优遇者”[⑤d]。军事近代化是近代中国最为显著的社会变化,军界地位亦因军事近代化和社会变革而获得实质性的提高,因此一些西方学者将近代军人阶层划入“特权阶级”之列不无道理[⑥d]。从晚清社会变迁的情况看,兵(军界)在士农工商兵的“五民”结构中,事实上已经处于“中间社会”(或中等社会)的位置。由于“兵”从传统的四民秩序之外步入近代社会秩序的主干中心,原先以士为四民之首的单线性运作机制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士”与“兵”共享社会领导角色的多线性网络运作体系。这种“五民”社会组织体系的输入、转换与输出过程,也由四民社会的士人主导天下,改变为士(绅、学)与兵(军)平分秋色。在士农工商兵一体化的社会组织体中,基本实现了各色人等的自由对流,这与传统的兵民阻隔相比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社会主导价值从传统儒学转向多元开放,但由于清末科举入仕与纳粟捐官的废止,社会一度仅存“出将入相”一途,行伍从军在向上社会流动中的地位更为突出一些。
1905年《东方杂志》第2期在一篇题为《社会思想》的社论中,载按“学子兵士商贾农夫工师”来安排社会秩序,客观地说,这种学、兵、商、农、工的排列,倒是比较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士(绅、学)与兵(军)在五位一体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居于“中等社会”的位置,其社会地位、作用和影响明显地在农、工、商界之上。晚清时期,除绅、学、军界之外,商人(尤其是近代绅商)地位的崛起,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近代商人与军学绅界同为晚清四大活跃社群,不过,软弱的商界由于自身条件局限而缺乏领导社会的能力,在军学绅商的社会互动中,往往扮演“甘附骥尾”的角色。它于工、农阶级,在清末民初仍旧处于社会底层,其社会政治表现也不如军学绅商积极活跃。
从传统的四民结构到近代社会的“五位一体”,表面上看仅仅是增加了“兵”,实则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由于近代军人社群的介入,传统士人阶层的裂变和近代工商业者的兴起,五位一体的社会组织结构展现出多线性、多向度和多元化的复杂运作特点。近代军人、学生、士绅、工商业者都试图按照各自的价值标准建构社会新秩序,尽管近代军、学、绅、商社群的价值观念存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作为近代社会变迁的新兴社群,他们都倾向于接受近代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意识,这种共识成为他们携手合作的基础。军学绅商的社会互动,使社会动员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各社会势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制衡也有所加强,单独由某个社会集团把持局面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五位一体的新格局,则为军人与绅士联合承担社会领导责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所谓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结构从“绅军”模式到“军绅”模式的转换,从这里也许能获得一些启示,当传统的“士绅之国”崩溃之后,取而代之的只能是军事权势为中心的新一轮社会整合。
①a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53页。
②a 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兵政》。
③a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37—238页。
①b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
②b 汤因比:《历史研究》(下),第275页。
③b 梁启超《学校总论》。
④b 梁启超:《南学会叙》。
⑤b 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译者序》。
⑥b 郭国灿:《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约戊戌—五四)》第89页。
①c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
②c 《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
③c 孙中山:《建国方略》。
④c 《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第258页。
⑤c 《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
⑥c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608页。
⑦c 胡祖舜:《六十谈往》。
⑧c 梁钟汉:《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
①d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749页。
②d 梁启超:《变法通义·论女学》。
③d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编译》第10期。
④d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编译》第10期。
⑤d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9540页。
⑥d 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602页。
标签:社会组织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变迁论文; 晚清论文; 梁启超论文; 士农工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