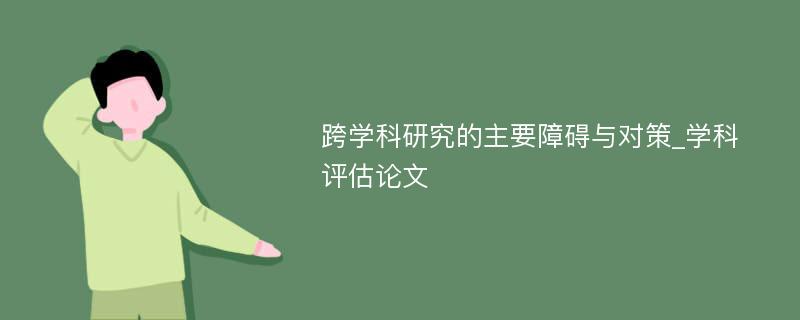
跨学科研究面临的主要障碍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障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数十年来,科学技术知识的激增,人类面临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和严峻,需要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以及工程技术人员聚集起来,共同进行研究和给予应对。迄今,这些跨学科的探索和研究既形成了一些新的热门话题和新兴领域,也产生了一些巨大的成就。可见,“由拥有不同专长的合作者组成的研究团队的生产率和效率是毋庸置疑的”。①
尽管不少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学术界对于跨学科研究在推进科学技术发展,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方面具有的巨大潜力已经达成共识,然而在实际推动跨学科活动的开展,对相关的教育和研究给予资助、管理和评价等方面,各国学术界仍然面对着不少困难和阻力。基于此,近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不少欧美国家的政府都委托科研单位或资助管理机构对本国的跨学科活动开展调查研究,并针对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例如1999年,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即发表了委托研究报告《跨学科研究》(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②专门讨论理事会内部对跨学科研究的支持,特别是与跨学科研究计划的评估相关的问题。荷兰科学技术政策咨询理事会(Dutch Advisory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在2003年提交了《推动多学科研究》(Promoting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的政策报告。③200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等机构发表的《促进跨学科研究》的报告也是基于全国性的调查,为政府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提出了全方位的对策建议。同是在2004年,欧盟研究咨询委员会(European Union Research Advisory Board)也发表了《研究的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 in Research)的政策报告,分析了欧盟在开展跨学科研究方面所存在的障碍,从研究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大学的结构和政策,以及研究资助机构等方面提出了建议。除了欧盟研究咨询委员会的总体建议,欧洲多个国家的科学院或研究理事会也承担了与美国国家科学院类似的任务,组成研究小组,对跨学科研究的内在力量进行阐述,展开调查以确认不利于跨学科活动开展的障碍,并提出消除这类障碍的资源和建议,例如芬兰科学院的《促进跨学科研究——芬兰科学院的案例》(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The Case of the Academy of Finland,2005),丹麦商业研究院(DEA)和丹麦商业教育论坛(FBE)的《跨学科思考——研究和教育中的跨学科性》(Thinking Across Disciplines,Interdisciplinarity in Research and Education,2008)以及英国赫尔大学学者撰写的《英国跨学科研究计划中的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rogrammes in the UK)④的分析报告等。这些报告对于调查中发现的问题给予了全面展示和翔尽描述,而其相关的改进措施和建议对于有意促进跨学科活动开展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综合上述报告和文献,可以看到,跨学科活动所面对的主要障碍和挑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来自组织、制度等方面的结构障碍
结构障碍主要涉及科学研究的组织结构,包括组织内部所形成的压力和激励机制。当今,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在某种组织的背景下进行的,大学、公立和私立研究所,或是工业实验室等,因此,组织的决策和组织规范的结构影响着研究的性质。
传统上,多数大学都是由不同的系和大大小小的学科所组成,这样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内部结构日渐僵化,既不利于部门间的接触,也不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开展。英国研究高等教育的知名学者斯蒂芬·罗兰(Stephen Rowland)⑤在《探索大学》(The Enquiring University)一书中就指出,学科的界限和系之间的界限并不是一回事,跨学科的合作在跨越系的界限时会遇到很多困难,不仅如此,即使是在系的内部开展合作也并非易事,教学和研究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在同事之间造成隔阂,使他们很难顺畅地交流,而有些大学行政机构的官僚作风则可能会加剧这一影响。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制度僵化的情况下,跨学科活动所面对的管理层面的问题要多于知识层面的问题,而且,管理方要想建立新型的跨学科的制度结构阻力重重,因此,那些自下而上的跨学科合作似乎更易于推进和发展。
欧盟的报告还注意到,资助组织的结构是由大学的单一系科的传统结构引申而来,两相对应,其结果是,除非采取特别的举措,否则跨学科的研究计划就会被忽略掉。因此,如若不能在结构上应对跨学科的需求,这类研究体系就会丧失许多组织起创新性研究的机会,在一些重要研究领域中处于落后状态,同时也会流失很多最具创新精神的研究者。
在研究者个人方面,确有不少接受有关调查的学者反映,他们在尝试跨越科系和学院的界限开展合作研究时会感受到较大的制度压力,这些压力有的来自学科内部的考核评估制度,有的来自机构内部的资助惯例,还有的来自不同学科领域间在研究总量方面的竞争。⑥近年来一些工业化国家所出现的研究资助方式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使这种组织结构的影响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例如在芬兰,其研究资助体系正逐渐地从大学内部的资助转向外部的、由公共机构提供的竞争性资助,这一变化使得学科对研究的压力至少在短期内有所降低。⑦此外,一些调查和研究也显示,越是允许信息和人员在学院间的各项研究计划中自由流动的学术环境,越是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繁荣,而且一种允许研究者自由进出的合作关系更有利于他们的跨学科课题取得进展,研究者对他们的专业成就也有更高的满意度。
尽管出现了某些积极的变化,但是对建立新的组织模式的呼声从未停止。针对一些新兴研究领域中跨学科研究的快速发展,欧盟研究咨询委员会就十分关注欧洲的研究体系有没有必要的政策和手段来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委员会认为,学科的结构本身以及它们对新的学科的创造和接受,对于现代科学的进步是至关重要的,跨学科研究的政策和手段并非要挑战强大的学科研究,而是一种补充。而好的跨学科结构不仅是向新的研究领域开放,而且也为传统学科提供了灵活性和扩展的可能性。⑧
目前,有些欧美国家的研究机构已经开始设立跨学科的委员会来管理相关的事务,一些新成立的大学也倾向建立跨学科的系和学院,例如建立材料科学系,而不是物理系或化学系,建立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学院以取代传统的艺术学院等,有的大学组织结构甚至是以研究实验室为基础,而不是围绕系和学院来建立,其中最具历史标志性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
在解决组织和制度的问题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旧有组织结构的改造并非只是加上一个跨学科的标签,而应该以彻底变革的视角来看待跨学科的方法,否则,旧制度结构的保留必然会对跨学科研究形成抑制或造成妨碍。此外,仅仅冠之以跨学科的名号或围绕庞大主题而设立的组织(诸如“全球气候变化”、“环境影响”或是“可持续的资源”)往往发挥的是一个联系中心的作用,即只是与一些寻求跨部门合作的研究者个人保持松散的联系,而不是形成一个致力于解决特定问题的有凝聚力的群体。这样的组织可以缓解制度的影响,但也并非就形成了新的适宜的制度形式。
此外,正如前面提到的,越来越多的外部资助引导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而这些外部资助对研究的组织结构的长期影响可能是未来科研政策研究中所需要注意的一个有趣的问题。从多数情况来看,研究资助和研究计划一般在1~4年之间,这对个人研究者或是某个课题达成一些具体目标或许是足够了,但是对于推动新的领域的形成则远远不够,那么外部的研究资助机构在什么程度上能够推动新的跨学科领域的长期发展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知识专科化所造成的隔阂
知识障碍的概念涉及学者们对于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局限。芬兰科学院的报告对这类局限做了较为细致地分析。报告认为知识障碍首先表现为“知识赤字”(konwledge deficit),即研究项目的成员互相之间对别人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不了解、不熟悉,而这会导致若干困难出现。例如,研究人员对于不熟悉的领域可能抱有错误的概念;他们对于其他领域的学者可以做些什么,能有哪些贡献也会有不切实际的想象。学者们相互之间不熟悉还限制了对于领域之间联系以及合作机会的了解和确认,也就是说,若要明白别人的工作与自身工作是否相关,首先要知道别人从事什么研究以及为什么从事这些研究,而获得相关的知识通常需要时间以及较多的个人投资,这在设计跨学科的项目时是特别需要给予考虑的。
除了直接的知识问题,知识障碍还可能导致对其他的领域和研究者的刻板印象。英国学者托尼·比彻(Tony Becher)有关学科的经典研究⑨就揭示了学科之间的这种刻板概念,并指出这些刻板印象与学科代表的自我认知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同时也不利于学科之间开展顺畅地互动。因此,不管是作为某个学科的代表还是作为普通人,学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熟悉对于成功的跨学科活动都是重要的。
在克服知识障碍上,最重要的对策之一是为研究者提供教育和培训。欧盟研究咨询委员会就认为,大学本科一级的教育应该为学生搭建跨越学科界限的桥梁,各学科相互之间在教学和课程等方面应该更加开放。在研究生一级,美国科学院的调查报告认为,为促进研究生的跨学科思考的能力,大学应该采取更多举措,包括提供与其他科系的研究生共同工作和相互学习的机会,设置多个指导教授,使学生针对研究的问题获得多维的视角,允许他们利用多个学科的仪器设备和技能开展实验等。
除此之外,欧盟研究咨询委员会特别推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做法,认为其“研究生综合教育和研究研习奖学金计划”(NSF Integrative Graduat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raineeship Programme,IGERT Programme)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跨学科教育培训模式。该计划开始于1997年,重点对多学科的博士计划提供支持,旨在形成一个新的教育培训模式,即创新、灵活并对正在出现的跨越学科边界的研究机会做出反应。该计划的优势主要有三点,即为不同的系集合到一起提供资助,而不必为非系内的工作动用自身的资源;为在新的领域培养高质量的博士提供长期的支持;为在新的领域内发展关键的、可自我维系的规模提供充足的资源。⑩
三、学科文化差异的影响
在几乎所有的相关研究中,学科文化都被视作开展跨学科研究的主要障碍之一。特别是从参与跨学科活动的研究者本身出发,首先遇到的障碍或许正是来自于他们自身。
1.语言障碍
跨学科研究具有典型的合作性,聚集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因此参与者首先遇到的挑战就是如何克服交流和文化方面的障碍。多个调查报告都显示,接受调查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抱怨,即在跨学科的研究环境中,他们遇到的一个主要困难来自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所使用的语言,他们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很难理解,有时候相同的事情却被用不同的概念来谈论,或是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相同的概念。
加拿大学者索尔特(Liora Salter)和赫恩(Alison Hearn)曾就这一问题开展过研究。(11)在他们1996年编辑出版的《边界线之外:跨学科研究中的问题》(Outside the Lines:Issues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一书中,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被区分为两类,其一是翻译问题(translation problem),其二是语言问题(language problem)。翻译问题是由学科共同体谈论其论题的方式和从事研究的方式中所存在的差异造成的,这一差异使信息在学科间的交流变得复杂化,例如技术术语的构造、信息获得可信性的方式、信息被提供的次序、被认为合适的参照点,以及学者们对于什么需要讲清楚而什么是理所当然的默契程度。要克服翻译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关于适宜的语言使用的知识通常并不十分明确,只有通过经验来学习,类似一种社会化的过程,只有经历这一过程方可分享到那些心照不宣的知识,因此翻译的问题不单单是不同的术语问题,而是在具体情况下对于所讲所言的意义的理解。
语言问题主要指不同的学科在用词方面的差别。索尔特和赫恩将语言问题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不同学科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限定同一个词汇,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就会出现混乱;第二,有些词汇在有些学科中存在争议的情况,例如民主(democracy)和权力(power),因为它们的作用是在不同的相互竞争的范式之间作为争议点。争议的概念在跨学科工作中既可以发挥推进作用也可以成为障碍,在前一种情况中,它们可以作为桥接概念(bridging concepts)或是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s)(12)发挥作用,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们可能成为冲突的焦点。语言问题的第三个维度是由跨领域的概念借用造成的,这种借用常常导致同一个词具有多重的意义。
正是由于存在诸多的语言问题,因此参与跨学科的工作在使用语言上要较之平时更为明确,同时要注意运用有利于相互理解的方式来进行交流。
2.认识论和方法论障碍
学科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巨大的,语言只是其中之一,在其他一些重要方面,例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等,各个学科也存在巨大差异。
并不是所有的跨学科活动都会导致认识论问题,例如一些多学科的项目可能求助的是学科的专业知识,协调各个学科的努力来解决某一个问题,而并非要对参与学科的知识进行整合。而一旦整合(integration)在一个跨学科项目中发挥根本作用时,知识范畴的结构差异就会制造认识论的障碍。克莱恩认为,在跨学科工作中,可以采用两个主要战略将不同的领域联系起来,其一是偶发的联系,其二是系统的联系。在第一种情况中,只要是有益于研究目标,研究者就可以自由地相互借用问题和范畴。第二个战略是在不同领域之间建立更为稳定的联系。这类整合中的认识论挑战是研究者需要扩展现存领域的常规的认识论重心,这种扩展类似于一种投资,而且往往导致牺牲自己原有研究领域的进展,因此许多研究者对这种努力有一种天然的抵制。
跨学科研究不仅仅是面对认识论方面的挑战,也可以在认识论上获益,尤其是当研究者面对复杂的现象和问题,不咨询其他领域的学者就难以理解或做出解释时。通常这些复杂现象都源于领域之外,例如有某种社会和商业的需求背景。当然,跨学科研究也并非总是源于外部的激励,有时研究者也会发现如果不扩展认识论的范围,对一些本领域内的问题也难以做出回答,例如一些人工智能领域内的基础问题就有必要寻求心理学的帮助。
芬兰科学院的报告还强调了这样一点,即在强调整合的重要性上需要谨慎,因为跨学科的批评对于科学进步也是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可以被看做是跨学科现象的组成部分。
除了认识论的差异,学科研究中的战略、方法、技术技巧和所使用的工具设备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别,例如经验研究的进路——前提设定和推理方法——在生物物理学中是主导的方法,但是社会科学中的阐释和构建的方法则与此差异甚大。然而尽管存在冲突,方法论向不同领域的扩散以及学科间的相互借用趋势则非常明显,对于不同学科领域中范畴的构成产生重要影响,例如DNA与其他分子生物学技术的结合导致20世纪下半叶癌症研究中的重大转变,而计算机仿真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也日渐增大。(13)
从广义的角度而言,方法论是与研究设计、研究实施以及总结报告等有关的一套完整战略,因此方法论冲突可能会涉及许多问题。而且学科认同通常是与某种方法论的使用相关,鉴于方法论和方法技能在学科,特别是科学学科中的地位,这方面的障碍克服起来比较困难。而另一方面,学科领域之间相互借用工具和方法,使它们不断地跨越学科边界发挥作用,也使其成为跨学科工作的重要驱动力。
四、参与跨学科活动可能面对的心理障碍
有关开展或参与跨学科活动的心理方面的障碍,在各类文献中涉及不多,而芬兰科学院的报告,则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心理障碍的几个方面。
报告认为,首要的障碍源于决心,即做出超越传统的认识论和制度边界的决断,从传统社会学的观点看,这一点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这一障碍或许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讨论,美国学者莉萨·拉图凯(Lisa R.Lattuca)2001年曾对参加跨学科教学的学者开展了调查,(14)她发现,在不少学者对参与跨学科活动心存障碍的同时,还有一类学者,他们并不认为超越界限是一个障碍,而是视其为一种引人入胜的挑战,这些人被形容为“跨学科创业者”,他们具有心理学所谓的“创业警觉性”(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在别人感到是障碍时他们却看到了机会,他们有能力超越学科的界限来提出新的、有趣的研究问题,可以发现不同领域合作的机会。然而,一旦两类学者面临合作时,新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在一方可能视为机会时而另一方则视为问题,而且争论可能并非源于所研究问题的独特性,而是源于不同的心理构成和风格。
参与跨学科活动的另一个心理方面的问题来源于学者在学术共同体之间迁移所引发的边缘化感受。当研究者参与一个学术上头绪较多的跨学科项目时,他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此前所隶属的学科共同体,而加入一个新的研究者群体,而新的研究方向和侧重可能意味着研究者没有时间在其本领域的出版物上发表成果或是参加会议,同时,过去的同行可能也会对他的工作失去兴趣,于是一种边缘化的感觉便如影随形。而如果这个新的跨学科的共同体尚处于不完备的状态,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时,这一边缘化就尤其成问题,因为很难基于此而取得新的能够替代之前的身份认同。
正如上文所指,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文化,而有着不同学科文化的研究者聚集在一个跨学科团队中互动,可以引发大量的情感问题,包括一些负面的情绪,这就是报告所分析的第三个层面的心理问题。尽管在所有合作中,人际关系都是这类问题的潜在根源,但是在跨学科合作中,这类问题更易于出现,一方面由于参与者如何想和如何做都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不同学科在学术领域中不同的等级地位也是其原因。学科机制和学术环境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为研究者提供一个保护区域,在其中,没有人质疑其专业身份和行为基础,只要其符合学科的期望。然而,在跨学科的环境中,通常不存在保护带,研究者要面对他人的评判,而这通常是不愉快的经历,有时候冲突会是很深层的,因此,跨学科合作包含着情感压力,使它要比其他形式的合作更为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学者认为在这种合作中消除等级观念是一个重要前提。
五、资源以及评估所造成的外部压力
无论是知识、文化还是心理问题,都是源于研究者本身或是团队内部关系所产生的压力,而资源分配、项目评估和获得认可则更多地来自于外部,涉及计划申请可否获得资助、论文能否被刊物选用、项目成果如何评估以及研究成果和研究成就向社会公众的传播。
在研究者个人方面,常规的研究回报体系也是依照传统的单一学科的路径构成的,诸如在系或学院中获得职位提升、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由本学科领域中的评估小组给予评价、获得相应的声望,为未来的研究和获得进一步的资助创造条件等。然而,有些接受调查的学者表示,参与多学科的合作并没有被看做个人职业发展中的重要一环,(15)而且没有任何激励机制以敦促学者在研究中克服学科的局限,他们通常需要依靠个人的意志来完成工作,这对于吸引更多具有深厚学科知识根基的、有才华的学者参与跨学科活动无疑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
资源问题主要涉及研究可获得的资助。对跨学科研究参与者的调查显示,多数被调查者都反映现有的资助环境在他们看来无任何激励可言。目前大多数国家都是按照学科来申请和审议研究资助,以英国为例,英国有三个政府研究机构资助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其中,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资助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艺术和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AHRC)资助艺术和人文科学研究;英国学术院则为无法从其他研究机构获得经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支持。但在这种结构下,仍有些研究领域无法被覆盖,造成一些盲区。
同样的问题在芬兰也存在。芬兰的课题申报也必须分学科进行,课题申报首先要由一个同行评议小组或2~3名评议者来审查,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学科,审议时很注意研究计划的学术质量和申请者的水平,并采用了1~5级的划等标准;在第一轮初审之后,理事会的预选小组会提出初步的资助名单。预选小组中同样包括来自不同学科的成员,并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线;最后,理事会将就予以资助的项目做出最后决定,理事会的成员代表着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由于审议过程是按照学科进行的,所以跨学科课题也会遇到一定困难。“虽然预选小组和理事会本身都包括来自不同学科的成员,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所从事的就是跨学科研究,或者他们赞同跨学科的课题。”(16)
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各国具有跨学科特点的研究计划越来越普遍,有些国家还向跨学科课题提供长期资助,但文献调研显示,尚未有哪个国家针对跨学科课题建立“常规的”申请和审议制度。另一方面,即使是尝试改变申请和审议方法,相反的问题也会接踵而至。例如在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采用了复合审议申请(category of multi-panel application),将此作为其资助机制的一部分时,这一类别中却吸引了大量的质量较低的申请。(17)因此,学者也提醒,即使认识到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也还需要注意,即不是每项非常规的研究都代表创新和巨大的学术发展潜力,而为了解决接受和承认的问题进行一些特殊的安排,会人为地在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之间造成对立,也会招致研究者中的机会主义,在更小竞争环境中寻求最多机会和最好结果的心理会使许多低水平的申请涌入。
即使获得了研究所需的资源,在成果发表过程中,跨学科的研究也会遇到困难,因为跨学科的成果不容易找到合适的读者,其研究的问题并不是学科的热点问题,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范式和假设都不是现有学科所熟悉的,而且跨学科工作所产生的论文很容易被那些“学科意识形态”(disciplinary ideology)浓厚的刊物所拒绝,因此除非是专为学科整合创办的期刊,否则跨学科研究者在那些知名的学科刊物上发表论文是非常困难的。
近年来跨学科的综合性刊物的数量已经有所增多,但是除了个别刊物(美国科学院的报告提到了Science、Nature和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为较有影响的综合性刊物)之外,多数跨学科刊物都不具有单一学科刊物的声望和影响,(18)学者或研究生在这些刊物上获得发表机会并不能成为他们专业发展的资本。
与获得承认有关的另一个重大障碍是如何对研究成果进行整体评估以及研究者个人能获得哪些回报,即他们的地位能否得到承认。跨学科研究应该如何评估?基于同行评议的学科评估体系能否公平地对待跨学科的计划和论文?如何对新的且是陌生的研究进行评估?这些都是跨学科研究的从事者或推动者经常提到的令他们忧虑的问题。
澳大利亚知名学者斯图尔特·坎宁安(Stuart Cunningham)认为,“一项课题基于一个学科,并由来自那个学科的学者进行评价,得到的分数要远高于一项寻求跨学科合作的课题。目前缺少能够兼顾课题的技术方面和社会方面的高资质的评估者。”(19)英国学者斯蒂芬·罗兰(Stephen Rowland)也指出英国高校的学术研究评估机制(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加重了跨学科研究的不利状况,2007年的计划中也未见有相应的改进措施。在这一机制中,对跨学科工作的限定含混不清,研究者被建议将计划提交到一个最具相关性的学科评议小组,同时还建议他们提交给一个次相关的小组,罗兰认为,这一程序无助于提升跨学科研究的声望,而且更加令人感觉其缺乏学科的严密性。(20)
在对评估问题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例如,修改对跨学科研究和教育计划进行预期和回溯评价的同行评议过程;评估小组应在具有相关学科专门知识的学者之外,纳入具有跨学科知识的研究者等。
芬兰科学院的报告还指出,目前许多同行评议体系都是围绕个人评估工作建立的,专家独自从事评估,这种模块化的过程将评估分解成若干部分,而评估者也视自己为某一特定领域的代表,而没有关注研究中跨越学科界限的那些方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评估者之间的交流对于做出公平的评判是很重要的。芬兰科学院采用过集体评估的方式,为评估者和研究者之间开展交流提供论坛,这样可以减少误解和误导的风险。此外,在计划和论文中更加明确地强调为什么选择跨学科的方法,以及如何实施,也将有助于评估者将注意力放在这些方面。
目前,对于跨学科的评估已经有了不少专门的研究,有的研究特别提到跨学科工作并非一定要比学科工作在评估中处于劣势。芬兰科学院的调查也显示,在其2004年的一般研究资助(General Research Grant)中,跨学科的课题计划在获得资助上与学科的课题计划几乎持平,就此报告撰稿人还鼓励从事跨学科工作的学者坚信,现代科学理念的内在特征就是创造新的知识,不管它是产生于学科的工作还是跨学科的工作。
近年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地印证,科学发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科之间的边界地带,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正是重大科技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此外,经济和社会创新也呼唤来自更广泛的、不同学科的投入。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跨学科研究所呈现的巨大潜力和现存的整体研究体系结构、研究者的个人心理和能力、管理层的认识与作为,以及资助和评估体系之间依然存在着诸多的不相适应之处。
然而,尽管存在很多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并非不可克服。如前所述,以跨学科研究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它已经成为欧美不少国家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相关研究理事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且这些报告都包含了推动跨学科研究发展的战略和措施。目前,越来越多的学术和专业机构在更大程度上鼓励跨学科的活动,对于这些机构或组织的报告和文献都应予以认真地研究和讨论,以了解最新的变革,而与跨学科有关的聘用、任职、提升、薪金、奖励和工作合约等都应予以明文规定。总之,理论成果和实践的经验对于克服障碍,推进和支持跨学科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资源,不少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不少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和经验。而汲取经验,取长补短,最大限度地利用跨学科活动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正是各国科研管理和资助机构应予重视的问题。
注释:
①Committee on Facilita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Institute of Medicine,2004,Facilita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p.17,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②Grigg,Lyn,1999,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in http://www.arc.gov.au/general/arc_publications.htm#1999.
③Advisory Committe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AWT),2003,Promoting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Available on the AWT home page,http://www.awt.nl/en/index.html.
④Gabriele Griffin,Pam Medhurst and Trish Green,Interdisciplinarity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rogrammes in the UK,2006,in http://www.york.ac.uk/res/researchintegration/Interdisciplinarity_UK.pdf.
⑤Rowland,Stephen,2006,The Enquiring University,Chapter 7:Interdisciplinarity,McGraw-Hill.
⑥Grigg,L.; Johnston,R.& Milsom,N.,2003,Emerging Issues for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Dimensions(Electronic version),in http://www.dest.gov.au/sectors/research_sector/publications_resources/other_publications/emerging_issues_for_cross_disciplinary_research.htm.
⑦Bruun,Henrik et al.,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The Case of the Academy of Finland,2005,p.62.
⑧European Union Research Advisory Board,Interdisciplinarity in Research,in http://ec.europa.eu/research/eurab/pdf/eurab_04_009_interdisciplinarity_research_final.pdf.
⑨Becher,T.,(1989,1993),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s of Disciplines.Buckingham and Bristol: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 & Open University Press.中译本《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⑩参见http://www.nsf.gov/crssprgm/igert/intro.jsp。
(11)Salter,L & Hearn,A.Eds.,1996,Outside the Lines:Issues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Montreal and Kingst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2)boundary objects也译作边界物,指能够沟通不同的社会世界,却在各自的社会世界中保持自身同一性的事物。参见王程韡:《政策学习与全球化时代的话语权力——从政策知识到合法性的寻求》,《科学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321-326页。
(13)Bruun,Henrik et al.,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The Case of the Academy of Finland,2005,p.68.
(14)Lattuca,Lisa R.,2001,Creating interdisciplinarity: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teaching among college and university faculty,Nashville: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5)Cunningham,Stuart,Collaborating across the Sectors,in http://www.chass.org.au/papers/collaborations/Four_Barriers.pdf.
(16)参见[芬兰]S.凯斯基南、H.西利雅斯:《研究结构和研究资助的学科界限变化——欧洲8国调查》,黄育馥摘译,《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17)参见Grigg,L.,1999,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A Discussion Paper,Commissioned Report No.61,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18)Committee on Facilita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Institute of Medicine,Facilita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2004,p.139,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19)Cunningham,Stuart,Collaborating across the Sectors,in http://www.chass.org.au/papers/collaborations/Four_Barriers.pdf.
(20)Rowland,Stephen,2006,The Enquiring University,Chapter 7:Interdisciplinarity,McGraw-Hill.
标签:学科评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