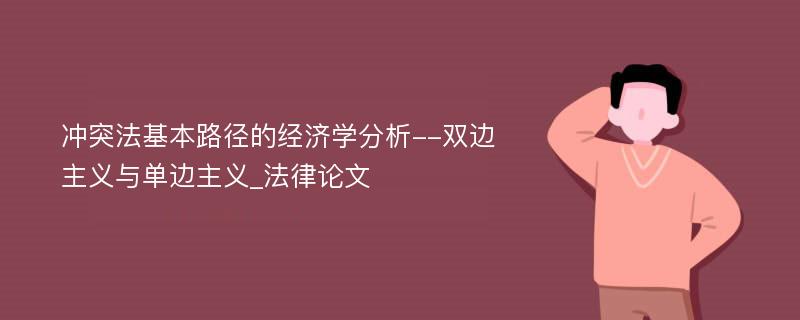
冲突法基本路径的经济分析——双边主义对单边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路径论文,经济分析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论
目前,主张内外国法平等适用的双边主义法律选择路径在各国的冲突法立法中虽然已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适用法院地法的单边主义偏好却始终存在。由此,在双边主义对单边主义的冲突法基本路径选择上,便形成了立法与司法之间的一种张力。如何评判这两种法律选择的基本路径,也构成了各种范式的冲突法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然而,在我国的冲突法学界,对于法律选择上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比较,以往的学说多注重以“公正”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而以法律适用的“效率”为价值取向展开研究的著述,尚未得见。
效率是法经济学追求的基本价值取向,冲突法的经济分析也不例外。在冲突法的经济分析中,可将法律适用的效率分为两大类:一是“冲突效率”(conflicts efficiency),即冲突法规范本身在适用过程中涉及的降低社会成本和促进社会收益提高的问题,主要由法律选择的稳定性、可预见性、一致性带来的“冲突效率”与适用法律的简便性带来的“冲突效率”两部分构成;二是“实体效率”(substantive efficiency),即依冲突规范选择最有效率之实体法的问题,① 而判断一个国家的实体法是否有效率,在法经济学中,主要采取“卡尔多-希克斯准则”。该准则是指,即使一方福利的增加会使他方的福利减少,那么,只要受益方增加的福利超过受损方减少的福利,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
本文拟结合我国的法律选择实际,在不损害公正的前提下,采取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及以“政府”、“私人”及“法官”为本位的三种进路,研究双边主义对单边主义的冲突法基本路径问题。
二、冲突法之立法取向:推行双边主义的经济分析
对于冲突法立法的经济分析,主要采取以“私人”及“政府”为本位的两种进路。以“政府”为本位的进路主要求得各国实体法之立法政策效用的最大化,即采取适当的政府利益分析方法实现法律选择的“实体效率”;而以“私人”为本位的进路所追求的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然而,无论是以“政府”为本位,还是以“私人”为本位的分析,在冲突法立法上,双边主义都是比单边主义更具效率的一种基本法律选择路径。
(一)以“政府”为本位的经济分析
美国现代冲突法鼻祖柯里采取的就是以“政府”为本位的解决法律冲突的进路。然而,柯氏提出的“政府利益分析说”带有浓厚的单边主义色彩。具体而言,对于跨州民商事案件,各州适用本州法,当然能求得本州政策效用的最大化。但事实上,任何一个州都不可能包揽对所有跨州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就X、Y两州间发生的跨州民商事案件,假如其中由X州法院受理的那些案件只适用X州法律,固然促进了X州政策效用的实现。但是,这等于Y州法律被完全排除适用,Y州的政策效用会因此而受损,而且Y州政策效用受损之程度可能会高于X州政策效用增进之程度;同样,假如由Y州法院受理的另一些案件一概适用Y州法律,Y州的政策效用得到了实现。但是,此时,因X州的法律没有得到适用,X州的政策效用受到了损害;而且其政策效用受损之程度可能会高于Y州政策效用增进之程度。显然,单边主义无法保证共同促进两州政策效用的最大化,是一种缺乏效率的法律选择路径。
美国另一位著名的冲突法学者巴克斯特在1963年发表的《法律选择与联邦制度》专论中,提出了“比较损害说”。巴氏虽然认同柯里以“政府利益”为基点的解决法律冲突的进路,但是反对柯氏的单边主义做法,赞成双边主义的法律选择方法。“比较损害说”主张,在两个州法律发生真实冲突的情况下,应选择假如不适用其中一州法律会对其利益造成更大损害的那一个州的法律。倘若各州都采取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卡尔多-希克斯准则),就能“达到所有政府实体的根本目的的最大化”。② 具体言之,只要X、 Y两州都以“比较损害分析”这样的双边主义方法选择法律,做到只有在X州法律得不到适用致使X州受损程度大于Y州法律得不到适用致使Y州受损的程度时,方才适用X州法;相反,在X州法律得不到适用致使X州受损程度小于Y州法律得不到适用致使Y州受损的程度时,就适用Y州法。巴氏进一步假设,假设X、Y两州展开谈判,则“各方将审慎地通过放弃可得利益少的去换取可得利益大的,各方顾及己方自我利益和它方目的考虑得到强化,由此而达成的最终协议将使各方接近各自效用的最大化”。③ 在该专论中,巴氏虽然没有明确,但实际上是运用了法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法律冲突问题。据此,巴氏被誉为冲突法经济分析之先驱。④
美国当代著名冲突法学者克雷默认为,各州对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冲突法基本路径的选择属于“囚徒困境”博弈。⑤ 对此,美国另一位当代著名冲突法学者布莱梅尔主张,尽管“囚徒困境”博弈模式广受重视,但并不意味着另外两种博弈模式——“猎鹿”博弈模式和“懦夫”博弈模式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布氏指出,判别各州对冲突法基本路径的选择到底属于哪一种博弈模式并不重要,进行这样的归类是一个需要实证的问题,其中的一种博弈模式的解释力是否强于其他两种博弈模式,有时并不清晰。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冲突法基本路径的选择,一州往往同时具有追求合作和私利的混合动机,所采用的三种博弈模式都有助于证明:通过发展理性的战略,各州有可能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追求短期私利之中,求得较好的结果。⑥ 无论是以上三种博弈模式中的哪一种,对各州来说,选择“背弃”(主张单边主义)虽然是个体的最优结果(“囚徒困境”博弈与“懦夫”博弈)或次优结果(“猎鹿”博弈),但问题是,各州都选择“背弃”(“相互背弃”)战略,无疑会带来集体最差的结局。因而,片面扩张法院地法适用之单边主义的盛行,对各州来说,终将是无效率之举;反之,各州均采取“相互合作”(主张双边主义)的战略,将会取得集体的最优结果,即可实现各州政策效用的最大化。
当然,以上无论哪一种博弈模式都表明,如一州选择“合作”,另一州却选择“背弃”,则选择合作的一方将损失惨重(出现个体最差的结果)。由此,互信对于促成各州的共同合作至关重要。就此,克雷默和布莱梅尔均依博弈论原理,以“囚徒困境”博弈为例说明:只要实施“投桃报李,以牙还牙”(Tit-Tat)的互惠策略,对选择“合作”(实行双边主义)的州给予报偿(以己方也采取双边主义作为奖赏),对选择“背弃”(采取单边主义)的州施以报复(以己方也采取单边主义作为惩罚),那么,在重复博弈中,各州之间就可建立互信,以致最终在法律选择上集体放弃单边主义,共同实行双边主义,获得有效率的结果。上述巴克斯特提出两州通过谈判达成共同采用“比较损害说”之假设,实际上就是在无意之中运用了博弈论的这一原理。
需要指出的是,通常只有美国的冲突法采取“政府利益分析”的范式,故以“政府”为本位分析法律选择中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之“实体效率”的方法,通常只适用于美国的“州际”法律冲突实践,对其他国家冲突法处理的“国际”法律冲突,这种冲突法的经济分析原理基本上不适用。这是因为:首先,将解决各国“私法”适用问题的冲突法全盘提升到政府利益的高度去认识,实际上完全抹杀了“私法”与“公法”之间的应有界限;其次,迄今仍缺乏有效的实证研究说明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没有签订统一冲突法条约的广大领域,正在有意识地进行合作。
(二)以“私人”为本位的经济分析
对于冲突法中双边主义对单边主义的立法取向,以“私人”为本位的分析是最为主要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冲突法毕竟是解决私人与私人之间跨国民商事法律冲突的法律部门。采取“私人本位制”分析冲突法的基本路径,具有双重目标:一是为了降低当事人诉前的交易成本和诉后的诉讼成本,以求当事人之间“冲突效率”的实现;二是为了选择最适合调整当事人参与之跨国民商事关系的实体法,以便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正义”。
1.当事人之间“冲突效率”的实现
实行法律选择上的单边主义,主张适用法院地法,在当事人之间,最多只有助于实现法律选择的“嗣后可预见性”(secondary predictability),即案件归哪个国家管辖,就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因此,案件起诉之后,所适用的法律便可得到确定。然而,单边主义将无以在当事人之间求得法律选择的“初始可预见性”(primary predictability),⑦ 即在诉讼开始之前的阶段,当事人无法预见相互间的跨国民商事关系将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以致难以对交易做出具体的安排和监督,从而带来交易成本的增加。
从诉讼制度运作成本来看,如采取单边主义的法律选择方法,只有待诉讼提起之后,所适用的法律才能确定。从表面上看,此乃管辖地决定法律选择,实则往往相反,蜕变成了当事人为了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而选择案件的管辖地;而当事人“选购法院”的结果,必然造成社会诉讼成本的提高。
第一,当原告可以通过有策略地“选购法院”来最大限度地获得其预期回报之时,就会导致潜在的被告迅速起诉以抢先对手获得对管辖的选择权。由此而引发的“诉讼竞赛”将加速起诉的过程,并使一些原本不会起诉的案件最终被当事人诉诸法院,从而浪费社会资源。⑧
第二,在可供选购的多个法院中,原告在一国起诉获得对己方有利的适用法律之后,为了对抗原告,被告有可能会在其他国家法院起诉,以便取得对自己有利的法律选择;或者,原告在一国败诉后,判定仍存在有利于己方的其他国家的法律,于是,再次在另一国法院起诉,从而形成“一事多诉”这种诉讼不经济现象。
第三,当案件所适用的法律给原告带来的边际赔偿金较小时,一个理性的原告可能会放弃诉讼;即便选择了起诉,也会通过减少诉讼成本来使自己的诉讼效益最大化。然而,在有“选购法院”机会的情况下,只要其中一个国家的法律会给原告带来很大的潜在预期赔偿金,就会助长原告起诉,并减少其控制诉讼成本的激励力度。⑨
第四,在实践中,原告为了获取于己有利的法律而“选购法院”,其所选择的法院地国未必与案件有密切的联系。倘若如此,案件由该等“不方便法院”审理,将会给当事人带来很高的诉讼成本,如取证难度和费用的增加以及出庭差旅费用的提高等。
第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赔偿金越多,原告就越愿意采取诉讼方式而不是通过庭外和解来解决纠纷。⑩ 在有多个法院可供起诉的情形下,只要依某个国家的法律,边际赔偿金上升到一定的幅度,原告就会选择该国法院起诉,而不会求诸和解。由于诉讼的社会成本一般大于和解的社会成本,就此而论,“挑选法院”将带来无效率的结果。(11)
最后,因单边主义主导下法律选择“初始可预见性”的缺失,在纠纷发生之后至起诉之前的这段期间,双方当事人因无法划定“和解范围”,也就难以确定对双方互利的和解条件,(12) 致使许多案件丧失和解的机会,从而增加社会诉讼成本。
从以上各个方面来判断,对于当事人而言,偏好法院地法的单边主义法律选择路径缺乏“冲突效率”。反之,倘若各国都采用一致的比较明确和具体的双边冲突规则,依这些双边冲突规则中连结点的指引,决定到底是适用内国法还是外国法,就可以大大提高当事人之间法律选择的“初始可预见性”。由此,一则可以降低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成本;二则,按照双边冲突规则选择法律,无论当事一方向哪个国家的法院起诉,纠纷适用的法律均相同,也可抑制“选购法院”现象的产生。
可见,无论是在降低当事人诉前的交易成本方面,还是在防止当事人“选购法院”以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方面,都是双边主义而不是单边主义更有助于当事人之间“冲突效率”的实现。
2.当事人之间“实体效率”的实现
以单边主义为主导,强调适用法院地法,显然不可能处处求得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效率”。因为任何人都无法断言,只有法院地法,而不是外国法,才是最适合调整当事人参与之跨国民商事关系的实体法。
法经济学的开创者波斯纳主张,在发生冲突的内外州法律中,倘若采取双边冲突规则,选择其中一个对调整跨州民商事关系最有“比较管理优势”那个州(如该州的立法者对某类跨州民商事关系最有管理经验以及最具有掌握相关信息的能力等)的法律,那么,这样的法律选择就能达到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的,也就是具有法律适用上的“实体效率”;相反,单边主义将阻碍各州“比较管理优势”的实现。(13)
现假设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司机在纽约市与另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司机发生撞车事故。纽约市采用的交通侵权法规定,司机只有尽到适当水平的注意,才能免责。应该说,作为交通事故的发生地,纽约市的法律规则一般最能与当地的行车条件(诸如道路、气候等)相适配,因而对发生在当地的交通事故具有“比较管理优势”;而南卡罗来纳州法律规定的注意标准过低,不利于促使司机谨慎驾驶,减少交通事故。如果该案起诉到南卡罗来纳州法院,南卡罗来纳州法院采取单边主义,只适用本州的法律,那么,纽约市的法律就得不到适用。由此,对于交通侵权没有“比较管理优势”的南卡罗来纳州法律便驱逐了有“比较管理优势”的纽约市法律,这样的法律选择肯定是没有效率的。反之,假如南卡罗来纳州法院采取双边主义,就该案选择纽约市的法律,要求路经纽约市的南卡罗来纳州司机都应遵守纽约市的法定注意标准,那么,就会促使纽约市将关于合理注意的法律规定修改得更好,从而进一步发挥其法律的“比较管理优势”。(14)
单边主义赋予原告单方面“选购法院”的权利,还可能会造成各国之间无效率的恶性“管理竞争”。兹以美国州际产品责任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为例:美国制造商在为产品定价时,一般都需考虑潜在的产品责任赔偿支出。然而,由于产品将销往美国各州,实际上根本无法分别计算出各州潜在赔偿支出的大小以便逐州订出不同的价格,于是,制造商只能采取全美统一定价的做法。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个州如果提高对原告产品责任的赔偿标准,制造商就会把这部分边际赔偿支出计入全美统一定价,转嫁给其他州的消费者分摊。这是一种没有效率的立法,等于认可一个州的消费者在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时可以不把其所产生的“外部性”内化,而是将它转变为由其他各州消费者承担的社会成本。其它各州也会如法炮制,纷纷提高本州立法的产品责任赔偿标准,并主张本州法院受理的产品责任案件应适用法院地法;且在保护本州原告的动因刺激下,各州将会展开此类“实体法上的竞争”和“冲突法上的竞争”,以致形成一种“越来越往底线”(race to the bottom)的恶性“管理竞争”。相反,如果采用侵权行为依侵权行为地法这样的双边冲突规则,一个州受理的产品侵权责任案件不一定适用法院地法,就会大大抑制各州竞相提高本州产品责任赔偿标准的动力。(15)
波斯纳认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使司法判决错误和诉讼制度运作两类成本最小化,这样的分析也适用于法律选择过程中对“冲突效率”的追求。(16) 除前文已探讨的涉及“冲突效率”之诉讼制度运作成本的问题外,从与“实体效率”相关的司法判决错误成本来看,(17) 法官对法院地法的理解程度一般甚于他们对外国法内容和精神的了解,因此,适用法院地法而发生司法判决错误的概率必定要小于适用法院地法的情形。
尽管单边主义的司法判决错误成本小于双边主义,但是,在促进各国实体法律“比较管理优势”的实现以及防止各国实体法之间的恶性“管理竞争”方面,双边主义比之单边主义显然更具效率。据此,从总体上看,在求得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效率”上,双边主义仍要优于单边主义。
三、冲突法之司法实践:抑制单边主义的经济分析
对冲突法的经济分析,除了本文上部分论述的“私人本位制”及“政府本位制”之外,还有以“法官”为本位的第三种进路。该进路是指,从司法经济原则出发,尽量减轻法官选择法律的成本,即肯定适用法院地法的简便性而给法官带来的“冲突效率”。例如, 1971年出版的《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第6条第2款列举的判断最密切联系程度七要素中的最后一项就是,法官“确定和适用将予适用之法律的简便性”。该条评注C明确指出,七要素的重要性并非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而是应视具体案情而定;换言之,在有些案件中,该第七项要素可能是最重要的。又如,美国现代冲突法最具代表性的学说之一——莱弗拉尔的“较好法说”主张的法官“法律选择的五点考虑”之一同样为“司法任务的简便化”。与对冲突法立法的经济分析不同,对于司法实践中单边主义的研究,应以探讨“法官本位制”作为起点。
(一)法官适用法院地法偏好的形成
从上述以“私人”及“政府”为本位的分析来看,片面扩大法院地法的适用,是一种缺乏“冲突效率”和“实体效率”的法律选择路径,目前,各国的冲突法立法已普遍摒弃单边主义。然而,双边主义虽已成为各国冲突法普适的立法取向,但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单边主义仍大受法官的青睐,我国更是如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2001-2002年间我国法院审结的涉外商事案件的抽样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50起案件中,适用中国法的比例高达90%(45件);适用外国法的只有4%(2件);适用国际公约的为2%(1件);适用国际惯例的占4%(2件)。(18) 另据我国学者对2003-2004年我国法院审结的涉外商事案件的抽样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100起案件中适用中国法的比例仍高达91%(91件);适用外国(外法域)法的仅为6%(3件);分别适用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的为2%(2件);分别适用中国法和国际公约(惯例)的占4%(4件)。(19)
从各国的法律选择实践来看,法官滥用法院地法的主要情形有二:一方面,他们可能会视先决问题、识别、反致以及公共秩序保留等传统冲突法制度为“玩偶”,不惜玩弄“概念游戏”,刻意回避依双边冲突规则原本应当适用的外国法,改取法院地法;(20) 另一方面,法官也可能先入为主,早已设定法院地法为案件的准据法,然后再“以结果为导向”,利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等现代法律选择方法的“弹性”特点,通过操纵其分析过程,达到既定的目标。近年来,我国法院依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择的几乎全为法院地法(中国法),明显表露出了这一倾向。(21) 此外,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法官未说明理由就适用法院地法的情形。在最高人民法院统计的2001-2002年间我国法院适用法院地法的 45起案件中,未说明理由的就有26起,所占比例高达58%;(22) 2003-2004年,这个比例虽趋于下降,但据我国学者统计,在适用中国法的91起案件中,仍有18起未说明理由,所占比例约为20%。(23)
在各国冲突法立法普遍反对单边主义的情形下,为何在司法实践中这种选择法律的路径仍然大行其道呢?从以法官为“本位”的冲突法经济分析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官熟悉法院地法,故法院地法易于适用,由此可以大大降低法官选择法律的司法成本,以致对法官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相反,在适用外国法的情形下,如由法官负责查明外国法的内容,并将之适用于涉外民商事案件,往往会带来司法成本的大幅增加。鉴此,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法官为了追求法律适用的“冲突效率”,必然会采取压制双边主义,扩张单边主义的做法。
无疑,法院地法主义的泛滥,实质上就等于否认内外国法律冲突现象的存在,最终将导致冲突法的衰退。为了抑制司法中的单边主义倾向,我们认为,在不损害冲突法中公正之基本价值的前提下,可将法院适用外国法的成本转移给当事人承担(即将这部分诉讼运作成本由公共成本转化为私人成本),但同时应允许当事人进行适当的成本控制。
(二)法官适用外国法之成本的转移
将法官适用外国法的成本转移给当事人承担,其主要的制度设计为:对于外国法性质的认定,应放弃“法律说”,改从“事实说”;相应的,应免除法官依职权查明外国法内容的义务,改由当事人负举证责任。
根据“法律说”,外国法与内国法一样,都是“法律”。据此,如就涉外民商事案件选择外国法,依“法官知法”的原则,法官得依职权查明外国法的内容,然后加以适用,这将会给他们带来高昂的司法成本;相反,“事实说”主张,外国法与内国法不同,其不是“法律”,而只是“事实”。据此,即便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的是外国法,依“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外国法的内容应由当事人负责举证,法官没有义务主动去查明,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法官审理案件的负担。例如,法国著名冲突法学者巴蒂福尔及拉加德认为,法国最高法院曾一度将外国法的举证责任转移给当事人,其原因就在于,“这样解决是考虑到无需没有必要地增加查明外国法内容的成本”。(24)
对于外国法的性质,我国的冲突法未予明确界定。但国内有冲突法权威教科书指出:“在我国,民事诉讼采取‘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要作出切合实际、合理的判决,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促进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不管是‘事实’还是‘法律’,都必须查清,因此,把外国法看成是‘法律’还是‘事实’的争论,在我国没有实际意义。”(25) 然而,目前,我国发生的大量涉外民商事关系与西方国家有关,由于东西方在语言、文化、社会、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存在巨大差异,要求中国法官查清、释明各西方国家法律的具体内容,尤显困难。此已成为导致中国司法实践中单边主义盛行的主因。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如果将由法官承担查明外国法内容责任的做法,改为由当事人负举证责任,(26) 那么,法官就不会因自己在查明外国法方面负担过重而轻易扩大法院地法的适用;相反,法官可能会尽量给当事人以举证外国法内容的机会,避免动辄以法院地法取而代之。例如,以色列冲突法就外国法的性质采“事实说”,要求当事人负举证责任。但在许多案件中,原告有时主张外国法的内容与以色列法类似,因而不再去举证外国法的内容。待法官审理之后发现,原告关于内外国法内容一致的主张并不成立,而此时原告又没有举证外国法的内容,本来法院可以适用法院地法(以色列法)了之,但在大多数这样的案件中,法官都会给当事人重新举证外国法内容的机会。除非当事人实在无法做到,才改用以色列法。(27)
依上而论,外国法查明责任由法官向当事人转移,不无现实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有法院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过程中采纳外国法的“事实说”,并以当事人不能举证为由,推定其放弃适用外国法的权利。(28)
(三)当事人对适用外国法之成本的控制
显然,查明外国法内容的责任由法官向当事人转移,只不过是负责查明工作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而已,因不能断言责令当事人举证外国法内容就比法官查明更为困难,因此,这种责任的转移并不会带来社会成本的提高。在将查明外国法内容的责任由法官转移给当事人之后,当事人可作的选择有二:
其一,当事人自感可以承受外国法举证的成本,于是继续主张外国法的适用。这样的决定是当事人在对整个诉讼成本进行分析之后自愿作出的选择,因而一般是有效率的。
其二,当事人认定外国法举证的成本太高,无力承担,需要进行成本控制。此时,冲突法应给当事人以放弃适用外国法的更大自由。这就牵涉到我国冲突法学界近年来兴起的有关冲突规则的强制性与任意性之争。(29) 该项争议的实质在于,法官是否必须依职权适用冲突规则,或曰当事人是否有权排除冲突规则适用的问题。从各国的法律实践来看,绝对地采用其中一种主张者并不多见,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是混合型的;亦即,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当事人合意排除冲突规则适用的权利。(30) 而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通常是有效率的:一方面,意思自治意味着当事人可以事先锁定跨国民商事关系的准据法,于是,法律适用自始便具有了相当大的稳定性,符合“冲突效率”的要求;另一方面,通过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法律,也能够实现“实体效率”之价值目标。按照法经济学原理,自愿交易可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亦是如此,因为当事人最了解适合调整自己参与之跨国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鉴于意思自治原则可达到“冲突效率”与“实体效率”的高度合一,从而为冲突法经济分析学派的一些学者所顶礼膜拜,他们甚至尊奉该原则为整个冲突法体系的基石。(31)
在合同等领域,各国业已普遍赋予当事人合意选择法律的权利。因此,有关冲突规则强制性与任意性争议的焦点实际上成了在更为广泛的法律冲突领域,法院能否以当事人存在默示同意选择法院地法为由,从而排除依冲突规则原应适用之外国法的问题。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给予当事人以更大的意思自治权。
在这里,当事人默示同意选择法院地法特指,一方当事人依法院地法提出请求,另一方当事人没有表示反对,并依法院地法进行抗辩的,可视为当事人双方默示接受法院地法的管辖。(32) 在实践中,当事人默示同意选择法院地法,放弃外国法适用的原因很多,大别为两类:一类是当事人对外国法的内容疏于举证或举证不能,即当事人没有意识到卷入的是一个涉及外国法适用问题的涉外案件;更为常见的是,当事人了解案件的涉外性质,但不知涉案外国法的具体内容。在这种情形下,既然当事人对外国法的内容疏于举证或举证不能,说明他们自始不了解该外国法的内容,从而也就谈不上事先已依该外国法安排交易的问题。因此,法官不适用该外国法,未必就会带来牺牲当事人之间“实体效率”的结果;另一类是当事人不愿举证,主要是因外国法查明的费用过高,当事人无法承受。(33) 据英国冲突法学者芬特曼的分析,后一种情形是主要的。芬氏断言:“诉讼,至少是商业诉讼,很少被当事各方看成是在追求正义,或探究真义。它是一项投资,即盘算着获取商业上的好处,通常意在就主张的损害获得金钱赔偿。这是一种成本/效益分析,其中所涉的突出因素是结果的可预见性以及获得该结果的支出。……诉求于外国法将带来高额的成本(专家证据是口头的,也许会采用报告的形式,但按规则要经过交叉询问,由此造成的诉讼拖延意味着成本和不可预见因素的增加)。”(34)
在法律选择上,当事人默示同意的法律效果应与明示同意相差无几,因为默示同意也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也表明当事双方均认同法院地法为适合调整其参与之跨国民商事关系的法律,只不过与明示同意相比,所采取的同意方式不同而已。据此,可以认定,当事双方默示同意选择法院地法一般同样具有“实体效率”;同时,当事双方默示同意选择法院地法,与单方通过“选购法院”不正当获取法院地法不同,不致带来缺乏“冲突效率”的结果。此外,由于法官熟悉法院地法,还可降低司法判决错误的成本。正因当事人默示同意选择法律的对象只是法院地法,而不是外国法,故不存在损害法院地公共利益的问题;如当事人默示同意选择法院地法构成对外国法中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则的规避,仍可依法律规避及强制性规则适用等制度对之加以限制。此外,虽认可当事人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可以默示同意的方式选择法院地法,但对该原则所适用的法律冲突领域也并非不加限制,如对于那些当事人“不可处分”的权利(如物权),冲突法仍可将它们排除在意思自治的作用范围之外。例如,法国就是对冲突规则“任意性说”和“强制性说”采取折衷态度之国家的典型代表,在1999年的Mutuelle du Man案中,法国最高法院判决,对于那些当事人“不可处分”的权利,法官还是有依职权适用外国法的义务;只是对于那些当事人“可处分”的权利,允许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选择法院地法。(35)
在涉外合同(含海商法中有关提单的案件)冲突法中,我国业已确认意思自治原则,包括承认当事人默示同意选择法院地法的权利。例如,在“富春航业股份有限公司、胜惟航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海上运输无单放货纠纷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在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对适用中国海商法未提出异议,故认定本案适用中国法律。”(36) 我们建议,应将当事人默示同意选择法院地法的权利推及至更为广泛的法律冲突领域。目前,我国法院主张适用中国法律,但又未提供理由的,多为当事双方均援用中国法主张权利和进行抗辩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如将这些案件中当事人默示同意选择中国法的行为加以合法化,就可名正言顺地避免因适用外国法而给我国法院带来的高司法成本。按照英国的经验,就涉外民商事纠纷,当事双方一般只根据英国法提交诉讼,而因为英国冲突法将这种情形视为对英国法的默示选择,所以,英国法院现已很少真正用到有可能指向外国法的冲突规则。(37)
需要指出的是,“推定当事人同意”与上述“当事人默示同意”不同,前者是法官根据各种因素推定当事人同意选择某一国法律(包括法院地国法,下同),而非当事人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其不一定代表当事人的真实意图。(38) 推定当事人同意选择某一国家法律所依据的因素包括:当事人适用该国的标准合同(如英国劳合社的格式保险合同)或该国法律中的特殊条款;当事人选择该国为法院地或仲裁地;相关的交易或以前的交易适用该国法律;当事双方拥有该国的共同国籍或在该国具有共同住所地;以及合同的特征履行地位于该国;等等。(39) 应该说,法官按照这些因素作出同意之推定,并不一定是对当事人本意的尊重,所选择的也并不一定是适合调整当事人参与之跨国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而且容易造成法官借当事人同意之名行盲目扩大法院地法适用之实。因此,由法官推定当事人同意选择法院地法既不能保证“实体效率”的实现;同时因推定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会带来当事人之间“冲突效率”的缺失。可见,对法官推定当事人同意之做法,应予否定,其不能作为主张冲突规则任意性的一个手段。
四、结论
各国冲突法现普遍以双边主义为立法导向。冲突法的经济分析表明,无论是就当事人之间的“冲突效率”而言,还是就其“实体效率”而言,法律选择上的双边主义均优于单边主义。众所周知,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最受诟病的是它尊奉的效率价值取向可能与正义之基本目标相悖。然而,事实上,冲突法中的单边主义既缺乏效率,也难有公正:一方面,采取单边主义意味着概采法院地法,而法院地法并非一定与跨国民商事关系在空间上存有最紧密的联系;而且,采取单边主义,实际上就是单方面赋予原告“选购法院”的机会。这些都将损害“冲突正义”;另一方面,实行单边主义,独尊法院地法的正义文本,并以此为据建立对法院地法的偏好,显然过于狭隘,与冲突法中的“实体正义”亦是不符。(40)
尽管双边主义已被各国冲突法立法尊奉为主导价值取向,但在司法实践中,各国法官对单边主义却钟爱有加。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官适用法院地法的司法成本要大大小于适用外国法的情形。在我国的涉外审判实践中,法院地法扩张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为了缓解冲突法立法上的双边主义与司法上的单边主义之间的张力,可以在选择法律的两个层面上采取相应的对策:首先,在外国法内容查明层面,应采纳“事实说”而非“法律说”。相应的,我国的冲突法立法亦应将查明外国法内容的责任由法官转移给当事人,这将在相当程度上降低法官适用法律的司法成本,使之不会在“舍繁就简”(放弃本应选择的外国法改取本不该适用的法院地法)动机的驱使下,产生法律选择上的“恋家情结”;而在当事人也无法承受外国法查明成本之时,则应允许他们在到底是选择适用法院地法还是外国法的层面上实行成本控制,即适度借鉴冲突规则的“任意性说”,在更为广泛的法律冲突领域赋予当事人默示同意选择法院地法的权利,使他们可以避免因适用外国法而带来的举证方面的高成本负担。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关于缓解冲突法立法上双边主义与司法上单边主义之间张力的两项主张虽是采取法经济学方法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但其本身也符合冲突法对正义的基本要求。其一,将法官查明外国内容的责任转移给当事人承担,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程序正义原则。进一步来看,如果不给予当事人以充分举证外国法内容的机会,任由法官查明,其主观臆断的结果,反而容易造成不公正的裁决。(41) 正如日本学者谷口安平所言:“法的判断不许当事人染指的结果往往是在程序上带来对当事者的不意打击。”(42) 其二,允许当事人在更广泛的冲突法领域默示同意选择法院地法,本身就体现了他们的自由意志,符合“实体正义”的基本要求。此外,当事双方默示同意选择法院地法,还可以排除当事一方“选购法院”现象的发生,也有利于“冲突正义”的求得。
毋庸讳言,学界对于采取外国法定性的“事实说”,从而将查明外国法的责任由法官转移给当事人的对策主张;以及对于适度借鉴冲突规则的“任意说”,从而在更为广泛的领域承认当事人默示同意选择法院地法的对策主张,均存在异议。异议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对理由,这些反对意见并非全无道理。然而,双边主义对单边主义不但是关于法律选择的基本路径之争,实际上涉及到是否承认内外国法律冲突存在这一关系冲突法生死存亡的根本性问题;而本文求证的上述两种对策主张可谓是抑制单边主义,支持双边主义的“良方”,是决定冲突法兴衰之命运的基本技术手段。在此“大义”的威压下,任何反对的具体理由终归是次要的,不能成为否定上述两种对策主张的根据,但在依该两种对策主张进行制度的具体设计时,仍应将这些反对的理由作为制约的因素加以考虑,以防止最终形成的制度带有偏颇性。
注释:
①有关“冲突效率”和“实体效率”的区分,参见乔伊尔·P·特拉希曼:“立法管辖权的经济分析”(Joel P.Trachtman,Economic Analysis of Prescriptive Jurisdiction,42 Va.J.Intl L.,2001,p.42.)。
②引自威廉·F·巴克斯特:《法律选择与联邦体系》(William F.Baxter,Choice of Law and the Federal System,16 Stan.L.Rev.,1963,p.12.)。从冲突法的经济分析角度对巴克斯特的“比较损害说”进行研究的,详见威廉· H·艾伦/伊瑞因·A·奥哈拉:《第二代法律与冲突法的经济分析:巴克斯特的比较损害方法及其他》(William H.Allen & Erin A.O' Hara,Second Generation Law and Economics of Conflict of Laws:Baxter' s Comparative Impairment and Beyond,51 Stan.L.Rev.,1999,pp.1011-1048.)。
③同注2引书,第7页。
④乔伊尔·P·特拉希曼:《冲突法与政府责任分配的精确性》(Joel P.Trachtman,Conflict of Laws and Accuracy in the Allocation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26 Vand.J.Transnat' l L.,1994,p.1017.)。
⑤拉瑞·克雷默:《法律选择的再思考》(Larry Kramer,Rethinking Choice of Law,90 Colum.L.Rev.,1990,pp.339-344.)。
⑥列·布莱梅尔:《冲突法:基础与未来走向》(Lea Brilmayer,Conflict of Laws:Found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Little,Brown and Company,2nd ed.,1995,pp.169-196.)。
⑦有关“初始可预见性”与“嗣后可预见性”之区分,最早见于巴克斯特,参见注2引书,第3页。
⑧皮特·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法律冲突”辞条(弗兰西斯科·帕里西/伊瑞因· A·奥哈拉),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8-439页。
⑨米歇尔·J·温考普/马瑞·凯耶斯:《冲突法的政策与实用主义》(Michael J.Whincop & Mary Keyes,Policy and Pragmatism in the Conflict of Law,Ashgate Publish Limiting Company,2001,p.27.)。
⑩当案件的赔偿金很少时,诉讼给原告带来的潜在收益也很小,而且这种收益可能低于诉讼对和解的成本差。倘若如此,原告就会选择诉讼而非和解。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Richard A.Posner,Economic Analysis of Law,CITIC Publishing House,2003,pp.568-569.)。
(11)拉瑞·瑞伯斯坦:《通过合同选择法律》(Larry E.Ribstein,Choosing Law by Contract,18 J.Corp.L.,1993,p.254.)
(12)犹如任何契约,和解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存在一个双方当事人认识到依之会增加他们福利的价格。由此,只有当原告在诉讼请求上愿意接受的妥协价格低于被告愿意赔付的最高价格时,和解才有可能,否则,当事人只能进入诉讼程序。而所谓的“和解范围”指的就是双方当事人间最低和解条件或保留价格的重叠区域。同注10引书,第567页。
(13)同注10引书,第602-603页。波斯纳的“比较管理优势说”得到了美国其他一些冲突法经济分析学者的支持和拓展。伊瑞因·A·奥哈拉/拉瑞·瑞伯斯坦:《法律选择中从政治到效率》(Erin A.O' Hara & Larry Ribstein,From Politics to Efficiency in Choice of Law,67 U.Chi.L.Rev.1151,pp.1153,1179-1180,1190-1192.)。
(14)该假设案例参见注8引书,第440页。
(15)详见米歇尔·E·索莱迈讷:《法律选择的一项经济和经验分析》(Michael E.Solimine,An Economic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oice of Law,24 Ga.L.Rev.,1989,pp.68-89.)。
(16)同注15引书,第59页。
(17)所谓的“司法判决错误成本”是指因法院作出错误判决的几率改变了当事人的行为选择而带来的社会成本的增加。现假设,某一类事故的预期成本是100美元,而潜在加害人避免事故的成本是90美元。如果法院准确适用事故责任法,那么,潜在加害人就会采取措施避免事故。然而,如果法院作出错误判决的几率为15%,那么,潜在加害人的预期事故成本就降到了85美元,低于避免事故的成本(90美元)。由此,事故就得不到防止,其结果将导致10美元的社会净损失。同注10引书,第563页。
(1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发布的《关于我国法院审理涉外商事案件适用法律情况的通报》,案件适用法律分布表(表二)。
(19)黄进/杜焕芳:“2003年中国国际私法的司法实践述评”,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2004年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黄进/李庆明/杜焕芳:“2004年中国国际私法司法实践述评”,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2005年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20)科特·G·塞尔赫:“欧洲的国内关系:欧洲之等效于美国的演变”(Kurt G.Siehr,Domestic Relations in Europe:European Equivalents to American Evolutions,30 Am.J.Comp.L.,1982,pp.63-65.)。
(21)据我国学者对2002-2004年间中国法院审结的涉外商事案件的抽样调查表明,在依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择法律的40起案件中,只有1起适用的是外法域法(香港法),1起并用中国法和国际商事惯例,其余均适用中国法。参见黄进/杜焕芳:“2002年中国国际私法的司法实践述评”,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2003年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1页;注19引刊(2004年第7卷),第119-133页;注19引刊(2005年第8卷),第79-93页。
(22)同注18文件,法律选择方法统计表(表三)。
(23)同注19引刊(2004年第7卷),第133页;注19引刊(2005年第8卷),第94页。
(24)转引自索菲尔·吉洛斯:《民事诉讼中的外国法:一种比较和功能之分析》(Sofie Geeroms,Foreign Law in Civil Litigation:A Comparative and Functional Analys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246.)。
(25)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26)按照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222条规定,当事人应该至少有配合法官查明外国法内容的义务。在采取“法律说”的国家,这种做法也很常见。然而,当事人配合法官查明外国法内容与“事实说”主张的由其负举证责任不同。在前一种情况下,法官仍不能摆脱查明外国法内容的最终责任。同注24引书,第127-129页。
(27)塔利尔·埃霍恩:《以色列法院中的外国法查明和适用——了解事实和谬误》(Talia Einhorn,The Ascertainment and Application of Foreign Law in Israeli Courts-Getting the Facts and Fallacies Straight,in Talia Einhorn & Kurt Siehr eds.,Intercontinental Cooperation through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T.M.C Asser Press,2004,p.111.)
(28)例如,在上海海事法院2003年裁决的“美亚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诉香港东航船务有限公司、民生轮船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差代位求偿纠纷”案中,当事双方约定适用英国法,但均未提供英国法的证明。法院最后以“当事人有义务提供约定的英国法律”,却没有提供为由,改用中国法。又如,在“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诉瑞士米歇尔贸易公司”案中,当事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合同争议首先适用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就该公约未规定事项,适用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如该公约和该通则仍未有规定的,则应当适用国际惯例及卖方主要营业地的法律。2004年,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裁定中认为,该案合同约定的补充或替代准据法——卖方主要营业地的法律为瑞士法,但申请人没有在举证期限内亦未在合议庭限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视为其放弃该权利。郑金雄/曹发贵:“不能仅凭涉外仲裁条款未明确约定仲裁机构而认定无效”,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1月4日C2版。
(29)参见王娟:“论冲突规则的性质”和徐鹏:“冲突规范适用初论”,分别载《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上卷,第422-428页;下卷,第263-282页;宋晓:“论冲突规则的依职权适用性质”和杜涛:“‘任意性冲突法’理论研究”,分别载《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05年年会发言代表论文集》,第203-210页;第224-230页。
(30)西蒙·C·西蒙尼德斯主编:《20世纪末的国际私法:进步还是退步?》(Symeon C.Symeonides ed.,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Progress or Regres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0,p.171.)。
(31)同注(13)引文,第1151-1232页。
(32)特瑞沃尔·C·哈特雷:《外国法的主张与证明:欧洲主要制度比较》(Trevor C.Hartley,Pleading and Proof of Foreign Law:The Major European Systems Compared,45 ICLQ,1996,p.45.)。
(33)鲁道夫·B·斯勒辛格:《跨国诉讼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无法援用或证明可适用之外国法的效果》(Rudolf B.Schlesinger,A Recurrent Problem in Transnational Litigation:The Effect of Failure to Invoke or Prove the Applicable Foreign Law,59 Cornell L.Rev.1973,pp.2-3.)。
(34)理查德·芬特曼:《英国法院中的外国法:主张、证明和法律选择》(Richard Fentiman,Foreign Law in English Courts:Pleading,Proof,and Choice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71.)。
(35)同注24引书,第70-72页。
(36)《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1期,第37页。
(37)同注30引书,第6页。
(38)同注21引刊(2003年第6卷),第39页。
(39)彼得·E·奈西:《国际合同的意思自治》(Peter E.Nych,Autonomy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Clarendon Press,1999,pp.113-120.)。
(40)冲突法的正义目标可一分为二:一是“冲突正义”,即冲突规范本身在适用过程中涉及的公正问题,主要是指应依适当的连结点指引,选择与跨国民商事关系在空间上有最紧密联系的法律,以求得法律选择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见性等。由此可见,当事人之间的“冲突正义”与“冲突效率”具有相合性;二是“实体正义”,是指按照冲突规范援引的实体法适用之结果,应能公正地调整当事人之间的跨国民商事权利义务关系。然而,体现当事人之间“实体效率”的法律,并不一定就符合“实体正义”的要求。一般认为,在冲突法中,有关“冲突正义”和“实体正义”之区分,最早由德国著名冲突法学者克格尔提出。杰哈德·克格尔:《祖屋与梦想:传统冲突法与美国改革》(Gerhard Kegel,Paternal Home and Dream:Traditional Conflict of Laws and the American Reformers,27 Am.J.Comp.L.,1979,pp.617-621.)。
(41)徐卉:“外国法证明问题研究”,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04-619页。
(42)[日]谷口安平:《程序正义与诉讼》(增补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