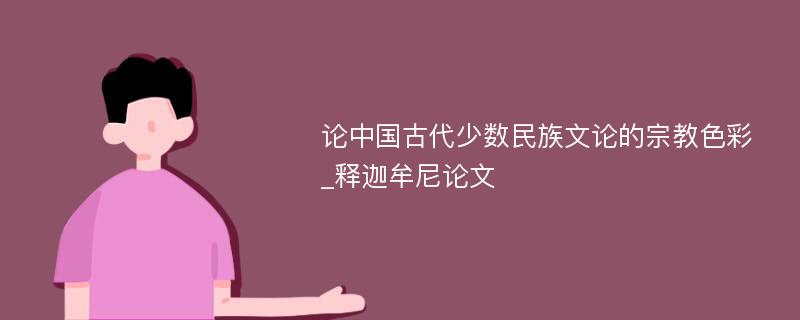
谫说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宗教色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宗教论文,色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对我国古代文论有独特的贡献,是我国古代文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许多有志于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教授、专家、学者,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对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生成发展、存在形态、价值地位等作了充分的肯定,丰富了我国古代文论的宝库。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古代文化著述中所蕴含着的宗教意识、宗教色彩,大家都来不及认真研究、阐释。而马克思说:“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就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的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页。)”。这段话的意思是阐明了宗教作为“颠倒了的世界观”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功能。马克思认为,宗教作为“颠倒了的世界”,其社会功能就是为了给“颠倒了的世界观”提供“总的理论”根据和思想上、道德上、感情上的“安慰”和“辩护”。当然,其它被“颠倒了的世界观”的意识形态(如唯心主义哲学等)也是具有这种功能的。那么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理论会不会受这种“总的理论”和“包罗万象的纲领”的制约呢?其间有没有“它的通俗逻辑”和“道德上的核准”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此古代文论中的宗教色彩如何反映出来?原因是什么?有何价值和意义?这些问题,我以为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故不揣浅陋,写成这篇短文,以抛砖引玉,偏颇之处,诚望方家斧正。
二
民族文论作家没有专门论述宗教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我们所论的“宗教色彩”,多流露于他们有关著述的字里行间,提法不一,说法各异,概而言之,不外这么几种:
1.“佛法”“神灵”说
这类说法多对文学起源而言。这种说法认为文学来自“佛法”和“神灵”,没有“佛法”和“神灵”,就没有文学作品的产生。
第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错(藏族)在著名的《西藏王臣记》中深刻地阐述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审美作用的同时,在《序诗》中流露出“智慧”来自“诸法的法性”的思想。所谓“诸法的法性”,是否可能理解为“佛法”“神灵”的别称。因为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能作为这样的加被者——文殊师利,愿我庄严的喉舌成为语自在王。”“妙音天女啊!愿我速成语自在王那样的智慧无边。”文殊师利即语自在王。大乘菩萨中视文殊师利为智慧之首。要得这位智慧之首的“加持”,要有语自在王的能耐,才能写出美妙的诗篇和文章。而妙音少女是《金刚乘事续部》中一个万能的艺术女神,求助于她给以智慧才能写出有份量的文章(作品)。
这种思想,还流露在下一节诗中:“雪域西藏,如同广阔的天空,它是十二份教之主的最胜幕房。/犹如天马行空的悲智力量,引导出祖孙三法王,以及众视如佛的海生金刚。/还有那通达佛教本末的智者寂护等,他们的恩泽普润了藏疆。/除用这些史实量知一切,还有什么能量度?”“十二份教”即十二部经,一切经均分为契经、应颂、讽诵、因缘、本事、本生、希法、警喻、论议、自说、方广、授记等十二种类。十二份教之主指释迦牟尼佛。“天马”藏文称“日马”,传说太阳神的马有七匹。“祖孙三法王”指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惹巴瑾三位信奉佛法的藏王,他们有三代的祖孙关系。“海生金刚”系红教祖莲花的别称。“寂护”系印度佛教中的天法师,藏王赤松德赞迎请他入藏宏法,莲花生和莲花戒都是经他介绍而传到西藏的。他在这里为什么如此虔诚地讴歌这些“教主”、“法王”、“教祖”、“法师”,“普润了藏疆”的“恩泽”呢?而且断定只有“这些史实”能“量知一切”!窃以为其旨意无非是祈求“佛法”和“神灵”的“加持”,创造一种特殊的写作环境;这种环境无形中笼罩上一层宗教的雾幛。祜巴勐(傣族)在《论傣族诗歌》一文中,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傣歌的产生、发展、分类和特点等文学创作的重大理论问题,书中贯串着作者朴素唯物论的光辉思想,是一部非常宝贵的诗论专著。在论及诗歌的起源时,他断定傣歌来自生产劳动,来自语言文字,这个观点的科学性是勿庸置疑的。但其中又有这样一段文字:
正因为如此,佛祖巡视全球以后,才写出经书《列罗龙》来。没有佛祖一百年的巡视,就不可能有今天长达十二册的《列罗龙》的语言,就没有足够的《列罗龙》的语言,就写不出伟大的《乌沙麻罗》和《大火烧天》的歌来。
这里首先要解释的是《列罗龙》,系佛教经书名,它记载了佛祖巡视地球的情景。列罗是巡视地球;龙是大的意思,句意是巡视地球的大书。记载佛祖巡视地球的经书有两种,一种是详细的记录本共22册,叫《列罗龙》;另一种是缩写本共11册,叫《列图囡》,也叫《小列罗》。《乌沙麻罗》是一部叙事长诗。乌沙,是一个长得最丑、最难看的国王;麻罗,是一个天下最靓的美女。此书被誉为傣族500部叙事长诗之大王,诗书重8斤多、49章约10万行。祜巴勐在这里把佛祖与人类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一方面说“没有人类千万年的活动,就不会有人的语言,停止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语言就必然断源,歌也就死亡了。”另一方面又强调“没有佛祖”和“巡视”,“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语言”,“就写不出伟大的……歌来”。“人佛”能“合二为一”吗?如果“佛祖”是子虚乌有的话,其“巡视”之举又从何而来,这岂不是唯心之推论。可见,前后的提法在逻辑上是有矛盾的。
祜巴勐还用唯心论的观点去考察语言的产生,认为有了语言才有歌谣,有了歌谣才逐步发展成为叙事诗;而且强调有了文字才产生《桑烘》这样的叙事诗。那末,文字又从何而来呢?他又断言是“佛祖送给我们”的。并且阐述:
居住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字都是至高无上的帕召给的。从我们的不可侵犯的圣洁如宝石般的佛教信仰以及道义上讲,我和大家一样虔诚地合掌致谢佛祖赠给我们文字。然而,作为无限忠实的佛教信徒的我,正是为了改造帕召的一再教诲:要忠实、纯正和善良,便积得一身福荫,避免死后落入阴间大油锅,让灵魂升天的谆谆教诫,而才不得不这样从道理上面对现实。……因为人是神造出来的,帕召也是神。
按照他的逻辑推论,有了文字才有诗歌(这个观点还可以讨论,在文字生产之前不是有过有声的诗歌吗?),而文字是佛祖送给的,那末诗歌的祖宗也当然是佛祖的了。而且他认为“人是神造出来的,帕召也是神。”所以他虔诚地“感谢帕召的神灵,为人类的发展兴旺制定了神圣的礼教,礼教带来了光明”。可见,他对“佛法”和“神灵”的顶礼膜拜!
在论述傣族诗歌的特点时,他强调其“不敢超越神佛的礼教的原则,不敢违背金殿王朝的旨意”的特点,“没有这个特点,傣族的叙事诗就成了没有翅膀和尾巴的凤凰了。”最后得出结论:“我们傣族的叙事长诗,妙就妙在塑造了神佛和鬼怪,……这个特点是在《王呵王》和根据佛祖的经书的不可逾越的社会和佛教的约束不必然产生的结果。”而且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的普遍道理”,其崇奉佛法与神灵的程度可想而知了。
2.“因缘写出”说
这种说法也针对文学产生而言,与前面说法接近,两者都试图以禅宗佛理来解释微妙而复杂的文学现象,当然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但两者的视角和侧重点还是不甚相同的。前者似乎强调“外因”,后者则强调“内律”。
这种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哈斯宝(蒙古族),他在批评《红楼梦》时这样写道:
据说,未临欲界之前人心原不动。世上人性本善,只因心动,成为游鬼,只因心动,才变奸佞……自古游鬼并不一定的鬼性,奸佞也无一定的狡计,才子写书也无一成不变的章法,只是因缘相结,便无所不成了。如此说来,作者是深通因缘之道的了。既深通因缘之道,就不必定是游鬼、奸佞,不仅如此,也不必定是智人志士,一派宗师了。因为志士、宗师,文章也可随因缘之道写出,而与作者本人无涉。
所谓“因缘”,系佛教术语。佛家常以事物相互间的关系来说明它们生起和变化的现象,其中把事物生起或坏灭的主要条件谓之为“因”,而其辅助条件则谓之为“缘”。哈氏在这里是认为曹雪芹能成功地塑造林黛玉等人物形象并没有什么奥秘,只是由于作者“深通因缘之道”,靠“因缘相结”,“随因缘之道写出;与作者本人无涉。”否定作者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亲身体验生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不是陷入了唯心论泥坑了吗?
蒲松龄(回族)在《〈聊斋志异〉自序》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他在阐述自己的创作动机时提到:“然五父衢头,或涉滥听,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三生石”传说唐朝李源与僧人圆观友好,圆观和李源约定,待他死后12年到杭州天竺寺相见。届时李源如期赴约,在寺前有一道童说:“三生石上旧精灵,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后来便常把三生石作为因缘前定的典故。这显然是宿命论(相信命运、听天由命)的形象说教而已!
3.“轮回报应”说
这种说法,有时用以阐述写作技巧,有时说明艺术构思,有时论证文学的作用和功能,李贽(回族)在《杂记》中谈到文学作品构思、立意的艺术技巧时主张“举一毛端建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用以说明文学作品反映的思想内容应小中见大。“宝王刹”系佛寺名。“大法轮”指佛教的道法。佛教认为自己的说法能摧毁众生之恶,犹如转轮王的宝轮,故称“法轮”。《大智度论》(佛教书名,简称《智度论》)卷二十五有语云:“转轮圣王手转宝轮,空中无碍;佛转法轮,一切世间及其人中无碍无遮。”道的是此种法法力无边。作者在此用比喻的构思立意,意思是在毫毛的尖端可以建立佛寺,坐在一粒微小的尘埃里也可以运转“大法轮”,意在说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作品的形式虽小,但内容涵量应当很丰富。由于用佛教的事象和语言来比喻,使其思想观点增添了宗教色彩。
第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错(藏族)在他的诗论著名《〈诗镜〉释难》中也有类似提法。他在阐述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和功能时说:“词义表达准确无误的诗学之光,如果不去照亮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整个轮回界,那么,包括天神、人和龙在内的全部三世间就会被无知的黑暗所遮没。”所谓“轮回”系佛教名词,梵文Samsara的意译,原意是“流转”。它本来是印度波罗门教的主要教义之一,佛教沿而用之,注入自己的教义,意思是说芸芸众生在生死的世界里如车轮回旋不止;也就是认为众生各依所作善恶业因,一直在所谓六道(天、地、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牲)中生死相续,升沉不定,有如车轮的旋转不停,循环转化。这说法当然是唯心的。但如果把“整个轮回界”视为“整个社会”,那其内核也还有合理成份的,还是有它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与此说相类似的还有蒲松龄(回族)的“有漏根由”说。他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谈到自己进人创作的特殊境界时,经常浮想联翩,“总爱联想到父亲梦中的瘦和尚真是自己的前身吗?”的时候,认为“盖有漏根由”,“未结人之天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意为:恐怕是有过失的原因在,前身也没有能修成正果,因而随风飘荡堕落,沦落到这般境地。)“有漏根由”系佛家用语,有烦恼谓之“漏”,“根由”均指缘由前因。“人天之果”则指天人之间因果报应关系,因前世未修炼到家,便有“随风堕落”的报应。其实,作者要宣泄的是“孤愤”的心情,抨击人情之冷酷,鞭挞世态之炎凉,表达自我“浮白载笔”的写作动机。用今天的话就是有感而抒发,忧愤出华章。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4.“圆满安乐”说
这类说法多在表述美学理论和追求时说的。第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错(藏族)在《西藏王臣记》中多次用此类词语来阐述自己的美学原则:“……大地转轮王,敦促我作起史文,/如传来王圣旨,命我圆满此使命。”“众生福德犹如春情绵绵孕育中,/出生美满的如意佛子大不同。/手执莲花执掌人间政,/无处引来圆满安乐的芳香气浓。”他表白自己之所以选择“圆满绝妙佳辞”,“运用十善法来治,”乃是为了“获得圆满吉祥,安乐无疆。”“圆满”本是佛教术语,“十界三千之诸法,倏然具跳,谓为圆满。”所言完善无缺之意。这种思维的结果,表达了作者及其信徒向往着人类本性中追求生命快乐的愿望。因为,“正是这种对享受永恒的生命的欢愉的寻求,使现实中无法获得种种精神满足的人们,在宗教的虚幻的诸多许诺中,获得了暂时的解脱,从而也就对宗教产生了一种涌自内心的激情,一种无比强烈的渴望,这是一种宗教快感。”(注:何云波:《论宗教意识产生于人的需要》,《湘潭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应当指出的是:宗教本来是把感情寄托在并不存在的虚无飘渺的幻境之中的,因此,他们所获得的快感是虚假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当然,如果所寻求的“圆满吉祥、安乐无疆”的愿望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凡此种种,我以为都是宗教色彩在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中的自然流露和特殊反映。
三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民族古代文论何以反映出如此浓烈的宗教意识、宗教色彩?而且以西藏、云南等大西南的周边地域为甚?这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在渗透佛教文化的土壤上生成、发展起来的民族古代文论浸润上了宗教的色彩,那就不足为怪了。上述实例告诉我们,这种宗教色彩属于“较早阶段的宗教”,它“是一种艺术极其感性的表现的宗教(注: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33页。)”。说明了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进行研究,揭示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
写到这里,我们用得着文学批评大师普列汉诺夫的一个论断来论证其价值之所在,他说:“那些表明艺术上往往是在宗教强烈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事实,一点也不能破坏唯物史观的正确性。(注:普列汉诺夫:《论艺术》第105页。)”用唯物史观来考察那些宗教色彩,我们发现这些民族古代文论家们有自己特殊的审美体验和表达方式。他们把“审美的狂喜和宗教的狂热联合在一起”,试图从“审美价值与宗教狂喜的价值(注:克莱夫·贝尔:《艺术》第62页。)”的结合上寻求思想感情和精神上的满足以及理论根据,以便引导、促进文学创作的发展。他们的主观愿望当然是好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注: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这种“幻想”和“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充满了浪漫色彩,它能启迪人的联想力、想象力和创造性,这不仅对古代作家,而且对现代作家的艺术虚构创作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