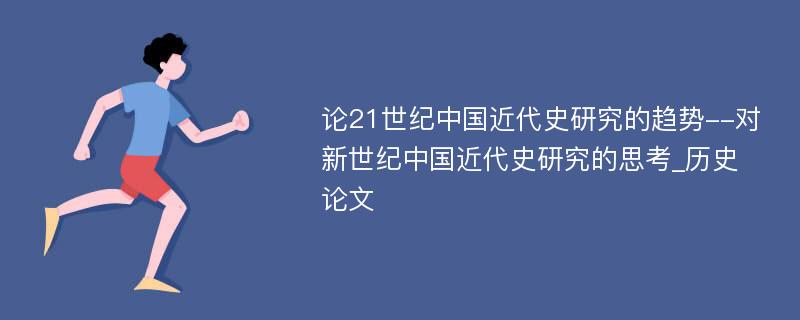
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笔谈——关于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新世纪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与前辈学者的引导分不开。刘大年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以经济史为突破口(注:刘大年先生发表于《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提出“应当狠抓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他把经济史看作是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内容”来寻找突破口的。),此后经济史的研究方兴未艾。章开沅则倡导社会集团史的研究,他指出:“在资本家个人和资产阶级整体(或其某一阶层的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等)的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所得结论可能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合实际一些。”(注:章开沅:《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此后,以商会史为代表的社会集团史的探讨蓬勃开展,推动了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深入发展。但是,毋庸讳言,近代史的研究也还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甚至存在着一些盲区。在我看来,下层社会的历史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以致于下层史“下沉”到了史海的底层,急需学者们关注的目光下移。《史学月刊》组织“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走向”的笔谈,藉此机会,笔者愿在此谈谈个人一孔之见,供学界同仁讨论。
一 下层史:重构老百姓自己的真实故事
下层史是一般民众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一般民众或普通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教育上,往往都处在社会的底层,举凡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日常生活等都应该纳入研究者的视野,通俗地讲,我们的研究应注重重构老百姓自己的真实故事。只有把老百姓的故事讲清楚了,才能揭示一部真实的中国近代史。
但是,重构并非易事。虽然无论在哪个朝代、哪种类型的社会里,一般民众均构成社会的主体,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弱势地位,不仅他们自己并不掌握主流话语权,而且记载他们历史的文献资料也很少,这就给以史料说话、着重实证研究的历史学出了一道难题:重构出来的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究竟是下层社会的历史、还是虚无缥缈的历史传说?这的确是一个富于挑战性的问题,需要历史研究者借助新的思维、新的技术和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去找寻下层社会的历史。“许多底层历史很像古代的犁迹。它似乎随着许多世纪前犁地的人一起杳无踪迹了。但每位航空摄影家都懂得,在一定的光线和从一定的角度下,被久已遗忘的田脊和犁沟的影子还可以看得到。”(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下层史研究者就应该像那些善于运用光线与角度的“航空摄影家”,这样重构出来的老百姓的故事就一定是真实的历史存在。
下层史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性的范畴,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内涵,在阶级社会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如奴隶社会中的奴隶、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等,都栖身于下层社会,他们的历史自然是一般意义上的下层史。除此之外,下层社会中还有很多特殊的群体,透过这些特殊的群体,也能够有效地从某些侧面观察到民众的观念与行为。如19世纪美国历史上的黑人、华工,就是一些特殊的下层群体,他们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于以白人为主体的上层史。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特殊群体,如流民、手工业者、学徒、人力车夫、码头工人、优伶、乞丐甚至川江航道上的船工(注:据曾亲历过川江船工生活的章开沅先生所述,船工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船工之间分工明确、一条船上一般由驾长、桡工、喊号子的、纤夫、伙夫、杂工等人组成,驾长的薪资四倍于纤夫、桡工三倍于纤夫、喊号子的二至三倍于纤夫,他们喊出的号子回荡在山谷间,纤夫伴着他们的号子,彼此协作,往往能起到提高效率并降低纤夫劳动强度的作用,其余人等待遇较低。)等,如能分门别类地对他们进行系统研究,必将展示出下层社会历史的不同画卷。中国近代史上还存在着一些下层社会组织或团体,如秘密社会组织(土匪、流氓、帮会等)、行会(以及由行会转化而来的同业公会),也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研究的拨乱反正和深入发展,下层社会的历史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蔡少卿等对中国近代秘密社会的研究、乔志强等对华北乡村社会的研究(注:乔志强先生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对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研究相当全面,涉及到乡村婚姻、家庭、宗族、物质生活、消费、社会风俗、民间信仰等各个侧面,是迄今为止研究近代华北乡村社会史最为全面系统的成果。)、赵世瑜等对民间庙会的研究、池子华等对中国近代流民的研究,还有一大批学者对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等等,无不显示出下层史研究的良好势头。一些学术机构或刊物也开始关注下层史的成果,如《史学月刊》开辟专栏发表乡村史研究的文章,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黄宗智主编的连续性刊物《中国乡村研究》,这些都为下层史的研究创造了较好的学术氛围。但是毋庸讳言,相对于老百姓丰富多彩的故事,上述研究不过是冰山一角,还需要学者们下大力气去进一步挖掘。何况现有的研究中,还有值得我们思考和改进的地方。
二 下层史何以“下沉”?
的确,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改变下层史沉入史海底层的状况。这既有历史传统、研究范式上存在的问题,也有资料搜集、运用与解读上存在的客观困难。
从历史传统看,封建传统史学局限在“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史的圈子里,史官修史的目的服从于封建皇朝的需要,并且很可能是为统治者的实际应用而撰写。二十四史是按照王朝体系划分的,除了一些为封建伦理殉道的节妇、烈女外,几乎看不见民众的影子。这种史观在晚清学者身上仍然存在,不仅使我们看不到晚清以来的近代历史中下层史的位置,也给我们今天探寻下层史造成了资料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史学忽视民众史的不足,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但在研究范式上,下层史被纳入到阶级斗争(或民众运动,如农民起义、工人运动)分析模式中,普通人只是作为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因素来叙述的,并且构成整个事件史的一个有机部分。作为对事件史的探讨,这种分析方法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模式下的民众史,并非真正的(至少也不是完整的)下层史,民众只不过是事件史或政治史中的一个角色,服从并服务于政治史的需要,相反,对于那些独立于政治领域之外的广泛存在的未知领域,缺乏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还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问题,为了强调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写成了一部农民战争史或革命运动史,而所谓的农民战争史又理所当然地演变成了“农民领袖史”,于是,中国革命史(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研究走入了一个怪圈:“过去的历史看不见人民群众的活动,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帝王将相;过去的历史看不见农民战争,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统治阶级的活动;过去的历史看不见经济基础,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政治制度;过去的历史专讲政治沿革,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来历不明;过去的历史专讲王朝始末,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一字不提;过去的历史不讲或少讲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现在我们就还他一个不讲各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注:剪伯赞:《史学理论》,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其实,这种矫枉过正在西方社会史研究中也曾经存在过,早期西方学术界认为,“社会史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特别是关于穷人运动(‘社会运动’)的历史”(注: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这种下层史被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社会主义运动史联系起来了,老百姓的观念、信仰、行为方式、日常生活等重要内容得不到充分反映。
我们并不否认农民战争或革命运动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不应忘记历史的进步都是在相对稳定时期渐进性地实现的,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角色并不总是体现在农民战争或工人运动之类的重大事件中,更多地是体现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这种相对独立于政治史、事件史之外的、反映下层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婚姻家庭、生老病死的历史,更能体现社会经济自身的进步状况以及人民群众对这种进步所起的作用,这是不是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呢?
当然,下层社会的历史之所以“下沉”,并非完全由于历史传统与研究范式上存在的问题。客观上讲,下层史在资料上存在着许多难题,首当其冲的就是资料不足。如前所述,下层民众并不掌握主流话语权,他们的思想、行为难以完整地在历史文献上反映出来,纵有当时的学者文人抱着同情民众的态度,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或编成调查报告、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但都比较分散,需要下大力气去搜集、整理,这些都给研究工作造成了相当难度。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作为社会史主干的普通人,要么被遗忘,要么被视为鲁钝,是上等人手中的玩物”(注: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看来,有志于下层史研究的学人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有坐十年冷板凳的意念与耐心,只有长期坚持下来,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因为“许多底层历史不会立即产生结果,但需要精心、费时和花费高昂的研究。它不像在河床里捡钻石,而更像是需要大量资金和高技术的现代钻石矿或金矿”(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238页。)。
三 下移:下大力气挖掘下层史
看来,下层史并非不可为,只是不易为。套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有的青年学者提出下层史是需要“打捞”的历史(注:苏全有:《后文革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状况忧思录》,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页,“研究生论坛”论文。),非常贴切。“打捞”沉入史海底部的历史,涉及到许多复杂的技术与技巧,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将关注的目光下移,群策群力,共同将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首先,需要研究者将关注的焦点下移到普通民众身上。就历史人物研究而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已经成了高悬于口头的空洞口号,在这一口号下,大量的研究却集中在精英人物身上,翻开近代史研究论文索引,印入眼帘的人物研究多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精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精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精英,以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精英。他们的思想、活动及对历史发展的影响都成为研究的重点,相形之下,民众的历史黯淡无光。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一批学者将关注的焦点下移到普通民众身上。在下层历史研究中,社会史研究者承担着重要角色。社会史研究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即通过普通人的经历和感受,而不是通过杰出活动家进行研究。在西方社会史学界,人们普遍地把社会史限定在对社会一般成员,而不是精英集团中的个人研究之上,人民大众及其日常生活的框架——家庭、生产品、社区生活、生与死——都必须加以研究。(注: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
其次,在空间上,需要研究者将目光由都市转向乡村。诚然,都市社会并不是上层社会的代名词,乡村社会也不是下层社会的同义语,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特征非常明显,都市主要作为上流社会的聚集地,乡村则集中了更多的贫民和平民,都市经济更多地具有现代经济性质(近代工商业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相反,乡村经济则更多地属于传统经济(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将目光由都市转向乡村,多少具有由上层史转向下层史的意义。当然,城市史中同样具有下层史的领地,尤其是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急剧变动的时期,大量农民离村进入城市,他们大多汇入城市下层社会,成为苦力、帮工、手工业者、乞丐、娼妓等,有些甚至散落街头成为黑社会搜罗的对象,对这些群体及其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市井文化加以研究,也是下层史需要深化的领域。但是,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者大多在城市化的视野下,着重探讨近代城市的形成、地位、作用,分析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及商会等近代社团的形成,近年来,这种状况正在逐步改变,有些研究的触角已开始深入下层史,如王笛对成都街头文化、茶馆文化的研究等,就颇具开拓性,这也更加激励城市史研究者在探讨近代城市化进程时,多将关注的目的投向城市下层群体,毕竟下层史的研究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依靠少数学者难竞其功。
经济史在下层史的研究中理应作出更大的贡献,正如罗素所言:“和其它各种更古老的历史学相形之下,它具有的优点乃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普通人身上,而不是集中在突出的个人身上。”(注:(英)岁素著,何兆武,肖巍,张文杰译:《论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但是,经济史的优点似乎正在逐步削弱,在西方经济学的冲击之下,经济史学者转向以更宏观视野探讨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走向,而对普通老百姓的经济生活如生产、消费等微观层面注意不够。经济史研究者也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对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现代部分(如现代工商业)投注了较大的精力,而对传统部分(如农业、手工业等)的探讨则略显薄弱。因此,对于经济史研究者而言,如何兼顾宏观经济走向与微观经济实态、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结合,是经济史研究者目光下移时应该考虑的问题。
再次,研究时段上的下移,下层史的研究需要突破一些人为的分界线,将1840年以来至20世纪的下层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由于高校长期以来的教学习惯,中国近代史被限定在1840~1949年间,但在研究工作中,学者们已不再局限于这个界限,他们在专题研究中纷纷突破这个时间点,将1840~1949年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这更加有利于探讨历史变迁的内在延续性。其实,近代史研究者还可以在时段上进一步下移,将20世纪的历史作为一个长时段进行整体观照。在我看来,所有历史分界线都是人为的,都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为标志的,这种划分是为了使历史研究更好地彰显不同时段的特点,掌握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如果过分坚守,画地为牢,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以重大事件为标志的分界线,总是与政治史有着较多的共时性,相反,与经济史、社会史则并不表现为必然的共时性,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与阶段并非总是与那些曾经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同步,它更多地表现为渐进性与长效性。下层社会的历史尤甚,一方面,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化传导到下层,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另一方面,下层社会经济往往表现出独立于上层社会的特点,其运动惯性也不会因为这些人为的分界线戛然而止,虽然有时可能由于上层建筑领域的强制而暂时中断,但它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生命力足以使它在条件许可时在更大规模上“复活”。如果以此分界为研究时段,很可能看不清社会经济演变的完整过程,如笔者在对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的探讨中,曾将20世纪初年在若干农村地区、若干行业中出现的手工业的发展进程总结为“半工业化”(注:参看笔者拙文:《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以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这种“半工业化”由于受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国内外战争的影响而被迫中断,但是中断也许并非必然意味着失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乡镇工业、尤其是江浙乡村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半工业化”的延续与深化(注:2003年11月在湖州召开的“中国江南市镇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与会学者曾对该市的织里镇进行了粗略的考察,织里镇以童装生产而闻名全国,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穷则思变的织里人挣脱束缚,操起一把剪刀、一管尺,从事起了家庭刺绣品加工,并凭着一根扁担二只包,踏上了闯市场的艰辛创业之路。在这一时期,织里的家庭工业也由最初的刺诱品加工,过渡到后来的香港衫,织棉缎棉袄,最终定位在童装生产上,2002年末,织里民营总产值达113.56亿元,在短短的20多年里走完了从家庭工业到“半工业化”再到工业化的全过程。参看湖州师院赵玉阁教授提交的学术论文:《浙江织里民营企业发展的特色及其档次提升》。),这种从家庭工业——“半工业化”——工业化的道路,很可能就是中国乡村工业化模式之一。在1949年之前,这只是一条可能的、但却没有走完的道路,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这种模式变成了现实,这种模式只有在研究时段上下移时才能诠释出来。
下层史的研究还有赖于资料的发掘与整理。资料的有无与多少决定着下层史研究的进展,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下层史,可供使用的现成资料并不多,需要在资料上下一番大力气:一是非主流报刊、杂志的挖掘和整理,这类报刊、杂志主要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较为贴近大众生活。二是私人笔记,家传家谱、野史资料的搜集,这类文献中也可能保存着较多的下层史资料。三是民间传承资料,存在于民间的口耳相传下来的许多传说、故事、神话,可能为下层史的研究别开一番史料的天地,将这种传承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有助于重构老百姓自己真实的故事,当然,难度也是很大的,需要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去整理与诠释,如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与解释方法。下层史的研究还有赖于良好的、宽松的学术氛围,学术刊物在这方面肩负着不可推却的责任。为了鼓励中青年学者开展下层史研究,学术刊物对这类文章不必求全责备,只要在观点或方法上有所创新即可。
总之,拓展下层史的研究是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惟一的。我们希望近代史研究者的目光下移,多关注下层社会的历史,绝不意味着忽视其他方面的研究,只是希望学术界应该在以后的研究中处理好如下关系:在重视精英史的同时,不要忽视民众的历史;在开展城市史研究时,也要关注乡村史;在研究近代工商业时,也要深入拓展农业史、手工业史等传统经济的研究,最后,在专题研究中突破现有的分界线,将20世纪作为一个长时段进行探讨。做到了这些,我们的中国近代史才能称得上是一部完整的历史,是一部“走出了近代”的中国近代史,是为吾辈之愿,亦为吾辈之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