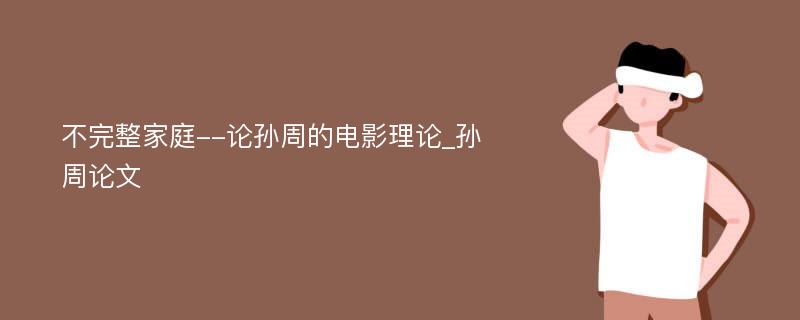
残缺的家庭——孙周电影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庭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04)01-0036-04
中国第五代导演按创作题材大致可分为偏重乡村与偏重城市两大类,前者的代表是陈凯歌、张艺谋,后者的代表是黄建新、夏刚。而孙周似乎是个例外,他并没有在乡村还是城市这个题材问题上纠缠不清,举棋不定,而是直接将导筒指向了社会最基本的组成细胞:家庭。孙周并不多产,迄今执导的电影作品只有5部,即1987年的《给咖啡加点糖》、1989年的《滴血黄昏》、1992年的《心香》、1998年的《漂亮妈妈》和2002年的《周渔的火车》,每一部电影都涉及到了家庭问题。
一
中国的社会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作坊相结合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对此,梁启超说道:“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1]正因为如此,相对于以个人为本体的西方社会来说,中国人的家庭意识更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家庭是温馨的港湾,是心灵的避难所,是疲惫灵魂得以休息的驿站。所谓“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即是对此的最好指认。但是,孙周电影中的家庭并没有充满温馨与浪漫的氛围,相反却是残缺不全,寒风凛冽。
具体说来,家庭在孙周电影中表现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残”,即由于各种原因,夫妻双方只好离婚,从而留下一个破碎不全的家庭,所谓的夫唱妻合,所谓的举案齐眉,所谓的琴瑟调和都不复存在。《滴血黄昏》、《心香》和《漂亮妈妈》三部影片中的家庭均是破碎不全的。富有意味的是三部影片都没有直接表现离婚的情景,而是把这种情景置于电影前史中。也就是说,当影片开始时,离婚大战已经成为过去,但是我们仍然能感受到那种被影片所遮蔽的离婚大战的硝烟和战火。三部影片的叙事重点都放在了家庭的破碎给孩子心灵造成的创伤上。《滴血黄昏》中的陆一因父亲离婚而失去了应该享受的父母关爱。虽然陆一跟父亲学打猎枪,但是陆一的心情却是惶恐不安的;虽然父亲也曾经带着陆一去坐空中缆车,但是那仅仅是出于一种作为父亲的应尽的义务而非出自本能的疼爱;陆一放学回家独模仿母亲的样子做菜,而与此同时,父亲却在和“新人”谈着恋爱,陆一只好暗自流泪。不过,陆一所受的最严重伤害莫过于被绑架了。他显然成了父母离婚最大的牺牲品。如果说陆一在父母离婚后还有幸能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话,那么,《心香》中的京京在父母离婚后似乎连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权利都没有了。他被送到了孤居的外公家。作为位噪一时的京剧演员,外公早年丧妻,与信佛的莲姑相依为命。京京俨然扮演了一个“闯入者”的角色,因为他的来到打乱了外公与莲姑平静的生活。京京与外公之间无疑存在着一定的鸿沟。尽管在莲姑的开导下,京京与外公能够做到相亲相爱,但想彻底填平两人之间的鸿沟显然是一件难事。最后,京京要回到了离异后的母亲身边,但无论结果会怎样,这么来回折腾,肯定会给京京的脆弱心灵造成难以抚平的伤痛。与陆一和京京不同的是,《漂亮妈妈》中的郑大是个失去听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残疾儿童,忍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打击。作为生理上的打击,他无法用正常的语言显示自己的存在,为此,给自己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母亲孙丽英为训练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受尽了苦头。作为心理的打击,郑大到处受到人的歧视,受到同学的嘲笑。富有意味的是,作为郑大的父亲,郑佩东对此漠然置之,不闻不问。一个很明显的镜头是,孙丽英带着郑大走在街上时,开着出租车的郑佩东看见后微笑地摇摇头,说道:“瞧,这娘俩!”与陆一和京京不同的是,郑大的父母虽然离婚了,但他还有着母亲的精心的呵护。尽管如此,郑大仍然抹不去心灵的阴影。
另一种表现是“缺”,即作为男女二人组合的家庭从来没有在影片中出现,男女双方只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个体形式而存在,家庭只能处于一种缺失状态。《给咖啡加点糖》中的刚仔、小弟和《周渔的火车》中的周渔、陈清、张强等人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他们的身边没有父母,不知道他们从何处来,也不知道到何处去。他们也试图努力组合成家庭,但都未能如愿以偿。在繁华的广州大都市闯荡的青年广告商刚仔寂寞之余,与“上个世纪的姑娘”林霞谈起了恋爱,但是,林霞却迫于农村换亲习俗的压力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对刚仔真挚的情感,悄然离开了刚仔。可以想象,林霞即使回到农村成立了家庭,也不是健全意义上的家庭,因为靠换亲关系组成的家庭实在无真情实感可言。周渔在两个男人之间不停地游走,最终也没能找到情感的归宿,组成男女的二人世界。
在孙周的影像世界中,由于家庭是残缺的,因而,从主题话语上讲,人物心态大都可以从孤独和无奈的话语角度得到很好的解读。
孤独是一种最深刻、最难耐的生命体验,因为人在孤独感中最能感受自己作为一种个体真实的存在。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卡姆(Emile Durkheim)用“迷惘(Anomie)”一词来描述这种感受。梵·高、茨威格等人的自杀和尼采、荷尔德林等人的精神失常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孤独对人的影响。《给咖啡加点糖》中的刚仔尽管在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成了个体小老板,但是,这并不能弥补他精神上的失落和茫然,孤独始终像狼一样地追逐着他。他泪眼朦胧地望着陌生、混沌、充满躁动和喧哗的都市,心绪一如大街上那个被踢来踢去的罐头盒,空空的、轻轻的。他说的话很有意思:“当生活贫困的时候,为生活痛苦;当生活不苦的时候,又不知道干什么。”于是,他开始浪漫的精神漫游。他用照相机发现了林霞。对于孤独的刚仔来说,林霞昭示出的分明是一个美轮美奂、充满无限诗意的美妙世界。但这一切只能放置在照片中,放置在刚仔的想象中。当刚仔试图把它变为现实时,它立刻就烟消云散,消失殆尽。他终于认识到:“夫妻俩躺在床上,看着结婚典礼时的录相,那种充满青春魅力的动态美,是化妆品和照片所能给予的吗?不。”刚仔与林霞爱情的幻灭,说明传统的爱情/糖并不能稀释现代都市生活/咖啡的苦涩。刚仔的形象反映了那些突破传统行为模式后还没有建立起现代价值观念的人的孤独状态。刚仔的孤独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实现理想的爱情和家庭,《漂亮妈妈》中的郑丽英的孤独却是因为爱情和家庭实现后变得支离破碎。作为一个离异的女性,她为郑大撑起了一片灿烂的晴空,而自己却地默默地品尝着孤独的滋味。她孤立无助,处处受挫。卖书被抓,卖报纸被偷。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孙丽英在郑大将助听器损坏后试图为他再买的情节。再买助听器的过程是那样的艰难,为此,她受到了贾老板的非礼。孙丽英要再买助听器的执着和坚强,很容易使人想起《秋菊打官司》(张艺谋,1992年)中执意要讨个说法的菊豆和《二嫫》(周晓文,1994年)中执意要卖回大彩电的二嫫。坚强就意味着孤独,孙丽英就是这样。她只能从郑大的成功中得到一定的解脱。影片结尾时,她看着郑大走进教室而绽放出的灿烂的笑容于是就成了世界上开得最美丽的花朵。
无奈是人们面临困难时无计可施或者迫不得已做出某种选择时的心态,这是一种充满着困惑和尴尬的生存状态。《给咖啡加点糖》中的林霞即是如此。她面前的是两种选择:一种是遵循自己的真情实感,与刚仔成家;另一种是遵循传统的换亲习俗,回到乡下,与自己不爱的男人成家。林霞在这两种选择之间,虽然最终她选择了后者,但仍然不无安慰地对刚仔发誓说:“我回来,我答应你,我一定回来。”这说明,她的心态是充满矛盾和困惑的。不过,最能说明无奈心态的还是《周渔的火车》中的周渔。她虽然像条鱼,在两个男人之间肆意地游走,但深深的无奈感死死地将她困住。陈清是一个“每天生活在梦里”的诗人,性格忧郁。周渔通过一首关于“仙湖”的诗爱上了他。但是,她对陈清无微不至的爱恋和顺从,使她觉得自己失去了自我。此时,她遇到了粗犷且具有男性魅力的兽医张强。于是,爱情之舟失去了方向。她时而与陈清缠绵不已,时而又与张强同床共枕。最终也未能做出理想的选择。却不幸地和汽车一起坠下悬崖,像一根抛物线似的落入水中。对此,导演孙周说道:“周渔的爱情就在那列火车上,承载着她的矛盾,欲望和对爱的幻想,经过大大小小的车站,卸下一些,又装上一些。”[2]
家庭是残缺的,人物的心态是孤独和无奈的,因而导致孙周的电影呈现出一种压抑和沉闷的风格,有时简直令人压抑和沉闷得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影片遭受批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比如,针对《滴血黄昏》,有人认为:“这是在商业文化大面积覆盖的境遇下,孙周做的一次万般无奈的妥协,因此尽管其中藏着一个导演的无限辛酸,煮出来的却仍是一锅夹生饭。”[3]针对《心香》,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暮气沉沉的影片”:“孙导演年轻,可拍出这么暮气沉沉的影片,这么早地由俗入佛,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的悲哀。整个影片的境界就是死,就是无差别的快感、子宫迷恋等弗洛伊德观点。一位新潮导演拍片子象是七八十岁的导演在作人生总结,使我感到非常吃惊。”[4]
二
孙周的电影在家庭模式上的残缺昭示出鲜明的文化意义,这便是传统和现代的冲突。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的市场经济、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过渡、变迁和转换的过程中。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必然呈现出一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冲突的状态。这里所谓的“传统文化”是指作为主流的儒家文化,这种文化讲究秩序、稳定和规范,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是对家庭观念的重视。不管是韩非子所说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还是董仲舒所说的“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我们都不难从中看出“家庭”在社会整个秩序中的作用。但是,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对个体的成长形成禁锢和障碍。历史流传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家训、家范无一不在强调长者和尊者的权威,强调幼者和卑者的顺从。借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就是强调“超我”对“本我”的压抑。这样,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就被消解在家庭的秩序中。但是,家庭又以其脉脉的亲情和温情让人们浑然不觉。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们积极倡导讲究个体意识和个性解放的现代文化。鲁迅、胡适、钱玄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纷纷向消解个性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李大钊就十分悲愤地说道:“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生活无一处不感到孤独的悲哀、苦痛;什么国,什么家,什么礼防,什么制度,都是束缚各个人精神上自由活动的东西,都是隔绝各个人之间相互好意、同情、爱慕的东西。人类活泼的生活,受惯了这些积久的束缚、隔绝,自然渐成一种犯忌、嫉妒、仇视、怨限的心理、这种病的心理,更反映到社会制度上,越颇加一层黑暗、障蔽,把愉快、幸福的光华完全排出,完全消灭。”[5]这里所说的,简言之,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人的独立性”。《给咖啡加点糖》中的刚仔身处中国社会改革的前沿地带。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而又充满诱惑力的世界,经过一番拼搏,他确立了自己的事业基点。他虽然发展了个性,找到了自我,但并没有完全割断身上与传统文化联系的脐带。于是,他想与林霞成立家庭,并从中得到慰藉。对此,导演孙周认为,在刚仔身上“融合着传统文化的亲源性和相对于我国落后地区而言的经济发达地区所产生的现代意识的两种文化现象。拒绝传统又无意识地继续着传统的两种极端,使他产生了一种新的精神的饥渴,即希望从繁忙的社会生活中相对地得到解脱。”[6]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在林霞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换亲从大的方面讲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习俗,从小的方面是父母为她定下的东西。当她在广州的繁华都市中遇到刚仔后,两人产生了恋情,对她来说,这是个人的自主选择。在影片中,父母是缺席的,如果说他们在场的话,充其量不过体现为送到林霞身边的信件。但就是这信件,就足以让林霞痛苦不已,并最终只好放弃了自己的真爱,回到乡下。《周渔的火车》中的周渔游走于两个男人之间无非是想找到自我,找到自己的独立性。拿导演孙周的话就是:“她的奔忙先是为了一个男人,然后是两个,最后,是为了她自己。”[7]“为了她自己”无非是指想鱼和熊掌兼得:既想得到像诗歌一样的陈清,又不愿放弃像通俗读物一样的张强。但是,这种观念和做法,必然受到“一夫一妻”的传统理念强有力的冲击。不是吗?当她对陈清说,自己还有一个男人时,陈清坚定地说,不可能,周渔只爱我一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此昭然若揭。
如果说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刚仔、林霞、周渔等“围城”之外的人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在孙丽英等“围城”之内的人身上体现得就比较隐蔽。随着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离婚率有所增长。离婚从某种角度上讲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表现。它除去了不和谐的婚姻对个体的压制和束缚,使男女双方获得了各自的生活空间。但是,在目前的中国,新的家庭道德规范尚未完全建立,人们对离婚仍然持比较保守的态度,认为离婚是不光彩的事,所以,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所难免。《心香》中的外公一直对京京父亲牢骚满腹,数落不停,可当他知道女儿女婿离婚之事后,就一言不发了。而作为新一代的京京却不以为然,认为:“好合好散,这种事现在电影里多着啦。”在《漂亮妈妈》中的孙丽英在离婚后独自一个哺养着郑大,表现出顽强的个体意识,同时也受尽了种种磨难。贾老板在对她非礼时就明明白白地说,反正她是离了婚的人了。
三
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当然会引起导演的关注。在中国电影史上出现过很多涉及到家庭题材的作品,如蔡楚生和郑君里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年)、费穆的《小城之春》(1948年)、水华的《林家铺子》(1959年)、谢铁骊的《早春二月》(1963年)、谢晋的《天云山传奇》(1980年)、张艺谋的《菊豆》(1990年)、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2002年)。但像孙周这样在自己所有的影片中都涉及到家庭问题的导演,恐怕并不多见;而在自己所有的影片中都能从残缺的角度透视家庭问题的导演,更是少之又少。孙周为何对家庭的残缺问题如此的偏爱?无外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原因。
从外部原因上说,是因为迅速发展的社会变革导致家庭不稳定的因素日益增加。社会变革就意味着机会增多,诱惑增多,传统家庭的稳定系数随之降低。据统计,1987年,全国离婚总数是28.5万对,站人口总数的0.30%,到了1996年,离婚总数增长到113万对,站人口总数的12%。这种现象无疑会引起导演的注意。
从内部原因、同时也是最根本原因上说,是因为导演孙周的个人家庭生活发生过一次变故。在此,我决不是妄加述说,证据有二:一是有人在评价《滴血黄昏》是说道:“影片沿袭了孙周一贯思考的基本主题,切入点仍是家庭问题。由于1987年前后他个人家庭生活的一次变故,因此切入点更为直接地放置在年轻家庭的裂解与重新组合中孩子的创伤上。”[8]二是在一篇关于《心香》访谈的文章中,有人问他为什么几部影片都涉及到孤独、离异的主题时。他沉吟半晌,回答道:“可能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吧。”[9]注意,1987年恰恰是孙周手执导筒的开始,个人家庭变故这种独特而真实的体验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孙周的电影艺术创作。
标签:孙周论文; 给咖啡加点糖论文; 周渔的火车论文; 漂亮妈妈论文; 滴血黄昏论文; 孙丽英论文; 林霞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