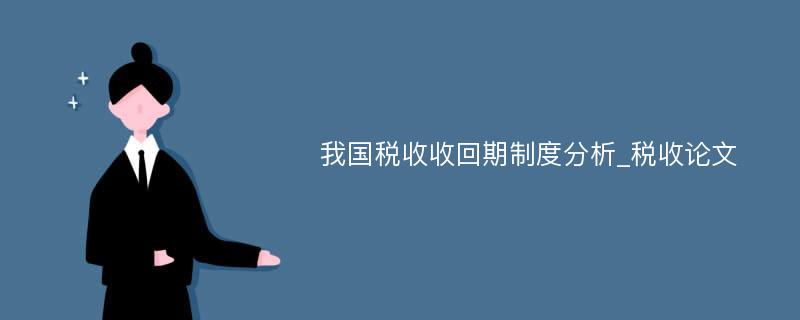
我国税收追征期制度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收论文,制度论文,我国论文,追征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5年。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追征期制度的设定,对税务机关的权力形成很大的限制。但追征期究竟属于消灭时效还是除斥期间,追征期的起算点如何确定,追征期届满的法律效力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加以明确。否则,就会在实践中引发歧义,削弱追征期制度功效的发挥。
一、税收追征期的性质
(一)税收追征期:核定期间还是征收期间
我国税法只规定了统一的追征期,但在德国、日本、美国,由于税法有核定程序和征收程序之分,因此税收时效也被分成核定时效和征收时效两种。例如,《德国租税通则》第169条专门规定核定期间,而第228条则专门针对税收债务关系的请求权规定纳付时效。又如,《日本国税通则法》第70条专门规定核定期间,其中既有一般核定期间,又有特别核定期间,而第72条则专门规定征收权的时效。此外,日本地方税法、关税法等都明确规定核定期间和征收期间,只是期间的长短有所区别而已。再如,《美国联邦所得税法》第6501条规定,该法所适用的税收应于申报书提出后3年内课征。如果以印花纳税,则于纳税期限开始后3年内征收。这其实是一种核定时效。至于征收时效,该法第6502条规定,在核定期限内课征的税收,应当在课征之后6年内以扣押或司法程序征收。如果纳税人与稽征机关协议延长征收期限,则遵循协议。除了上述国家之外,我国台湾地区的税收时效制度也属于这种类型,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21条和第23条即分别规定了核定期间和征收期间。①
在税收程序法中,税收核定和税收征收确实有区别的必要。一般情况下,除非纳税人主动缴纳税款,否则,都必须先经过税收核定,然后才能具体实施征收。我国税法虽然没有对此加以明确区分,但实际的操作过程也在遵循这一规则。例如,无论是采取税收保全措施还是强制执行措施,必须先行确定的是,纳税人是否欠缴税款,以及欠缴多少税款。如果没有税收核定作为前提,征收行为就会失去依据。既然如此,我国税法中的追征期究竟是核定期间还是征收期间?如果将追征期理解为税收核定期间,可能带来的问题是,税收经过核定后,其具体征收的过程将毫无期限限制。如果将追征期理解为征收期间,那么,超出征收期间的核定事实上将无法得到执行,因此也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将追征期的效力扩大至核定和征收两个阶段,上述问题虽然得以解决,但是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即当税务机关在核定期间的最后一天作出课税决定时,其可用于征收的时间已经十分有限了。
在我国刑事处罚及行政处罚领域,也存在相关的时效制度。不过,法律都没有区分处罚决定时效与处罚执行时效。这说明,税收追征期制度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个别,而是在我国公法领域普遍存在。总体来说,我国税法应当克服目前过于简化的缺点,通过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逐渐予以细致和完善。因此,将来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时应将核定期间与征收期间分别加以规定,这样可以在根本上解决目前的问题。至于核定期间和征收期间如何衔接,可参考《日本国税通则法》第73条及《德国租税通则》第231条的做法,将征收期间从法定纳税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起算。如果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收核定,征收期间中断,则从税收核定书指定的缴纳期限届满之日重新起算。如果税务机关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税收核定,税收债权因时效届满而消灭,征收期间也就失去了意义。不过,在法律修改前,笔者认为追征期只能被理解为核定期间。至于征收期间,暂且沿袭传统思维将其理解为不受限制。
(二)税收追征期:消灭时效还是除斥期间
在法律上,为了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设有消灭时效或除斥期间的规定。税收的追征期究竟是消灭时效,还是除斥期间,我国法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一番探讨。
如前所述,在德国、日本、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核定期间和征收期间是分立的。由于征收期间主要针对税收请求权,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立法,都认为其属于消灭时效。至于核定期间,人们的认识则不一致。在《德国租税通则》中,核定期间规定在第四章第三节第1款第2目,该目的标题即为“核定时效”。从其内容来看,《德国租税通则》第171条还专门规定了核定期间的时效中止。因此,德国的税收核定期间应当属于消灭时效。在《日本国税通则法》中,核定期间规定在第七章第一节,其标题为“国税的更正、决定等的期间限制”,而征收期间则规定在该章第二节,其标题为“国税征收权的消灭时效”。不仅如此,从内容上看,核定期间只有固定的期限,没有中断或者中止的规定。因此,似乎表现出非常强烈的除斥期间特性。在学术界,人们也倾向于否定核定期间的消灭时效性质。例如,金子宏即直截了当地将核定期间称之为“除斥期间”。②我国台湾地区“税法”虽然对两者都以期间相称,且都没有规定中断或中止的事由,但学界通行的观点是,核定期间的对象是核课权,而核课权是一种形成权,因此核定期间属于除斥期间。征收期间的对象是征收权,而征收权是一种请求权,因此征收期间属于消灭时效。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核定期间的性质触及税法最基本的法理。如果税收债务在法定构成要件实现时即行成立,则稽征机关的核课只是一种宣言性质的确认行为,不具有创设效力。因此,核定期间也只能是消灭时效,而不是除斥期间。如果税收债务在法定构成要件实现时并不发生,还需得到稽征机关作出核课行为后方才成立,那么,稽征机关的核课行为就是一种创设性的形成行为,而核定期间也只能是除斥期间,而不是消灭时效。现实的情况是,从德国1919年《帝国租税通则》的立法开始,经过1926年德国法学家大会的激烈辩论,目前各国立法和学说都已经接受“税收债务关系说”的观点,实体法上的“权力关系说”被彻底摒弃。这样一来,核定期间作为消灭时效的特性就十分鲜明了。况且,如果核定期间是除斥期间,那么它应该维持期间届满前的旧秩序,即纳税人因税收构成要件实现而成立税收债务。但核定期间届满的法律后果是税收债务归于消灭。因此,核定期间维持的是期间届满后的新秩序,属于消灭时效的范畴。③有学者认为,德国之所以将核定期间视为消灭时效,主要是因为其税法采纳债务关系说,主张纳税义务自构成要件实现时成立。这样,税收核定就只是一种确认行为,而非创设税收债权。由于核定期间的对象不是形成权,因此,核定期间不符合除斥期间的特征。而在日本,国家行使课征权之后,税收债权才能成立。国家必须先行确定税收债权的内容,纳税义务人才有纳税的义务。这种课征权宜早日确定,所以法律规定其存续期间。期间届满后,权利不得再行使,也不发生期间的中断或中止等问题。④笔者以为,如果日本税法确实规定税收债权始于税收核定,那么就意味着税收核定行为的创设效力,其形成权的性质一览无遗。不过,从1987年最后修改的《日本国税通则法》来看,上述观点似乎难以成立。事实上,《日本国税通则法》第15条直接规定了各种纳税义务成立的时间。一旦构成要件实现,纳税义务自动成立,不需要经过稽征机关的核定。这一点在日本税法学界已经得到基本的确认。⑤因此,即使在日本,税收核定权也不是一种形成权,核定期间的除斥期间特性也难以成立。
我国税法虽然没有明文肯定债务关系说,但税收债权的成立从来不依赖税务机关的核定行为,因此,税收核定行为也不是一种形成权。这样,无论追征期是税法对核定税收的期限要求,还是对征收税收的期限要求,追征期的性质都只能是消灭时效,不能是除斥期间。至于目前的追征期没有规定中断或中止,这并不代表追征期不能中断或中止,只能说明税收立法机关有不同的政策选择。将来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时,如果需要,仍然可以进行探索和尝试。
二、税收追征期的起算日及期限
按照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的规定,追征期的期限一般为3年。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5年。对偷税、抗税、骗税行为,追征期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不过,税法并没有对追征期的起算日作出规定。实际上,起算日关系到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不过,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民法上请求权消灭时效之起算点有统一之规定,刑法上消灭时效之起算点,亦有统一之规定,但租税时效却无法为统一之规定。盖租税之课征,在权力方面,则有课征权与征收权之不同;在程序方面,又有申报税与查证税之差异,于是其消灭时效之起算点,即应分别情形,作个别之规定,而无法加以统一。尤其印花税,情形更为特殊,既无需申报,亦无需查征,只有‘实贴’与‘总缴’两种方式,因而其消灭时效之起算点,自又与申报税及查征税不同。可见租税时效在起算点上与其他公法上消灭时效不能不有所差别也”。⑥
在日本税法上,时效起算点的复杂性表现得最为明显。《日本国税通则法》第70条对此作了如下规定。(1)对于纳税申请的更正期间,自该税种的法定申报期限届满起3年。在赋课征收的场合,如果要求提出课税标准申报书,赋课决定的期间,自该申报书的提出期限届满起3年。⑦(2)如果属于减少应纳税额的更正或赋课决定,增加或减少纯损失金额的更正,以及对于超过法定申报期限3年后提出的申报书的更正,上述核定期间改为5年。(3)税务署长如果认为有申报义务的人为提交申报书,其就课税标准及税额作出调查决定的期间,为相关税收法定申报期限届满起5年。(4)在赋课征收的场合,如果要求提出课税标准申报书而未提出,赋课决定的期间从申报书提出期限届满起5年。对于不要求提出课税标准申报书的国税,为纳税义务成立之日起5年。(5)如果纳税人因作弊或其他不正当行为导致少纳税款,核定期间改为7年。其起算点为,在更正或决定的场合,为相关税收法定申报期限届满之日起。在赋课征收的场合,如果要求提出课税标准申报书,则为该申报书提出期限届满起;如果不要求提出课税标准申报书,则为纳税义务成立之日。至于征收期间,根据《日本国税通则法》第72条的规定,为国税法定纳税期限届满之日起5年。
德国税法时效起算日的特色为,无论是核定期间还是征收期间,它都以特定行为或事实日历年度届满之日起算。《德国租税通则》第170条规定,一般情况下,核定期间因租税成立之日历年度届满而开始。附条件成立的租税,在条件成立之日历年度届满而开始。另据该法第229条规定,征收期间自请求权首次届至清偿期之日历年度届满而开始。课税决定做出后,如果未附有缴纳催告,时效因课税决定生效之日历年度届满而开始。至于具体的期限,《德国租税通则》第16条规定,关税、消费税、关税退给及消费税退给的核定期间为1年,其他税收及税收退给为4年。如果因重大过失而短漏税收,核定期间为5年。如果逃漏税收则为10年。另据《德国租税通则》第228条规定,税收的征收时效为5年。
我国台湾地区税收时效的起算与日本相似,没有采纳德国的历年时效。依据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22条规定,依法应由纳税义务人申报缴纳的税收,已在规定期间内申报的,自申报日起算。未在规定期间内申报的,自规定申报期间届满之翌日起算。印花税自依法应贴用印花税票之日起算。由稽征机关按税籍底册或查得资料课定征收的税收,自该税收所属征期届满的翌日起算。另据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23条规定,税收的征收期间自缴纳期间届满之翌日起算。⑧至于具体的期限,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21条规定,依法应由纳税人申报缴纳的税收,如果已在规定的期间内申报,且没有故意以诈欺或其他不正当方法逃漏税收,其核定期间为5年。依法应由纳税人实贴的印花,以及应由税收稽征机关依据税籍底册或查得资料核定课征的税收,其核定期间为5年。未于规定期间内申报,或故意以诈欺或其他不正当方法逃漏税收的,其核定期间为7年。而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23条所规定的征收期间则为5年。⑨
按照前面的分析,我国税法中的追征期只相当于核定期间,其起算日也应该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对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要求申报的税收,如果纳税人已经及时申报,其追征期应当从纳税申报之日起算;如果纳税人没有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其追征期应当自纳税申报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对于代扣代缴的税收,针对纳税人的追征期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算;针对扣缴义务人的追征期,如果扣缴义务人及时申报,其追征期应当从申报之日起算;如果扣缴义务人没有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其追征期应当自申报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至于贴花缴纳的印花税,其追征期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算。如果将来增加有关征收期间的规定,其起算日不妨效仿日本的做法,定为法定的缴纳期限届满之日。不过,这些都只是理论上的构想,不是对现行追征期制度进行解释的结果。因此,为了避免实践中的争议,应当尽早启动法律解释程序。如果不能通过立法程序进行解释,最起码应当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予以规范。
对于偷税、骗税、抗税等税收违法行为,税收追征期是否有必要不受限制,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于这类行为,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了一个较长的核定期间。超过该期间,税收债权仍然予以消灭。但英国和美国为了加重对逃税行为的惩罚,规定随时可以核课,或不经核课而直接通过扣押及司法程序予以征收。对比而言,我国的做法与英美法系国家更为接近。不过,笔者以为,在法律上,消灭时效制度设立的意义在于,解决因时间迁移而带来的举证困难,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实现法的安定性和法律秩序的和平。从行为的后果比较,对偷税、骗税、抗税等违法行为,国家的行政处罚权有时效的限制。即便构成犯罪,国家的刑罚权也有时效的限制。对于税收征收设定期限限制似乎没有必要。况且,对于税款本身而言,否定消灭时效可能仅具有象征意义,表明国家对这类违法犯罪行为的谴责。至于其实际功效,恐怕难如人意。客观的事实是,纳税人的账簿、原始凭证等都只有一定的保存期限。如果这些资料被销毁,追征税款也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从现实的角度出发,针对偷税、骗税、抗税行为的税收追征期还是应该有所限制。
至于追征期适用的范围,《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已经有所区别。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只能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以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可见,追征的对象只包括税收债权及附带债权,罚款、罚金不在追征期的适用范围内。
三、税收追征期的中断与中止
追征期的中断,是指因为法定事由的出现,已经过的期间不再考虑,在中断事由完结后,全部期间重新开始起算。目前,我国税法没有追征期中断的规定,但是,从完善立法的角度看,将来应该对此予以补充。不过,如果将追征期理解为核定期间,由于核课行为作出后即已经达到效果,不需要进行时效中断。因此,各国税法都没有核定期间中断的规定。不过,如果将来设定征收期间,由于征收行为不一定一次就能达到目的,因此,有必要考虑时效中断。在民法上,时效一般因为债权人行使权利或债务人承诺履行义务而中断。由于税法时效的目的在于督促稽征机关及时行使权利,因此,征收期间的中断不宜过多地考虑纳税人的因素。从行使权利的角度看,稽征机关针对税款所采取的任何行为,都可以导致期间中断。
追征期的中止,是指由于法定事由的出现,影响权利人行使权利,导致追征期暂停计算。待中止事由消失后,追征期的计算继续进行。在税收债务关系中,如果因为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致使稽征机关不能作出变更或废弃征税决定,或者不能具体行使征收权,则有必要使追征期中止。对于民事权利,我国《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不过,税收追征期的中止对纳税人不利,如果没有税法的明文规定,不宜直接类推适用民法的规定。目前,我国税法中也没有追征期中止的内容,有必要通过修改法律予以完善。在这方面,《德国租税通则》有关核定期间与征收期间中止的规定非常值得借鉴。
《德国租税通则》第171条共规定了13项导致核定期间中止的事由,其中较为重要的有:(1)在核定期间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做成税收核定时;(2)课税处分显然错误,处分通知后未届满1年时;(3)核定期间届满前,申请税收核定或税收核定的废弃、变更,对于该申请做成不可争议的决定前;(4)在核定期间届满前就已经开始调查,根据调查而做成不可争议的税收核定前;(5)对于税收核定具有拘束力的基础裁决,在通知后届满1年以前;(6)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如果没有法定代理人,自其成为行为能力人或法定代理人就职起,届满6个月前;(7)税收如果涉及遗产,自继承人承认继承,或对遗产开始破产程序,或对代理人核定税收之时起,届满6个月前;(8)未经核定的税收,在核定期间届满前,如果在破产程序中已经申报,自破产程序终了后届满3个月前。至于征收期间的中止,《德国租税通则》第230条规定,在时效期间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而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不终止。
四、税收追征期届满的法律效力
在民法上,关于消灭时效届满后的法律效力,存在债权消灭主义、诉权消灭主义和抗辩权发生主义等不同观点。债权消灭主义认为,消灭时效的完成将导致权利的绝对消灭。《日本民法典》第167条的规定即属于这种类型。诉权消灭主义认为,消灭时效完成后,债权本身并不消灭,只是实现债权的诉权归于消灭,从而导致自然债务的发生。如果义务人主动履行,权利人有权接受,不会成为不当得利。《法国民法典》第2262条的规定即属于这种类型。抗辩权消灭主义认为,消灭时效完成后,不仅债权本身不消灭,其诉权也不消灭,但债务人获得拒绝给付的抗辩权。如果债务人不行使抗辩权,债权则不受任何影响。《德国民法典》第222条的规定即属于这种类型。我国《民法通则》只规定了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我国的做法与上述三种做法均不相同。诉讼时效完成后,债权人只是丧失胜诉权,不能得到人民法院的保护。如果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只规定税务机关可以在追征期内追缴税款,并没有清楚地说明税收在追征期届满后是否消灭。根据该法第51条的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不受纳税人退税请求权时效的限制。如果纳税人在退税请求权时效届满后仍然可以接受退税,那么,从对等的角度看,纳税人在追征期届满后主动缴纳的税款,稽征机关似乎也可以接受。笔者认为,如果法律肯定税收债权在追征期届满后仍然存在,就应该像纳税人退税权那样明确。既然税法没有这种规定,从限制公权的角度出发,权利消灭主义似乎更为可取。事实上,德国、日本、韩国等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在民法上采纳抗辩权发生主义及诉权消灭主义的时效制度,但对于税收债权的时效则普遍采纳权利消灭主义。只有英国、美国,其税法及民法的消灭时效采纳抗辩权发生主义。
有学者认为,行政法发展较迟,所以技术上常借用民法的规定,以规范行政法律关系。此现象在英美法系国家无可厚非,因为英美法上本无公法与私法之区分。但大陆法系国家既然已经承认公法与私法的本质差异,公法之发展就不能长久停留于依赖私法的阶段。例如,德国税法有关时效规定,不准用民法的规定,而是另辟条文,参照民法规定,并融合税法之特征。诸如时效的期间起算、中断、不完成以及其效力等,都自成体系,这样更符合公法之精神。⑩还有学者认为,大陆法系国家之所以采用权利消灭主义,是因为一方面,国家与个人实力悬殊,如果采用抗辩权发生主义,个人将不敢行使抗辩权,公务人员也容易滥用权限,另一方面,抗辩权发生主义将产生公法上的自然债务,有违公法的强制性。而采用权利消灭主义,对所有的纳税义务人都发生相同的结果,符合平等原则,并利于大量重复性税收事件的统一处理。(11)这些论点对我国税法采纳权利消灭主义的时效制度有很强的说服力。
注释:
①郑玉波、翁岳生:《租税稽征之时效问题》,载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三)》,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版。
②金子宏:《租税法》,蔡宗义译,台湾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5年版,第341页。
③陈敏:《租税法上消灭时效》,载《政大法学评论》第32期。
④郑玉波、翁岳生:《租税稽征之时效问题》,载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三)》,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版。
⑤[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陈刚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⑥参见郑玉波、翁岳生:《租税稽征之时效问题》,载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三)》,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版。
⑦日本税法上的更正是指对纳税申报错误的纠正。赋课决定是指税收稽征机关主动课税行为,该行为虽然不是税收债务成立的前提,但如果税务机关没有作出赋课决定,纳税人没有缴纳税款的义务。这种方式只在日本的个别税种,特别是地方税中存在。有的赋课决定不需要纳税人申报,税务机关直接依据查得的资料课征,有的则要求纳税人申报。不过这种申报不是纳税申报,只相当于给税务机关提供信息。这里所谓的课税标准申报书就是这种情况。
⑧有学者认为,已在核定期间内核课的税收,自该核课处分确定之日起,征收期间开始起算。陈敏:《租税法之消灭时效》,载《政大法学评论》第32期。笔者认为,核课处分确定之日是指该处分不得再为争议之日,与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23条所谓的缴纳期限届满似乎相去甚远。不过,这种缴纳期间究竟是法定的缴纳期限,还是税收核课处分所指定的缴纳期限,不无疑问。如果按后者理解,在没有进行核课处分的场合,征收期间似乎又失去了依托。如果按前者理解,由于我国台湾地区没有因税收核定而中断征收期间的规定,当税收核定发生在核定期间即将届满时,征收期间也就所剩无几了。这就会带来执行过程中的一些矛盾。
⑨陈清秀:《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390页。
⑩郑玉波、翁岳生:《租税稽征之时效问题》,载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三)》,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版。
(11)陈敏:《租税法之消灭时效》,载《政大法学评论》第3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