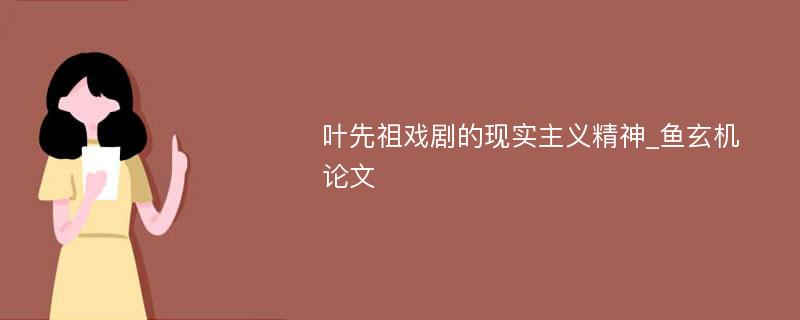
叶宪祖剧作的现实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作论文,现实论文,精神论文,叶宪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叶宪祖(1566-1641),是晚明剧坛上著名戏剧家,一生著有传奇七种,现仅存《鸾鎞记》一种,杂剧二十四种,现存《四艳记》等十二种。长期以来,对叶宪祖及其剧作存在着完全否定的倾向,一是认为他是“团圆迷”的代表作家,“专以改古之悲剧而后快”。①二是认为其剧作“不仅没有什么反封建反礼教的意义,反而宣传了形形色色的封建阶级思想。”②果真如此吗?本文认为,叶氏剧作不仅具有反叛礼教的意义,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精神。这种进步倾向正是从以“团圆”结尾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应给予恰当而切实的肯定。
一
在古代,哲人及统治者对妇女的地位和价值从没给予过公正的评价。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③和刘备的“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而尚有更换,使手足若废,安能再续乎?”④是人所共知的“名言”。亚里斯多德说:“丈夫象一个国君一样统治着妻子,象一个皇帝一样统治着孩子”。⑤直到十九、二十世纪,叔本华还说:“妇女终身都只是些孩子。”⑥尼采认为,男人应该把女人看作“占有的对象,应该关锁起来的私有物。”他还叮嘱人们去找女人时,“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⑦可见对妇女歧视的根深蒂固。因此,妇女地位的高下成为检验社会文明程度和人的解放程度的标准。同理,妇女观的进步与否也就成为衡量古代作家进步与否的标志。曹雪芹及其《红楼梦》之所以享有盛誉,就在于他用十年心血写出了“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人生悲剧,表现了对妇女命运的极大同情和深切关注。在礼教森严的明代,叶宪祖以热情洋溢的笔调,精心刻划了一批要求个性自由、保持人格尊严的女性形象。她们既不是相国小姐,也不是知府千金,而是一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不幸妇女:寡妇、妓女、侍妾、女冠、孤女等。叶氏把满腔同情倾注在这些小人物身上,肯定她们的价值,赋予她们人最美好的东西:姣丽的外貌、善良的心灵、高尚的情操、不屈不挠的品质。她们虽有许多不幸,但从没有失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一旦看准目标,就勇敢行动,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如《鸾鎞记》中的鱼玄机,为了使赵文姝与未婚夫杜羔早成连理,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和幸福,顶替赵文姝到李亿补阙家为妾。这种崇高的牺牲精神表现在一弱女子身上,实在令人钦佩。鱼玄机出家为冠后,对生活仍满怀信心,对爱情寄予无限希望。她与温庭筠相互仰幕,写诗唱和,一往情深。经过努力,终于结为伉俪,有了人间的美满归宿,“得成比目不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鱼玄机由闺门少女、守寡侍妾到远离人寰的道姑,过的都是人性压抑、人格扭曲的生活,直到与温庭筠结合,才体会到人间的欢乐。作者通过鱼玄机的经历,表现了对扼杀人性的封建道德和宗教的否定,对世俗生活的赞扬和对女性人格、价值的肯定。《夭桃纨扇》中,秀才石千之与妓女任夭桃“两意相投幸有缘”。花前盟誓,白头偕老。石千之不是把任夭桃当妓女、玩物,而是把她当平等的“人”来对待,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倾心相爱。这是尊重女性人格的表现。叶宪祖不仅肯定妇女的地位、价值,还极力称颂女性的才智。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个个聪明伶俐,多才多艺。诗词歌赋,样样精通。《鸾鎞记》中《闺咏》一出,赵文姝与鱼玄机的一段对话,可以说是对妇女才学的直接颂扬:
赵文姝:妹子,我二人如此诗才,若去应举,那女状元怕轮不到锦江拾翠的黄姑。
鱼玄机:正是,若使天下词坛姐姐主盟,小妹佐之,那些做歪诗的措大,怕不剥了面皮。
在《品诗》出,入道后的鱼玄机把前来献诗求爱的人鄙薄得一钱不值。这是很有意义的。在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明代的《温氏母训》云:“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百字,多识字,无益而有害也。”“今人养女,多不教读书识字,亦防微杜渐之意”。即使读书识字,也只是“教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经》、《列女传》、《女训》、《女诫》之类,不可不熟读讲明,使其心上开朗,亦阃教之不可少也”⑧。目的是把她们培养成“三从四德”的奴才。叶氏剧作中的女性可不管这些,她们写诗作文,评判男子高下,投诗相赠,互吐衷肠。她们对男子一统天下的科场十分神往,一代才女鱼玄机就为自己是女人而不能逞才科场深以为憾。可以说,这是作者间接地为男权统治下的妇女的地位鸣不平,吐怨气,表现了对妇女命运的关怀和价值的重视。这与李贽所说的“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⑨的观点如出一辙,其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
二
在封建社会,男婚女嫁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对统治者来说,婚姻还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婚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⑩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就是封建社会婚姻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反映。在这种婚姻观的支配下,“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11)因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追求婚姻自主成为青年男女与封建道德冲突的焦点,歌颂爱情也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永恒主题。叶氏如实地写出了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欢乐与忧悉,思考与行动。他们敢于冲破礼教的束缚,不要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而是把有情有义放在首位。如《素梅玉蟾》中的素梅,与穷书生凤来仪情愫互通,大胆幽会,为无赖宝尚文、宝尚武冲散。凤来仪为舅父所迫,进城赴试。临行前考虑的是“同心未结,是我姻缘薄劣;况曾亲厮会,怎生撇下些。”而素梅则被舅母接到冯家。两个音信阻隔,不能相会。后来,双方各有所配,皆不遂愿,一心思念对方。当素梅了解到所嫁之人正是凤来仪时,还不十分相信,派侍女探看的确,才放下心来。《鸾鎞记》中,赵文姝与杜羔、鱼玄机与温庭筠的结合,也是把“情”放在首位。婚前,鱼玄机慨叹的是:“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杜羔进退两难的是“小生功名之念虽切,儿女之情更长”。《丹桂钿盒》中的徐丹桂失侣新寡,权次卿是个“断弦而未娶”的鳏夫。两人相见后,都感到“情之一字,好缠害人也”。权次卿并不因丹桂是寡妇就轻视她,反而爱得更加真挚热烈。他假冒徐母远侄,到徐家认亲。治愈了徐母疾病,获得她的好感。加之权次卿又有与丹桂婚约的凭证——紫金钿盒。这样,顺理成章,鳏夫娶上寡妇,“假侄今成真婿”。叶氏在《开场·折桂歌》中说:“司马文君史传奇,于今重见缀新词。一段姻缘钿盒里,千秋几个有情痴。”他还有一个专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故事的杂剧《琴心雅调》。这说明他对寡妇再嫁是肯定的。不要小看了这样的肯定,因为在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往往也凝聚着前人不断抗争的艰辛。因为明代是一个礼教泛滥的朝代,人们的一言一行必须纳入礼教的规范之中,“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2)稍有越轨,即被视为大逆不道。思想先驱李贽就因“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入狱而死。不仅如此,统治者还不断炮制出一些精神枷锁,禁锢人们的心灵。如朱元璋即位之初,就颁行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明会典》)后来的皇帝还不断命人辑刊《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及《性理大全》,作为官方道德教科书,“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好马不配二鞍,好女不嫁二男”的礼教训言象瘟役一样弥漫着当时的空气,夫死守节、从一而终成为每个妇女应尽的义务。正是在统治者提倡贞女烈妇炽盛的年代,叶宪祖在剧作中表达了与此相反的观点,肯定寡妇再嫁,对节烈观表示轻视和冷漠,这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这与李贽肯定卓文君改嫁司马相如的言论“徒失佳偶,定负良缘,不如早日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13)的精神是一致的。与寡妇再嫁相似题材的作品《寒衣记》也特别值得一提。金定和翠翠从小青梅竹马,同窗习文,私订终身。成婚后,夫妻和乐,恩爱无比。但好景不长,动荡的时局造成了他们的分离。为求与丈夫团聚,翠翠委曲求全——“强从李氏”(李将军)。金定辞家遍访,历时七年,毫不气馁,得知翠翠下落后,并不因妻子委身他人而恋情稍减,寻找各种途径与妻子见面。他谎称翠翠之兄,在衣服中夹诗送给翠翠。翠翠也回诗相赠,表达两人始终不渝的爱情。最后,金定将李将军的不法之事上告徐达,使李将军治罪,夫妻团聚。叶氏将《剪灯新话》中《翠翠传》里两人抑郁而死的悲剧结局改为团圆结尾,既表达了作者愿天下有情人最终团聚的善良愿望,也说明当时的人正在逐渐淡化贞节观念,贞节正慢慢让位于爱情,爱情的光芒可以驱除不贞不节的阴影。即使女子失身,丈夫也恩爱如故。淡化贞节观的影响也是对贞节观的一种背离和反叛。
“人生来是要有伴侣的。如果夺走他的伴侣,把他隔离起来,那他的思想就会失去常态,性格就被扭曲,千百种可笑的激情就会在他心头升起。”(14)封建统治者正是通过“天理”来灭绝“人欲”,造成古代中国妇女毁容、自残、性格变态等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儒林外史》中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并大叫“死得好!死得好!”就可说明礼教对人的心灵的毒害何等之深。叶氏在剧作中艺术地说明“天理”的不近人情,“人欲”的合情合理。如《碧莲绣符》中的陈碧莲,本系秦侍中之妾。秦侍中死后,秦夫人行使家长权力,“也不打她骂她,只要禁她孤零上眠床,空自薰香,待梳头不许临镜,逢月朗不许登楼,遇花开怎容穿径,还须着意关防”,从精神上加以折磨。碧莲不堪忍受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为了获得“人”的幸福和权利,奋起抗争。端午佳节,她不顾“闭房独坐”的禁令,游园赏春,萌动了求一可意之人的心愿。遭到秦夫人的严厉训斥,并派专人拘管,监视她的一举一动,收束其心。可是,人的天性是禁止不住的,你越是用外力强行禁止,它越是通过各种渠道爆发出来。碧莲与章斌一见钟情,朝思暮想,不能见面。于是章斌化名自荐到秦家做记室,深得秦公子的信任。他通过秦公子向夫人施加压力,允许他娶碧莲为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夫人拼命压制陈碧莲作为人的正当要求,死不同意她与章斌结合,但最后还是抵挡不住人性的攻势,不得不同意他们的要求。这是情欲对禁欲的胜利,爱情对礼教的胜利,说明人的天性不可抗拒。
“爱情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冲动”(15)。确实,叶氏爱情剧大多为才子佳人戏,他们结合的方式,用现代眼光来看,是有局限性的。但不能据此否定叶氏爱情剧的价值。因为叶氏剧作同样写出了青年男女精神上的“最深沉的冲动”,写出了这种“看不见的强劲电弧一样在男女之间产生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强烈的倾慕之情。”因为在封建社会,青年男女极少有相互接触的机会,他们的青春热情被长期压抑在心中,对爱情的渴望使他们成日情思昏昏,在自己心中构筑理想恋人的模式。一旦有了偶然相遇的机会,便使他们积压的感情找到了突破口,一见钟情,一订终身。这种爱情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但它毕竟是两厢情愿——爱的结果。叶氏剧作栩栩如生地刻划了青年男女由一见钟情而结成婚姻的过程,吕天成评《四艳记》就说:“词调俊雅,姿态横生,密约幽会,宛宛如见”(16)祁彪佳论《寒衣记》:“传儿女离怨之情,深情以浅调写之,故能宛宛逼肖。”(17)他笔下的男女双方通过一见而看到了彼此的外貌、风度举止,有的还通过谈话、赠诗、幽会,了解对方的人品、才学和性格,从而产生了相互的“钟情”。这种“钟情”不是外人强制的结果,而是男女双方的主动追求。他们的行为完全受自我意志的支配,选择的标准摆脱了门第家世、金钱地位等社会功利的目的,双方强调的是心灵的契合,感情的相融,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表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的崛起。与包办婚姻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所具有的反礼教的价值也是不能低估的。与《情邮记》、《燕子笺》、《怜香伴》、《奈何天》等美化一夫多妻制、描写风流文人淫佚生活内容相比,格调要高得多,意义也要大得多。
三
叶氏在剧作中不仅塑造了一批聪慧、俊美、痴情、大胆追求爱情幸福的青年女性形象,还塑造了两个刚直不阿、叱咤风云、性格鲜明的英雄豪杰形象——荆轲和灌夫。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易水寒》就是一出描写荆轲刺秦王故事的燕赵悲歌。该剧基本上以《史记》为依据,但对荆轲形象进行了重塑和再造。《易》剧以第三折《壮别》为戏胆,前勾秦王征燕,荆轲出山,后连刺秦壮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褒燕反秦的总体倾向中塑造荆轲形象。
荆轲重义气,讲然诺,集勇、智、豪、侠于一身。在未遇太子丹之前,他只知饮酒作乐,“喜来时唱几曲短长歌,闷来时洒几点英雄泪”。秦军逼近燕国,田光向太子丹推荐荆轲,荆轲极力推辞,考虑的是个人的安危:“俺不比囊中脱颖锥,……只图向春风弄锦弦,超韶年倒玉杯,那晓得帝王忧军国计。”作者没有把荆轲神化,而是把他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荆轲留恋生而抛弃死。这就很有真实感,造成荆轲最初不愿受命,后来又毅然赴秦的原因,即有太子丹的以诚相待,田光、樊于期的以死相激,又有他的“士为知己者死”、以义、侠行世的思想因素的影响。第三折《壮别》,在浓郁的悲剧气氛中,突出表现荆轲大义凛然、义无反顾与众人别泪相向、风景惨然的巨大反差,衬托出荆轲的一身虎胆、视死如归的伟岸正气,戏剧效果十分强烈。太子丹、高渐离设宴饯别,一面是“无情易水下西风”,“坐客相看泪如雨”,生离死别的阴影笼罩在众人的心头。一面是高渐离击筑而歌,荆轲和而歌,在羽声慷慨中,荆轲情傲河山,谈笑风声,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博清名万古留,觑一身似浮蝣”,悲壮感人。荆轲在秦宫经历了一场扣人心弦的惊险搏斗,不辱使命,终于完成了刺秦任务。对于第四折,作者将荆轲刺秦失败改为生擒秦王,尽归六国之地,历来为人所诟,这也确为不容忽视的败笔。但我们不能因局部的失误而否定整体,也不必斤斤计较于作者是否遵循史实细节的真实。因为历史剧并不等于历史。它虽以一定的历史事实作根据,但必须有作家浓烈的激情和鲜明的倾向,作家借历史题材来作为现实世界和自己心态的载体。大凡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都有一种反历史的倾向。指出其失误是必要的,但不能据此全部否定,而应仔细探究作者这样写的真实意图,理解作品的真正意蕴。叶氏写出荆轲抗暴扶弱威慑秦宫,压倒一切的神威,终于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洋溢着不甘屈辱的浩然正气和正义必胜的乐观情绪,歌颂荆轲、田光、樊于期等人“人生留得丹青在,纵死犹闻侠骨香”的献身精神和生命价值,这与明末林党人杨涟、黄尊素等人为正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品格是一致的。《易》剧虽然改变结局,但并没有改变事件本身的悲剧力量,聪明的观众或读者关注的更多的往往是悲剧发生的过程而非仅仅是结局而已。古往今来赞赏这部作品的大有人在。祁彪佳《剧品》将此剧列入雅品,谓“荆卿挟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即事败身死,犹足为千古快事。桐柏与死者生之,败者成之,荆卿今日得知己矣。”(18)青木正儿也极为欣赏这个剧本:“此曲事既壮烈沉痛,曲调亦相称,彼之杂剧中,此为余所最爱者。”(19)
叶氏不仅写出了英雄人物一往无敌的豪迈气势,而且以沉雄悲壮的笔调,写出他们的坎坷遭遇。如果说《易水寒》塑造了一个功成名就的英雄形象的话(按照叶氏的意愿如此),那么,《骂座记》则塑造了一个失败英雄灌夫的形象。
《骂座记》的题材来自《史记》的《魏其武安侯列传》。剧本第一折写骂座起因,第二折写骂座,第三折写廷辩,第四折写复仇,完整再现了灌夫生为英雄、死为鬼雄的全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暴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着力表现灌夫嫉恶如仇、正直仗义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冲突始于丞相田蚡新近得势,位高权重。窦婴的宾客都弃窦投田。只有灌夫一如既往,与窦婴保持交情。在田蚡的家宴上,灌夫有感于世态炎凉使酒骂座,痛斥了以田蚡为首的贵族官僚飞扬跋扈和谄媚小人的趋炎附势,被诬以骂座不敬的罪名论死。窦婴为救灌夫,四处奔走,直到上诉皇帝,也未能救出灌夫。同一切优秀悲剧一样,《骂座记》所以能吸引读者,也是以悲剧人物灌夫的不幸遭遇、斗争意志和高尚品德来感动读者,赢得读者同情的。对一般人来说,死,标志着个体生命的结束,一切未了之事,只能依靠活着的人才能继续干下去。而灌夫却不是这样,他死后的鬼魂以超人的神力,缠住田蚡,直到讨还血债,他的行动才告结束。复仇是他屈死后的必然行为。鬼魂复仇在现实活中显然是不可能有的事情。但作为复仇者灌夫的鬼魂,表现了英雄人物死后不已的韧性斗争精神,其斗争结局使沉冤得伸,大快人心。
作者歌颂灌夫和窦婴的这种生死之交,描绘出“世情逐冷暖,人面看高低”的世人俗情眼浅的丑态,是有现实意义的。明代的士大夫不讲节气是有名的。他们对待故交至友很少遵守信义,见利忘义,卖身求荣是常有的事。如沈璟在《埋剑记》的开场中就说:“达道彝伦,终古常新。友朋中无几何存。朝同兰蕙,暮变荆榛,又陡成波翻作雨、复为云。所以先贤著绝交文,畏人间轻薄纷纷。”据说康海的《中山狼》杂剧就是为讥刺李梦阳的忘恩负义而作。叶氏在生活中可能也有所感受,不满这种现状,才这样极力歌颂灌、窦的刎颈之交,使那些不讲节操,没有骨气的士大夫在灌、窦面前无地自容,相形见绌。《骂座记》的现实意义不仅在此,它通过灌、窦的不幸遭遇,说明在封建社会里,正直之士的不遇于时,正如文人的怀才不遇一样,也是一个普遍现象,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它还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明末官场的腐败和黑暗,反映了明代政治斗争的险恶。第三折《廷辩》,当窦婴对皇帝给灌夫的判决前后相背表示大惑不解时,宫中女官的回答是:“你们外面官儿,那晓得宫中事体来?……他手足自相遮,旁人怎间别?”窦婴还要据理力争,也不过是“枉费唇舌”而已,因为即使窦、灌再有道理,“怎当他坐椒房亲姐姐,宫深路绝,想不得宫深路绝。”这并不是无足轻重之笔,大有深意在此。剧作把封建社会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写得是非不分、任人摆布、糊糊涂涂,说明在万民仰视的皇帝那儿,也没有公正可言。这个社会黑暗到了极点。皇帝的昏聩是造成灌夫屈死的终极原因。这在明代显然是有所指的。有明一代,统治者昏庸腐朽,有的终年深居宫中,不理朝政,致使宦官大权独揽,朝政日非。嘉靖以前,有过王振、刘瑾专权的历史。隆庆、万历间的改革家居正就是利用宦官冯保才取得首辅职位的。天启年间的魏忠贤更是恶贯满盈,罄竹难书。他与皇帝乳母客氏勾结,控制厂、卫,陷害忠良。他先是害死正直太监王安,再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六人逮捕,严刑追逼。他还大搞株连,杜撰出一个《东林点将录》来,血腥镇压正直官僚和士大夫。我们虽不能判断《骂座记》的具体写作年代和所指何事,但断定其中寄托了作者对朝政腐败,当道权贵为虎作伥的极大愤慨和对清明政治的殷切期望,当不是无知妄说。祁彪佳早就看出了这一点:“灌仲孺(夫)感愤不平之语,槲园居士以纯雅之词发之,其婉刺处有更甚于快骂者。此槲园得意笔也。”(20)另外,从叶氏的生平行事来看,他也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叶宪祖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参政意识,他能在阉党横行、大肆迫害东林党人的时候,将女儿嫁给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而黄尊素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又被阉党杀害。这门亲事自然触怒了权臣,影响了叶氏的升迁,他也在所不惜(21)。叶氏还能与魏阉及其干儿义子作斗争,“逆阉建祠长安街,宪祖笑谓同官曰:‘此天子走辟雍道也,土偶岂能起立乎?’逆阉闻之大怒,‘吾乃为郎所谐’,削籍。”(22)叶氏自己不畏强暴,不惧淫威,与逆阉坚决斗争的行为也是《骂座记》以古刺今,具有强烈现实批判精神的有力证据。叶宪祖也是最早向科举制度发起攻击的作家之一。由于他目睹和经历了明代科场的黑暗——历“公车之苦”二十余年,因此,他借《鸾鎞记》中杜羔、贾岛、温庭筠之口,对科举的不公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已有文章论述,本文就不必多费笔墨了。(23)
注释:
①邵曾祺:《试论古典戏曲中的悲剧》,《中国古典悲剧喜剧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13-14页。
②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中),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73页。
③《论语·阳货篇》第十七,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1页。
④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142页。
⑤⑥⑦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5-54页。
⑧转引自徐扶明:《元明情戏曲探索》,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265-266页。
⑨李贽:《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焚书》卷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⑩(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12)《论语·颜渊篇》第十二,《论语译注》,第123页。
(13)李贽:《司马相如传论》,《藏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26页。
(14)《情爱论》,第8页。
(15) 《情爱论》,第6页。
(16)吕天成:《曲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7月版,第234页。
(17)祁彪佳:《剧品》,同上,第156页。
(18)祁彪佳:《剧品》,《集成》(六),第157页。
(19)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上),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223页。
(20)祁彪佳:《剧品》,《集成》(六),第157页。
(21)《康熙绍兴府志》五十,见赵景深、张增元《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3-124页。
(22)《康熙浙江通志》三七,同上,第124页。
(23)魏奕祉:《叶宪祖〈鸾鎞记〉论考》,《中国古代戏剧论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4月版。
标签:鱼玄机论文; 叶宪祖论文; 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荆轲论文; 灌夫论文; 荆轲刺秦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战国时期论文; 西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