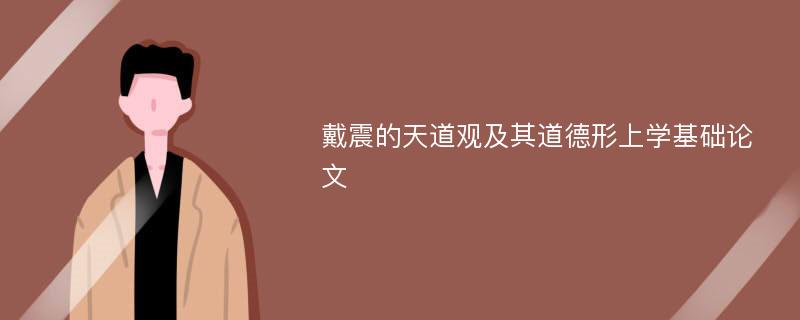
戴震的天道观及其道德形上学基础
孙邦金
(温州大学 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 近世诸多“尊戴”、“释戴”性作品对于戴震哲学颇多推重,但现代新儒家对戴震哲学评价很低,认为戴震“达情遂欲”的道德哲学局限于知性运用和情欲满足,未能就情欲的限制、超越界的关怀和形上学的根据给出圆满解释,因而批评戴学是一种缺少贞定基础和规范性的情欲主义、精于算计的功利主义。其实,这一批评明显带有某种形而上学基础主义的定见。在戴震“人道本于性,性原于天道”的理论架构中,其“道赅理气”且具有先天道德完满性的天道论,通过“人道遡之天道”的天人关系论,以一种十分经济朴素的自然合目的论形式为其人性论和伦理学奠定了本体论基础。这在清儒形上思维普遍衰降和道德异化之时代,殊为难得,应予充分肯定。
关键词: 戴震;天道观;道德形上学;天人关系论;自然合目的论
近代以来,诸多“尊戴”、“释戴”作品对于戴震哲学颇多推重,然而也有不少人认为戴震哲学仅仅局限于知性的运用和情欲的满足,未能就情欲的限制、超越界的关怀和形上学的根据给出圆满解释,因而批评戴学是一种缺少贞定基础和规范性的情欲主义、精于算计的功利主义,或者流于平面肤浅甚至扞格不通的智识主义。在众多批评声音中,从宋明儒学“接着讲”的现代新儒家对戴震的批评最为激烈。继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批判“清儒自戴震昌言崇欲,以天理为桎梏”[1](P.115)之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冯友兰、刘述先、郑宗义、李明辉等现代新儒家对于戴震哲学的评价基本上也是负面的。在他们看来,在“超越性”之减杀甚至否定的思想基调之下,清儒多遵从一种气性之自然人性论传统,反对从超越层面的义理之性来理解人性,缺少贞定的本体基础和向上提升的超越空间。[2](P.71)由于失去了天地义理之性的基础,“到头来只剩下外在的规范”,“不过皆为与道德无关的利益计算,而道德意识亦彻底萎缩矣!”[3](P.250)甚至直指戴震“达情遂欲”的伦理学开启了另一种“以礼杀人的传统”[4](P.103),批评可谓极为严厉!
采取儿童依从性评分量表评估接种儿童的依从性,评估内容主要为接种儿童的配合情况、哭闹程度等,量表总分为100分,得分越高则依从性越高。采取问卷形式评估家长的护理满意情况,行百分制,评分越高则护理满意度越高。
其实,戴震不愿依从宋明儒学的形上学思路是一回事,而他有没有另外一套形上学思想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清儒形上思维普遍衰降与乾嘉时代道德异化严重之时代,戴震确实在形上本体的 “去实体化转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既没有悬置更没有拒斥道德形上学思考,而是以一种更为经济朴素的、具有先天道德完满性的天道观为其自然与必然、情与理、天与人相统一的哲学建构奠定了本体论基础。本文拟通过揭示天人关系论及道论形上学在戴震哲学中的基础性作用,对上述批评作一回应。
依据西方经典学说,社会救助即“公权力为了达成生存照顾之目的所使用之手段”,因此,宪法上的生存权一般被作为社会救助的主要依据,如《日本国宪法》第25条“全体国民都享有健康和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权利”即被认为是日本生活保护制度的宪法根源。将社会救助权的宪法基点定位于生存权划定了公民所能请求的社会救助的限度和范围,基于此也发展出支配社会救助权最为核心的原则——最低限度原则和辅助性原则。[5]69与此不同的是,我国《宪法》上并未直接规定生存权,需要透过对既有宪法条款的解释导出社会救助权的宪法基点,这也意味着我国社会救助权的性质与目标在基点上即与西方国家相分野。
按照《兽用消毒剂鉴定技术规范》[8],配制成中和剂:为含0.5%卵磷脂、0.5%硫代硫酸钠、3%吐温-80及磷酸盐缓冲液,再以金黄色葡萄球菌或白色念珠菌为受试菌,分6 组进行中和剂性能的鉴别,具体分组如表1 所示。
一、清儒形上思维的衰降与戴震的反应
出于对明末儒学流于虚玄的反动,清代儒学不断从形上义理界向经验知识界落实,从内在心性向外在事理铺陈,由“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方向性转型非常明显。这有如近代西方哲学界“拒斥形而上学”运动一样,清儒也不无类似地表现出“一形上心灵的萎缩,对一切形上本体论说的厌恶”[3](P.172)。到了乾嘉考据学界,吴派领袖惠栋以昌明汉学著称,他曾斩钉截铁地说“若经学,则断推两汉!”[5](P.645)在经学研究方面,惠栋从文本乃至思想上推崇汉代是有其理由的,但排斥形上义理的诠释和发挥则未免泥古不化、画地为牢。在乾嘉史学界,同样偏重史实而有意地避免道德上的议论和褒贬。在乾嘉三大考据史家之中,钱大昕说研究历史“奚庸别为褒贬之词”[6](P.285),赵翼最欣赏的良史是“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7](P.117),王鸣盛则干脆宣称“议论褒贬皆虚文”也乾嘉文坛翘楚袁枚也不免囿于时风之影响而贬低义理思维的必要性。他曾自道“孔郑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明确表示不掺和义理之学和考据学术的争议。事实上,从袁枚“作史者只须据事真书,而其人之善恶自见”[9](P.58)等主张中,可以看出他对理学的厌恶程度还是明显胜过考据。如果说宋明儒者尤其是王门后学流于“虚玄而荡”是一种形上学空描的话,那么清儒“学求其是”,不“空言性命”[10](P.264)的做法意在扭转和补救这一偏执。只不过物极必反,极端厌恶和排斥形而上学成风而将思想仅局限于“实事求是”的经验领域,这无疑又陷入了另外一种时代的锢蔽。唐君毅等人就此批评清儒“盖不免有昧于义理天地之广大”[11](PP.105-126),当非冤词。
不过,每个时代的哲学家虽然都有其时代潮流的锢蔽,但彼此存在着自觉不自觉和程度轻重的差异。清儒对道德形上学的拒斥,需要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戴学作为清学之新典型,对于清代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的反应有其两面性:既有认同之处,又有超脱之处。一方面,戴震受到清初思想日趋征实、反对影谈的学风影响,同样表现出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想反转。除了义理之外,在历算、地理、礼制、小学等主要治学领域里,戴震通过自己偏主经验主义认识论的考据学成就塑造并强化了清代道问学“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这一治学范式。无论是理学家方东树还是他的思想知己兼论敌章学诚,都看出了戴学“力禁言理”、“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的特质。戴震认为:“理散在事物”,“理义岂别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进于神明,岂求诸气禀之外哉!”[12](《孟子字义疏证》,P.156)事物之理与道德理义不在气禀之外而在经验界之中,故只能通过感性经验和理性归纳透过现象方能认知,“冥心求理”无异于缘木求鱼。他直指宋儒“自信之理非理也”[12](《孟子字义疏证》,P.212),认为本体之“理”是一种形而上的主观臆断或独断,对于道德形上学采取了一种拒斥的态度。这从他将朱子超越经验之“天理”努力拉回到经验界,脱离其超验性,使其变为一种可以经验认知的“条理”可以看得很清楚。客观地讲,反对形而上学的时代蔽锢给戴震的哲学建构带来了很大的束缚,尤其是限制了他对孟子性善论之超越性的诠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在重构了天道本体论之后,戴震借用孟子“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的说法,依据天人相通不隔(“一本”)与相隔不通(“二本”)这两个标准,对儒学史上不同的本体论形态进行了判教,并以此来说明其天道一本论的伦理学意义。
相较之下,唯有以“合血气心知为一本”[12](《孟子字义疏证》,P.172)的天道作为宇宙之根源且为道德之本体,而非单纯以气或理为本体,才能避免陷于戴震所说的“二本”之论。由于“理”一般意味着一种理性的道德法则,“气”意味着一种具体感性的情欲需求,因此兼摄“理”、“气”就意味着兼顾人的“理”、“欲”。戴震“理存乎欲”的伦理学主张,恰是建基于“道赅理气”的天道论基础之上的。理、气兼备的天道一元论的优点,即在于“气不与天地隔者生,道不与天地隔者圣” [12](《原善》,P.15),即能够保证天人之间“不隔”而相通,避免陷入人性中的理、欲仍各有所本的二元分裂与对立的困难。有学者就此指出,天道一本论就是改静态的形上学为一动态的存有论,改一“规范性之道德观”为一“发展性之道德观”[24](P.119),较之理本论或是气本论更为浑沦与圆融,具有贯通天与人、自然与必然、情欲与理义的优点,能够更好地诠释接续“赞育天地”、“生生不已”之易道精神。
二、“道赅理气”的天道观
1776年,戴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作序时指出,自己小时候读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话大惑不解,到了晚年“读《易》,乃知言性与天道在是!” [12](P.147)戴震早年主张“周易当读程子《易传》”[14](P.714),从其《法象论》《读易系辞论性》诸文中可以看出,戴震宇宙论和天道论的直接理论来源是《易传》。其中《法象论》一文,是戴震对易传“法象莫大乎天地”(象天法地)的宇宙论所作的诠释,基本上重申了汉唐乃至宋明儒学的宇宙论模式。此文初步建构起了戴震的一套天人同构与相应(天地-日月-阴阳-乾坤-男女-夫妇-君臣)的天人关系论,以及“人道本于性,性原于天道”的整体理论架构。不过,中年以后,戴震“隐然以道自任”,对于程朱“理本气末”的本体论架构日趋不满。他说:“后世儒者以两仪为阴阳,而求太极于阴阳之所由生,岂孔子之言乎!况‘气生于理’,岂其然乎!”[12](《绪言》,P.85)这里的“气生于理”显指朱子的理本气末、理先气后论,批判的矛头非常清楚。朱熹在道器、理气关系论上,认为“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16](P.72),把阴阳五行之气皆认作是形下经验的范畴。这一处理早在戴震之前,就遭致越来越多的人的批评。例如,刘宗周明确反对说,“象山曰:‘阴阳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极乎’,近之矣”[17](P.235)。同样的意思,王夫之则说“阴阳,无始者也,太极非孤立于阴阳之上者也” [18](P.562)。戴震在继承明清日渐兴盛的气论思想基础之上,进而开启了以“(天)道”代“(天)理”的本体论转向。
道、理二字在宋代以前原本很少连用,但随着“理”之地位上升为一本体概念之后,道理不加区分地使用的现象日渐常见。不过到了朱熹那里,则明确申说“道,即理之谓也”[16](P.98),“道也者,阴阳之理也”[19](P.1935),将“道”与“理”皆看成绝对的至理,“理”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后来陈淳干脆说“道与理大概只是一件物”[20](P.41),道与理成为同一层次的本体概念。可是在朱子“物物各一太极”的“理一分殊”理论中,如何界定作为形上本体之“至理”与作为众多分殊之“分理”的关系始终是其一大难题。清初以后,王夫之、惠栋、戴震、章学诚、焦循、凌廷堪等乾嘉学者各自从不同角度分疏了道与理的异同之处,逐渐使得“道一理殊”论成为乾嘉学界一个基本共识。[21](PP.60-69)
当然,朱子理气论固然有二元论的倾向,但如果撇开“理”之规范性而只以无定形之气为本体的话,则人性的先天内容只能是自然的本能和欲望而已;失去了先天的形上根据,仁义外在、性恶之论恐怕是难以避免的结论。因此戴震所论理与气、血气与心知,总是一体同时出现的。至于由孟子“本心”、“良知”概念发展而来的心本论,戴震认为它只是“气之精爽”——生命进化至最高级阶段所拥有的一种主观思维能力而已。虽然他特别看重“心知”及其能够“进乎神明”的道德功用,对于心知之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能力皆有极致的发挥,不过此“心”多是从认知功能意义上来谈的,基本上不具备道德本体之涵义。总之,宋明儒学的气本论、理本论与心本论这三大本体论形态,皆与天道有间而不能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地全然相通。
辅导班是另一种学习方法,它是在学习书本知识之后进行的课后辅导,一般通过老师的讲解,自己的多次练习去学习,对掌握的知识进行再次巩固。这种现象也最常见在我们的学生当中,学生们从刚开始上学就开始被安排上各种辅导班,有学舞蹈,有学画画,到了大学毕业后,通过各种专业的考研辅导、国家公务员考试等辅导班,来强化各种能力。尤其在现在的社会中竞争激烈,辅导班的学习也逐渐成为潮流。
三轴式摊铺机是一种中档型机械,主要的组成部分包括2个驱动器和3根轴,这种机械设备与小型机械和滑模摊铺机均存在不同之处。三轴式摊铺机通过两个驱动器以实现摊铺和振动功能以及带动整个设备进行移动[1]。在摊铺机上还配套有其他相应的设备,比如说拌和楼、自卸汽车及洒水车等。三轴式摊铺机的基本性能为:一次摊铺宽度7.5~8.5m;摊铺速度15~30m/h;1d摊铺工作量200m。
戴震还运用了语言学方法,论证了“道赅理气”——道体兼含实体与理则的本根地位。首先,他从句法结构上分析了《易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两句话的不同。戴震这么细微地辨析“之谓”与“谓之”间的差别,似乎有点吹毛求疵,其用意只有一个,即反对朱熹将阴阳之气看成是形而下的观点。反之,则是要证明早在《易传》中“谓之”句式中,已经将阴阳五行之气看成与道一样都是属于形而上的了。其次,在分辨“之谓”与“谓之”之后,戴震接着又对“形上”与“形下”分别作了定义。正所谓“阴阳之未成形质,是谓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不徒阴阳非形而下,……其五行之气,人物咸禀受于此,则形而上者也”[12](《孟子字义疏证》,P.176)。在他看来,形上就是指无定形、有形之先,形下就是指有定形、有形之后。这与朱子所说的形上(先验)与形下(经验)有本质的区别。如此一来,太极、道、理、阴阳五行之气同时皆纳入到戴震天道论所含摄的范围。这充分显示出戴震哲学的气论色彩,与朱子的理气二元论相比,显然是两套有着根本差异的本体论系统。
戴震在《绪言》中说,“六经、孔、孟之书,不闻理气之分,而宋儒创言之,又以道属之理,实失道之名义也”[12](P.84),着力批评了前人不加区别地使用“道”与“理”的做法,认为朱子对“道”的解释其实难以自圆其说。宋儒(实指程、朱)完全反过来将“道属之理”,置“道”于“理”之下,其创生、统摄的本体地位渐被“理”所取代。戴震指出,虽然古人亦经常将“道、理二字对举”,但他们“或以道属动,理属静。……或道主统,理主分。或道赅变,理主常。此皆虚以会之于事为,而非言乎实体也”[12](《绪言》,P.88)。无论是从动静、统分、常变哪一种角度来区别,“理”都只是不包括道之实体——阴阳二气与五行的“不易之则”,从属于“道”之下的。戴震认为,宋儒将超脱阴阳之气和具体实际的虚玄之“理”视作本体的做法,绝不可能从《易》《庸》之学中演绎而来,只能是从老庄与释氏的道论转化而来。如其曰:“宋儒合仁义礼而统谓之理,……盖由老庄、释氏之舍人伦日用而别有所(贵)[谓]道,遂转之以言夫理。”[12](《孟子字义疏证》,P.202)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大体上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只是儒学接受佛、道的形上刺激倒不是件坏事。相较之下,《易》《庸》之“道”不仅包含“虚理”而且还包含“实体”,因此它才应该是儒家形上学体系中的最高概念。
戴震很特别地将老、庄、告子、释氏心学归之于佛教,且一并予以批判:“告子以自然为性使之然,以义为非自然,转制其自然,使之强而相从,故言‘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立说之指归,保其生而已矣。陆子静云:‘恶能害心,善亦能害心。’此言实老、庄、告子、释氏之宗旨,贵其自然以保其生。”[12](《孟子字义疏证》,P.182)告子是以自然情欲论人性,“以义为非自然”,使得必然的道德理义成了不自然的负担;而陆王心学虽要求顺由自然本心而行,不假外求和强制,可如此简单直截的做法是很难保证自然的同时又是必然的。总之,无论是告子还是陆王,他们的思想宗旨与释老“贵其自然以保其生”并无二致,都将情欲心知与道德名教分开甚至对立起来看,都不能够辩证统一地对待自然与必然的关系。戴震这种大而话之的笼统讲法,显然难称得上是客观的态度,不过他对儒学史上诸种自然与必然关系类型的总结还是颇有见地的。相对而言,自然与必然的断裂、必然对自然的超克压制在朱子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但影响却最大,因此戴震将批判的重点指向了朱子学。在朱子的理本论架构中,“理”只是作为单纯抽象的至道,与阴阳五行之气相即不杂,难免给人一种理气分裂、视理“如有物焉”的缺憾。换言之,陈来认为,朱子的天理确实“如有物焉”,具有某种超越气化事物之上的、超绝的实在性,只不过随着明清理学“去实体化转向”,“理不再是首出的第一实体,而变为气的条理,因此人性的善和理本身的善,需要在气为首出的体系下来重新定义”[23](P.194)。王船山、戴震即是明清天理“去实体化转向”运动中力求沟通天人、实现自然与必然相统一的两位哲学健将。
三、“道不与天地隔者圣”的天道一本论
另一方面,从戴震的思想发展演进过程来看,却又有一个从知识研习到道德思考的形上转进。戴震晚年在给段玉裁的信中说:“竭数年之力,勒成一书,明孔、孟之道。余力整其从前所订于字学、经学者。”[12](《与段玉裁第九札》,P.542)戴震直到40岁左右才开始将阐发“曲尽物情,游心物之先”[12](《与方希原书》,P.375)的圣人之道当作自己最为重要的一个治学方向。这类似于拒斥形而上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到最后又引入某种“本体论的承诺”。(1) 这是借自美国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蒯因的说法。他在当时“拒斥形而上学”情绪弥漫的时代中,率先提出恢复本体论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可谓起到了扭转风气的作用。参见陈波《蒯因》,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284-285页。 在此之前,他与大多数考据学者类似,都压制了对于形上义理之学的系统思考。其实,戴震天性有强烈的怀疑精神与问题意识,对于义理的偏爱远胜过对考据的兴趣。用余英时的说法,戴震“一身兼擅考证与义理,在乾嘉学术史上为仅有之例”,本性上是一个“刺猬型”的人物却又戴着一个“狐狸”的面具。戴震在当时承受了来自学术界的巨大压力,可谓两面受敌:一方面,其极其鲜明的反理学立场招致了当时理学家的攻击;另一方面,由于其“经之至者道也”[12](《与是仲明论学书》,P.370)的强烈义理诉求,也颇为当时厌恶谈论心性义理之学的考据学者所非议。在厌谈义理之学的“狐狸”得势的18世纪,戴震面对考据学者讨厌刺猬型人物的压力,必须敷衍狐狸一番。[13](P.96)章学诚说“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10](《书朱陆篇后》,P.275)。当时认为戴震哲学诸篇可以不作的“时人”,包括纪昀、朱筠、钱大昕、王鸣盛、王昶等官学两界的达人,可见“狐狸”之人多势众。戴震狐狸之表象掩藏了很长一段时间,自17岁至40岁左右期间,主要精力皆集中于考据学。而自1763年《原善》三篇著成之后,“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14](P.674),其在义理思考中所得到的一种智性的满足非考据学可比。此后,戴震在义理之学上的思考便一发不可收拾,不再绕路说禅,“乃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耳”[15](P.184),刺猬的本来面目日渐清晰起来。他在《与某书》中更是直言“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12](P.495)。这里的“空所依傍”,是说人的问学过程中要有自我裁断、自作主宰的主体性,强调的其实就是理性精神自为演绎的一种能力。戴震已经突破了考据学由训诂而明义理的“信条”,而达到了抽象义理思辨的层次,在经典文本与诠释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诠释的良性循环。
不过,严格地讲,“气”在戴震哲学中并不是最高的概念,它也是从属于“道”的。在论及道与气的关系时,戴震始终认为,“天道,五行、阴阳而已矣”[12](《原善》,P.12),“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12](《孟子字义疏证》,P.175),气还只是天道化生万物的一种物质实体。在这实体之中,还同时寓有阴阳气化流行的道理——“不易之则”。在戴震看来,“古人言道,恒赅理气;理乃专属不易之则,不赅道之实体”[12](《绪言》,P.88),并非如朱子所说“辨别所以阴阳而始可当道之称”[12](《孟子字义疏证》,P.176)。天道“赅理气”、“合物与则”,是阴阴五行之“气”之实体与不易之“理”的统合体,乃是气和理二者之浑沦。这与庄子的能够“生天生地”、“万物毕罗”之“道”颇有几分类似,皆是本体论层面的本根之道。张立文曾根据“谓之气者,指其实体之名;谓之道者,指其流行之名”[12](《孟子私淑录》,P.37)的说法,将戴震的道、气关系界定为“气言其体,道言其化”的“气体道化”论。[22](P.134)其实,戴震在这里只是把气作为道的“实体”,绝非道之“本体”之意。依据戴震“道赅理气”之命题,道作为最高概念,是理与气的浑沦,是同时包含理和气的。他显然有意地避免将气与道等同视之的,因此不能将其天道论简单化约为气本论。在某种意义上,此“道”不仅是物质性的,也兼具有精神性或伦理性的意义。因此戴震天道本体论既非单纯的气本论,更非单纯的理本体,而是综合宋明儒学气本论与理本论两种传统之后产生的新形态。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开篇先谈“理”(15条),接着论“天道”(4条),先“理”后“天道”的顺序显然是精心设计的,意在先破后立。他先严格地区分了道与理,释“理”为“条理”,颠覆了宋明理学六百年来最核心观念的定义,消解了“天理”的本体地位。紧接着他通过恢复“道”的本体地位来取代“天理”,重塑了儒家的本体概念。在戴震哲学体系之中,“道”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统合理、气、心等前代本体性概念的最高概念,并由此建构起一套沟通实然宇宙与应然道德世界的“新道论形上学”。
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戴震凭其对道德形上义理的偏好,以过人的孤勇提出了自己一套以性善论为核心的道德学说,最经济地恢复了对儒家心性之学的形上思辨。总体上看,在戴震“人道本于性,性原于天道” [12](《孟子字义疏证》,P.200)的整体架构中,其“达情遂欲”伦理学和“合血气、心知为一本”的人性论皆“原于天道”,皆以自然合目的的、道德化的天道观为本体论基础。换言之,在这个三元一体之理论架构中,天道论就是其本体论,是戴震哲学追求情感与理性、自然与必然、天与人相统一的道德形上学基础,只是由于戴震的简约处理而容易被人所忽视。接下来,就具体揭示戴震的本体论思考——天道观的内涵及其特别之处。
四、“人道遡之天道”的道德形上学诉求
戴震用“天道”取代了“天理”作为其终极的本体概念,既是为了满足一种宇宙生成论之解释,更是意在为其性善论主张提供形上依据。换言之,戴震的天道观既是宇宙论也是道德本体论。以往研究,大多注意到戴震天道观的宇宙论性质或自然主义特质[25](P.30),而对于天道一本论之于戴震的性善论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则不甚明了。由于戴震悬置形而上学的思维局限,对其天道论的道德内涵阐释多是点到即止,没有充分展开,这给我们理解戴震是如何解释人性为什么是善的问题带来了一定困难。对此,劳思光先生认为,戴震哲学对于天道论与人性论的理论勾连,匆匆跳过,语焉不详,“于是其他理论皆成无根之意见矣” [26](P.783)。甚至有人认为,戴震的性善论与其本体宇宙论并无关联。[27](P.214)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为戴震天道观的道德形上学意义作一合理的补充与回应。
戴震认为“道有天道、人道”,只不过“天道以天地之化言也,人道以人伦日用言也” [12](《孟子私淑录》,PP.37-38),或者说“在天为天道,在人,咸根于性而见于日用事为,为人道”[12](《原善》,P.11)。天道经由一个“继善成性”的环节而与人道连为一体,且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易传》中所谓的“继善成性”,是说“人物之生,其善则与天地继承不隔者也”[12](《原善》,P.9),即人之善性分于天道,生生之天德内在于人性之中,并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展现出天德生生而有条理之完善状态。“在天为气化之生生,在人为其生生之心”[12](《孟子字义疏证》,P.205),复经由人“心”作为能动转换,使人在自上而下的“继善成性”与自下而上的“下学上达”之间,实现天道与人道之间往复循环。天道有生生之天德,人道有生生之性;天地大化流行而有条不紊,人之日用常行亦有不易之则(条理)。简言之,天道善,人道善,如此天道论遂成为戴震论证其性善论的形上根据。戴震依据《易传》中“继善成性”的逻辑来论证天道运动方向与人类道德发展的一致性,非常接近于一种“目的论的自然主义”。[28](PP.328-329)可是问题在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拥有道德意志者才有道德目的可言,无意志之天又怎么能说是有道德目的的呢?天道又如何能够作为人性的本体依据呢?戴震在这里,展现了中国道德哲学传统中很特别的一种前定和谐的德性自然主义传统。
戴震虽然颇推崇汉学,可是他对“天”的理解,与孟子的义命之天、荀子的自然之天、汉代天人感应的神秘之天皆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从戴震对《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解释中就可以看出来。他说“论气数,论理义,命皆为限制之名” [12](《答彭进士允初书》,P.357),“命”只是作为先天自然的限定性(“受命之初”)和后天不可逾越的律则规定性(“非受命者所得踰”),用来解释天地万物“各限于所分”而各不同的原因,完全消解了孔孟之“天命”作为先天道德义务、命令之义涵。由此可见,戴震哲学中的“天”首先是“自然”之天,非是一个有道德意志和赏善罚恶之能力的神秘之天。可是与荀子自然之天不同的是,戴震虽然否认了“天命”的道德涵义,也不承认有一个超越的意志存在,却并不否认天或自然具有某种道德性——“天德”。戴震哲学中的“自然之天”虽然没有道德意志,却同时还是个高度拟人化的“义理”之天。在他看来,“善,以言乎天下之大共也”[12](《原善》,P.9),“仁义之心,原于天地之德者也”[12](《原善》,P.11),天道在道德上并不是中立的,而是自然而然地具有合乎人类道德之至善目的的完满性。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天道不是由某个神圣的意志所给定的,它是自然而然的,是非人为的;另一方面,天道虽不是由一个有超越的道德意志所主宰,却先天地包含着生生之德、有条不紊之理则(天理)、和谐的道德秩序在其中。因之戴震的“天道”既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天行有常),又同时是合乎人类道德目的(天有生生之德)的。此时,自然之宇宙也是一个道德之宇宙,自然天道之运行既遵循自然因果律,同时又能够符合应然的道德法则,成为一种自然与应然的统一体。正所谓“自人道遡之天道,自人之德性遡之天德,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12](《孟子字义疏证》,P.205)。此处的天道,显然已经上升到为一种道德价值上的本体,乃人极之所从出。对天道自然而又合乎目的的解释,如同预设一个全善的上帝存在一样,这其实是戴震一笔带过而未明言的“本体论承诺”。
在戴震看来,自然是生、息循环的,自然状态是仁慈、明智且和谐的。人类心智的责任就是发现它并遵守它,实现那自然、前定的和谐。对于相信自然道德完满性的自然合目的论,黑格尔曾这样解释:“当我们说世界是受天道的支配时,这意思就包含那前定的目的或神意在世界中是普遍有效力的,所以依此而产生出来的事物是与前此所意识着、意愿着的目的相符合。” [29](P.330)卢梭也认为,只有在“自然状态”中才能“最能保持和平,对于人类也是最为适宜的”[30](P.98)。要说与戴震的自然合目论最接近的,则非斯宾诺莎的自然神论莫属,两人“置伦理学于宇宙观的基础之上”[31](P.430),都对自然天道的道德完满性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其相似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两人在天道完美无缺的自足性认知上有共通之处。戴震相信天道生生之仁与人道生生之仁是一体相通的,他说:“与天地通者生,与天地隔者死。……人物于天地,犹然合如一体也。”[12](《答彭进士允初书》,P.358)依据天道而创生的人类,其本性也拥有了这种道德的完满性(还只是潜在的),通过人的道德实践最终展现出一种合乎天道的道德秩序。此种人为的道德秩序源于天道而又复归于天道,天与人、自然之宇宙与道德之宇宙最终真正地合二为一。持有自然神论的斯宾诺莎则不无类似地认为:“所有的自然现象,就其精妙与完善的程度来说,实包含并表明上帝这个概念。……所以我们最高的善不但有赖于对于上帝有所知,也完全在于对于上帝有所知。”[32](PP.61-62)此处的“上帝”可以与“自然”互换,所拥有的“最高的善”其实不是上帝的有意造作之结果,而是“自然”的天然本性使然。其二,两人在解释天地为何有不仁之现象时亦有异曲同工之妙。戴震认为这不能怪罪自然本身,而应归之于生物不顺应天道而“失其养”的结果。正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杀者,岂天地之失德哉!”[12](《孟子字义疏证》,P.200)斯宾诺莎也反对将先天的缺陷归之于自然,他说:“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是起于自然的缺陷,因为自然是永远和到处同一(和谐)的。”[33](P.96)两个人都认为,天地有生生之仁德、有天地万物相生相克之和,展现出一种仁爱、和谐的道德之大全,具有先天的道德完满性。其三,双方在伦理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上也有一致性。在自然天德具足无漏的前提下,斯宾诺莎认为伦理学的任务就是寻求“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而戴震则认为成德之教就是要人“归于必然”,认识并践履那生生不已的“自然之极则”(“不易之则”)。
当然,无论是斯宾诺莎的自然神论还是戴震的自然合目的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类道德理想在宇宙万物上的主观投射,饱含了一种过分拔高自然的浪漫主义情怀。其实,我们很容易找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反例,证明自然宇宙并非是一个完全合乎道德的宇宙。冯友兰就认为,“宇宙是道德底”的观点其实是一种“实体形上学”,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说法。可是在中国大多数儒者看来,恐怕并不认为天地有生生之仁只是一种理论上的预设或承诺,而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实。戴震认为“人之神明出于心,纯懿中正,其明德与天地合矣”[12](《原善》,P.15),天道与人道“斯二者,一也”[12](《原善》,P.11)。天道生生不息之伟力是人们可以真切感受到的,天道造物之广大与多样亦让人赞叹不已,人类倾向于相信天、地、人、我皆共有一体生生之仁。此一体之“仁”作为一种前反思的、主客未分的浑然在世的生存论体验,大概是儒者共认的“生命共感的情调”[34](PP.19-30),或者“本体论的觉情”[35](P.308)。这种生命仁心之体验和基调,不是等到宋明儒学那里才出现,早在《易传》“继善成性”的表述中就已经深探其源,只是为后来的宋明儒家“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观所认可和张大。戴震虽然批判宋明儒学,但道德主义的宇宙观传统则是明明白白地继承了下来。
市场发展和深化需要逐步打破基于家族和血缘关系以及师徒关系、同门关系的信任。要克服儒家文化存在的这种局限性,除了“君子”身份激励和教化以外,必须依赖良好的法治环境。
戴震的自然主义却又道德化的天道观,对于其建构一套道德哲学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这是对形而上学的“回归”,恢复了天道生生之仁的价值本体地位;另一方面,它又是对形而上学的“袪魅”,自然主义的合目的论与宋明时期理本论或心本论的独断、虚玄拉开了距离。这不仅为戴震接引孟子仁义内在于人性之中的观点奠定了形上学基础,为戴震“由自然归于必然(应然)”的道德学说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最关键的是为戴震的絜情理论提供了先天内在的情感驱动力。正是有了这种源于天德之仁心的内在驱动,人类自一开始就是非单纯追求情欲满足的道德动物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明乎‘生生’在东原道德哲学中所具有的枢纽地位,我们才不致误将东原视为与西方伦理学中的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或效益主义(utilitariansim)同科”[3](P.346)。总而言之,戴震哲学不是没有本体论,只是坚持了一种朴素而内在的、自然主义一元论立场。因此,如果囿于某一种形而上学基础主义的定见,批评戴震哲学为“无根之意见”[26](P.791),缺少一种“普遍原理的形上安立”[36](PP.25-44),或者批评戴震不懂“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区别,其实都是一种误解。
参考文献:
[1] 熊十力:《读经示要》,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
[2] 李明辉:《孟子重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3] 郑宗义:《明清儒学转型探析:从刘蕺山到戴东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刘述先:《儒学思想意涵之现代阐释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年。
[5] 惠栋:《九曜斋笔记》,《丛书集成续编》第9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
[6] 钱大昕:《续通志列传总序》,《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7] 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
[8]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9] 袁枚:《袁枚全集》第5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10]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11]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
[12] 戴震:《戴震全书》第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
[13] 余英时:《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14] 段玉裁撰、杨应芹订补:《东原年谱订補》,载《戴震全书》第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
[15]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6] 朱熹:《太极图说解》,《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17] 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
[18]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
[19]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2,《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20] 陈淳:《北溪字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1] 孙邦金:《乾嘉易学与“道论”形上学之重构》,《周易研究》,2013年第6期
[22] 张立文:《戴震》,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23] 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4] 戴景贤:《明清学术思想史论集》(下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
[25]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
[26]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下)》,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27] 岑溢成:《戴震孟子学的基础》,载黄俊杰编:《孟子思想的历史发展》,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
[28] 倪德卫:《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万白安编、周炽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29] 黑格尔:《小逻辑》,载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
[30]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31]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32]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33]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34] 陈立胜:《恻隐之心:“同感”、“同情”与“在世基调”》,《哲学研究》,2011年第12期。
[35]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36] 杜保瑞:《戴震重建儒学概念的理解与评价》,《哲学与文化》,2005年第378期。
Dai Zhen ’s View of Nature Law and Its Moral Metaphysics Foundation
SUN Bang-ji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China)
Abstract: Dai Zhen’s philosophy is highly valued by many works in modern times while the modern neo-Confucian appraisal of his philosophy is very low, which believes that his moral philosophy fails to give a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on the limitation of lust, the care of transcendence, and the basis of metaphysics. Thus, it is criticized as a utilitarianism, normative sentimentalism and scheming utilitarianism. In fact, the criticism, in some degree, has stereotyped views of metaphysical fundamentalism. However, the view of nature law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s constitute Dai Zhen’s theory — a very economical and simple form of natural integration theory 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ursuit of human nature and ethics. This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era of the general decline of morality and moral alienation in the Confucianism, which should be given full affirmation.
Key words: Dai Zhen; view of nature law; moral metaphysics; theor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中图分类号: B249.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338(2019)06-0012-08
DOI: 10.3969/j.issn.1674-2338.2019.06.002
收稿日期: 2019-09-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儒家仁学与共同体美德振兴研究”(18BZX080)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孙邦金,温州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哲学与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