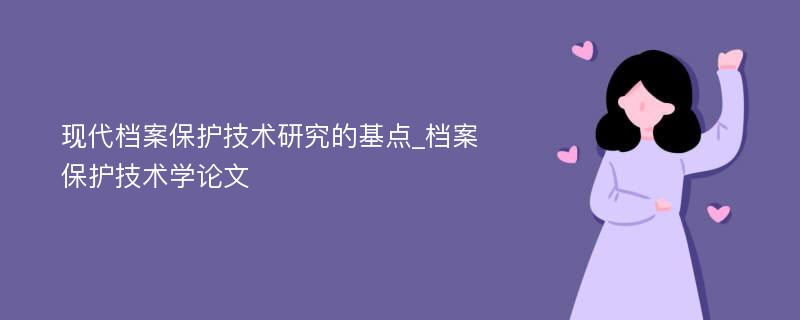
论现代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基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点论文,档案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点是指“中心”、“重点”、“基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19页。)。由此可以认为,学科研究的基点是该门学科研究的起点和要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学科方法论的选择都必须以学科基点为基础,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学科基点便会产生什么样的理论体系。”(注:彭斐章教授七秩寿庆论文集编辑小组:《当代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论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这充分表现了学科基点对于学科建设不可低估的作用。
档案保护技术在我国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注:金波:《档案保护技术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此后,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经历了起步、停顿和发展的阶段,迎来了90年代初的高峰,步入了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注:周耀林:《对1949-2000年的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档案学研究》2002年第4期,第36~37页。)。现阶段,探讨本学科研究的基点,规范其内容、体系及方法论,不仅有利于促进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有助于推动本学科走向成熟。
一、历史回顾: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基点的探索
我国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基点的探索经历了40余年的历史。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目前只有只鳞片爪,没有完整的专门著述,却可以让我们追寻本学科研究基点探讨的历史足迹。
从文献回溯上看,我国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基点的探讨以1961年出版的《档案保管技术学》为嚆矢。此后,随着多次再版、修订,该教材的内容和体系日臻完善,并逐渐达成了共识:档案保护技术学就是“根据档案制成材料的损坏原因,研究保管档案的技术方法的一门学科。”(注:冯乐耘等:《档案保管技术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1991年,冯乐耘和李鸿健同全国7所高等院校的专业教师合作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档案保护技术学文科教材,提出了“档案保护技术学是研究档案制成材料变化规律和保护档案的技术方法的学科。”(注:冯乐耘,李鸿健:《档案保护技术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由于档案制成材料和保护技术方法被并列为本学科研究的基本内容,笔者将这种学科基点观归纳为“两点论”。10年后出版的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中,郭莉珠沿袭了“两点论”,并以此建构了档案保护技术学的学科体系(注:郭莉珠:《档案保护技术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两点论”一直引导着我国的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被公认为是学科传统的基点理论,对于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作用不容忽视:它率先规范了本学科研究的基点,建立了学科基本理论,增强了学科理论建设,引领着学科逐渐走向成熟。
进入90年代后,随着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高潮的迭起,本学科研究基点这一理论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出现了一些崭新的观点。
刘家真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文献保护学研究的基点,提出了“矛盾论”:“文献保护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运动着的过程,在运动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矛盾,如‘变质与保存’,‘保护与使用’等。”(注:刘家真:《文献保护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这一观点首次突破了传统的理论,燃起了学科基点理论探讨的火把。12年以后,罗茂斌发扬了这一理论,旗帜鲜明地指出,档案保护技术学以“档案价值的长期性和永久性与档案制成材料寿命的有限性这一特殊矛盾为研究对象的。”(注:罗茂斌:《档案保护技术学》,云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还有一种理论可以称之为“档案材料主体论”。“档案制成材料损毁规律的研究是学科的基石”(注:周耀林:《新编档案保护技术学》,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在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金波提出,档案保护技术学“主要以研究档案的物质材料为依据,并通过研究物质材料的特性和损毁规律进一步研究保护档案的技术方法,以延长档案的寿命。”(注:金波:《档案保护技术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这是对“两点论”的改进,既继承了“两点论”,又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其中的重点,体现了对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基点的反思。
此外,还有“技术论”。现代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现代化材料(感光材料、磁性材料等)的保护技术方法……”(注:周耀林:《档案保护技术学体系结构之我见》,《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1期,第45页。)。这突出了本学科的技术特征,反映了档案保护学界对技术层面的重视。
可以看到,历时40余年,我国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基点的探讨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不仅丰富了档案保护技术学的理论研究,也为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走向新时代铺垫了基础。
二、现实反思:信息环境对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基点的影响
世纪之交,回顾、总结、反思与展望构成了本学科研究的一道风景线。经过了40余年的发展后,面对信息社会化和社会信息化,相对冷静的思考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正是我国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
赵淑梅认为,在信息技术面前,档案保护技术需要进行“革新”;这个革新是“整个体系的,而非在传统技术体系中的局部调整和修补……”(注:赵淑梅:《21世纪档案保护技术体系的革新》,《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第57页。)。她提出了建立“电子档案保护技术学”的主张,以“探索数字信息的完整、安全、可靠的技术手段和法规体系,其目的是保持数字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长期可读性。”(注:赵淑梅:《电子档案保护技术学初探》,《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4期,第69页。)张美芳分析了传统档案保护技术指导思想的实质以及数字时代档案保护的新问题,认为现代档案保护所“保护的内容拓宽了,保护的范围变广了,保护的难度加大了”,传统的档案保护已经很难“正确地体现”现代档案保护技术学的研究内容了,字里行间渗透了变革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要求和呼声。(注:张美芳:《数字时代档案保护指导思想的变化》,《档案与建设》2002年第2期,第16页。)
透过以上代表性观点不难看到,受当代信息环境的影响,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面临着新的问题,例如新型信息载体、新兴技术方法的选择和运用等。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下的文档管理一体化所带来的保护问题。
第一,文档管理一体化改变了传统档案保护的程式。传统的档案保护通常发生在库内,针对于收集入库的档案。OA环境下,文件一经生成,便可以成为档案,“档案无孕期出生”,档案与文件的界限越来越不分明(注:张美芳:《数字时代档案保护指导思想的变化》,《档案与建设》2002年第2期,第15页。)。这种形势下,档案保护不再局限于库房,而是渗透到文件形成之初,需要采取安全防护的思想,通过前端控制来确保文档的安全。
第二,文档管理一体化拓宽了档案保护的对象。由于目前信息存取及信息备份材料的法规上的缺位,任何信息载体都可能成为物理存档的载体,最终转化为保护的对象。既使是某些不具耐久性的信息载体,随着实践活动的需要,或迟或早也会进入档案馆,因此,现代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宽泛了。
第三,文档管理一体化扩充了档案保护的主体。传统档案保护的主体是档案工作人员。现在和将来,这种情形不会发生多大变化。但是,随着保护文档的需要,与电子文件形成和保管有关的人员,如文秘、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数据安全维护等方面的人员也加入了保护文档的行列,客观上加强了档案保护的队伍。
正是因为这些变化,现代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学科研究范畴。革新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不仅是一种感慨和呼声,而且是大势所趋。这种革新,正如赵淑梅所言,是“整个体系”的“革新”。由于学科基点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和重点,它自然而然就成为学科革新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最基本的问题。因此,立足于信息时代的变化,如何重新审视本科学的研究基点并树立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这既是对过去我国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基本概括,也将促使本科学的研究走向新的起点。
三、走向未来:现代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基点的确立
确立现代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基点必须站在当代科学发展的潮流上,以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为依据,进行理性地思考。
当代科学的发展显示出了两种相反的趋势:分化和综合。分化使得学科分支越来越深入和细微,综合则形成了横断学科、交叉学科等。档案保护技术学的分化有目共睹,《缩微复制技术》、《档案修复技术》、《声像档案保护技术》早已自立门户就是最好的例子。与此同时,档案保护技术学的综合化也已经初露端倪。
传统的档案保护技术学比较强调本学科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联系。现代档案保护技术学与这些自然学科的联系日益加深,同时与信息管理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等也发生了联系。2002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偏微分方程的动态图像的恢复》就是以计算机为工具,运用偏微分方程的理论对已经褪变、划伤的电影胶片进行修复,这是传统的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望尘莫及的。这种变化趋势在确立现代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基点时不容忽视。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现代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基点是信息载体,即记录信息的各种物质材料。这是笔者对“档案材料主体论”的进一步思考,其主要原因有:
首先,存档载体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所有形式的信息载体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存档载体,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馆藏档案。换言之,信息载体与档案记录材料是同源的:信息载体的变革肯定会带动档案记录材料的变化。因此,要延长档案的寿命,不是消极地、被动地保护馆藏档案,而是需要树立前端控制的思想,从源头抓起,从研究信息载体的质量入手,从中遴选优质的档案记录材料,真正做到“以防为主”。
其次,离开了对信息载体的研究,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将会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关于光盘存档的讨论就是一例。国外有人通过媒体选择记分卡方法的研究,提出了CD-R和DVD-R是适于存档的光盘类型(注:Selecting Storage Media for Long-Term Preservation.http://www.pro.gov.uk/about/preservation/digital/guidance/selecting-storage-media.pdf。)。法国国家标准NFZ 42-013将CD-ROM作为存档载体(注:周耀林:《法国档案文件数字化实践》,《北京档案》2002年第4期,第37页。)。在我国,新近颁布的国家行业标准《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并没有具体的规定(注:GB/T18894-2002。),有人建议用CD-R存档(注:郭莉珠等:《CD-R光盘预期寿命探析》,《档案学通讯》2002年第4期,第68页。),也有人认为完整结构的CD-ROM和含酞菁染料的CD-R更具有存档的资格(注:周耀林:《存档光盘质量的比较研究》,《档案学研究》2003年第6期,第39页。)。国内外对光盘存档的种类莫衷一是。这表明,离开了对信息载体的研究,档案记录材料的选择就无所适从,档案记录材料的质量就无法保证,日后的保护工作将会更加困难,保护档案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第三,信息环境下电子文件的归档保管也难以离开信息载体。目前,电子文件的归档主要有物理归档和逻辑归档两条途径。物理归档需要一定种类和格式的信息载体实体,否则便不能完成;逻辑归档以网络载体为工具,对信息载体实体的依赖性似乎不大。但是,为了保证脱机状态下信息的可存取性,也必须使用特定类型与格式的信息载体实体。从这个意义上看,信息载体是决定电子文件能否长期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为了保证电子文件的归档保管及其长期可读,就必须选择利用合适的信息载体。
综上所述,以信息载体为基点是现代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客观要求。以信息载体作为本学科研究的基点,可以促使本学科在以下方面发生变化:
第一,积极进行前端控制,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真正做到“以防为主”。以信息载体为基点的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可以通过信息载体的研究,对不同质量的信息载体进行功能定位、合理使用、科学管理,甄别并挑选恰当的存档载体,并通过法规政策进行规范,从而保证存档载体的质量,这将减轻了日后保护工作的负担。
第二,主动采取防护措施,变消极保护为积极保护,使得保护过程更加科学化。以信息载体为基点的现代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对不同信息载体的综合性能更加熟悉,对各种信息载体的损毁规律更加了解,就可以有的放矢地为各种材料设计不同的保护条件和保护方法,使得保护工作更加科学、合理,有利于各种档案材料的延年益寿。
第三,正确指导选取修复材料,变盲目使用为科学选用,以保证修复的质量。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面貌,对遭受破坏的档案或者丢失的档案进行实体修复、信息恢复已经成为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如何选择恰当的修复材料和信息存取载体是修复工作必须面对的问题。通过信息载体的研究,可以为修复工作提供科学的参考。
可见,信息载体在档案保护的全程都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以它作为现代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基点,不仅会带来学科研究体系和内容的变革,而且会促使档案保护技术学沿着不同的路径与其它科学发生整合: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相联系,融合在自然科学中;与材料学、计算机科学等相结合,聚合在技术科学中;与环境管理学、信息管理学、组织科学、行为科学等相交叉,整合在保护管理科学中。这样,如果把传统的档案保护技术作为微观研究层次,文档一体化过程中的文档保护是中观研究层次,那么,学科正在发生的整合则属于宏观研究层次。以信息载体为基点,立足微观研究,胸怀中观研究,放眼宏观研究,这体现了本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以信息载体为研究基点,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化趋势,体现了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本质特征,提高了学科的理论性、科学性、技术性和应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