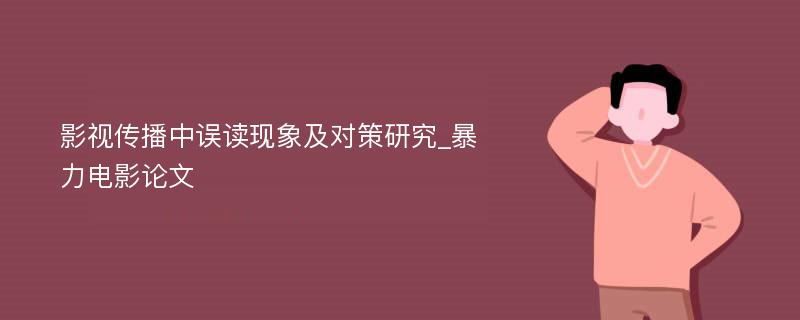
影视传播中的误读现象及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读论文,现象论文,对策研究论文,影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今天高度互动的传播环境中,资讯的传播速度与层面都远远超过传统的单向式传播,而在诸多的媒介中又以电视、电影包括光碟、录影带以及有线电视、网络等以声像传递信息的视听媒介为时代的佼佼者。但是在为视听媒介能提供如此便捷而影响广泛的传播而欢呼之后,人们迅即发现视听媒介在传播过程中亦能造成误读。 误读, 在英文中与misunderstanding相对应,意即不能得出事物正确的或原本的含义。在视听媒介高速发展的今天,阅听人不能得到视听传媒所传播信息的原本含义,必将引发十分严重的后果。
一、若干误读个案的分析
①1995年,美国著名导演奥立弗·斯通拍了一部名为《天生杀人狂》的暴力电影。美国的一对年轻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就开始了一场射杀的狂欢,并由此引发了一宗针对该影片的诉讼案,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奥立弗·斯通的影片诱发了这一暴力事件的产生。(注:参见[美]Mark Miller,Hollywood Goes On trail,NEWSWEEK,1999,8.)
②1997年,震惊台湾、香港、大陆三地的白晓燕被绑架案,歹徒曾经在电话中对白冰冰提及《绑票通辑令》的电影,作案手段相似。(注:转引自董素兰:《传播媒体对阅听人的潜藏影响》,载《民意》1998年7月号。)
③1989年,台湾一对正值青春期的兄妹,趁大人不在家,在客厅的地毯上跟着黄色录影带依样画葫芦,造成尚在念中学的妹妹怀孕。(注:转引自董素兰:《传播媒体对阅听人的潜藏影响》,载《民意》1998年7月号。)
④1988年,国产电影《红高粱》上映,在全国观众中欣起轩然大波,有不少人对这部电影进行了严厉的斥责,把《红高粱》说成是“一部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同时也是一部矛盾百出、胡编乱造的影片。”(注:D.W:《〈红高粱〉是丑化中国人的影片》,载《中国电影时报》1998年5月5日。)
⑤1997年,由话剧《雷雨》改编而成的电视连续剧,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原著中深刻的社会批判主题消失了,悲剧的实质变成了女性情感追求与这种追求的不可能实现的冲突……于是分量厚重的题材变成了通俗、言情的风月故事。”(注:桑宁霞:《名著的思想主题不容背离》,载《文艺报》1997年4月24日。)
上面所列举的个案都是十分典型的误读的现象。
个案①中奥立弗·斯通的《天生杀人狂》、个案②中《绑票通辑令》和个案③中无名的黄色录影带,在制作意图上有着明显的差异。研究电影的人很少有不知道奥立弗·斯通的,他的这部电影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在于,他用一对杀人狂的经历展示了他对电影所造成视觉效果的探索,MTV的拍摄手法、歪斜的地平线、戏剧舞台的布光, 在极短暂的时间里迅速变化画面而达到的视觉轰炸等等。个案②和个案③也不是以教唆人怎样犯罪为目的的,无非是以色情和暴力作为刺激,引诱阅听人潜在的感官欲望,以便获得利益。然而,青少年作为自控力低的人群,却从中看到了实施罪恶的手段和被挑逗起来的淫邪之欲。
发生上述误读的心理原因,在学界往往用“心灵瘘管”论来解释:色情和暴力通过心灵施加超强的刺激,留下的记忆痕迹会在潜意识中形成顽固的通道——“心灵瘘管”,能够摆脱理性和道德监控。这种“瘘管”一旦形成,每当人有类似的骚动和刺激后需求发生时,就会避开理性和道德的控制,而接通色情与暴力所留下来的“瘘管”,重复同样的行为。视听媒介,尤其是电影和电视,由于具备形象生动的再现功能,容易对阅听人产生巨大心理冲击力,因而经常会导致实施类似的偏误行为。
在国外,由视听媒介造成的青少年色情与暴力的误读,已经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在我国,电影电视的播放与制作都对色情和暴力成分有严格的限制,但盗版淫秽暴力录影带和光碟造成的青少年的不良误读也越来越严重。
个案④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意义上的误读。电影《红高粱》的导演张艺谋曾多次明确表示过他的拍片意图:“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具有粗旷、浓郁的风格和灌注着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作品。莫言的小说《红高粱》的气质正与我的喜好相投。那高梁地里如火如荼的爱情,那无边无际的红高梁的勃然生气,那些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浑身热气和火力、随心所欲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的男人和女人们,都强烈的吸引着我。这部影片表达了我对生活、对电影的思考,是一次真正的自我写照。”(注:刘炳琦、刘国梁:《生活艺术民族精神——张艺谋就电影〈红高粱〉答本报记者问》,《光明日报》1998年3月15日。 )“我就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爱就真爱、恨就真恨,大生大死,大恨大爱,我就是要赞美生命的纯洁……发乎自然,合乎性情,坦坦荡荡,”(注:周友朝:《张艺谋谈电影〈红高粱〉》,载《大西北电影》,1998年第4期。 )张艺谋表白的导演意图与个案④中的批评相比,两者相去甚远,仿佛讨论的不是一个作品。
那时候的观众,多年来受传统电影单一僵化模式的熏染,对张艺谋技巧与思想方面都显示出极其前卫特征的《红高粱》,很难准确阅听。在技巧层面,《红高粱》第一次把仅属背景的——高梁——自然景物,渲染得如此浓烈:当“我奶奶”牺牲时,更是大胆使用象征手法,将天空中的一轮红日变成了黑太阳,这些电影技巧在视觉方面都对长期惯于欣赏现实主义电影,讲求象生活一样真实感的观众,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红高粱》也时时透露出反传统的思想,几千年来遭人唾弃的“野合”,成了张艺谋歌颂生命与人性的象征,一段抗日的历史被用“恶作剧式”的而不是严肃认真的态度讲述出来,抗日英雄和农民也一改往日高、大、全和朴实憨厚的传统形象。观众对《红高粱》的误读更多的是来自一种对突破原有模式而带来的无所适从的愤怒。
个案⑤则完全是对原著进行了有意识的误读,导演要“以电视剧的眼光来拍”《雷雨》。电视连续剧《雷雨》的导演李少红认为:男人和女人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女人靠她的思维理解事物,男人用理性主导行为选择”。由此,她对《雷雨》中男女主人公的行动重新进行读解。然而作为面向大众的视听媒介,把对经典名著仅具探索性诠释的信息作普遍的传播,不仅难于让业已形成的原著的巨大读者群服气,而且对没有接触过原著的阅听人则造成了错误信息的传播,因而在影视传播领域,导演的误读就变成了一种不良性质的误读。
上述个案,分别代表了几种典型的误读方式,误读可以发生在主题方面、文化方面、视像方面等等。各种各样的误读,在这个视听媒介无处不在的时代,正伴随资讯传播的发达而不断产生。
二、视听媒介的影响及误读的普遍性
误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就是一种误读。然而,在视听媒介的传播过程出现的误读现象,就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不良影响。
首先,视听媒介传播的范围广,影响力度深。电影可供复制的拷贝,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录影带和光碟,使得同一声像信息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里,被不断的进行传播,录影带和光碟由于操作技术的方便和价格低的低廉,更是可以达到凝固稍纵即逝的影像目的,并提供反复仔细阅听的便利;卫星电视的出现,则使同一声像信息在同一时间内,向某一区域乃至全球的范围进行传播成为可能。同时,与其他的媒介相比,报刊只能诉诸人的视觉,并且其信息主要是逻辑化、抽象化的,广播只诉诸人的听觉,而听觉又不如视觉敏锐,只有视听媒介不仅调动人的听觉与视觉,而且可以以具体生动的画面“虚拟实境”,刺激人的感官。因而“视听媒介在传播一定数量的有关某种主题的信息上,要比单纯的听觉或视觉媒介更为优越一些。”(注:转引自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29页。)
那么,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视听媒介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1949年初版的《大众传播实验》汇集了霍夫兰等心理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做的传播实验。其中关于影片《英国之战》的实验,被一些传播学研究者认为是最完善的实验。这部影片真实的描述了英国与德国的战斗,并提出英国的英勇抵抗为美国赢得宝贵的备战时间。经实验证实,该片能提高士兵对英国的信心。结论是影片确实有影响观看者态度的作用。1969年美国公共卫生局长报告的《电视和社会学习》部分曾指出:“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公认个人的态度,价值和行为都可由观察中学习……。虽然学习不一定导致行为,却可能成为优先的选择。”(注:[美]Shearon A.Lowery Melvin L.De Fleur著.王嵩音译:《传播研究里程碑》,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初版。)在前述个案①②③中当事人虽然无法确定是模仿了哪一个镜头中的哪一个行为,但他们在实施行为时是有意识的倾向于模仿某一影片的。
其次,按照拉斯威尔(Harold Lasswell)的观点, 大众传播有三大社会功能,其第三大功能即传播文化,使社会上世世代代能承袭固有文化。这种功能使得传媒扮演起了一个“凡人之职,圣人之责”的角色。作为“固有文化”守望者,传播从业人员必须对“固有文化”持有一份准确的认识和理解,并在传递的过程中,尽可能少的施加从业人员的个人意见和影响,在排除即使准确的进行了文化的转述,阅听人也可能因为自身的文化修养、欣赏习惯、性格气质、职业乃至阅听环境等因素而导致误读的情况下,传媒应当成为克尽职守的传递文化的中转站。
在当今传播高度技术化,覆盖面广而又影响深远的时代,视听媒介越来越成为建立文化霸权的一种最便利的道路。美国好莱坞的电影是美国在世界各个角落推销其价值观、人生态度和文化的一张最有效的王牌。在影片的潜移默化之下,一些观众在获得娱乐的同时被轻而易举的说服,接纳了美国式的英雄、美国式的爱情、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不知不觉中,好莱坞的电影蚕食了观看者的“固有文化”,培育出一批批“崇美”、“亲美”的阅听人,这些人不满足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却对电影中出现的国度怀着幻想式的温情;而另一些观众则会强烈的感到民族文化尊严的极度受挫,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在法国就遭到了愤怒的观众焚烧拷贝的命运。为了实现对“固有文化”的捍卫与传递,如何有效的防止对通过视听媒介入侵的外来文化的消极误读,在伴随信息产业高速发展而带来的全球化过程中,将越来越成为文化本土化的重要方面。
阅听人发生误读往往是“非外化的”。正如前文提到的美国卫生局长报告中所说的那样,(误读)“不一定导致行为,却可能成为优先的选择”,这意味着阅听人在阅听过程中发生误读,并不立即表现为行为,误读只是作为一种潜在的态度存在于阅听人身上,不易被发现,也不引起人们的警觉。然而,一旦阅听人以误读到的信息指导实施行为时,再试图消除误读的影响就为时晚已。以前,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视听媒介中色情与暴力镜头会对儿童和青少年产生恶劣影响之前,美国的许多父母都放心地把孩子交给电视,因此电视又被称之为baby-sitter,意即临时保姆。只是当出现大量儿童和青少年模仿电视中色情与暴力镜头进行犯罪时,人们才感到震惊并开始关注。
儿童和青少年对视听媒介中色情与暴力的误读,至少会在一定时间内以行动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成年阅听人在文化方面的误读则很难被发现。成年人由于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往往可以隐藏自己真实的态度和思想,被误读的信息就此转化为内在的知识、态度、观念、倾向和心理内涵等等,没有极为适当的时机或者遇到与其极其相左的意见而不得不一吐为快时,这种误读的结果就不会被表现出来。
三、警惕和防范误读
对误读的防微杜渐当然首先应起于传播业内,即对视听媒介进行必要的把关。施拉姆把记者、编辑、作家、电影和电视的制片人、影片剪辑、图书管理员等等都归结为“把关人”。电影和电视的制片人决定着摄影机应该指向哪里,剪辑师确定影片中应剪掉和保留哪些内容。事实是,面对金钱的诱惑,市场激烈竞争的压力,“把关人”已经越来越多地失去了“把关”的作用,以至于色情暴力成分屡屡出现在视听媒介中。据统计,好莱坞电影中有23%属于儿童不宜,法国录影带出租店有30%属于“黄色窝点”,从1992年到1993年美国《电视暴力管理法》出台,美国三大电视网仍保持每个小时最少有18个暴力镜头。
当媒介的自律已不能有效的阻止易于被误读信息的传播时,国家机器的力量对媒体的强制制约,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美国自1997年10月1日,继电影的分级制度之后,开始实施电视分级制度,使用V—chip晶片过滤电视里的“性”、“暴力”、“脏话”与“性讽刺的对话”。然而与电影的分级制度实施后的情况相类似,分级制度并没有有效的控制该媒介中的“性”“暴力”的成分。
真正的对视听媒介中的色情与暴力等易被误读因素进行坚决抵制的,是公众。早在三十年前,美国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牛顿·迈诺曾激烈地抨击电视说:“我请你们坐在电视机前,一直盯着电视,直到播送完毕,我敢保证,你们将会看到大片荒原。你们会看到一系列的游戏与暴力节目,令人无法相信的、公式化的家庭喜剧,以及流血杀人,残暴的色情狂、侦探、匪徒、西部牛仔,还有没完没了的广告。不错,你们只想看到高雅有益的东西,而这些又非常少。如果你们认为我言过其实,那么不妨去试一下。”(注: 转引自李彬: 《反观电视》,载《学习》,1994年第3期。 )美国大众更是对电影电视中的精神污染持批评态度。据《纽约时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4%的父母曾限制子女收看某些节目;64%的家长曾限制孩子观看近期电影;52%的人认为影视中的色情内容导致青少年放纵;56%的人认为,影视的暴力内容是青少年趋向暴力的主要原因。《电视暴力管理法》就是在公众的批评舆论的压力下促成的。1998年5月15日,在台湾更是发生了一起很有意义的事件。 是日,台湾电视研究文化委员会联合励馨基金会、妇女救援会、富邦基金会以及现代基金会四个团体,成立了“拒绝脱轨色情律师团”,一同检查267集册录影带,详附影片内容及播出时间, 告发有线电视“星颖”、“彩虹”、“S频道”涉嫌触犯刑法妨害风化罪。 在以后防止色情与暴力等易被误读信息在视听媒介上的传播的斗争中,公众批评的怒火仍将是中坚的力量。
英国学者霍尔(Stuart Hall)认为, 传媒是现代文化符号编码的(encoding)工具,事实上,虽然支配性的力量可以通过传媒对其“可欲文化”加以编码,但是对文化符号的解码(decoding)则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对于影视工作者而言,电影和电视,不仅是一种信息传递的方式和渠道,同时还是一种艺术形式。但由于文化理解的多样性的原因,在解码者与编码者的编码发生误读的时候,需要有另一种文化批评在两者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譬如,巴拉兹在《电影美学》的“理论礼赞”篇里说,诗人、画家和作曲家也许会被湮没,但他们的作品却能流传,而电影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鉴赏,首先遭到灭亡的不是艺术家,而是艺术作品本身,甚至在作品还没有问世之前。这一点在电影王国——美国得到了很好的认识。在美国,除了电影媒介自身外,其他重要媒介如电视、报纸、杂志,每周每期都有关于电影的信息,而且不仅仅是拍摄花絮或电影明星的花边新闻,还包括大量的专家的批评性文字。比如知名杂志《时代》(TIME)、《新闻周刊》(NEWSWEEK)都不会放过对近期有影响力的影片进行较有深度的讨论;各家电视台更扮演起了对电影进行阅听指导的角色,“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的专职影评人员每周都有二个小时的专题节目对正在上映和将要上映的影片进行评论,有两位评论家以讨论的形式来进行——这个节目的视率很高,包括一些知识分子的观念。”(注:[美]鲍玉珩:《美国影评家眼中的当代美国电影》,载《电影艺术》,1998年第1期。)电影虽然是一种娱乐形式, 但并非人人会看,发生误读更是再所难免,正是这些各种各样的、不厌其烦的批评为美国电影培养出一批爱看电影会看电影的观众,电影的解码者和电影的编码者的差异被减少到最低限度。
时值视听媒介与阅听人频繁互动的今天,针对误读的批评不仅给既成事实的误读现象以当头的棒喝,更重要的是教会阅听人如何避免误读。虽然阅听人受视听媒介误读信息的影响并不会有恒久性,但误读的影响往往要延续到阅听人接触到正确的信息之后,就象没有读过曹禺《雷雨》而只看到了电视剧《雷雨》的人,只有等到他阅读了原著后才有可能修正他对《雷雨》的认识。然而,批评的出现却可以大大缩短消除修正所需的时间,并教会观众有选择的接受信息。在各种戏说历史的电视连续剧占据荧屏后,出现了激烈的关于“历史剧”的历史与艺术、历史与娱乐关系的讨论,完全对立的立论基础使讨论并无结果,但是却使观众懂得了学会甄别传播内容的正误。于是出现了由于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演播热潮引发了公众读清史的热潮。
当然,批评对于“非外化”的隐性误读并无良策,只能充当最有效的预防药。当人们陶醉于《独立日》里地球人与外星人逼真变幻的战斗场面时,也看到了美国人企图领导全球的那种大国的自我膨胀。批评这时要告诉大家的是:《独立日》只不过是美国人的一个想象力丰富的科幻影片,其中美国人对自己要作全球领袖的欲望做了毫不掩饰的投射,而观众则完全没有必要因此生出顺从影片情感倾向的“崇美”情绪来,即便这只是一种没有导致任何行为的情绪。
批评对于匡正阅听人阅听视听媒介所产生的误读,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进行耳提面命的灌输,它需要传媒载体,它也可能并非完全正确,但批评对于现代视听媒介的传播是必须的——有了批评,才有可能引起疗救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