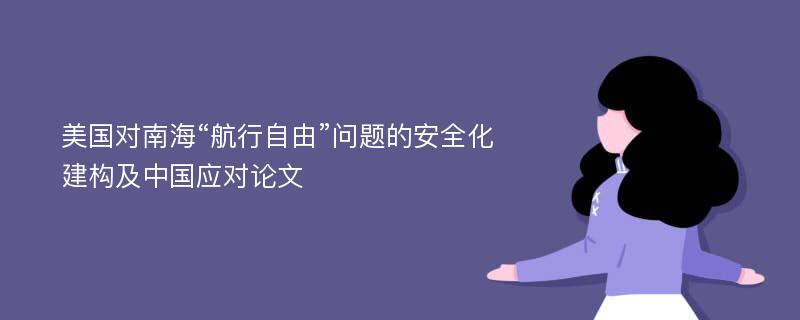
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安全化建构及中国应对
邢瑞利1, 2
(1.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210046;2.中共南通市委党校,江苏 南通226001)
摘要: 安全化理论是哥本哈根学派的核心理论,其主要论点是安全并非客观既定而是“言语-行为”的主体间社会建构,任何问题都能被主观建构成安全问题。安全化包括三种建构路径:话语凸显与安全化启动、话语框定与安全化传播、话语定位与安全化行动。南海“航行自由”本不是安全问题,但近年来美国试图将之安全化。美国作为安全化主体,有意通过“话语凸显”方式宣布南海“航行自由”存在威胁;借助媒体载体渲染所谓的安全威胁,并进行“话语框定”将其定位成国家利益;最后通过“话语定位”采取行动措施应对,从而使南海“航行自由”迅速演变成中美乃至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美国较为成功的安全化取决于其拥有强大的传播和动员能力以及得天独厚的国内制度优势,并利用了南海安全困境下争端相关国家的忧虑情绪。鉴于此,中国需进行“去安全化”努力,促使美国的安全化只是一种主观意图。
关键词: 南海“航行自由”;美国;安全化建构;中美关系
中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主要指双方针对外国军用船只、舰机在中国南海附近水域及空域是否具有活动权限而产生的分歧及摩擦。① 李岩:“中美关系中的航行自由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1期,第22页。 近几年,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愈发成为中美两国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尤其是2015年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频繁提到南海“航行自由”,美国国内鹰派强烈建议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并且派遣军机军舰进行巡航侦查,关于是否应该及如何开展行动的争论长达半年。② 吴士存、胡楠:“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体系与遵约议价模式研究——兼论对南海形势的影响”,《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4期,第104-105页。 最终,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海军在南海先后开展了4次“航行自由”行动,而特朗普上台之后,截至2019年2月11日,美国军舰也已10次闯入南海。美国频繁在南海行使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增加了中美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使得双方战略疑惧加深。
目前国内关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研究成果已比较丰富。分析来看,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视角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展开探究:第一,从历史视角探究美国“航行自由”计划的历史演进、思想及政策渊源。从卡特政府制定出台“航行自由”计划后,美国逐渐在全球范围开展“航行自由”行动,近几年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就是该计划的产物。① 马得懿:“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与北极航道秩序”,《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1期,第1-11页;张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变化与应对”,《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9期,第94-100页;张小奕:“试论航行自由的历史演进”,《国际法研究》,2014年第4期,第22-34页;曲升:“美国航行自由计划初探”,《美国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2-116页;叶强:“南海航行自由:中美在较量什么”,《世界知识》,2015年第16期,第34-36页;段琼:“从南海争端看中美航行自由制度”,《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7期,第27-28页;李岩:“中美关系中的航行自由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1期,第22-28页。 第二,从理论视角探究美国“航行自由”计划的理论逻辑。例如,吴士存等认为,美国的南海“航行自由”计划采取一种“遵约议价”的模式;② 吴士存、胡楠:“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体系与遵约议价模式研究——兼论对南海形势的影响”,《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4期,第104-116页。 包毅楠指出,美国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理论基础是“过度海洋主张”理论。③ 包毅楠:“美国过度海洋主张理论及其实践的批判性分析”,《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5期,第124页。 第三,从国际法和认知理论视角揭示近年来中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愈演愈烈的原因。国际法学者认为“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产生的法理诱因在于中美对国际海洋法内容的认知分歧。④ 李岩:“中美关系中的航行自由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1期,第24页;黄凤志、刘瑞:“应对中美关系南海困局的思考”,《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2期,第38页。 国内学者还引入认知理论,认为近年来中美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存在较为明显的认知错觉,对身份的错误认知致使冲突的产生。⑤ 荣正通:“身份认知差异与中美关系中的南海问题”,《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2期,第140-152页;柳思思:“身份认知与不对称冲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2期,第114-127页;齐尚才:“错误知觉、议题身份与国际冲突——以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议为例”,《外交评论》,2017年第5期,第65页。 第四,揭露美国实施南海“航行自由”计划的意图、目的及实质,并对中国如何应对提出具体对策建议。⑥ 张景全、潘玉:“美国航行自由计划与中美在南海的博弈”,《国际观察》,2016年第2期,第87-99页;曲升:“美国航行自由计划初探”,《美国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2页;曹文振、李文斌:“航行自由:中美两国的分歧及对策”,《国际论坛》,2016年第1期,第20-25页;袁发强:“航行自由制度与中国的政策选择”,《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第82-99页;黄凤志、刘瑞:“应对中美关系南海困局的思考”,《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2期,第35-46页;黄冕:“中国外交中的南海航行自由话语研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4期,第40-55页;齐皓:“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国内争论及政策逻辑”,《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1期,第21-30页。
综合国内研究状况可以看出,已有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产生的思想与政策渊源,美国强硬推行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现实逻辑,以及中美对该问题的认知分歧等。然而,已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国内已有研究更多是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时政性研究,缺乏理论的深度。尽管有学者以“遵约议价”模式来解释美国实施南海“航行自由”计划的理论逻辑抑或用认知理论来阐释中美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持不同解读背后的深刻根源,然而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早在1995年中菲“美济礁事件”后就被美国提及,为什么在2015年才突然成为南海争端争议的焦点,已有研究并未作出回答。第二,国内已有研究仅仅停留在静态层面,并未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是如何凸显的,是否具有阶段性,美国推进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动态路径是什么等问题作出详细回答。
事实上,关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安全化研究视角还未引起学界太多的关注。南海“航行自由”在当前存在争论:即它是一个安全问题吗?从安全化理论(Securitization Theory)出发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所谓“安全化”是指安全化主体以“言语-行为”(speech-act)形式将某些普通议题主观建构为安全议题的过程。哥本哈根学派⑦ “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这一术语是比尔·马克斯威尼(Bill McSweeney)提出的,他认为前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出版了多部与安全有关的著作,完全可被授予学派称号。参见潘亚玲:“安全化、国际合作与国际规范的动态发展”,《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第51页。 认为,安全已经超越“客观上无威胁,主观上无恐惧”的传统简单认识,表现为更具有社会互动意义的、体现关系性质的主体间无冲突。安全化理论创始人奥利·维夫(Ole Waever)指出,安全问题的产生并非客观既定,而是在社会建构中被认定,被认定的过程就是安全化的过程。① Ole Waever, “Politics, Security, Theory”, Security Dialogue ,Vol.42, No.4, 2011, p.469.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安全化过程体现为一种社会主体间建构,任何问题都能升级转化为安全问题。② [英]巴里·布赞、琳娜·汉森著,余潇枫译:《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227页。 安全化主体可以对任一问题进行主观建构,推动其进入政治议程成为安全议题,在某种程度上将安全沦为某一国家的政策附属品。③ [英]巴瑞·布赞、[丹麦]奥利·维夫、迪·怀尔德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3页。 尽管南海“航行自由”本不是一个安全问题,但是从安全化理论来看,美国确实基于政治和私利考量,而有意将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建构成安全议题。探究这种主观建构的进程和影响有助于丰富对南海“航行自由”的认识。基于此,文章致力于梳理安全化理论,论述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安全化企图及建构进程,厘清美国安全化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较为成功背后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去安全化”努力提出更好的应对建议。
一、安全化理论内涵及其建构路径
20世纪90年代初,哥本哈根学派学者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等提出了安全化理论,即安全是一种社会主体间建构,一旦某个问题或现象被认定为威胁时,它就上升为安全问题。受此影响,国外学界安全化理论发展总体上形成了两条路径:一是“哲学安全化”的哲学化路径,以语言(如“言语-行为”)为核心变量;二是“社会学安全化”的社会学化路径,以非语言(如“因果-习惯”)为核心变量。④ 余潇枫、谢贵平:“选择性再建构:安全化理论的新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第107页。 国内学界也对安全化理论进行扩展完善。一方面,对安全化理论存在的盲点与不足进行修缮,使之适应中国语境。余潇枫针对安全化理论的“选择”困境,创造性提出选择性再建构的基本路径,丰富了安全化理论中安全治理目标多向性、安全治理主体多元性、安全治理方式多样性、安全治理合作制度多维性的选择性内涵。艾喜荣针对安全化理论对“话语”在安全化过程中的作用缺乏详尽阐述,提出话语凸显、话语框定和话语定位的“话语操控”分析框架以补充安全化过程中话语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注重安全化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实证探究。例如,国内学者通过安全化理论框架解释艾滋病问题、国际规范的建立、恐怖主义以及生态问题等,以凸显安全化理论的实践运用价值。⑤ 赵岚、郑先武:“安全化视域下的中韩渔业纠纷”,载余潇枫、罗中枢主编:《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6—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96页。
1.1 “安全化”核心概念界定
第一,“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哥本哈根学派将语言学建构视角运用到安全研究中的一大创新。安全化理论把安全化视为一种“言语-行为”,通过一定的言语表达,某一问题被视为安全威胁提出来,以国家为代表的安全化主体推动其进入政治进程,采取必要行动或手段以阻止威胁的产生。⑥ 王凌:“安全化的路径分析——以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案为例”,《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78页。 “言语-行为”通常与国家等安全化主体的话语权力结合在一起,与威胁相关联。
自1995年起,美国政府通过政府声明和文件以及官方讲话等话语手段有意对南海“航行自由”进行话语凸显,将其列为关键词并且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强调和公开使用,以建构安全威胁和引起受众关注。1995年5月,美国政府就中菲“美济礁事件”发表声明成为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话语凸显的起点。时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里斯丁·谢利(Christine Shelly)宣读了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声明,称所有船只和飞机在南海均享有航行自由权及无害通过权,这关乎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是美国的根本利益。① Christine Shell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aily Press Briefi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May 10, 1995, http://dosfan.lib.uic.edu/ERC/briefing/daily_briefings/1995/9505/950510db.html. 这是美国首次提及南海“航行自由”涉及美国基本利益。此后美国政府就该问题发起一系列言语行为:1995年6月,时任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瑟夫·奈(Joseph Nye)表示,一旦南海发生冲突危及美国“航行自由”,美国应采取必要的军事干预手段。同年8月,时任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在东盟会议上再次强调,维护南海“航行自由”是美国的基本利益,希望相关各方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② 余颂:“美国对南中国海的军事渗透”,《国际资料信息》,2000年第12期,第29页。 1997年7月,时任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康尼·麦克(Connie Mack)在《美中国家安全与自由保护法案》中提议美国向南海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以威慑中国,通过联合巡航来保障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③ “United States-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Security and Freedom Protection Act of 1997”, United States Congress, July 29, 1997,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5th-congress/senate-bill/1083. 1997年9月,时任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也表示,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以及军事化行为给南海“航行自由”蒙上了一层阴影。④ 李贵州:“从美国国会议案看其南海问题态度及其根源”,《当代亚太》,2016年第5期,第122页。 1997年,美国国会更是在《199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特别增加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相关法律,强调南海“航行自由”关乎美国“国家利益”,要确保美国军机军舰顺利通过南海而不被沿岸国干扰。⑤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1998”,United States Congress, March 19, 1997,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5th-congress/house-bill/1119. 这也为今后十余年美国将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框定为“国家利益”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1998年至2008年期间,基于这一时期美国的战略重心在中东地区以及南海整体和平稳定的大背景,美国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整体比较低调。直至2009年,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再次被美国刻意凸显。2009年7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称,美国不允许海军进入中国南沙群岛周围12海里是非常危险的错误,这实际上等于默认了中国的主权声索。⑥ “Maritime Disputes and Sovereignty Issues in East Asia”,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uly 15, 2009, https://www.gpo.gov/fdsys/pkg/CHRG-111shrg53022/html/CHRG-111shrg53022.htm.
第三,四类要素主体。安全化过程涉及四类要素主体:安全化主体、指涉对象(reference objective)、威胁代理(threat agent)、受众。 其一,安全化主体即开启和进行安全化操作的安全施动者。安全化主体主要包括启动行为体、催化行为体和实施行为体三类:承担首要责任的是“启动行为体”——中央政府;起关键作用的是“催化行为体”——国际机构和他国的中央政府;起特殊作用的是“实施行为体”——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或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媒体、私人企业和工会。这些安全化主体的不同范围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使得安全化过程变得十分复杂。① [新加坡]梅利·卡拉贝若-安东尼、拉尔夫·埃莫斯、[美]阿米塔夫· 阿查亚编著,段青译:《安全化困境:亚洲的视角》,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其二,指涉对象是安全化主体所认定的威胁及需要被保护的客体。指涉对象可以是普遍性的共同威胁,也可以认为特定国家或行为体导致了威胁。② 潘亚玲:“安全化、国际合作与国际规范的动态发展”,《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第54页。 后者包含了安全化主体的政治意图及私利考虑。其三,威胁代理,即威胁的来源。其四,受众,即安全化逻辑的听众,决定安全化成功与否。此外,媒体聚焦并传播扩散热点事件是受众接受安全认知的关键。安全化过程表现为安全化主体认定指涉对象正遭受威胁,借助媒介载体向受众传播扩散威胁并使受众接受安全化逻辑,将某个议题主观构建成安全议题的过程。
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预期型框定。美国根据本国国家利益,提出解决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具体的策略、手段及目标。其一,美国认为应通过国际法解决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然而,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国际法解释并不客观。美国认为所有国家的船只,包括军用船只均有权在专属经济区自由航行,但中国认为这一原则只适用于商用船只,军用船只不得在专属经济区进行演习或监视。⑥ “Chinese Security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ast Asia Forum, June 5, 2017,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7/06/05/chinese-security-and-freedom-of-navigationin-the-south-china-sea. 其二,美国认为应通过多边协商解决南海“航行自由”问题。2011年6月,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吉姆·韦伯(James Webb)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呼吁以和平及多边途径解决东南亚海洋领土争端的议案》。其中,韦伯借“无暇”号事件和“麦凯恩”号事件,指责中国妨碍美国军舰和商船在南海的“航行自由”。韦伯声明美国支持以和平及多边途径解决南海争端,以便为美军南海巡航提供便利。⑦ 李贵州:“从美国国会议案看其南海问题态度及其根源”,《当代亚太》,2016年第5期,第126页。 其三,美国认为应该在南海进行监视活动或常态化“航行自由”行动。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行动和战略领导系副教授肖恩·亨斯勒(Sean P.Henseler)认为,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是必需的,有助于增强美国盟友和地区伙伴的信心,是确保美国南海“航行自由”权利的有效手段。⑧ Sean P.Henseler, “Why We Need South China Sea Freedom of Navigation Patrols”, The Diplomat, October 6, 2015, https://thediplomat.com/2015/10/why-we-need-south-china-sea-freedom-ofnavigation-patrols/.
第五,“宏观安全化”(macrosecuritization)。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主要集中探讨中观层次的国家和非国家集合体,认为中观层次的政治集合体最活跃且能够相互建构威胁。巴里·布赞为超越中观层次的集合体而在更宏大的视角中建构国际政治,后来对安全化理论加以完善,又补充了“宏观安全化”概念。⑥ 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Macrosecuritization and Security Constellations: Reconsidering Scale in Securitization Theo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35, No.2, 2009, p.253.“宏观安全化”扩大了安全化主体和受众之间的关系维度,其指涉对象通常为地缘经济、全球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以及核扩散等跨国性和全球性安全威胁。“宏观安全化”往往与有能力的大国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是大国推动某些议题跨国安全化从而实现其全球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例如,冷战时期美国成功地将苏联渲染成跨国安全威胁,小布什政府时期将恐怖主义广泛安全化并发动全球反恐战争,都是“宏观安全化”。因此,巴里·布赞认为“宏观安全化”是一种重蹈冷战期间研究路径的选择。⑦ [英]巴里·布赞、琳娜·汉森著,余潇枫译:《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页。 需要指出的是,“宏观安全化”与其他的安全化过程一样,也具有安全化主体、指涉对象、威胁代理和受众等四类要素主体。然而,“宏观安全化”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安全化,与非跨国的安全化不同之处是“受众”的不确定与可变性,因而对“去安全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5年至今,随着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入国际议程引起广泛关注,美国盟友、伙伴国等受众已经接受安全认知并将采取行动以应对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威胁视为自身的权利和义务。
1.2 安全化的建构路径
安全化更多的是安全化主体的一种主观构建。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化主体往往会采取三种步骤,识别威胁、采取紧急行动、通过破坏和摆脱自由规则来影响单元间关系。但忽视了其他影响因素:其一,媒体作为安全化载体在安全化主体和受众之间的传输作用未被重视;其二,安全化本质是伴随着权力话语,把“安全”表达出来就是一种言语行为。基于此,本文试结合“话语操控”分析框架① “话语操控”理论分析框架把安全化过程中的“言语行为”或“话语实践”具体操作化为话语凸显、话语框定和话语定位三个变量,即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这三个变量的话语操控手段或过程来实现对某一问题安全化程度高低的控制。参见艾喜荣:“话语操控与安全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3期,第57-78页。 提出一个更为完整的安全化建构路径:安全化启动,安全化主体依凭“话语凸显”(discursive salience)将某一问题建构成安全威胁,推动其进入政治议程上升为安全问题;安全化传播,安全化主体借助媒体进行“话语框定”(discursive framing),② “话语框定”源于社会学关于社会运动中的“框定理论”。该理论强调“社会构建意义”的框定对说服目标行为体接受某些观念、态度、习惯和行为的重要性。参见黄超:“框定战略与保护的责任:规范扩散的动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58-72页;[美]西德尼·塔罗著,吴庆宏译:《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赵鼎新著:《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David A.Snow,“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Vol.51, No.4, 1986, pp.464-481.通过议程设置和框架构建来说服受众接受安全议题;安全化行动,安全化主体通过“话语定位”(discursive positioning),采取行动使受众接受安全化动议甚至追随安全化主体应对安全威胁。
此后的时间里,王施凯仿佛突然被打通了任督二脉,开始发愤图强,努力学习……过了一个春·天一个夏天后,期末考试他竟真的考到了班级中游。王施凯本人的说法是有天晚上起夜,发现老爸在看他小时候的照片和奖状,一时间激发了奋斗的意志。当然,大老爷们半夜抹眼泪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告诉赵明月的。赵明月也没多问,心照不宣地继续为他讲题。
其一,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话语定位并开始频繁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2015年9月,美国国在《201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特别增加了“1263号南海行动”章节,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干预南海问题的具体条文。②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6”,United States Congress, November 25, 2015, https://www.congress.gov/114/plaws/publ92/PLAW-114publ92.pdf. 在该法案颁布后,美国随后就于同年10月启动针对中国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军舰在南海共进行了4次“航行自由”行动。2015年10月27日,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以宣示“航行自由”权为借口,首次在南沙群岛渚碧礁12海里范围内航行。此后,奥巴马政府于2016年1月、5月和10月又先后在南海开展了3次“航行自由”行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加大了实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力度,截至到2019年2月,美国已经在南海开展了10次“航行自由”行动。2017年和2018年分别进行4次,2019年以来已经进行了2次。2019年1月7日,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麦克坎贝尔”号在中国南海西沙群岛海域开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③ “US Destroyer Sails in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amid Trade Talks”, Reuters, January 7, 2019, https://www.financialexpress.com/defence/us-destroyer-sails-in-disputed-south-china-sea-amid-trade-talks/1436459/. 2019年2月11日,美国海军“斯普鲁恩斯”号和“普雷贝尔”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这是特朗普政府首次连续两个月在南海开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由此可见,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有所强化,南海局势并不太平。
第三,话语定位与安全化行动。对安全威胁成功进行“话语凸显”和“话语框定”之后,安全化过程并未结束,还需进行“话语定位”并采取安全化行动,至此,安全化才能得以完成。某一问题被成功凸显和框定为安全威胁并且成为受众的共同认知,之后安全化主体会通过话语建构某种故事情节,在其中预先设定安全化主体与受众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以防范安全威胁或者维护安全的具体行动。这一赋予了行动者以权利与义务的过程被称为“话语定位”,具体包括三个要素:故事情节、位置和社会行为,三者之间是一种线性发展和相互影响作用的关系。③ Rom Harré and Luk Van Langenhove, Positioning Theory :Moral Contexts of Intentional Action ,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9,pp.5-9.具体而言,安全化主体对故事情节中各自的角色预先进行定位,并且赋予占据位置的主体以社会行动的权利与义务。“故事情节”是话语定位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要素,指的是一种用来组织和赋予意义的叙述结构,个体通过话语实践使故事情节得到明确的显现;“位置”意味着需要执行一系列特定的权利和义务,位置不同则权利和义务不同,即便安全化主体的位置具有行事的特权,但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社会行为”也是话语定位过程中的重要要素,在特定的故事情节背景下,特定的位置所赋予的权利与义务,最终决定行为体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和行为模式。④ 艾喜荣:“话语操控与安全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3期,第75-76页。 在安全化过程中,任何的话语定位,都包括上述三个要素,安全化主体通过话语实践与参与者就安全威胁共同认知进行互动(故事情节),进而清晰界定安全化主体自身立场和参与者立场及权利义务(位置),最后共同采取相应的行为举措以应对安全威胁(社会行为)。
二、美国企图对南海“航行自由”安全化的表现
对某一问题的主观建构是成为安全议题的必经过程。鉴于南海“航行自由”并非安全议题,因此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安全化,更多体现为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主观建构,是美国的一种意图。文章接下来就结合理论详细地论述美国近年来有意将南海“航行自由”主观建构成一种安全议题的企图及进程。这种主观构建有如下三个表现:
结果表明,在自由度为1时的χ2统计量为11.660 2,且P<0.05,拒绝原假设,通过Hausman检验,因而该面板数据模型最终应为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
2.1 安全化启动:话语凸显与威胁构建(1995—2009年)
冷战结束至2009年,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关注是润物细无声的,并没有将“航行自由”视为中美南海博弈的焦点。美国这一时期的政策重点,只是将维护南海“航行自由”视为自身的霸权责任,通过敦促相关方以外交谈判方式和平解决南海争端,来最大程度上防止地区冲突危及其南海“航行自由”。
第二,“主体间性”。安全化理论核心论点就是并不存在客观既定的安全,安全是一种社会主体间建构。一旦某个问题或现象被贴上了安全标签,其就被建构成了安全问题。传统上,安全通常被理解为“客观上无威胁,主观上无恐惧”,安全化理论则超越了对安全的主客体二分,通过在安全分析中引入主体间性视角,安全议题的主体间建构特点也就得以体现。⑦ 同④。
从美国政府的一系列言语行为可以看出,其有意将南海“航行自由”安全化,进行话语凸显与话语实践。拥有话语权力的政府精英或高层官员通过聚焦放大中菲美济礁等特定热点事件,凸显“航行自由”的安全威胁,使之呈现在公众面前。
2.2 安全化传播:话语框定与议程设置(2009—2015年)
自2009年起,美国有倾向性地将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框定为本国的“国家利益”,通过媒体进行话语传播,歪曲中国“破坏”南海“航行自由”,使得公众对南海“航行自由”存在威胁达成了共同认知。
所有病例在入院时均接受超声检查,检查仪器为GELOGIQ E9型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仪,设定探头的工作频率位4~11MHz。患者采用仰卧位,颈前区充分暴露,常规扫查甲状腺双侧叶及峡部,观察甲状腺位置、外形、大小;随后使用二维超声检查甲状腺结节的部位、大小、形态、数目、边界、声晕、内部回声变化、血流情况。
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诊断型框定。一方面,美国将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界定为其“国家利益”,是“普世原则”,推动该问题进入国际议程。例如,201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发表“河内讲话”,声称确保南海公海海域开放,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赋予的航行自由权是美国的“国家利益”。① Catherine Putz and Shannon Tiezzi, “Did Hillary Clinton’s Pivot to Asia Work?” The Diplomat, April 15, 2016, https://thediplomat.com/2016/04/did-hillary-clintons-pivot-to-asia-work/. 希拉里此番言论是美国将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话语框定的转折点,据她后来承认称,这些精心挑选的措辞是为了反击中国宣称南海领土属于其核心利益的主张。② 杨志荣:“中美南海战略博弈的焦点、根源及发展趋势”,《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4期,第19页。 此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成为中美博弈的聚焦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维权行动频繁被美国指责为妨碍“航行自由”。2015年7月,时任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称,与南海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相比,美国更在乎南海“航行自由”等普世原则。③ Prashanth Parameswaran, “US Not ‘Neutral’ i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Top US Diplomat”, The Diplomat, July 22,2015, https://thediplomat.com/2015/07/us-not-neutral-in-southchina-sea-disputes-top-us-diplomat/. 另一方面,美国在各种场合歪曲指责中国是地区稳定与南海“航行自由”的“破坏者”和“责任者”。2012年9月,美国政府官员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借“无暇”号事件指责中国妨碍南海“航行自由”,破坏了南海的稳定局势。④ 杨光海、严浙:“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理性思考”,《新东方》,2014年第5期,第29页。 2014年2月,时任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更是强硬表示,“领海要求须符合国际法,美国反对侵犯他国海洋‘航行自由’和合法使用海洋的权利。‘航行自由’是由联合国海洋法所赋予的,而非大国对他国施予的赠惠。”⑤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5, 2014, https://2009-2017.state.gov/p/eap/rls/rm/2014/02/221293.htm.
第四,“去安全化”。安全化是某一问题被主观建构为安全问题的过程。“去安全化”正好相反,它是阻止某一问题被主观建构成安全问题。安全化理论虽有助于人们摆脱对安全的简单认识,但可能使安全化沦为安全化主体操纵安全议题以牟取私利的工具。安全分析中所谓的威胁,通常只是安全化主体为达到特定政治目的的幌子、借口,威胁本身并不重要。③ 李开盛:“去安全化理论的逻辑与路径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期,第57页。 更多原本不该被安全化的问题被有意安全化,极易导致安全的不可持续,甚至引发国际紧张与冲突。因此,奥利·维夫特别强调“去安全化”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探究“去安全化”的路径。④ Ole Wae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D.Lipschutz, ed.,On Security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75.他指出,“去安全化”是安全理论的真正价值取向,其有两个路径:一是不让一般问题成为安全议题而进入安全议程,二是让被安全化的问题退出安全议程。琳娜·汉森(Lene Hansen)进一步提到“去安全化”有稳定转化、置换议题、重新定位及沉默等四种模式。⑤ 张青磊:“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进程、动因与解决路径”,《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第19页。
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激励型框定。美国鼓励同盟及伙伴国参与集体行动以维持其参与的积极性。其一,美国通过渲染炒作南海“军事化”和中国“强硬论”,为同盟国寻求介入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借口,维持其参与积极性。美国通过话语优势和媒体传播,将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与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如岛礁建设,以及南海主权争端等联系起来,肆意渲染中国“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和“过度的海洋主张”。在美国舆论引导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积极呼应,纷纷寻求介入南海以示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担忧关切,一时间南海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其二,美国促使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入香格里拉对话、东盟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政治议程,促使东盟关注。例如,2012年6月,在美国的推动下,保护南海“航行自由”成功进入第十一届香格里拉对话议程。2012年11月,美国在《第四次东盟—美国领导人联合声明》中特别指出,美国与东盟在亚太地区和平稳定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拥有在南海“航行自由”及飞越的权利。① Phnom Penh, “Joint Statement of the 4th ASEAN-U.S.Leaders’ Meeting”,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20, 2012,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2/11/20/jointstatement-4th-asean-us-leaders-meeting. 美国呼吁东盟关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显然收到成效。2014年5月,第二十四届东盟峰会首次在《主席声明》中特别提及南海“航行自由”,随后召开的第二十一届东盟地区论坛也同样提到南海“航行自由”问题。
在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话语框定之外,不能忽视媒体的传播功能。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倾向采用拥有话语权的政治精英和智库学者的观点看法来构建话语框定框架,影响受众接受安全认知。以美国媒体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宣传为例,最典型的就是美军P-8A“海神”巡逻机在巡逻南海时搭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美国借助媒体高调报道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意在将之渲染成国际社会公认的安全威胁。
2.3 安全化行动:话语定位与采取行动(2015
年至今)
湖南雷锋纪念馆(雷锋故居所在地)位于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1968年11月建成开馆,其后多次进行了改扩建和陈列更新,现纪念馆总面积108000平方米。主要内容有雷锋故居、雷锋生平事迹陈列馆、领袖名人题词碑廊、雷锋塑像广场、长沙国防教育馆、十大元帅广场等。 雷锋生平事迹陈列展览以“平凡伟大、无私奉献”为主题,通过文物、图片、场景、视频、动漫等多种展示手段,共展出展品560余件,真实再现了雷锋生平、雷锋精神和学雷锋的先进事迹。
写景,要情景交融。写景,不仅是客观事物的再现,更是作者主观情感的外观。因此我们不能单独写景,而要借助景物,抒发自己一定的思想感情。
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发现,留学生的语用能力普遍较低,并没有随着其语言能力的提高而增强。同一年级的留学生,其语用能力发展也不平衡,差别较大。相对而言,留学生的社交语用能力要低于其语用语言能力。同时,教材编写、课堂教学都存在着语用能力培养方面的问题,需要改进和提高。在今后的教学中,应加强对留学生根据具体的语境来进行得体交际的能力的培养。这就对我们今后的教学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二,话语框定与安全化传播。在成功将安全威胁进行凸显并成为受众关注的热点话题之后,安全化主体还需要对安全威胁产生的根源、性质以及解决举措等问题进行阐释,以进一步影响受众形成共同的安全威胁认知,这就涉及“话语框定”。安全化主体借助媒体载体,使用“话语框定”策略来传播安全威胁,影响和说服受众对某一安全威胁的认知。“话语框定”的作用类似于一个画框,活动家通过有选择性地赋予某一问题特定的意义,形成固定的认知框架,以一种更容易被接受的话语来达到影响塑造个人或集体行为的目的。① David A.Snow,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1, No.4, 1986, p.464.安全化主体在安全化传播中倾向使用该策略以便把某一议题框定为安全威胁,以寻求说服受众共享安全认知。“话语框定”包含三种核心方式:诊断型框定(diagnostic framing),即清晰判定并阐明制造安全威胁的责任者,这种框定方式强调“谁是受害者”、“谁是制造安全威胁的责任者”等问题;在对安全威胁进行定位和阐明原因后,还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涉及第二种核心方式,即预期型框定(prognostic framing),这种框定方式根据安全威胁性质提出应对策略以及实现目标的方式及手段;在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之后,还要最终付诸实施,这就涉及第三种核心方式,即激励型框定(motivational framing),这种框定方式指的是呼吁行为体及其支持者积极采取行动,确保和维持支持者参与应对安全威胁的积极性。② Robert D.Benford and David A.Snow,“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 Vol.26, No.1, 2000, pp.616-617.在安全化过程中,对同一安全威胁进行不同方式的话语框定会使受众建构出完全不同的安全认知,安全化的程度及效果也会因此而不同。
其二,美国还频频派遣舰机在南海进行海上和空中巡航侦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利益。2015年5月11日,美军派遣“沃斯堡”号濒海战斗舰在南海展开例行巡逻。同年5月20日,美军派遣P-8A“海神”反潜巡逻机以执行侦察任务为借口闯入南海岛礁上空。同年11月8日至9日,美军B-52战略轰炸机连续两天在南海扩建岛礁附近海域飞越。同年12月10日,美军B-52战略轰炸机飞赴华阳礁上空,美国国防部官员称是“误入”中国岛礁附近争议空域。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海军官员表示,2015年美国舰机对中国南海地区进行了700多次巡航。④ Helene Cooper, “ Patrolling Disputed Waters, U.S.and China Jockey for Dominanc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30,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3/31/world/asia/southchina-sea-us-navy.html. 2016年7月6日,美军“里根”号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在南海海域巡航。同年7月7日,美军“阿利·伯克”级“宙斯盾”导弹驱逐舰DDG-56、DDG-100、DDG-63在中国南海海域进行编队航行。2017年2月18日,美军“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进行巡航。同年7月6日,美军B-1B“枪骑兵”战略轰炸机以执行飞越自由为名闯入南海上空。而在2018年,美军B-52战略轰炸机几乎每隔一个月就要非法闯入南海一次。
第一,话语凸显与安全化启动。安全化主体要想对某一安全威胁进行安全化,首先是要促使受众关注这一威胁,在此过程中,运用“话语凸显”工具引导受众对安全威胁产生关注是决定安全化能否成功启动的关键。换言之,安全化启动的标志就是安全化主体依靠自身的话语优势,以“话语凸显”方式将某一问题建构成安全威胁,并推动上升为安全问题。“话语凸显”指的是行为体通过有选择性的使用某些词汇或话语反复强调和凸显某一问题,从而使之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③ Stuart N.Soroka,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 Vol.8, No.1,2003,pp.27-48.安全化主体具体通过三种方式对某一安全威胁进行“话语凸显”:一是话题凸显,表现为与问题或威胁相关的词语高频出现,尤其是中心词或关键词被多次强调;二是句式凸显,主要体现为高频率运用强调、排比、感叹等功能句法来描述问题或威胁;三是语气凸显,体现为在描述问题或威胁时倾向运用表示程度、范围的形容词或副词等修饰词以达到凸显的效果。④ 艾喜荣:《话语操控与安全化:克林顿政府与小布什政府气候变化政策对比研究》,外交学院2016年博士论文,第6页。 显然,“话语凸显”是安全化主体推动某一问题进入政治议程的重要手段。安全化的首要是凸显某一问题,引起受众对该问题的关注。受众获得信息的来源主要是政府声明及文件、官方讲话、智库报告、媒体宣传等。安全化主体往往通过首次使用某个关键词或频繁在各种场合强调某个问题来达到话语凸显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话语凸显与否,凸显何种类型的问题,主要取决于安全化主体的偏好和政策取向。一国政治家和决策精英们掌握权力资源以及对“话语凸显”的运用,他们如果将某个问题定性为安全威胁,就很容易通过话语凸显呈现给受众。某个问题被认定为安全威胁是安全化主体的政治选择、是被话语建构的结果,并非总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⑤ 刘永涛:“建构安全威胁:美国战略的政治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期,第128页。
其三,美国积极拉拢、鼓动盟友和伙伴加入联合航行计划以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外交压力,掣肘中国海上崛起。首先,随着美菲、美越关系不断加强,菲律宾和越南都极力支持美国参与南海联合巡逻。例如,在“拉森”号事件中,越南和菲律宾都公开支持美国,在2016年1月“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中建岛区域12海里范围后,原本在“领海的无害通过权”问题上与中国立场相同的越南却转而支持美国。① Mira Rapp-Hooper, “Confronting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8, 201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6-02-08/confronting-china-south-chinasea. 越南和菲律宾的行为态度无疑加剧了南海紧张局势。其次,美国敦促日本海上自卫队加入南海巡逻。2015年1月,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称,美国希望日本将空中巡逻区域覆盖至南海上空,以制衡中国在南海日益自信的姿态。② Sam LaGrone, “U.S.7th Fleet CO: Japanese Patrols of South China Sea ‘Makes Sense’”, USNI News, January 29, 2015,https://news.usni.org/2015/01/29/u-s-7th-fleet-co-japanesenaval-forces-patrol-south-china-sea. 面对美国的邀请,前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Tomomi Inada)称日本始终支持美国的南海“航行自由”计划。③ “Japan Supports but Won’t Join U.S.Operations in South China Sea: Inada”, Japan Times, February 5, 2017,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7/02/05/national/sdf-wont-join-u-s-operations-south-china-sea-inada/#.WgRIr0xtbVo. 再次,美国呼吁澳大利亚尽快推出南海“航行自由”计划。对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法专家唐纳德·罗斯韦尔(Donald Rothwell)认为,澳大利亚始终是国际法的坚定支持者,尊重海上“航行自由”规则是澳大利亚贸易繁荣的基础,不支持外国军舰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权利只是中国等少数国家的立场,澳大利亚应积极支持美国的“航行自由”计划以防止中国所持立场成为事实。④ Donald Rothwell,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ustralia Must Take a Stand”,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June 14, 2017,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freedom-navigation-south-china-sea-australia-must-take-stand/.
三、美国成功安全化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原因
显然,透过安全化理论可以看出,美国近年来有意将南海“航行自由”主观建构成一种安全议题。美国作为安全化主体,有意通过话语凸显方式宣布其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受到了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借助媒体这一安全化载体,大肆报道渲染所谓的安全威胁,并将之进行话语框定,定位成“国家利益”,从而成功引起受众关注。此后,美国通过话语定位采取行动措施,南海“航行自由”迅速成为中美乃至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美国为什么能够较为成功地把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安全化”?其所依赖的资源、条件或者影响因素是什么?唯有厘清美国安全化较为成功背后的原因,方能对中国接下来的“去安全化”提出更好的应对建议。
第一,美国强大的传播和动员能力是其能够较为成功地将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安全化的资源体现。一方面,美国较为成功的安全化得益于其在亚太安全机制中享有很大的话语权。美国将南海“航行自由”宣传为“国家利益”和“普世原则”,无视地区国家对主权的合理诉求。201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发表“河内讲话”,将南海“航行自由”进行话语框定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在此之后,美国试图安全化南海“航行自由”问题,通过渲染南海“航行自由”存在安全威胁,影响其盟友及南海相关国家接受这一安全认知,将中国置于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违背者甚至挑战者的位置上。⑤ 李向阳:“中国崛起过程中解决边海问题的出路”,《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8期,第18页。 另一方面,美国较为成功的安全化也得益于美国政府借力媒体在南海鼓势。例如,在中国南海岛礁建设期间,美国政府借助媒体高调报道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美军P-8A“海神”巡逻机在巡逻南海岛礁建设时就搭载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美国媒体也倾向于采用拥有话语权的政治精英和智库学者的观点来构建关于“航行自由”的话语框定框架。国际社会之所以对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活动反响剧烈,主要原因正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以及“英国简氏防务周刊”(IHS Jane’s)披露有关岛礁建设进度照片和发表相关评论,引起了东南亚国家媒体和世界舆论的仿效与跟随。① 刘艳峰、邢瑞利、郑先武:“中国南海岛礁建设与东南亚国家的反应”,《南海学刊》,2016年第1期,第74页。 总之,美国较为成功的安全化得益于,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和代理国家配合构成安全化传播的主体,官方声明、媒体、智库报告等构成安全化传播途径,这体现了美国强大的传播和动员能力。② 傅莹:“失序与秩序再构建——7月6日在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演讲”,《中国人大》,2016年第14期,第25-26页。
第二,美国得天独厚的国内制度优势和对外影响力是其能够较为成功地将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安全化的重要条件。一方面,美国安全化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得益于本国国内制度。美国是典型的社会主导型国家,社会利益集团对国家政策和行为的影响力很大。例如,在1995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项明显针对中国的政策声明,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明了美国保护南海“航行自由”的必要性。很快在1996年8月,美国和平研究所就发表了所谓的“斯奈德报告”,其中正式提出了美国应当在南海问题上奉行“积极的中立主义”政策,通过开展预防性外交来防止中国威胁南海“航行自由”。③ 王传剑:“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当代亚太》,2014年第2期,第8页。 另一方面,安全化受众国的国内制度为美国安全化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提供了机会。国内制度确定了民众和政府之间的游戏规则及彼此的权利义务,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帮助国内行为体界定他们的国内利益和国际利益。④ 林民旺、朱立群:“国际规范的国内化:国内结构的影响及传播机制”,《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140页。 通常,美国总是针对安全化受众国特定的利益群体进行有倾向性地战略宣传和话语动员,使它们成为潜在的安全化支持者。安全化受众国国内可被利用的制度主要有国内大选制度和国内政治博弈。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国内利益群体博弈的最终结果。美国往往通过在国际和区域制度中创造或排斥机会,使某些支持美国安全化立场的国内利益群体比其他反对美国的利益群体获益更多。一旦没有遵循美国想要达成的战略目标,他们就会在机制中遭受排斥,进而受到其他国内利益群体的压制而在国内政治博弈中失利,最终也将会失去相应的利益和名誉。⑤ [美]乔纳森·科什纳:“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古典现实主义与中国崛起”,《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4期,第67页。
造成志愿者语言服务现状的原因有诸多方面,要想真正提高这一群体的整体语言能力和综合服务素质需要从各个方面加以改进。因篇幅限制和研究时间有限,该文仅选取一个方面来提供一些解决思路。笔者从与志愿者群体直接对接的活动主办方这一角度出发,就应如何提升其服务能力进行分析,笔者从高校志愿者英语服务能力现状和各大赛事活动的现实需求出发,提出以下可供参考的培训途径:
第三,美国较为成功地将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安全化关键在于其抓住了南海争端相关国家的利益诉求。中国与美国及东南亚国家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分歧的核心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制度的理解,以及对中国南海“九段线”的性质持不同意见。⑥ 张景全、潘玉:“美国航行自由计划与中美在南海的博弈”,《国际观察》,2016年第2期,第91页。 中国坚持主权原则,而美国及东南亚国家坚持所谓“法理化”,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充斥着主权原则与“国际规则”的斗争冲突。在此情形下,美国利用双方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理解差异以及南海“九段线”性质分歧,借助智库报告和学者声音,成功给中国塑造了“不合国际法”的身份。例如,美国注意到南海相关国家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主张后,美国智库很快就发布相关研究报告,陈述美国政府立场。早在2014年12月,美国国务院海洋、国际环境和科学署海洋与极地事务办公室就联合发布一份题为《海洋边界: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的研究报告,完全质疑南海“九段线”的法律含义甚至否定中国的南海主张,认为“九段线”模糊不清且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侵犯了南海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⑦ 刘艳峰:《规范扩散视角下的南海安全秩序重塑研究》,南京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第76-77页。 美国著名学者葛来仪(Bonnie Glaser)则发声指出,南海“九段线”将大部分国际海域划为内海,这极大限制了美国的“航行自由”。① Bonnie Glaser, “Beijing as an Emerging Pow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ptember 12, 2012, http://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attachments/ts120912_glaser.pdf. 总之,通过利用南海相关国家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对中国的忧虑情绪和利益诉求,美国的安全化企图明显收到了成效,中国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的威胁者负面形象似乎越来越成为南海相关国家所“公认”的事实。
底肥施用新洋丰微生物菌剂40kg/亩+有机肥120kg/亩+百倍邦海藻肥50kg/亩;追肥按需分4次施百倍邦海藻肥+百倍邦生根剂。右边转租出去土地,仍按当地习惯施用相等数量的某国产有机肥加某进口复合肥。追肥分4次按需施用。
第四,中美南海博弈与安全困境是美国能够较为成功地将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安全化的影响因素。一方面,中美南海博弈已成事实,影响了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安全化。基于对南海地区国际规则主导权的维护,美国不惜引发中美南海两极军事对抗,也要利用南海声索国与中国的纠纷来安全化南海“航行自由”问题。② [韩]金硕洙:“南海争端与中美战略博弈研究”,《南洋资料译丛》,2016年第2期,第1页。 尽管南海“航行自由”事实上不存在安全威胁,但中国南海岛礁建设这一合理维权行动仍然遭到了域外大国和南海相关国家的指责与强烈反应,他们忧虑中国是否想用武力控制南海。③ John Chen and Bonnie Glaser, “What China’s Militariz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Would Actually Look Like”, The Diplomat,November 5, 2015, https://thediplomat.com/2015/11/what-chinasmilitarization-of-the-south-china-sea-would-actually-look-like/. 因此,美国持续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安全化建构时,南海相关国家基于对中国强劲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担忧也愿意美国扮演安全提供者角色,乐于见到中国是南海地区“破坏者”形象的传播和塑造。另一方面,南海安全困境愈演愈烈,客观上作用于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安全化。南海地区有复杂的政治制度,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充斥着文化、宗教、海洋与边界的纷争与矛盾,彼此之间还没有完全消除敌意和对抗情绪,地区武装军备竞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这表明南海仍然处于安全困境中。④ 葛红亮:“南海安全区城间治理模式探析”,《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2期,第95页。 在此态势下,南海相关国家会受到地区安全主导权力的牵制以及承受来自邻国的战略压力,因此通过争相成为美国的安全化支持国和追随国来提升本国的防务能力;长期以来,南海相关国家甘愿受到美国安全化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话语及政策宣传的带动,忍受着美国安全化进程对他们润物细无声的“牵引”与“强迫”。
总而言之,美国之所以能够较为成功地把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安全化在于其拥有强大的传播和动员能力、得天独厚的国内制度优势以及利用了南海安全困境下争端相关国家的忧虑情绪。美国企图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安全化是一种危险的战略和消极的举措,加剧了南海地区冲突对抗的风险,中国应对美国的这一主观意图和主观建构进行批判。在美国企图持续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安全化的情形下,其作为安全化主体往往缺乏“去安全化”的动力,这就迫使中国需要作出诸多“去安全化”的努力。
长期以来,全市合力,省市重视、理念制胜,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全民参与、社会共建的工作机制,视造林绿化为一场绿色接力赛,坚持全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化,广泛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省市各单位、个人划片包区、共同参与,掀起全社会植绿爱绿的高潮。
四、中国应对
在未来,中国需要对被持续安全化的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做出“去安全化”努力。奥利·维夫强调“去安全化”的重要性,指出“去安全化”是“安全化”的逆向政治进程,要阻止某一问题持续的安全化状态并使之退出政治议程。⑤ Ole Wae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D.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75.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是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结构性矛盾和内在张力的反映,或者说是中美在南海博弈的一个聚集点,而不是一个安全议题也不能被主观构建成一个安全议题。“去安全化”的努力就体现为使“航行自由”退出美国的政治议程,阻止美国的主观构建。国内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定位非常清晰,并且一再强调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引起的分歧不能仅仅依靠沉默应对。在中国看来,美国的主观构建是一种话语策略,因此中国选择了正确引导国际舆论的“话语引导”,连同“稳定转化”和“转换议题”共同构成了近年来中国“去安全化”的路径。此外,在上述基础上,中国还应重视做好启动行为体、催化行为体和实施行为体等各类安全化主体的工作,方能最终达成有效“去安全化”的效果。
英语学科是初高中学习甚至以后孩子步入大学学习进入社会的重要学科之一。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对于英语学科,很多家长认为自己是门外汉,不懂英语,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辅导孩子。单词不认识,不会读,没法对孩子进行监管。其实家长们可以做的很多。接下来我会具体教会家长一些可操作的办法来使用。英语学习有四个很重要,希望家长们能记住并督促孩子。
第一,中国正逐渐脱离“刺激—反应”的被动模式,主动将南海“航行自由”纳入到海洋强国战略框架下,从而实现“稳定转化”。作为安全化主体,美国是意图推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安全化的关键责任者。针对美国的安全化企图,中国选择了在现有的海洋法框架下发挥主动性,实现问题的稳定转化。其一,中国化被动为主动,通过提供“航行自由”的公共产品以扭转美国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给中国造成的不利局面,减少南海相关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疑惧。例如,中国积极主办“航行自由”相关论坛与学术会议,组织南海海上人道主义救援,建设灯塔来提供照明和引导服务,增强自身议题提出和设置能力,积极推进南海非传统安全合作,纠正美国及南海争端各国对中国妨碍南海“航行自由”的偏见及误解。其二,中国也与美国建立了定期沟通会晤机制,增强战略互信,有效管控意外冲突和分歧。早在2014年,中美就签署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等互信机制。中国还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增进彼此的战略互信和沟通合作,共同管控南海分歧和冲突风险,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第二,中国也增强了“置换议题”的能力,以削弱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关注度。首先,中国致力于促进国内法与国际法的相互贯通。中国完善了相关国内法资源,既遵循与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航行自由权,也想方设法为南海“航行自由”设立国内法框架与限制。尤其,中国正在努力研究并且明确南海断续线的国内法性质及地位,以尽快消除国际误解与质疑。其次,中国积极推动国际法规则与缔结相关条约或协定。基于很多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是否适用于“航行自由”问题上同中国持相同立场,中国选择与这些国家共同缔结条约或达成协定,就潜在危害国家海洋权益或者有损国际法公正公平的模糊情况作出限制,一方面促进议题的转换,另一方面降低国家间围绕国际法而产生的冲突。最后,中国增强了议题设置能力,在不同场合都曾提出与南海相关国家共同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建设性方案。例如,中国与东盟已推动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的第一份草案就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中国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指导建构南海区域机制,为南海“航行自由”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中国也在通过媒体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话语引导”,发挥国际舆论正面效应。针对美国大肆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军事、外交、舆论渲染,中国尽量避免陷入舆论被动的不利境地,甚至还做到了正确引导。其一,中国通过揭露美国制造的南海“航行自由”存在威胁是伪命题,来加强话语和舆论引导。近来中国都在努力向各国申明,应该厘清国际法中的“航行自由”与美国语境中“航行自由”的区别,并在不同场合指责美国故意混淆两个概念,渲染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揭露其意在护持其在南海及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其二,中国也在主动构筑维护自身利益的话语系统,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增强南海“航行自由”的中国方案的号召力。中国一直积极利用国内外学术力量,对相关事件进行客观详实的研究,否弃错误的观念而宏扬中国支持南海“航行自由”的正确观点。中国还做到了在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以及相关研讨会上的正确发声,尽可能地团结各方友好人士,宣传中国正面的守法形象。其三,媒体作为传播载体,在美国意图推动南海“航行自由”安全化中的作用不容小觑,中国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致力于引导国内媒体在国际上精准发声。中国一再敦促媒体提高自身战略前瞻能力,对突发的热点事件有敏锐和及时的预判,形成舆论应对方案为维护国家利益服务。
第四,中国还需做好启动行为体、催化行为体和实施行为体等安全化主体的工作,以最终达到有效“去安全化”的效果。在美国持续将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安全化的过程中,美国中央政府作为“启动行为体”,通过与“催化行为体”——日本、澳大利亚、越南、菲律宾等相关国家以及东盟、欧盟、联合国等相关国际组织进行沟通互动,达成南海“航行自由”存在安全威胁的共识。美国作为“启动行为体”,不仅授权五角大楼开展年度“航行自由”计划并让军方掌握了更大的自由权来独立决定在何时何地开展“航行自由”行动,① 刘艳峰、邢瑞利:“美国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探析——基于规范扩散视角的分析”,《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29-44页。 而且积极与媒体、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实施行为体”互动交流,渲染和传播所谓的安全威胁,拉拢相关国家在南海开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因此,中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去安全化”的过程中,还需要注重与不同的行为主体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沟通,力求获得更多行为主体的理解。一方面,中国需要重视做“催化行为体”——日本、澳大利亚、越南、菲律宾等相关国家以及东盟、欧盟、联合国等相关国际组织的工作。针对日本、澳大利亚、越南、菲律宾等相关国家,中国在严正立场的同时应加强与之接触沟通,在增信释疑的基础上寻求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同合作的切入点;针对东盟、欧盟、联合国等相关国际组织,中国应借助各种双边和多边场合与之就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定位达成共识并保持同步,让它们意识到过多介入的危害。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重视做美国军方、媒体、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实施行为体”的工作。继续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两军关系,在以军事危机通报及空中相遇规则两个互信机制的基础上相向而行,推动两军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② “推动中美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稳定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2018年 10月 25日,http://www.mod.gov.cn/topnews/2018-10/25/content_4827765.htm。 在与其他行为体打交道过程中,中国要善于把握话语主动权,澄清不必要的误解和过度炒作,引导媒体舆论、相关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发挥正向积极作用。唯有各方面努力都做到位,方能达到有效“去安全化”的效果。
手术前,两组患者血清 CRP、IL-6、TNF-α 及IL-8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第3天,2组患者血清 CRP、IL-6、TNF-α及 IL-8水平显著高于手术前,开腹组显著高于联合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安全化理论的核心要义即安全是一种社会主体间建构,一旦某个问题被认定为威胁时,安全化主体往往会借助“言语—行为”形式将之主观建构成安全议题。理论上,安全化主体可以对任一问题进行主观建构,推动一些原本不在安全领域之内的问题进入政治议程升级为安全议题,这就容易导致安全化沦为某一国家谋求政治私利的工具和外交政策的附属品。从安全化理论分析中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来看,南海“航行自由”本不是安全问题,然而自2015年以来频繁被美国提及并最终成为国际社会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其背后深层次的根源就在于美国持续对这一议题进行安全化建构和主观渲染。
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安全化建构大体经过三个阶段:1995—2009年是安全化启动阶段,美国通过“话语凸显”方式宣布南海“航行自由”存在威胁;2009—2015年是安全化传播阶段,美国借助媒体载体渲染所谓的安全威胁,并进行“话语框定”将其定位成国家利益;2015年至今是安全化行动阶段,美国通过“话语定位”采取行动措施,促使南海“航行自由”迅速演变成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美国较为成功地把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安全化关键在于其拥有强大的传播和动员能力、得天独厚的国内制度优势并利用了南海争端相关国家的忧虑情绪。美国这一安全化企图及实践是一种危险的战略和消极的举措,加剧了南海地区冲突对抗的风险,中国应对此进行关注和批判。
当前,不同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次性”活动,特朗普政府已批准了五角大楼要求美军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的年度计划。③ Fang Tian, “Trump Reportedly Approves US Navy’s Annual Operation Plan in South China Sea”, People’s Daily Online, July 25,2017, http://en.people.cn/n3/2017/0725/c90000-9246195.html. 显然,美国有自己的政治意图和私利考量,在未来极有可能继续对南海“航行自由”进行安全化尝试。在此情形下,美国作为安全化主体往往缺乏“去安全化”的意愿,这就迫使中国需作出诸多“去安全化”的努力。鉴于此,中国应积极通过媒体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进行“话语引导”,增强“置换议题”和“稳定转化”的能力,主动将南海“航行自由”纳入到海洋强国战略框架下,削弱美国及相关国家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关注度。此外,中国还需做好启动行为体、催化行为体和实施行为体等安全化主体的工作,唯有各方面努力都做到位,方能使得美国安全化南海“航行自由”努力的失败,从而最终达到有效“去安全化”的效果。
The U.S.Securitization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XING Ruili1,2
(1.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China ; 2.Nantong Party School ,Nantong 226001,China )
Abstract: Securitization is the core theory of the Copenhagen school, of which the main argument is that security is a social construction between “speech act” agents rather than objectively established, and any problem could be subjectively constructed as a security problem.Securitization includes three procedures:discursive salience and securitization initiation, discursive framing and securitization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discursive positioning and securitization measure.In recent years,the U.S.has attempted to propose freedom of navigation(F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 a security issue.As the securitization agent,the U.S.intends to highlight the threats to F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At the same time,it takes advantage of the media reports to exaggerate the so-called security threats and asserts FON as its national interests.Since then, the U.S.has taken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threats, and F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rapidly become the focus of China-U.S.relations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The success of the U.S.securitization depends on its strong capabilit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mobilization,as well as its unique domestic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and it takes advantage of concerns of the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confronted with a security dilemma.In view of this,China needs to make efforts in de-securitization,rendering the U.S.securitization only a subjective intention.
Key words: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U.S.; securitization; Sino-U.S.relations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9)04-0025-15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9.04.003
邢瑞利:“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安全化建构及中国应对”,《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4期,第25-39页。
XING Ruili, “The U.S.Securitization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Pacific Journal , Vol.27,No.4, 2019, pp.25-39.
收稿日期: 2018-11-06;
修订日期: 2019-01-24。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14AZD055)、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中国东南周边地区安全机制构建研究”(14ZDA08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邢瑞利(1991—),女,河南洛阳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共南通市委党校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南海问题、安全私人化与海上安保。
∗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编辑 邓文科
勘误: 我刊2019年第2期张远鹏研究员等的《陆海统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探索》一文页眉和DOI中的“第27卷 第3期”“2019年3月”“Vol.27,No.3”“March 2019”“2019年第 3期”更正为“第 27卷 第2期”“2019年2月”“Vol.27,No.2”“February 2019”“2019年第2期”,“文章编号”中的“03”改为“02”;2019年第3期第 61页 DOI中的“03”更正为“02”。
标签:南海"论文; 航行自由"论文; 美国论文; 安全化建构论文; 中美关系论文; 南京大学论文;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