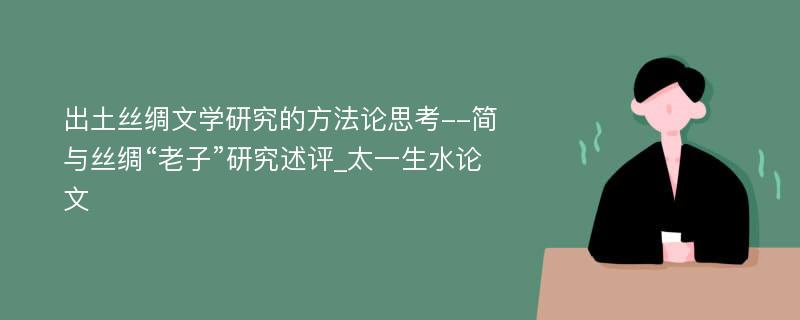
关于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思考——回顾简、帛《老子》研究有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老子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30年来,我国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辉煌业绩。尤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了一批批具有很高文献价值的竹简和帛书,其中主要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兵书;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文子》和《论语》、《儒家者言》等竹简古籍;1973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和《经法》、《十六经》、《五行篇》、《战国纵横家书》、《五星占》等重要古文献;1993年冬,湖北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太一生水》和《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语丛》等十余篇道家和儒家故籍。这些简帛文献的出土,使今人大开眼界,得到读到汉以后历代学者未能读到的许多古佚书以及与传世本有所不同的一些古文献。它不仅为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可信史料,而且也为世界各国人民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提供了新的实证材料。可以预见,这些简帛文献的出土,必将对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发展,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
简帛文献的纷纷出土,对当代史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机遇,亦是挑战。说它是“机遇”,是因为这些古文献资料重见天日,使史学研究人员大有用武之地,藉助对之研究,学者们可以更好地锻炼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而为整理祖国故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说它是“挑战”,是因为这些古文献资料,毕竟是两千余年以前的东西,它不仅覆盖上了沉重的“历史尘埃”,而且还牵连不少“千古悬案”,要对之进行整理和研究,难度很大,任重道远。研究者只有知难而进,严谨求是,才有可能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必须自觉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在研究中作出成绩。
应当指出,我国学者过去在研究简帛文献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很艰巨,必须再接再励,在21世纪作出更大成绩。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过去的研究工作做一回顾总结,并从方法论角度作一反思。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摘录黑格尔的一段话:“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注: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6页。)我们研究简帛文献,只有在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下,才能少犯错误,事半功倍。本文拟以我国学界研究简帛《老子》所涉及的有关方法论问题为视角,谈点切身感受和粗浅认识,希望能对整个简帛文献研究有所助益。
我国学术界过去在研究简帛《老子》方面,有经验,也有教训,从方法论角度对之反思,愚以为以下一些方法、原则,是值得特别引为重视的。
一、对出土简帛文献的评价不能人为拔高
简帛文献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客观价值,对其价值,我们既不能人为地贬低,也不能人为地拔高。人为地贬低,将之视作敝屡,那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人为地拔高,将其价值无限夸大,也必将引导人们走向谬误。这两种倾向,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似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两相比较,似乎拔高的情况尤为严重,需要特别引起重视。
记得帛书《老子》出土后,有人撰文主张“用帛书本校勘今本,判别今本的正与误;用帛书本研读今本,审定旧注的是与非。”这实际上是要以帛书本之是为是,以帛书本之非为非,一切以帛书《老子》为准绳。这种主张过于偏激,因而理所当然地为多数学者所不赞同。人所共知,帛书并非《老子》原本,它们也只是一种手抄本。作为一种手抄本,它也难免有错字、漏字和衍字的情况发生。加之,它在地下埋藏年深月久,脱坏严重。对于这些缺陷,有的论者却视而不见,他们沉醉于“以帛书之是非为是非”的错误成见中,以致在校读《老子》书时,竟把帛书之误字,加以肯定,乃至出现了是非颠倒的情况。
例如,今本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句中的“不争”,帛书乙本写作“有争”,这纯属失误。可是,有的论者却将“有争”加以肯定,说这“体现了《老子》‘柔而有争’的思想。”这个看法显然是立不住的。虽然,《老子》哲学是“柔而有争”的,但在《老子》那里,其“有争”是以“不争”为前提的,“不争”是条件,“有争”是归宿。这种思考问题的逻辑,在《老子》中随处可见。第二十二章说:“夫惟不争,故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说:“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八章说:“夫惟不争,故无尤!”无庸置疑,“不争”是老子无为之道的关键所在,它的思维逻辑是“无争而无不争”,这同“无为而无不为”的思维逻辑是一致的。所以,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才合老子本意,作“水善利万物而有争”,则恰恰背离了老子的思想。从第八章之上下文来看,问题也十分清楚。前面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后文应之:“夫惟不争,故无尤!”前文为后文埋下伏笔,前呼后应,文通理顺。如果前面作“水善利万物而有争”,(注:着重点为引者所加,以下均同。)则后文“夫惟不争……”就语无伦次了!这都说明,帛书乙本之“有争”实为讹误。把帛书中错误的东西判定为正确的东西,显然是把帛书看成“金科玉律”,犯了人为地拔高帛书文献价值的错误。
又如,今本第十四章末段:“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检帛书甲、乙本,其“执古之道”乃为“执今之道”。从《老子》本意看,似乎作“执古之道”为是。可是有的论者却拔高帛书,说帛书“执今之道”表现了《老子》“讲道论德的立足点正在今而不在古”;更有甚者,竟说这是“老子坚持‘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法家’路线。”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只要我们细读《老子》书,就不难发现老子强调的是“古道”,而并非“今道”。我们知道,《老子》中多次赞颂“古之善为道者”,多次引证古圣人的格言。第三十八章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是说,社会道德每况愈下,愈来愈不如从前。而古道退化到极点,就出现了“礼”这一“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东西。这表明老子希望恢复“古之道”。孔子曾评价老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也从侧面证明老子要执的是“古之道”。据此,当从今本作“执古之道”。那种主张依帛书作“执今之道”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他们之所以犯了这一错误,除了受“以帛书之是非为是非”思想的影响外,还由于不懂得训诂学。原来,古人有“反义通假”的习惯,《尔雅·释诂》中,就有:“故,今也”之说。可见,帛书之“今”乃为“古”之假字(假借字在帛书中是很多的),我们只要依据“反义互训”的原则,将“今”字训为“古”字就行了。该位论者不懂这一点,只知在那里固执地去维护帛书之“今”字,结果陷入误区。
由此可见,人为地拔高帛书《老子》的价值,在研究的实践中,是很有害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人为拔高帛书《老子》价值这一方法论上的失误,到了竹简《老子》出土,仍未得到克服。在竹简《老子》的研究中,有的论者提出:竹简《老子》是《老子》抄本中“最原始的本子”、“最完整的本子”、“最好的本子”。这里用“三最”来评价竹简《老子》的文献价值,显然,也有人为拔高之嫌。因为,从现存资料来看,说简本“最原始”、“最完整”、“最好”,似乎都证据不足。首先,说简本“最原始”,经不起推敲。人所共知,竹简《老子》也只是一种手抄本,如果要证明该种手抄本为“最原始”,那就必须先证明它是《老子》作者的手稿本或与手稿本完全相同的抄本,但这在现有资料条件下,研究者是无法办到的;其次,说简本“最完整”,也很难令人信服。因为与竹简《老子》时代相近的一些著作(如韩非《解老》、《喻老》和《庄子》等)所引用的《老子》语,均有一些不见于竹简《老子》。如,韩非《解老》、《喻老》所涉《老子》内容共23章,其中只有6章与竹简《老子》重合(注:请参见拙作《竹简〈老子〉的版本归宿及其文献价值探微》,载《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尚有17章不见于竹简《老子》;又如,《庄子》一书所涉《老子》内容,据陈鼓应先生统计,共达29章(注:请参见《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第6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8月版。),笔者以之为据,对照竹简《老子》,发现尚有14章不见于竹简《老子》。实事证明,竹简《老子》并非当时最完整的本子;最后,说简本《老子》是“最好的本子”,也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我们既然不能证明它是“最原始的本子”和“最完整的本子”,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说它是“最好的本子”呢?既然竹简《老子》之“三最”立不起来,而却硬要给它披上“三最”的外衣,这显然是在人为地拔高竹简《老子》的文献价值。
人为拔高竹简《老子》的文献价值,这在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从表面上看,“三最”使竹简《老子》披上一身荣耀;但深入下去,我们就不难发现,“三最”恰恰低估了中华民族文化进步的历程。众所共知,《老子》是我们民族第一部哲理诗,它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之思,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成书时代,当在春秋末年至战国前期,与西腊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创造相媲美。如果我们认可“三最”,那就是要告诉世人:直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著作——《老子》,还只有今本五分之二那么一点内容。这个结论,显然只会贬低我们祖先的文化创造。有一位外国学者,从“最原始”之论出发,说竹简《老子》“并非后代定型的《老子》五千言中的一部分,可以说它是尚处于形成阶段的、目前所见最古的《老子》文本”。郭店一号楚墓下葬时间,据专家考证,其下限为公元前278年。如果我们接受那位外国学者的观点,那就等于承认《老子》一书在公元前278年之前,还未形成。这无疑是要把《老子》成书的时间向后拉。若《老子》成书真的那么晚,我们也只好任人说去;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细思该位学者的见解,可知它同梁启超所谓“《老子》书著于战国末年”之论一脉相通。梁氏之说,早被我国学界所批驳而难以成立。帛书《老子》和竹简《老子》的相继出土,是对梁氏之说的有力冲击。懂得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论者都明白,“战国末年”之论,同我国古代许多历史文献记载相悖。最近,陈鼓应先生又著文认为:“先秦诸子的重要典籍几乎没有哪一家可以摆脱老子的影响。除了道家学派的著作之外,无论《论语》、《墨子》、《管子》、《孟子》、《申子》,各家各派无不或多或少地受到《老子》的影。”(注:请参见《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第6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8月版。)他的论述,是言之有据的。我们没有理由将《老子》成书的时间拉得太晚。
以上说明,人为拔高出土简、帛《老子》的文献价值,必将最终陷入谬误。这从方法论上来说,对于其他简帛文献的研究,也具有参考意义。
二、对传世今本文献的评价不能人为贬低
在研究出土简帛文献时,必然涉及相应的传世今本文献。如果说有的人在评价出土简帛文献时,有人为拔高的倾向;那么,与此相反,有的人在评价与简帛文献相对应的传世今本时,却又存在人为贬低的倾向。回顾简帛《老子》的研究情况,人们都还清楚记得,一些人在惊呼出土简帛《老子》的文献价值时,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贬低传世今本《老子》的价值。他们认为,传世今本《老子》“被人窜改”、“不可信”。有的论者在列举传世今本《老子》“五失真”之后,主张要以帛书《老子》为据,来改正今本《老子》的方方面面,或者干脆“用帛书《老子》来取代今本《老子》”;更有甚者,有的提出“要重写中国学术史”。愚以为这些看法都有人为贬低传世今本之嫌,值得进一步讨论和推敲。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反对参考出土文献来改正传世今本中某些失误。无庸讳言,传世今本也非《老子》原本,它们在流传过程中,难免出现失误。古人曰:“书三写,鱼成鲁,帝(似应作虑)成虎。”这说的是抄写中因字形相近而导致失误的情况;此外,还会有因音近致误以及由其他原因致误的情况。由于传抄中难免失误,借助出土文献对之作某些校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不赞同简单地“用帛书《老子》取代今本《老子》”。因为如前所述,帛书《老子》也只是一种手抄本,它也难免有错,而且它们自身也需要借助今本加以校正。同时,我更不赞同因一些简帛文献的出土,就提出“重写中国学术史”的主张。因为“中国学术史”所涉内容极其广泛,它是以浩如烟海的传世资料为依据的,岂是近年出土的一些文献所能全部推翻得了的?
首先,我们应当正确认识传世今本的价值。传世今本是经历代传承才得以保存下来的本子,它们被世代相传,乃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一本书是好是坏,不由某一两个人说了算,它往往要由历史来检验。一般说来,能在历史上传承一两千年而不被遗忘的著作,都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看不到这一点,简单地用出土文献来取代传世今本,那是极不慎重的作法。从常理来看,传世今本《老子》的最初被流传,当是开始流传的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本子,或者说是经学者认可的范本,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而新出土的《老子》本,仅是墓主的殉葬品,它的抄写是否出自学者之手,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这样说,决无意否定出土《老子》的文献价值。出土的《老子》本,保存了古代《老子》本的某些长处,对于校正今本确有重要参考价值。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拙著《帛书〈老子〉校注析》(注:《帛书〈老子〉校注析》,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的《代序》中,已作论述,此不赘语。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要轻易地用出土古本来否定传世今本。
其次,对于传世今本与出土古本文字上的差异,我们应当历史主义地看待它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慎重裁断。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论者一看到古本与今本不同的字句,就匆忙指责今本被人“窜改”,应当说这是欠妥的。对于传世今本与出土古本之异,应当从历史发展进化的角度去审视它。须知,传世今本打上了历史发展进化的印记。以传世《老子》为例,它的语言、词汇、文字都吸取了社会进步的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渗透着历代学人的心血。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我们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这样说,并非要否定《老子》一书由老子其人所作;而是要提醒人们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由于我国古代未有“著作权”的限制,《老子》书被流传之后和在未成为“传世定本”(注:所谓“传世定本”,指的是在世间流传中已成为固定的本子,如王弼本、傅奕本、河上公本等都可称为“传世定本”。)之前,确曾在历史上被一些学人对之予以提炼、修饰过。比如王弼所保存的《老子》本,就属“文人系统”,具有“文笔晓畅”的特征,其中无疑打上了文人对之提炼、修饰的烙印。从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我认为这种提炼、修饰将会更加符合群众阅读的需要,更易于流传开来,因而功不可没。因此,对于这种必要的提炼和修饰,我们不应轻易地给他戴上“窜改”的帽子。当然,这种提炼、修饰的作法,只能限于“传世定本”出现以前,一旦有了“传世定本”,再对之作文字改动,则必须有某种文本作依据,否则就会泛滥成灾。还应当指出,传世今本《老子》同帛书《老子》相较,虽然文句上有所不同,但就其所表达的基本思想而言,是大体一致的,且传世今本比出土古本文字精炼而又较为通俗,似乎更适合于普及的需要。只要对照出土古本作必要的修正,它就更有实用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我们没有理由简单地用出土古本取代传世今本。
再次,在评价出土文献的重大价值时,似不宜匆忙提出“重写中国学术史”。什么叫“重写”?顾名思义,所谓“重写”,就是要把过去的学术史推倒,另起炉灶,重构中国学术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这种“重写”的主张,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考虑不周:其一,是未能周密考虑汉以后两千年中国学术史的客观情况。我们知道,近三十年来我国考古发掘的古墓,多为汉墓或先秦墓。与之相应的出土文献,多为汉以前的文献资料。这就是说,这些古文献资料已在地下埋藏两千余年,它们对汉以后两千年的学术发展,难说有什么影响。而汉以后我国学术发展,靠的是传世今本文献。换句话说,传世今本文献是我国汉以后学术发展的思想源泉。因此,即使汉以前出土文献再多,它也不应当推翻汉以后两千年的中国学术发展史,也就是说汉以后的学术发展史,似乎不存在需要“重写”的问题。其二,是未能周密考虑先秦学术史的客观情况。在出土文献中,有一些先秦古佚书,由于它们重被发现,因而先秦学术发展的某些环节(如子思学派、孙膑兵法等)就需要补写某些内容,这种“补写”,对于整个中国学术史来说,也只是部分改写,而不是推倒“重写”。所以,基于以上认识,我以为提出“重写中国学术史”,似乎言之过重。综上所述,提出传世今本“不可信”,强调“以出土古本取代传世今本”以及提出“重写中国学术史”等,难免有人为贬低传世今本之失。这种方法论上的失误,如不及时纠正,必将给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的研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三、研究出土文献切忌主观臆恻
科学研究是一项十分严谨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人们在研究中所作的结论,必须言之有据。这一原则,对于研究简帛文献来说,同样是适用的。回顾我国简帛文献研究的情况,不难发现有的论者恰恰在这方面不够谨慎,以致把研究的结论置于主观想象的基础上,结果难免走向失误。下面试举几例:
帛书《老子》出土后,人们发现它的篇序与传世《老子》本不同。传世《老子》本,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人们称之为《道德经》;帛书《老子》恰好相反,它上篇为《德经》,下篇为《道经》,照这种排列,人们将之称为《德道经》。有人为了证明这种《德道经》在先秦时代早已出现,便举韩非著作《解老》、《喻老》为例,说韩非在写《解》、《喻》二篇时,也是先解《德经》,后解《道经》。此论一出,不少人信以为真。但是,细读韩非《解》、《喻》二篇,就会发现那位论者的说法是不可靠的。现将二篇所涉《老子》章次排列如下:
《解老》所涉的《老子》章次是:38章、58章、59章、60章、46章、8章、14章、1章、50章、67章、53章、54章等。
《喻老》所涉的《老子》章次是:46章、54章、26章、36章、63章、64章、52章、71章、64章、47章、41章、33章、27章等(其中64章两见)。
以上《解老》所涉章次,虽然前面几章属《德经》内容,但它后面几章也属《德经》内容。从这种情况看,我们很难判定它是先解《德经》、后解《道经》;《喻老篇》虽然末尾两章为《道经》的内容,但前面处于第三位(26章)和第四位(36章)两章也属《道经》内容,据此,似乎也很难说韩非《喻老》是先《德经》、后《道经》。只要我们不带成见,就会看到,在韩非《解老》、《喻老》二书篇中,《老子》之《德经》与《道经》未有明确划分,说它“先解《德经》,后解《道经》”,在很大程度上与实际情况不符。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余年之后的今天,有人竟在继续照抄这种说法。一位论者著文说:“《韩非子》一书中,《解老》、《喻老》两篇,先解《德经》而后解《道经》,这种先后顺序与帛书《老子》一致,而且全部内容互见。所以,被称为《德道经》的《老子》,在韩非子时代已成定本。”这段文字不仅人云亦云地照抄了前面那位论者的基本观点,而且有了新的“发明”和“突破”:认为韩非《解老》、《喻老》不仅在篇目“先后顺序”上与帛书《老子》一致,而且“全部内容”亦与帛书“互见”。这个判断,实在太离谱了。我们知道,《解老》、《喻老》二书,所涉今本《老子》文共23章,这与总数81章《老子》文(帛书虽未分章,但仍包含今本81章的内容)相比,尚有58章未能问津。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能够说韩非《解老》、《喻老》与帛书《老子》“全部内容互见”呢?这位论者显然未读过《解老》、《喻老》二书,以致犯了主观臆恻的错误。
郭店楚简《老子》出土后,有人把与《老子》简放在一起的《太一生水》篇,视为今本《老子》第四十二章的原型,著文说:《太一生水》中“这种由‘一’而发生的天地万物,在传世本《老子》第四十二章表述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中可见,前者是实指,后者是虚指,是以数字对具体事物进行抽象概括。”我们知道,《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我国古代道家创始人关于宇宙生成学说的高度概括,它不仅明确表达了一元化本体论的基本思想,而且高度抽象地描述了万物生成的复杂过程。这一思想,决非《太一生水》篇所能包容得了的。该位论者把《太一生水》看作是“实指”,而把《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看作“虚指”,将两者联贯起来,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我们不禁要问,在《太一生水》中,究竟哪些文句体现了“道是一”?又有哪些文句体现了“一生二”、“二生三”以至“三生万物”呢?只要坚持严谨求实,我们就很难找到二者相互对应的内容。而且,《太一生水》以“实指”为特点,这在竹简《老子》的其他章节中,也很难找到类似情况。就是说,《太一生水》和竹简《老子》其他章节的风格是不同的。这也足以证明《太一生水》不是《老子》书的组成部分。楚简文献的整理者已正确地将之列为另一文献。可见,将“太一生水”视为《老子》内容,也有主观臆恻之失。
此外,还有一位论者在研究了楚简之后,著文认为郭店楚墓之墓主为屈原。其说可谓新颖,但细读其文,似乎论据似是而非。
例如,为了论证该墓骸骨为屈原之遗骨,文章写道:“据挖掘报告,墓主遗骨仰身直肢,两手交置于腹部,双腿分开,这很像是墓主抱石投水而淹死后,被打捞上来,因尸体僵硬未能复原的姿势。”这里把该墓遗骨放置状况同屈原“抱石投江”联系起来,确实富有想象力。然而,细读这段文字,感到疑点不少。那位论者大概自己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于是用“很像是”来为自己找退路。然而,严肃的论证,怎么能靠“很像是”这种似是而非的语言来支撑其说呢?退一步说,即使郭店楚墓墓主的那种姿势是“抱石投江”者死后的姿势,我们也很难判定该墓骸骨为屈原所遗。因为,在古代抱石投水而死者,并非屈原一人,何以能够证明该骸骨为屈原所遗?
又如,该文为了说明屈原有“投水而死后归葬于郢都”的“安排”,写了如下一段文字:屈原“在死前不久写的《哀郢》,有‘狐死必首丘’的句子,可能这时已有了自己‘从彭城之所居’投水而死后,归葬于郢都楚贵族墓地的安排。”屈原是否真有这一“安排”?作者用“可能这时已有……”的说法来作判断。不仅如此,他还以这种不可靠的判断进一步推论说:“屈原抱石投汩罗江自尽后,尸体被弟子和家人们打捞上来,按其遗愿运回旧都郢贵族墓地安葬。”这里讲述的这些情况(特别是打着重点的部分),究竟见于何种文献资料?如无确凿史料为依据,那就将写学术论文等同于写小说、编故事。写小论、编故事,作者可以任意构造种种情节,而写论文则必须言之有据啊!
再如,为了说明楚墓中竹简与屈原的关系,文章写道:“墓中的陪葬竹书,只有像屈原这种身份的人才会有。但墓中为什么只有他从稷下带回的竹书,而没有他自己的作品呢?除了可能墓中竹书有遗失之外,亦可能下葬时屈原身旁的人只收藏了其手稿的孤本,而没来得及重抄一份作为陪葬,当然,也许更可能是,由于屈原作品多为发牢骚的讽喻文学创作,多有指责君王‘称其君之恶’的内容,写成以后便在民间流传,而不适宜葬入贵族墓地。”这一段论述,也全由揣测构成,其中漏洞很多。其一,墓中的竹书究竟是不是屈原所有?文章没有作肯定性回答,只是说:“只有像屈原这种身份的人才会有。”关于屈原的身份,该文作者将之定为“上士”,然而,当时处于“上士”地位的人,决非屈子一人,我们又怎么能据这一身份证明该批竹书之主人为屈原呢?其二,该文作者自己似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墓中为什么只有抄写古文献的竹书,而没有屈原自己的作品呢?应当说这是 个很重要的问题,作者必须对此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可惜,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也令人失望。文章用“可能”、“亦可能”、“更可能”三个揣测性的词语所构成的推理性认识来作解释,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比如由于屈原其文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不能葬入贵族墓地;而写文章的屈原其人却可以葬入贵族墓地。这怎么能自圆其说呢?总之,该文从头至尾似都证据不足。缺乏证据而勉强立论,就难免陷入主观臆测。
综上所述,从方法论角度对近三十年我国简帛文献研究特别是简帛《老子》研究的反思,我们深深感到,简帛文献研究和一切科学研究一样,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既不能对出土简帛文献价值人为地拔高,也不能对传世今本文献价值人为地贬低,更不能靠主观想象立论。因此,只有从方法论上吸取教训,提高认识,我们才有可能在新世纪的简帛文献研究中,严谨求实,再造辉煌。
标签:太一生水论文; 出土文献论文; 老子论文; 文献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屈原论文; 德道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