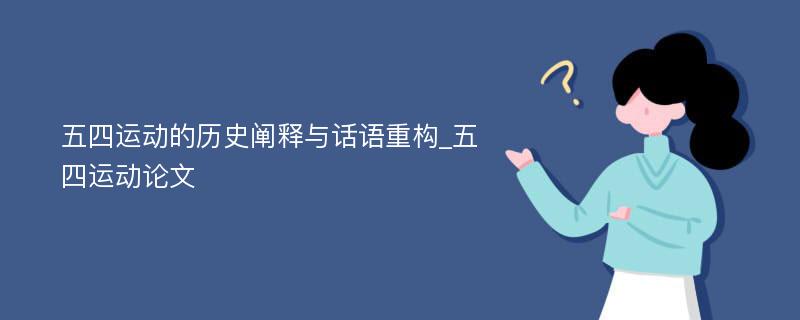
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与话语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构论文,话语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
近年来人们在反思中国近代激进主义形成时,五四再次成为议论的中心话题。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海内外学界可谓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不同立场的人受不同的认知、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的情感反应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答。由于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因此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哲学思潮、保守主义派的文化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潮对五四话语的重构强调了五四运动不同的方面,也就是说以五四运动为思想源头的各大思想流派在构建自己的“五四”话语和“五四”形象时,都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文化思想争辩交织在一起,因而所谓的“五四”话语和“五四”传统不仅是对历史的叙述,而且还参与现实的实践。(注:欧阳哲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之卷,第42页。)正如薇娜·舒衡哲所提出的:“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为浮现出什么样的被修正的‘五四’形象而进行的斗争,伴随着中国革命的政治战争而展开。革命进程的曲折和转向反映在杰出政治领袖精心制作的、变化着的‘五四’的解释中。这些领袖要从过去抽取出有用的东西,舍弃掉其他的东西,这样就不得不对‘五四’进行解释。”杰出的政治领袖人物如此,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也不例外。“1919年事件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都学会了相当有选择地使用他们的记忆。每当救国的压力增大的时候,他们就更多地加快政治性的细节;每当气候变得更加适宜于思想解放的目标时,他们就又忆起了为启蒙而进行文化斗争的细节。”(注:薇娜·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151页。)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进步主义者一提五四便欣然向往。他们认为五四运动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进步主义者只注意到五四运动里那些响亮的揭示而忽视了它的破坏性的副作用。于是,他们心目中的五四运动只是‘科学’、‘民主’和‘启蒙’所构成的一幅图画。”(注: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188页。)保守主义者提起五四运动似乎余恨犹存,他们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祸乱之由。“保守主义者只注意到五四运动里那些破坏性的副作用而忽视了它的真实启发作用。于是,他们心目中的五四运动只有‘打倒孔家店’,‘动摇民族文化的命脉’这些节目。”(注: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页。)这表明,不同的人对五四运动有不同的看法,而五四形象和五四话语就是在不断的纪念、研究和回忆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本文认为,在五四研究中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话语”系统,造成了三种不同的五四形象。这里以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陈旭麓和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对参加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分类和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为例,展示三种不同的“话语”系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陈旭麓曾指出: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为期不过短短的二十年,然而思想界的新陈代谢却体现了三代人的不同经历。作为“第一代”的康有为、严复等人,他们吸收和传播资产阶级新文化,是维新志士,然而在时代的激变中,他们很快就堕落为反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封建卫道者了。这种堕落,除了他们自己不知道及时地从错误的改良主义道路拔出来的因素外,也恰恰反映了中国封建文化的顽固性,不是已经取得的资产阶级文化打退了他们身上的封建主义,而是他们身上的封建主义打退了已经取得的资产阶级文化。曾经领导过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算是“第二代”,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们虽然还在继续着没有胜利希望的政治斗争,而在文化战线上却是一无表现,孙中山此时虽然也注意到改变思想的重要性,却在那里搞回避实际战斗的“心理建设”。到了五四时期的“第三代”,除蔡元培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而与新文化运动有关系外,其他多为辛亥革命以外的力量,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分子虽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却只能是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了。而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一批人,虽然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主要的人却都是激进主义者,如果将参加五四初期新文化运动(指1915年9 月著名的《新青年》杂志创刊到1919年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加以区分,大体上有三种情况:(1)以蔡元培为代表的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刘半农、沈尹默等人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他们赞同反对儒家伦理,赞同反对封建旧文学,也在不同方面介绍和中国封建思想文化对立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蔡元培在北大的“兼容并包”的态度,对新文化运动有所掖进和卫护,他写的《洪水猛兽》、《劳工神圣》等,表现了在那时他还是一个愿意接受时代思潮的人。至于初期新文化运动的胡适是以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在革命的旗帜下,参加了一些活动。 (2)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就那个时候发表的文章来看,钱玄同、吴虞大体上也要算到这一类型。对“打倒孔家店”也好,对文化革命也好,他们是冲锋陷阵的主要力量。这些人后来的发展不一样,有的由民主主义者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的没有跟着时代猛进,后来回到书斋里去了。(3 )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过渡,即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最初酝酿,在五四前夜,似乎还只有李大钊。总之,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在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推动下展开的。(注: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194页。)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则认为有三个“五四”:第一个“五四”是被毛泽东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相连续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这个“五四”观只是抽出了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有关的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道路,而舍去了民国时期丰富多彩的其他各种思想和文化流派。第二个“五四”是从右的方面,作为中国革命潜在前提的轨迹,这就是如胡适等后来走上与中共对立的道路的人士的轨迹。第三个“五四”是指梁漱溟的轨迹。“这是一条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基本上在同一路线上并行,但同时又有对立的‘另一个’中国革命的轨迹。”(注:沟口雄三:《另一个“五四”》,《中国文化》第十五、十六期,第306页。 )沟口雄三认为,梁漱溟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三人有某种共鸣,因此,他们大致是属于同一“五四”阵营的,这样的“五四”,就是我们一直作为“五四”运动形象的“五四”。通过沟口雄三教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目的是“在于判明梁濑溟从‘五四’到新中国的思想轨迹,是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区别开来而属于‘另一个’。梁漱溟的这‘另一个五四’,是不同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共道路的非中共道路,不同于阶级斗争的非阶级斗争的道路。而且也不同于以往人们由常识所认为的‘五四’是反对和打倒宗法的、儒教的传统思想这样的道路。总之,这是一条与毫不妥协相对立的另外一条道路。”(注:沟口雄三:《另一个“五四”》,《中国文化》第十五、 十六期, 第315页。)由此可见,三个“五四”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五四话语。
综上所述,由于五四运动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站在不同立场的人看到的五四运动的面相就不完全一样,不同的文化派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也就强调了五四运动的不同方面,构建了不同的话语系统。具体来说,唯物史观派建构了一种“五四”运动的革命强势话语系统,自由主义西化派建构了一种“五四”运动的弱势渐进话语系统,而文化保守主义则建构了一种特定的反“五四”话语系统。
二、唯物史观派:“五四”运动的革命话语系统
从激进民主主义派到唯物史观派的发展,“五四”运动的革命话语系统日渐形成,并成为一套强势话语系统。它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从陈独秀开始,中经瞿秋白、新启蒙运动,到毛泽东臻于成熟。
陈独秀高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甚赞“五四”运动的“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注: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原载《时事新报》1920年4月20日。); 瞿秋白突显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三十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则构筑了启蒙与救亡两大命题;毛泽东高屋建瓴,对“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及其历史作用作出了合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解释。值得指出的是,张申府、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作为新启蒙运动的主要理论发言人,他们的理论研究,尤其是陈伯达和艾思奇两人的著作,对毛泽东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有关“五四”运动的论述基本上沿袭了他们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启蒙运动是革命话语系统的“五四”文本之形成的重要基础。(注:欧阳哲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之卷,第43页。)毛泽东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时指出:“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页。 )他还说:“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2页。)又说:“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第一次大革命。那么,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干部。”(注: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显然,毛泽东是突出了五四运动的社会政治意义和民族救亡意识。以后史学界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视为一体,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后期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前者是鸦片战争以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后者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开端。当然,毛泽东后来对“五四”运动的片面性也予以了深刻的揭示。他在40年代总结“五四”以来的文化运动时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对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是不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注:《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1953年版,第833页。)这里所谓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所谓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则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在政治、军事、文化上都有许多表现。进入9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代表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是爱国青年发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运动。“五四运动的精神,最根本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注: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反复强调: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派是五四精神的主要分享者,她所建构的五四话语是最为系统,影响也最为广泛。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新的建设时代的到来,唯物史观派对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继承的空间在不断的拓展,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反思也在不断的深化,“五四”运动的革命话语系统的建构也终将从很强的意识形态化而被学术化所转换。
三、自由主义西化派:“五四”运动的渐进话语系统
自由主义从20年代以后创建《努力》、《现代评论》、《新月》,到30年代创办《独立评论》,再到40年代后期发刊《独立时论》、《观察》等刊,为追求自己的民主政治理想做出了艰苦的探索,然而因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它未能构筑起成熟的思想体系,更不用说意识形态。因此,它构筑的“五四”话语系统也只能是一种弱势话语。“五四”时期,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对新文化运动应具有的精神气质和理性选择作出了明确的阐释,这是一篇纲领性的文献。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1921年5月2日,胡适为纪念“五四”运动两周年,又发表了《黄梨洲论学生运动》一文。综观这些论文,可以看出胡适对“五四”运动主要是从狭义的角度去阐释的。1935年5月,为纪念被时人冷淡的“五四”, 胡适接连发表了《纪念“五四”》和《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两文。在这两篇文章中,胡适回顾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对新文化运动如何由文化思想层面衍及政治层面的原初动力作了解释,并就自由主义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做了说明,从而将“五四”运动注入了强烈的自由主义的色彩。职是之故,胡适对新文化运动也好,“五四”运动也罢,都作了充分肯定。50年代以后,由于此时大陆易帜,毛泽东从建构新的意识形态出发,组织了“胡适大批判”运动,许多知识分子纷纷与胡适划清界限;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后,对自由主义也是或公开打压,或幕后怂恿攻讦,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文化保守主义也借“五四”运动这一话题不断攻击自由主义,迫使胡适重新反省“五四”运动。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中用整整三章的篇幅叙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史。这时,他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区别开来。关于新文化运动,胡适给其一个特定名称——“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关于五四运动,胡适认为它“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注: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五四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这里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两者之间的性质不同,前者是文化运动,后者是政治运动;二是五四运动作为一项不幸的政治干扰,把文化运动转变成了政治运动。由此可见,胡适晚年对“五四”运动作了低调处理。
与第一代自由主义西化论者有所不同,第二代自由主义西化派的重要代表之一殷海光对五四运动的功绩及其影响则给予了“一高一低”的评价。所谓“一高”,就是说,“在中国现代史上,五四运动形成了几乎空前的社会文化及思想的巨大动力”。(注: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因此, 五四运动对于其后中国的种种演变之影响是很深远而无可抹煞的,其主要表现在新文学的滋长、新思想的吸收、社会改革等。所谓“一低”,就是在殷海光看来,“五四运动是一些抱持不同的观念者在爱国、趋新、弃旧、科学及民主这几点上盟结起来的一个运动。除此之外,五四运动并没有一个巩固而又结实的思想核心”。“五四运动的声威大过它的实质,五四运动的光焰大过它的成就”(注: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页。),因而在学术思想上, 五四运动所成就的只比新闻式的介绍高一点点。(注: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页。)与此同时, 殷海光还指出了在五四运动内部存在着对极的性格,其主要表现在:“爱国”、“反对卖国”,这些要求所含有的心理情况与“民主”、“科学”所需要准备及训练大不相同。前者是逆境的反应;而后者需要顺利和安定的环境,及长时间的培养。殷海光对五四运动“一高调”和“一低调”的处理,表明他作为后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代表人物的矛盾心理。
八十年代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李泽厚则认为“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他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提出了后来影响很大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并认为“启蒙与救亡(革命)的双重主题的关系在五四以后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予以真正的探讨和足够的重视……终于带来了巨大的恶果。”(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4—45页。)
自由主义西化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曾就五四精神、五四目标、五四思想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只有迈出五四才能光大五四。“我肯定了五四运动所揭橥的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目标。……我们除了对五四思潮需做一番历史的了解与分析的批评以外,更需超越五四时代对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口号式的了解的层次,进而掌握这些观念的实质内容与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注: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4页。)他在其著名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中,运用比较思想史的方法,“对以五四激烈反传统为主轴的中国现代思想进行理性分析的工作”,认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占主流地位的是“全盘性反传统思潮”。他甚至认为,“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这两次革命的产生,都是基于一种相同的假设,即:如果要进行意义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基本前提是要先使人们的价值和精神整体地改变。如果实现这样的革命,就必须激进地拒斥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注: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第2—3页。)此论一出,引起了祖国大陆学者的广泛关注,从而将大陆80年代的“文化热”推向深入,使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成为这场文化讨论的思想特征。
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海外学者张灏指出“五四”文化重建运动所反映的关怀有两个来源,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这两个关怀一个是民族主义情绪,另一个是世界主义精神。他说:“谁也不能否认,今天的国内外局势是和五四时代很不同,至少帝国主义的凶焰已没有当时之盛,但是我们也得承认:民族竞争仍是今天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而且在今天这场民族竞争里,中国人的文化和民族自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今天代表东方文化而受世界尊重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因此,现在谈文化重建,我们仍得正视民族主义这个文化动力。”但是,他又接着说:“今天我们应该强调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五四关怀的另一面——世界主义。当然,对于五四的世界主义,我们的态度并不是无条件地承受,而是批判地肯定。”(注:张灏:《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载美国《当代》1996年创刊号,第53—54页。)张灏所肯定的是“五四”知识分子对世界文化的开放心态,而批判的则是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他认为这是“五四”心态的一个必须警惕的“盲点”,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综上所述,自由主义西化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和肯定者,有的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但由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之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缺乏全面、正确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他们在肯定和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之批判的同时,则又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存在的那些缺点:如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失简单化,有某些虚无主义的思想倾向,忽视了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弘扬等。
四、文化保守主义:反“五四”话语系统
与唯物史观派和自由主义西化派均有所不同,保守主义派始终抓住“五四”运动中某些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言词和推崇西方文化的形式主义倾向,制造了一个反“五四”话语系统或五四运动的批判话语系统。“对于高举‘科学’、‘民主’大旗,英勇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五四’健将们,现代新儒家是很不宽容的,不仅指责他们提倡的科学、民主是‘科学一层论’和‘空头民主’,甚至直骂他们反对传统文化是‘庶孽无知’、‘丧心病狂’。这表现了新儒家在对待科学、民主问题上的矛盾心理。”(注: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实际上,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高歌猛进的时候,杜亚泉、章士钊、染漱溟、梅光迪、吴宓等一大批文化保守主义者就纷纷作文著书,批评或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说成是“人心之迷乱”,“国是之丧失”,“精神界之破产”。(注:伧父(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吴宓、 章士钊和梅光迪等人的文章,其标题就叫做《论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化运动》和《评提倡新文化运动者》。他们根本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对新文化诸义多所曲解。例如“学衡派”健将吴宓即认为“所谓新文化者似即西洋文化之别名,简称之曰欧化”。他甚至攻击“新文化运动之流,乃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以饷我国之人。”(注: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以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大体都沿袭此种偏见, 把新文化运动只看作是一此“西化”运动,而且是很肤浅很要不得的西化运动。
进入30年代后,批评、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者共同的思想倾向。1935年1月10日的“十教授宣言”认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应为“中国在文化领域中的消失”负完全责任,因为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引进,造成中国文化特征的“丧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批评最为激烈,否定最为彻底的大概要算现代新儒家了。例如,冯友兰在他的《新事论》,又叫《中国到自由之路》中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清算,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批判中国封建旧文化、旧论理、旧道德,提倡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他说:“清末人认为,我们只要有机器、实业等,其余可以‘依然故我’。这种见解,固然是不对底。而民初人不知只要有了机器、实业等,其余方面自然会跟着来,跟着变。这亦是他们底无知。如果清末人的见解,是‘体用两橛’,民初人的见解,可以说是‘体用倒置’。从学术底观点说,纯粹科学等是体,实用科学、技艺等是用。但自社会改革之观点说,则用机器,兴实业等是体,社会之别方面底改革是用。这两部分人的见解,都是错误底。不过清末人若照着他们的办法,办下去,可以得到他们所意想不到的结果;民初人若照着他们的想法,想下去,或照着他们的说法,说下去,他们所希望底结果,却很难得到”。(注:冯友兰:《贞元六书》(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页。)所以,冯友兰对清末人(即洋务派)“表示敬意”, 而对民初人(即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则不能不表示批评了。钱穆则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悍于求变,而忍于谋安,果于为率导,而殆于务研寻。又复羼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靡已”。(注: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直到70年代,乃至80年代,钱穆仍认定新文化运动是“一意西化”。(注:《太炎论学述》,转引自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载《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116页。 )张君劢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使国人丧失自信心。他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写道:“国中少数学者,不特不能窥见前人制作之精意,专毁谤先人以自眩其新奇,冥冥之中,使国人丧失其自信心,实即所以摧毁其自己”。与第一代新儒家相比,第二代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更激烈、尖刻和意气用事。第二代新儒家对“五四”的批判,有着更多的情绪色彩,他们要么斥责“五四”主流知识分子对孔教的批判是“无知”的“谎言”(徐复观),要么认为“五四”所讲的“民主”、“科学”只是一种“幻觉”(牟宗三)。在牟宗三、唐君毅等人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述中,诸如“丧心病狂”、“全无心肝”,“浅薄轻浮”,“无耻无知”等咒骂的字眼比比皆是。他们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消极的、破坏性的、片面的运动,是“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运动,犯了“科学一层论”、“理智一元论”的错误,其结果不仅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动摇了自己的命脉”,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并最后取得了胜利。尤其是对后一结果,第二代新儒家们始终是耿耿于怀。例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在《中国文化宣言》中认为“五四”运动以来胡适的整理国故之口号,是把中国以前之学术文化,统一于“国故”之名词下,视之如字纸篓中之物,只待整理一番,以便归档存案。陈独秀以民主科学之口号,去与数千年中国历史文化斗争,中国文化固然被摧毁,而民主亦生不了根,亦不能为中国人共信。这说明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除了其文化的立场外,还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在第三代新儒家中对“五四”运动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超越牟宗三等人的政治和文化立场,具体地分析五四运动的成绩与局限;另一种是蔡仁厚承袭牟宗三的立场,认定民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把孔子的地位拉下来与诸子并列,“是浅陋、一版糕的头脑”,根本没有学术价值的层序观。“打倒孔家店”是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糟蹋自己的圣人到“无心肝”的地步。蔡仁厚也宣称“新儒家的批判性与战斗性”,但他所谓的“批判”的对象不是儒学的缺陷,而是批判西化思想;批判外来意识形态喧宾夺主的野心;批判泛自由主义之无益于民主建国,批判科学一层论之垄断,宣扬中国本位文化论。(注:韩强、赵光辉:《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他的这种立场不仅继承了唐、牟那种中、西对立,而且正如他同时代的刘述先、杜维明所指出的那样,带有强烈的排外性的“义和团心理”,或者说仍停留在唐、牟时代。
以上所说现当代新儒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是就整体而言的,这并不表明在新儒家中没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予积极反思的。实际上,作为第一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之一的贺麟先生在其《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就已经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之积极意义。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表面上虽主张推翻儒家,打倒孔家店,然而实际上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大转机,其功绩和重要性,乃远远超过了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因为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与实行,只是旧儒家思想的回光返照,是其最后的表现与挣扎,对于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却殊少直接的贡献,相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批判打倒的对象。“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注:宋志明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诚然,贺麟是站在现代新儒家的立场上,来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之积极意义的。但他能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批判,这本身就表明它的积极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第三代新儒家中著名代表杜维明、刘述先等人从精神上接续了贺麟对五四运动的评价,突破了第二代新儒家的限制。例如,在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或在对待五四知识分子对儒家进行猛烈批判的问题之评价上,杜维明既不同于现代新儒家学派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的主张即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一种保守回应,代表中国传统哲学力图适应现代、走向世界的一种努力的心态,也不同于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对五四的仇视心态,而是站在比较理性的立场上来评价五四知识分子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种种努力。所以,杜维明认为,“要发扬儒学的真精神,必须首先发扬五四精神”。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第一,五四知识分子对儒学传统进行的猛烈批判有其很健康的意义;第二,由于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儒学传统进行的猛烈批判使得儒学符号系统更加纯洁;第三,五四时代狠批“封建遗毒”的努力确实为儒学研究开辟了新道路。在杜维明看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固然有偏激之处,但也起了把儒学和政治化的道德说教区别开来因而对儒学传统的真精神有净化作用的功能。严格地说,如果没有五四的反“传统”(反“封建遗毒”的“传统”),儒学的真精神就不可能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起步。这些评价,表现出杜维明作为新一代学人远距离观察历史所采取的平实的辩证态度。正是这种较其前辈更为开阔的胸襟,使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何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来研究儒学的现代意义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大课题。如何批判封建遗毒和如何继承传统精神是同一课题的两面;把封建遗毒和传统精神混为一谈在理论上站不住,在实践上也行不通。同样,作为第三代新儒家,刘述先表现出比其前辈更为开放、平实的心态,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一向对五四采取一种既肯定而又批评的态度”(注:景海峰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 他反复强调“五四这样的运动之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五四所指出的大方向并无差错”(注:景海峰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179页。),“五四”的“眼光一点也没有错。错的是五四把传统说得一无是处”(注:景海峰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五四时代提出的德先生、 赛先生的口号,提倡科学工业化,主张民主、法治,追求人权的保障、个性的表达,这些都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应该讨论的问题,决不是要不要这些东西的问题,而是我们做到了几分的问题,是怎样的因素阻碍了我们大踏步地向前推进,这些需要我们作最严肃的检讨。而在另一方面,五四自有其偏颇处,五四只能看到传统的缺陷,完全看不到传统的优点”。应该说,刘述先对“五四”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与杜维明、刘述先略有不同,余英时一方面同意通行的把五四当做一次反传统、反儒学运动的观点,一方面又注意到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认为五四运动自有其中国传统的根源,它的反传统反礼教思想基本上导源于传统中的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思想。因此,他提出了超越“五四”思想境界的口号。“一方面肯定‘五四’的启蒙精神,另一方面超越‘五四’的思想境界,这就是中国文化重建在历史现阶段所面临的基本情势。”1988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的讲演,对五四时代的激进思潮作了严厉的批评。他的观点在大陆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大陆界“保守主义”盛行,“五四”被当做一次激烈的反传统运动而受到普遍的质疑和批判。
综上所述,无论是唯物史观派作为意识形态的“五四”革命的强势话语系统,还是自由主义西化派有关“五四”启蒙的渐进的弱势话语系统,或者文化保守主义者构建的反“五四”话语系统,都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动态地发展变化的。就其总体倾向而言,唯物史观派在获得政治权力之后,尤其是在充分汲取“文化大革命”血的经验教训之后,在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越来越以“兼容并蓄”的心态看待“五四”;自由主义西化派亦经过几代人的反思,充分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存在的局限,因而提出了“继承五四,超越五四”的口号;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样经过几代人的深刻反思,尤其是一些海外华裔学者通过自己的检讨,也在冷静地调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与失误的称星了。可以说,三派文化哲学家建构的不同的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话语系统,到了20世纪90年代逐渐形成了“视界融合”,达成了共识——这就是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历史的发展昭示人们,三派文化哲学家们建构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的发展。我相信,在三派文化哲学流派已经形成的一些共识的基础上,合理地利用和开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资源,对于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21世纪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都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收稿日期:1999—11—08
标签:五四运动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文化的展望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胡适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陈独秀论文; 殷海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