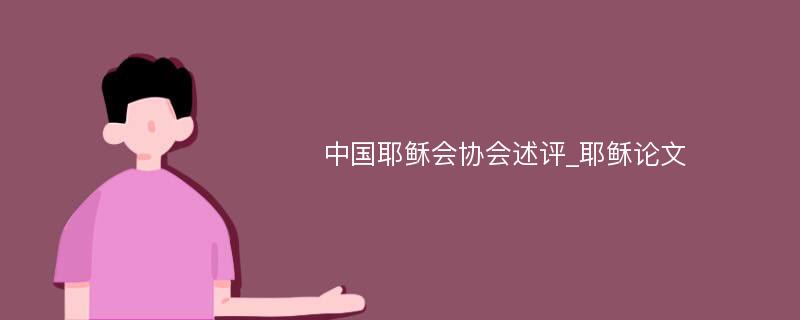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耶稣教论文,述评论文,自立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凡讨论中国基督教自立问题,总要述及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由于资料原因,其产生、发展、变化、结局尚未见全面描述,其特点及在中国基督教史中的地位尚未见评说,本文拟作一尝试。
本文所述“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包括初创于上海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及其在各地名称各异的分、支会;描述重点是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本文时限始于该会创办,下限定于1958年,因为自立会各分、支会这年分别参加了各地的联合礼拜,接受各地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领导,自立会全国总会不再独立开展组织活动。描述的重点是创办至1949年。为省篇幅,在不产生歧义的情况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一般只称自立会。
一、自立会的历程
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人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国家和民族的“自治、自立”成为普遍要求,教会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关系国家政局稳定的政治问题。
中国基督教会人士反省的主要对策是教会自立。〔1 〕天津教会在1899年至1902年间3次创办自立教会,3次受挫。1900年,高凤池等在上海闸北恒业路创设上海基督教会(自理会)。〔2〕1903 年因湖南辰州教案,“士民侧目”,上海谢洪赉、王正廷、俞国桢、高凤池、夏粹芳等发起中国基督徒会,“妥筹预弭教祸之法”,宣传“中国信徒宜在本国传道之要理”,〔3〕香港、北京、宁波等地信徒响应,成立支会。1903年,广州兴华浸信自理会成立。1905年,广州长老会自立会、广州自理会自立会、救世自立浸信会分别成立。这些自立教会或维持不久,或未得发展,未成声势。
1904年,后来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发起人俞国桢被推为中国基督徒会会正。这时,他已经在由美国北长老会差会设立的上海虹口长老会堂当了13年牧师。该堂租屋等费用和牧师“束修”除靠30多位信徒“奉献”外,不足部分由差会补贴,由美国传教士范约翰经手发放。俞国桢去领津贴每每受侮,久有自立之志。这年筹资在海宁路、克能海路(今康乐路)口购地建堂,三上三下楼房分作两半,一半作教堂、办学校,一半出租,以租金还借款。〔4〕至此, 差会司库来函宣告与该堂断绝经济关系。〔5〕俞国桢初试教会自立获得成功。
1905年冬,俞国桢和同志者认为中国基督徒会只注重自养,而他们志在自立。于是,俞和黄治基牧师、黄迺裳孝廉、缪颂懋医士等召开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发起人会议。他们定了会名,设临时事务所于海宁路教堂,订立大纲,起草宣言。〔6〕1906年1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一,乘全市信徒在红礼拜堂公祈时,宣告成立。〔7〕随后, 俞国桢和黄治基、黄迺裳、俞廉泉、缪颂懋、丁楚范、谢永钦七人呈报苏松太兵备道,要求给予保护,道台瑞澂准于立案,于1906年3月27日出示晓喻。〔8〕
自立会“由基督教各会华教友忧教案之烈,悲外患之侵,为图消弭挽救而组织,并无西人插足其间。具有爱国爱教之思想,自立自治之精神”。〔9〕向来由西人掌管的基督教会居然拒西人于门外, 自然引起西人反对。清政府徇外人之请也有取缔之谋,光绪帝于1906年3月5日发布上谕,提出“团体原宜团结,而断不可有仇视外洋之心,权利固当保全,而断不可有违背条约之举”;重申保护“外国人命财产及各教堂”。〔10〕因自立会将由各会教友组成,有“拉羊”之嫌,也被一些教会视为不祥之物。在起伏不定时,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中外日报》、《京话日报》、《福建日报》发表时论,赞成国人自立教会,也有基督徒投函报馆表示愿意出头自立。自立会总算站住了脚。
面对中国教会纷纷自立的形势,1907年第三次传教士大会决定:在中国人承担传教经费和人力的基础上,逐步“培养中国教会自立之心,令其能善为督理各务”。〔11〕“又议定请商量筹办中华全国之自立会”。〔12〕不管他们要办的自立教会性质如何,“自立”已是一种不得不认可的现实。在以后中国信徒的自立实践中,传教士较少公开反对,有的还表示支持。天津信徒于1908年再次筹办中国基督教会,得到英国传教士施敏斯(Smith)和王山达(King,Alexander)的支持,获得成功。虽然他们和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没有组织关系,但壮大了自立声势。
1910年6月,浙江省平阳县自立会首先加入中国耶稣教自立会, 该县1914年已有40所教堂,1919年全县自立,平阳始终是自立会的重要基地。1910年隶属自立会的还有湖北天门、京山两县原伦敦会教会。1911年底,山西运城成立自立会。
1911年9月,自立会机关月刊《圣报》创办。1919年时每年发行1.5万册。正常出版至1931年12月;1932年9月复刊后基本正常出至1935年1月;以后继继续续出至1951年5月。
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教自由,信教得到“法律”保证,可以不靠外国势力保护。1913年,自立会报中央政府内政部立案,5月22日政府公报刊登了该部第344号准自立会立案的批文,自立会首次得到中央政府批准。此后,自立会在全国发展速度加快。其他自立教会也纷纷涌现。1913年,穆德主持下的中华续行委办会拟对中国教会进行总调查,调查宗旨有:使华信徒“图教会自立,自行布道,以养成其自行发展之能力。〔13〕”如此,差会控制下的教会也纷纷“自立”。
1914年,因信徒增加,海宁路堂座不能容,又因商务印书馆文昌阁印刷厂迁宝山路,乃倍价出售海宁路堂,在闸北宝通路购地建堂。1915年6月13日闸北堂落成前,上海自立总会于5月30日决定:上海自立总会与上海自立会分开。上海自立总会会长俞国桢,副会长柴连复;上海自立会会长黄家柟。〔14〕总会会所设沪宁火车站北义品里第一弄258号,〔15〕1921年2月从义品里迁宝通路俞(国桢)公馆。〔16〕
1919年至1921年,自立会进入第一个发展高峰,1920年已有189 个教堂,信徒万余人。〔17〕与各地自立会代表共建全国性组织势在必行。1920年6月28日至7月2日,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联合大会在上海闸北自立长老会堂隆重开幕,在军乐声中16省120 余名代表由招待荷旗引导入座,〔18〕其中以浙江、福建代表为多。会议决定:取消上海自立总会,组成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会长俞国桢,副会长林溥泉、郭维新,总干事韩镜湖,审察长柴连复;董事35人,根据各地信徒多少分配名额。会议修订了章程〔19〕
1922年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教会被责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教徒为帝国主义走狗,基督教为迷信;国民革命中,有的教堂、学校被占,传道人和士豪劣坤一样被戴上高帽子游街。教会被迫刷洗洋教形象,建立自立或本色教会,以求国人认同,保教会生存。湖南、武汉、杭州等国民革命军重要活动区域内的教会纷纷革新、独立。1927年全国8000名传教士中约5000名撤离中国或撤到租界,内地教会客观上由华人负责,促成了教会的自立。
1922年5月,基督教全国大会在上海举行, 组成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其宪章表示要“协助各地更普遍的承认中国教会在国内之基督教运动中,当占中枢地位,注意并研究中国教会之自养自治自传之进步”。〔20〕俞国桢代表自立派与会,自立会加入协进会为团体会员,以后历次年会自立会都派代表参加。〔21〕协进会在1924年第二届年会上,成立了本色教会委员会,发起并推动本色化运动以回应非基运动,“本色教会”风行一时。在其内涵未阐明和未被正确理解时,客观上为自立会创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自立”成为时髦。
五卅以后,自立会在《申报》发通告:吾会“二十余年前已窥破西人侵略欺人之隐而力辟其奸,毅然脱离关系,由华民自立自养自传。故吾会对于此次英日蛮横举行,目眦尽裂,决以公理拥护各界,一息尚存,此志不懈。”〔22〕其态度之坚在基督教中可以称道,深得教内外爱国者好感。1923年至1925年,自立会发展形成第二个高峰,据1924年底统计:全国有310多个教堂,其中自建150多个,自购自助30多个;领圣餐信徒2.2万,慕道友2800多人;受薪宣教师150多名, 义务宣教师270名;两等小学80余所;医馆、诊室40所。〔23〕
1926年差会进一步调整政策,1 月的穆德会议决定:差会向中国教会移交权力。〔24〕10月协进会第四届年会上绝大多数会员同意废除不平等条约。〔25〕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了差会经费来源,差会加紧“培养”中国教会的自养能力,1934年1 月协进会组设受托主义委员会,促进自养,〔26〕各教会设计了各种促进自养的方法。这些活动客观上推进了教会自立。1930年至1931年,自立会发展形成第三个高峰,但程度有所减弱。在新自立会成立的同时,也有自立会因种种原因放弃自立立场。1932年有教堂309个,分布20多省及南洋。〔27〕
上海自立总会从1918年开始筹建总会教堂。1921年得到聂云台母亲捐赠价值2万元地皮的许诺,建堂热情高涨,拟与协赞会、 国语讲道会、上海中华基督徒布道团共建公共礼堂,俞国桢为建筑委办长。〔28〕然而聂老夫人去世后,丧家食言。这时俞等已脱离闸北堂,失去原来一批殷实信徒的资助。但自立会坚韧不拔,两次派人往南洋募捐。1926年在江湾翔殷路购地4.2亩,于1929年勉力建成永志堂,1930年7月正式启用。〔29〕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0年10月22日至24日在永志堂开会。到代表53人,23日举行四典礼,即自立会成立25周年、《圣报》创办20周年、第一次全国大会十周年、全国总堂开幕。这次会议具有庆典性。会后成立了总务科,处理总会日常事务。
1932年,一·二八战火毁掉了俞公馆和总会事务所。一枚炮弹击穿永志堂屋顶落在教堂里,幸未爆炸,但室内物件俱失。江湾久被日军占据,信徒的主要居住地闸北成为战区,信徒避走租界。自立会深度受挫。11月俞国桢逝世,自立会从此一蹶不振。
1932年9月,在全国总会总务委员会主持下修复永志堂,1933年1月选柴连复继任会长,〔30〕但会务进行已依赖于总务委员会,委员长由任职江海关的谢永钦担任。1933年3月谢调汉口海关后, 由林鸿斌接任。总会没有专职牧师。
1933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修复的永志堂召开。各地97名代表与会,大会邀请了在南京的中央国术馆馆长、中华基督徒信行救国十人团团长张之江,张只派代表参加。大会改会长制为委员会制,设全国总会执行委员会(后改为理事会),有委员33人,张之江为主席,王鸿为总干事,林鸿斌为教务部长,柴连复为会务部长,谢永钦等七人为常委。
这次会议“深觉前非,思有以改弦易辙,严加纠正,重申目标”。〔31〕对宪章作了较大修改。削弱了自治、挽回教权的内容,增加了“与各方道友协同合作”,“实现本色之基督教会”的内容。并“得请公正之西宣教师担任”“随时指导教务会务”的“名誉顾问”。〔32〕
张之江勉强就职以后,对会务十分冷漠。1934年11月30日至12 月2日总会举行执行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张之江参加,竭力提议修改已经相当温和的总章。要删去“抱定民族自决之心志”,“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保教权”,“谢绝西国差会之任何权益”等内容,认为自立会是敬神团体,与“民族”、“政治”无关。〔33〕1935年9月, 张终于辞职,由邵长庚长老代理主席,〔34〕邵有足疾,不能经常到堂视事。〔35〕事实上操持会务者是王鸿。王曾留学日本,精于法律。会务也仅限于上海,各地分支会对总会“尚多漠视之处”,连会员登记表也“填报者寥寥”。〔36〕
永志堂修复后,因地方偏远,参与礼拜人数多则十余人,少则二、三人。为改变这种状况,1935年总会事务所从四达里迁永志堂,四达里信徒随之前往礼拜,并成立永志堂教务委员会。1936年6月、1937 年12月《圣报》出“永志堂教务委员会特刊”。1935年10月上海6 个自立会教堂按章成立特别区联会,〔37〕区联会开展了一些活动。这些比较实际的组织行为使自立会一息尚存,也使其全国组织的性质发生变化。
1937年八·一三战火对自立会是雪上加霜,永志堂瓦砾无存,档案帐册尽毁。1938年12月,原自立会理事史麟芳、朱保罗重新组织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筹备会,设通讯处于贾西义路(今泰康路)326 号自立会信德堂。〔38〕1939年2月,租大西路108号为礼拜场所兼总会会所。
1939年5月,谢永钦在海关服务35年后退休回沪, 得到一大笔退休金,决心重整自立会。8 月谢出任组设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临时执行部总务股长,恢复永志堂名称。10月《圣报》复刊。1940年1 月永志堂与自立总会分开,总会临时办事处设于海格路237弄1号谢永钦家中。1940年11月谢独资购买宝通路地皮5.3分,捐献以备建永志堂。 〔39〕1941年2月,永志堂也移至谢家。谢受牧职后,成为专职牧师。
日本势力控制租界后, 为管理一向由英美势力控制的基督教, 于1942年组织了上海中华基督教联合会促进委员会,强迫各教派参加,命自立会各堂组织起来以加入该联合会。〔40〕11月27日自立会11个教堂组成上海中华基督教联会,谢永钦任主席,〔41〕1947年改名为基督教自立会上海联会。1943年10月自立会总会和上海联会合作出版季刊《自立》,以一比四分担经费。总会的组织能量已远远不及上海联会。
1939年10月,原全国总会理事陈品洁等人在河南周口成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驻豫办事处,报内政部立案,〔42〕于是出现两个“中央”。1943年,陈借口响应政府内迁号召,下令取消上海总会,将总会内迁周口,上海以迁渝较宜为由指责陈。战时信息不灵,河南、陕西、安徽等地一半自立会归属周口。〔43〕抗战胜利后,一方要上海诸人赴周口执行会务,一方要将总会复员上海。闹到1947年7月, 社会部调解会议主席命令:将驻豫总会复员上海;成立第四次全国大会的改选筹备委员会,维持会务到四全大会;由陈任主任,谢任副主任,在陈未到达以前由谢代理会务;〔44〕解散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临时执行部。〔45〕事实上陈品洁并未到沪就任,在周口另立中国耶稣教会全国总会。
抗战中总会与分支会联络极少,1945年只剩二三处通信息,各地各显神通,自生自灭。
抗战后,总会又作努力,调查各分支会状况,筹备召开四全大会,恢复出版《圣报》,于1947年建成宝通路永志堂。然时局未稳,自立会也已成强弩之末,各地与总会联络热情下降,两次拟开大会,两次延期。〔46〕更可悲的是自立会开始接受西方津贴。1946年9月, 接受协进会200万元补助贫苦传道人的战时救济金,而且继续申请救济。〔47 〕1947年至1949年,多次接受美国教会援华委员会和基督教世界服务委员会中国分会的救济物资。〔48〕至此,自立会从组织上和精神上都已名存实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自立会大都积极参加三自爱国运动。1950年10月,谢永钦在协进会第十四届年会上作了“提倡义工、量入为出”等内容的典型报告。上海联会订立爱国公约,认购爱国胜利公债,捐献救护袋,举办控诉会,参加三自组织,也曾多次讨论参加自立会全国总会,终因总会四全大会未开,组织不健全而“暂搁”。
1954年2月22日至3月14日,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三自革新学习会在永志堂召开。47位学员在政府和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筹委会领导下,进行宗教政策、总路线、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三自革新运动的意义等专题学习,代表们“学习后,检讨自己,都承认曾甘心乐意地作了帝国主义的传声筒”。〔49〕会议用12个小时讨论会务,修改章程、选出新理事,〔50〕谢永钦为理事长。虽然学习会深愿上海联会派代表参加,但上海只派2名列席代表。〔51〕事实上, 这次会议后全国总会再未行使过其组织职能。1956年谢永钦任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1958年,各地自立会参加联合礼拜,接受三自领导。
二、自立会的内部状况与外部关系
(一)组织状况
自立会初创时,虽有全国性名称,其批准机构只是上海地方政府,只在上海活动;1911年浙江、湖北等地成立自立会,自立会已走向全国,但领导人的角色尚未转换,这年发布的简章中仍有“每星期晚七点半钟开会”〔52〕等地方独立性机构的条文。民国后自立会初具规模,才报中央政府核准,成为“合法的”全国机构。
自立会组织不严密。一般某地某人领头成立自立会后,给俞国桢去函,表示遵从自立会宗旨,加入自立会,俞根据来函备文并附上自立会立案批文送当地官府,当地官员一般会复函承认该会,俞将往来信函登载于《圣报》,其组织程序即告完毕。1922年总会规定:各埠报请立案手续由该省董事负责,〔53〕亦即总会不再审核各地成立的自立会是否合格。2年后虽收回此令,各地仍各行其便。 所以总会不时要各地填表,以了解实际规模。1933年前的总纲对各级自立会组织形式未作规定,组织形态各异势所必然;有所规定后的总会组织作用渐失,各地既无求于总会,谁愿自居属会?于是各自为政。1940年,谢永钦面对现实,提议自立教会不问名称、系统联袂,改总会为协会,各地自立会地位平等。〔54〕此提议虽需待四全大会通过方能生效,但主要负责人在机关报上发表的“论说”,其影响自不可低估。此后总会更难“组织”。总会和各地的主要沟通渠道下行靠《圣报》,上行靠信函和人员交往。
各地自立会名称各异。总会理解的“自立”:“乃指自立之教会而言,凡中国耶稣教、中华基督教及名隶公会,而实际归华人已经自养、自传、自理、自治者,均包括在内。”〔55〕如此界定,规模虽大,内部必杂。不久总会着意整顿,多次声明,“各处混称自立名义之教会,非用(中国耶教自立会)某分、支会之名称,或未经本总会许可代为立案者,概不列本总会辖下范围”。〔56〕事实上名称始终没有统一,福建莆田城区堂是自建教堂中的姣姣者,名称为“中国耶稣教”;连上海各堂名称也未统一。
(二)经济状况
经济自养是自立会生存的基础,但也是牵制自立会大量精力的一道难题。
早期上海自立会的经费主要来自以商务印书馆经理、董事、所长等为主的民族资产阶级信徒。
1920年,全国总会开始收“2角捐”充常年经费,即每人每年捐2角钱,此捐后来定名为“自立捐”;1922年,一向赠阅的《圣报》因经费困难几欲停刊,后改收《圣报》捐;〔57〕1923年定7月2日为自立节,这天的纪念捐也上缴总会。总会虽定了各种捐项和奖惩办法,但常常“困难已达极点”,〔58〕2角捐从未收全过,1933年时仅收到10—20 %,“会务幸得上海同志维持”。〔59〕为使常年经费有稳定来源,三全大会决定设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永久基金,存金用息。〔60〕然而除了当时主持会务的林鸿斌将女儿结婚所得礼金435元充作基金外, 再不见基金扩充的记载。1939年以后,总会未得各地捐款,职员全尽义务,少量必需经费由上海同人、主要是谢永钦支撑,真可谓惨淡经营。抗战后,谢永钦仿效俞国桢往各地募款,但效果不好,又拟前往最易筹款的南洋,一方面受行政院约束,〔61〕又未得南洋复函响应,〔62〕终未成行。自立会还曾天真地恳请各国将庚子余款移作自立会经费,当然不会有结果。〔63〕
各地自立会各显神通自养。他们将日常开支压到最低限度,很少办学校、医院及慈善事业,大部分传道人尽义务。日常经费由信徒捐献,不足部分由少数殷实信徒贴补,1925年人均年捐献1.4元,〔64 〕极少有不动产或生息基金,个别办有企业,〔65〕极端的例子是靠传道人往外地游行布道、鬻书画筹集经费。〔66〕
(三)构成和分布
自立会300 多处教堂大部分是各宗派的少数信徒从家庭聚会开始,逐步发展后建立会堂,成立自立会。大部分没有牧师,由教师、长老、执事等传道人主持。据1946年的一份调查,56个教堂中有7个牧师, 其中3个受过神学教育,负责人有4人大学毕业。传道人平均年龄46岁,最大76岁,最小21岁。〔67〕大部分牧师和几乎所有传道人的圣职由自立会总会授予,如平阳的林溥泉、范志笃,南洋的黄汉光、黄约翰,河南李执中、孙真洗,温州梁景山,福建何学诚、李昆岗,湖北彭邦铨以及谢永钦,这些各地主要骨干无不如此。1916年规定牧师资格为“道学院毕业、能晓国语音乐者”,〔68〕现实迫使他们在1920年就修订为:“信心、学问、道德为全教会所推许”。〔69〕事实上受职者绝大部分没有受过神学教育或高等教育,一般由会众公举,总会发给证书并举行按手仪式。对此,大公会颇多非议,认为牧职必须授予大学神学毕业者,岂可轻率从事?平阳曾设考场,公开考试择优录用助工传道。
据这份调查,每个教堂平均有信徒和慕道友95人,其中46%为农民,19%为工人,17%为商人,9%为学生。据1930年调查,309个教堂分布于21个省及南洋,其中浙江142个,河南65个,福建18个,江苏、 四川各15个,黑龙江9个,湖南、上海、南洋各6个,安徽3个, 其余各地1—2个。〔70〕1947年时有211个教堂,分布于12个省及南洋, 分布状况与此大致相同。〔71〕
自立会原属教派没有系统资料,据零星资料可知:内地会、伦敦会、长老会、浸信宗较多。来自各教派的信徒,信仰特点各异,总会取宽容、包涵态度,只规定了一些原则性信条。但主要分布乡间、由本地未受过神学训练的传道人带领的自立会普遍流行赶鬼医病,追求灵性经验,几次全国大会上都有赶鬼医病经验介绍。
(四)与外界关系
自立会离差会而去,自然失去外国势力的“保护”,也没有像佛、道教的一些寺观那样寻求流氓、帮会的“保护”,却十分注意寻求中国官方的保护。自立会经历了清朝、民国、汪伪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历史时期,十来次政权变更,与每个政权都尽可能保护良好关系,前后约十次分别呈报备案。
自立会宗旨中消弭教案、挽回教权、爱国、维持公益等内容赢得中国士绅的普遍赞许,各地自立会大部分得到他们支持。冯玉祥帮助河南自立会;山西运城民政司赠给会所和开办费;河南汝南县西楚铺士绅将149亩公产地充自立会办学经费。
自立会不断调整与差会的关系,态度渐趋温和。创办时,俞国桢等鉴于“吾国教务向由西人主持,吾国信徒地居主位,反致因人成事,不能发起个人主体之思想”〔72〕的局面,不要西人插足。绝大部分差会对自立会侧目,阻扰各地自立会诞生。1911年简章去掉了“无西人插足”,增加了“为西国差会在内地传教者求恩”〔73〕的内容,区别对待传教士和差会。1916年会纲特加声明:“饮水思源,不敢忘本,任重道远正赖提携,乃外间有谓本会与西教会素称水火,积不相能者,殊属昧于真相。”〔74〕1922年自立会加入协进会,差会对自立会一度比较“宽容”。1924年为闸北堂教产,总会与长老会差会势不两立。1933年后自立会方针大变,差会不再在意自立会。
因自立会有“拉羊”之嫌,又因自立会和俞国桢一度赢得全国上下赞誉,妒嫉难免。中国教会人士往往讥笑自立会租房设堂以自炫,指责他们尊己抑人,其支持度不及士绅。浙江镇海小港偕我会以为与自立会势难两立,负责人纵妻登门嘲骂,沿街毁谤。〔75〕自立会努力改变姿态,缓和矛盾。1916年的会纲特加“附说”:“若统国教会皆能达自立之目的,自立二字便当取消。”〔76〕俞国桢等对上海教会联合布道等活动总是热情参与。
三、自立会与时代
由前所述可见,自立会的产生、发展是顺应了时代需要,其历史轨迹和中国人民族意识的潮涨潮落同步,与当时的政治风潮、思想文化思潮相关,与教会自立发展趋势一致。
自立会成立时的首要宗旨是消弭教案,调和民教,让国家不再继续19世纪下半叶的悲剧,因教案与西方列强引起争端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在当时是现实而迫切的、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但20世纪以后,差会和中国政府都调整政策,教内外华人也改变对策,民教矛盾不再经常表现为“教案”,民教纠纷往往不再激化,处理结果与19世纪大相径庭。也就是说,自立会创办后,其首要宗旨已由社会各方“协力”逐步实现。
自立会宗旨中消弭外患,挽回权力,拒斥西人的目标正义而高远,但决非一个不大的基督教团体力所能及,其实现更多地取决于国家意志。1927年,蒋介石与在美国长大的宋美龄结婚,国民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依靠美国。1930年,蒋受洗入教,政教关系空前融洽,基督教成为建国和抗战的助手。以美国为主的差会已经找到既无需交出教权,又让中国教会“自立”的模式:中西共组“中华教会”,差会向其交权。再与差会、传教士对峙已不合时宜。自立会要么失去宗旨,结束其历史使命;要么调整自己的宗旨,改变形象。自立会选择的是后者。
所以自立会不停地修改大纲。1916年会纲的宗旨去掉了“消弭教案”,增加了“实行圣道,宣传救恩”的内容,而且特意加注:“基督为救世主,凡属人类皆应皈依,国人不察,往往目基督教为外国教,种种蜚言殊多障碍。本会对内免假借外力之嫌疑,对外负自立自养之责任。”〔77〕1920年的大纲去掉了过去直露的注,增加了“使各会教友,不分界限,联络同志,以大一统为唯一之宗旨,”〔78〕可见自立会在追赶潮流,参与各教派“合一”的大工程。1933年的总章称:“本会抱定民族自决之心志,遵守信教自由之原则,并本于基督教义及其博爱、牺牲、救人之精神,阐扬真理,废除不平等条约中之保教权利;唤起全国民众,实现本色之基督教会以期适合中国国情,深印人心为宗旨。”〔79〕其中,传教是基督教会的当然任务,废约已是当时教内外的普遍要求,本色教会是差会系统的口号。自立会实际上没有了自己的宗旨。
逐渐失去自己宗旨的自立会得以生存和发展,主要是其“自立”的主张顺应了时代需求。但是,当时居中国教会“正统”地位的是差会,随着差会支持的、组织规范的“中华教会”不断产生,尤其是1927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产生后,自立会魅力大失。30年代后自立会逐渐放弃“自立”。1940年谢永钦在《圣报》发表论说,主张取消会名中的“自立”二字,因为自立已为全国教会普遍赞许,虽有急进缓进之分,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今后的工作应由立而行,积极传教。〔80〕如此,自立会还有何生存价值?
自立会总会在创办和发展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少地区的自立会因总会代为立案才摆脱差会纠缠、民教纠纷,获得发展。随着教案的和缓、法律的完善、立案手续的下放,到30年代,时代将总会的组织功能也逐步削弱殆尽。
四、自立会的历史地位
自立和合一是涌动于中国基督教历史长河中的两股潮流。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之前的早期自立运动,按组织系统、活动时期和教会特点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差会控制下的主流派教会的自立运动,1922年后逐步明确为本色化运动。和国民政府拥有名义上的国家主权一样,这类教会也有“中华教会”的名称。中西人士共组教会,不少主要职务由华人担任,但经济、人事实权多操西人之手。经济自养是差会竭力促成的目标,甚至以自治诱取自养,由于其庞大的教会机构和众多附属事业,主要还是靠差会津贴。这类教会比直接用差会名义设立大英国某会、大美国某会是种进步,华人跻身教会领导层,比纯粹由西人决定中国教会大小事务也是种进步,这种进步亦非一帆风顺,其中凝聚了不少先进的中国基督徒的努力,涌现了一批华人教会领袖,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三自爱国运动的领袖。这类教会和组织可以追溯到1862年英国长老会和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合作在福建建立的漳泉长老大会。1912年中华圣公会成立后发展速度加快,后来成立的有中华信义会、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中华基督循道公会、基督教中华浸信会联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华总会等,逐步成为中国的主流派教会。
第二类是自立教会。他们脱离差会,由中国信徒承担传教经费,担任传道人,自己管理。他们一般都寻求中国政府的承认和保护。但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政权不稳,自顾不暇,自然不愿重蹈19世纪复辙,因教会问题,尤其是教会内部问题引起外交麻烦,波及政局,所以他们的支持往往在时效性和区域性上有限,或系非正式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不断寻求、不断得到的庇护都是这样。这就注定了这类教会不会有大的发展,其命运往往和主要组织者的命运紧密相联。这类教会和组织可以追溯到1872年广东陈梦南建立的广肇华人宣道会,后来还有广东诸多的自立教会、中国基督徒会、天津中国基督教会、山东的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杭州市中华基督教会、武汉基督徒革新联合会、山东通圣会复兴团等。其中革新运动多在国民革命高潮中出现,马日事变后流产;其余多在20世纪初至1927年间出现。30年代后有的改变了宗旨,有的改宗“中华教会”,回到原宗派,真正坚持到1949年后的很少。
第三类是信仰上追求属灵,组织上独立于主流派教会体系,也不和自立教会发生关系,往往自称是土生土长的教会。他们在经济上不完全拒绝国外资助,有的资助还不少,人事上不完全拒绝外国人担任教会职务,但人事、经济等支配权和教会管理权在华人手中;他们与国外宗教组织有交往,但不是母会与子会的关系;他们在宗教崇拜仪式上往往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组织形式也往往与众不同;他们认为物质世界充满了罪恶、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对社会政治潮流取回避或不合作态度。这类教会和组织有真耶稣教会、耶稣家庭、基督徒聚会处、伯特利教会、中国基督教长老总会、基督徒会堂、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等。这类教会主要产生于20年代以后,而且有绵延不断的发展,包括抗战中和抗战后,至50年代初拥有大量信徒。
在早期自立运动中,自立教会最早最彻底地实现自治;虽然经济困难,但努力实现自养。最早提出挽回教权,最关心社会热点问题,最热忱参与社会变革和公益事业,其着眼点在改变教会的政治面貌,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另两类教会的自立、自养、或自传的着眼点都在于如何使基督教在中国更便捷地传播,是一种宗教行为。就此意义而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和自立教会一脉相承。这也是这类教会最早并最广泛地赢得中国官方和士绅同情和支持的原因。自立教会各种组织中,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是最早成立并组成相当规模教会的全国性组织,在自立教会中奏出了最强音。自立会的成立和最初的发展带动了中国基督教自立潮流的形成和发展。
注释:
〔1〕华友来稿《中国教会自立策》,《中西教会报》1903年9月第6页。
〔2〕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年版,第554页。
〔3〕《中国基督徒会小启》,《中西教会报》1903年4月第14页。
〔4〕参见周盛清《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史略》。
〔5〕《自立堂保护文告》,《圣报》1924年7月第17页。
〔6〕庞树桑《本会沿革》,《圣报》1933年1月《俞公宗周专号》第5页。
〔7〕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年版,第611页。
〔8〕《钦加二品衔 赏戴花翎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瑞
出示晓喻》,《圣报》1911年9月第10页。
〔9〕《追录鼓吹自立会之缘起》,《圣报》1924年7月第2页。
〔10〕转引自陈庆华《四十五年前开始的中国基督教爱国自立运动》,《大公报》1951年2月9日。
〔11〕《百年大会集议》,《中西教会报》1907年第7期第32页。
〔12〕《百年大会集议》,《中西教会报》1907年第8期第22页。
〔13〕司德敷《调查中国宣教事业之露布》,《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5期第174页1918年出版。
〔14〕觉非《上海总会议事纪要》,《圣报》1915年6月第9页。
〔15〕《注意迁移广告》,《圣报》1915年1月封三。
〔16〕《俞宗周为建总堂敬告认捐诸君》,《圣报》1921年2 月扉页。
〔17〕〔19〕韩镜湖《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联合大会纪实》,《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6期第57页1921年出版。
〔18〕《耶教自立会联合会之第一日》,《申报》1920年6月29 日第11版。
〔20〕《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宪章》,《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一届年会记录》第1页。
〔21〕《总务委员会通告(二)》,《圣报》1932年12月扉页。
〔22〕《耶稣教自立会总会之通告》,《申报》1925年6月13日。
〔23〕《驳大中华厂总理反教辨惑复函》,《圣报》1925年1 月第11—12页。
〔24〕董健吾《中西瞩目的穆德会议》,《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9期第153页民国十六年出版。
〔25〕《年会中之三大讨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第四届年会报告》1926年10月13日至20日第150页。
〔26〕朱立德《受托主义委员会报告》,《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十届大会报告》第59—60页1934年出版。
〔27〕1932年俞宗周“呈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文”,《圣报》1933年1月第14页。
〔28〕《俞宗周为建总堂敬告认捐诸君》,《圣报》1921年2 月扉页。
〔29〕庞树桑《本会沿革》,《圣报》1933年1 月《俞公宗周专号》第8页。
〔30〕《总务委员会通告(一)》,《圣报》1933年2月扉页。
〔31〕王鸿《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近两年来之检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3期第22页1936年出版。
〔32〕《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总章》原件, 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14目录号1卷号1。
〔33〕《本会执行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圣报》1934年12月第2—4页。
〔34〕《本会代理主席业已蒙准备案》,《圣报》1935年9月第7页。
〔35〕韦绍曾《邵长庚》,《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六十周年、新堂落成纪念特刊》1948年3月14日出版。
〔36〕鸿《本会今后应有之努力》,《圣报》1934年3月第1—4 页。
〔37〕《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会议记录》,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14号目录号2卷号5第19页。
〔38〕《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会议记录》,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14目录号2卷号5第3页。
〔39〕《永志堂会议记录 1940年11月16日》,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14目录号2卷号6。
〔40〕《永志堂会议记录 1942年10月17日》,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14目录号2卷号6。
〔41〕《上海基督教自立团记略》,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33 目录号2卷号26第2—9页。
〔42〕《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驻豫办事处成立宣言》,原件存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14目录号1卷号2第144页。
〔43〕《李天相致谢永钦函》,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14 目录号3卷号16第13页。
〔44〕“1947年8月7日全国总会呈社会部文”,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14目录号1卷号1第68页。
〔45〕《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理事陈品洁、谢永钦启事》,《圣报》复刊后第2期1947年9月出版第1—2页。
〔46〕曾定1937年1月1日至3日及1948年2月18日至22日召开,均被延期。见《圣报》1937年1月第7及《圣报》1948年12月第4页。
〔47〕《Survey of the Chinese Churches after the War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Biennial Meeting,December 1946》,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14目录号1卷号1第17页。
〔48〕《基督教自立会上海联会执委月会记录1947年9月至1949 年12月》,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14目录号2卷号11第4—22页。
〔49〕〔50〕谢永钦《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三自革新学习会总结报告》,《天风》总407号第1页1954年3月29日出版。
〔51〕《基督教自立会上海联会执委月会记录 1954年2月21 日》,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14目录号2卷号11第76页。
〔52〕《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简章》,《圣报》1911年9月第10页。
〔53〕庞子贤《总会董事会三日记》,《圣报》1922年5月第6页。
〔54〕谢永钦《改组本会全国总会之建议》,《圣报》1940年1 月第7—9页
〔55〕庞子贤《为自立会全国联合大会事答客问》,《圣报》1920年7月扉页。
〔56〕《全国总会声明》,《圣报》1924年8月第29—30页。
〔57〕《俞宗周三次通告各省自立会》,《圣报》1922年3月第1页。
〔58〕《本馆聘请维持员并募捐奖则》,《圣报》1926年11、12合期第29页。
〔59〕谢永钦《本会今后之方针》,《圣报》1933年7月第1页。
〔60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永久基金保管条例草案》, 《圣报》1933年3月第14页。
〔61〕《社会部训令,1946年2月5日》,见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14目录号1卷号1第71页。
〔62〕《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记录 1946年6月9日》,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14目录号2卷号9第29页。
〔63〕乐诗农《提议恳请各国允将庚子余款移作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传道经费意见书》,《圣报》1920年4月第4—5页。
〔64〕《驳大中华厂总理反教辨惑复函》,《圣报》1925年1 月第12页。
〔65〕浙江瑞安办过席厂。见《圣报》1924年7月第3页。
〔66〕澹人《李君茂榛小传(续)》,《圣报》1925年4月第18 页。
〔67〕《调查表》,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14目录号1卷号2 第88—143页。
〔68〕《自立会会纲露布》,《圣报》1916年3月第10页。
〔69〕《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大纲》,《圣报》1920年2月第1页。
〔70 〕庞子贤《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统计表》, 《圣报》1930年12月第10—13页。
〔71〕《圣报》复刊后1—4期,1947年6月起出版。
〔72〕《追录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宣言》,《圣报》1924年7月第2页。
〔73〕《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简章》、《圣报》1911年9月第10页。
〔74〕《自立会会纲露布》,《圣报》1916年3月第9页。
〔75〕乐诗农《镇海小港自立会近闻》,《圣报》1920年5 月第11—12页。
〔76〕《自立会会纲露布》,《圣报》1916年3月第9页。
〔77〕《自立会会纲露布》,《圣报》1916年3月第9页。
〔78〕《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大纲》,《圣报》1920年2月第1页。
〔79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总章》原件, 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14目录号1卷号1。
〔80〕谢永钦《改组本会全国总会之建议》,《圣报》1940年1 月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