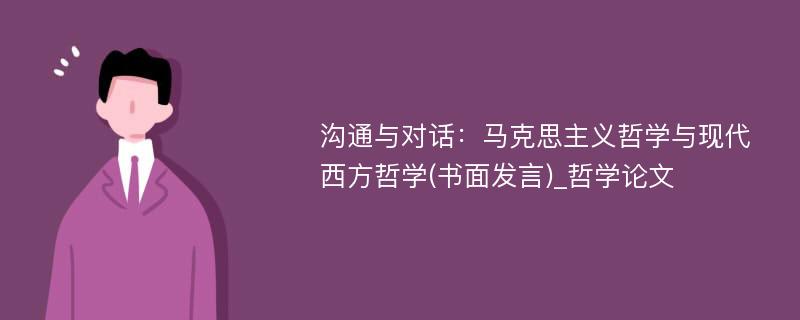
沟通与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
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对于为什 么要开展这种对话,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这种对话到底应在什么基础上展开以及在什么 程度上成为可能,人们实际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说缺乏必要的和深层的追问;相应地, 对于如何才能更加自觉和有效地开展对话,人们也缺乏深入的探讨。由此,尽管在一些学者 的个体性学术研究活动中,这种对话实际上一直在进行,但在很大的程度上却处于一种自发 的状态,并往往局限于个体的学术活动内部或不同个体之间。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 方哲学这两个学科之间,在不同学科的教师群体之间,在不同的哲学观念和方法之间,却很 难说是真正自觉合理有效地在开展对话。本文就积极开展这种对话的一些前提和方法论提供 以下不成熟的断想,向学界同仁讨教。
这种对话在什么意义上是必要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德国,本来就是一种西方哲学。为什么会在马克思主义 哲学产生一个半世纪以后,提出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这本来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产生以后主要是在苏联、东欧和 中国等国家得到了发展和实现,而与西方文化有所脱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走向了对峙。现 在 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问题,正是为了打破这种隔离与对峙,加强二者的交 流与沟通。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就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还是看作一种外来 的思想理论文化,强调它的外化和世界化的问题,那么我们自己目前的理论定位究竟在哪里 ?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被看作一种中国哲学还是外来哲学?它在当今中国的根源性和基础性 究竟何在?这既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前提性问题,也直接涉及到对 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理解。我们认为,对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对于自 觉合理设定我们在对话中的位置至关重要。
在本来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是德意志民族的一种哲学,不可避免地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 ,同时由于它依托于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加上马克思对于人类命运的特别关注并将对其的 思考自觉地融会到自己的哲学思想之中,因而又具有强烈的人类性和世界性,从而能够对于 其他地域和民族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正是在这种交流与沟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挥着自己作为一种世界哲学的功能和作用。而对每个民族来说,则有一个对于外来哲学的 了解和认同的问题。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结合中 ,尤其是在与俄国、中国等国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认同,也得到了实现。然而它的进一步发 展又需要进一步走向世界,走向当代人类文明。这就提出了与当代世界哲学进行对话的问题 。
当然,对于为什么要在中国哲学界开展这种对话,今天人们实际上有不同的理解和期望。 对此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角度和看法:在最低的程度上说,现代西方哲学的存在是客观事实, 因此,即便为了批判西方哲学也要了解西方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了解 和学习西方哲学是为拓展自己的哲学研究视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西方哲学研究的角 度来看,要说通过这种对话去发展本来意义上的现代西方哲学,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恐怕还只 能是一种愿望,但通过这种对话可以有助于发展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与教学,这大概是没 有疑义的。正是从这些不同的目的和愿望出发,人们对于这种跨学科对话实际上有着不同的 期待和态度,采取着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也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哲学 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的划分本身就是一种不尽合理的现象,仅仅 从各个学科的角度来考虑对话问题,尽管都有一定的历史缘由和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有相 当的片面性。我们认为,哲学研究应立足于当代中国哲学的高度来考虑现有各分支哲学的对 话问题,使之能够真正超越各具体学科的局限和狭隘眼界,促进各分支哲学的沟通与融合, 建构起既有传统根基又有当代内涵、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当代中国哲学体系。从这 样的高度上,也许我们能够提高开展对话的自觉性和有效性。
这种对话在什么程度上是可能的?
一般承认不同哲学之间可以对话并不困难,但要说清这种对话在何种意义上真正可能的则 不那么简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形成并发展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与文化土 壤之中,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思潮,有不同的学术基点和关注重心;不同的哲学流 派之成为独特的哲学流派,本身就在于它们有不同的哲学观念、哲学范式和哲学方法,有不 同的哲学理解和价值观念等;某些哲学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定哲学流派的研究者和代言人, 正在于他们能够接受并运用一定的哲学理论、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等,而这必然带来他们不 同的致思理路和学术取向。这样,不同哲学之间的对话表面看来是哲学家之间以直接或间接 的方式在对话,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哲学理念、不同哲学方法等之 间在进行着交流与碰撞。这里实际上存在一种重要的“文化围场”或叫“哲学围场”——你 不真正进入一种哲学你就没有能力和资格以某种哲学的名义来说话,而当你真正进入一种哲 学后则必然表现出对于其它哲学的异己性和排他性。这就势必使不同哲学之间的真正有效对 话 变得更加困难。应该说,文化围场和哲学围场都是客观的现实,我们的任务正在于提高对于 围场的认识,从而能够更加自觉地进入围场和走出围场。
这种对话在什么层面上是有效的?
这里可能有许多的层面。比较基础和广泛的层面,主要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 和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对话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们依据于各自所理解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来进行的,实际上是中国学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 代西方哲学之间的碰撞。由于他们各自的理解都带有很强的个体性,不同哲学家之间的哲学 理解则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对话既是非常普遍的,同时也有相当的局限 性。在较为直接也更为重要的层面上,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与当代西方哲学家之 间的对话,当代西方哲学家作为西方哲学发展的主体力量和推进者,对于当代西方哲学的 了解当然比局外人要深入和透彻,因此这种对话无疑更显重要和有效。但应当注意到,这种 对话对于双方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外语水平和知识背景无疑都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否则难以达到一种真正的对话和理解。在更高的层面上,则是哲学观念、哲学理想 和哲学方法等之间的对话,这是以真正哲学的方式来展开对话的关键之处,也是这种对话的 难点所在。我们知道,即便是西方哲学内部,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不仅在许多具体 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学术分歧,还有一个彼此之间是否把对方看作哲学的问题,他们都在实 际上对对方作为哲学的合法性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和挑战。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区别与差异 ,从根本上说是不同哲学观念、哲学理解和哲学方法的不同和差异。既然如此,从根本上来 说,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哲学对话就应当在哲学观念、哲学理想和哲学的层面与高度上来 进行。但要做到这一点则格外不容易。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差 异既有学术方面的,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这就使得这种对话更加复杂和困难。但这并不排 除他们之间在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可以发现共同的兴趣,找到共同的语言,运用相关的方 法,并相互有所启发、有所借鉴、有所共鸣。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认为,真正的对话,应当 是以问题来引发、激起和带动的。所有真正的哲学都应当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在对于当 代人类在生活生存中的难题与困惑、生产实践的多重价值、科学技术的正负效应、人文命运 的前途忧患、活动方式的合理化规范、社会发展空间及其阈限等的深度哲学关注与前提性追 问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可以找到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也能在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中相 互沟通,彼此借鉴,从而不仅促进自身的发展,也能为人类哲学思维的整体发展作出自己的 应有贡献。
欧洋,1954年生,哲学博士,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路径
首先需要辨析的是,是否存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真正对话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一般而言,二者是在基本相同的西方 社会条件和理论背景下产生的。从理论背景上说,近代西方哲学表现了一种共同的思维特征 和传统,就是将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看作是彼此独立互相分离的。这种思维特征和传统 已 使哲学的发展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和困境之中。
近代哲学上述思维特征和传统的根源在于:(1)心理主义的原则。所谓心理主义,是指把世 界区分为(人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人的(内部)意识世界就象一所带有墙壁和楼层的房子 ,是人的全部体验的寄居地,被称为“心灵”;心灵能确定人的体验之界限并将它集中于该 界限之内。心理主义由此为哲学家们制造了一个永恒的认识论难题:人如何走出这个自身的 心理世界去获得关于外界的可靠认识呢?与心理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生理主义主张只能依 靠经过感官和周围神经系统这类途径,以及它们所获得的刺激程度来接受和传递外界信息。 这样便极易混淆意识的判断行为(作为心理学的对象)和判断内容(作为逻辑学的对象),以判 断行为的主观性消融判断内容的客观性,否认自身意识的经验感知和判断内容具有客观存在 的特征,实际上也就是把意识的感知和判断内容的“为我存在”与被感知和判断对象的“自 在存在”区分和对立了起来。(2)主体实在论的原则。近代西方哲学从人和人所具有的认识 能力即主体性出发,去讨论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极大地推进了对主 体认识能力及认识方法的研究,推进了自然科学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近代西方哲学 家视野中的人,不是作为简单的自然存在物就是作为抽象的精神存在物,人的理性、主体性 ,也被看作是一种反思的对象而成为与其它对象一样的独立实在,从而将认识主体和认识对 象看作是两种彼此分离的独立实在。因此可以说,心理主义-主体实在论的原则是决定思有 、心物和主客分离这一特征与传统的近代西方哲学思维范式。
摆脱近代哲学发展的矛盾和困境的出路,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超越这种思维范式进而克服 由它所决定的近代哲学特征和传统。这正是西方哲学继续发展所面临的基本课题,也是近代 哲学向现代哲学转折的主要标志和真实意义。从哲学史的逻辑和历史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 恰恰是在对近代哲学思维范式的超越和突破中产生的。由此可以明确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 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面临着基本相同或者说相似的课题,二者的理论目标是相近的或是相似的 。这种基本相同的哲学课题和理论目标,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运用新的 思维范式超越传统哲学时,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可容性,体现了在哲学发展史上具有某 种共同的意义,应该说,这种一致性和共同意义,便是今天我们讨论加强二者之间对话的基 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存在的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可容性,以及所体现的某种共 同的哲学史意义,主要可以从下述几方面进行思考和把握:
1.关于哲学课题和视域的转变。现代西方的大多数哲学家都已不再局限于一般的唯物唯心 、可知不可知之争,而是力图回避或超越这种传统争论;也不再集中于论证(超经验的)本体 世界的存在,而是把外部自然界的自在存在作为哲学研究(不言自明)的前提,将重点转向具 有主体意识的人及与人相联系的对象世界。这表明,现代西方哲学的课题和视域已从建构 抽象的形而上学体系,追求终极意义的基础、本体,转向注目于和人相关联的客观世界,关 切人类自身生存的客观基础、关切人的现实生活。
这显然也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的出发点和方向。马克思哲学产生的理论标志正是在于,从人 的存在方式即感性的实践的活动出发,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彻底颠倒,将哲学的课题和视野 确定在研究人的现实存在和发展,以实践为中介的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物质变换与交互 活动上。
2.关于主体与对象关系问题的转变。近代西方哲学主要是论证思维对存在、主体对客体的 把握和认识关系,现代西方哲学课题和视野的转换,同时也使这种把握和认识关系不再成为 哲学家们关注的中心和论证的重点了。科学主义思潮固然如此,人本主义思潮更不例外,它 不但将传统理性哲学的主体与对象的认识关系排除在哲学讨论的视野之外,而且还将这种关 系转变为显现和构成关系。从叔本华、尼采等早期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开始,一般都是如 此,而在胡塞尔和萨特那里得到了系统而细致的描述。
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之间具有类似性和可 相容性。在马克思看来,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又是在创造一个对象世界。这“创造”,一方 面表现在,通过主体的理性能力揭示、整合所面对的自然和社会现实,形成知识系统和科学 理论 ,并通过内化为劳动者的智力、技能诸素质,物化为表现技术进步的劳动工具等成为更有效 地改造实在世界的手段;另一方面表现在,人通过改变自然的活动,在客观对象中实现着人 所特有的目的、意志、情感和价值观念,建构起一个属人的意义世界,使“人化自然”打上 了主体的烙印。
3.关于主体自身意义的转变。近代西方哲学将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看成是具有形而上学意 义的独立存在的实体,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各派哲学家,强调人作为主体及 作为主体的自我之意义,在于它趋向于对象的活动性和实践性,在于它超越的意向行为和构 成能力。换言之,是把人理解成超越性的、创造性的活动和过程本身,主体、自我是自由、 自主、自为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肯定人首先是物质的存在,但同样从人的活动和实践、自由和自主的 角度确定作为主体的人的意义。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动物是凭本能自发 自在地生活于自然界之中,而人则是以实践活动不断地改造对象,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是一个 自己创造出来的人化自然,一个属人的世界。因此,作为主体的人,是实践的存在。实践构 成人的本质,是人所特有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这些内容上的一致性和可容性说明,在超越近代传统哲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 哲学都强调哲学以人及由人所对象化客体化的现实世界和生活为自己特有的课题与对象,人 的 自由和自主、活动和实践则是此课题与对象展开的基础,这是现代西方哲学与近代传统哲学 划界的主要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所共同体现出来的哲学 史意义。
毫无疑问,指出上述这样一些一致性和可容性的内容,并不是忽视或者否认二者在理论内 容和社会阶级属性上所存在的重要乃至本质的区别。
今天,实事求是地开展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批判地研究和借鉴其中的某些 合理东西,也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条可行途径。
就基本理念和方法论而言,可以提出如下几个比较重要的对话切入点。
1.关于哲学评价的视角和标准。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唯物论唯心论、可知论不可知论的 划 界已是一种哲学的常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抛弃了那种以经验常识方式对哲学的简单化 庸俗化理解,却没有深刻反思简单地用这种哲学常识作为评价哲学理论之标准的做法所可能 出现的危险。因此,我们不能再抽象地以基本问题这个划界的标准,简单评价现代西方哲学 理论观点,而是应该超越近代哲学的思维范式和特征,从时代要求和哲学发展出发评价现代 哲学的探索视野、思维方式和理论内容。同时也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研究和评价,也应该转换视角和标准。改变传统的思考视角和评价标准,从现实生活的要求 和哲学的现代水平出发,借鉴现代西方哲学对哲学的本质、功能和意义等的有价值思考,彻 底摆脱近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克服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教条式理解,消除抽象区分唯物唯 心和简单重复哲学常识的作法,这对于当前进一步解放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 教学改革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是有重要意义的。
2.关于体系观念。随着哲学自身思想解放和研究的深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和 解释,无论从内容或形式都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但与此同时,人们又总是希望并力图以新的 形式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表现出了难以割舍的体系观念和体系情结,只是这种重 新建构的基础或核心概念、重点方面或主导线索各异,加上建构者们各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不同解读,因而不但形成的体系面貌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就连以何种名称来表达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特征也颇多争论。这里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建立完整严密的体系,是不是马克 思本人的希望和要求?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所批判超越的其它哲学之间相区别的一种 标志?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并讨论的“马克思主义是体系 还是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这类问题,对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从 体系观念转向问题意识,从单纯考虑理论建构到着重以其科学方法论为武器自觉参与对现实 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是有启发意义的。
3.关于哲学研究领域、视角和方法的多样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包括哲学研究和教学改革 在内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面对已经发生了极其巨大变化的现实世 界和形形色色的现代西方哲学理论,我们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以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依据实践,努力在哲学研究中开辟新领域,寻找新视角,运用 新方法。这是在新条件下深化哲学研究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更深刻地认识和更 有效地改造世界的必然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 正确地分析和恰当地吸取与借鉴其中的合理成分,对于我们更好地适应时代对哲学研究和哲 学教学改革的要求,拓宽我们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创新研究方法,应该是有价值的。
庞学铨,1954年生,现为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与犹太人问题
尽管马克思的父辈已放弃了犹太教而改信新教,马克思仍十分关注犹太人问题。这倒并不 仅仅因为马克思是一位犹太人,或如海涅那样觉得为了获得“进入欧洲文化的入场券”就必 须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是因为第一,哪怕就是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犹太人作为一种 特殊身份的政治—文化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这可以从当时所展开的讨论及马克思所发表的《 论犹太人问题》中看出;其次,在当时,正如马克思所说,“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 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所以“宗教的统治 被当成了前提” (注: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 社1956年版,第448页。)。而且宗教问题是当时可以结成不同阵线进行自由争论的唯一场所;最后 ,那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乱”(马克思语)也恰恰是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 开始的,这指的是D.F.施特劳斯《耶酥传》的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认为整个黑格尔体系的解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今天重读这本书,结合本文所想阐明的 问题,至少在这两点上很有启发:第一,D.F.施特劳斯在这本书中再三强调了犹太主义的普 世主义特征,认为“凡是略去了一个犹太主义特征的地方,也一定略去了一个普世主义的特 征” (注:D.F.施特劳斯:《耶稣传》(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3页。)。第二,福音书中说耶稣是从圣灵而生,施特劳斯指出,这样一个基督教的基本观念 ,应该理解为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每个人都应该承认它、尊重它,即“道成肉身”的不只是 指耶稣一个人,而是说全人类都是上帝的儿女。(注:D.F.施特劳斯:《耶稣传》(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0页。)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指出,犹太教 对基督教最不满、也最表怀疑的就是基督教所宣扬的自己的“非世俗的起源”,鲍威尔赞美 “约翰福音”,也就是想把“作为黑暗因素的犹太人的不信和表现于耶稣身上的光明与生命 加以对比” (注:D.F.施特劳斯:《耶稣传》(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4页。)。施特劳斯在对前三福音书与第四福音书作了详尽的对比分析后,才认为基督 教的神圣起源实际上表达的是人民的意愿,它的神圣本质的唯一活动场所并不限于耶稣一个 人,而是整个人类。这一解释肯定深得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一切具有“人人平等”意识的启蒙 思想家们的赞赏。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就恰恰是立足于人类的解放来理解犹太人问题的解决的,他在 这篇文章的最后宣告:“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人手中获得解放。”(注: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
社1956年版,第451页。)
“社会从犹太人手中获得解放”,这里的犹太人已不仅仅作为一个种族、一种宗教信仰来 加以界定,而是指一种犹太精神,一种犹太人赖以存在的世俗基础。
这种精神与世俗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或可理解为市民社会的最高原则,即“实际需要 ,自私自利”,而“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钱” (注: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8页。)。
马克思的论证是这样展开的:布鲁诺·鲍威尔指出,要求犹太人以放弃犹太教来换取政治 解放(取得与基督徒一样的平等权利)是不对的,因为就是当时的基督徒也未获得政治解放, 而且这样要求等于承认了“基督教国家”(以基督教为国教)是正当的,等于承认了基督徒的 特权、承认了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区分国民、实施宗教迫害是正当的。鲍威尔的结论是犹太 人的政治解放并不在于要求犹太人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在于犹太人、基督徒必须同时放 弃各自的宗教信仰,只有这样才能“消灭宗教”。“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 除。以宗教为前提的国家还不是真正的实在的国家。”(注: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3页。)
马克思肯定了鲍威尔的思路是有道理的(他对问题的提出就是对问题的解决),但同时指出 他对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很片面,因为他只批判了“基督教国家”,而没有上升为对“ 一 般国家”的批判;与此相对应的,也就是说他没有认识到人类的普遍解放。
只有超出了宗教对立意义上的犹太人才不再是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平素的犹太人”。
“平素的犹太人”的“世俗基础”(秘密)就是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金钱。” (注: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 社1956年版,第446页。)
从这一角度去看,就会发现犹太教与基督教在宗教上的对立只是现象;犹太人之所以能在 基督教社会存在并得到高度发展,就在于犹太人并未违反历史,而是顺应历史,成了资本主 义精神的具体体现。马克思说,要是消除了做生意这一前提,消除了做生意的可能性,犹太 人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他们的宗教意识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的现实 的、蓬勃的空气中自行消失。”(注: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8页。)所以正如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一样,现在的基督教又还原 为犹太教,犹太人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殊的组成部分,成了市民社会的特殊的体现者。从观念 上看,基督教国家的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但在世俗生活中,“犹太人的神成了世 俗的神,世界的神。”(注: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8页。)一句话:“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 德文Judc除了‘犹太人’这个基本含义外,还有‘高利贷者’、‘商人’的意思)”中获得 解放。(注: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 社1956年版,第446页。)
后来,马克思在《神圣家庭,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又围绕着犹太人问题连续发 表了三号“文告”,从“问题的提法”说起,讨论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精神的、意志的自 由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间的关系,法同情感与良心的关系,着重强调了犹太人问题决不仅 仅是个“纯宗教”问题,即使把无神论作为市民社会平等的必要条件也远远不够。马克思说 ,必须用现实的犹太人去解释犹太教的秘密,而不是用犹太教来解释现实的犹太人,犹太人 的解放是“彻头彻尾渗透着犹太精神的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实践任务” (注:《神圣家庭,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2卷,第141页。)。当时的启蒙思想 家 认为解放宗教与政治冲突的唯一途径在于不再把宗教当作公事而只当作个人的私事来加以对 待,“国家宣布:宗教,正像市民生活的其他要素一样,只有自国家公布它们是非政治的因 而让它们自行其事的时候起,才开始获得充分的存在。”(注:《神圣家庭,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2卷,第149页。)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把问题再推 进一步:就是在发达的现代国家,即在把划分为非宗教的公民与宗教的个人的国家里,所谓 的“自由的人性”(普遍人权)虽说给了人宗教的与私人占有财产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正如古 代国家所给予的奴隶的自由一样,只不过承认了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天赋权利)是市民社会 中的人,这种自由对于犹太人来说,同时具有两方面的制约性:一是从君主立宪制到民主代 议制,把人从各种特权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就是又把人放在了特权(或可理解为每个人的 特性)的位置上,使人与人处于相互争斗的无政府状态之中。无政府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既摆 脱了使社会解体的特权,又使人与整个社会分离开来,使他们只生活在狭小的团体里面的状 态。这也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公法状态”。在公法状态下,犹太人一方面有了行动自由、 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经营自由的纯粹商业活动的人权,另一方面又生活在彼此分离的相互 争斗之中,现代国家“反而成了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制和人性的直接对立物。这里,代替了特 权的是法” (注:《神圣家庭,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2卷,第149页。)。
从马克思的上述论证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第一,现代国家(当时的德国还远远算不上) 在给了犹太人政治权利(人权)的同时,也使犹太人处于与社会相分离、处于人与人相互争斗 的“公法状态”之中;第二,所以犹太人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宗教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政 治解放问题,它应该与对市民社会的最高原则(货币制度、金钱至上)的批判结合起来;第三 ,这种把社会从犹太人手中解放出来的目标奠基于人类的普遍解放之上。
从哲学观念上看,它鲜明地体现出马克思不是从概念、意志、理论上去诠释犹太人的社会 存在,而是反过来,用犹太人的经济行为去理解犹太人的宗教意识及民族特性,说明犹太人 的“狡猾”、“狭隘”恰恰体现出一个自私自利的社会和统治它的法律之间的关系,犹太人 的“狡猾”和“狭隘”也就是整个社会的狡猾与狭隘。
从对历史发展的理解上看,马克思显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是历史的必然,犹太 人正是因为顺应了这一必然才可能在基督教国家里存在下来。
最有意味和最易引起争论的问题集中在非宗教的公事与宗教的私事的区分上。发达的现代 国家认为这就解决了宗教与政治的冲突,而在马克思看来,这恰好导致人与社会的分离,导 致人与人的争斗。K.施密特对此也持批判态度,认为提出价值中立的政治观,把天赋人权( 自然权利)视为最高的道德,企求靠多元价值的自主性文化和中立化政治来避免人类自然冲 突的恶,这就放弃了对何为“好的”政治制度的关切;而且这种自由主义由于将宗教和道德 逐至私人领域,这就为极权主义、放纵种族歧视的自我中心主义提供了政治条件。这也是L.施特劳斯的观点。在他看来,恰好是魏玛民国的自由民主宪政为纳粹政制铺平了道路。(注:刘小枫:《刺猥的温顺》,见《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
施特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在奥斯威辛之后,“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无疑变得更为尖锐,而且这一提法本身就含有希 特勒大屠杀的恐怖意味。它实际上想告诉人们的就是当所有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都宣告失 败后,就只剩下了大屠杀。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I.伯林认为犹太人只有建立自己的国家 才能生存下去,而据说是保守主义思想最深刻的教父的L.施特劳斯则认为犹太人问题不可解 决,“犹太人问题是人的问题的样板:人的存在依群而分,群与群之间总是相互对抗,不同 的生活理想难免相互抵触。”(注:刘小枫:《刺猥的温顺》,见《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
施特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L.施特劳斯由此开始思考他的政治哲学。仍然围绕着犹太 人问题,除在具体的解决途径上有各自不同的想法外,就学理上对西方哲学(西方文化)的重 新思考而言,旧约与新约、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无疑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马克思虽 说是犹太人,但他始终站在启蒙思想运动(也就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立场上讨论犹太 人问题,他对基督教的批判着眼于对“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与国家的批判,着眼于全人类的 解放。而在L.施特劳斯看来,路德的宗教改革恰恰背离了宗教的神圣性,使神的真理(启示) 可以被任何人得取,只要你有信仰。“基督论使神的真理成为大众的真理,‘基督教成了大 众的柏拉图主义’(尼采)。——而犹太教是少数人(先知)的柏拉图主义,正如真正的柏拉图 主义是少数人的先知书。道成肉身的真理传达方式鼓励着肉身成道的真理接受方式;不是知 ,而是由信而‘成’。肉身成道的真实意思是人模仿神,而在犹太教,神的真理经先知转手 并律法化。其含义是让民众服从神,做神要他们去做的。而模仿则是做神所做的。”(注:林国华:《在不幸中骗人:论政治哲学是对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Leo Strauss 思想的几项注释》,见《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249页。)
看来马克思由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想到人类的普遍解放是有道理的——当然有人会说这是乌 托邦,是在做神所做的,但既然有那么多人以“先知”的面目出卖,离开了传统形而上学的 普世主义而大谈道德价值的绝对主义,那么,作为对“美好生活”的理论关切,乌托邦和“ 做神所做的”就是完全正当的;至于手段上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恢复贵族等级制的“好人当 政”,理论上的论述将同样有力。
霍克海默曾指出,“反犹主义的酒窖政治,说明它根植于它曾得以发迹、最后又趋于衰败 的德国自由主义的土壤之中。”(注:刘小枫:《刺猥的温顺》,见《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
施特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马克思批判德国自由主义,是因为“自由派政治”的注 意力只在国家与宗教的对立上,“以致对政治解放的批判变成了对犹太教的批判”,认为“ 宗教为国家牺牲”是完全正当的。(注:《神圣家庭,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2卷,第144页。)而在“保守派政治”看来,问题只在于要把“古人” 的世界从“今人”的视野中解救出来,(注:林国华:《在不幸中骗人:论政治哲学是对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Leo Strauss 思想的几项注释》,见《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207页。)把宗教从国家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希特勒德国 的一个好公民,在别处就是坏公民”,“好人的意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同样的” (注:刘小枫:《刺猥的温顺》,见《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
施特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这里的“好”,是超历史、超地域、超民族的,它指的是作为美德的价值意义上的“自 然”(physis),而非意识形态的公民品德与民族道德。马克思是肯定不相信这种只存在于人 的哲学沉思中的美德的,他认为,凡在意识活动中想挣脱宗教局限性的斗争,所争取到的自 我意识的“纯洁性”和“无限性”“也同样是神学的局限性”,这里特别指出的是在犹太教 与基督教的关系上的“神学局限性” (注:《神圣家庭,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2卷,第141页。)。所以马克思的传人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才 在读完L.施特劳斯的《什么是政治哲学?》后批上“施特劳斯=神学”这样的字样。(注:刘小枫:《刺猥的温顺》,见《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
施特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这里引人注意的地方在于马克思与L.施特劳斯都反对德国的“自由派政治”,马克思反对 的是他们的妥协、动摇、不彻底,特别是他们在为争取政治自由时,对构成现代国家本质的 “相对缺陷和绝对缺陷”缺乏意识,(注:《神圣家庭,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2卷,第147页。)而在L.施特劳斯看来,整个近代性就表现为世俗性 ,表现为对犹太教的神圣性的反动;近代性(contemporary,也可译为现代性)的世俗性,再 加上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怀疑论、相对论,使得哲学不得不在不幸中骗人,并 重新思考上帝与政治的关系,为哲学生活进行政治辩护。
所以重温马克思150多年前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有关论述,不但可以加深理解马克思如何从犹 太人的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进展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而 且对于如何理解整个西方文化的源流、演进过程,特别是对于在有关重新理解启蒙运动、重 新理解近代性、理解政治制度的价值标准等有争议的问题上有着新的启迪作用。
陈家琪,1947年生,现为海南大学社科中心教授。
现状与限度
据说,“马哲”与“西哲”同属西方思想的现代性范畴,有相同的生成时间和生成环境, 所不同者,马哲是世界观的学问,具有总体性,西哲则是部门性的;以前排斥西哲是不对的 ,因为它有部分真理,但是今天抬高西哲也不对,部分毕竟要服从总体。
我有三个问题。
一
马哲西哲是西方人的东西。这是第一个共识。
这个共识意味着什么?至少它们对于我们是移植的、派生的。如果橘逾淮而北为枳,那是枳 而不再是橘了。我们所共识的是橘是枳?
不管马哲西哲,作为西方思想,至今他们反省到什么地步?我们应该心中有数。如果他们在 反省中发生了演变,例如早已不再把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哲学当作世界观看,而且提供了大 量的事实证据和理论根据,包括马克思哲学本身的反讽性质,致使马克思哲学以所谓“西马 ”的种种形式成为西方现代思想的重要构成因素。这时,我们仍然把马哲说成是世界观的学 问,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说的是自己的枳,与别人的橘无关。因而尽管叫马哲,也 是“东马”,不再属于西方现代思想的范围了。
这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应该分清楚,不该把谈枳自以为是谈橘,混在一起。否则,我们 就成了现代的“刻舟求剑”人。
我谈的是橘,即西方人的马哲。别的不说了,有一点已成常识。马克思成其为马克思,是 以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起家的。马克思给意识形态规定了两个基本特征:“把特殊的东西说 成是普遍的东西”——“真理性”其实是“伪科学性”;“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 西”——“权力性”。不管是马克思本人,还是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是否逃脱了这样的“ 意识形态命运”呢?
二
学现代西哲有很多学法,但不管有多少学法,有一个“概念”应成为共识,那就是“界限 意识”。这一点模糊不清,暖昧不明,至少可以判断:不得心法,不得要领。
这无非是说了一句大白话:凡人的理性、人的智慧,包括它的工具,都是有限的。否认这 一点,例如想依据所谓辩证法把人的理性变成无限、绝对,甚至借历史的无限未来的空头支 票以贴现,这是非法的、狂妄的、欺骗的“僭越行为”。
从好的方面看(即不从统治意识形态看),这可能是把理性与信仰混淆了,说得确切点,是 把理性的理想(含“应该”)与信仰混淆了,抹煞了它们之间的界限,以至当作直接同一性( 辩证同一不过是伪装的直接同一,同一者早已“原形先蕴”了)看待。
例如,信仰者说“上帝与我同在”,信仰者很清楚,我绝对不是上帝,否则是原罪、渎神 。但是,理性者或意志者说:“我是上帝”、“朕即国家”、“天人合一”,这不仅是“把 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我即真理),尤其是或归根结底是“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 统 治的东西”(我即权力)。
西方的现代哲学对自身前提的反省已经反省到任何形式的“唯我中心主义”的不可避免的 虚假,以至有陷于“虚无主义”的危险。
我们对此该怎么看呢?
简单地否定,简单地肯定,还是另有取舍的眼光?
三
西方早有人出来断然否定了。
列奥·施特劳斯以他犹太神学、古典哲学、政治哲学的精深修养,洞识现代思想的根本缺 陷乃在于“虚无主义”。用他的话说:“理性主义本身建立在非理性、非明证的假设之上; 无论它看上去多么有力量,理性主义实际上是空洞的。”(《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再生》)他 还承接休谟、雅可比的论证说:“理性主义必然导致怀疑主义、相对主义,最后是虚无主义 。”(转引自古内尔《理性、启示和自然——施特劳斯主义之前的施特劳斯》,见《启示与 哲学的政治冲突》,载《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14期)。
用不着在这儿花力气证实施特劳斯的判断。只要精于理性主义之道的人,自会自知理性的 最终根据作为前提不过是人为设定的。所以靠理性达到的“真理”避免不了意识形态独断论 。 在西方,这已成为常识,成为人们重新思索的起点。
在这一面,大概没有人同施特劳斯较真。问题出在如何克服虚无主义的出路上。出路不同 ,对上述即便为真的判断,也并非没有重新解释的余地。比如对尼采的判断“虚无主义即颠 倒的柏拉图主义”,不是不可以作悖论偶在论揭示的。我特别提请注意,悖论偶在是非同一 的断裂的限制性相关,而不可能像矛盾或辩证法预设了同一的转换。
至少有三种出路。
一种是坚持虚无主义,但在相对主义或历史相对主义的规范形式上,这是一种没有出路的 出路。西方新潮哲学大体如此,几位“临界哲学家”除外,如康德、海德格、卢曼等。
一种是坚持绝对主义,但不是启蒙理性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绝对主义,而是犹太正教与希腊 哲学相结合的古典绝对主义。施特劳斯为其代表。
第三种是既不绝对也不虚无而含两者断裂式相关的悖论偶在论。由于后现代性对现代性前 提的审理,少数哲学家已经接受了“悖论”的启示。联系现象学的“先天性相关”、海德格 的“本体论差异”、“语言的显隐二重性”、卢曼的“上帝是集中的悖论”等,一种端倪已 然指示,现代智慧并非像施特劳斯断言的“理性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一滑到底 的深渊。偶在论不仅可以救治现代理性的虚无主义放纵,而且同样可以救治古典理性的完美 等级主义虚妄。
当然,情况远未明朗,争论与探索仍在继续。值此西学反省之际,我们照原样定谁于一尊 ,所谓“整体部分”、“一体两翼”云云,总算不得一个好办法。
张志扬,1940年生,现为海南大学社科中心教授。
标签:哲学论文;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论犹太人问题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基督教论文; 耶稣传论文; 犹太民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