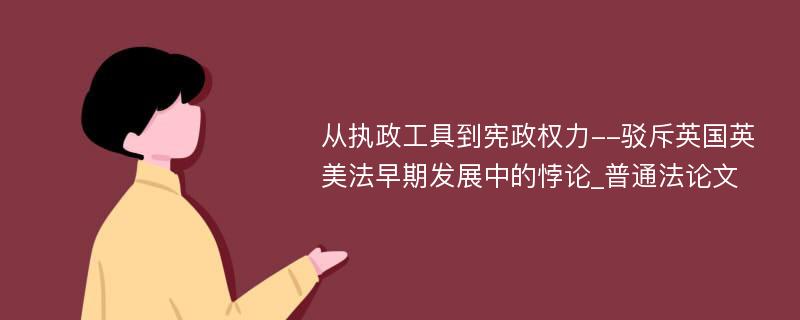
从治理工具到宪政力量——驳英国普通法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通法论文,宪政论文,悖论论文,英国论文,过程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88X(2009)06-0149-06
普通法是英格兰政府在与多元分散的地方势力相互制衡、妥协、竞争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中央集权化的产物,如同英国著名的法律史学者S.F.C.Milsom所言,“普通法是在英格兰被诺曼人征服后的几个世纪里,英格兰政府逐步走向中央集权和特殊化的进程中,行政权力全面胜利的一种副产品。”[1]
然而,细究下来,普通法仅仅就是中央集权过程中行政权力的副产品吗?考察16世纪以后的英国法律史,曾经是英王权力忠实象征的普通法,为什么逐渐与王权发生冲突,甚至转而成为抗衡君主专制的独立力量?本文将试图分析普通法自身在发展演进中这一必然展开的悖谬。
普通法最初的确是作为巩固国王权威和统治的工具,在向全国各地的逐步渗透中形成发展起来的。然而在这一漫长的演变过程中,衍生、分化并附着于其上的权力机构、职业群体、实践技艺以及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潜移默化之中凝固并强化了普通法的自主性,使之不仅最终脱离了王权的荫蔽,而且摇身一变,成为维护法律至上,反对王权恣意的抗衡力量,从而具有了现代法治意义上的宪政色彩。
一、英国普通法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地方势力极为分散的情况下,当时普通法成为王权向王国下层延伸的工具,最鲜明的体现是巡回法院的产生及运作。
(一)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面临的重要政治问题
1066年诺曼人的铁骑横扫英格兰岛后,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留下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并没有改变,但封建制度的某些特点却已正在发展。塔形社会的底层是奴隶,上面是自由民或平民,依赖于贵族或贵族的自由侍者(如骑士)。每个平民之上通常都有一个领主,建立了人身依附关系。为便于行政管理,全国到11世纪就分成若干郡(shire),为国内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设有郡长,负责维持治安、征收税收;每郡分为许多分区,称为百户区(hundred,或译为分区),或在北方某些地方分为小邑或小区。百户区又分为镇或村,这些就相当于后来的教区。较大的设防城镇称之为自治城镇,经常进行贸易。[2]
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随即面临如下几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1.地方势力过于分散。诺曼人势单力孤,在当地仅为少数,中央力量相当薄弱。而地方行政、封建势力与社区自治等力量却错综复杂。就地方行政而言,郡和百户区的公共治理机构——郡法院、百户法院,兼理司法、行政事务,一般都适用地方的习惯法,而且各地的习惯均有差异。诺曼征服导致了盎格鲁—萨克逊法律的中断,而诺曼人并没有自己的立法可以借鉴。①同时,在早期英国习惯法体系下,国王政府既没有控制立法权,也没有完全垄断司法权,这意味着那时英国的法律运行机制——从规则的创制到规则的适用——基本上外在于国家政治权力系统之外。[3]
2.诺曼贵族的威胁及教会的影响。战功显赫的诺曼贵族在和平年代可能成为王权的威胁者,英王必须建立对贵族势力的控制;教会无处不在的影响,在司法管辖权上常常与地方法院如百户区法院发生重叠和冲突。
(二)行政控制体系的相应建立,为普通法的产生、发展奠定基础。
为此,威廉一世及其后继者们需要通过各种措施建立自己的行政控制体系,这从当时对各类法院的治理上表现的尤为鲜明。
1.实行一系列措施以确保皇室地位。英王任命诺曼人为郡和百户区法院的长官[4],令其宣誓效忠皇室,并通过令状制使国王的命令得以自上而下的传达。后来又派遣专员、设立巡回法院审查地方事务,有时甚至由国王亲自出行逐郡视察。这使得地方纠纷得以从底层转移到上层来,由国王直接统治臣民。
2.颁布“英国土地簿”。对于诺曼贵族的治理,尤为重要的举措是威廉一世在1086年颁布的“英国土地簿”(Domesday Book,又称《末日审判书》),即对全国每个土地持有者的财产状况登记造册,规定税赋,并宣称全英国的土地归王室所有[5]。英王通过土地分封制将大部分土地逐次分封给侍从(即国王的佃户),以换取他们的效忠和服务。这种封建式金字塔奠定了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框架。在诺曼人入侵之前的英格兰,农业生产造就了封建经济的基本单位即庄园,庄园的领主对本领区内的案件有司法管辖权[6]。由于诺曼人需要自己的法庭处理贵族之间及贵族与皇室的内部纠纷,于是在郡和百户区法院以外,许多新的封建法庭(feudal courts)应运而生[7]。封建法庭一般只有权处理民事问题,但偶而国王也会授权领主审理刑事案件,他的法庭就成了特许法庭(franchise courts)。领地内的平民大都诉诸于领主法庭(seignorial or lords' courts),级别较低的领主则可以向上诉诸于更高层级的领主,直至英王。由此,一大批法庭和管辖权的网络在英格兰发展起来。
3.划清王权统治下的世俗事务与宗教权力的界限。由于盎格鲁—萨克逊时代,地方法院由主教和伯爵共同审理包括世俗和宗教纠纷在内的所有案件,教会对此颇有不满。威廉一世在征服英格兰之前就答应建立分离的教会法院(ecclesiastical courts),以换取教皇的保佑和支持。威廉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把对“灵魂的治理”从世俗法院转移给教会法院,从此开始了世俗法院与教会法院的分离。通过建立教会法院,威廉一世得以划清了王权统治下的世俗事务与宗教权力的界限。[8]
4.建立“巡回法院”。确保国王权威深入各郡并向一切人开放的措施始于巡回法院(General Eyre)的建立。从巡回法院的工作可见其作为中央集权化的最初阶段的职能,这也是在地方规则混乱的情况下实现法律统一的工具。由国王近臣和教会人员组成的中央政府机构——御前库里亚(Curia Regis)派出巡回法官,以国王名义视察各地。其核心是一系列有关国王利益的问题。法官们最初也适用当地的习惯法,但很快就用他们普遍适用于王国全境的法律取而代之(这种统一的法律,即为英国“普通法”的由来),因为巡回法院的首要任务是强制执行规则,而非对其内容作缜密推敲。巡回法院所提出的其他问题更明显的具有统治的特征,比如特许问题、布匹和酒类市场的问题,或郡长和其他王室官员的行为不端问题等等。由此可以看到,巡回法院对地方行政事务进行的“司法”审查活动,突出表现了普通法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特点,尤其在普通法早期的形成阶段行政与司法活动的结合。[9]
5.保留地方法院的结构和对习惯法的适用。威廉一世保留了地方法院的结构和对习惯法的适用,封建司法通常流行的做法以及用超自然方法进行鉴定(诸如神裁法,格斗,起誓及他人证誓)的古老做法在理论上仍然受到尊重。但在特殊情况下,任何一个能按规定的诉讼格式(forms of action)以言语阐明其案情的人都可援用皇家补救办法。这种情况不久就逐渐消灭了以前的那些做法。中央法院的权威和声望,较为稳定便捷的诉讼程序等等,都成为王室法院在与地方法院竞争的过程中逐渐取胜的因素。但问题也是存在的:巡回法院的审期至少要7年一次,并且法院本身要在全国各地流动,给诉讼带来很大不便。到1215年,按照大宪章的规定,王室法院最终固定在威斯敏斯特宫。[10]
二、普通法势力随着中央集权化和司法分工专业化日益壮大
(一)中央集权化和司法分工专业化促使普通法在英格兰全境成长传播
中央集权意味着早期出现在地方法院并就地解决的大量纠纷,如今转移到王室法院的法官面前。来自民间的诉讼请求通过令状制度从地方移转到中央,并使地方法院处在经常的中央监控之下。
随着中央集权化而来的是司法机构的专业分工化。中央三大王室法院的兴起均可溯源于古老的国王常设机构“御前库里亚”,最初这一组织尚未分化,政治的、财务的、司法的各种事务均由非职业化的人员来处理。随着诉讼案件的增长,日益紧张的工作压力带来了劳动分工的发展——最初王室法院的成员是临时从其他岗位上抽调来的,后来王室司法的工作成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其职业视野和专业知识随之改善。这些人组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群体,适用同一套普通法和同一套诉讼制度[11]。“普通法”就在这里成长并在英格兰全境传播开来。
(二)随着普通法早期最重要的特色制度“令状制”的发展演变,各种案件越来越与中央司法权威发生关联,普通法势力日益壮大
1.“令状制”产生初期。司法管辖权的控制要通过具体制度来完成。普通法早期的最重要的特色制度即令状制,原则上它不过是中央集权化过程中必要的行政管理事务的一部分。令状最初是国王发出的文件和命令。从盎格鲁—萨克逊时代就是重要的行政手段。早期的例子表明,当时的令状仅仅是国王根据原告的请求,命令作恶者(wrong doer)恢复其侵占的原告土地。如果被告拒绝,则由郡长执行。其出现只是为了临时、应急的目的,作为政府的官方文件签发。
2.“令状制”的发展演变。但是随着纠纷的大量发生,对行政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诉讼形式逐渐固定下来,后来,王室法庭利用权利令状展开了与领主法庭争夺司法管辖权的斗争,[12]令状演变成为直接签发给郡长的指令,由他命令被告更正过错,或者到国王的大法官面前说明理由。到爱德华三世时,到威斯敏斯特宫王室法院起诉必须具备某一类型的令状,否则会被驳回起诉,而令状选择错误将导致败诉。[13]
令状的发展不仅突出体现了普通法程序制度先于实体法的特点,也使各种案件越来越与中央司法权威发生关联,为熟悉、参与并尽可能赢得诉讼,当事人必须购买并了解令状(因而律师在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与此同时,随着案件越来越向适用普通法的王室法院倾斜,原有的地方司法与封建性的领主法庭及其所适用的地方习惯法和封建法律,或者被吸收到普通法中,或逐渐萎缩,在1534年,一位普通法法官断言,“令状是整个法律依赖的基础”。②
三、随着法律职业化进程发展,普通法制度最终走向独立,完成了从“治理工具”到“宪政力量”的蜕变
司法随着英国普通法的日益壮大而渐趋发达,从而附着于司法权周围的大批职业群体开始发展起来。王室法院、令状制度在普通法的国家治理过程中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起着重要作用的是法律职业的兴起。
(一)法律职业的兴起和法律教育促使法律职业凝聚力增强、自主性提高,从而赋予了普通法在演进过程中独立精神的张扬
最初,主持王室法院的法官同欧陆一样,主要是国王近臣,具有近现代的“公务员”色彩,而且行政、司法职能混同在一起。但从12世纪中期到14世纪末的一个半世纪时间里,伴随着王室法院的发展,法律诉讼程序的技术化与复杂化,普通法法院日益由专门的法律家,而不再是政治官员来充任法官。同时,普通法的卷帙浩繁以及繁琐的诉讼形式虽然增加了非专业人员了解和进入法律领域的难度,在另一个侧面也促成了律师职业的兴起。现代意义上的“律师”,逐步从社区间受人信任、能言善辩的“陈述士”走向伦敦城普通法法院的固定法庭上,到13世纪末已成为一种封闭性职业,只有经一定方式获得许可的人方可执业,从“陈述士”转为“御用状师”,垄断了所有普通民事诉讼。早在亨利三世时期(1216-1273)就有从律师阶层选拔皇家法院法官的倾向;自14世纪起,虽然没有制定法这样规定,但此做法已经成为确定的习惯,并一直保留至今。实际上,早期的法官是从少数的律师精英即“高级律师”(serjeants at law)中选拔出来,因而法官与高级律师的关系尤为密切。在主要法院集中的地方,法官和律师在生活中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独立自主的法律专家群体,这一群体通过严密组织起来的职业团体和垄断的法律教育,逐渐在英国社会中占据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③
法律职业家的形成离不开法律教育的培养。职业化带来的必然结果除了行业术语和惯例的大量使用以外,另一点就是专门化的职业训练,在增加职业威望的同时为外来者的自由进入增设门槛。大约在14世纪初,法律实务者组成了自己的独立行会,即律师公会(Inns of Court),由资深律师主持并执教。在英格兰,整个中世纪直到19世纪,法律教育都由律师公会垄断,侧重于实践和经验,注重发展职业技术而非学术教育,不仅教授学生实用的法庭技巧,而且致力于通过共同生活塑造学生的品格,培养礼仪教育,为未来政治活动打造社会关系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行业的凝聚力逐渐得到增强。[14]从治理的角度看,这种法律职业化最初是在延伸国王的人身化权威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不过,法官、律师本身并不具有国王的人身权威,而需要依靠法律的权威来维持自身的权威和法律的稳定性,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律师慢慢形成了自身的实践技艺和价值取向——构成法律职业自主性的内在基础。有人这样评价:“13世纪末,英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法律职业……成功的出庭律师与皇家法官一起构成了一个亲密融洽、同质化的共同体。普通法就是这个共同体诸多价值的表现。”[15]
现代研究已经表明,职业专门化与劳动分工是导致意识形态差异的重要原因。[16]英国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的统一性、封闭性进一步促成了普通法内在的自主精神,行业利益与职业道德、职业信念的多重作用赋予了普通法在演进过程中独立精神的张扬。普通法被看作经过漫长时间检验、凝聚了无数智慧的法律理性的化身。在一段广为人知的论述中,爱德华·柯克大法官断言道:
“理性是法律的生命,普通法本身不是别的,就是理性。应该把这种理性理解为通过漫长的研究、考察和经验而实现的一种在技艺上对理性的完善,而非每个人都具有的自然理性,因为没有人生来是有技艺的。这种法律理性是最高的理性……”④
(二)普通法完成从“治理工具”向“宪政力量”的最终蜕变
当代普通法学者简明地概括道:“在普通法制度中,说一些问题的特定解决方式是遵循法律,与说它是理性的,公正的或正义的解决方式,事实上,这两种说法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⑤正是这种与普通法在法律职业、法律教育等方面的特点密切相关的技艺理性,构成了普通法的司法理性的核心。也正是在这样的信念下,普通法法官和律师都深信,任何当权者,无论是国王还是议会、多数派,其行为都必须在立法中的权力不能更改的理性和权利等基本原则范围之内。法律至上的原则就这样发展并流行开来。柯克在1622年与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对话出色的反映了普通法法官这一“法律至上”理念。[17]当詹姆士一世试图自己断案时,柯克援引先例拒绝了国王的要求。他指出,尽管国王和法官一样具有自然理性,但英国的案件却是依据人为理性(artificial reason,又译技艺理性)和法律判决的。柯克诉诸的技艺理性从根本上否定了普通人尤其是主权者在制定法律、理解法律和运用法律的可能。因为技艺理性既非与生俱来,也非人所共有,只有在法学教育中浸淫数年,阅读过无数历史判例的法官们才可能获得这种理性,也因此才能把握法律的内容,并依据其对案件做出合理的裁决。[18]柯克引用Bracton的名言,“国王不应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坚决捍卫普通法的权威。普通法法官对法律至上理念的追求,开始与王权的自由行使发生冲突。
这种冲突在17世纪初还具体表现为英国普通法法院与衡平法院的紧张关系上。16世纪兴起的衡平法院(Court of Chancery,或Court of Equity),不仅在诉讼形式上是对普通法日趋僵硬的程序规则的修正和补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其深远的政治意味。经过玫瑰战争的长期混乱,都铎王朝加强了君主统治,在司法上新设了衡平法院和星宫法院(Court of Star Chamber)。前者处理民事案件,后者专理严重的刑事犯罪。国王意图以此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削弱普通法法院的势力。到17世纪初,王权与普通法之间的紧张关系日趋激化。普通诉讼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柯克在经过与国王的数次激烈辩论后终被解职,后来成为议会中反王派的主要领导人,起草《权利请愿书》,成为反对国王恣意、捍卫普通法权威的代表人物。[19]由柯克张扬的“法律至上”理念一直被带进了现代英国法律思想中,成为英国现代宪政理念中“法治”原则的根本内核。
四、结语——对制度构建及发展的反思
由此我们看到英国普通法早期发展(16世纪以前)呈现的特点。诺曼征服之初,普通法作为英王对分散的地方势力进行统治的工具,在与地方法院、教会法院、封建法院等的竞争与博弈中,以中央强大的权威为后盾,通过巡回法院、令状制度和固定的诉讼形式等手段,逐步实现了王权对英格兰全境的治理与渗透。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王室官员的法官们在审判实践中吸收了地方习惯,去芜取精,以判决的方式逐步发展出了一套适用于英格兰全境的法律,由此而诞生了后来声名远播世界的普通法。
然而极具悖谬性的是,当英王出于人身的有限性而不得不把处理讼争的权威委托给司法职业群体来解决时,他决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从此开创了一项闻名于后世的普通法制度。他也万万不会料到,这项制度后来逐步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和职业传统,拥有了自己的信仰和权威。普通法法官们以“习惯和正义”的保护人自居,唯法律理性至上,坚决反对任何“自由意志和权力滥用”,甚至连国王也不排除在外。国王个人的君主专制统治一次次遭到抵制,普通法已成为不受国王摆布的独立力量。直至16世纪,普通法及其职业群体,从最初作为延伸和拓展国王的人身化权威的工具,摇身一变,成为约束国王恣意权力的政治力量,从而发展成为具有宪政色彩的法治环节。
当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回望历史的时候,尽管可以出于便捷把握知识的考虑,对普通法的历史加以条理化的描述和分析,然而我们必须清楚,许多令后人赞叹不已的杰作,当时也许仅仅是无意识,甚至应急之作的产物。如同从普通法早期的历史中所看到的,事物发展的方向可能与其初衷大相径庭。由此,制度一旦诞生便具有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生命力,在漫长的演进中,所谓附着于其上的职业利益、行业理念和政治影响,最终都归因于制度的构建者——以其有意无意的行动构筑并生活于其中的活生生的人,正是他们,塑造并推动着制度变迁的轨迹。
注释:
①当时罗马法还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1135年左右,意大利人才发现《学说汇纂》的手抄本。参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②Baker,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Common Law[M].p67.转引自李猛.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M].韦伯:法律与价值[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02页。
③Baker,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Common Law[M].p67.转引自李猛.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M].韦伯:法律与价值[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05页。
④译文见李猛前注文,页169—170,英文转引自Sir Edward Coke,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M],I,p97b.
⑤转引自A.W.Simpson,The Common Lawand Legal History[M],in Oxford Esasys in Jurisprudence(Oxford:Clarenden,1973),p79.
标签:普通法论文; 法律论文; 英格兰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时间悖论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法官职业道德论文; 巡回法庭论文; 法官论文; 律师论文; 王权论文; 法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