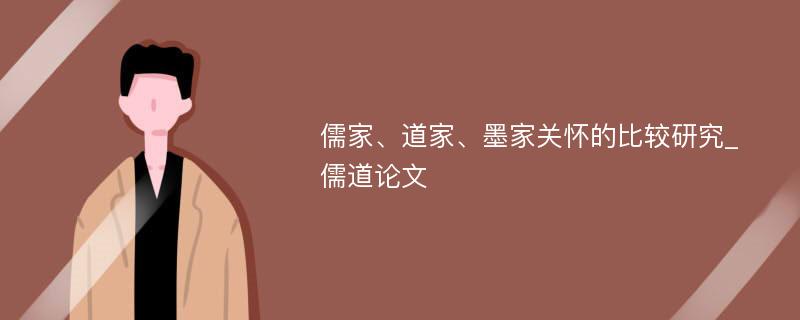
儒道墨人的关怀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春秋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谓“礼崩乐坏”,指的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倒台,更重要的是指人的价值观念崩溃、精神流离失所,而新的价值体系又还不曾产生。所以,当时真是所谓“天崩”、“地解”一时交聚。也许正是这一深重的灾难,反倒引发了当时知识分子要为深远的思考。其思考的结果,由此奠定了往后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也许是当时的社会灾难主要显发为人的危机,故而中国最早的思想流派——儒、道、墨三家全都围绕人的问题展开,这就形成了所谓共同的人的关怀。但是,由于这三家的创始人各自有着不同的社会出身与自我期许,因而其对人的关怀也各有侧重。这样,各家之间必然交光互射,一时有“儒道互绌”、“杨墨之辩”以及“儒墨之是非”等争论。就在其“绌”与“辩”的过程中,各家不仅相互了解,也相互借鉴与相互吸取。所以,“绌”与“辩”,对各家来说,也是一个使自身完善并走向成熟的过程。等到《孟》、《庄》问世时,其思想便已经吸取、凝聚了前人“绌”、“辩”的成果,故而其间表现为相对的沉默;而墨家却在三家的角逐中,宣告“中绝”了。这样,孟、庄便成了后世思想家的基本出发点,而儒道互补也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旋律。但是,当儒道墨三足鼎立让位于儒道二元互补时,也就预定了中国文化以后发展的某种不平衡。
《易传》说:“原始反终”。“原始”未必就一定是“终”,但反归“原始”,反刍儒道墨三家对人的关怀,对于我们新的人文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关怀的不同视域与侧重
三家中最早形成思想流派的是儒家。道家的老子虽年长于孔子,其思想成熟也比孔子为早,但由于其隐世的趣向,故其对社会的影响比儒家为晚。
孔子出生在周文化保持最完好的鲁国,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故可以说是饱受周礼文化的熏陶。孔子对“礼崩乐坏”的感受十分强烈,当景公问政时,他即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对。这说明,在孔子看来,“君不君,臣不臣”即“人而不仁”的问题,既是“礼崩乐坏”的表现,同时也是其根源。对于“人而不仁”的问题,孔子诉之于个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同上)由于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人伦关系中,故以仁为核心的这种人伦关怀便不仅是政治的、文化的,而且确实是普天之下而遍及一切人的。孔子由此上溯三代,详细考察其礼之沿革与损益,这就形成了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道德关怀取向。
老子作为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汉书·艺文志》),对“君不君,臣不臣”的现象见得多了。在他看来,所谓“君不君,臣不臣”,与其说是由于“人而不仁”,不如说正是礼乐教化的产物,所以有“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道德经》第十八章)以及“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同上,第三十八章)的批判。老子认为,正像物之“各复归其根”一样,每个人都应当“复归于朴”,复归于生命的本然状态。所以,他对“小国寡民”以及“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向往之至,而对周之礼乐、孔子之仁爱,均持否定态度。显然,儒道两家的共同出发点是从个体出发,但是,是寻找人的生命之本然,还是探寻人之社会人伦的根本依据,是儒道两家在人的关怀上的根本分歧。
正当儒道两家因“道不同,不相为谋”时,出身于工匠、并曾“习儒者之业”的墨子,以比儒家更激进的姿态,登上了整饬世道人心的论坛。在墨子看来,儒家的仁爱之说其始也“泛爱”,其终也“亲亲”,故墨子以“兼爱”——对所有的人一无差别的爱为宗旨,发起了对儒家的批判,一时与儒并列为“显学”。但是,由于墨子的“兼爱”一经向社会落实,也要以个体为现实始点。因而在其“兼爱”落实为“兼相爱”的同时,“交相利”便成为必要的补充与保证;又由于“利从爱生”,故即使为了个体之利,也必须首先予人以爱。所以,兼爱交利之说便被墨子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准则推向了整个社会。在墨子看来,只要人与人能相施以爱,那么,其间也必然会互报以惠,这样,人与人之间便不仅是“亲亲”,而是互爱互惠,而整个天下也就由此而成为相爱互惠的天下了。显然,如果说墨家是以显明的群体关怀来冲击儒家的,那么,它与将关怀视域牢牢限定在个体范围内的道家便构成了一种截然对反的关系。
让我们再看看这三家人的关怀的不同侧重。
老子对人的关注以个体为范围。他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第十三章)这说明,老子之患虽然在于“有身”,但其之所以患,却在于心,是心对身之患。老子虽以有身为患,却并不是要弃身而独立,而是要达到身心一体,与世无伤,这就是婴儿状态。而这又主要是通过息心来实现的,所以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同上,第五十五章)值得注意的是,在《道德经》中,这种对婴儿状态的向往与赞美随处可见,如“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同上,第十章)“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道德经》第二十章)“为天下谿,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同上,第二十八章)甚至,圣人之所以为圣,也就在于保持了婴儿状态,故有“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同上,第四十九章)那么,到底是婴儿的那一方面引起了老子如此强烈的兴趣,从而将婴儿状态界定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呢?应当说是婴儿的无知无识、无思无为,一切发乎本性,显乎自然而又与世无伤,故“蜂虿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同上,第五十五章)显然,老子对个体的关注是要使个体达到既隐世、又存世,全性葆真而又不为世所伤的身心一体状态,而这种状态又是通过息心(有为)以归身(自然无为)来达到的。
在从个体出发这一点上,孔子与老子并无不同。但是,作为周文化的继承者,“礼崩乐坏”的现实不能不使孔子痛心疾首,故在“摄礼归仁”之后,“人而不仁”的问题便不能不成为他的头等关怀。对孔子来说,“仁”虽落脚于个体,却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而“仁”对于人的普遍性,又正是群体得以认同的基础。所以,他一面周游列国,试图通过政权以推行教化,同时又广收弟子,以讲学的方式宣传其思想。在讲学授徒中,他又言传身教,以孝弟的外向扩充与忠恕的内向反省,互补互证,以使人达到仁之自觉。显然,无论是孔子为了从政的游说还是言传身教的讲学,都是以个体为出发点,而以天下群体的普遍认同为指归的。因此,孔子仁的学说虽然立足于个体之孝弟忠恕,其目的却是“天下归仁”的群体关怀。
虽然老子与孔子都从个体出发形成了不同的关怀面向,但这种不同却又大致停留在人的同一层面上,这就主要是人的精神层面。老子对个体之“有身”的忧患源于心,且所谓“不螫”、“不据”与“不搏”,也都反映了其心对身的冀望。这样,作为社会动物,人的生存基础一面便恰好成了空缺,而这正是由墨家来弥补的。
在当时,墨家看到最多的社会现象是“国与国之相攻,家与家之相篡,人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兼爱》中),表现在人与人之间,也就是“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贼,诈必欺愚。”(同上)墨家的十大救世主张,正是为了杜绝或根除这些现象而提出的。这也是由其群体关怀所决定的。但是,如果稍微品味一下墨家的救世主张,便可发现其“节用”、“节葬”、“非乐”、“非命”,是直接从群体生存角度提出的,而“尚贤”、“尚同”、“兼爱”、“非攻”,又是从社会下层的生存危机中引申出来的。墨子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非乐》上),所谓“民之巨患”,实际上也就是墨子的心头大患,其所以要“形劳天下”、“自苦为极”,就是为了解决社会下层的生存问题;而墨家之所以号召兼相爱交相利,也就是试图以衣食之利为纽带,建立起一个相爱互惠的社会群体。
老子对人的关怀显然是以个体之身心统一为其焦点,而以全性葆真为其祈向。墨家正好相反,其“兼爱”虽要落实于个体,但一当落实于个体,即表现为“兼相爱”,进而通过兼相爱、交相利,来解决天下群体之基本的生存问题。儒家则一方面因其群体主义指向而与道家相悖,同时又以其人伦道德的立足点而与墨家相对。但是,在侧重于个体之精神上,儒道有相通处;而在群体主义的指向上,儒墨又相互一致。正因为三家既相对反又相联结,因而在其宗旨形成之后,相互批判与相互借鉴便成了它们的共同任务。
二、三足鼎立与彼此消长
儒道墨的创始人创立思想时,虽然有着不同的关怀视域与侧重,但彼此基本上都是按各自对“礼崩乐坏”的思考为出发点进行创造的。可是,当三家宗旨相继确立之后,相互的思想接触便在所难免。这样,其间的相互批判与相互吸取也就同时开始了。
首先在思想上遭遇的便是儒道两家。孔子曾入周见老子,老子对孔子的救世主张进行了一番嘲讽性的批判:“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史记·孔子世家》也有大致相近的记载。虽然前人发现这一说法可能“取材于道家传说”(注: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但孔子见老子史册多载,当确有其事;即使这一说法源自道家,起码也可以视为道家对儒家的基本看法。因此,这一批评在把握儒道之分歧上,还不失其意义。老子指出孔子的主张是“无益于子之身”,也许对孔子有警示的作用。《论语》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以及大量对“己”的强调,可能就既有对老子贵己思想的吸取,也有对老子批判的回答之意。
这一从对“身”的忧患到对“己”的强调,再次显示了儒道两家个体观念的分歧。道家更关心个体精神的自然性,故从是否有益于身的角度来权衡儒家的救世主张;而儒家则更关心个体精神的人伦普遍性,所以其“为仁由己”表现的恰恰是立足于个体之普遍本质基础上的群体关怀。在上述儒道第一次思想交流中,儒家的救世热情确实受到了道家“为己”的警示,而孔子之所以从为己、成己的角度立仁,也许就与其对道家思想的借鉴有关。
与儒家“修己安人”之道相比,道家修己的目的不是外向的群体关怀,而是自我的身心一体,从而于乱世中全性葆真。所以,它无须像儒家那样上说下教、周游列国,而是存世而隐世。但是,当墨家以比儒家更激进的态度倡言兼爱天下时,本来就只是隐世而非弃世的道家,便不能不“显”于世了,“杨墨之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杨朱是介于老、庄之间的道家代表人物,当墨子兼爱之言“盈天下”时,他再也无法保持道家的冷静与超然了。不过,由于道墨之间非但“道不同”,甚至连儒道之间共同的“己”都找不到,这样,杨朱便无法对墨家直下针砭,只能抓住凡人所不能无的“我”来做文章,而所谓“为我”,就是杨朱既遵道家之意又批墨子兼爱之失的焦点。这种“为我”表达出来,就是孟子的“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尽心》上),或者如韩非子所概括的“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显学》)。
既然“为我”是对“兼爱”而发,那就有必要对墨子的“兼爱”作一简析。在墨子思想中,兼爱作为其根本宗旨,是真正具有形上意味的概念,其提出主要是针对儒家仁爱说的“孝悌”、“亲亲”而言的,其基本涵义即以全然无我之心兼爱天下之人。所以,无我既是墨子兼爱的基本前提与背景预设,同时也是其思想核心。即使如后墨所辩解的“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大取》),以证明墨家是有我的,但是,其“伦列之爱己,爱人也”(《大取》),恰恰证明了其爱人爱己的无私无我性。所以,兼爱之成为爱,正是以彻底的无我为前提的,也是其彻底无我的表现。正是这种彻底的无我,才与杨朱的“为我”构成了对反。
平心而论,从老子到杨朱虽然都重视“贵己”,却并非自私;杨朱的“为我”一说,也并非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因为在道家看来,“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道德经》第十三章)像墨子那样全然无我地兼爱天下,并还要推行于群体大众之间,简直是荒谬至极,其结果只能是《庄子·天下》所说的“反天下之心”。所以,杨朱的“为我”,实际上只是以这种“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极端方式反讽墨家的自我缺失之病。
真正能够在形上与形下、理论与实践两个向度给墨家以致命打击的是儒家,但这恰恰不是通过批判,而是通过吸取,通过对“儒墨之是非”的消化来实现的。
还在“杨墨之辩”以前,“儒墨之是非”就已经产生了。因为墨家的产生本身就是“儒墨之是非”的肇始,甚至可以说,墨家正是顶着这一“是非”而成长为学派的。如前所述,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一方面“摄礼归仁”,以仁为人之为人的依据,进而又从为仁之内省与扩充的两路并进,以达到成己成人的目的。对于孔子的这一主张来说,其优点在于兼顾了形上与形下、个体与群体两个方面。但是,它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这就是为仁之途必须以我为始,所谓“能取近譬”的“仁之方”,正是其以我为出发点的反证。这样,虽然它强调“泛爱众”、“立己立人”、“达己达仁”,而事实上却有可能仅仅流于自爱或限于“亲亲”一步。显然,这种对群体关怀的匮乏与薄弱,正是墨子由“习儒者之业”而“背周道”、倡“兼爱”的动因。
墨子的“兼爱”首先便是针对儒家的“亲亲”之爱提出的。对“兼爱”来说,无我与其说是它的预设背景,不如说就是它的实质和实现前提,因为只有彻底的无我,才能真正地兼爱;否则,一当有我,“兼”就无法兑现了。但是,“兼爱”的关怀面向却使它必然要向社会落实,必然要依靠个体作为其实现的主体。这样,一当兼爱落实于个体,其“兼”的性质同时便失去了,因为不仅其主体是有我的,且其客体也不再具有“兼”的性质而只能是一个个体,所以,它只能落实、表现为“爱人若爱其身”的“兼相爱”。但是,由于“兼相爱”只能实现于人与人之间,且由“兼爱”到“兼相爱”的这一落实,不仅失去了“兼”的周遍性,且还不能回答“我何以要爱人”以及为何要“爱人若爱其身”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兼爱”既已入世,就不能不受社会现实的制约与牵引,所以,它不得不以其原初的形上之爱从属于现实的形下之利,进而由“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而以爱求利了。这样,“兼相爱”就变成了“兼相爱交相利”,而功利主义也就成为其兼爱交利之说的真正归宿了。
从“兼爱”到功利主义,这既是墨子兼爱情怀的社会落实,也是其爱之浓度的一步步稀释,当其最后以功利作为爱之动力时,我们固然很难说这还是一种真正的爱,但却无法怀疑其群体关怀的落实指向性。所以,墨家正是通过爱与利的并举与前后夹持,凸显并实现着其比儒家更强烈的群体主义关怀。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儒家。由于儒家的主体地位,它始终处于道墨两家的夹击状态,这种状况决定它不仅要回答来自道墨两方的责难,同时也要双向地吸取借鉴。首先,面对道家“贵己”、“为己”的警示,孔门弟子曾子强化了其本来就有的“为仁由己”的内省方向,至其弟子子思,遂有《中庸》之作。子思的使命首先在于吸取并回应道家的批评。从儒道互鉴的角度看,《中庸》的重要在于提出了“中”、“中和”与“诚”等概念:“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而“诚”,则是由“中”致“和”的“人之道”,故“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在这里,“诚”不仅使人“聪明睿知”、“宽裕温厚”、“发强刚毅”、“斋壮中正”,而且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总之,道家“贵己”所能达到的一切,儒家之“诚”全然具有。显然,《中庸》既有对道家批评的借鉴一面,同时还有对道家的蕴含与超越之意。
与《中庸》前后形成的《大学》,则发扬了儒家的另一面,这就是以群体关怀为特征的内圣外王之道。《大学》过去被看作是秦汉儒家的作品,现在学界将其考定于曾、孟之间(注:邹化政:《先秦儒家思想新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8页。又见李景林:《孔孟心性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10月,第77页。)。笔者基本同意这一看法,认为它可能是晚于子思的曾子后学所为(注:请参阅郭沂:《“大学”新论——兼评新儒家的有关论述》,载于《新儒家评论》第二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关于《大学》之晚于《中庸》及其对《中庸》思想的发挥,该文有详细的考论。)。《大学》以“明明德”、“亲民”、“止至善”的三纲为起,从个体之格致诚正,层层推至治国平天下。就其实质而言,则主要发挥《中庸》的“诚意”一意,故明儒王阳明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注:《大学古本序》,《王阳明全集》卷七。)至于其“一家仁,一国兴仁;……一人贪戾,一国作乱”的逻辑,显然是对孔子“近譬”之方的直接运用。有趣的是,《大学》以“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作结论,并认为“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似乎就是直接针对墨家功利主义的群体关怀而言的。
这样,道、墨对儒家从两个不同方向的批判及其所长,便一齐被儒家借鉴、吸收并且扬弃了。从修己之内圣,到平天下的群体关怀,也就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一体化了。这当然是由其主体的地位、致中和的取向以及善于取长补短的为学方法决定的。但是,由于儒家通过“以义为利”来实现其群体关怀,故墨家功利主义的群体取向便被儒家抛弃了。而这一抛弃,便使它永远地失去了来自功利的动力。
三、回溯性的前赡
儒道墨三家,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绌”、“辩”与“是非”之争,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其他两家的长处,也都一定程度上发展、完善了自身。剩下的,便是三家的最后角逐了。
首先发难的是儒家。孟子之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滕文公》下)但是,在孟子看来,“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同上)故“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而“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词”,正是孟子自我设定的历史使命。
在孟子看来,杨朱的“为我”,是唯以“自适”为务而无有群体关怀,所以是“无君”;而墨子却又因为“兼爱”天下,无有人我之别,从而陷入“无父”。两者看似相反,但作为无人伦的禽兽之道却是一致的。孟子又说: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尽心》上)|孟子的这一划分,不仅体现了儒家对杨儒两家的双向借鉴,而且也显现了其双向批判的锋芒。孟子立足于儒家仁心善性之“权”基础上的“执中”。正因为以“权”执中,故其能立足于人之为人的性,“养气”、“集义”两路并举,“仁政”、“民本”双面竞开,从而使己“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达道”(《滕文公》下);对人则“孝弟”、“推恩”而“达于四海”。这样,整个人伦世界,从个体之安身立命到群体之政教风化,就非儒家莫属了。
就在孟子“劈杨墨”的同时,道家的庄子也展开了其“剽剥儒墨”以“适己”的活动。在庄子看来,“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这就是说,所谓儒墨之不同主张,不过是小成荣华之言;其所以有是非,是因为他们都“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而从道的角度看,则既无所谓人我之别,也无所谓是非之争,这就是“道通为一”。另一方面庄子又认为,“骈于辩者,纍瓦结绳竄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放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骈拇》)显然,不仅“儒墨之是非”是庄子所要消解的,就是“杨墨之辩”也同样是嘲笑的对象。
庄子本人的旨趣,是通过“心斋”、“坐忘”,由“有待”至于“无待”,从而“均是非”、“齐物我”、“泯生死”、“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大宗师》),可以“自适”于“无何有之乡”,陶醉于“广漠之野”。当然,庄子是通过“寓言”来表达所有这一切的,但透过其种种意向,不难发现庄子确实为个体勾画了一条泯是非、去成见的存世自适的解脱之道。如果说立足于道德善性以仁政天下的人伦关怀已非儒家莫属,那么,对于个体之如何存世自适、摆脱烦恼而一任本真之性,道家也就当仁不让了。
这样,在这个三角角逐中,真正失败的便只是墨家了。其“贱人”的出身、功利主义的群体关怀与形上思辨的先天不足,本来就使其在儒道墨三家中居于劣势;在儒道两家的左右夹击面前,又缺乏孟、庄那样能力挽狂澜的巨擘。所以,它只能悲壮地退出整饬人文的论坛,而以墨侠的形式回归于作为其原初产地的社会下层。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每当群体之生存遇到危机,它要么借宗教的形式(如原始道教),要么以农民起义的形式发出呼喊,以拨正儒道两家对人之关怀的偏颇,从而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建构起到一种制衡作用;至于其立足功利的群体关怀却真正地被历史遗忘了。这固然是墨家的失败,但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历史性失败。
在汉初,黄老之学作为一种“与民休息”的政治哲学曾风行一时,但由于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注:马司谈:《论六家之要旨》。),故很难直接将其归类于先秦道家。而儒家由于立足于善性,起始于成已,归结于成人而王天下,故到了汉武帝时代终于上升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不过,作为官方哲学,毕竟要以群体关怀为重心,而儒家推己及人的群体之道却不仅使其经典变得越来越烦琐,而且由于谶纬的夹杂也使其越来越庸俗化、迷信化。这就是经学的衰微。其后,玄学家引老庄入儒,倡清谈之风,但又因其行为乖张,冲决人伦而为世所弃。由于其时佛教已开始盛行,故儒道一起卷入了三教论争的旋涡中。
直到中唐,韩愈始以排佛发出了儒学再振的呼声,故自北宋起,儒学再次成为思想领地的主体。但是,由于有儒与佛的华夷之辩为背景,因而儒家事实上便是通过援道人儒以再振的。作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本身即有很浓的仙风道气,其所谓“光风霁月”的胸次,实际上正是道家人格的儒家表现。而作为理学另一开创者的张载,其为儒家的“造道之言”又更多地源自道家(注:请参阅李申:《气质之性原于道教说》,载于《道家文化研究》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所以,在整个宋明理学中,“敬畏”与“洒落”这两种风气(注:请参阅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正是儒道两家不同为人风格渗入理学内部的表现。直到理学的最后一个高峰王阳明,其为学宗旨仍然是“就云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遗风,求孔颜之真趣;洒然而乐,超然而游。”(注:《别三子序》、《王阳明全集》卷七。)以道家之“自适”与佛家之“妙智”充实儒家的内圣修己之学,这就是宋明儒学崛起的“秘密”,也是从宋至明整个理学发展的主施律。
但是,这种以“自适”为宗旨的儒学必定由淡化渐次失去其群体关怀。虽然理学家还在高唱修齐治平,但却终生不出“诚意”一关;虽然他们也都入仕,但却以野鹤闲云以相高。在他们看来,只要一关心政事,便流入法家或俗儒。(注:请参阅李泽厚:《经世观念随笔》,载于《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7页。)这样,儒家的群体关怀便只能萎缩于现实生活,而“万物一体之仁”、“浑然与物同体”等境界的显扬,正是其群体关怀萎缩于现实生活的一种补偿。更为重要的是,生存必定是人的第一需求,而群体之间的利益纽带被理学家以“存天理去人欲”斥而不谈,人的这种生存、利益之欲便必然要披上“天理”的外衣肆意横行,从而又反回来更有力地摧毁、腐蚀着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请看青年王阳明对这种现象的揭露:“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汑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敬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注:《陈言边务疏》、《王阳明全集》卷九。)当上下左右都挟天理之名以谋其私利之实时,其群体关怀与群体精神便是真正的瓦解了,一如孙中山所谓的“一盘散沙”。在这种状况下,一败于满清,再败于英,已经成为以儒学为官方哲学的明清统治者的必然结局了。
如果说在先秦,由于有墨家的反衬,故儒家还能本仁心善性以展修齐治平的期望,那么,到了宋明,在墨家群体关怀已经中绝的情况下,儒家便只能以佛道为参照坐标而津津于“自家身心”了。这样,它的意向也就必然日益内缩,最后只能集中于“身心日用之间”而无所谓天下苍生之念了。这可能又是宋明儒家意向内缩的外在因缘。
在近代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不断地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从兵革利器到君主宪政乃至整个文化,都在大量的引进,却似乎于中国本来具有的基于生存功利的墨家群体关怀注意不够。所以,虽有所谓先进的经验,却经不住“一盘散沙”的侵蚀,结果便使各种学习不得不常常陷于流产,以至于辛亥革命的参加者熊十力在目睹“党人竞权争利”的情况下,不得不悲愤地抱怨:“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注:徐复观:《有关熊十力先生的片鳞只爪》,《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348页。)实际上,这种现实对道德的扭曲,功利对道义的消解,才是真正的普遍性,这也是近代中国各种发自道德善性以赶超世界先进的学习运动不断流产的真正原因。
在当代的儒学研究中,人们似乎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难题。如新儒家的精神领袖牟宗三所说:“以往两千年来,从儒家的传统看外王,外王是内圣的直接延长。……修身齐家在这个时代,不能直接推出治国平天下;不能由内圣直接推出外王,这就显出现代化的意义。”(注: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56-357页。)所谓“现代化的意义”,自然包含着对这一难题的自觉,但新儒家为儒学所规定的出路却是变“直通”为“曲通”,即通过道德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知性主体”,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从而实现其群体关怀。应当承认,这一道德理性的优先性确实是儒家自古及今的一贯立场,但从实现群体关怀的角度看,仅仅将“直通”变为“曲通”,却难免有翻山引水之嫌。反过来看,科学、民主等等群体性的设施也不一定只有以道德理性为前提才能建立起来,两千多年前的墨家并没有多么高深的形上道德,不同样有着明显的群体关怀与强烈的群体精神以及与之相应的科学与逻辑思想吗?
所以,在本世纪即将告结之际,反思中国历史上儒道墨三家人的关怀,反刍其相互批判、相互借鉴的历史,对墨家的中绝与思想的废弃,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惋惜之情。固然,其学派的中绝在当时确有其必然性,但其思想的废弃却只能是后人的责任。新世纪的人文重建当然需要儒道两家丰富的形上思辨与高明的个体境界,但比照现实,我们更需要虽不怎么高明、但却确实能落实于群体层面,为平民生存计虑的墨家功利原则,因为只有这种基于平民生存利益的群体原则与群体关怀,才是现实、普遍的群体性。因此,如何立足于人的生存向度、基于功利原则来组建我们民族的群体精神,是我们新的人文建设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本文这一人的关怀之比较的结论。
标签:儒道论文; 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墨家论文; 道家论文; 王阳明全集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道德经论文; 大学论文; 墨子论文; 中庸论文;
